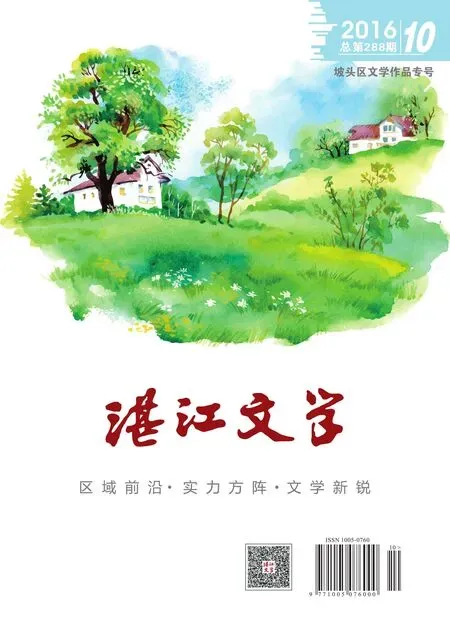调丰三章
※ 卢凌日
调丰三章
※ 卢凌日
从湛江市区沿湛徐高速南走,约20分钟的车程,到了遂溪县岭北镇,由这里掉头东向,再沿仲建公路开出8公里,一个久负盛名的古村落,因为它的古老,因为它的厚重,因为它的人文气息,调丰的名字便会在你的耳际响起。“调丰”,一个昭示美好吉祥的名字——风调雨顺,丰饶富足,数千年来浮动在农耕社会的理想与愿望,有什么可以与之比拟或替代?带着惊异,带着期待,放眼四望,你已经被无边的青翠簇拥,蔗林如海,稻浪千重,花果飘香,满目田园风光。
调丰为古越语地名,意思即大片土地。对于农民,土地就是财富,拥有大片土地就意味着拥有金山银山。这里,东西丘陵环抱,赤土如膏;南面田畴平展,阡陌纵横。银溪清澈见底,环绕东流;湖塘明净如镜,点缀映照。肥沃的土地,丰沛的水源,注定了它是个盛产米粮、蔗糖、果菜的富庶之乡。然而,虽然有了上天优越的恩赐,如果没有结满厚茧双手的劳动创造,神马都是浮云。“调丰”,包含着上天的恩惠,也包含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汗水。
古云,衣食足则知荣辱,衣食也是文化的媬姆。调丰是米粮丰盛的调丰,也是人文丰赡的调丰。聚族而居的调丰程氏,上数其先贤,稍有文化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存孤全义的程婴,倾盖论交的程本,师范千古的程頣……一出《赵氏孤儿》,一句“程门立雪”,已是传统剧目和词书中抹不掉的经典。就是当你打开《程氏调丰村族谱》时,也会惊讶其始祖的不凡。据族谱记载:始祖程浪斋为宋代进士、任职雷州知军事、诰封奉直大夫。他是在宋嘉定年间举族从滨海的东岸迁来定居的。天时地利,钟灵毓秀,一方福土,看来他也是个很有发展眼光的开拓者。有道是习俗移志,安久移质,族得贤者而成风气,犹如蓬草长在麻园中,你不用去扶它,它也会笔直地生长。始祖程浪斋带着中原的书香传统,家传代续,形成了一族淳朴的村风民风,也形成了一村书声琅琅的耕读气象。曾经的一门三代四进士,是多么罕见的光荣纪录。人文的流注,人文的积淀,流传至今,文物古迹就有12处之多,一个小村落,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一、古官道
人逐水草而居,路逐足迹而延。这里优越的农耕条件,引来了连绵不断的聚居村落。人聚了,自自然然,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也走出来了。
车辚辚,马笃笃,大路通向中原帝都名府、往来朝廷政令文书、交流南北货源物产、迎来行商脚夫,送往求名学子……走着走着,走出了一条闹哄哄的官道,文明便穿越梅关,从这里往南伸延,城月、客路、雷州、龙门、英利、徐闻。连横亘的海峡也隔不断,一直跨海通向三亚的天崖海角,走出了一条满载文化的斑斓彩带,
上苍是否特别垂注调丰这个节点?为什么官道穿越过那么多鄉镇,偏偏在这里留下这么多名人的足迹?古官道设在这里的茅亭驿站便是南来北往的钦差、官员,文人、儒士,行商、学子的一个必经落足点。宋代贬谪雷州的“十贤”,几乎一个个都在这里停留过。在调丰北面的石坡上,现在还遗留下一段宽1.6米、深60厘米的车辙。这是雷州人使用的大轱辘高脚牛车,它包镶着铁皮的车轮,在玄武岩石坡上咿咿欸欸地辗碾,春夏秋冬,雨露风霜,日出日落,一遍遍一回回的,一条深沟便碾出来了。这不是天工,却是天意,是上天有意在这里铺设了一段玄武岩石坡,让大轱辘牛车铁轮啃下了一段历史奇迹。
古官道,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湮没了踪迹。假如没有这段车辙的印记,古官道已是无从考证了。悠悠千载,古官道阅尽了诡谲多变的历史风云,阅尽了酸甜苦辣的人间况味,诉说着它的沧桑与古老。
我想,古官道已不仅仅是古迹了,它会让人思索,它是多么的倔强和多么的固执。据说,在日夜不停的辗碾中,辙沟越碾越深,直到搁碍了牛车主轴的运转,它也不让更弦易辙,仍然固执着依旧的轨迹,只不过它让人们填上碎石,垫高了车轮妨碍不着主轴,待碾粉了再来一次轮回。这是多么可怕的重复,多么可怕的顽固,但它又是让人惊讶,它那份安静与坚强,不管春风秋雨,不管酷暑寒霜,它依然冷静的躺着,任你轻轻重重的碾压,没有叹息,没有呻吟,也没有期待,还有意让牛蹄敲击着它而发出清脆的声响来愉悦车把式的心情,驱走车把式的疲劳。
古官道,长满了苍凉的青苔,原始,简单。或许青苔无心,但人却有意,作为古迹,古官道的现代意义,是否就在于让人体验着顽固偏执与落后的关系?
二、东坡井
也许,这口井就是为了一个名字而来。它在岁月的流逝中等待,在风雨的明晦中祈盼。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一个阳春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向朝廷呈上一份《湖州谢上表》,这本来是例行公事,形式地略叙自己的愆过,再颂皇恩之浩荡。是有点怨气吧,他在后面夹上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在一些嗅觉灵敏的新政人物中,“新进”剌痛了他们,“乌台诗案”便缘此而起。幸运的是,认为必死而给弟弟写了诀别诗的他,却被他“天下名士”的光环挡了一刀,只降职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当个团练副使。自此之后,苏东坡便一路仕途颠簸,流放式地知登州(今山东蓬莱)赴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任宁远军节度副使,再因“元祐党人”而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但这里还不是他厄运的终点,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再蒙“讥斥先朝”之罪,责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四月十九日,苏东坡从惠州乘船经西江来到了调丰茅亭驿站。苏东坡的不幸,却成全了这口井的大幸,它等待的一天终于来了。高兴、激动,一股清泉便笑逐颜开地迎接这位文魁词宗的“天下名士”。
这是一口神奇的古井。曾经有一个神话般的传说:每年清明时节与腊月卯晨,人们就会听到井底有悦耳的蛙声鸣叫。清澈见底的泉水,却从来没有人看到这只鸣叫青蛙的出没。更奇特的是,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雨季旱季,它的泉水总是溢出井面而汩汩地流出井沿,即使现在地下水位普遍降低,它还是依然如故。是不是因为那时苏东坡的到来,这口井激动得亢奋而“热血沸腾”?旅途颠簸疲惫的苏东坡,只须俯身一掬,就可以舀到那清涼甘冽的泉水,解渴、涤洗,南国的暑热,一腔的委屈,满腹的惆怅,为之一消而尽。也许是一个承诺,它坚守着至今。
苏东坡不仅仅拥有文名,他也是一个心中装载着人民的好官吏。所到之处,他都想着为当地人民造福。即使只做了五天的登州太守,他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形成了两份很有份量的调查报告——《乞罢登州榷盐状》、《登州招还议水军状》上奏朝廷。为登州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地人民为了寄托对苏东坡的感激和缅怀之情,专门建起一座纪念的祠堂——“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只在短短的五天呀!
这一回,这口井邂逅的苏东坡,他已是一个披罪之身。他没有了发言权,他没有了施为的印把子,他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了。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没有留连的余地,没有吟咏的空间,他要向一个云水苍茫的海岛进发。但这口井却很荣幸,群众为了纪念苏东坡而把一个光辉的名字留下给它,它和“苏堤”一样,有了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号。
三、景兰阁
“景接三山,阅千秋古色;兰沁一阁,传百代文光”,这是景兰阁重修后的大门楹联。景兰阁,从茅亭驿站转过身段,在向往文明的行进中,沿着琅琅书声的起落,风雨明晦,晨昏相继,不经意,一个颇具规模的书院便渐行渐近。
调丰村二世祖程雷发,一个与文天祥同榜的南宋宝祐年间丙辰科进士,曽被宋理宗封为建极学士。他也许不满于昏黑的官场,无意于乱世仕途;他也许景慕先祖的高风,追随“程门立雪”的脚印,他不去当官作吏而在茅亭驿站集八方学子开馆讲学。在一个文化进程较为落后的雷州半岛,这无疑是个颇得人心的善举。立志于传道授业的调丰二世祖,毕生致力,数十年如一日,春风桃李,诗、书、礼、乐,便在吟咏声中,漫化成了景观映日,龙光射斗;兰香覆地,陈榻重铺的一团氤氲。
越是处于文化的荒野,人们就越渴望文化足迹的降临。清嘉庆年间,一名誉满京师的硕儒走了进来——他就是参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编校工作的陈昌齐。陈昌齐的官不大而学问大。他“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无所不精”。当时的硕学鸿儒纪昀、戴震、钱大昕等对他也刮目相看,交游甚笃。这一年他走进调丰,是他上任温州兵备道北上顺道而拐进来探望他的侄女。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知书重贤的调丰父老没有错过,恭备了文房四宝,请陈昌齐写下了笔力苍劲的“景兰阁”三字。
景兰阁在书声中成长,在书声中壮大。仰望着这一片灿烂的云霞,雷州半岛的儒生学子趋之若鹜。到了清道光三十年间(公元1821年),求学人数已多达800人,一座两进院的景兰阁显得挤拥了。换一个意思,“有容乃大”,雷州各地学子、绅士及商贾便纷纷解囊,为景兰阁建起了两座规模一样的分院,当地群众管叫它“小书房”。
景兰阁,数百年连绵不断的书声,数百年的传承赓续,它吸纳着、传播着,中原文化便从这里升腾、弥漫、覆盖。据不完全统计,从宋至清,这里走出了8名进士,20多位各等贡生、廪生,雷州半岛有30名进士曾经在这里求学、讲学、切磋学问。虽然,这比起文化发达地区,是一个非常寒酸的小数目,但在宋明还作为贬官的流放地,又在一个僻处一隅的村落,这不能不是个可称可道的辉煌了。
景兰阁,历史上曾经的风风雨雨,有的不必重提。可喜的是,盛世重文,原来在文革中受到的摧残与破坏,今天都在政府、乡贤的呵护中面目焕然一新了。它虽然寂寞了书声,可是它的文化精气神,依然饱满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