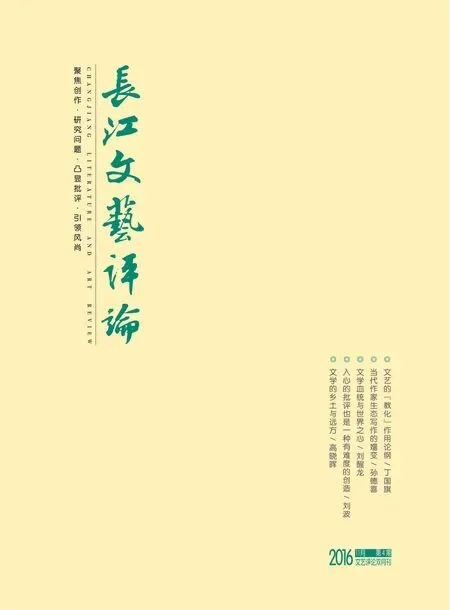当代作家生态写作的嬗变
◎ 孙德喜
当代作家生态写作的嬗变
◎ 孙德喜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至今已经近3 0年,作家众多,作品数量也早已经汗牛充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那么,如何审视当代文学中的这个特殊题材里存在的问题?本期特别约请扬州大学文学院孙德喜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汪树东教授、河北大学文学院雷鸣教授三位专家就此发表各自的思考。应该说,三位专家行文角度虽有不同,但他们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整体性反思有助于我们认识生态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助于生态作家寻求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突破方向。
——主持人 汪树东
生态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既具有当代文学的某些共同特性,又具有其独特个性。60多年来,当代生态文学经历了从不了解生态,到认识到生态问题,再到深化对生态的理解和认识,最终上升到对于生命感悟的形而上层面的过程。与之相对应,当代文学生态写作发生了嬗变,而这种变化既与文学语境的变迁息息相关,又与全社会的生态观联系密切,还与作家个人对于生态的体悟关系紧密。
一、反生态写作
所谓反生态写作,就是指作家在创作时缺乏生态意识与生态知识,无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并且表现出某种反生态倾向的写作。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代文学所涉及生态的写作基本上都具有反生态的倾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战争的结束,我们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作家们面对着国家经济建设热潮,深受感动,于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就使作家们一方面为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呐喊助威,为辛勤的劳动鼓劲加油,另一方面竭力描写和歌颂火热的经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此时的作家们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也不了解生态常识,但是他们的作品却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对自然资源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表现出的就是作家的反生态观念。
自新中国建立开始,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建设材料,其中尤以木材、煤炭、钢铁等需求量极大;另一方面需要开垦荒地,扩大种植,提高农作物生产。在这种形势的感召下,作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中来,广泛宣传生产与劳动中的先进事迹。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作家们在为劳动者鼓劲助威的同时,大力歌颂劳动者的劳动干劲。被誉为“森林诗人”的傅仇早在1950年代就出版了诗集《伐木者》,歌颂伐木工人,赞扬伐木行为。著名诗人郭小川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他的《林区三唱》。[1]他在其中的《祝酒歌》中写道:“广厦亿万间,∕等这儿的木材做门楣;∕铁路千百条,∕等这儿的枕木铺钢轨。∕国家的任务是大旗,∕咱是旗下的突击队。……∕机器如乐队;森林铁路上,∕火车似滚雷。∕一声令下,∕万树来归;∕冰雪滑道上,∕木材如流水;∕贮木场上,∕枕木似山堆。”这是诗人为伐木工人所唱的赞歌,歌颂他们为祖国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然而,由于诗人缺乏生态意识,而鼓动砍伐森林,要让“万树归来”。其实,这还不是单纯的鼓噪砍伐的问题,而且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森林中的树木在诗人的眼里没有生命,只是劳动对象和建设材料;二是在索取自然资源时忽视了节制,诗人在这里只强调“广厦亿万间”需要“木材如流水”,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郭小川的这种对于自然资源的态度当然不是他个人的,也不只是几个诗人或者作家们的,而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态度。然而,这种态度所表现的是人的自我中心,没有考虑对自然应有的保护,其直接后果就是乱砍滥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与此同时,在经济建设的急躁症的作用下,从政治家到作家都急切地描摹着国家工业化的图景,而这图景在作家那里则具体化为烟囱的意象,并且竭力将这一意象予以诗化。郭沫若与周扬所编的《红旗歌谣》[2]中就有这样描写烟囱的诗句:“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白昼在天上绘出黑色的牡丹。”在这里,严重的空气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却看不到,黑色的烟尘居然被诗意化地比喻成“黑牡丹”,化为美的事物。诗人如此审美观同样出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样存在着因人的自我中心化而无视自然环境的污染。
对于劳动者的叙述和描写中,作家往往出于歌颂的需要而突出劳动场所的环境恶劣,以表现劳动者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而这劳动场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然环境,那么劳动者克服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既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困扰,也可以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历史上的道家文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口号,特别强调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不少作家叙述和描写了人与自然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但是,在1949年以后30年中,人与自然的冲突得到了强化,而且在这种冲突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夸大,进而提出了“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等口号。于是文学作品则常常以“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作为主题。大跃进民歌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还有被喻为铁人的王进喜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广为流传的名言。这里所显示的看似抒情主体藐视困难,实际上是在极度夸张中显示其严重的自我膨胀,无视客观自然的强大力量,具有狂妄性。而且,“征服自然”与“战胜自然”都是将自然视为敌人,斗争的对象,其意识深处恰恰是阶级斗争思维的自然流露。正是出于这种思维,人们对待自然采取的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有利于主体的事物大肆夸张,而对那些自认为有害的事物则予以坚决的否定。大跃进期间,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了“除四害”的号召,麻雀被认为是害鸟,列为“四害”之一。著名诗人郭沫若就写了《咒麻雀》一诗:“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3]且不说对于麻雀的误解,郭沫若的这首诗不仅以咒骂代替抒情,而且怀着对麻雀的满腔仇恨要将其灭绝。那个时代的大跃进民歌对于农作物的描写都很夸张,给人的感觉整个世界都为中心硕大的农作物所占据。而这些农作物的极端庞大所体现的是农民的劳动成果,以表达劳动者的所谓自豪,同时表达对劳动的歌颂,然而,简单化和绝对化思维显而易见,而且作品的主题也十分浅薄。
二、环保写作
当代文学关注生态是从环保写作开始的。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们一方面开始反思历史,另一方面关注现实,同时还广泛引进西方的思想理论,进而发现过去所强调的大肆砍伐森林破坏了生态,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过去所欢呼的大烟囱冒出的黑烟已经严重地污染了空气。这就是说,作家们在创作中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由于环保意识淡薄,人在向自然的索取中没有节制,导致环境的严重恶化,从而令作家们看到了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于是,忧患意识鼓荡于胸中,大声疾呼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这就形成了1980年代以来的生态写作。
在生态写作中,首先令人关注的是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轮》等知青系列小说。其中《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4]对下放知青李晓燕等人的生态观进行了反思。李晓燕等人生活在“文革”时期,深受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她和她的同学们(战友们)来到北大荒是为了将这个荒凉的地方开垦成米粮仓。但是,北大荒是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酷寒、沼泽和野狼出没,构成对他们生命的严重威胁。然而,他们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决心很大,精神非常可贵。但是,他们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根本没有考虑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幻想着自己力量的超强,可以“征服自然”,因而忽视了人必将受到自然的限制,而且能力非常有限,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改造北大荒的科学知识,也缺乏应有的装备。因而,这样的改造自然必然以失败告终。李晓燕生病而死,王志刚遭到狼群袭击丢了性命,叙述人妹妹梁晓珊陷入了沼泽地而白白牺牲。梁晓声通过这个悲剧叙述反思了“文革”时代青年人的理想,而这理想反映了反生态造成的悲剧。虽然梁晓声不一定明确意识到自己以反思的方式投入生态写作,但是其小说在生态写作中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进入1980年代,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刺激起人们长期蛰伏的欲望,急速致富的焦虑在国人身上越来越严重。在这种严重的焦虑之下,大开发形成了热潮。所谓大开发,实际上就是向自然的无穷索取,而且没有节制,变得越来越疯狂,进而不顾自然环境的恶化与生态严重失衡,从而造成生态危机。此时的作家已经不再像此前那样为形势所裹挟跟着唱颂歌,而是以独立的主体姿态出现,以他们深深的忧患意识为环保问题大声疾呼,竭力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于是在这一时期,以徐刚、岳非丘为代表的作家创作出一批环保主题的报告文学。徐刚自1988年在《新观察》发表第一部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以来,确立了生态与环保创作主题,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相继推出了《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江河并非万古流》《长江传》《黄河传》《地球传》《高坝大环境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中国江河大坝的思考》《大地工程——内蒙古田野调查》《国难》等一大批作品,进而赢得了“中国环境作家第一人”和“环保作家”的美誉。[5]徐刚等人的环保写作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作家在写作时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发现我们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环境与生态问题:水土污染、流失与荒漠化、生态失衡,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乃至民族的生存。在描写了大量的惊心触目的生态恶化的景象的同时,作家深刻批判了国人贪婪、短视、愚昧和麻木等人性阴暗与弊病。
就在徐刚等人为环保呐喊的同时,有些作家则以追求原生态文化作为逃离被污染的世界的一种追求。所谓“原生态文化”“就是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边缘的、更接近原始的、质朴的、原始艺术源头的并融进了现代其他学科文化的一种文化形式。”[6]原生态文化崇尚原始的、质朴的存在,也就是拒绝现代工业化时代的各种污染,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融洽与和谐,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之梦,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老子。老子提出的“复归于婴儿”,便是强调婴儿的纯真,要求人们弃绝各种智慧,返回到婴儿般的纯真状态。老子所言虽然不是关于环保与生态的话题,但无疑是1980年代人们所提倡的“原生态文化”的源头。而原生态文化之所以得到追捧是因为现实环境的严重恶化,正如道德的败坏与崩溃促使一些人追捧童真一样。当然,也有人将原生态文化置于现实工业化的对面,通过相互比对展开深入的思考。高行健的话剧《野人》[7]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部戏剧以生态学家到神农架考察野人为线索,将现代工业文明与代表原生态文化的民间文化与远古的原始文化等并置于同一时空,进而思考现代人的窘境。而现代人之所以陷入窘境,完全是自己的贪婪,不仅乱砍滥伐,而且猎杀各种各样动物,结果使自己陷入了荒漠化与孤寂的境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原生态文化中,人是那么的单纯,既敬畏自然,又将身边的各种动植物都视为自己的朋友,与之友善相处,而人在大自然中自得其乐。到了新世纪,藏族作家阿来的《蘑菇圈》[8]仍然对原生态文化展开思考,小说以具有灵性的“蘑菇圈”来隐喻原生态文化,思考的是在现代社会,受到国家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冲击的原生态文化走向衰落的命运。然而,原生态文化既有其纯净和富有灵性与诗意的一面,又有其封闭与脆弱的一面。作家在思考中提出了一个悖论:原生态文化虽富有诗意,但毕竟是生产力低下、封闭环境中的产物,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提了出来:在现代化的今天,如何保持某些原生态文化的灵性与诗意,让现代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呢?
在1980年代的作家中,莫言从物种的变异发现了生态的危机。他早期的中篇小说系列《红高粱》[9]将原种红高粱与变种(杂交)红高粱作了对比,写出了变种高粱的矮小和羸弱,进而诅咒这种杂交品种。莫言虽然不是从生态的意义上来创作这部系列小说,他以此来隐喻人种的退化,但是他对红高粱的变种的叙述恰恰具有生态学的意义──杂交所带来的可能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但是严重改变了原有的品味。
三、感悟生命的写作
所谓环保问题,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体现着作为主体的人对于生命的理解和认识由此而体现出对于生命的态度。生命在生态学理论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因为生态的危机实际上也就是生命的危机,当表现为生命的物种大量灭绝的时候,生态失去了平衡,甚至出现生物链断裂,那么人类的生存也必将受到威胁,同样存在着灭绝的危险。然而,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复杂,既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又相互厮杀撕咬,激烈竞争,彼此相扰与争夺。因此,在生态学意义上对待生命的态度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与万物平等,相互尊重的反人类中心论──深层生态主义。于是,不同的作家虽然都对生命有所理解与认识,但是在具体的写作中也同样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深层生态主义的差异。
史铁生是一个特别具有悟性的作家,他在双腿残疾以后,以其敏锐的感觉和宁静的心灵体悟生命的存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他的生命观。最能代表史铁生生命观的散文是《我与地坛》[10]。这篇散文记述的是作家在荒凉的地坛公园里面对着各种微小的生命所展开的沉思与深切的生命感悟。在这许多人觉得“荒芜冷落”的地坛,作家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坚强、活泼与可爱,从草木到雨燕、麻雀再到孩子们,都令史铁生非常感动。就在作家与地坛中的这些动植物友爱相处时,就在作家从它们身上感悟到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人们不难发现作为主体的人置于宇宙的中心──生命因他的感悟而存在而提升。由此可以联想到贾平凹的散文《游了一回龙门》[11]。在这篇散文中,贾平凹位于天地宇宙中心的“游龙”——“我”的形象,而云霞翔凤与山水等祥瑞之物都作为挂在“我”胸前的美丽的花环而衬托着顶天立地的“我”。这是作家唱给自我的颂歌,表现了他宇宙万物皆为我生,皆围转于我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自我中心意识显然是生态学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延伸与扩展。
韩少功无疑是深层生态主义者的代表,他既是这一理论的践行者,又以创作《山南水北》[12]表达自己的生态观。进入新世纪以后,韩少功对于生命表现出极大的爱惜和敬畏。他在与动物的交往过程中从其身上发现了可贵的个性和灵光,他虽然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是他对猪和牛都非常感激,因为他为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而吃过不少猪肉,他看到了牛在人类的粮食生产过程中付出了最沉重的一份辛劳。他在饲养鸡、狗这些动物的过程中,不仅与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还发现这些动物身上所显现的灵性。对于人们讨厌的老鼠、蛀虫、蚊子等动物,韩少功为他曾经伤害过它们感到歉疚和悔意。他认为:这些动物也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在他看来,既然人类有权吞食其他动物和植物,那么老鼠蚊虫也就应该有同样的权利。与此同时,韩少功还对我们汉语中的“衣冠禽兽”“兽性大发”“人面兽心”等词语提出了质疑,他觉得在许多时候人的道德未必比动物们强,动物的情义未必就比人差,人的凶残、暴戾、奸诈、贪婪往往远远超过动物。韩少功的这些思想观念或许有些极端和过激,不一定为世人所认同和接受,但是在这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社会严重失范的时代,韩少功的这些思想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我们无意于评论人类中心主义与深层生态主义的优劣,但是二者都有可取之处,也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走极端的倾向,这都在作家的创作中显露出来。然后克服极端倾向是作家在创作中需要思考与克服的问题。
四、由生态悟人性
自然界的各种动物个性各异,各种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随着对生态认识的深化,作家们对于动物的理解和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思考也更加深入。过去,人们习惯于将动物分为有益与有害两大类,于是对有害动物便产生痛恨之情并且予以否定,予以消灭。而对于有益动物则希望多多益善。事实上,世界并非如此的简单,且不说在深层生态主义那里,各种动物都拥有其生存的权利,就是各种动物之间也应该维系一定的平衡,否则,不仅物种多样化遭到了破坏,而且由于这种破坏而改变了许多动物原先的本性。其实,就某种动物的品性而言,我们的判断往往也是从人类自身视角来作出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对于动物的认识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新的认识。贾平凹与姜戎在转换了视角之后有了豁然开朗的发现。贾平凹在世纪之交出版了长篇小说《怀念狼》[13],姜戎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狼图腾》[14],都写出了不同于通常人们视域中的狼的形象。
狼,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基本上就是凶狠与残暴的象征,是凶恶敌人的比喻。在以往的许多文学作品中,狼的形象是反面事物的代表,基本上受到否定。但是在贾平凹的《怀念狼》中,狼已经成为怀念的对象。当然,狼的凶狠没有改变,但是其意义已经明显不同,狼不再是人类生存的一大威胁。由于人类的猎杀,狼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几乎绝迹。而以猎杀为职业的猎手们则很难找到猎杀对象,于是他们落寞了。久而久之,猎手们猎狼的技艺荒废了,他们在与狼的搏击过程中形成的强健的体魄也开始日渐退化了,肢体的许多能力也日渐消失了。在贾平凹这里,狼与人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人与狼既相互搏击,又彼此促进,一旦对手消失了,那么自身也将面临着退化的危机,甚至有灭种的危险。
姜戎的《狼图腾》对狼的描写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狼的形象,这些生活在草原上的狼充满野性和血性,而且智勇双全,它们集群驰骋于广阔的草原之上,围捕各种猎物,勇猛顽强,果断坚决。这些狼虽然没有摆脱凶狠的血腥暴戾特性,但是更具有了人应有的某些特性,因而可以称得上是草原上的英雄。从姜戎笔下的狼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狼的英雄与悲壮,它们的自由与独立,野性与豪迈,而且,狼在草原上的存在既是对黄羊、旱獭、野兔和牛羊马乃至人的生命构成威胁,又以格斗、追逐和猎杀促进对手的进化与强壮,将那些孱弱而退化的动物予以淘汰,从而在更高意义上维持着草原上的生态平衡。这篇小说与贾平凹的《怀念狼》一样,都从狼的身上感悟到人性,在现代社会里,人不仅要在与狼的较量中强健自身,而且还应保持某种程度上狼的血性和野性。
与贾平凹和姜戎描写狼相类似的是王小波的散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15]。在这篇大约两千字的散文中,作家描述了一头脱离了人的控制而获得自由的猪。它居然无视人对它“生活的设置”,以其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的生活,既活出了十足的个性,也活得十分潇洒。显然,王小波借写这样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以呼唤人的个性与自由。
五、结语
当代生态文学在生态描写、叙述和表达上虽然具有这四种基本的主题形态,但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变迁,而是错综复杂的嬗变过程。一般而言,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涉及生态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反生态的,这是与那个时代的愚昧无知、缺乏生态意识密切相关,与那个时代阶级斗争观念和二元对立思维方法联系紧密。然而,即使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反生态写作并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消失,而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在1980年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不少作家站在人类中心的立场上,以人类的优越性去丑化自己所不喜欢的动物,而对于某些动物的美化,恰恰又是以人类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将其宠物化与奴性化(突出其对人的忠诚)。进入1990年代与新世纪,一些作家受到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在文学作品中大写特写各种豪华盛宴、高级皮毛制品、木制高级家具以及高档消费品,从而为各种高消费推波助澜。然而这些高消费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无视生态与环保。这就是说,自从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生态写作其实也呈现出共时性多样化的特征,这既与文化多元化密切相关,也是由作家个人的生态观和生态意识所决定。
当代作家的生态写作如果要取得新的突破,既要环顾我们所处的生态现实(不能局限于自然环境),更需要对各种生命形态及其相互联系展开思考,还需要从哲学的层面上思索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就人类遇到的各种生态问题进行探索,进而将现代化生活条件与生活方式的悖论以及现代化中的人的种种尴尬展现在读者面前。
孙德喜:扬州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傅仇:《伐木者》,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郭沫若、周扬:《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
[3]郭沫若:《咒麻雀》,北京晚报1958年4月21日。
[4]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5]贡玮、徐刚:《用热血撰写中国绿色圣经的人》,《诗歌月刊》,2009年第8期。
[6]邹德志:《浅析“原生态文化”的概念内涵》,《安徽文学》,2007年第9期。
[7]高行健:《野人》,《十月》,1985年第2期。
[8]阿来:《蘑菇圈》,《收获》,2015年第3期。
[9]莫言:《红高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钱理群:《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12]韩少功:《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13]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14]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5]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