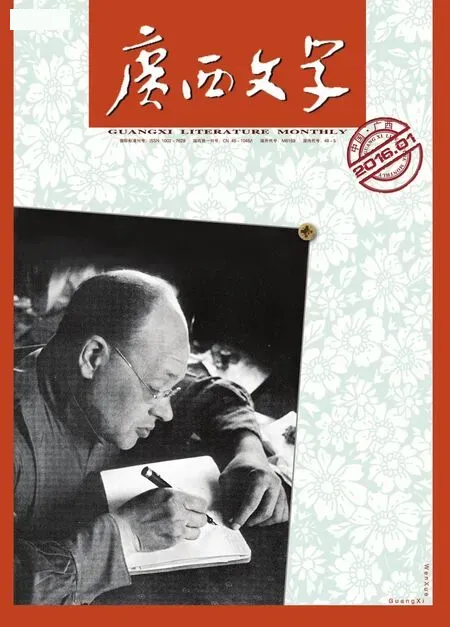微笑的动物
王 族/著
1. 一只狼跟在一个女人身后
人是复杂的,狼看着人的一举一动,所以,狼的目光便也变得复杂。不知道狼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发现像它一样的一个人,人与动物相处得时间长了,喜欢的总是它身上跟自己相似的东西,不知道一只狼是不是也和人一样。
闲着没事,大家说起了多年前在牧区发生的一件事。到了夏季,男人们都赶着羊去放牧,让羊吃一座又一座山上的草,一个夏天都不回去。这时候,留在家里的都是女人,女人们忙着里里外外的事情,从来都不能闲下来。有一户牧民孤独地住在牧场对面的一个小山包上,女主人要干点什么事情,总是要走很远的路。她的男人走了,她就变成了这个家的男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只狼接近了她,她走在路上,那只狼远远地跟在她身后,踩着她的脚印。多少天过去了,她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身后有一只狼,而那只狼似乎只对她的脚印感兴趣,用爪子稳稳地一下又一下踩上,在山路上走。如果她在半路上停下干点什么,或者有要回头的意思,那只狼马上就会走开。
整整一个夏天,她都不知道自己身后有一只狼,而那只狼每天都悄悄跟在她身后,重复做着那么一件事,她由于总是忙碌,对身后的一只狼居然丝毫没有察觉。终于在夏末的一天,这一幕被另一个女人看见了,她马上去给牧区的其他女人讲了,女人们躲在帐篷里看着山路上的那一幕,感到惊奇不已。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她们都对那个女人守口如瓶,只是私下里议论着,最后,她们一致认为她和那只狼有性关系,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但事情却被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便都信以为真。
很快,男人们赶着羊群回来了。女人们把那件事情悄悄讲给了那个女人的丈夫。她的丈夫为了证实事情的真相,躲在别人的帐篷里,等待着妻子在山道上出现。过了一会儿,她出现了,那只狼也出现了,一切都和人们说的一模一样。他愤怒而又羞耻,抓起一支猎枪向着那只狼扣动了扳机。那只狼被打个正着,一头栽倒在地。他的妻子被突然响起的一声枪响吓坏了,等回过神,看见身后有一只被打死的狼,惊恐不已,突然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一吓一惊,她暴病而亡。
没有什么能证明她了,人们从此都看紧了自己的女人,防牲畜比防那些喜欢寻花问柳的男人还谨慎,人们只要一提起她,就说她不要脸,她就是一只动物,她的丈夫觉得没脸见人,赶着羊去了一个人们不知道名字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在牧区,牧民们最仇恨的是狼,但在这件事情上,人们反而没有指责那只狼,只是认为那个女人罪不可恕。
后来,狼踩人脚印的事情又发生了。看见那一幕的那个人手头没有猎枪,就吆喝了一声,狼跑了,被狼跟踪的那个女人从山坡上跑下来,惊恐万状,久久不能平静。人们觉得同一件事情在牧区重复发生,真是有点奇怪。但一只狼为什么总是要跟在一个女人的背后呢?谁也无法解释这一切。慢慢地,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个谜。有些谜是永远无法解开的,但它却有存在的理由。这个世界太大了,不管有多少未解之谜,它都能装得下。
……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看着前前后后的人们都匆匆忙忙在往前走着,就想起那个女人和那只狼。我想,一辈子人生长路,前面走着谁,后面走的又是谁,没有人能说得清,而在走完漫漫长路的过程中,谁知道又会发生些什么呢?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了那个女人,或者那只狼。
2. 被母亲抛弃
在牧区听到的一件与鹰有关的事,大概更加接近人的生存状态。只是作为母亲的那只鹰,在做出决定和为决定而实施具体行动时,少了些人的难舍难分和悲悲戚戚。那只母鹰在悬崖上的巢中生下了一只小鹰,它每天飞出去为小鹰觅食,喂养它一天天长大。对于鹰来说,这段时期是母与子非常难得的相处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它们必将分开,一生一世,母亲不可能再见小鹰,小鹰长大,也不可能再见母亲。鹰在飞翔时,都是独立的,从不合群。曾见过有人写过鹰群的文章,我觉得作者不了解鹰,他只是觉得鹰强大,就以“鹰群”来强化一种气势,但真正的鹰群是从来都不会出现的,所谓的“鹰群”,也只是作者的一种臆想或愿望。那只小鹰长到了可以爬行的时候,母亲就把它推到巢边,让它向悬崖下张望。崖中的冷风和暗淡的光线使它浑身发抖,想缩回身子进入母亲的怀抱。母亲这时候突然从巢中飞出,在崖中上下起伏,自己的身躯划出漂亮的弧线。母亲是为了让小鹰看看飞翔是怎样的,作为一只鹰,是不应该恐惧悬崖和黑暗的。
小鹰当然看得很痴迷,母亲的飞姿,使空旷和幽暗的崖谷顿时显得活泼起来。它上下翻飞,犹如一片火花从一个地方飘移向另一个地方,也像一个移动着的琴键,和空旷撞击,发出一种音乐。也许鹰的耳朵长在心灵中,它用心灵聆听着大自然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音乐。天长日久,聆听就变成了一种对飞翔的引领,变成了暗暗蛰伏在大地身上的一个梦想,它最终要用这个梦想丈量大地,覆盖大地,完毕之后,把大地留给另外一些正在长大的鹰,然后,神秘地消失。
盘飞一会儿后,母亲回到巢中,用身体将小鹰一点一点向巢外推去。小鹰吓得缩紧了身子。岩壁布满荆棘,有尖利棱角的岩石,还有深不见底的河流和尖叫着跑来跑去的土拨鼠。母亲长鸣一声,用力将小鹰推了出去,小鹰哀叫着,身体在空中飘来飘去。天空虽未入秋,小鹰就像一片飘零的叶片,过早地要落到崖底去。母亲将小鹰推向崖谷的同时,振翅而起飞向山后面去了。小鹰在坠落中想攀住树枝和藤蔓,但都没有成功,眼看就要落地了,它突然在挣扎中展开了双翅,旋起一个漂亮的弧线向上飞起。这转瞬间的动作,又是一片火花,将幽暗的崖谷照亮了。它缓缓地向上飞动,最后落在了山顶的一块石头上。崖谷依然幽暗而无声,小鹰看着深崖,好像第一次认识它似的,久久没有转动一下头颅。后来,小鹰发出一声鸣叫,从石头上起飞,向远处飞去。天空高远,太阳赤烈,它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一直飞向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是一位六十八岁的哈萨克牧民,回到村里,他突然变得有些痴呆,碰到人了,不管男女老少,就向人家说这件事。由于他过于激动,说起来总是喃喃自语,所以,人们听上半天,才能大概听出个意思来。他的痴呆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就自己给自己说,他说些什么,谁也听不懂,但他却一直喃喃自语,好像只有他能听懂自己说的话。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地坐在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不知在想什么。他发现了我后,转过头来看我。天啊,他的一双眼睛里面充满了非常坚毅的神情,我原本打算和他聊一聊的,但看着这双眼睛,我觉得他所有的话语都在这里面了。话语被我们不厌其烦地应用着,总想用它去解决所有的事情,但有时候话语也是有限度的,是无法表达人的内心的。所以,有时候在感受中传达的话语可能更好一些。你所感受的对象传达出的话语是隐隐约约的,这是一种自由的交流。人与世界的交流,也大致属于这样。
这几年,我一直留意着有关他的消息。人们传过来的话是一致的,即他每隔一段时间都去那个悬崖边看一看,大概是还想看到曾经看到过的一幕。我猜想,他可能再也看不到了。即使在高原,人一生中能有几次那么近地看到鹰的机会呢?人的居所是固定的,而鹰以世界为家园,二者本身就有着不可接近的距离。至于他目睹的那一幕,本身就是一种神遇。
当他失望并平静地回去之后,一切便就都显得正常了。从此,鹰在他的心里就变成了一种明朗的东西。那一次神遇,对他来说已经足够怀念一辈子了,怀念会使他变得更加坚毅,更加赤诚,更加沉迷。鹰有时候是神。
3. 最后一头驴
驴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是独特的,几乎不让任何人知道它最后会怎样倒地而亡。驴忍辱负重一辈子,到最后仍不与人走得太近,而是悄悄地选择一个角落死掉。驴的这种死法,是不是对人的一种蔑视呢?我在阿尔泰的白哈巴村听到的村子里的最后一头驴的经历,似乎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明确的回答。
驴是偶尔进入这个地处高原的村子的,繁衍了几代,并未发挥出什么作用。后来,便越来越少,只剩下这一头了。人与驴之间实际上只存在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驴发挥不出作用,自然就被冷落了。而驴呢,由于在村里被人冷落,居然连繁殖能力也一再退化,到了现存的这最后一头,生得又瘦又小,全然没了驴的样子。它的主人巴也丹在去年让它拉车,它拉到半途被累得趴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它。巴也丹说,我的驴是一头废驴。从此它的名声就坏了,人们视它的存在为乌有,它无知无觉,慢慢地闲了下来,真的成了一头废驴。在村子里,一个人无所事事成为闲人,会招来人们的议论和指责,因为他的行为是人们苦心维护的生存规则所不容许的。而一头驴,因为不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所以,没有谁会去指责它。慢慢地,眼见它再无生殖能力,一日日老去,变成了村里最后一头驴。
有一天,人们突然想起了它。两个小伙子下石子棋,输了的一方为躲避败局的尴尬,说他能使这头驴按照它的指令走动,他让它趴下,它就会趴下;他让它跑,它就会跑。众人一听来了兴趣,呼啦啦一起涌到了驴跟前。他们把驴牵到那个小伙子家门口,小伙子说,驴,你进去,我给你吃的。驴纹丝不动,他又重复了一遍,驴仍不动。小伙子着急了,捡了一根树枝抽它,驴仍纹丝不动,任他抽打。有人出主意,把驴的眼睛蒙上,可牵入房内。小伙子脱下上衣,蒙住驴头,牵它,但它却似乎早已明白了他的用意,仍站着不动。有人又出主意,听说过驴推磨吗?拉着驴转,它转着转着就迷失了方向,然后就可以把它牵进屋去。小伙子便用衣服蒙了它的头牵着它转,转了好多圈,人都觉得有点晕了,但一停,它仍倔强地背对着房门不肯进屋。大家都蔫了,就这么一头废驴,但谁也拿它没办法。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的结论,驴要是犟起来,就是天打雷轰也拿它没办法。要不,人们怎么说驴认真起来是犟驴呢!嬉闹一番,众人都觉无趣。正要散去,忽见它把头一低径直进入房门。众人又兴起,复又赶过来看它会做何,它走进屋内屁股一动便屙下一泡驴粪。众人大惑,刚才费尽周折它都不肯进屋,甚至用尽了蒙头、驴推磨的办法,想想,这些也就是人类多少年来对待驴的办法,都拿它没辙,但它却自己走进了屋子屙下一泡粪,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它在屋中站了一会儿,头一扭走了出来。众人像是恐惧它似的纷纷给它让出一条道。它在村子里慢悠悠地走着,像一个年迈的老人。
这件事过去后,人们很快就又忘记了它。一头不会发挥出实际作用的驴,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至于它想了些什么,它所目睹的这个村庄是什么样子,它不会说话,不和村里人交流,因而谁也无从知晓。
过了几年,它已彻底老了。人老先老眼,牲畜们老了则先老腿。它的走动已变得极为不便,很少见它在村子里走动。偶尔出来了,也是摇摇晃晃,很短的一点路要走很长时间。它的主人已彻底不重视它了,想起它的时候给它一点草,想不起的时候它就得饿好多天,这样便加快了它衰老的速度。有时候,它在村子里与牛和马相遇了,便停下来与它们对视良久。牛和马都走了,它仍在原地停留一会儿,似是在想什么。动物们有它们交流的方式和语言,不知道它刚才和那些健壮的牛和马说了什么话。那些牛和马有很好的胃口,还要去吃草,只有它走不动,在村子里神情恍惚,不知所措。再后来它彻底走不动了,只能站在村子中间四处张望。它望着自己曾经走过的许多地方,眸中似有想再去走走的冲动,但又有些许无奈,于是凝望便成了它每日最重要的事情。村子里每天都有热闹的事情,却不能吸引它的目光。它总是朝着一个地方看,似乎那个地方保留着它以前的什么东西,成了现在它凝望的资本。
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它不见了。几天前,村子里就没有了它的身影,只是因为人们太忙,未曾留意它。人们去找它,在村东面通向铁列克乡的一个山脊上,发现了它的尸体。它已死去多时,但仍保持着欲向前爬行的姿势。也许它在咽气的最后一瞬,仍想挣扎着向前爬去。
好几年过去了,村里人始终不明白,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何要离开村庄,它想去哪里呢?
4. 无声的离去
另一匹马与人们的生活贴得比较近,稍显平静一些,但它在平静中也坚持了内心至高的尊严。在下马崖边防连,有一匹给连队拉了好几年水的马。连队附近有水井,但里面的水却无法饮用,因此就只好到山下的河中去拉水。战士们动手制作了一辆拉水车,一天拉三趟,足够保障所有人使用。刚开始,每拉一趟都必须要有人跟着,后来有一次,一个战士不想来回跑,在装好水后就对拉水的马说,已经跑了无数次,你应该认得路了吧,今天你试着单独拉一次。马好像听明白了他的话,拉着水车就走了。它确实认得路,顺顺当当地将水车拉到了连队。从此以后,拉水的战士只要把水装好,对它说一声,回去吧,它拉起水车就走了。那个战士躺在石头上休息,嘴里南腔北调地唱几句歌。那匹马一到连队,炊事班的战士把水卸下后,也对它说一句,回去吧,它便又向河边走去。这样,它在一条路上来回走了四年。它的沉默与执着,支撑着连队的正常运转,保障着战士们每天在山野之中大声喊出一二一,在翻山越岭时有足够的力气。
后来,连队有了自来水,那匹马的工作自然而然地中断了。人在一般情况下,对生活的要求都是无止境的,而且总是喜欢让新的东西取代旧的东西。新的东西往往代表的是生活的变化,人与生活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变化。而由于生活的变化又总能够给人更多的安慰,所以,人还是喜欢生活的变化的。事实上,人的一生,也就是变化的一生,生命就是在不断地变化中被完成的。另一个事实是,人变化的时候,对另外的东西却是很少关注的,变化的新鲜感可以使人欣喜、疯狂,甚至昏晕,很少对使自己变化的客观体关注。比如这匹马,在连队通上自来水后,它自然而然地就被遗忘了。如果连队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甚至连吃水也成了问题,它的价值就体现得更加充分了。但连队要改变生活条件,自来水是必须要通的。所以,一匹马的工作自然而然就被废黜了。战士们围着水龙头洗脸,洗衣服。多好的水啊,想怎样用就怎样用,想用多少就用多少,那种用水如用油的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了。那匹马望着水龙头,神情复杂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候走到以前负责拉水的那个战士门前,便停下朝里张望,过一会儿,不见有任何动静,便转过头默默地走了。后来,它不再在院子里走动,卧在院子外面,一会儿望望天空,一会儿望望远处的树。有人在附近走动,它便盯着看,直到他们消失。有一天早晨,战士们发现它不见了。有人在昨天晚上曾听见它叫过几声,在那几声后,有一阵很响的蹄声驶向了远处。大家一致推论,它走了。大家隐隐约约感觉到它出走的原因,望一望无边无际的沙漠,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两年后的一天,它突然又回来了。这两年多的时间,它一直在外面流浪,瘦得浑身没有一点肉,身上的毛长得杂而长,有很多树叶夹杂在其间。战士们心疼它,也为它在出走两年多以后还能够回来而高兴,他们给它洗澡,喂它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它能够回来,肯定以后会把这里当家。第二天,天降一场大雪,水龙头被冻住了,战士们便点火去烧,很快,水龙头就化冻了,水哗哗哗地流了出来。那匹马看见水龙头里流出的水,突然痛心疾首地叫了一声,冲出院子,奔向茫茫雪野深处。
它又走了。
好几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它再也没有回来。
5. 绝境中的生命
夏天的雪豹是流浪者。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一只雪豹走进了牧场。西边还有些霞光,将草叶照得泛出了明亮的光,牧民们都已将牛羊收拢,有几户牧民的帐篷上空已升起炊烟,空气中飘着一股奶香和羊肉的香味。那只雪豹从山上走了下来,径直向牧民们走来。它长得很高大,通体泛白,被夕阳一照,便闪闪发光。
牧民们都很惊讶,一只雪豹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向人走来。而它呢,似乎对这些人视而不见,一直将头扬得很高,迈着稳健的四只爪子走到了一条小河边,牧民们以为它要停住了,而它却一跃而起越过了小河,又继续向人们走去。慢慢地,人们便感觉到了这只雪豹的某种态度,它像一个勇敢走向战场的士兵,尽管知道前面有危险存在,但却毫不胆怯,要冲上去奋力一搏。牧民们感到这只雪豹在示威,他们今年赶着牛羊进入牧场前,牧场是雪豹、野鹿、野猪等动物的生存之地,人和牛羊进来后,喧闹的声音把它们赶走了。野鹿性情温柔,爬过几座山,越过几条河,就又找到了草场;野猪力气大,随便选一个地方用嘴拱开草地,就可以找到吃的;只有雪豹性情高傲,而且对饮食的要求极高,找不到好的草场不随便对付自己。牧民们想,这只雪豹可能去了很多地方,对那里的水草均不满意就又回来了。而现在,白花花的羊已撒满山坡和草地,高大壮实的牛更是分布于草场的角角落落,哪里还有它的立足之地。更重要的是,它是雪豹,而牛和羊是家畜,它们无法融到一起。但牧民们从它高扬的头和迈得很稳健的步伐上断定,它要“收复失地”。这样一想,人们便觉得如果它与牛羊发生冲突,难免少不了一场流血事件,到时候,死的不是它,就是牧民的牛羊。而目前的事实是,它只是一只孤独的雪豹,而牧区有成千上万的牛羊,要是一拥而上足以将它踩成肉泥。牧民们对牲畜有很深的感情,对山上的动物也厚爱有加,是不情愿让那样的事情发生的。
它越来越近,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有人想朝它喊一声,把它吓走,但还没等开口,它却站住了,它望着牛羊,眸子里闪着复杂的光。有一只羊朝它咩咩叫了几声,它也回应着叫,声音急躁而又不安。牧民们想,如果它果真冲向羊群的话,就必须在它刚流露出意图的时候把它拦住。牧民们之所以这样想,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怕它把羊冲乱,使羊群受到惊吓,不好再收拢;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出于对牲畜本能的一种怜爱,都是动物,何必互相伤害呢!他们不愿意看到牧场上出现死亡的事情。这样想着,人们便屏气凝神等待着它冲向羊群的一刻,但它却并没有冲向羊群,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羊群出神。牧民们想,它虽然是一只雪豹,但与羊仍是同类,说不定它们互相凝望就是一种交流或对话,它们的语言就是此时互相凝望的目光。过了一会儿,紧张的气氛慢慢变得轻松起来,牧民们似乎也感到正处于一种冥冥的对话之中。这种气氛在阿尔泰会经常出现,牛羊、大树、风、河流等,时不时地都会给人带来奇妙的感觉。人的心思被这些东西吸引着,变得浪漫起来。这种时候,人便变得更快乐了,牧场便变得更美丽了。牧民们唱歌喝酒,大多都是在这种时候。
它望了一会儿牛羊,又望了一会儿牧民和帐篷,突然转身走了。它转身离去的动作像来时一样,稳健、坚决,而且还似乎夹杂着些许高傲。牧民们无言地望着它离去,牛羊也默不作声。一只雪豹只是这样走进了牧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一匹马却被它激怒了,刚才,它望了牛羊,也望了人和帐篷,唯独没有望这匹马。这是一匹还没有被骟的儿马,性烈气盛,忍受不了它对自己的漠视,尤其是它离去时流露出的高傲,它长鸣一声,腾起四蹄向那只雪豹追去。牧民们大惊,但却已经无法阻挡,只好看着它冲了过去。雪豹回头看了一眼马,也倏地腾开四蹄跑了起来,它边跑边回头向后张望,似含有挑衅之意,马更愤怒了,加快速度向雪豹追去。牧民们都围了过来,刚才担心牧场上出现死亡,看来这会儿真的要发生了。它们跑到牧场边缘,雪豹一看马已经接近自己了,便飞速窜入林子,向山岩上攀去。山岩奇形怪状,几近无路可走,但它却闪转腾挪,非常灵巧地在山岩上跳来跳去,不一会儿便爬上了山顶。马只好在林子边停住望山兴叹。马只能在平地上施展本事,在山岩上便寸步难行。很快,雪豹已在山顶没有了踪影,而马却仍在下面呆呆地望着。也许,它在这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些什么。少顷,它默默地转身而回。牧民们和牛羊都望着它,它低着头,像一个战败了的士兵。
这件事过去好几天后,又有一只鹿像那只雪豹一样走进了牧场。在短短的时间内,事情又像那天一样重复着上演了一次,那只鹿也是向牛羊和牧民望了一会儿后便又离去。结果那匹马又追了上去。那匹马也许是想借这头鹿洗刷前几天的屈辱,但它还是被鹿甩在了后面,那头鹿攀越山岩的速度比雪豹还快,从几块石头上飞跃过去,转眼就不见了。
牧民们都责怪那匹马,说它像村里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村子里对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有严格的衡量方法,比如你长到现在吃了几只羊,骑过什么马,翻过多少座山,都是有多大本事的标志。牧民们说,这匹马明年无论如何得骟了,不然,它老是干傻事。比如追鹿,一般情况下,马都不会干这样的事情,鹿的灵活没有哪种动物能比得上。在牧区,人们曾亲眼见过一头鹿将一头狼一蹄子踢死。还有一次,一群狼将一只鹿围住,准备合拢后将它咬死,但它却从狼群头顶如流星一般一跃而过,转眼就跑出了很远,狼群被惊得愣怔半天才有了反应。
过了几天,那只雪豹又走进了牧场。也许因为前面已经来过一次,加之又战胜了那匹马,它轻松自如地在牧场走动,毫无陌生感,就像羊群中的一只羊一样。那匹马也许已彻底服了它,对它消除了敌意。慢慢地,它和牛羊成了朋友,与那匹马更是显得亲近。它每天都从林子里出来,到牧场上吃草,并不时地发出长鸣,那匹马和牛羊一听到它的声音便遥相呼应,纷纷与它对鸣,牧场上出现了非常热闹的嘶鸣声。牧民们看到牧场上出现如此热闹的景象,也颇为高兴,他们觉得,一只雪豹与一群牛羊融到了一起,是牧场上一种新的生机。
后来,一帮猎人来到了牧场,他们听了那只雪豹的故事后对它动了心思,牧民们警告他们,如果谁敢动那只雪豹,我们跟他动刀子;谁让那只雪豹流血,我们就让他流血。那些猎人不吭气了。但牧民们却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偷偷地下手。预料不到的事情,往往会导致可怕的后果。那天早晨,那只雪豹刚走到牧场中间,他们就把它围住了,它想钻入林子攀山岩离去,但那些人早已摸清了它的动机,派两个人死死地把守住了它的退路,无奈之下,它只有向另一个方向奔突,挡他的那个人没拦住它,它便冲出了包围圈,那些人在它后面穷追不舍,一直把它赶到了一个悬崖边。它站在悬崖边悲哀地嘶鸣着,牧场上的牛羊和那匹马都听见了,应和着发出躁动不安的叫声。那些人逼近,用枪瞄准了它,它停住嘶鸣,纵身跳入崖中……
我到牧场的时候,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多天了。牧民们时不时地仍要提起那只雪豹,牧场上的牛羊吃着草,不时地扭头向悬崖那边张望。那帮猎人早已经跑了,牧民们要找他们算账,他们怕流血,怕死,他们没有一只雪豹跳入悬崖的勇气。
一天,我走到了那个悬崖边,悬崖深不见底,黑乎乎的,似有什么鬼魅在游动。正要离去,却见对面的崖壁上有几朵花,红艳艳地开着。崖壁陡峭,不长一树一木,但这几朵花却选择绝壁而生,而且开出了鲜红的花朵。想着一只雪豹就是从这儿跳下去的,心便沉了,它跳下去的一刻,是不是看到了这几朵花?
6. 生命的加冕
从天山牧场往东行三四公里,就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草场。尽管牧民将其称之为草场,但里面却有水,密密匝匝在悄悄流淌,也有一些圆石分布其中,太阳一照便闪闪发光。吐尔洪说这里其实是牦牛自下而上的好地方,每年夏天都有成群的牦牛到这里来,吃那些一簇一簇疯长的野草,吃饱后便踩水嬉闹,很是热闹。
我等待着牦牛群出现,我已经在藏北阿里和帕米尔见过牦牛,我十分喜欢它们在高原上行走的姿势,那种稳健和强大,犹如是在检阅高原。曾经有一头牦牛挡住我们的车,任凭司机怎么按喇叭就是不让路,它很平静,既不愤怒,也不蛮横,似乎在它的观念里从来没有给别人让道这一说法。等了几分钟,我发现它始终在抬头凝望雪山,便似乎明白了什么,就让司机绕道而行。走远之后回头一看,发现它扭过头在望着我们。我对那只牦牛记忆深刻,它与雪峰一起给我留下了让我在心头久久怀念的感觉……
我爬上一座小山,还没有喘过气,就为眼前的情景大吃一惊,对面的山坡上正黑压压地走过来一群牦牛。它们似乎是一个排列得很有秩序的方队,潮水一般冲向坡顶,又漫漶而下进入坡底。进入草场后,忽然,它们像是听到了一个无声的命令似的站在原地不动了。太阳已经升起,草地上正泛起一层亮光,它们盯着那层亮光不再前进一步。静止的牦牛群,和被太阳照亮的草在这一时刻又构成了一幅很美的画。我已有些沉醉。过了一会儿,太阳已慢慢升高,牦牛群散开,三五个一堆,各自吃起了草。慢慢地,它们便一个一个独自去寻草。从远处看,依稀分开的牦牛犹如无数个静止的小黑点,而成群的牦牛又好像一片低矮的灌木丛。
我走下山坡静静观察它们,而它们却毫不在意我的到来,只是低着头把嘴伸向那些嫩绿的野草,嘴巴一抿一抿地吃着。有几头牦牛的角很长,以至于嘴还未伸到草跟前,角却先触了地。因此,它们就不得不把头弯下,歪着脑袋把草吞进嘴里。看着它们,我感到了大地上生灵无可避免的沉重,叹服于它们的笨重和沉默,但它们却别无选择,这似乎就是它们的命运。
我在它们中间走动。我想起吐尔洪的话,他说这块草地其实就是牦牛的天地,它们每天早上到这里来吃草,一直到下午回去,这里的草被它们啃了一遍又一遍,但似乎总是啃不完。我注意到了这些野草,它们是不懈的雨水滋润大地之后,大地对天空回报的崭新容颜。雨水冲刷着万物,一切都在生长,这就是大地的力量。这生动的大地,本身就是一个真理,它让任何用心的劳作都不会落空,都留下自己的足迹。
这时,一头牦牛走到了我跟前,它的巨大犄角上挑着一只不知毙命于何时的狼的尸架,由于时间太久,狼的尸架被完全风干,固定在了它的头顶。这只牦牛已完全适应了狼尸的重负,所以在行走和吃草时显得很自如。我跟着它的走动,那副狼的尸架上下起伏,仿佛是一尊加冕于牦牛头上的王冠。后来,牦牛发觉我在观察它,便警觉地逃入牦牛群中去。当它把头低下,我便再也找不到哪一头是刚才享戴圣冠的牦牛。返回乌鲁木齐后,我从一位野生动物学家处得知,牦牛将一只狼用角刺死后,狼尸被挂在它的角上,尸肉一日日脱落,只剩下了一副骨架。牦牛在那一瞬间竭尽全力用角刺向那只狼,双角刺入了狼的骨头中,从此狼的尸架不再掉下。狼是高原上食肉类动物中的强者,但在那一瞬的灭顶之灾中,它绝望的瞳孔里会不会有一种古怪的驯顺呢?
第二天,我在那块草地上看到牦牛真正激扬的一面。那些高大健壮的牦牛正在吃着草,却忽然聚拢在了一起,冷冷地互相盯着对方,像是怀疑对方与自己并非一类似的。过了一会儿,不知是哪头牦牛嘶鸣了一声,整个牦牛群马上变得混乱了。混乱之中,可以看出有的牦牛在努力向外突围,而处在外围的牦牛却像不明事态似的在往里面冲。草被它们踏倒,水也被蹄子溅起,带着泥巴沾在了它们的身上。我不知道这些牦牛要干什么,但从它们的架势上隐隐约约感到有一股杀气。我在内心祈求它们不要互相残杀,尽量地平静下来,像亲兄弟一样在天山上相处。人类对牦牛的残害已经越来越猖狂,有一段时间,牦牛尾巴做成的掸子很畅销,有人便在牦牛身上大发横财,他们拿一把刀子悄悄走到牦牛身后,一手将它们的尾巴提起,一刀下去就将尾巴砍了下来。被砍掉尾巴的牦牛痛得狂奔而去,有时一头撞在石头上便死了。
想到这些,我担心今天的这群牦牛会相互伤害,很快,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牦牛开始互相撞碰起来。它们先是用身体去撞对方,不一会儿便都兴起,用角去刺对方。那些乌黑的犄角像一把把利剑似的在对方身上划出口子,血很快就从里面流了出来。这时候,我注意到牦牛都开始叫了,它们像是变得很兴奋似的, 在“呜呜呜”地叫着向对方凶猛攻击。当然,在进攻中它们也不时地被对方的角刺中。渐渐的,有一部分牦牛因体力不支或受伤过重,退到了一边。血从伤口中大滴大滴地流着,使它们不停地战栗,但它们都不离开,仍像是很兴奋似的看着那些正在战斗的牦牛。那些正在战斗的牦牛显然是这一大群牦牛中的佼佼者,它们不光身体敏捷,而且特别善战,也特别能忍耐。它们身上已经有很多伤口,血甚至已经染红了身子,但它们却丝毫没有要退下的意思。但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它必须要求参战者全神贯注地投入,而结局无外乎两种,要么失败,要么战死。至于胜利者,则是这两者中的幸存者。很快,又有一批牦牛退了下来。又过了一会儿,第三批失败者也退了下来,留在格斗场上的几乎都是胜利者。而正因为它们都是胜利者,所以紧接着的战斗就更激烈也更残酷了。可能是因为距最后的胜利已经不远,所以,它们再次兴奋起来。一阵猛烈的攻击过后,又有几头牦牛退下了。有一头很健壮的牦牛似是不甘心,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立刻,有两头已明显取胜的牦牛便一起向它发起了攻击。当四只尖利的长角刺进它肚子时,在“噗噗”的响声中,它如一座轰然倾倒的大山,趴在了地上。
战斗终于结束了,剩下的几头牦牛就是胜利者。它们高扬着头,长嗥几声,向伫立在远处的几头牦牛走去。这时候,我才发觉远处的那几头牦牛一直伫立在那儿,它们像我一样在观察着刚才的一场战斗。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加入战斗,从它们的体形上看,有可能是母牦牛,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它们中的一头牦牛叫了一声,我从它的叫声中听出它们的确是一群母牦牛。牦牛生活的地方随季节变化而变,冬季聚集到平原,夏秋到高原的雪线附近交配繁殖。那几个胜利者径直走到母牦牛跟前,用嘴去吻它们。母牦牛像是已经等待了许久似的,一对一的与它们依偎在一起,胜利者不时地发出喜悦的嗥叫,母牦牛用嘴舔着它们伤口的血,舔完之后,它们便头挨着头缠绵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母牦牛便显得兴奋了,它们静静地站着,让公牦牛从后面爬到自己身上,完成一头公牦牛的生命喷射和飞翔。至此,我才知道了这群牦牛为什么奋战,几头母牦牛在远处发出了信号,它们便为之奋争。这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份光荣,也是一次十分难得的交配机会。所以,它们都奋不顾身,几乎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经过血的代价换来的幸福,已使它们忘记了身体的疼痛。这与光荣和鲜血同在的幸福,是属于牦牛自己独享的美妙时刻。
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失败者,此时都悄悄地把头扭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