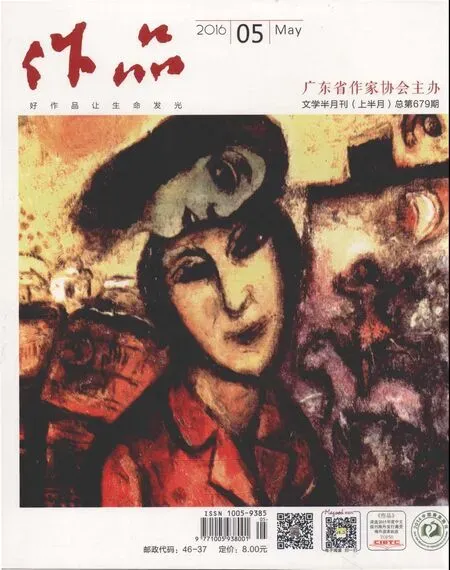101进站
文/魏 姣
101进站
文/魏 姣
魏 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空港手记》、 《爱情看上去很偶然》、 《24小时约会》。
提前内退一年后,邱兰有了新岗位,在四通桥公交站当交通协管员。社区给她配发了桔色凉帽,黄色体恤衫和黑裤子,还有一把小红旗,上面写着“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四通桥毗邻两所高校、一家医院和两个大型商场,高峰时段被喻为“肠梗阻”。这里的车站是个大枢纽,设有两个站牌,共8条线路经停,早晚排队候车的人熙熙攘攘。初次上岗,邱兰面对汹涌的人流不知所措。她默默注视着两位久经考验的同事。一个是马小翠,不到50岁的女人,瘦小精干。还有个男的叫孙力,60上下,高大魁梧。他俩的共同点是大嗓门。“101路进站,请排队候车,先下后上!”“远途的乘客请往车厢中部走!”“下车的乘客请别忘记刷卡!”浑厚的男音和高亢的女声此起彼伏,穿透噪杂的车鸣,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让不堪重负的车站有了某种约束和秩序。
邱兰和马小翠共同负责东边的站牌,不到半个钟头,嗓子就哑了。不远处的孙力潇洒地挥挥小红旗,送走一辆满满堂堂的大公交,走到邱兰身边,塞给她一枚口哨。这神器还真有威慑力。邱兰眼见车都要挤爆了,一个小伙子还扒着车门拼命往里拱,喊他也不理会,就鼓足腮帮吹了声口哨。他回头张望一下,悻悻地退下来。
吃晚饭时女儿惊呼:“妈你半天儿就晒黑啦!”
邱兰拉起短袖一对比,小臂就像上了层釉。
邱兰也没想到,自己会干起这行儿。她本来满怀欣喜等着照看外孙。女儿怀孕是她退休生活的最大慰藉。婴儿床和小衣服都备齐了,她天天研读育儿大百科。可四个月的时候,胎心停了。医生说免疫排斥反应遗传基因异常,她听不懂。女婿是列车员,东奔西跑顾不上家。女儿是机场安检员,把这次惨痛经历归咎于常年作息不规律加之辐射危害,一气之下辞职了。邱兰急得嘴上长泡,埋怨女儿鲁莽丢掉铁饭碗。女儿却满不在乎,说大不了开网店呗!邱兰心里嘀咕,你个中专生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谋生跟网购一样简单呢。
邱兰想给女儿加强营养,正发愁每月两千元的退休金入不敷出,碰巧听说社区招聘交通协管员,每天工作5小时,月薪1500元,既不影响照顾女儿,又能贴补家用,便欣然报名。
邱兰的工作时间分成两段,早上七点到九点半,晚上五点到七点半。早晚高峰如同打仗,马不停蹄地指挥车辆进站出站,引导乘客排队候车,还得解答各式各样的问询。最夸张的时候8辆公交车同时进站,乘客蜂拥而上,自行车七扭八拐,整条马路车鸣混战。到了下班前半小时,路况明显好转,每两三分钟才会有车进站。马小翠便打开话匣子,跟邱兰聊东聊西。
聊得最多的是孙力。他是老北京,当过兵,退伍后在一家机关的保卫处工作二十多年,退休后又当协管,已经干了七个年头。他的种种光辉事迹经过马小翠声情并茂的渲染,让邱兰听得如痴如醉。仅徒手擒贼的故事就有六个版本。大致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有小偷从101路公交车蹿下,向西狂奔,孙力用旋风般的扫堂腿把他踢了个狗啃泥,趁势将他摁倒在地。不料那厮藏有凶器,一刀刺中孙力的右掌,刹时血流如注。围观者里外三层,竟无一人敢上前相助。两人殊死搏斗数回,眼看刀子就要刺进孙力的胸膛,女失主才哭哭啼啼找来警察擒获了恶贼。
马小翠每次叙述的细节都略有出入,那贼掏过匕首,也掏过剪刀,钱包是红色真皮,也曾金光闪闪。邱兰从不揭穿她,而是望着孙力健硕的侧影,享受电影画面般的浮想联翩。他年轻的时候必然非常英俊,如今两鬓斑白,眉目间仍英气逼人。
孙力对马小翠的叽叽喳喳不以为然,他笔挺端立,每个指挥动作近乎完美,音色如同广播员,让这烦琐的岗位有了几分神圣感。休息喝水时他偶然听到马小翠说扫堂腿,差点喷出来,说你把我吹成白眉大侠了,不过是急中生智绊了他一跤。马小翠拉过他的手让邱兰看,沟沟壑壑的伤痕一闪而过。孙力抽开手,哪个男人没几道疤?
比起身上的疤痕,邱兰更想洞悉他内心的伤痛。马小翠说他离婚十多年了,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的。邱兰想不通,这样的男人怎么会被抛弃?
时常有乘客来问路,这让邱兰有点发憷。这些年,除了单位和超市,她基本上窝在家里,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她让女儿找来四通桥这几路公交车的线路图和换乘站,装订成小册子装在口袋,闲了就背。
这天有两个女人问她双秀公园怎么走,邱兰答不上来。她俩儿手挽手走了,议论声传回邱兰的耳朵:“傻了吧唧的!”邱兰愣了,从小到大还没被人这样数落过。
马小翠说:“坐101到马甸桥西就是双秀公园了,你光背站名没用,得熟悉景点和标志性建筑。”邱兰恍然大悟,原来功课还差得远呢。马小翠给她支招,下次遇到问路的就推给孙力,他简直一活地图。
邱兰也发现,几乎没人能问住孙力。他总是胸有成竹地给他们指明方向,附加最佳出行方案:您到金旺福呀?甭坐地铁了,够挤的,出来还得走一大截儿呢,不如坐79路到十院,原地换乘308,两站地就饭店到门口。西单羊肉胡同?您坐地铁4号线到西四站,出C口右转就是。问路者脸上的疑惑往往烟消云散,连声道谢。
邱兰羡慕他记性好,他说一个人嘛,在家闲不住,喜欢走街串巷瞎溜达。周末经常骑车出游,从后海绕到前门,从南城飙到奥林匹克公园。如果不是楼盖得太多,路修得太快,他对北京城会更加了如指掌。
邱兰上班满两周,孙力提出跟马小翠调换位置,由他和邱兰共同负责东站牌。理由是车都从东边过来,需要更加有力的疏导,而且东站牌的101路最拥挤,可以让邱兰专职协调。
马小翠说:“您是站长您说了算。”脸色却暗沉下来。
邱兰看得出,马小翠对孙力很殷勤,三句话必然提到他,早上常给他带包子。有一回孙力早早把水喝光了,马小翠指着马路对面的海悦大酒店,说那里面有饮水机。孙力迟疑了片刻,说进那种地方不自在。马小翠一把抢过他的杯子,说我正好活动活动筋骨。马小翠家里有三套房,以前做过生意,不差钱。她在家闷得慌,便出来当协管员。她说过,这活儿费力不讨好,但跟着孙力就有干劲儿。
晚上回到家,女儿迫不及待地告诉邱兰有好消息。原来她逛街时遇到一个中学同学,在街道办事处上班,说可以帮邱兰调换到家门口的地铁站当协管员。“不用换!”邱兰慌忙问她,“你还没跟同学说吧?”女儿很纳闷:“你在公交站风吹日晒,地铁站多舒服呀!”邱兰说:“年纪大了,晒晒太阳还补钙。”女儿说:“昨儿你还抱怨脖子晒爆皮了,衣领天天都是黑的。”邱兰说:“跟同事都混熟了,懒得换地儿。”女儿从鼻子发出笑声:“啥同事呀,一老头儿一老太太。”
就是这个常人眼中普普通通的老头儿,让邱兰突然感到生活有了一丝盼头。他们的岗位距离将缩短十米,几乎并肩作战!早上出门前,她照镜子的时间延长了,从未如此嫌弃自己寡淡的眉毛和鼻尖上的雀斑。她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抹上防晒霜,撕掉嘴角的一块小干皮。见女儿还在酣睡,她偷偷打开她的化妆包,挑出一只眉笔在眉毛上蹭蹭,左看右看不自然,又赶紧用毛巾擦掉。
邱兰比平时早到十分钟,孙力已经来了。他把杯子挂在车站铁栏杆上,从挎包里掏出小红旗抖落平展,顺手捡起一只易拉罐丢进垃圾箱。
在声如洪钟的孙力面前,邱兰对自己的蚊子声更为自卑。车来了,幸好孙力连珠炮般帮她接话:“后面还有一辆101,上不去车的乘客别着急!”“门口的乘客不要挤,让抱小孩儿的先上车!”“抬脚——关门儿——走喽!”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能监测远处的车辆,又能注意到每个乘客的细节,还让邱兰往马路牙子里侧站站,说当心自行车剐着你。
“邱兰不是101专员嘛,你怎么揽人家的活儿?”马小翠不知从哪儿蹦出来。
“我这叫传帮带。”孙力说。
“当初怎么没带过我呀?咱俩儿一东一西,独挡一面。如今来了朵兰花儿,还得捧着供着。”
孙力躬身给马小翠作揖,她才抿着嘴去了,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摆。
孙力扭头对邱兰说:“你喊不出来别勉强,要学会用气,一口气吸到丹田,然后放松胸腔,像自来水似的慢慢呼出来。”他用手在腹部比划着,给她做示范。
邱兰乖乖地跟着他深呼吸。
孙力并没她印象中那么严肃,有空也跟她闲聊。他最发愁儿子不找对象。儿子在外企工作,忙时不要命,闲时疯狂玩,提起终身大事就打马虎眼儿。他说那臭小子想找漂亮的,还不能矫情,这不自相矛盾嘛。
在邱兰眼里,乘客是个庞杂而陌生的群体,来去匆匆,不留痕迹。而对于驻守在小小站台长达数年的孙力来说,不少路人已成熟人。他们热情地跟孙力打招呼,拉家常,逛完早市的大妈有时会塞给他几个水果。不少公交司机和售票员会在短暂的停歇时刻跟孙力搭讪,他们亲切地叫他孙大哥。
有时,孙力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脸上似乎有丝惘然若失的神情。邱兰便揣测他惦记着某位乘客。
有些日子不见小秦了。孙力曾自言自语,回过神儿来跟邱兰解释:挺文气一小姑娘,就在路口那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她住在通州,傍晚老在这等323。她跟我说在北京活着太累,路上太疲惫,想回湖南老家,可男友在房产公司打工呢,说什么也不肯离京。
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家住车站附近的小南庄,每周四下午坐33路去广渠门看中医,五点左右返回。三年了,孙力雷打不动地护送她从车站走到小区门口。她的两腿因严重风湿成拱形,一手挽着孙力,一手拄着拐杖艰难移步。腿疼发作时,孙力便直接背她回家。
这天老太太刚下车就迫不及待地抓住孙力的手:“哎,上回跟你介绍的那个孟大夫怎么样啊?”
邱兰的心提起来。
孙力低头笑笑:“挺好,可我一人自在惯了,不想受管束。”
“不是管束,是照顾你。再硬朗的身子也有失灵的时候。人家是心脑血管专家,越老越吃香。家有医生,如有一宝啊!”
“我可不想连累人家,动弹不了就去养老院呗。”
“胡说八道!”老太太嗔怪地拍了他一把。
他们走远了。想到自己也将孤独终老,邱兰陷入一股莫名的忧伤。
有多少人喜欢孙力,大概就有多少人讨厌他,因为他管得太宽了。
只要车站出现小广告,他便怒不可遏地从挎包掏出小刀刮掉。碰到顽固的胶渍,他还备有一瓶风油精,洒上几滴,拿抹布沾上热水擦净为止。那些贴广告的往往在夜里行动,白天还真让孙力逮住一回。两个小青年脚下生风,眼疾手快,边走边从挎包里掏出小广告,靠近车站时嗖地贴上双面胶,藏在掌心,趁人不备往站牌和宣传栏上拍几下,顿时歪歪斜斜冒出一串广告。
孙力用旗子指着他们高声呵斥,小伙子我给你脸上贴块膏药好看吗?车站就是城市的脸你懂不懂啊?年轻力壮的干点啥不好啊?光天化日之下毁市容你害不害臊?
两人仓皇溜走。此后,四通桥车站的小广告比周边车站都要少。
孙力不允许候车乘客在高峰时段抽烟,如果劝说无效,就给他背诵《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直到他掐掉烟为止。
有人往垃圾箱吐痰,孙力也要干预:您这一口痛快了,保洁员得用双手掏垃圾!
每当这时候,邱兰都有些提心吊胆,因为孙力难免会遭到白眼、讽刺和谩骂。可他总是面不改色,四处出击。
孙力也摊上过麻烦。有人在车站附近停车,孙力让他赶快离开,他眼珠一瞪,破口就骂:“你他妈一破协管,装什么交警?”
马小翠挺身而出:“你非法停车!”
那人转而攻击马小翠。邱兰从没听过那么肮脏、下流的语言,如同把人当街扒光了拿皮带抽打,简直是赤裸裸的暴力。她一句也插不上,只觉得血往头上涌,胸口剧烈起伏快要爆炸了。可孙力无动于衷地站着,甚至还阻拦马小翠:“别吵了,回到你的岗位! ”
马小翠发起飙来也不要命,嘴比刀子快,刀刀见血。那人急红眼了,挥拳要打她,被孙力一把挡开。旁边几个男乘客合力把那人抱住,他两脚乱踢。
直到邱兰大喊警察来了,他才挣脱身子,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开车走了。
孙力疏散开人群,责问马小翠:“为什么不听指挥?”
马小翠的发丝湿漉漉贴着额头,梗着脖子盯了他一阵,鼻翼开始抽动,豆大的泪珠喷涌而出。她转身拦下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孙力摘下帽子,灰白的头发被汗水浸透,额头上留下红色的勒痕。
邱兰突然对这份工作充满了质疑。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要冒着酷暑在这个鬼地方跟三教九流碰撞?为什么要以位卑权轻的角色去管控那些低劣的违规?为什么非要对野兽诠释文明的定义?
孙力说:“小翠是委屈,可穿着工作服,你就是不能吐脏字儿。自己不讲文明,怎么要求别人文明?”
第二天马小翠没来上班。孙力在西站牌替她值班,邱兰算是第一次独立上岗。时值秋季,他们已换上夹棉工作服,不出一个钟头便汗如雨下。她觉得孙力离她很远很远,只能偶尔瞟他几眼。他看到她,就会打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傍晚,不时有些男女学生在车站缠绵,有一对格外忘情。男孩瘦高,靠在广告栏上,戴副黑框眼镜。女孩贴在他怀里,齐齐的刘海挡住眼睛。他们穿着松垮的校服,背红蓝荧光情侣书包。天色逐渐暗下来,他们搂得更紧,品尝佳酿般没完没了地亲吻,仿佛到了世界末日。
孙力黑着脸忍了很久,终于在收工前大喝一声:“嗨,那两学生该回家了!”女孩扭头剜了孙力一眼,继续揪着男友的衣领窃窃私语。孙力喊:“你家的菜凉了,你妈的心也凉了!”引得四面路人注目。女孩羞愤难当,拽着男友匆匆离去。男孩回头冲孙力竖起中指。
邱兰说:“你又狗拿耗子。”
孙力振振有词:“就是管闲事的人太少了,社会风气才这么败坏。”
邱兰把水杯和旗子收进绣花手袋里。孙力说:“小包儿够精致的。”邱兰让他猜猜多少钱,他竖起两个手指头:“二百?”邱兰乐了,那是她边看电视边做的小活计。她最新的作品是个暗红色的布艺钱包,一针一线格外用心,完工后感觉稍有点单调,便打算在拉锁下方绣只小猴子。
孙力说:“今儿我没骑车,跟你溜达到四季青坐车去。”
两人并肩而行。孙力一改往日大步流星,慢悠悠地陪她走。邱兰问:“小翠怎么样了?”孙力说:“还怄气呢,你劝劝她。”邱兰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呀。”孙力嘿嘿一笑。
路过“食八方”,孙力突然停下脚步说:“咱顺便把晚饭解决了吧,省得回家开火。”
邱兰有点不知所措,支支吾吾说女儿一人在家呢。
孙力说:“一大活人还能饿着?到了咱这岁数,也该为自己想想了。”说罢,推开餐馆玻璃门。
他们选定里侧靠墙的座位,点了鱼香肉丝和香菇鸡饭。孙力要了瓶青岛啤酒,尽管邱兰直摆手,还是坚持给她倒了半杯。邱兰悄悄给女儿发短信:我到你马阿姨家坐坐,你煮点面条吃吧。
一有顾客进来,邱兰就惴惴不安地往门口张望。几口酒下去,灯光的色泽似乎更加柔和,邱兰也慢慢放松下来。
孙力说:“家门口的馆子早就吃腻了,以后咱开发一下四通桥附近的美食。”
邱兰喜欢听他说咱,带着北京味儿的干脆和温暖。
两人东拉西扯了一阵,邱兰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向她最好奇的领域,你怎么会一个人?
孙力沉默了片刻,说:“那家伙有模样儿,还能唱两嗓子,在歌舞团干过几年,跟他们书记好上了。我一直蒙在鼓里,书记老婆闹上家门才知道。离呗。她在单位呆不下去,跑广州做生意去了。那时候儿子才六岁,头几年她还给孩子写写信寄些玩具,后来就没音了。”
邱兰问:“你不恨她?”
孙力笑了:“我他妈气吐血了,估摸少活十年。后来我才想明白,那家伙就算给你生八个孩子,也不会跟你踏实过日子。她就是那样一种女人,眼睛永远瞅着窗外,心里跟有盆火似的。”
聊完那家伙,难免谈起邱兰那口子。
“他脾气好,结婚28年没跟我红过脸,还做得一手好菜。五十岁生日刚过,他嗓子疼得厉害,吞咽困难,一查就是喉癌,拖了半年,受尽折磨。他走了以后,我做的饭女儿吃不惯,所以营养跟不上,孙子也没保住,我真是没用。”邱兰哽咽了。
孙力闷头喝了一口酒。
消失一周后,马小翠神清气爽地回来了,辫子上扎了朵玫瑰花,腋下夹着本歌谱。原来她加入了葵花合唱团,每天上午十点在玉渊潭公园排练。
“我们指挥特有气质,以前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我给他露了一嗓子,他立马让我站到高音声部第一排!”马小翠兴奋不已。
孙力说:“有空我和邱兰给你捧场去。”
马小翠说:“择日不如撞日,明天是周六!”
孙力悄悄问邱兰:“我一高兴就答应她了,明儿你能去不?”邱兰笑而不语。孙力说:“到时给你闺女烙张饼挂脖子上。”
“讨厌。”邱兰说,“你自个去吧,加入低声部,你俩儿一对金嗓子。”
孙力说:“人家都有著名指挥家了,我得带个伴儿,不能当灯泡啊。”
邱兰说:“带个心脑血管专家多提气呀!”
孙力一愣,笑道:“蔫儿坏!”
邱兰很多年没跟人逗贫了。女人撒娇的天性似乎在体内悄然复苏,带着微微发痒的欢乐,让清冷的秋风有了一丝醉意。
他们约好明天上午九点在公园门口见面。接下来的时间,她一边指挥车辆,一边思忖着该穿哪件衣服。网眼衫太单薄,新买的棉服太厚,风衣又做作。鞋子同样让人头疼,皮鞋走路多了脚疼,运动鞋不好配衣服。她决定晚饭后拉女儿去逛商场,买双坡跟休闲鞋。
匆匆赶回家,邱兰觉得不对劲儿。屋里没开灯,地上扔满纸团。女儿躺在床上,脸轻微浮肿。拉着她问了半天,女儿才说老公有相好了,一个四川女人。她发现他用支付宝给那女的买过首饰。
邱兰问:“他承认吗?”女儿说:“我们刚吵完,我说离,他说好。”
邱兰傻了,不相信这种电视剧和八卦杂志上的事会发生在自己家里。她给女儿拿了条毛巾,把她搂在怀里,真希望她又变回小小的婴儿,可以用自己的臂弯为她抵挡一切伤害。女儿哭累了睡去,睡醒了又哭,不知道怎么熬过的一夜。天蒙蒙亮时,邱兰收到孙力的短信,说今天风大,嘱咐她出门穿厚点,戴上帽子。她心里一阵酸楚,这是她人生中最无奈的爽约。
邱兰买了女儿最爱吃的基围虾,做了一桌菜叫她起床。女儿懒懒地靠在椅背上,不动筷子,开始追溯老公出轨的种种迹象。上个月给同事替班去了两趟成都,好几个晚上没接她的电话,回来后行李箱里多了新的睡衣……她断定是因为没有孩子,他精神空虚,才会渐渐离她远去。回到这个沉重的话题,她又泪水涟涟。
邱兰理不出头绪,只觉两肋胀痛,对女婿充满了怨忿。无论如何,他不该在女儿最虚弱的时候叛离。墙上的钟表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正午十二点。这时候,马小翠应该已经练完歌了,孙力还在公园吗?
家里电话响了,邱兰接起来,是女婿。他说到广州了,刚下火车。邱兰恨不得劈头盖脸责骂他一番,嘴里却客客气气地说了句注意身体。女婿抬高嗓门,让你女儿找点事儿干,省得吃饱了撑的胡思乱想!即使他用教训的口吻对她讲话,邱兰仍然无法还击,一方面源于她骨子里的软弱,一方面她在试图维系他和女儿的感情。毕竟,这不是她的儿子。儿子骂完还是儿子,女婿骂完可能就是仇人了。如果女儿婚姻破裂,她们就真成了一对孤儿寡母。
城市越大就越脆弱,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几乎让路面陷入瘫痪。公交车姗姗来迟,且辆辆超载。天黑了,冷风飕飕,小小的站台积压了很多乘客,还不断涌入避雨的行人,弥漫着烦躁不安的情绪。
在这样的夜晚,连孙力和马小翠的大嗓门也被淹没在滂沱的喧嚣中。只要来一辆车,人们便蜂拥而上,拼死拼活也要挤上去。被伞尖儿戳痛的,踩着脚的,衣服蹭湿的,骂骂咧咧,连推带搡。
孙力阔步走出站台,立在一辆被层层围堵的101前门口,举起大黑伞,给一位正在奋力登车的男子遮住了雨。邱兰也走下站台,用打蔫儿的小旗子指挥大家排队。路面上积水很深,她的胶鞋湿透了,冰冷的袜子缠着麻木的脚趾。乘客们陆陆续续排成一条长队。
孙力指挥车辆尽量靠边停,这样乘客就可以从站台直接迈入车厢,而他一直给他们撑着伞,半个身子浸在雨中。有人上车后把自己的雨披送给他,他转身就给邱兰套上。像一个突如其来的拥抱,邱兰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就被裹住了,连帽子都严严实实的戴好了。虽然只是薄薄一层塑料,但是挡住了刺骨的寒风。再定神看他,还是撑伞的动作,胳膊举得那样高,嘴唇微青,竟然有点英勇就义的感觉。她想哭。
七点半,马小翠的老公开车来接她,让邱兰一起搭车回家。她执意不肯。她知道像这样的天气,晚高峰会持续到八点半以后,而孙力不等到站台寂静是不会离开的。他那股认真劲儿让她无奈,也让她心疼。马小翠意味深长地看看邱兰,又看看孙力,细声细气地说那你俩儿相依取暖吧。
幸亏天黑,邱兰的脸烧到耳根。孙力倒没在意,跑去吆喝伺机停靠的黑车了。
雨停了,天空变得舒朗,站台的人也渐渐少了。孙力宣布收工,陪着邱兰走到家门口。她一点都不冷了,湿透的双脚微微发胀。她把雨披脱下来,用袖子擦掉上面的水珠,折成小方块,塞进孙力的挎包里。他们面对面站着,说了好几声再见,可谁也不动。
孙力说:“你回吧,好好睡一觉,明早不用着急上班。”
邱兰挥挥手,就上楼了。女儿在洗澡,从浴室里传出歌声,看来心情转好。邱兰走到窗边,发现孙力还在楼下,坐在小区的石凳上歇着呢。她有种预感,这时候她再下楼,她暗淡的生活就会改变。她涌起十八岁的冲动,但没有那时候的勇气。她揪着窗帘,陷入低烧般的恍惚中。
“妈,帮我拿浴巾!”女儿清脆的声音将她唤回现实。
“你们到什么程度了?”马小翠逮空盘问邱兰,一面上下打量着她,“原来你是闷骚型的。”
邱兰无从解释。谁会知道,她目前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孙力逛一次公园。
前一阵老有雾霾,后来又阴雨连天。好不容易天儿好了,又感冒了。下周吧,下个周末去玉渊潭走走,瞧瞧马小翠唱歌去。从深秋到严冬,她跟孙力一次次约定着。阳光好的话还可以划划船,公园北门新开了家巫山烤鱼,据说味道不错。孙力不断充实着计划,让她充满期待。
元旦前夕,邱兰破天荒一个人到岗。
七点钟,乘客明显增多。邱兰两个站牌来回跑,气喘吁吁。孙力平日一向来得最早,难道今儿病啦?马小翠迟到几分钟不奇怪,她儿子元月结婚,现在正忙乎着呢。邱兰和孙力早就收到了婚宴请柬。邱兰跟他商量份子钱,孙力说咱俩儿还用分着给?说得她脸红心跳。可惜她精心缝制的布艺钱包被女儿抢去了,要给女婿当新年礼物。孙力的本命年生日怎么办呢?她决定给他织条红围巾。
过了七点半,马小翠从过街天桥上走来,步履有点凌乱,不像往日那么轻快。奇怪的是,她还戴着一副茶色眼镜。
邱兰的胸口被箍住了。
走近了,马小翠眼瞅着别处对她说:“老孙没了,心肌梗。昨晚跟几个哥们喝点酒,到家就不行了……”
邱兰突然想起丈夫去世的情景,医生默默摘下伴随他痛苦挣扎数日的呼吸机,他平静得像一条冰柜里的鱼。耳边似乎又传来女儿流产后的哭声,说孩子没了。没了,就是彻底隔绝,没有温度,也没有回音。无论你如何抗拒,这一页从你生命之书中翻过去了,天知道再翻几页就到头了。等自己没了,那些重重叠叠的悲伤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日头已经升高,街道上依旧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一辆不堪重负的公交车缓缓驶来,邱兰举起旗子:“101进站,请大家先下后上,不要拥挤!”
(责编: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