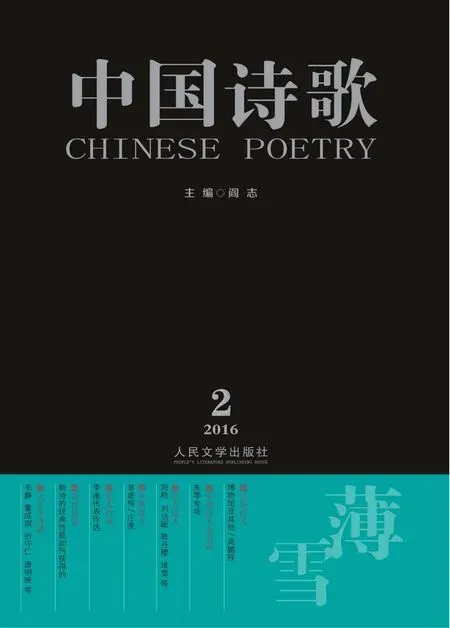博物馆及其他(组诗)
□高鹏程
头条诗人
博物馆及其他(组诗)
□高鹏程
刀剑博物馆
时间带来了锈迹。
也洗净了血迹和仇恨。
马放南山。鸟尽弓藏。刀剑
进入了博物馆。
用柴薪铺作它的展床。
悬黑熊胆以为灯。
黑暗的剑匣中,一柄剑收敛了它的锋芒。
承影、纯钧、鱼肠、湛卢、干将、莫邪之外
有过另外几把绝世的刀剑:
一把曾在越溪浣纱,另一把在温泉沐浴
另外两把,曾经让月色失去了光芒
让凌空的雁阵,忘却了划动翅膀……
刀剑无辜。它们
以人心为鞘。以人的胆魄、贪婪和私欲
作为它的锋芒
它们都曾是光的主人。而现在
它们是黑暗的囚徒。在我们身体
某个隐秘的角落。一个枕剑昏睡的君王
化装成盛世的书生
一个忧郁的女子
从一柄寒芒上,照见了自己的前世
海盐博物馆
首先需要以阳光的名义,让海水和晒盐人
经历双重的煎熬
纳潮。制卤。测卤。结晶。归坨。终于
多余的水分消失了,晒盐人
交出了皮肤里的黑
而大海
析出了它白色的骨头。
无需青花和白瓷
陶罐、卤缸以及任何一种寻常器具
都是盛殓舍利的佛塔
由此,人间有一种至味被称为清欢
有一种日子被叫作清白。
而更多的事物还将因此被
一再提纯。
海水平静。曾经的沸腾冷却了
那些结晶的事物,
将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眼眶中的咸,骨骼中的釉色以及血液中的黏度
茶叶博物馆
其实,只要一只青瓷盖碗或者
一只紫砂陶壶就够了。
无论红茶绿茶,还是乌龙普洱
核心的关键词
都只是同一个:煎熬
最好的,来自春风唤醒的
最嫩的芽尖:雀舌、旗枪、鹰爪
从来佳茗似佳人
这是不是说,一只紫砂壶内浸泡的
就是一位受难的少女?
壶内的人在煎熬
壶外的人,在清谈、阔论,并且把壶内的沸腾
听成了满山的松涛。
把一缕春天的芳魂
听成深秋的气象
世事大抵如此:
熄灭的炉火。凉掉的茶
这是个简单的比喻。但可以继续延伸
一片神奇的东方树叶,暗含着更多
古老的辩证法
它是生活的。也是宗教的。
是茶禅一味。也是澡雪精神。
而灵魂的香气都需要干枯的肉体为代价
而重新唤醒它的,同样是
又一次的煎熬
沸腾之后,同样会有人,嗅着香气慢啜细饮
直到炉火熄灭,人走茶凉
直到杯底露出残山剩水
我说的也许是一个女子的香消玉殒
我说的,也许是一个王朝的荣枯兴衰
蝴蝶博物馆
它曾在一个西方诗人的诗行里跨海飞行
作为某种神秘的力量之源
它果真策动过一场遥远海岸的风暴?
它脆薄翼翅上闪烁的
粉末,用来提供女巫制造的蛊毒迷幻剂
构成了一个未来诗人眼中世界的幻象
而在东方古老的传说中,它之所以能够
化身为爱情
在于它的轻盈、美丽,看上去
更加接近灵魂
或者它只是灵魂
蜕去了肉体的丑陋和生活的沉重
蝴蝶飞舞。
在某个具体的故事中
它们曾经替一对死去的情人,驮起了两扇
沉重的爱情墓门
蝴蝶飞舞。
炫目的光斑里,有迷幻的图案,也有
枯叶一样的纹理
——莫非灵魂也会黯淡、枯萎?
现在,这些飞翔都是静止的,
肉体消弭了
灵魂也凝固在一小片玻璃里,
它来自天堂?
一束薄薄的光打过来,这使它们看上去更加接近某种真相:
那薄如蝉翼的想象
带着死亡的甜味
油漆博物馆
我熟悉这危险
而古老的职业。它们的痕迹曾经出现在七千年前
一只木胎漆碗上。而接下来的所有历史
都可以概括为一部髹漆史
他们作为漆匠的身份不停地变化:伶人。乐伎。附会在
帝王和权贵帐前的翰林、门客、幕僚、史官
他们使一个时代
看上去更加光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
披着华丽光泽的文饰,替代了历史真实的书写
但他们,并不属于其中的部分
一具棺椁髹漆之后,一个漆匠成为众多陪葬品之一
一个强盛的王朝背面
一个史官受尽宫刑
一曲羽衣霓裳幕后,是一个诗歌天才黯然的身影
当无数王朝湮没于荒草古丘
一只汉代朱砂木碗
一件唐代金银平脱镜盒、一盏宋代素漆茶杯
以及明清家具上的雕漆
依旧鲜亮
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些文过饰非的花纹
帮助我们恢复了对于历史的想象
一个古老的职业。在今天,依旧有着
强大的生命力
如同眼前船厂里的一群,继续在数十米高空里涂抹着一艘大船
他们被普通话改造过的方言,混合着吸进喉咙里的漆气
听上去五颜六色
生动、鲜艳,却又充满毒素
午休时他们沾满油漆的身体
躺在巨大船体的阴影里
看上去
更像是一个白日梦,与高大船身构成的某种隐喻
耕泽博物馆:石头的表情
这是石刻的字:仁、义、信、忠、孝、礼
它们同样在另一些地方被镌刻。
这是石刻的鼓:坚实。厚重。
但都不再被敲响。
这是石刻的碾子和磨盘:无论物质还是精神,要成为粮食
都需要经过反复的碾压和磨砺
这是石头的猪槽,长满了碧绿的铜钱草
这是石头的拴马桩,它的根基深埋于土。据说
跑得最快的马,需要埋得最深的石桩才能拴牢。
这是石头的墓碑,一生的苦痛不过是石缝里
几个不曾刻出的字
这是石头的狮子:汇集人间百态,嬉笑怒骂,都是人的表情
如何分辨它们?据说
最能代表江南石雕技艺的狮子,都长着一张哭脸
我感叹于这匠心的隐喻:再吉祥的寓意里,艺术的意义和生命
都源自于生活
一场又一场悲剧
居家博物馆:木居年代
这是木质的建筑、栏杆和回廊。
质朴、简单。散发着久远年代
居家的味道
这是木质的书桌。
木质的纹路里
凝固着一个古代书生,一生的波澜。
木质的窗格下,有孤独燃烧过的红烛
和窗外
很远地方传来的尺素
这是木质的床。
有过生活真实的喘息、摇晃和梦呓
现在,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木质的门板上,有漂亮的木雕
精湛的刀法下
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被雕琢,被镌刻,被再现
成为时光真实的见证
在居家博物馆,我们消耗着半个冬日午后的时光
然后,我们在矮下来的黄昏和屋檐下
吃农家饭
我们吃白菜、豆腐,猪头肉,那些久远的外婆家的味道
我们喝茶——
这是青花茶盏、这是洋铁煤油灯
昏黄的灯光下,一位老兄执起了久违的毛笔
这古老的书写,能够把我们带回纸片后面的另一座家园?
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当这木质的生活,
成为博物馆里被展览的对象
成为我们这些从钢铁、玻璃和被过度消费的数码世界里
逃离者的
最真实的渴望
这是否说明,我们此刻
只是另外一些标本和行尸走肉
活在未来目光的展览里?
刺绣博物馆
她们耗尽了一生。
在一面薄薄的丝帛上
除了金线、银线,还有没有第三种线?
这需要从一根纤维深处去谛听
需要从一朵桃花的红
她们咳在缎面上的鲜血中去仔细分辨
挂在墙上的织锦
平坦。温顺。闪着柔和的光泽
背面,是无数线头打成的死结
我觉得,那里面,肯定藏着机器和时光
所不能理解的东西
但她们并不试着去解释。而是继续
把身体微微下倾
哦,这些指间的舞蹈。缎面上的芭蕾。随一根
伶仃的银针翻飞的光。偶尔
它们也会停下来
这时候,它们肯定和某些词语的疼
有了幽暗的牵连
一枚刺破手指的针。和它带出的丝线
逐渐
走向了丝帛之外
船模博物馆
他的胸腔里藏着一小片汪洋。
一个微缩了的大海。依然有着比实际海洋
更为广阔的疆域
他用废弃的船木,造了一艘又一艘船模
从绿眉毛到机帆船。再到渔轮。战舰。商船。
白天他耐心地给它们安置好龙骨,桅杆和帆
夜晚他驾驶着它们远涉重洋
从泉州到印度
从宁波到遥远的东非海岸
最隐秘的航线,驶向一个不为人知的港湾
那是真实的。当他
从夜半或清晨醒来,额头还留着触礁的痕迹
来自海上的风暴与挣扎
纽扣博物馆
结绳记事。
最早的纽结显然与美无关。与爱情
或者风月无关。
直到纽扣出现。直到作为纽扣的绳结把美
和隐秘的香气扣进她的身体
丝丝入扣。
她腰肢间的柳色,身体里的春水
都被胸襟和领口的几粒纽扣牢牢扣住
一双想象中的手,总是试图探向美
和原罪的部位。
但它们
只向更深的夜色敞开。
向更隐秘的,懂的那双手敞开
“不懂的,永远解不开。
尤其是,那看不见但肯定存在的第二粒纽扣”①引号内借用娜夜诗句。
现在,身体消失了。但爱情
依旧打着死结。
空荡荡的旗袍下积满了夜色
一把生锈的锁。一座衰败的秘密花园
断章:有关长城的长短句
1
……现在,它能否被我想象成一条在山岭晃动的扁担?
一个习惯负重的民族,一头挑着山海关楼头的一轮落日
另一头,担着嘉峪关檐角的一弯残月
如果再从更远一点的位置打量,它只是穿行在汉装和胡服
之间的一根丝线
破绽处,是几粒风化的纽扣
嘉峪关:祁连山上的一粒无法扣紧的风雪
山海关:衣领下的一滴化不开的泪痕
2
冷兵器时代的奇迹。在今天
沦为一件装饰品
这是一个游览长城的时代。一个
似乎谁都可以把它踩在脚下,并且再跺几下脚的时代
八达岭上
一块被无数鞋底磨成镜面的地砖
映照着一张张因头轻脚重而变形的身影
3
你见过一条能在山脊上蜿蜒、奔涌的河流吗
你见过一座一万里长的
墓碑吗?
你能体会到一滴祁连山上的雪水抵达东海时的呜咽
和疼痛吗
沿途,那些流水和亡魂的身影
都变成了方形的水滴,凝固在了它夯土筑成的河床里
4
如同眼前的这一截残垣
我们看到的长城
只是它的残骸和遗址
这座由砖石、强权、雄略、血肉和白骨砌成的建筑
肯定还有
另外一种存在的形式
也许,它只是
史书上一个长长的病句
不符合语法,更不符合逻辑
只适合抒情。
沉郁、悲怆、愤怒的抒情
但它们最终,都置换成了一声苍凉的叹息
5
“北方有佳人,一笑倾人城
再笑倾人国”
事实上,如果能回到古代
我同样愿意我的女人
再次点燃一炷狼烟
我愿意为她再一次遗臭万年,得罪所有的道德
和核心价值观
事实上,两千多年了,有关长城最动人的描绘
依旧由以下几个词语组成:烽火、诸侯、美人、倾城
她回眸一笑的瞬间,山河摇摇欲坠
就连充血的落日也黯然失色
6
那些马蹄没有压住的
被一轮大漠的残月压住
那些青砖没有封住的
被一层褐色的苔藓封存
只有一炷狼烟,支撑着帝国边塞倾斜的天空
只有几行砖石一样
方块的汉字
固守在一个民族因溃疡出现的豁口
抵御着精神异族的入侵
7
写了这么多,该用怎样的比喻来描绘这道残损的
让我们熟视无睹的
让我们面临尴尬避而不谈却又永远无法绕开的
拙劣的、伟大的墙?
它既是一条刀疤
也是一道焊缝
它是帝国的边境
也是一首诗的核心
但同时也可能是它们的起点
套用一句话:我们看到的辽阔,只是辽阔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的长城,也只是长城的一部分
8
也许,长城早就流往别处
它在另外的地方,建筑自己的领土、尊严和荣耀
它在某种境遇的最低处
建筑自己的高度
缓释胶囊
早些年前,我挑选最重的词语熬炼药丸
我磨制汉语的锋芒以期让它
变成一把手术刀。
我受困于病痛的折磨并试图自救。
是的,为了感知生活我不惜站在对立面和它
狠狠相撞
我收集钻心的疼痛并且让自己觉得
我就是世界的伤口
但事实上,在这座南方小县城里
我的生活琐碎、细小。
我的经历也是。我的每一份爱恨、悲伤、愤怒
都是如此细小。小如针尖、小如尘埃
这么些年,我的伤口逐渐向内生长
我用沉默包裹着它
——以前,我以为诗歌是一帖猛药
现在,我希望它是一粒
缓释胶囊,为自己和生活的隐疾消炎
县城:世相之一
如果你愿意
在夜晚,踅进任何一家酒楼、KTV
你都能看到觥筹交错和一掷千金
如果你愿意
可以在它附近的街巷里
看见坐等生意的黄包车夫、百无聊赖的出租司机
昏黄路灯下瑟瑟发抖的
卖茶叶蛋和馄饨的中年妇女
如果你愿意再等一等
在凌晨2点,那些从KTV走出来的年轻女郎
蹲在新华河边,用手伸进喉咙
呕吐出尚未消化的洋酒
然后拐进隔壁的小摊,双手捧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灯红酒绿和微黄的路灯
照到的其实都是,生活的真相
从不值得惊讶
遥远的,亲爱的
我固执地给我抒写的对象,都加上这个修饰。
仿佛这样,就可以把
身边的事物推远。把远处的
推得更远
一直到达,想象的边缘
近处无风景。近处
也没有我的所爱
这些年,我虚构马匹、船帆、一匹骆驼或者
一只瘦小的蚂蚁
仿佛这样,才能把自己从生活的泥淖中拔出
仿佛
只有遥远的,才会是亲爱的
那些近乎虚幻的
从来无法抵达之处、之人、之事
那一滴海水中的殿堂
一粒沙子中的庙宇
哦,那些沉默的沙丘和波浪的言辞无法说出的
遥远的、沉默的天际线
遥远的沉默的嘴唇
牛皮信封
它装好消息。也装噩耗。
朴素年代里,它装一个人一生的承诺。
它有泥封的唇印
铜、铅和锡押盖的火漆
它装闪电、爱情、连天烽火里抵得上万金的
老母妻儿的嘱托
灯火昏黑的驿站或者
荒烟蔓草的古道上
彻夜响着的马蹄
有时候,它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它包住秘密的火。交通站、暗语。穿过幽暗雨夜的
匆匆的脚步。绿皮火车。模糊的车窗,一闪
而逝的身影
哦,曾经
它装着另一个我试图敲开这个世界大门
一封过去的牛皮信封里
有我所有
对于远方的想象。
但这些
都过去了。现在,它被一根光纤拉下了马
现在,它更像一个时间的棺椁
瘪下去的空壳
比人世空虚,比人情更加凉薄
熬药的人
他习惯在夜晚干活。习惯把满怀忧愤
和黏稠的夜色一同倒入砂锅。
像一个熟练的药剂师,
他熟悉每一种药材的属性
也懂得火候的把握
此间不同的是,他使用的药材,采自
古老的诗经。那些前世的草木
带着山野和汉语的芬芳
他小心地收集它们,安排其中的起承转合
仿佛用恰当的火候
转化一服汤药中的君臣佐使
夜色太浓,也许
还需要加入三克泪水,七钱淡薄稀释
胆汁太苦,
有时,还需要加入更多的热爱作为蜜炼
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他熬灯泡里的钨丝,头发里的黑
他熬炼着这些汉字的药丸
直到鬓角和天色一样稀薄、发白——
当更多的药被取走,作用于这个世上的某处病灶
熬药的人
形销骨立,像一堆被榨干的药渣
起初与最终
起初是你涨满绿色血液的手指
擦去了我脸上的积雪
最终是一根枯枝,拨开我墓碑上的落叶
让凝固的大理石,露出新鲜的凿痕
起初是一根新生的光线,
唤醒地下沉睡的蛹
让白蝴蝶的翅膀,在一朵豌豆花上掀起涟漪和风暴
最终是陈旧的雨水,
洗净了人间恩仇
一阵晚风,带来了永世的安宁和沉沉的暮霭
起初……最终。中间
是广袤、狭窄。是疼痛、麻木、缠绕。是纵有万千语。
是茫茫忘川……
当最后一粒
人间灯火被带入星空
死去如我者,也如静默的山峦微微抬起了头颅
在大港头谈论乡愁
一个宁静的小镇。一条江水穿镇而过。
村口,几个闲散的人。一棵古树。一个埠头。流水
晃动着一些古老或者
新鲜的光阴
伊甸说,这个村口,符合中国人
乡愁的理念
我扭头看江面,看山气。又看村口。然后
点头称是
这乡愁忽焉似有。但很快会转浓。如果有人从这里走出。很多年
如果山岚转淡,江面上的雾气
能散去一些,如果那艘来接我的船已经抵达埠头
当然这乡愁也可能会更浓一些,如果上面的第三
到第四行诗是这样:一些新鲜的日子正在老去,或者
已经古老
如果这乡愁要刻骨铭心,那么上面的第一
到第二行诗
要这样写:埠头下的船
已经走远
江水继续流淌。村口,只有一棵老树。已
没有人
在磁窑堡废墟里审视一只陶罐
很显然,它和鼓腹的女人有着天然的隐喻
它腰腹间的纹饰
和妊娠纹并无区别
它喝鸳鸯湖的清水
就怀孕清水,就会为我们产下清洁的日子
她怀孕谷物,就会产下东塔、临河、郝家桥
和更多的子嗣
它喝黄河的水和泥沙
就会孕育黄色的种族、血脉
就会产下兴庆、兴武、中原、西夏……一条
更加斑驳的河流
它怀孕盐,为我们产下白色的骨头
就会为我们血液
和泪水的浓度提供保证
现在,在磁窑堡的废墟里
她怀孕一坛空虚
——嘘,安静点
她就要为我们产下方圆数百里的辽阔和寂静
清水营
清水营里已没有清水。也没有营
但肯定
曾经有过。
能够想象的场景是:一场数百年前的鏖战
战事惨烈。到最后,作为敌我
双方的军士都已精疲力竭。
焦渴的嘴唇
死死盯住了营口内最后一罐清水……
人头落地。
清水洒落。一场时间的风暴迅疾
而缓慢地席卷了整个营盘
……若干年
清水营,
虚无的营盘内依旧蓄涵着一罐虚无的清水
豢养青草,白云的嘴唇以及
时间的马匹
又若干年后
我和诗人杨森君一行再次到来
两个男人惺惺相惜,但他们的眼眶内
也不会滴下清水
而当他们离去
清水营的清水,并不会多出两滴
当然,也不会因此少去
薄雪
一场发生在春天的落雪是否说明
这个世界上依旧有没有被寒冷填满的缝隙?
而它的薄,是否意味着它是
最后的冷?
雪落到屋檐下,人世间的苦难被压得更低。
落到屋内的酒桌上
代替一杯薄酒衡量着人情的温度
雪落进山野,一个一直沉默的人
微微抬起了苍茫的额头
它骨骺内的雪线同样在缓慢地抬升
雪落进一棵白杨树的体内
雪落到电线上
这带电的事物出现了一阵些微的战栗
像我乡下的穷亲戚,眼神里闪过的
最后一丝寒意
时光考古——与万俊诸诗友一席谈
早年的爱情诗人,现在痴迷于考古。
貌似巨大的反差里,其实有着
某种必然:世间多数爱情,到最后
都会像某个遗址。相关的人和事大都下落不明。
这个下午,我们谈到黑风寨。花马池。以及最后
一批党项人的去向。
一个强悍的种族忽然消失了。连同一些神秘的地名
一处古老的宅院。弥漫的荒草,超过
几人合抱的古木
在说到一个隐秘洞窟时气氛
有些凝固
——时光也许是最严密的封土但也可能
存在着盗洞。但我们
可能都是些失败的考古者:一个
王朝陷落了,留下的蛛丝马迹也难以考证
而我们卑微、单薄的个体,更加无足轻重
如同眼前的一堆宋代铜钱,
它们被一根绳索串起的
共同的命运已经各自散落
如同你曾挖出的一窟糜子,重见天日之后
外表保持着新鲜的金黄而内部已经被时光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