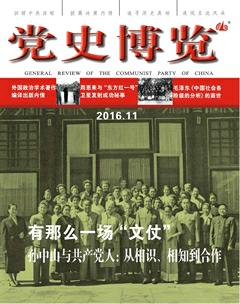国民党与《野百合花》事件
卢毅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全党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旨虽在解决中共党内的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影响,但延安文艺界的动向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亦是他密切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作为始终潜在的对手,国民党的态度和反应也是毛泽东考虑整风部署的重要外部因素,甚至由此改变了整风运动的进程。关于“王实味案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毛泽东对“王实味案件”的认识变化
1942年3月,全党整风开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就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并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写了三篇短文,批评延安领导干部中存在特权主义和忽视民主的倾向。这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毛泽东对此也颇为关注。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看了《野百合花》后曾拍桌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立即打电话要求报社做出检查,后来又强调:“《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而在挑灯夜读《矢与的》墙报后,毛泽东更断言:“思想斗争有目标了。”
不过总体来看,毛泽东最初还只是将之视为思想问题,并未与组织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尽管他在1942年4月初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曾指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但这里仍主要是批评王实味具有“托派”思想,尚未做组织上的结论。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转告王实味,希望其“改正错误立场”。5月28日,毛泽东又在高级学习组会议上明确表示: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他还特别点到王实味:“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此仍然称王实味为“同志”,而且只是批评其思想问题。他还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对被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
这些迹象似乎表明,毛泽东此时仍想挽救王实味。
到了6月份,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王实味被打成了“托派”分子。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他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这显然已是在组织意义上言之,而非仅限于思想问题。10月,中组部和中央研究院党委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原先的判断,将王实味问题从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今天看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康生直接介入所致,但另一方面或许也与当时国共关系的紧张尤其是国民党对《野百合花》事件的炒作不无关联。
国民党对《野百合花》事件的炒作
1942年4月,国民党开始积极准备进攻边区。针对这一紧急情况,毛泽东在5月19日写了一封信,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直接送给胡宗南,内称:“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与此同时,为防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央加强了军事部署,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毛泽东还告诫大家,无论什么时候对国民党都不要放松警惕,要提防内奸,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
恰在此时,外界舆论开始对《野百合花》事件做出了一些反应。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的李言回忆,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便在中央社会部干部大会上透露:王实味的《野百合花》4月就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了。李言还分析:“王实味的文章在香港的报刊上登载,中央当然很注意。康生在这时实际上就已经认为王实味是敌我性质的了。”并说:“这次会议以后,我为了解王实味的历史情况,到中央组织部去看王实味的档案。这才看到了他自己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的关于同托派关系的材料。”这说明外界的有关舆论已引起康生等人的关注,并由此联想和怀疑到王实味的身份,最后通过查档案牵出了所谓“托派”问题。
相比于香港,国民党对《野百合花》的反应较为迟钝,最初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延安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李维汉、张如心等人在1942年6月份的《解放日报》上发文提及:“《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他的言论和行动已经为反革命、反共分子所赞扬,所欢迎”,“《野百合花》之类东西,到了反动派手中,竟如获至宝似的,把它广为翻印,大事宣传,这件事情,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些论断应当是源于康生对香港舆论的捕风捉影,并没有国民党方面确凿材料的佐证。
事实上,恰恰是延安对王实味展开大规模批判才引起了国民党有关部门的警觉。从1942年4月7日至7月29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齐肃、杨维哲、罗迈(李维汉)、金灿然、范文澜、李伯钊、陈道、蔡天心、陈伯达、丁玲、周扬、张如心等人撰写的18篇文章,对王实味大加批判,其中多篇又于8月份被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机关刊物《群众》周刊转载。这自然引起了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宣传部门的高度关注。
1942年9月19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三科签发了一份第1972号密函,内称:“查昨日送审之《群众》七卷十五期中有范文澜《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及周文著《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两文,细核内容,觉共产党内部中又已因思想问题发生纠纷,谨附审查报告呈核。”这份密函是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亲自撰写的,呈报中央宣传部三民主义研究会、军事委员会党政联席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和中央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等重要机构。该函还明确建议由中统进一步调查,“拟请转函调查统计局详查王实味在共产党中之地位及其有关之各项材料,如能将《野百合花》等文觅得一份,则于研究之进行更有莫大之便利”。很明显,潘公展等人此时尚未获见《野百合花》原文,故亟欲觅得。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中统确实对此事相当重视,立即组织人手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一书,由统一出版社在1942年9月发行。曾任中统局本部科长的张文回忆:“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煌等编定了《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一书,其中除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
在此之前,一个署名邹正之的人已捷足先登,在重庆翻印出版了《野百合花》。该书标明6月初版、8月再版,不过其序言的编者落款却是7月,故初版时间应在7月之后。8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编的《民族文化》月刊亦将《野百合花》作为“延安文献”全文照录,并介绍说:“延安的作品原是难得在本刊上见到的。只因为这是在延安里发出的正义呼声,我们该使它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转载过来。”此后,国民党不满足于转载,又开始增添了许多评论。9月和11月,《新认识》月刊与《文化导报》分别发表了《闲话“野百合花”案》《我读完了〈野百合花〉》二文,对这一事件加以热议和炒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宣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也对《野百合花》事件做了连续报道,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案详情》《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等文,甚至还专门刊发了一期特辑《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并附编者按:“轰动延安的野百合花事件,本刊曾略有报道。兹有友人转赠《野百合花》全文共五节,同时在最新一期《群众》上看到范文澜先生《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因得窥野百合花事件之全豹。为使读者亦能共赏此项传诵一时之文件,特转载其全文。……两文原载共党机关报,本刊不欲有所评论,请读者自定其是非曲直可也。”
由此可见,《野百合花》事件在当时的国统区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轰动效应。时人曾描述说:“近来有所谓‘野百合花事件的传说,喧腾众口,形诸党报党刊。据说这个事件在延安闹得相当厉害,但在重庆也闹得不能不算厉害了。”而从国民党方面这些书刊的内容来看,大多是借此事件攻击中共和边区。
邹正之在翻印《野百合花》的前言中煽动读者:“《野百合花》,是写着一位中共党员——当然就是王实味先生自己——为了追求光明而踏进延安,在那里所听到的,看到的,身受到的,却意想不到的苦难与挫折……在这件事上,使我深深感到,今日之延安,是否只允许奴性人物的存在,是否定了人性人物底生存权利?我希望全国的青年们,不仅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大家都注意这件事的发展,因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问题,在延安还在展开着,并未告一段落;并且大家都应该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研究,因为这并不是王实味个人的问题啊!”
显而易见,这些文字是具有较强的党派色彩和相当挑衅性的。
对此,晚年力主为王实味平反的温济泽也回忆说:“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国民党炒作的影响
国民党的这些炒作究竟对延安产生了多大影响,目前尚无直接材料证明。从王实味一案的处理来看,延安对其大规模批判主要是从1942年6月开始的,而国民党方面借此事件大加炒作的时间则稍晚于此,是延安的批判已经基本结束以后的事。如《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的作者便说:“最近《野百合花》突然在延安被禁,我渐渐有些奇怪。读到另外一部分人反驳《野百合花》的文章之后,我才明白这件事情的真相。”这无疑说明是延安的批判才引起了其关注。况且,王实味被打成“托派”也是早在6月初已形成定论,与国民党方面的炒作亦无直接关联。邹正之就提到当他最早翻印《野百合花》时,王实味已经“获得了‘托派的天大的罪名”。
不过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康生此时还给王实味扣上了复兴社分子和国民党兼差特务的帽子。康生在6月初告诉延安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王实味是双料的,不仅是“托派”分子,还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这就促使“王实味案件”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这一判断后来虽未正式形成组织上的结论(这除查无实据外,或许也与当时国共关系尚未完全破裂有关,故不宜公开宣判该项罪名,以免授人以柄,被国民党再度炒作),但康生此说可谓根深蒂固、谬种流传,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时隔20年后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提到王实味时,仍称之为“暗藏的国民党探子”。
王实味的特务嫌疑究竟缘何而来,个中详情尚不完全知晓。唯不难想见,在国共关系十分紧张、敌我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由于国统区众多媒体对《野百合花》事件大肆炒作,延安方面极易将王实味问题的性质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联系起来,从而在非公开的场合将其罪加一等。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大会的报告中就断言:“大家晓得王实味是托派汉奸,但更要晓得他同时也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王实味与国特分子纠缠在一起呢?因为他一方面为日寇服务,同时又为国民党服务,他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康生还说:“当我们与王实味斗争时,为什么一些敌探国特不惜揭破了左倾面目,出来为王实味打抱不平呢?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为什么国民党为了声援一个托匪汉奸,动员了他们大后方所有的报纸杂志向共产党进攻呢?因为……王实味也正是国民党的特务人员。”
此间逻辑虽存在着明显漏洞,二者实际上缺乏内在的因果关联,但由此可见国民党对《野百合花》的利用和炒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延安对王实味一案的处理,至少被康生等人所利用,为其提供了罗织罪名和加以整肃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