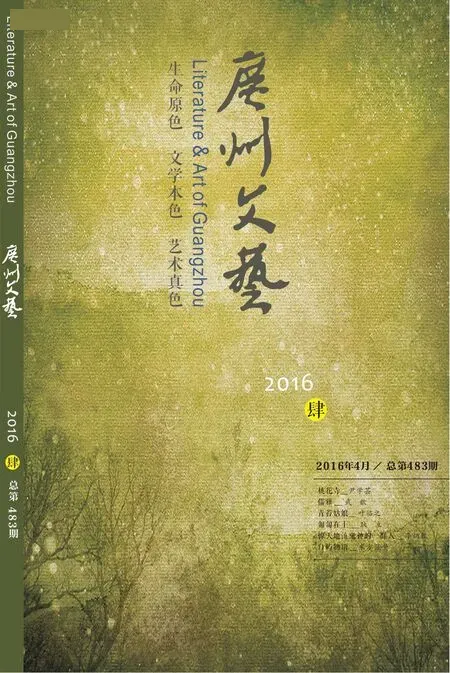带回外婆的心(外一篇)
Text-周伟兵
带回外婆的心(外一篇)
Text-周伟兵
父亲心性颇高,从不轻易赞人,但是他却对他的岳母赞赏有加,多次对我说:你外婆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是最有善心的劳动人民。
其实,论外婆的出身,属于大户人家的独生子女,本来应该是贵如碧玉、娇生惯养的。姥爷的早逝和战火硝烟,改变了她的成长轨迹和人生状态,使她年幼之时就失去了父亲的娇宠,跟着姥姥孤儿寡母地寄人篱下,虽锦衣玉食,却赔着小心捱时光。年少至年轻时连天战火,摧毁了她贵为小姐的身份,她与姥姥在逃难途中彻底沦为难民,一路流亡从湖南徒步到广州,从此天涯为家。人生的苦难,在姥姥和外婆这对母女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姥姥身上明显遗留着大家贵妇的种种作派,比如毕生佩饰品,勤梳妆,重视穿戴,讲究仪表,零食天天吃,珍宝悄悄藏,小脚颤颤挺身立,女红家务均不沾。而到下一代,则家道败落的颓相尽显。外婆不饰粉黛,粗手大脚,忍辱负重;侍母相夫、生儿育女,成天忙得团团转;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愁喜了她整个的生活。在我诞生之时,立于我眼前的外婆,已经是个地道的平民百姓了。
外婆的中晚年,一直在打理着两个家,一个是她自己的家,一个是她孩子的家。这后一个家先是我们家,我们家调走后就成了舅舅家。
外婆在她自己的家主要负责侍母与相夫。她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她一定会在鸡叫三遍前起身,先生火做饭,再放鸡喂鸭,接着洒扫庭院;待姥姥外公起床后,她便去倒马桶,收拾床铺,清洁家中。姥姥外公吃罢早餐,喝茶的喝茶,上班的上班,外婆就开始洗刷碗筷,烧水灌暖瓶,之后,便挽一个竹篮,提一个布袋,夹一把桐油伞,到两里外的集市去购物买菜。这一来一回,是外婆最开心快乐的时光,一路上“张妈妈”“彭娭毑”“吴姐姐”地叫将过去,家长里短、世道时事地聊上几句,让外婆感到了新鲜,领略了情分,丰富了生活。一番讨价还价的买卖之后,外婆提着菜篮急急赶回家,换过煤,便一盆水满桶衣地浆洗起来。而这时,姥姥必是坐在洗衣盆边,听外婆诉说着外出的见闻,满心欢喜。而她们聊的东西,无非是谁家又添丁了,谁家又吵架了,市场的菜价为什么涨了,什么东西又新鲜上市了。偶尔外婆会压低声音,看到四周无人后,说谁谁谁被批斗了,“东风派”和 “红旗派”又在哪儿干了一杖,毛主席又有什么最新指示等等。而这时姥姥是会竭力配合的,弯弯腰侧侧身把耳朵贴近外婆的嘴巴,凝神而严肃地把这些东西听进去,记下来。之后,姥姥会喋喋不休地告诉外婆,芦花鸡生了蛋,麻黄鸡好像要抱窝了,要快点找邻居们换几个交配过的蛋,好让麻黄鸡孵它一窝小鸡仔。晾晒衣服的时候姥姥会帮把手,中午的做饭炒菜她就不管了。吃了午饭后,外婆照例地洗碗刷锅收拾餐桌,待把姥姥打发午睡,把外公打发上班,她便戴上老花镜,静静地坐在门口做针线或编织毛衣。下午的时光外婆比较活跃,总是走东家跑西家地弄来一些衣样,然后在正房里架起门板,铺开报纸,照葫芦画瓢地裁剪出来,然后兴高采烈地坐在缝纫机前 “嗒嗒嗒嗒”地忙上一两个小时。那个时候,缝纫机是奢侈品,外婆家所在的铁路宿舍区极为少见,外婆的那些老姐妹们就总是找个借口来串门,边欣赏外婆的缝纫手艺, “啧啧啧”地赏叹外婆缝制出的新衣裤,边满脸堆笑地从随身小布袋里掏出一件要修补的旧衣裳,让外婆帮忙缝纫一下。外婆当然是来者不拒,谁的忙都乐意帮,这样一来,她的每个下午就格外繁忙起来。但不管忙成什么样子,到了做晚饭的钟点,外婆都会急急收摊,清理好针头线脑,还原一个整整洁洁的家,然后再去添煤加火,洗菜做饭。吃罢晚饭,姥姥去乘凉,外公去倒腾自己的小爱好,外婆便又在家务事中团团旋转。抹桌洗碗,扫地关鸡,收衣折叠,烧水侍弄姥姥外公洗漱,再自己洗漱,接着就封炉关门,与外公对一对买菜购物的支出账,俩人聊聊家里的和外面的见闻,商量一下这种事那种事,然后就熄灯睡觉了。
如果就是上述那些事儿,一般家庭妇女大抵都能做到,难就难在外婆还要同时照顾我们家,具体点讲,就是时不时地要照顾和看管我和姐姐,这让她付出了比许多其他家庭妇女更多的辛劳。那时我们家距外婆家不算远,大概步行三四十分钟的样子,正因如此,我和姐姐经常地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时父母不知成天忙些什么,总是出差,搞 “大批判”,参加各种集会游行,常常把我和姐姐撇在家里,自理生活。这让姥姥和外婆无比的牵挂。特别是那时我们所在部队大院的孩子东一派西一派,常常争斗打架,头破血流,外婆就替代了我们父母的职责,几乎每天走过来看望一下,送些香菜热饭,而一到节假日特别是寒暑假,就干脆把我们接过去带,让父母骑单车来看望我们。有勤劳的外婆,我和姐姐的童年很滋润。在外婆家,三位老人总是围绕两个孩子转圈圈,我是男孩,年岁又最小,便成了中心里的中心。姥姥、外公自然是爱我们的,特别是姥姥,千宠万娇,恨不能把心都掏出来给我。但是,遇上衣食住行方面的具体事,还是得靠外婆身体力行,实在相帮。比如我喜欢热闹,热衷到街上和集市里去玩,姥姥小脚走不动,只有外婆能带我去。所以,外婆外出时,我成了她的小跟屁虫,牵着她的衣角,紧跟她的身后,还积极地帮她扛那把桐油伞,赢得了她那些老姐妹的夸奖,还赚回不少的零食,非常开心。又比如我那时肚里蛔虫多,体弱多病,饭食不香,外婆就隔三岔五地背着或牵着我到一个叫小街的地方去看中医。那个中医爷爷真就医术高明,妙手回春,把我那厌食多疾的毛病治好了。当回到自己家里大碗大碗地吃起饭来,父亲和母亲都高兴得面面相观,喜从心来。再比如我喜欢吃的那几样饭菜,也只有外婆能随点随做,甜酒灰面疙瘩、煮沙河粉、萝卜干炒油渣、榨菜肉丝、辣椒香干子等等,哎呀呀,在那种生活艰难的日子里,能吃到这些可口的菜式,全凭外婆那颗爱心和一手好厨艺。外婆这个人,好像是不知疲倦的机器,事越多越精神,活越重越有劲。我和姐姐的到来,使她的家务事倍增,烦心事见长,但她仍旧得心应手,应对自如,从不发脾气,讲怨言。早上,她叫醒我时唱的是《国歌》,被一掀,拉住我双手向上一拽,接着就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晚上,她忙完所有事,如果见我在姥姥房中还没睡,就会拿着把蒲扇坐到姥姥床边,一边给我们打扇子,一边讲些小笑话。她的幽默,常常把我和姥姥弄得开怀大笑,就更睡不着了。为了能满足我们姐弟俩贪吃的毛病,外婆背着外公,找到一份在家加工铁路行李标签的活路,趁外公上班和家务事剩下的空隙,争分夺秒地赚点小钱,让我们能吃上甘草姜、甜橄榄、咸金桔和爆米花。以前办这些事,她在与外公对账时总是吞吞吐吐,要听一箩筐外公的唠叨。而自从手头有了点活钱,能让两只 “小馋猫”欢享口福,外婆觉得格外地扬眉吐气,说起话来顺溜了,走到哪里腰板都挺得直直的。在外婆那群老姐妹中,她有点文化,又乐于帮人,还心地善良,渐渐地就成为了小头目,一呼百应,从者如流。正因如此,后来有许多个晚上外婆收拾完家务,便带着我去串门。说是串门,其实是去别人家做纠纷调解工作,儿对母不孝的,夫妻间拌嘴的,婆媳闹矛盾的,她都去说,都要管,而且还百战百胜,总是成功。每次从别人家摸黑返回,外婆总喜欢跟我一道数天上的星星。天上星星数不清,但外婆寄望于我的,是做一颗明亮的星星。
十二岁那年,我随父母离粤赴湘定居,离开了亲爱的外婆。临别时,在广州老火车站,外婆搂着我悄悄耳语,让我忘记她讲过的老虎外婆和狼外婆的故事,她说她不应该给我讲那样的故事,天下没有如虎似狼的外婆,只有像她这样爱我的外婆。她还说我这一走把她的那颗心也带走了,所以要赶紧学会写信给她,把她的那颗心还回来。
离开外婆后,在父母写信给外婆时,我总会写上几句话,或专门叫父母写上我想念她,这让外婆很高兴。外婆也写回信,用的是圆珠笔,字迹工整,用力很大,话语极为朴实。十多年间,她告诉过我们她被选到居委会去上班了,很忙的,但她喜欢这个差事;又说她干不了居委会了,因为舅舅的孩子出生了,她要好好带自己的孙女;还说外公中风了,瘫在床上,没法唠叨了,像个顽皮的孩子,什么都要靠人侍候。有一次她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吃鸡爪不会影响写字的,以前父母不让我们吃,为的是孝顺她,把鸡爪留给她吃,她真不应该任由父母蒙骗我们。再后来她写信说,舅舅舅妈不让她去买菜了,因为她快走不动了,购物买菜的事都交给舅舅舅妈了。听说我下放农村当知青,她着急,担心我的身板能否承受住乡下繁重的劳动;听说我子承父业当兵了,她格外高兴,嘱咐我打仗时要注意安全,但不能当胆小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母由湘返粤回到广州定居,据说外婆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以后我与外婆的联系,就总是通过与父母通信来维持了。在部队提干后,我终于能享受探亲假回广州了,记得第一次从部队回家,行李刚放下,父母就催我去看外婆,说外婆老是在念叨我怎么还不回来。我骑了辆自行车赶到外婆家,那一带的居民区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外婆还是以前那个外婆,是心房里千思百念的那个外婆。站在外婆家小屋的窗外,我久久没有进门,就那么隔窗望着她,望着她。除了头发花白一些,身体瘦弱一些,她确实变化不大,还穿着那种她喜欢的兰色带花的婆婆服,还是踏一双老式黑布鞋。她没看见我,侧身坐在凳子上看书,那个翘翘的极有特色的上唇依然噘着,越过了鼻尖;戴上老花眼镜的样儿与十多年前剪裁衣服时的光景没啥两样。她一边用手指在书页上移动,一边自言自语地不知说些什么,大概是在念书上的文字吧;一束阳光透过窗棂照着外婆,在墙壁和地砖上留下长长的影子,也照在门后面的一把伞和一个布兜上。往事依稀,相见如梦。我的一声激动人心的“外婆”,顿时让她宁静的午后变得喧腾。从外婆的角度来看,还有什么事情能比送走一个少年迎来一个军官,看着自己带过的外孙长大成人更高兴的呢?!
拉着外婆的手诉说别情时,才知外婆其实变化很大。最主要的是不能走远了,与外面的世界逐渐隔开了。然而,家里的事儿永远是她的拿手好戏,她让我坐着等等,转眼间魔术般地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甜酒灰面疙瘩。就这样,婆孙俩你一句我一句,边吃疙瘩边把现实场景拉回到十多年前。外婆老花镜后的那双眯眯眼,一直都充满着泪花,其实我何尝不是热泪盈眶呢?这一刻,我终于把她的心,又带回到她身旁。
“草民”外公的快乐生活
与外婆相比,外公在我心中的分量要轻一些。我年轻时读过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 《童年》,发现他笔下的外祖父外祖母竟然非常相似于我的外公外婆,一个严厉冷淡,一个慈祥温和,孰优孰劣自然泾渭分明。
不过,我的外公比高尔基的外祖父实在是要好许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经历的不断积累,我现在发现他老人家身上的闪光点还着实不少,值得怀念的地方相当之多。比如他一介 “草民”,当年在铁路系统谋得一份普通职员的差事后,硬是一柱撑天,养活了岳母、妻子和五个子女,还把五个子女中的三人培养成了 “文革”前的老牌大学生。他经历的是什么时代?是上世纪初叶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时代。皇帝倒台,民国建立,军阀割据,革命兴起。接着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与建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春天的到来。在战火硝烟与大风大浪中,“草民”外公一步也没走错,驾着家庭这条小船左闪右避一路行来,终于抵达了平安宁静的港湾。再比如他老人家孜孜以求 “世外桃源”般的闲情逸致,把生活经营得忧里含乐,苦中有甜,许多灰暗苦涩的日子都被他化解成轻松快乐的时光。
我的童年一半在部队大院中的父母家度过,一半在铁路宿舍区的外公外婆家度过。这两个家相隔不远,所以父母一忙起来,就会把我往外公外婆家一送了事。而到了外公外婆家,我就成了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因为当时我是能绕膝在他们身边的唯一一个外孙,又聪明懂事嘴甜听话,姥姥和外婆都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揣在怀里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所以,一到外公外婆家,我就满屋子地找吃的和玩的,而姥姥和外婆都会争相地把她们的饼干盒打开,那里面积攒的零食都属于我。
但到了外公下班和休假的时光,我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外公虽然喜欢我,但却并不善于表达,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玩家,玩这玩那,自娱自乐,沉醉在自己喜爱的事物中流连忘返,以避开现实社会的风浪凶险与人事纷争。外公的书桌有七个抽屉,但真正放书的仅有一个,其他六个都分门别类地放着各种工具和零配件,真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外公一回到家,架起眼镜,叼上香烟,就开始东敲敲西捶捶,围着书桌翻箱倒柜,不停地鼓捣他脑袋中的那些奇思妙想。而他的工具抽屉便也成了我的玩具储藏箱,我不仅在他聚精会神鼓捣的时候紧紧陪伴着,而且在他上班离家之后把抽屉全搬出来大玩特玩。多好玩的吸铁石呀,往钉子堆里一扫,石上就粘满了横七竖八的铁钉;轴承上掉出来的小钢珠也不错,亮晶晶的,正好用来弹珠子;那锤头、钳子被我用来敲打阳光中在窗台上成群结队攀行的蚂蚁;而木柄起子和大长钉则被用来挖屋檐下湿土中的蚯蚓,以慰劳家里的芦花鸡。倘若这时外公回来,我必然会挨几声大骂,说是把他的工具弄脏了,零件弄丢了,器械弄乱了,之后他会一个屉子一个屉子地检查,直到重要的东西都完好无损才放心。这几个抽屉,也就成为我与外公矛盾的导火索,我为了这几个抽屉而挨骂的次数比里面的工具加零件都多。
不过,我是不太害怕外公的,一来知道外公骂人就那 “三板斧”,绝不会动起手来的;二来知道外公其实挺喜欢我,骂完之后肯定会雨过天晴;三来我还有姥姥和外婆护着。有几次外公骂得挺凶,姥姥一出面劝阻,外公就马上不做声了。
女婿嘛,哪能跟丈母娘叫板哩。久而久之,外公也就不太骂我了,有时反而把我当成了他的玩伴和助手。有一阵子,他对捣鼓自行车入了迷,一会儿拆去铃铛换上喇叭,一会儿在车头添加照明灯和反光镜,一会儿做个铁椅架置放在三角钢叉上,一会儿又制作带有流苏穗子的丝绒套罩在车座上,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活脱脱玩成了皇帝出巡的华丽大轿,好不威风。之后,他便载着我一路按喇叭、闪照明灯地在铁路宿舍区内招摇过市,满面春风地迎接着人们的啧啧称奇。还有一阵子,他玩上了半导体收音机,不知从哪个旧货市场淘来一些小管子、线圈和耳机,折腾了好一阵光景,最终让我天天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小喇叭正在广播”。外公的玩兴是充足的和全方位的,家里那台老式古董挂钟被他玩过,之后 “当当当”的钟声响彻全屋;家里的日历牌是他自己设计的,每天他轻轻拨弄那么两下,“年月日”和“星期几”便配套出现,在那样一个年代,这是极其稀奇和时髦的;外婆有台老掉牙的缝纫机,更是被外公革新来改造去,修得比新的还好使,外婆每次用后都喜笑颜开;我喜欢帮姥姥养鸡,求外公把鸡窝修整一下,他开始说没空,突然有一天斧凿锯刨叮叮当当地忙了一整日,从此家里的公鸡母鸡们欢天喜地地搬进了能防风防雨又防晒的新鸡舍。那时 “文革”进入到了武斗阶段,天天的 “造反有理”和游行示威,搞得外公无所适从,没事就躲在家里拉二胡,其烦闷心绪都咿咿呀呀地通过胡琴声传递出来,不高兴时拉得一屋子噪音,难听死了。退休后,作为给自己的奖励,他花钱买回一台半旧绿壳的留声机,天天翘起二郎腿,左手烟右手茶,眯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沉浸在美妙的音韵中。姨妈舅舅和我的父母时常前来看望,顺便就送上一些好唱碟。每当家人团聚为了 “东风派”和“红旗派”的事儿争论不休时,外公就一下打断让大家陪他听音乐。他还真会欣赏,反复地播放西藏歌手才旦卓玛的歌曲,他说这是他听到的最好的歌声。经才旦卓玛那么一唱,《毛主席的光辉》果然听得外公暖洋洋。
外公从不给我买零食,也从不迁就我,给我的笑脸和温存也没有多少,但是,我就是喜欢粘着他,烦着他,还时不时地把他的东西搞烂弄乱,害得他常常发脾气并破口大骂。然而,在我父母那儿,外公却从来不说我一个 “差”字,父母问起,他总是“好好好”地点头微笑,让我把一颗快跳出口腔的心又安放回胸窝。我知道,外公其实是爱着我的,他的爱是表现在允许我跟他一道去玩上,并且让我一道分享他玩出的得意成果。
我外公叫蔡增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铁路职员。他退休时用自行车载着我到他的单位去与火车告别。望着长长的列车,他说了一句话:这火车可是个好东西,成天拉着那么多的人和货,不怕重又不嫌累,就这么一直快乐地向前跑,真不简单呀!
他是说火车还是说自己呢?当年我年纪太小弄不明白,但是现在,我已经彻底地明白了。
注:在湖南方言中,姥爷意为曾 (外)祖父,姥姥意为曾 (外)祖母。
责任编辑梁智强
周伟兵ZhouWeibing
1959年生,浙江绍兴人。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199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在省级报刊上开辟散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