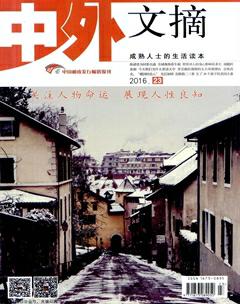斯诺登为何要出逃
□ 程 蒙
斯诺登为何要出逃
□ 程蒙

约翰·克兰住在波托马克河南岸,那里森林茂密、丘陵起伏,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总部也不远;沿着河流往上几英里,便是五角大楼。身为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员,克兰一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在这个情报体系里,他已经干了25年了。对克兰来说,这个情报体系就是一种信仰,然而这个情报机构却已视克兰为敌。
斯诺登只能逃出去
克兰坐在厨房里,他面前放着一个公文袋,上面盖着美国政府印章。克兰已经60岁了,梳着大背头,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依然穿着日常制服:一件印有他姓名首字母的衬衫,上面钉了袖扣;外套上钉着一排金色纽扣。25年来,他每天都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去上班,到安保门禁时亮出自己的徽章,然后径直开进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基地,走进办公室。他时常可以看到五角大楼,就在他办公室窗户的右边。
之后克兰他们搬了一次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无名之塔中;他们依然是美国国防部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军队中工作;最终,他当上了副总监察长,成功跻身高层。总监察长手下有1600名公务员,其中有90人归克兰管辖。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内部问题、腐败和其他违法行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总监察长一职就像橄榄球的自由后卫,确保整个政府体系在法治环境中正常运转。
克兰在五角大楼的工作非常敏感。他的职责就是“擦屁股”——从解决办公室纠纷到处理重大丑闻,而这些问题都是军队内部的问题。具体来说,他的首要之责便是协调美国国会和国防部内部举报体系之间的关系。说起来,这个国防部内部举报体系就是一个面向五角大楼300万雇员的“举报箱”,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在受监督的范围之内,毕竟它也隶属于五角大楼。克兰一直做着这个工作,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上司滥用职权,干预一桩举报。
这个事件让克兰开始质疑他所为之奉献的一切。而正是因为这起事件,这位五角大楼高官与上司发生了争执,最终他在2013年被踢出局。在25年的职业生涯中,克兰处理了无数的举报案件,这次他决定向媒体爆料,自己也做回举报人。
克兰要说的这个事情源自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们俩都谈到过一个人:爱德华·斯诺登。美国政府反复强调,斯诺登本不必潜藏起来,也不必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他们的潜台词就是:监控体系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斯诺登自己。
对于斯诺登这个人,奥巴马曾表示“对政府行为有良心不安的人来说,总还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在民主党初选中,希拉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斯诺登可以在政府机构内检举揭发,他会成为检举人,然后得到保护。他可以举报一切问题,政府部门也一定会给他积极回应的。”
在弗吉尼亚的家里,克兰目光远眺,望向波托马克河对岸,那个方向朝着五角大楼。克兰知道事实的真相并非奥巴马和希拉里说的那么简单。如果真如他们所说,斯诺登该如何通过国内渠道来检举揭发?他并不是政府官员,他只是一个国家安全局外包公司的雇员。所以,斯诺登怎样才能像公务员一样,在告密之后得到政府的法律保护呢?即便当事人不是斯诺登这种平民,而是克兰这种军方高官,恐怕也没法顺利过关。
克兰叹了一口气,努力拼凑着词句来解释自己内心的疑虑:“我可是亲眼见识过如果当事人按照规定,通过官方渠道检举揭发,他会发生什么。”说来有意思,美国政府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为军队内部和国安局的揭发检举准备了相应的应对方案。
大学毕业后,克兰就为一个名叫比尔·迪金森的共和党众议员工作。迪金森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同时他还是成立总监察办公室的倡议者之一。这一职位甫一设立,克兰就成为办公室的首批雇员。在职业生涯中,克兰为12位总监察长工作过,在他的帮助下,该机构为检举人设立了“热线”。在克兰看来,检举人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这些人的存在可以帮助政府改进工作。
在切尔西·曼宁向维基解密披露了大量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文件后,克兰就力促建立一个新的内部制度,专门应对涉及机密情报的申诉,并为此确立了高度机密的程序,之后这一制度成文出台。在克兰供职五角大楼期间,他把1978年出台的检举人保护法案打印成册,以确保总监察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能对这个随时会付诸实践的法案了然于胸。在克兰看来,他的本意就是要确保不会再出现下一个斯诺登。
直到现在,克兰依然不太赞成曼宁和斯诺登的做法。他觉得斯诺登逃到俄罗斯去实属悲剧,而这一悲剧本可以避免。他依然认为内部方式解决问题才是好的出路。而内部渠道行不通不是因为制度的问题,而是那些在上位者的过错,正是这些在上位者才未能让法律得以充分实现。
监守自盗的监察机构
约翰·克兰起初有所怀疑是在2004年,在那不久前,他被提拔为副总监察长,这个职位算是五角大楼的高层了。彼时距离2001年的9·11事件时隔不远,针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安全部门的运作方式。在小布什总统的授权下,安全部门很快得到了大笔预算和更高级别的权限。
国安局内部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些变化背后的东西。他们发现,监控不仅针对恐怖分子,还会瞄准普通美国公民,而这在他们看来是违反宪法的。监控项目耗资近40亿美元,钱都流向了与国安局签了合同的私人公司,这些纳税人的钱最终都被用来监视纳税人。为此,有人提出了一个名叫“细针”的内部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可以更好地处理好反恐监控,而且还能节约数十亿美元。
这群质疑者就包括三名国安局的前雇员,一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前雇员,还有一个便是国安局监控项目核心领导之一的托马斯·德雷克。
德雷克将自己的不满直接告诉了国安局总监察长。其他几位(比尔·宾利、科尔克·维贝、埃德·卢米斯和戴安·罗克)则向五角大楼总监察长发出了投诉,而那里正是克兰工作的地方。2002年9月,正式的投诉文书送到了克兰的办公桌前。
2003年1月,克兰手下的监察员们与德雷克见了面,之后好几年对他进行了多次盘问。德雷克也向监察室递交了国安局的文件,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安保人员将德雷克每次进出总监察长办公室的信息都记录下来,德雷克感觉自己已经被人监视了。
克兰的手下经过仔细调查,确认了德雷克所说的大部分属实,这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国安局局长迈克尔·海登的脸上。2006年,美国国会经过投票,叫停了饱受争议的“开拓者”项目。然而,国安局依然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监控。
德雷克事件可以说是举报人制度的一次成功案例。但从一开始,德雷克和他那四个同伴都觉得自己会被报复。这五人小组中,有四个人在举报时用了真名,而德雷克自己却因为害怕只用了“管理层高级主管”的身份来做化名。在克兰看来,德雷克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于是,他打算在内部展开更深入的调查。
克兰的上司没有批准这项深入调查,这让克兰愤愤不平。在他看来,自家老板的行为就是在妨碍监察工作。克兰说:“这恰恰说明,这个事情必须得深入彻查。”
担心很快被证实了。2007年7月的一个早上,联邦调查局特工突击搜查了四位举报人的公寓。四个月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又出现在德雷克家门口,要知道,德雷克的名字在内部调查报告上可是匿名的。
德雷克长期为情报部门工作,在为美国空军情报部门工作期间,他曾监听东德情报机构史塔西秘密警察之间的电报往来。后来他调往国安局,第一天上班他就遇到了9·11事件。
现在,德雷克被联邦调查局关押了起来,可能会面临35年监禁。德雷克在忠诚调查中没有过关,他的职业生涯被毁掉了,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他所信赖的内部举报渠道。在针对德雷克的指控中,有一项指控他向《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泄露机密情报,还有一项指控他用个人电脑保存国安局机密文件,这些都被他一一否认了。
就在德雷克的审判即将开始之前,联邦政府撤消了所有指控。德雷克最终因为误用国安局电脑被判处一年缓刑,并被处罚社区服务。在宣判时,法官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公诉人,认为他们对德雷克的行为“毫无良心”。尽管法律还了德雷克公道,但他却已经丢了工作,没了养老金,还失去了很多朋友。
德雷克并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案子会把克兰这个监察办公室高官打入对手之手。而考虑到德雷克害怕被报复的处境,克兰决定要把这事一查到底,他内心深处的怀疑也隐隐透出一丝不安。
上面插手了
2005年,《纽约时报》报道了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监控项目,此文一出,举世关注。时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下令追查新闻根源。很快,五名国安局举报人变成了嫌疑犯,这五个人有一个共性:他们都在内部抨击过监控项目。
约翰·克兰至今仍记得,自己的上司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议将举报人的名单转给调查此事的美国司法部,克兰则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对匿名举报人的迫害。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从会议室吵到会议室外,最终克兰掏出那本写有举报人保护条例的小册子。末了,克兰的上司只得说,既然克兰是负责协调与司法部关系的人,那克兰自己好自为之吧。
对于克兰的这番说法,五角大楼和监察办公室方面都拒绝向媒体作出回应。而克兰当时的那位上司也以保密条例为由不予回应,他甚至说,如果这一事件公开调查,他有信心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克兰的怀疑有增无减,特别是与德雷克事件有关的重要文件从总监察办公室消失之后,这种怀疑越来越重。德雷克的律师杰希林·拉达克曾请求法庭询问这份文件的去向,因为这份文件可以证明德雷克只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上存了这唯一一份文件,其目的是向监察室举报,而不涉及泄密。如是这般,德雷克便可免遭起诉。
然而这份文件却没能在总监察办公室找到,据说这份文件已经被碎纸机粉碎了。而克兰的上司这么跟他说:“替大家伙想想。”之后,这位上司告诉法官,文件是因为工作失误而不幸丢失。对此,克兰却是一个字也不相信。在他看来,这份文件是被故意销毁的。“在刑事诉讼中对法官撒谎可是重罪。”克兰说。
克兰并不想“为大伙想想”。他要反抗,要投诉,他向上司表示自己不会就此沉默。由于事关德雷克案,当时便可预见克兰不会有好结果。2013年,总监察长把克兰叫到办公室,当着他的面把解职书递给了他,随后一名安保人员取走了克兰的通行证。
祖父的榜样
在做了25年勤恳的公务员后,克兰为何选择了反抗?究竟是什么让他可以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公职人员的名誉、友谊甚至养老金来冒险?
克兰走过五角大楼附近的伯德·约翰逊夫人公园,如今他不必每天一大早赶去办公室,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散步的时候,他双手背在背后。他还在五角大楼时,跟他打交道的都是参众两院的议员,他也把自己视为执法机关和立法机构的纽带。在克兰看来,像奥巴马总统这样的政治家是希望改善民主的。“我必须得做正确的事,”克兰说,“就像我那位德国爷爷一样。”
克兰的祖父名叫金特尔·里德尔,是德国空军上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3年11月8日,当阿道夫·希特勒和其党徒打算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著名的啤酒馆暴动时,里德尔和几个其他的士兵也在啤酒馆里。当希特勒拿着手枪对准里德尔的一位朋友时,里德尔挡在了枪口前,说道:“希特勒先生,你绝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解放德国人民。”
希特勒最终放下了武器,然后转身去发动暴动了。里德尔平息了事态,之后在一份长达8页的个人档案里记录了此事,由于有目击证人,此事的真实性得到验证。后来德国政府在战后针对希特勒发起的公诉中打算邀请里德尔出庭作证,不过最终没能成行。
克兰说,直到今天,他还是非常崇拜自己的祖父,1923年的历史事迹一直都激励着他。不过克兰也知道,祖父的个人事迹不只有光辉的一面,后来里德尔留在了纳粹国防军,成为纳粹空军的中坚力量,并被晋升为将军。1942年,里德尔被解职,之后全家搬往巴伐利亚定居。
2000年,里德尔在二战中的经历再度被翻了出来,时任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将一个以里德尔的名字命名的空军营改了名;与此同时,有消息显示里德尔还出任过纳粹德国人民法庭的志愿陪审员,这个法庭就是纳粹政权用来迫害政敌的。不过进一步的调查显示,里德尔只参加过一场听证会,而且还主张释放被告人。而那个更名的空军营又把指挥官办公室命名为里德尔办公室,克兰和自己的母亲还亲自出席了命名仪式。
“我从我爷爷身上学到了一种道德责任感,那就是如果政府违法了,身为个人就应该挺身而出。”克兰如是说。他也坦承,这种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会让人难免觉得痛苦,但又令人义无反顾,“在我眼里,监察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使命。”克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德国神学家、著名的反纳粹斗士马丁·尼莫拉的那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读完这段话,克兰沉默了好一会儿。
“体制还有用”
“克兰‘反水’,本质上是因为监察制度不管用了,”托马斯·德雷克说,“他救了我。”德雷克和克兰在双双被解除公职后私下里仅见过一次。两人都坚信证明自己是无罪的那一刻终会来临。德雷克说,自己很快就会拿回自己的养老金,当下他还在苹果店里做销售员。
而克兰这边,他已经向当局提交多份书面申请,控告当局滥用权力。他的律师也向特别检察官办公室递交了投诉书,投诉克兰前同事的不当行为——破坏举报者的正当权利。
斯诺登曾说,德雷克的下场让他感觉无法信任当局,所以他带着秘密潜逃。“在德雷克眼里,当局是绝对正确的,”斯诺登评价说,“然而当局不会保护这些举报人,反而会迫害他们。”
在克兰看来,斯诺登被迫流亡真的是美国的悲哀,因为对于斯诺登来说,他无处伸冤,他们如此这般不过是自我保护。克兰说,自己的那帮同事本来就差点把斯诺登变成下一个德雷克了,这简直就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耻辱,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有德雷克的范例在先,斯诺登怎么还会相信这个制度?”克兰如是说。
“我还在国安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出了问题走官方渠道,很可能结局就是滚蛋,这还算是好的了。这就是一种官场文化,”在跟媒体谈到克兰的案子时,斯诺登如是说,“如果你只是举报你的上司,那总监察长或许会看两眼你的举报信;可如果你举报的是下令监控全美的美国总统呢?你觉得总监察长会怎么办?那他们会把你碾得粉碎。”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斯诺登补充道:“我去找过同事,找过上司,甚至找过律师,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你简直是在玩火’。”

约翰·克兰在五角大楼的通行证
“如今这种政策的悲哀现实就是,拿证据去找总监察长都没法说理。找媒体爆料也要冒很大风险,不过至少你还有一线生机。”斯诺登说。按照斯诺登的说法,直到今天,情报部门内部举报者无一不遭到报复:“举报者需要有一个坚强可靠的保护,可如今的法律根本就不会鼓励人们站出来对错误的行为说不,这才是要改革的地方。”
在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克兰想再去看看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开着自己那辆深红色的沃尔沃汽车,驶向了波托马克河的一处游艇停靠点。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角大楼、华盛顿纪念碑、白宫以及美国所有的权力机构。附近便是罗纳德·里根机场,喷气式飞机从那里起飞,呼啸而过。克兰远远地凝视着五角大楼,他本应该满腹牢骚的,可他却只言未提。
根据独立调查机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给出的结论,克兰案存在可疑之处,其主张观点可能为真;美国司法部裁定重启对克兰案的调查。预计一年后,结果将公布,克兰很可能将胜诉。到那时,克兰打算退休在家,照顾孩子。
那么克兰想过有朝一日重返五角大楼吗?“当然,”克兰如是说,不过他的表情显得很错愕,显然他没想到会有人这么问,“如果我回去了,就证明这个体制还是有用的。”
(摘自《看世界》2016年6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