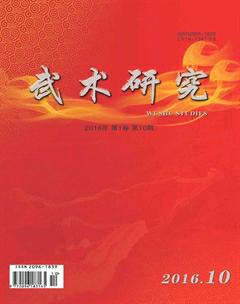近代码头的兴起及其对武术的影响研究
王校中 谭广鑫.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0635;.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0036
近代码头的兴起及其对武术的影响研究
王校中1谭广鑫2
1.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635;
2.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036
近代码头的兴盛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机遇,其特有的群体特性与内在组织形式一直是诸多学者的研究热点,而其中武术的开展及其影响一种是未被涉及的课题,文章通过对码头群体的形成及码头组织形式的阐述,指出码头社会的传统宗法制度倾向,并以汉口、上海、淮河等码头为背景,对其中的武术的开展及其相互作用做了详细解析,指出武术的技击性与宗法群体性对码头群体的生存环境起到了平和调节作用,同时码头社会为武术的传播、开展及革新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武术码头文化帮会宗法制
中国武术产生于民间,根植于民间,作为农耕文化背景下孕育出的独特身体活动形式来说,武术本身充斥着浓郁的民间生态气息。自古的中国民间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祥和的生存环境,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更自觉或不自觉的搅动着这片以土为生、以血相连的社会群体,脱离原有生态环境的民众群体带着根深蒂固的思维形态,寻求存活的一线生机。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外国资本文化的侵入,国内社会统治制度的腐朽,人口的过剩,资源的枯竭,迁徙的不定性,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与现象,这其中码头就是一例。
通常意义上的码头有三种解释:(1)船只停泊处;(2)交通便利的商业城市;(3)流氓活动、霸占的地盘。[1]这里明显有一个狭义与广义的概念之分,船只停泊处,即狭义的码头概念;而因船只停泊,引发的贸易交流,形成的商业集镇及地盘争夺是码头的广义概念。王玉德在《武汉码头文化的历史源流与发展演变》中指出:“码头是个综合的社会概念。码头文化的内在本质是商业文化,商品在物流过程中形成码头,资源与产品都经过码头而实行其价值转换。有了码头就有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业,如烟馆、茶馆、妓馆、会馆、武馆、医馆。各种人群也应运而生,如搬运工人、修理工人、各种手工业者,江湖浪人……,因而就有了纷繁的社会。”
而在中国传统“重本抑末”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压抑而缓慢的状态,近代以前的河岸码头基本用于船只停泊与客旅运输。而处于地理形势优越的码头也可能因农副产品的交易而形成繁荣的商贸城镇,如晚清以前,因商贸物流而兴起的汉口,但其商贸内容也仅限于农业物资的交换,所能提供的工作空间及人员容纳量及其有限,而近代中国商业文明的兴起及与此相应的近代码头运输业的产生无疑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有着莫大的关系。
1 近代码头兴起的背景及码头群体的产生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腐朽而停滞的封建帝国,强大的西方文明,迫使中国开始脱离固有的模式,而转向于西方所构建的政治及资本体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列强陆续夺得了沿江、沿海口岸通商设厂的特权。而内陆的丰富的矿产资源及农业资源成为了列强掠夺的主要对象,这一需要促使了近代内陆交通运输的变革,从1878年至1911年,西方国家先后与清政府合建了“津芦”“京汉”“胶济”“道清”“正太”“京张”“汴洛”等铁路干线,[2]为更好地沟通内地与沿海口岸的运输,铁路设计基本是南北走向,与自西向东的江河水路系统相结合,构成四通八达的运输系统,随着国内及国际间商品交易量的增加,许多河流与铁路结合的装卸码头,逐渐衍生出了商贸发达的城镇,如长江流域汉口码头,淮河流域的蚌埠码头及黄河流域的潼关码头。这些城镇的兴盛完全依赖于近代铁路运输的发展,而运输业的兴盛同时促进了周边城镇的近代化进程,为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生存的岗位。
晚晴之际,满清的政治权力已摇摇欲坠,与以往朝代变更的规律相似,大范围的农民起义与社会动乱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而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清王朝在相对稳定平和的二百年里,促使了人口的急剧膨胀,“清朝人口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总人口从1.19亿增加到4.3亿,”[3]庞大的人口积压,大规模的农民斗争,外国列强的凌辱以及不尽的天灾,导致清末的社会异常的动荡与残酷,大量的失业农民背井离乡,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流民势力,池子华在《中国近代流民史》中引用的一首诗,生动地描绘了灾荒之后流民四起的残酷景象:
黄水望无边,灾情实堪伤,
村村皆淹没,家家尽饥荒,
贫者本贫苦,富者亦无粮,
结队离田园,流浪至何方,
忍饿暑天行,面瘦黑又黄,
偕妇载婴儿,涕号道路旁,
日落原野宿,辗转秋风凉,
流民成千万,何处是安乡。[4]
众多的流民群体为求资源、寻求活路,纷纷涌向中心城市,池子华把这种现象称为“向心运动”,此时的中心城市,基本集中于水陆便捷的港口城市,如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大港的上海,“1852年的上海人口不过50万,但到1949年增至近550万,”[5]淮河第一港的蚌埠码头,铁路筑通前仅是700多口人的小村落,开埠以后人口迅速增至两万,高峰期近二十余万人,[6]武汉的汉口,在光绪三十四年(1888年)的18.10万,而到1911年初汉口城区人口达59万。[7]这种机械性的人口增长正是流民涌入的结果。职业的谋求成为了流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农村出身的流民综合素质较低,许多的”粗、脏、累的低贱职业如市政建设、码头工、车站脚夫、拉黄包车、清道夫、仆役等似乎天然属之流民。[8]“而以物资集散为主的商业城镇,码头搬运成为了流民首选的职业,以武汉码头为例,民国时期,武汉共有水码头243个,陆码头220个,码头工人五万左右,在1913年的一份汉口民人身份调查表中[9],列出的49个职业岗位,码头工人的数量仅次于小贸与佣工而排在第三位。当时有外洋商家对武汉汉口码头繁荣景象,大为惊叹“载货物则有二十余处,所有船舶俱湾泊于港内,舳舻相衔,殆无隙地,仅余水种一线,以为船舶往来之所也”,[10]据不完全统计,交易高峰时期,汉口码头商船日停泊量达两万多艘。以码头为圆点,环形经济圈的扩充,成为近代商贸码头城镇的重要特点,随之而兴起的搬运运输业、餐饮服务业、工厂制造业等产业为大批流民提供了生存的机遇。
2 码头社会的组织形式及武术的进入
2.1码头社会的帮会现象
帮会现象是码头群体主要的组织形式与生存形态,易江波指出“码头社会的各色人等,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码头利益的争夺,成为码头社会空间的活跃角色,这就是码头江湖社会形成的一个基本模式。而帮的日常化与繁荣状态,是近代码头社会不同于其他形态的民间社会的基本特征。”[11],上海码头有句谚语“好人不吃码头饭,要吃码头饭,就得拜个老头子。”以汉口为例,沿汉水的30多个码头分别由宝庆帮、汉宁帮、徽州帮、荆州帮、黄州帮、咸宁帮。公馆、会所、黑社会共同维持。[12]淮河蚌埠码头素有“一百零八帮”之称,按乡土结合的有河南帮、江苏帮、河北帮、山东帮、湖北帮等,按河流又有淮河帮、浍河帮、沙河帮等,按行当结合的有丝网帮、草帮、号盐帮、工匠帮等,“大大小小各帮会普及全市各行各业。”[13]
帮会现象绝对不是凭空而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帮会就是血缘家族的一种变异形态,其中“帮”是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 “会”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14]。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法性社会,以宗法制度为结构的生存观念已牢牢根植于农耕文化下的群族,从文化遗存角度来说,即使脱离了固有环境以后,这种观念依然存在,且在适当的环境中会死灰复燃。而大量脱离农耕的流民正是这种文化遗存的载体,为确保自身的安全及利益,以师徒为父子,以“结义”为兄弟的“虚拟血缘制”[15]的组织便自然形成了,这种帮会组织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具自发性和自愿性的“抱团求生”的行为,在无序动乱的时代,很大程度上为远离故土的人民提供了帮助。
2.2码头械斗的常态化
在许多亲历码头的老人心之,码头不是一个和平安静的工作场所,而是一个充满暴力与强权的是非地——码头是打出来的。正如解放以后码头工人所揭露的那样,“这些码头老板们把蚌埠分成许多块,个把一方,和往年军阀割据一样,争权夺利,常起冲突,动不动就喊打,谁都想扩展自己的地盘。”资源的有限与劳动力的过剩构成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在没有文治政府的管制之下,靠武力的争夺似乎是解决争端最直接而又有效的办法。如淮河码头老工人所说“不打很多人会饿死,打了大家都有饭吃,即便打死了几个人。”以汉口码头为例,据1947年官方统计,汉口全市经法院办理的码头械斗纠纷案达965起,平均每月达80多起,而未经统计的小型纠纷更不计其数。[16]
对地盘与资源的抢夺似乎并不能太完美解释工人们以死拼杀的现象,码头规矩,要成为合法码头工人必须要花钱买“扁担”,这个“扁担”即是自己合法的财产,可以转租,也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无数工人终其一生为的正是能买得起一个“扁担”,而这其中对“扁担”的追求,似乎成了他们对土地追求的一个映射,“中国农民对土地有着深沉的刻骨铭心的眷恋之情,土地不仅是他们的命根子还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四处漂泊的流民,寻找一片可以耕作的土地不亚于寻找到了生存的希望,“被抛向社会的流民涌动着,举目四望,泥土的芬芳,依然清新、诱人,他们希望重新回到土地上,拥有一小块土。这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绝大部分流民对未来职业流向的理智选择。”[17]
在未脱离传统农耕思维的观念下,码头就是土地,对码头的眷恋与坚守实则就是对土地的坚守“码头工人与农民相似的地方,是他们把码头当作赖以活命的土地,把扁担当作他们的家产,子孙世袭,世代相传,人与人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码头与码头之间,一个劳动团体与另一个劳动团体之间都划下了很清晰明确的界限,一旦有人来侵犯他,他一定会拼命,这是很必然的事情。”[18]对土地的迷恋与追求,对家族利益的维护,正是码头纷争不断出现的深层原因。
2.3武术的进入
程大力先生指出“武术绝大部分内容产生于、用于私斗”[19],引发民间私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限资源利益的争夺,包括水源、土地等等,宗法社会有种内向的凝聚性,所以民间械斗基本是宗族与宗族之间大规模的争斗,而在文治政府的监管下,民间私斗基本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民间武术基本在家族内部传播,而在失去法律制度下的码头群体,为武术的根植与传播提供的优越的空间。
以广州港为例,控制永安码头的”东莞同乡国术团“头子陈年柏,利用宗族关系,规定凡同乡皆可到本码头工作,但要以参加”国术团“为先决条件。[20]以蚌埠码头为例,蚌埠码头开埠以后,北方各省大批流民纷沓至此谋生活命,这其中亦有众多的拳术高手,早期的蚌埠码头由青帮头目曹杰臣与铁路工头张凤祥把持,并高价聘请外来拳师专为“打码头”服务,后又规定入班工人一律要拜师、学拳,随着蚌埠码头兴盛,许多封建把头割据一方,纷纷效法,如二号码头的张云山一个粮班班竟请七位拳师。练拳术、“打码头”成了蚌埠码头工人的必修课。而如今流传于蚌埠武术界的宋、胡、房、郭、时五大门,其开山鼻祖均是民国时期,流徒于蚌埠的拳师,其凭借一身武艺,受雇于码头大佬,在码头工人和其他行帮群体里面传授武艺,使得各家拳术得以流传与弘扬。[21]
3 武术与码头的二元关系
近代码头与武术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码头对武术来说,一方面为武术提供了得以施展与传播的空间,弱肉强食、残酷无情码头生态环境对各色拳术会被迫进行一次筛选与淘汰,而优秀拳更种会在交流中得到升华,同时迫使武术更趋向与实战技击,如蚌埠码头的宋门心意与胡门少林拳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宋门的打法,胡门的破法”之说,而宋门自身又在形意五行拳的基础上,演化出安徽派形意拳独有的心意五行连环拳;另一方面码头又为武术提供了得以传承的载体,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的,武术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足量的群体大众,武艺的习得对码头个体自身安全及资源抢夺都有直接的实效性,而这种实效性正是码头武术得以大范围开展的真正原因,解放以后,蚌埠码头帮会现象得以治理,码头械斗不复存在,而脱离码头组织的群体依然携带武术行走各地,使得蚌埠码头武术拳派在各地生根发芽。
武术的进入同时为码头社会提供了相对的平和与秩序,一方面武术的宗法制在码头社会中表现的淋淋尽致,同习一拳门,同为一家人,门派中,大家以父子兄弟相称,这种父子、兄弟的结构秩序,弱化了个体的差异性,同时为整个的群体获得了一份平和与安定,且随着各帮会、各门派及各群体受到武术的影响而壮大时,彼此间会形成一种权力的制约,迫使各个群体之间均保持一种畏惧感,从而在问题的解决上会寻求一种相对和平的解决方法,进而避免残暴的流血冲突。
4 码头环境下武术的群体性表现
如程大力先生指出“武术就是徒手或手持武器搏杀格斗的方法或武艺。”[22]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武术就是一种搏杀取胜的工具,或就是一种工具,搏杀技击只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在特定的环境中,武术除了搏杀,会不会还有别的功能作用?关于蚌埠心意拳在码头开展的情况《蚌埠市志》有“至解放初期,心意拳习练人数达2500多人,而投过帖子,学过几趟拳的更不计其数。”而这其中真正得到宋门真传的也仅仅几十人之多,除此之外不计其数的跟随者,为的绝不是单纯的对武术的热爱或追求,而是通过武术在动荡中寻求一份安全。
血缘宗法制是中国农耕社会的独特结构,其一个显著特点是群体性,如梁漱溟在论及中国文化特征时讲到“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的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23]对于整体而言,个体必须服从整体的意愿与安排,但对个体而言,整个家族又会为个体提供生活、安全、教育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在这种惯性之下,许多脱离宗族保护的个体会自觉或不自觉的组成一个群体或寻求一个群体的庇护,而近代盛行的八拜之交、煞血为盟、投贴拜师等仪式,正是“虚拟血缘”宗法制度形成的产物。武术根植于民间,同时移植宗法特性,形成了一种师徒如父子,门内如手足的宗法观念,但与其他结拜不同的在于,武术团体确有其如血液般流淌于家族成员中的实质,那就是各门各派独有的拳术体系。
在动乱的码头社会中,习练拳术一方面在于搏杀自卫,而众多投拜师贴,仅学两趟拳的,为的不是搏杀,而是通过拳术这一“血缘”纽带加入这一群体,在恪守门户的情况下,追随者仅学一两套拳术,基本就完成了进入这一门派群体的目的,且获得了这一宗族的“血脉”及认可。这里的武术就是一个工具,连接个体与群体的之间“血缘”纽带的工具,不含有半点搏杀技击的含义,甚至门派群体中有的个体所进行的武术练习不是为了获得技能,只是沟通情感。乃至当其拳术遗忘以后,而师徒、师兄弟情分依然不减,因为彼此间追求的不是拳术的境界,而是情感的境界。
[1] 读秀搜索,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 =900015804432&d=5D9213A325B3926FBC71A860AF27 9CFC.
[2]马义平.近代铁路兴起于华北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变迁[J].中州学刊,2014(4):148-150.
[3]易富贤.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J].社会科学论坛,2010(1):150.
[4]池子华.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9.
[5]池子华.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16.
[6]蚌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蚌埠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1324.
[7]苏长梅.武汉人口[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3.
[8]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98.
[9]汤黎. 人口、空间与汉口的城市发展 1460-193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91.
[10]皮明庥.武汉简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125.
[11]易江波.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43.
[12]王玉德.武汉码头文化的历史源流与发展演变[J].世纪行,2011(5):45.
[13]蚌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蚌埠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779.
[14]杨立民.传统帮会规则的宗法特性探析[J].民间法,2011(0):175-181.
[15]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46.
[16]涂文学.武汉码头的转型及其大码头文化[J].荆楚文化,2009(3):187.
[17]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66.
[18]易江波.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98.
[19]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52.
[20]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323.
[21]王校中.蚌埠心意拳研究[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15:37—42.
[22]程大力.体育文化历史论稿[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220.
[2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e of the Modern Port on Wushu Development
Wang Xiaozhong1Tan Guangxin2
(1.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5, China;2.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36, China)
The rise of modern port has a unique era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y, its unique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organization forms have been the hot topics in the study of many scholars, of which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s a kind of subject.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erminal groups and terminal organization form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of wharf social tendencies, and in Hankou, Shanghai, such as terminal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Huaihe river, analyzes in detail Wushu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orts, points out that the nature of Wushu and the patriarchal clan group of wharf group played a peaceful living environment regulation and balance, ports played a powerful role for the sprea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Wushu.
WushuWharf cultureGangPatriarchal clan
G85
A
2096—1839(2016)10—0012—04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武舞历史文化流变及其启示研究,编号:15CTY020。
1.王校中(1989~),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武术史及武术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