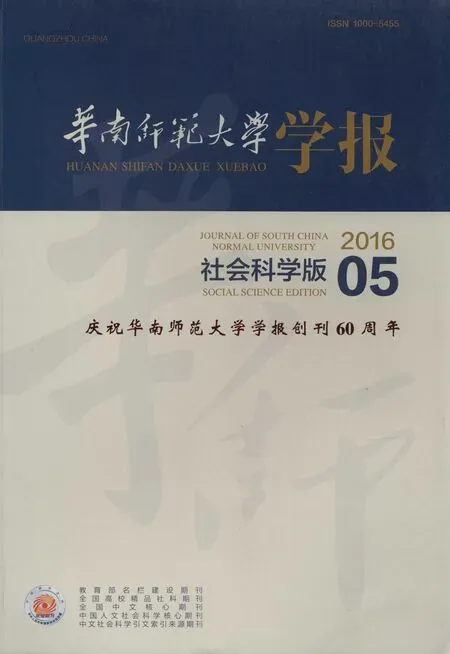乔亿《大历诗略》与格调诗学的深化
蒋 寅
乔亿《大历诗略》与格调诗学的深化
蒋 寅
宝应才子乔亿深为沈德潜所赏,是乾隆间格调诗学最重要的传人。其诗歌观念以性情为体,但主张“所谓性情者,不必义关乎伦常,意深于美刺,但触物起兴有真趣存焉耳”,则异于沈德潜之说。其论诗之用,主张根于经史,积学知道,着眼于大处,对沈德潜诗学之精深博厚固能大体仿佛,而于沈之迂腐肤廓也未能或免。其《大历诗略》是古代唯一一部大历诗评选,也是格调派诗歌评点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集中展示了格调派评点的批评风格和批评话语。乔亿诗学总体上显示出格调诗学在乾隆年间的深化。
乔亿 格调派 诗学 大历诗略
一、乔亿其人及其诗学
沈德潜的新格调诗学是乾隆前期诗坛最有影响力的诗学思潮。在沈德潜沐浴着高宗空前绝后的荣宠告老还乡后,吴中士子向风景从,传习其诗学,其中尤以“吴中七子”最负时名。但在已知的沈门弟子之外,还有一个后辈诗人,对格调诗学的承传和发挥作出了更令人瞩目的贡献,那就是宝应才子乔亿。
乔亿(1702-1788),字慕韩,号剑溪,江苏宝应人。祖莱,号石林,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宏词,官翰林侍读,是江淮间声望仅次于冒辟疆的诗人。乔亿初为太学生,应试不第,遂弃举业,肆力于诗。尝客游山西,主讲猗氏书院、郇阳书院。晚归教授乡里,从游者有著名学者刘台拱、朱彬,可惜都以经学名世,未传其诗学。*乔亿事迹详(清)朱彬:《剑溪先生墓表》,见《游道堂集》卷四,光绪刊本。乾隆初,沈德潜执东南坛坫牛耳,海宁查氏群从以诗鸣于浙西,乔亿游于其间而能自树一帜。同郡后学焦循跋《大历诗略》,惋惜乔亿“以诗名江淮间,与长洲沈归愚宗伯之名相埒而不相下。宗伯晚年遭遇特隆,而剑溪以太学生老,故其名不甚彰显”*(清)焦循:《书乔剑溪选大历诗后》,见《焦循诗文集》,上册,第331—332页,广陵书社2009年版。,可能有点夸大了乔亿的声望。姑不论沈、乔两人名声显晦,仅就年辈而言也是有明显差距的,沈德潜要长乔亿近30岁。所以朱彬提到乔亿早年与沈德潜、沈起元的交往,称忘年交。*(清)朱彬:《剑溪先生墓表》,又见《游道堂集》卷二《兰言集序》。
考乔亿与沈德潜的交往始于乾隆六年(1741)。是年乔亿入京,以诗投贽,请沈德潜为撰诗序。乾隆十六年(1751)冬,沈德潜为《剑溪说诗》作序。乔亿有《沈归愚先生过访奉呈十六韵》致意,沈德潜以四言古体三首作答,称:“诗道波流,滔滔何底?雕斲伤真,绮靡乖体。不图今日,复闻正始!”*潘务正、李言编校:《沈德潜诗文集》,第1册,第46页。乔亿《剑溪说诗》附录载沈德潜诗,题作《壬申冬日乔君慕韩自白田至感旧言怀出示近诗并剑溪说诗二卷未远风骚欣然成咏》,壬申纪年似有误。言下流露出对乔亿诗学观念的由衷赞赏,当时因视乔亿为沈德潜诗学的传人。吴本锡《狂歌呈乔五丈慕韩》有云:“当今风雅孰宗主,国老尚书沈先生。海内英俊待甲乙,人人自拟登龙门。尚书汲引无不可,心眼所照惟髯卿。”*(清)吴本锡:《寄云楼诗集》卷二,嘉庆二十五年刊本。按:诗作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之前。但就沈、乔两人诗学的交集而言,似乎更多是同道相应而非师弟承传。
乔亿的诗学观念集中表述于《剑溪说诗》一书,他对诗歌的看法,很多地方都与沈德潜的见解相近。这也很自然。沈德潜诗学多承王渔洋之说;乔亿最服膺的同样是王渔洋,书中取渔洋之说甚多。乔亿论诗难得用“格调”概念,却多用“格韵”一词,似乎直接将神韵融入其中。总之,在他的诗论中明显可见新格调诗学与神韵诗学一以贯之的精神。
乔亿持论颇为闳通,这正是王渔洋、沈德潜论诗的共同特点。朱彬述乃师平生诗学进阶:“始学汉魏、六朝、中唐人,中岁肆力于杜,晚年泛滥于韩、苏、白、陆诸家。靡不撷其菁英,探其奥窔,磨肌戛骨,剥肤椎瀡,高情远韵,邈然绝俗。其取人不专一能,凡韵语单词,佳者辄录藏箧中,对人讽诵,不可弭忘。主教河东猗氏,河东人士能诗者咸宗仰之。迨归休于家,淮扬之诗人不远数百里,出所作质翁。翁于诗不专一格,意所不可,涂抹不少贷。虽负盛气者,鲜不心服。”*(清)朱彬:《剑溪先生墓表》,又见《游道堂集》卷二《兰言集序》。虽然中年以后致力于杜诗,但我们读《李白论》《书元稹李杜优劣论后》,都见议论很持平,没有一般宗杜者那种对李白的偏见。



《剑溪说诗》的议论,整体上比沈德潜《说诗晬语》更有深度。除了诗歌体制和范式的研究更为全面和具体,写作技巧层面的揣摩也更加细腻和深入。其独到见解还包括:
古诗云者,托兴古、命意古、格古、气古、词古、色古、音节古也。后人古诗不古,直可谓之拗字体耳。
转韵无定句,过意转、气转、调转,而韵转亦随之。⑩

唐人对古诗的把握原本于体制、声调无所偏倚,宋代以后开始关注古诗的声调规则,清初诗家对古诗声调的细致揣摩使古诗写作愈益朝声调取向倾斜。乔亿有感于此,从托兴到音节全方位强调古诗的诗性特征,重塑了格调派的古诗观念。前人讲转韵,只包括韵、意两个要素,乔亿这里又补充气、调两个要素,丰富了对诗歌意脉层次的认知。音节则将近体、古体分而论之,近体讲究字音的轻重清浊,古体则讲究韵律的舒疾低昂,这是远比前人深刻的见解。自从唐代近体格律定型后,讲声律都着眼于平仄谐和,顶多顾及上去入三声的调配;乔亿提出音节的讲究不只限于四声,还要兼顾喉舌腭齿唇五音,接近词曲的声律要求,是对诗歌声调的进一步细化,开了乾隆时代新一轮诗歌声律学研究热潮的先声。
另外,乔亿诗歌评点的细腻同样使沈德潜相形逊色。沈德潜《别裁》诸选,不仅评语寥寥,措辞也极其简略。乔亿《大历诗略》的批评却细致到与翁方纲的肌理批评堪有一比。如卷五选皇甫冉《三月三日义兴李明府后亭泛舟》诗:
江南烟景复何如,闻道新亭更可过。处处艺兰春浦绿,萋萋藉草远山多,壶觞须就陶彭泽,风俗犹传晋永和。更使轻桡徐转去,微风落日水增波。
乔亿在首句旁批“义兴”,次句批“后亭”,五句批“李明府”,六句批“三月三日”,七句批“倒出泛舟”,*(清)乔亿:《大历诗略》卷五,乾隆三十六年居安乐玩之堂刊本。全诗的脉络剖析得一清二楚。卷六刘复《春雨》,乔亿批:“刘水部诗肌理细腻,气味恬雅,殆无一字类唐人,真绝尘品也。”这里正巧也用了“肌理”一词,说是偶然却又像有着某种必然。乔亿的《剑溪说诗》虽然比袁枚、翁方纲的诗话更早写成,但其中却似已综合了两家的思想,或者说蕴含了性灵、肌理说的部分观念。这一方面可认为乔亿诗学具有某种兼综色彩,另一方面又可说反映了乾隆诗学的特点,各家诗学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乔亿仿佛站在三家诗学的交叉点上,比同时代的其他诗论家具有更多的可能性。而比起沈德潜来,后者的精深博厚固能仿佛之,而其迂腐肤廓也未能避免,并且时而流露出明代格调派那种画地为牢的武断习气,如称“六朝诗音无不善,唐音有善有不善,宋以下率皆有声无音”*②⑨⑩ (清)乔亿:《剑溪说诗》又编,见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127,1117,1127,1127页。;又言“五言盛于汉魏,大衍于晋,衰于齐梁,杂于唐,亡于宋”②;或干脆断言“长庆后无五言诗”*(清)乔亿:《剑溪说诗》卷上,见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084页。。这就像叶夑说的,“其取资之数,皆如有分量以限之”*(清)叶夑:《原诗》外篇上,见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90页。。沈德潜基本上已没有这种毛病,但乔亿仍时常好作大言,是其一病。
二、大历诗研究与格调派批评话语
以享寿八十七而言,《剑溪说诗》只能说是乔亿中年的著作,20年后他又刊行了一部《大历诗略》。据书前乾隆三十七年(1772)所作自序,本书创始于乾隆二十二、二十三年间,历14年四易其稿而成。这个六卷本的大历诗选评应该集中了他晚年的诗学见解。由于大历诗歌历来不受重视,乔亿这部评选也一直不入研究者视野,直到近年才成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为学界所关注。*郝润华:《乔亿及其〈大历诗略〉》,载《文献》1996年第2期;吴小娟《乔亿〈大历诗略〉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关于乔亿诗学的根基,朱彬说是“始学汉魏六朝中唐人”,乔亿自己则称“习复于杜而涉猎于李”*(清)乔亿:《书元稹李杜优劣论后》,见《剑溪说诗》又编,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119页。。焦循读过他《小独秀斋诗》等五种诗集,也说“不专主大历家数”*(清)焦循:《书乔剑溪选大历诗后》,见《焦循诗文集》,上册,第332页,广陵书社2009年版。。但笔者细读《剑溪说诗》,仍感觉乔亿对中唐诗曾下过很深的功夫。那么,在中年学杜之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又转而重治大历诗呢?笔者推测可能出于现实的取法策略。他训导后学确实说过:
大历诸子力虽不厚,而体制轻圆,血脉动荡,可为发轫标准。*(清)乔亿:《郇阳书院条约十二则》,见《剑溪文略》,乾隆刊本。
这虽是就试帖而言,但包含了他对大历诗的总体认识和基本定位。对于一个成熟的诗人来说,趣味和师法途径的不一致,正如理想和现实的差异,是自然而然的事。王渔洋诗学标举盛唐,但实际取法多从中唐入手。这自宋以降实在是很常见的现象,晚唐、南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明人自闽中十子、泰和派直到前后七子,虽言必称盛唐,实际多从钱起、刘长卿、刘禹锡入手,上溯于王维、李颀。乔亿钻研杜诗后发现不易入门,退而取径于大历,也是很自然的结果。
但问题是,自格调派的鼻祖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唐诗划分为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大历诗就不曾获得较高的评价。明七子独宗盛唐,“大历积衰,至于元、宋极矣”,几成世间定论。以至于钱谦益感叹道:“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余子焉。”入清以来,虽有王渔洋推崇刘长卿七律和韦应物古诗,一些唐诗派名家也颇学钱起、刘长卿,但大历诗的整体评价并无改观。在这种情况下,要确认大历诗“可为发轫标准”,首先面临一个提升其价值品味的问题。《大历诗略》卷首“说诗五则”首先揭示“为诗者不祖开元、大历有故,一为格韵高,非后人易到……一为语清省,无以展拓才思”,将大历与开元相提并论,等于将大历纳入了盛唐的范畴,这便将大历诗评价置于一个较高的平台上,所有后续的言说从而顺理成章。众所周知,对于大历诗,诗家向来有两个较负面的印象,一是边幅狭窄,二是面目雷同。乔亿虽不反对这种看法,但从内外两方面做了点修正。这就是《剑溪说诗》又编所说的:
大历诗品可贵,而边幅稍狭。长庆间规模较阔,而气味逊之。⑨
大历诸子诗,相似处如出一手,及细玩之,自有各家面目在。⑩
从外部纵向比较,大历诗虽边幅稍狭,但较后来的长庆诗品格为高,气味较胜;从内部横向比较,大历诸子虽有相似之处,但谛审之其面目各有不同。这样,大历诗人就有了一个新的定位——境界虽不算阔大,却是颇有品格和特色的一群诗人。
针对历史上有关大历十才子记载的分歧,乔亿根据现有文献,去掉作品不传的吉中孚、苗发和夏侯审,增入皇甫冉,重为编排,“以钱、郎、三李、皇甫分列中四卷为之冠,卢、韩、司空、崔、耿及冉弟曾各缀于其下。而首卷独刘长卿,体气开大历之先也。刘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后翱翔于天宝、贞元之际,不皆与钱、郎诸家接席,而散帙清华之气,湛若方新,无弗同也。惟刘复气韵尤高,顾况歌词骏发踔厉而外,录其能类似者。戎昱、戴叔伦尚存雅调,都为末卷,以尽大历之体制无遗”*(清)乔亿:《大历诗略》自序,乾隆三十六年居安乐玩之堂刊本。。入选作者凡32人。其中刘长卿85首、钱起72首、卢纶21首、郎士元30首、韩翃33首、司空曙20首、李益44首、李端26首、耿16首、李嘉祐23首、皇甫冉44首、皇甫曾15首、刘方平14首、顾况12首、戎昱9首、戴叔伦11首,重要诗人没有遗漏。书中不但收录了一些很少为人注意的诗人,如卷六之刘商、刘复等;各体作品的比例,也把握了大历诗的特长,其中收五古56首、七古33首、五律202首、七律78首、五绝42首、七绝66首、五排50首、六言1首,抓住了大历诗工于五言的特点,又显示了大历诗人写作七律的兴趣。具体到各位作者,除了卢纶、李嘉祐、顾况三家收录偏少,其余大体与各人成就相称;又能关注其个人特色,如李益多采录边塞之作。刘方平、柳中庸存诗无多而入选不少,足见乔亿对二人才华的爱重,他的眼光显然是不错的。
相比选目来,《大历诗略》更值得重视的是评点,其体例是句中有评点,诗后有总评,重要作家尚有总论。如卷一论刘长卿:“文房古体概乏气骨,就中歌行情调极佳,然无复崔颢、王昌龄古致矣。”卷二论钱起:“此公惯用颓色字,殆无一不澹雅自然。”都显出独到的批评眼光。卷二评卢纶《宴席赋得姚美人拍筝歌》:“其纤丽元人能之,恐无此矜贵也。唐人擅场在此,只六朝乐府烂熟耳。”又显示出对唐人诗学渊源的独到见识。
格调派论诗首重体制,格调派鼻祖严羽言“论诗之法有五”,第一就是体制。乔亿评诗也以体制为先,既包括扣题,如卷二评卢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如题起止,无一语溢出。”也包括风格的相称,如卷四评李益《北至太原》:“有唐发迹太原,此诗微婉郑重,最为得体。”或声韵的妥帖,如同卷评李益《效古促促曲为河上思妇作》:“兴调古,节拍又甚急,乃为肖题,真乐府也。”有些批评非常微妙,足见玩味作品之细。如卷五评皇甫曾《早朝日寄所知》,肯定“此亦早朝佳制,第四妙丽绝伦,结复轩举有致”;但同时指出“起句失势,似专为寄所知,与早朝微隔也”。按此诗首联作“长安雪后见归鸿,紫禁朝天拜舞同”,系扣紧寄所而言,点明时令兼寓“人归落雁后”的感慨,倒也寄意微婉;但相对早朝的主题来说就显得有点游离,而且也未能烘托早朝的堂皇气象,乔亿谓之“失势”即气势低落,切中其微瑕。最有意味的是卷二评钱起《东皋早春寄郎四校书》“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一联:“三四得立言之体,亦几于敦厚矣。”就连诗教在这里也是从体制而不是作为创作原则来把握的,足见乔亿是个纯粹立足于格调派立场的批评家。
凡格调派诗家都主气象。严羽将格调作为论诗的五个要素之一,许学夷以气象“概论唐律”*(清)许学夷:《诗源辩体》,第3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乔亿论诗则每用气象来概括作品或作家的整体风貌。如卷一评刘长卿《新息道中作》“七字画出离乱惨悽气象”;卷二评钱起《寄郢州刺史郎士元》“气象好,结尤高浑”;评钱起《和李员外扈驾幸温泉宫》“清丽是右丞一派,但气象未能浑阔耳”,评柳中庸《幽院早春》“《玉台》佳境,前六句具有娇贵气象,结殊不称”;卷三评韩翃《寒食》“气象词调居然江宁、嘉州作”;卷四评李益《送人归岳阳》“放笔阔远,亦青莲气象”;卷五评皇甫冉《同温丹徒登万岁楼》称孟浩然、王昌龄登楼诗“气象并皆浑阔”;卷六评刘方平《寄陇右严判官》“无开宝宏深气象,而章法次第井井”。从这些用例不难看出,乔亿对作品的把握通常是整体性的。他偶尔也用“格调”一词,如卷三评郎士元《宿杜判官江楼》:“格调绝类孟襄阳。”但更多的时候是用相近的概念,如卷三崔峒《题桐庐李明府官舍》评:“格韵自好。”这里的韵基本也就是调,格韵就是格调。
相对“格调”这一专门术语,乔亿经常将格、调分开来使用,比如他经常称许一些诗人笔下仍保留着不同寻常的高格。如卷三评韩翃《题仙游观》:“诗格平正,忽湔去佻小之习。”又评韩翃《送中兄典邵州》:“此一结浑雅有远致,稍见品格。”卷四评李益《五城道中》:“诗格严整,亦如军行,偏伍弥缝而不可攻。”卷五评李嘉祐《与从弟正字从兄兵曹宴集园林》:“格制平正,结复有情有态,良佳。”卷六评张南史《陆胜宅秋暮雨中探韵同作》:“季直五言高格,可匹懿孙,非戎昱诸人所及。”与“格”相近的是“风格”,也经常使用。如卷一评刘长卿《北归次秋浦界清溪馆》:“风格苍然,不减孟六。”卷三评韩翃《送客游江南》:“风格忽高。”又评韩翃《题慈恩寺振上人院》:“颔联亦风格仅高。”又评韩翃《送刘评事赴广州使幕》:“此篇风格稍上。”卷六评顾况《小孤山》:“以下二诗,风格并高。”又评顾况《奉同郎中韦使君郡斋雨中宴集》:“亦风格仅高。”
在评价作品的声律方面,乔亿使用的概念则基本是围绕着调、韵二字来构词。单用“调”字之例,有卷四评李益《山鹧鸪词》:“平调,古意。”卷五评李嘉祐《赠别严士元》:“五六神彩飞动,调亦高朗。”卷六评张南史《奉酬李舍人秋日寓直见寄》:“结体清华,调亦高朗。”这里的“调”都指声调,而用“调”构成的复合词,如“风调”和“兴调”,就评语的语境来看,也多与声律相关。用“风调”之例,如卷三评韩翃《送故人赴江陵寻庾牧》等四首:“属对太工,伤浑雅之气,而风调仍佳。”卷四评李益《边思》:“本色,有风调。”至于“兴调”,已见于前举李益《效古促促曲为河上思妇作》评“兴调古”,还有卷三评司空曙《长安晓望寄程补阙》:“颔联亦兴调绝佳。”卷四评李益《宫怨》:“兴调已是龙标,又加沉着。”将调与兴组成一个复合词,可能是他的独特用法,是用以表达他的某种趣味的概念。还有卷三评韩翃《赠别华阴道士》“歌行诸制笔力不高,而调态新颖动人”,也是一个很少见的特殊例子,以新颖动人来形容“调态”,显然指神情而非音律。
“韵”字通常不单用,与声律相关的复合词有音韵和韵调。前者如卷二评钱起《送毕侍御谪居》:“音韵弥清。”卷五评皇甫冉诗《与张补阙王炼师……》:“音韵酷似何仲言。”后者如卷一评刘长卿《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元中丞》:“不矜才不使气,右丞东川以下无此韵调也。”卷三评司空曙《送程秀才》:“情思绵绵,当于韵调转换处求之。”卷五评皇甫冉《同温丹徒登万岁楼》:“此诗韵调绝佳。”这里的“韵调”大体符合了“调”的内涵,不过当“韵”与“气”合成“气韵”概念时,它就与音韵无关而只与艺术表现相关了。卷二评钱起《裴迪书斋玩月》:“刻划不伤气韵。”卷三评郎士元《盩厔县郑礒宅送钱大》:“气韵高绝。”卷三评韩翃《送长史李少府入蜀》:“锻炼无迹,而气韵犹存也。”卷四评李端《赠康洽》:“气韵高极不见。”卷五评皇甫曾《送少微上人东南游》:“稍具气韵。”卷六评刘复《出东城》:“气韵在典午之世,唐五言及此者亦不多见。”都是很明显的例子。由卷五评李嘉祐诗“逊钱郎气韵,而情彩音格居然妙品”来看,气韵与音格即格调也不是同一级次的概念。气韵应是更高位的概念,与作品的整体有机性相关,这是由“气”本身的内涵决定的。
气作为构成性概念,在乔亿的诗歌批评中通常与作品的有机性相关。卷三评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惜落句气尽,不为完璧”,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基本上,气无论与什么概念构成复合词,最终都偏重于格的一面。卷二评卢纶《晚次鄂州》:“有情景,有声调气势,亦足大历名篇。”以声调与气势对举,气势即意味着格。卷二评钱起《送王季友赴洪州幕下》:“稍具气骨,非仲文本色。”气骨也偏重于格的方面。卷四评李益《临滹沱见蕃使列名》“有气焰”,则有点接近于卷五评皇甫冉《送李录事赴饶州》的“对仗有光焰”,有英气勃勃之义。但殊觉意外的是,气与调构成的复合概念——气调,涵义却偏向了声律方面。如卷二评钱起《早下江宁》:“气调高朗,不减右丞。”卷六评顾况《宿昭应》:“气调忽似龙标。”又评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弦急柱促,张王乐府无此气调。”由卷四评李益《从军北征》引李攀龙云:“全是王龙标气调。”可知这是沿袭明代格调派的概念。
总体看来,在乔亿的批评中,格、调两个字各有独立性,并不互相依存。既有卷六戴叔伦《女耕田行》等乐府“诸篇风格未上,雅调犹存”的反差情形,也有卷四卢纶《夜投丰德寺谒海上人》“起结俱乏风调,而品格自高”的不一致状况。但相对来说,格显然比调要更为基础。这应该反映了体格、声调两方面在格调派诗家心目中的权重。虽然格调派是诗学史上很重要的流派,其理论和批评夙来为诗家所重,属于格调派的诗歌选本也不少;但以评点著名的选本却不多见。在笔者寓目的范围中,乔亿《大历诗略》应该算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其批评风格和批评话语都是格调派评点的集中展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无论从哪方面说,乔亿都是一个很典型的格调派批评家。虽然他没有沈德潜那么大的影响,但他的诗论却更典型地体现了格调派的艺术倾向,他的诗歌批评也更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格调派的批评话语。如果要从乾隆时期格调派诗论家中选择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笔者觉得乔亿或许是比沈德潜更合适的人选。
【责任编辑:赵小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研究”(12BZW051)
2016-06-18
I207.21
A
1000-5455(2016)05-0151-06
蒋寅,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