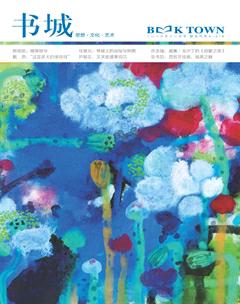文求堂遗事钩沉
尹敏志
东京专卖汉籍的文求堂书店,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了。
我最早得知这个名字,是今年六月初在神保町的原书房,收购了一批京都大学保田清教授的旧藏。保田生前专治哲学史,故这批藏书中多是梁启超、冯友兰、胡适、谢无量等人的民国老版著作。其中也有若干和本,包括朱熹《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单行本各一册,为昭和四年(1929)文求堂书店根据璜川吴氏仿宋刻本影印,从底本、用纸到印刷质量都很精良,每页密密麻麻,都是保田教授的红笔点断和黑笔批注。
几星期后,去东京古书会馆参加一年一度的“七夕入札会”,拍品预展上又看到文求堂印的另一套书:昭和十年(1935)版的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函五册线装。这套书当年印数极少,所以虽然已经有了些微虫蛀,起拍价仍高达十万日元。既售书又印书,是日本书店的特色,文求堂的出版物除了学术著作外,还有《蒙古语会话》《广东语入门》《官话北京事情》等实用小书。这家当年东京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学书店,虽然早已湮没,但其遗事仍然散落各处,雪泥鸿爪,待人摭拾。
一
根据郭沫若的自传第三部《革命春秋》,他在文求堂书店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实属无奈之举。
事情还要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说起。那年四月十二日,国共分裂,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清党,一时间腥风血雨。原本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撰文批评蒋介石“罪恶书不胜书”,不久被迫逃亡日本。虽然有创造社同仁的资助,但无奈杯水车薪,他不得不以卖文为生。结果旅日十年,成为郭沫若最高产的时期,他曾经“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费了六天工夫,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真可谓文思泉涌。
但毕竟人在异乡,获取资料并不方便。一九二八年他在寻找罗振玉的甲骨文著作时,走进了文求堂书店。郭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还在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时,他就已经来过这里,只是当年矮小的日式平房,现在已经焕然一新,被黑色三层大理石西式建筑取代,屋脊的中式造型“看起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其实当年文求堂的店铺,在本乡一丁目六番地,一九二三年地震被毁后,已迁至本乡二丁目二番地,前后不是同一处,郭沫若的记忆略有偏差。
店里面“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古今中外、新旧和洋夹杂的布局,正是昭和前期特殊的时代氛围:“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休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
在餐桌后面坐着的,是当时五十多岁的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郭氏如此刻薄地描述。虽然其貌不扬,但田中“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救堂”。
那天表明来意后,田中很快就帮郭沫若找到了店里的石印本《殷墟书契考释》,开价十二元。由于囊中羞涩,郭提出,以身上仅有的六元钱作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田中犹豫了一番婉拒了,但告诉郭:要看这一类的书,最好去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那里应有尽有,只要有人介绍,就可以随时阅览。说完,他还将在东洋文库工作的熟人介绍给郭。通过田中的引导,郭沫若发现了东洋文库藏有的一大批无人问津的甲骨文材料,学问开始突飞猛进。
两三年后再去求田中庆太郎时,郭沫若已经不是为了买书而是鬻书。当时他和日本妻子安娜一家六口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国内创造社的钱不再按时寄来,而且在汇率波动之下,他在中国发表的文章,稿费也根本兑换不了多少日元。无奈之下,郭沫若只好再次走进本乡二丁目二番地: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没有办法,只好去求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元的版税。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本书是很难再版的。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元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啦。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自己的最软弱的要害。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元老头票到手。从此,我的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连二地在日本印出了。
文中所说的书店,无疑就是文求堂。田中不愧是经常从中国进口古籍的,随口就换算出日币三百元“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平心而论,这笔钱其实不算少,因为当时傅抱石在中国留学生监督处担任书记,也不过“月领薪水六十元”。所以田中支付的版税,已经相当于国民政府一个中高级外交官员半年的收入了。后来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认,这笔钱“使我能在日本立足,识我于稠人之中,那不能不说救堂是个世故很深而具有锐利眼光的人”。
而根据其他人的记载,田中庆太郎对流亡时期的郭,可谓百般照顾。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说,自己在第一高校当教师时,经常事先给文求堂打电话,预订中午在店内吃的盒饭。有时电话打过去,正好郭氏也在店内,主人就邀请两人一起去“天满佐”饭馆吃午饭,这样的事情有过好多次。另一位日本学者增井经夫也说:“先生侨居日本的十年间,交游并不那么广……郭先生最经常出入的,是文求堂书店。那一时期,我每次到文求堂去,郭先生几乎总是坐在客席上。我常常坐在他的近旁,同他长时间地闲谈。先生始终保持着刚强的神态。”
郭尽量避免与人来往,是因为在一九一○年的“大逆事件”后,日本政府对于“赤化分子”的监视非常严密。郭沫若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外国人,自然成为便衣警察重点关注的对象:“日本警视厅常到文求堂去,向主人一一查问郭氏的动向,文求堂主人一概都设法给庇护过去了。战争开始后,郭氏对文求堂主人什么都没说,就将太太、儿子留在这里,自己秘密地独自回国了。他走之后,主人对郭氏的行为也是能够理解的。”
二
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究竟是像郭沫若自传所描述的,仅仅是个商人,还是如长泽、增井所说的,是郭氏的恩人?对于郭沫若一九三七年回国后态度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在殷尘(金祖同)《郭沫若归国秘记》中对田中有“满肚子怀着鬼胎”“把钱看得很重”“具有一般日本人的小家气”“一个侵略主义者的信徒”之类的酷评,不少日本人闻之错愕,用伊藤虎丸的话说:“郭先生回国之后,却有时表示对田中先生不满,至少据说如此,这当时就使日本方面的有关人感到难以理解。”
一九五一年田中去世后,留下了二百多封郭沫若的私信,起于一九三一年六月,终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它们在田中女婿增井经夫手里,一存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良春、广岛大学教授伊藤虎丸才开始负责整理这批文件。十一年后,《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出版,比起掺杂个人感情的回忆录,这批原始档案,无疑是还原两人关系的最佳材料。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一九三一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和《金文丛考》在文求堂出版,并大受学界好评后,郭氏与田中的关系变得很亲密。当年九月,郭氏在信中写道:“顷颇欲决心于中国文学史之述作,拟分为三部,商周秦汉为一部,魏晋六朝隋唐为一部,宋元明清为一部。期于一二年内次第成书。此书如成,需要必多。特憾家计无着,不识有何良策见教否?”很明显,郭沫若是希望田中预支其稿费。虽然看不到田中的回信,但从郭氏一个月后“诸蒙厚待,衷心感谢”的句子推断,至少是满足了部分要求。这样的情况非一次两次,就在回国那年,郭氏还因为债主催逼,向田中“再欲支三百元”。
除了预支生活费外,田中还为郭氏的妻弟佐藤俊男来东京求职提供过帮助,在店里招待过其妻及长子,赠毛笔,赠杂志,赠暑衣数件。更令人讶异的是,田中在经营书店的百忙之中,扮演郭沫若的研究助理角色,为其去上野图书馆摹写《古玉群谱》中的玉雕全佩图,抄录陈奂《毛诗传疏》中《小戎》篇“蒙伐有苑”句之疏文,向河井仙郎、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接洽制作他们藏品的拓片,并将店里的《周礼正义》《籀范》等书借给郭参考,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在旅日十年间,郭沫若的考古学著作全部由文求堂书店出版,总计九部。根据殷尘的记载,郭曾“带着思虑和愤怒”向他抱怨,这些书出版时,田中从来没给他登过广告,书的销路,完全是卖“郭鼎堂”三个字(《郭沫若归国秘记》),实际情况如何呢?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的上海《申报》上,就有这么一则广告:
郭沫若新著考古学书三种
文学家郭沫若自译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更潜心于甲骨学之专门研究,近日在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新著三种:
(一)《金文丛考》(八元二角五分)
(二)《金文余辞之余》(二元七角五分)
(三)《卜辞通纂》(十三元二角)
其《金文丛考》中,如《传统思想考》《新出土三器释》,均有精湛之考释。《卜辞通纂》为治甲骨学之总集,均为我国治此学者所当参考。现由本埠四马路现代书局代售,书到无多,欲购宜从速。
可见正是借助田中庆太郎的关系和销售渠道,郭沫若虽然流亡日本,不但研究条件到基本满足,还能与国内学界保持联系。比如在鲁迅的日记和书账中,就可看到他对于文求堂所出郭沫若的著作,基本上是见一本买一本。故郭氏与田中的关系,恐怕还是长泽、增井的说法更接近实情。
日方证词的真实性,有另一佐证,即《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中日期为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的信件:“日前奉上信片,云拟约长泽先生作伴同赴金泽文库。特地烦劳长泽先生,实无必要,故此约作罢。匆匆专此奉闻。” 由此可知田中、长泽、郭氏三人相互熟稔,长泽规矩也没有信口胡说。
很多迹象显示,田中庆太郎对郭氏之照顾,纯粹是因为钦佩后者之学问。否则,他不可能让自己最钟爱的次子田中震二拜郭沫若为师,随郭氏一起去京都等地游历。那么,为什么郭沫若要刻意掩盖他与田中的私人关系呢?除了中日开战的因素以外,恐怕也与后来政治环境的突变有关。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政策,全面拥抱社会主义阵营。翌年,《革命春秋》在海燕书店出版,当时身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的郭沫若,是不太可能逆势而为,津津乐道于与田中的往还的。强调自己与文求堂老板仅是顾客与商人的关系,无疑在政治上更为保险。曾在东京共同赏春,“步《岚之歌》韵,赋狂歌一首”,“相对素心人,神游话悠久”,这些则都是不可言说的。
但在私底下,郭沫若对于田中,恐怕也不无愧疚。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他率团访问日本,待了近三周,其间受到热情招待。在此期间,郭沫若特地抽空,独自赴神奈川县叶山高德寺,祭奠过世不久的老友。当时田中的遗孀田中岭在场迎接,据说两人皆泪洒墓前。“我对郭氏的敬佩之处是,在他来日的百忙之中,还特意赴叶山,到文求堂主人的墓前表示敬意”,后来得知此事的长泽规矩也评价道。
三
文久元年(1861),文求堂书店创业于京都寺町街四条北边路西,原本是一家皇宫御用的书店,店名“文求”,乃年号“文久”的谐音。江户末年日本内忧外患,尊王攘夷论随之兴起。文求堂大量出版西南藩维新派的著作,为之推波助澜。二代目田中治兵卫还以书店为据点,照顾各方维新志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的驻德公使、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1843-1900)。天皇与新政府迁都后,一九○一年,文求堂也将店址搬到东京。
田中庆太郎出生于一八八○年,年轻时就读于东京外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是著名书志学家岛田翰(1879-1915)的同班同学。岛田博闻强识,著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勘》,其最重要的事迹,就是帮助三菱老板岩崎弥之助买下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十五万卷,建起静嘉堂文库,但他后来因为在图书馆窃书的行径而声名狼藉。内藤湖南回忆:“光绪末年,中国各省的提学使十余人来到日本,其中还有几位校勘学的大家,却都被岛田很是戏弄了一番。”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暂且存疑,但从这位精通版本的岛田那里,田中肯定学到不少。
大学毕业后,田中庆太郎经常去中国游历。从一九○八年开始,更是在北京购置房产,一住就是三年。刚开始,他对中国古书的版本还一无所知,故购买了邵懿辰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书目》等书日夜研读,与傅增湘等中国版本目录学家来往,并大量购买古籍、书画、碑帖邮寄回日本。日积月累,他逐渐锻炼出了“看汉籍的天头地脚,便可以认出书籍的好坏”的锐利眼光。
北京琉璃厂一带的旧书肆自不必论,上海专卖线装书与新版木刻书的老店,如中国书店、蟫隐庐、博古斋、来青阁、汉文涧等,也与文求堂有密切的业务往来。多年经营之下,来自北京的旧版书,来自上海的新刻书,再加上日本的和刻本和舶来汉籍,各路汉籍百川归一,文求堂贩售的书日益可观。
这从大正二年(1913)一月的《文求堂唐本目录》中可窥知一二。目录上以清刊本和明刊本居多,后者包括南监本《后汉书》、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通记》等。南明史料方面,则有震川温睿临原刊本《南疆逸史》、钱谦益《初学集》崇祯原刊本、吴应箕《楼山堂集》。更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宋版书,比如著名的南宋绍兴年间“眉山七史”,又称“九行邋遢本”,文求堂仅缺其中《梁书》一种而已。
单套书的价格,一般在十元以下,其中初印本、宣纸印本会提价到几十元,标价几百元的,就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珍品。至于上千元的书,翻遍目录,也仅有宋版《史记集解》一部而已。此部书一匣十四册,为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本,原本一百三十卷,但仅存五十八卷,由于是天下孤本,所以标价高达一千五百圆。再翻阅二月的《文求堂唐本目录》,已经不见此书的条目,谁那么快就把书买走了呢?
此人正是东洋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说宋元版》一文中,他在讲到坊刻本多精于官刻本时,提到一句:“例如家藏绍兴八年《史记集解》,虽然比《毛诗正义》还要早一年,样式上却和宋元版相同。”说的便是这部天价书,只是绍兴八年的说法有误,应是绍兴十年。从所附书影中,可知此书曾先后被井井居士及岛田重礼收藏。井井居士,即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竹添进一郎(1842-1917),以研究中国经书闻名,著有《栈云峡雨日记》。岛田重礼(1838-1898)则是岛田翰之父,所以这部《史记集解》,很可能是经岛田翰之手卖至文求堂的。
在得到此书之前,湖南已经收入一部北宋小字刊本《史记集解》。在得到两部宋版《史记集解》后,他志得意满,先是特制一枚印章“宝马盦”,后又写下一首诗,曰:“史记并收南北宋,书生此处足称豪。”
一九二九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访问日本,调查中国古籍。十月底,他慕名来到京都府南郊加茂町瓶原村的恭仁山庄,已经退官三年多的内藤湖南,给傅氏看了这部绍兴版《史记集解》。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史部”中,描述完了此部书的版式后,傅氏接着论证其为南宋版无疑:
每叶钤“兰陵家藏书籍”朱文印,为日本飞鸟井伯爵故物。
按:此本铁画银勾,字体雕工与瞿氏藏周易相类,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又,此书行款前后不同,或有因此致疑者。然以余所见,宋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半叶十行十八字,卷十五以后则为每行十九字。又见元刊《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半叶十二行二十一至二十四字,卷三以后有十三行十四行不等,并有缩至十一行者,宋元本间有如此者,不足怪也。
现藏京都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的《清三朝实录》,据学生神田信夫所说,也是内藤湖南一九一三年从文求堂购入的,当时的价格是三百元。但这部关于清太祖、太宗、世祖的编年体史书,究竟是辛亥革命后由大陆流出,还是江户时代便已随唐船来日的旧抄本,真相却一直不太明了。我倾向于认为是前者,因为辛亥革命之后那几年中国政局不稳,旗人生活无着,大量清宫旧藏流散国外,时间正好是一九一三年前后。
在一九一七年发表在《史林》上的一篇考证《宪台通记》的文章中,内藤湖南提到:“数年前,现任中国大理院院长董康氏侨居京都吉田山时,带来了十六七册从北京书肆买到的《永乐大典》,分给了我、京都帝国大学、其他大图书馆及个别学者。之后,东京文求堂也从北京弄到了几本,最后都被富冈谦藏氏收藏。我从董康氏那里也分得一册,为两卷装订在一起。”
但据田中自己所说,他从北京总共购买了二十册《永乐大典》,其中五册后来辗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十五册归东洋文库:“进入中华民国后,关于清朝掌故类的满文、蒙文书籍,比如在清朝非常贵的《皇朝礼器图式》《皇清职贡图》等,一时间价格都降了下来,当时我搜集购买了不少这些便宜的书……再以几倍的价格卖出去,也还是便宜。”
湖南提到的董康(1867-1947),字授经,江苏武进人,为清末进士,辛亥革命后流亡日本学习法律。当时他和罗振玉、王国维,都是旅日中国学人中与日本京都学派关系密切者,只是著述不多,名气远不如雪堂、观堂二老大。回国后,他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法制史学家仁井田陞访华时,他曾带着后者去菜市口,参观清朝的监狱和凌迟用具(仁井田陞《中国の伝統と革命》)。但在抗战期间,却因为加入汪伪政府而堕入深渊。
董康酷爱藏书,专收戏曲小说,他在日本既售书又购书,与岛田翰志同道合,两人曾一起“秋日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纵观古刹旧家之藏,浃旬而返”,后著有日本访书记《书舶庸谈》,并编纂《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修正案》。近年北京大学花高价从日本回购的“大仓文库”,大部分都是董氏诵芬室的旧藏。只不过鲁迅颇看不上董康,曾在给内山初枝的私信中评价他只不过因印制“贅沢な本”(复刻古本)而闻名,“在中国算不得学者”。
董康当年也是文求堂的常客,时任东洋文库长石田干之助回忆:“在田中先生处相遇最多的……外国方面,有中国的董授经先生。”一九二六年,因为北伐战争波及,他再次避居日本半年,基本每天都在宫内厅图书寮、尊经阁文库、内阁文库等地调查古籍善本,牵桥搭线的多是田中庆太郎。翌年三月二十九日,董康的日记中有“田中约至(东京)大学赤门前杏花楼晚餐”的记录。当天到场的,还有内藤湖南及其学生稻叶岩吉,四位版本学家畅饮至深夜方散。
四
文求堂的第一次经营危机,发生在一九二三年。那年九月一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大藏省、文部省等公共机构,南天庄文库、黑川文库、松栖舍文库等私人图书馆,都有大量藏书损失。在这场堪与“应仁之乱”并称的浩劫中,单是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一处,就有七十六万册图书被烧毁,其中包括德国梵学家马克思·穆勒(Max Muller)的全部藏书、五台山本朝鲜《李朝实录》《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西藏文大藏经》等等。文求堂也难逃一劫,辛苦搜集的所有的书籍和字画都付之一炬。
吸取了教训的田中庆太郎,毅然决定在重建书店时,放弃传统的木质结构,改用钢筋混凝土建筑,店铺和住宅一体,这就是后来连二战时盟军空袭都未能摧毁的新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地震后,田中暂时放弃经营古书,改从上海大量输入白话文教科书,由于价格低廉、需求量大,故收到很多订单,“从资本收回、资金流动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我经营最成功的,因为程度相对低等的书籍比高等的书籍更容易收回资本”。
更大的危机是来自家业继承方面。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寄予厚望的次子田中震二早逝。震二很早就跟随郭沫若学习中文及历史,聪明机敏,还翻译了郭的《青铜器研究要纂》,不料二十六岁便身亡。爱子病逝对田中打击极大,两年多后,他在书志学著作《羽陵馀蟫》的附记中还这么写道:“六月六日完成此书时,已是深夜,本乡区的街道,万物寂静……依稀中仿佛听到亡儿震二的声音。”真是痛彻心扉。但在那以后,他重新振作,改让长子乾吉克绍箕裘,为此特地派他去北京,进修汉籍知识,为接班做准备。
随着中日战争逐步升级,中国作家学者纷纷回国,文求堂书店里说中文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时荷兰外交家、后以《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成名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恰好来东京公使馆工作。高罗佩回忆自己刚去文求堂时:“我的日语还说不好,但是同他(田中)却可以用北京话对谈,因而感到非常的愉快。”一九四○年五月,德军入侵荷兰的消息传来时,田中打电话邀高罗佩来店里看一部新到的明版书:“看过之后,又经他邀请去日本餐厅……我当时只顾吃饭,事后想起来才明白,他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做的。”
高罗佩的学术趣味异于常人,研究古琴、长臂猿及房中术,严谨到近乎古板的日本学者,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长泽规矩也回忆这位身材高大的外交官“日语讲得好,北京话也说得好,还会弹中国琴。在酒席上和着三味线琴唱俗曲,净是些下流的歌,也不知是谁教给他的”。当时在店里帮忙,端茶倒水的三子田中壮吉则记得,高罗佩每天和父亲嘻嘻哈哈时,嘴里经常蹦出从日本歌舞伎那里学来的俚俗词汇,“地道的东京下町艺人们说的方言,想回答都很为难”。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高罗佩最后一次来到文求堂,当时日荷两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那晚下着雨,他既没有带伞,也没脱被雨淋湿的外套,就这样在门口与田中庆太郎谈了五分钟,然后又坐车匆匆离去。离开日本后,痛心国难的他先是在荷兰军中服务,后辗转来到国民政府陪都,在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中任职。一九五一年,等他再度回到日本时,文求堂已经物是人非了。
战争期间,从日本向中国汇款变得困难,邮路也时断时续。大部分日本人连温饱都成问题,根本没余力再购买书籍。为了支撑战争,日本政府开始加强对物资的管控,古书合作社也变成了统一管制的对象。此时田中庆太郎被诸理事推举为理事长,其工作得到同僚的一致肯定。至于文求堂的日常工作,则已经渐渐落到长子、三代目乾吉肩上。
熬过了最苦难时期的文求堂,却在战争结束六七年后连续遭到打击。先是一九五一年,七十二岁的田中庆太郎因病去世。次年,田中乾吉也在四十三岁的壮年身亡。三子田中壮吉由于成长于战时,不具备汉籍版本目录学知识,明显不适合经营书店。最后的希望全落在田中的女婿增井经夫(1907-1995)身上,但立志于中国史研究的他却决定赴金泽大学任教。
后继乏人之下,终于到了一九五四年,延续了九十多年的文求堂书店要关门歇业了。其实当时由于新中国采取管制书籍出口的政策,帝国时代那种中国古书经营模式,本来就难以为继。以日本“古典研究会”为代表的古籍影印,之后成为汉籍传播的主流模式。长江后浪推前浪,但跟同类书店相比,文求堂因为老板的古道热肠而显得格外令人怀念。比如一九三三年二月,郭沫若冒春雪拜访田中家,回到市川后手书明信片一张感谢,结尾云:
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貌损,顿感泪痕幽。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江上路,冰雪满汀州。
二○一六年十月十日
参考书目:
《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二卷),郭沫若著,海燕书店1950年版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郭沫若著,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郭沫若归国秘记》,殷尘著,言行社1945年版
《藏园群书经眼录》,傅增湘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
《书舶庸谭》,董康著,中华书局2013年版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文求堂书目》(16册),田中慶太郎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
《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田中壮吉编,汛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年版
《日本文庫史》,小野則秋著,教育圖書1942年版
《羽陵馀蟫》,田中慶太郎著,文求堂書店1937年版
《讀史叢録》,内藤湖南著,弘文堂書房1929年版
《清朝史論考》,神田新夫著,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の伝統と革命》,仁井田陞著,平凡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