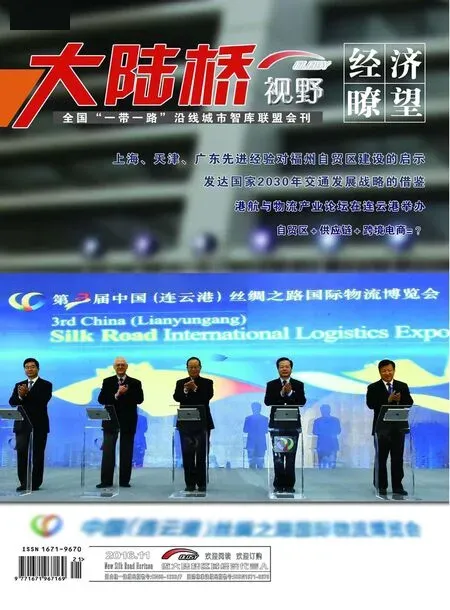文化心理学视阈下的徐福东渡
文/石荣伦
文化心理学视阈下的徐福东渡
文/石荣伦
过去学术界对徐福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民俗学的角度来展开的。我想尝试一下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去考察“徐福东渡”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看看能有怎样的发现。
我的第一个发现是这事只能发生在秦朝,准确地说只能发生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秦始皇是什么人,是毛泽东最为佩服的五个皇帝之一,被称为千古一帝。秦始皇要么不做事,做事就是大手笔。长城、阿房宫、骊山墓以及从首都咸阳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每项都是浩大的工程。“窥一斑而知全豹”,当我们走进秦始皇墓兵马俑坑时,人人皆为那雄伟的气势所震撼。有道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何况秦始皇是一个“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而“任心而行”的君王(《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给秦始皇评语是“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还说他一生“成功大”(同上)。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绝非普通帝王所能抗衡,更不可以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他所做的一切。所以,当徐福提出要带三千童男童女出海求仙人仙药时,在秦始皇的眼里,工程量并不大,于是就同意了。
那秦始皇为什么要同意徐福的计划呢?这是因为秦始皇由于过于贪恋皇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一国之事无论大小都要亲力亲为,长期加班,超负荷拼体力,还不到五十岁就老得不行了。秦始皇经常感到,他离死亡已经不远了。死亡是人生大事,相较于活,死更加重要。世界三大宗教中有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为解决人类的死亡问题而被人尊崇的。人总是要死的,可秦始皇不这么看。秦始皇不关心他是怎么来的,他关心的是他是怎么走的,他想再活五百年!所以他才让人出海去找,上山去炼,找什么炼什么,“不死之药”(同上)。
我的第二个发现是司马迁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写下来。大家知道,《史记》一书在《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 《封禅书》等不同的地方记载了徐福东渡一事,从出海的理由、出海所需的人财物、出海的规模、出海的结果等等,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得非常清楚、详细。所以,从“信史”的角度看,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东渡的历史真实性不应该再有怀疑。“徐福确有其人,徐福受秦始皇之命出海确有其事。”(王妙发:《徐福东渡日本研究中的史实、传说与假说 》《中国文化》,1995年第一期)“徐福东渡事,《史记》中的记述断非虚妄。”(阎孝慈:《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一期)司马迁惜墨如金,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于后人”“扬名于后世”的(《史记·报任安书》),也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意在“立言”,实现人生最高追求即实现人生“三不朽”中的“立言”的。从黄帝到今上汉武帝,那么多年、那么多人、发生了那么多事,所以,他对于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是非常审慎、精心的选择的。事实上,徐福并不是古代中国东渡第一人,从石器时代开始,至战国秦汉时期,因种种原因,有大量的大陆东部沿海的的中国人流亡或逃亡到了日本,在日本史上他们被成为“渡来人”,这一点已被考古学和人类学所证实。但是,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将自己名字留下来。徐福是他们的代表,是他们的英雄,是他们的图腾,是他们的文化符号。司马迁写徐福,实际上是写千千万万离开大陆,开创新生活的人。一部东北亚的民族迁移史司马迁通过徐福东渡展现了出来。这是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高明之处。
我的第三个发现是中国人面临文化冲突时所采取的态度,那就是躲避,另找人间乐土,建设新的家园。《诗·小雅·四月》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理想,《论语·公冶长》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夙愿。其实,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述而》)才是后来中国读书人的文化人格。陪不起咱躲得起,这就是中国历代士人对现行政治的心态和选择。美国学者、哈弗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告诫美国政客要防备中国文明,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甚至更为激烈的暴力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见中文版序言),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徐福作为方士,尚黄老之学,与秦始皇的崇尚法家施行苛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没有选择直接对抗,而是凭着自己的才智,乘船远离暴秦。秦代的方士命运多舛,少数人成功逃亡了,大多数人被“坑杀”,唯独徐福凭借其高才和高智,离开故土的整个过程是那么的富有传奇、那么的惊心动魄、那么的波澜壮阔、那么的轰轰烈烈!
我的第四个发现是徐福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人文主义一向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咱们在看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电影,当灾难来临时,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儿童、妇女和老人,让他们先下船,远离灾难,着实让人感动。其实,我们中国人早早就有了矜老恤幼的观念,“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在徐福看来,暴秦统治下的土地生存太过艰辛,他要带领这片土地的人们离开故乡,寻找新的家园。带谁走?他想到的是儿童,“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是说被徐福带走的童男童女中,大的只有12岁,小的才10岁。(《文选·张衡〈东京赋〉》云:“振子万童,丹首玄制。”李善注引《续汉书》云:“大摊逐疫,选中黄门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振子……。”薛综注:“振之言善;善童,幼子也。”)在徐福看来,儿童才是人类的未来,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徐福的船队比泰坦尼克号更加感人,更加令人自豪。由此我还想到了哥伦布船上的贼人、“五月花号”船上的罪犯。对徐福团队而言,不论他们到了哪里,他们都不会成为征服者。有学者认为徐福是和平的使者,这个认识是有见地的。也正因如此,历代日本人、韩国人会为徐福建祠,面对徐福像而顶礼膜拜。他们这样做,是自然地,是发自内心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学者认为徐福害怕因找不到“不死之药”而受到秦法的严酷追究,东渡的主要目的是避难,所谓“求药是假,避难为真,徐福二次东渡寻药不归,正是对卢生等‘亡去’不归的效仿,完全是一种政治避难行为了。”( 韩玉德:《徐福其人及其东渡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二期)。这种认识表面上看好像有道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参与为秦始皇找不死之药的方士不止徐福一人,“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史记·封禅书》)《史记》一书明确记载姓名的方士就有韩终、侯公、石生等数人,他们寻药不得害怕秦始皇秋后算账而逃亡,采取的都是秘密的方式、一个人出走的办法进行的,弄他个下落不明,不知所踪。大家知道,对于逃亡或避难而言,知道消息的人越少逃亡或避难就越容易、越安全,只要不被抓到就算成功。而徐福不是这样,他是公开走的,而且还带着庞大的队伍。显然地,这不是消极的逃亡或避难,而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地谋划,为自己更为儿童找寻新的家园,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目的而进行的。人生往往要面对选择,然文化学养的不同所选择的路径却意趣大异,结果也迥然不同,所以人应该选择智慧的生活。
我的第五个发现是古代中国人向外探寻世界时选择方向因东西部地域的不同而截然相反,东部的人向东走,西部的人向西行。洛阳的老子“见周之衰”,骑着牛向西而去;曲阜的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向东而行(当然孔子是只说不练)。同为唐朝高僧,西安的玄奘“西游”,扬州的鉴真“东渡”。赣榆徐福作为东部的人,自然选择东方的大海。这是一种特别有趣的文化现象,值得深入挖掘。
我的第六个发现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尤其是价值观和传统是那么的贴合。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是普通人的理想,追求“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是士子的情怀。《孝经·开宗明义章》提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段评语用在徐福身上也是切合的,试想在徐福以前,有多少君主皇王,多少名士贤人,活着的时候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然时过境迁,数十年后,便被历史遗忘得干干净净。而徐福,虽一介布衣,然凭借其东渡之“大功”,二千二百多年后的今天,还被中外学者想起,在赣榆区组织的盛会上,被我们奉之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楷模,学习他、研究他。司马迁因为写下《史记》实现了“三不朽”,徐福因东渡也实现了“三不朽”。徐福在历史上绝不是有学者所说的是个小丑,而是一个伟人。
(作者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地方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