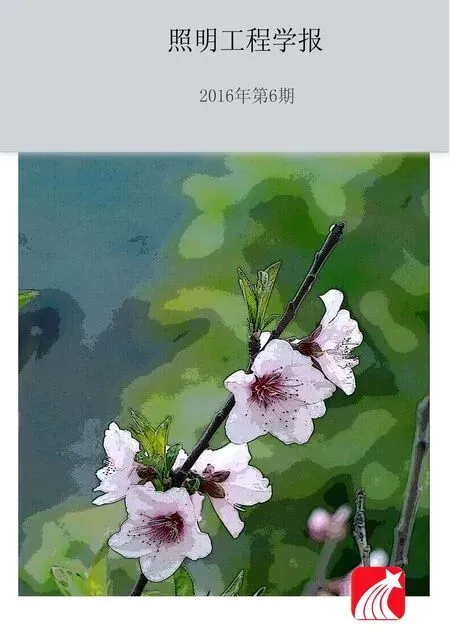工厂环境下的工作-休息排程与动态光策略研究初探
何思琪
(1.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2.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30)
工厂环境下的工作-休息排程与动态光策略研究初探
何思琪1,2
(1.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2.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30)
中国工人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问题受到国内外相关机构密切关注,是工人阶层民生状况的重要议题。本文旨在基于动态变化的工业生产背景,探索工人工作时间、疲劳周期、光生理心理效应之间的关系,从工人群体共性问题探讨到个体差异,提出应对工人作息的动态光策略研究方向。通过实地调研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的方式,探索未来研究方向与方法的可能性:当下和未来的工作时间系统、动态光策略应对工人的节律差异,心理偏好,疲劳周期具有良好适应性,包含时间系统设置,光剂量设置,亮度与色温配对设置,以达到工作节奏与生理节律匹配,适当提高警觉度、缓解工作疲劳的目的,从而改善工人健康状况并提升生产效率。
工作-休息时间排程;生理节律;疲劳周期;动态光环境
引言
疲劳生产加剧工伤事件的发生[1],长期疲劳积累亦对工人生理、心理产生不良影响,导致疾病。多年来,中国工人工作状况已得改善,大部分规范经营的工厂严格控制工时。但工厂工作环境与一般办公室环境仍存在巨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①行动自由程度低;②夜间工作普遍。工作排程研究应探索如何预防或缓解工厂工作造成工人生理、心理健康隐患的工作模式。
工作-休息时间排程是工业生产、工人健康、工业能耗三者的博弈(如图1所示),它包括工作时间设定与休息时间设置,工作环境因素亦关键。在工作排程的博弈中,如何平衡三者、达到整体最优,是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对视、脑疲劳、睡眠节律与工作照明的关系展开讨论,探索健康照明策略。传统工厂车间中,高效高强度人工光源广泛应用于工厂工作照明,造成高能耗与工人健康隐患,而近年来,具有节能环保、体积小等优势的LED技术借助产业资本与政府补贴的双重推动作用下,逐步进入室内照明,但LED光品质具有与人体生物不一致、不和谐效应[2]。前期研究多聚焦于视功效,视舒适度,工作者偏好照明等方面,多用主观评价的方法,而背后的复杂生理心理机制还未深挖掘。昼夜倒班的流水线工人接受长时间、大剂量的高强度人工光的照射是流水线生产的普遍现象,导致工人节律被扰乱、工作疲劳高频发生且程度严重。

图1 工作休息排程优化的博弈Fig.1 Gambling of work-rest schedule
1 初步研究
该厂总装车间尺寸为 94 m×51 m×9 m,为无天窗、机械通风车间如图2所示,目前,该电子工厂室内照明以局部工作台照明为主(图3)。在冬季进行的测量中,由于无天窗,车间中部区域色温明显低于室外,在3 000 K~5 000 K之间(图4)。单层彩钢板屋顶的工业厂房室内空气温度、室内相对湿度主要受当地气候环境温度影响;空气流速受建筑围护结构影响,且室内空气流速远小于室外的,夏季工人工作需电扇辅助通风。电机机械厂室内噪声A声级为70~75 dB(A),远大于室外噪声57 dB(A),且全天室内声环境差异较小。工业厂房的光环境主要受当地气候与车间开窗形式影响;天窗对室内光环境的改善起到极其显著的作用。电子机械工业车间的噪声级在 70~110 dB(A),频谱主要集中于500~2 000 Hz范围内。[3]

图2 工人工作环境与工种调研(图片由李训智[2]提供)Fig.2 Investigation on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type of work

图3 总装车间各时段照度实测数据Fig.3 Illuminance test data of assembly workshop

图4 总装车间各时段色温实测数据Fig.4 CCT test data of assembly workshop

图5 工作-休息-排程与轮班模式调研Fig.5 Investigation of work-rest schedule and shift work schedule
实地调研对车间工作环境与工人行为展开研究。实验变量控制须排除骨骼肌疲劳的显著影响,因此选择具有持续视觉工作和注意力的代表性的工种,此调研择了总装和注塑为典型工种。接受调查的工人年龄基本分布在19~28岁之间,普遍采用的工时为8小时,白班从早上8:00—12:00,午休时间为12:00—13:30,下午从13:30—17:30,夜班轮班为顺时针方向的三班倒班。调查发现,男女工人各自缓解疲劳的方式不同,疲劳程度变化与机体忍耐程度亦不相同。重庆大学张璐[4]根据调研情况展开替代实验,发现在白班系统中,全人工光500 lx,5500 K恒定光环境下,疲劳积累发生在上、下午各一次,每日16:00—16:30是疲劳积累最大时段。轮班系统一般按顺时针进行,早班开始时段与夜班结束时段的疲劳程度较高,如图5。目前研究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工作疲劳背后复杂的机制与优化措施将在未来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讨论。
2 人体疲劳-恢复机制
2.1 疲劳的阈限
人体疲劳有多种定义方式,例如,按照程度等级分为一般轻度疲劳,中度疲劳,重度疲劳;根据机体产生机制,则分为骨骼肌疲劳,视疲劳,脑疲劳,心理疲劳等。在生物心理学研究中,疲劳需要一个阈限进行实验操作,而反应时间、行动效率等方法能量化疲劳程度,反映其时序变化。如Pnar Güzel[5]等采用Wechsler Memory Scale-Revised (WMS-R)量表测定记忆量,Auditory Verbal Learning Test (AVLT)测定瞬时记忆与学习量,反映脑力工作、疲劳程度。现代疲劳研究借助众多生物、医学测试作为疲劳设定阈限(表1),不同的操作定义的设定也可表明不同机制产生的疲劳及其程度变化,其中存在不同神经系统间系统交互作用。对同一个刺激下不同类型疲劳的变化展开研究,可研究发掘其交互作用与综合作用。

表1 疲劳的度量方式
2.2 疲劳相关的排程研究
无论人类、其他生物还是其他物质,如材料,自身都存在 “疲劳周期”,体现了人体功效与时间维度的复杂关系。生物体疲劳机制更为复杂,因体内有多套疲劳系统交互作用。 睡眠情况、工作时间、工种特点、休息行为等均能对疲劳与恢复速度产生影响。
2.2.1 轮班系统优化
工厂环境工人疲劳研究最早聚焦于夜班轮班对工人的影响上。早期研究中,针对工人夜班满意度和接受度进行调查的问卷表明[6],夜班影响到工人的精神状态,生活习惯和社交生活。虽然如此,夜班的奖励机制亦能激发工人的兴奋情绪,使之在12小时一换班的排班系统中基本不产生消极行为[7]。Czeisler CA等在研究中讨论了睡眠区间与生理相位的关系,至此,研究者们意识到夜班对人体最大的影响在于睡眠障碍:当剥夺睡眠持续到56小时,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反应将发生变化[8]。直到David Berson[9]发现人体的光生物通路,将光与人体生物钟联系在一起,发掘了光剂量对睡眠相位、困倦程度与警觉度的影响,为解决夜班引起的睡眠障碍问题指引新的方向。
前期研究大量实验对轮班系统展开,发现夜班疲劳适应程度与工种特点有关。要求持续注意力的工种,夜班中认知反应力会降低;无持续注意力,高认知负荷的夜班工作其生产效率不变。夜晚的视觉搜索能力与手工技术水平极低,但语言推理与计算能力相对有良好适应性,而反应效率和心算能力均能提高。在疲劳缓解的光策略研究中,是否能针对工种的特点给以适当刺激以提高警觉度,亦是值得讨论的议题。
夜班出错率相比早班较高,通过工时控制能有效缓解:体动测试显示,夜班之后,工人睡眠时间减少,而Cruz C, Boquet[10]等学者提出缩短工作时间到每周60小时,能明显降低夜班出错率。
不仅在时间段上需要对工作时间进行控制,研究发现人体生物钟也存在个体间差异,对于某些工人,早班(早晨4:00—5:00开始)可能造成整日困倦的状态[11]。Juslen所研究的三班倒轮班系统中,早班开始时和晚班结束前工人困倦程度最高,下午班时工人最为清醒。工人在第二次和第四次休息时比第一次和第三次休息时困倦。而午饭前,是困倦爆发时段,该研究考虑到工人睡眠类型的评估,发现与早起型工人相比,晚睡型工人对顺时针轮班的适应性更强,强光刺激对其警觉性提高、困倦度抑制产生效应更明显[12]。

图6 睡眠类型与工作时间(根据Gamble K.[13]2015研究成果绘制)Fig.6 Effect of chrono-type and work duration on circadian rhythm (According to Gamble K.[13]2015)
生物钟差异的本质是不同的睡眠类型,一般的睡眠类型在两种极端类型之间变化:晨鸟型(睡眠时间:12:00am—6:00am)和夜猫型(睡眠时间:3:00am—10:00am)[13],工作时段应与睡眠时段尽量减少重叠,否则将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和工人的健康隐患(图6)。Ce′line Vetter[14]等将适应睡眠类型的工作排班(CTA)应用于实际生产线,根据慕尼黑睡眠类型问卷(MSFEsc)[15]测试结果对工人进行分类,研究结果显示:适应睡眠类型的工作排班(CTA)能显著增加夜班工人在工作日的睡眠时间、提升睡眠质量并减缓夜班引起的昼夜节律失调。
2.2.2 工作-休息系统优化
现阶段工作-休息排程研究通过生物指标检测进行疲劳检验。为得出工人最大可接受工作时间[16],可利用本身最大摄氧量作为评估依据,判定工作者的生理作业能力[17],或利用工作效率、正确率、身体各部分的RPE评分依据Borg量表评分[18]。根据工人的疲劳程度不同为其安排不同的休息时间[19]的相关实验研究已触及到个体差异, 赵小松[20]等以Wu和Wang提出根据工人个体的最大可接受工作时间设定休息区间,建立了单人工作-休息排程的数学模型。
总体来看,基于人体生理因素的排程优化研究主要呈现为两阶段:
1)疲劳参数检验:将工作效率衰退-时间模型假设为线性函数和指数函数,提出工作疲劳具有前端负载特性,因此短期休息应设置在工作时间轴的前端[21],能有效提升工人生产效率。
2)工作休息最优组合:短暂休息能促进生理、情绪上的疲劳恢复,工作期间的休息按照时间长短被划分为放假,正式休息(三餐),非正式休息(如厕,饮水等),微型休息(工作台上暂时停止工作)[22],以此为基础比较工作休息时间设置下工人工作效率。根据工人个体疲劳状态调节工作系统,设置休息时段后,工人疲劳恢复不必达到100%,就能有效平衡工作效率与疲劳舒缓[23]。
在我国情景下,《中国工人工间休息,轮班起始时间,睡眠影响的工伤发病调查》[24]指出,工间休息能延迟工伤发生,同时缓解疲劳。中国工业的安全生产与工人健康权益的意识正在觉醒。
前期研究中,工厂视疲劳研究主要对精细加工作业、视觉作业密集等问题展开讨论,由于研究视觉界面不同,视觉作业类型不同,众多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工业环境的视觉需求主要集中在工人视功效,以提高工作效率,但视疲劳周期研究尚不足。Haider的研究表明,工作4小时休息16分钟能使视觉恢复到工作前水平,视觉疲劳得到舒缓。Misawa,Floro和Parimal分别对VDT视觉作业展开研究,发现数据输入作业效率在45~60分钟后达到最低,至少应每工作60分钟休息10分钟。然而,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研究所基于的图像显示技术背景早已不适用于当下,近年来成像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超过视疲劳研究跟进速度,工作人群的视觉作业强度愈大,探索普适的视疲劳研究方法,以此探寻适应不同视觉界面下的视疲劳缓解方法是未来研究一大挑战。
3 工厂环境光暴露
工人工作排程优化应平衡生产效率与安全、健康生产两者关系,工厂作业照明通过光策略增加视觉舒适度,缓解疲劳,以达到提高工人生产效率的目的。工厂光环境改变从而影响工人行为与工作效率的10种机制有:视功效,视舒适度,视觉环境, 人际关系,生物钟,刺激效应,工作满意度,困难排解能力,晕轮效应,作用过程。此模型(见图7)基本概括了工厂环境人工照明与工人绩效、工厂总体收益的关系。[25]

图7 照明措施对工厂收益影响模型(根据HT. Juslen[24]2005研究成果绘制)Fig.7 Model of lighting effects o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ccording to HT. Juslen[24]2005)
3.1 生理节律调节
早在1995年,Dawson[26]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强光对急速分泌和生物钟控制有显著作用,褪黑素分泌机制对460nm的光波段最敏感[27],每种单色光刺激与褪黑素抑制程度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28],为生理节律光疗的光剂量研究打下基础。蓝光辐射大于20J·cm-2后将导致眼底变化,因此曝光剂量控制至关重要[2]。Sasseville A指出,可用短波光与蓝光镜能为人体创造“生理黑暗”,从而重设人体生物钟[29]。除要求持续注意力的工种外,强光能切实改善夜班中年工人的工作记忆和精力集中程度[30]。长期非时限的日间曝光蓝白光,经过视黑素研究优化,能建立稳定的生理节律相位,提高认知能力与情绪水平[31]。
充分认识到光环境与人体关系后,工作环境的生物钟照明模型应运而生,其在办公室[32]和医疗环境[33]中有所发展。基于光生物效应的人体生物钟重设配合上文提到的基于睡眠类型的工作排班(CTA),两种方法相互配合,未来研究将探索是否能将工人的生理节律紊乱调节至最小化。虽然国外相关研究已有一定程度开展,但国内外国情差异明显,不同地域文化、社会制度下,工人年龄、生理、心理等情况亦不同,针对我国工人的相关研究应及时展开。
3.2 工作疲劳的心理生理调节
视觉刺激效应与心理变化问题由于涉及到变量外心理因素的干扰,因而具有一定复杂性。 如Hawthorne[34]效应是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发现,Hawthorne实验的原本目是为探究照度等级与工作效率的关系,却意外发现实验评估本身对被试者产生关注感,因而对工作者工作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而工厂工人行为自由度不高,相比一般工作者习惯于受监督与控制,因此效应对实地工厂实验的影响相对较小。
工人的偏好照度水平随着日、周、月,甚至年周期变化,实验初始照度值越高,调光偏好照度越高[35],因此调光作业并不确定最佳照度的合适方法[36]。在探讨照度升高与效率提升的调光实验中发现,工作照度从500lx提高到2 500lx,生理参数中仅警觉度发生变化[37]。HT. Juslen与严永红等学者的实验均证明,由于生理反应相对滞后,主观评价与生理测试结果不一致。因此,工厂环境下高效高强度的工作面照明的可行性还需考量。相关照度偏好研究已深入到行为心理层面,工人偏好,心理适应性,动态调光系统的关系,以及照度与色温的最优配对仍值得探讨。
前期限于照度等级的探索将延伸到光色、光剂量层面研究,在工厂工作台蓝白光照明实验中,发现,蓝白光能缓解视疲劳,提升视功效[38],但此研究其未考虑长时暴露于蓝光对人视觉机能产生的光化学损伤。在7 000 K的色温下,脑波活性达到最大,但极易积累疲劳;在3 000 K色温下,脑波活力最低,LU S.指出5 000 K为工作照明的最佳色温[39],而严永红的实验证明4 000 K的识别率相对较高,最佳色温配对比为4 000 K配2 700 K[40]。并且长期、高负荷的工作者行为与累时效应将在视疲劳-恢复机制中得到讨论[41]。总之,高强度,高照度照明易引起脑疲劳,而相对低照度低色温光策略是未来工作照明的研究方向。工作面的局部照明策略同样值得探讨,其能有效控制照明能耗,并有效应对工人个体差异化的需求。
4 未来挑战
当今世界工业站在第四次革命的转折点,未来工业生产将是怎样的?工厂是否将走向去人工化?Wolfgang博士认为,工厂将不会走向去人工化,相反,工人工作模式与社会阶层将发生转变。工业智慧生产时代即将来到,从现有的局部自动化、通讯自动化,到未来人类远程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供应系统,达到工业生产自组织管理。至此,工人群体将面临以下变化:
1)工作模式改变工人心理:工人在生产系统中不再作为生产者发挥作用,而是以更主动的角色作用于生产链,即管理者、设计者和消费者。机械劳动能力将被决策、排难能力取代,脑力劳动的比重将大幅上升。由于工作方式、角色不同,该群体的社会阶层也将发生变化,从前的“蓝领”群体,将转变为介于蓝、白领之间的“灰领”[42]群体,个人的人际关系,心理压力发生机制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2)工作界面革新加剧视、脑疲劳:传统制造业的工作面实物操作将转变为模拟数据、图像,平面化地展示在屏幕上,甚至将来,随着成像技术飞速发展及其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更加仿真化的视觉界面,如VR、AR,未来将在工业生产中掀起视觉工作界面的革命,视、脑疲劳研究将面临不断变化的需求。
3)工作时间自由化与夜晚工作普遍化:传统工厂主要在生产线进行昼夜工作,而随着24小时经济的推进,工作时间越来越自由,社交时间比重加大,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将选择在夜晚开展工作,并且时间安排更自由。抑制节律紊乱的夜班照明与工作-休息时间排程研究体现其重要性。
5 结束语
人工照明研究在智能控制系统上已获得相当突破,技术上的进展将应用于促进人类群体身心健康的目标。动态照明与智慧控制能实现照明系统的感应刺激、定时、动态同步等,技术应用的依据来源于睡眠类型评估、疲劳周期、心理偏好,以此回应工作者包含个体差异的视觉光感知、非视觉光感知,以及心理感受(图8)。所以包含着时间设置、光剂量设置、亮度与色温最优配对的光策略背后是复杂的人体生理心理机制和技术经济综合效益,其最终的目的是让提升工人工作效率与促进工人身心健康并行。照明研究者应综合考虑、求证,选择能让工作者生理节律与工作时间同步,心理压力、视疲劳、脑疲劳得到适当缓解的最优解。

图8 回应人工人生理心理需求的动态光策略Fig.8 Dynamic lighting strategy responding to workers’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
解决工人阶层工作健康问题亦是社会安定的良药。即将面临的工业变革引起工人工作模式、社会关系变化、视觉工作界面革新的作用不容小视,研究者须抓住技术变化趋势,在变化来临前预测未来工人面临的健康隐患,以此对“征”下药。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n China manual,2013.
[2] 赵介军, 乔波, 过峰. LED 蓝光危害研究[J]. 照明工程学报, 2015,26(1):84-87.
[3] 李训智. 基于瞬变应激理论的工厂休憩场所设计策略研究 [D]. 重庆:重庆大学, 2015.
[4] 张璐.全人工恒定光环境下流水线工人的疲劳周期研究 [D]. 重庆:重庆大学, 2016.
[5] CRUZ C, BOQUET A, DETWILER C, et al. Clockwise and counter-clockwise rotating shifts: effects on vigilance and performance[J]. Aviat Space Environ Med, 2003,74: 606.
[6] AGERVOLD. M. Shiftwork-a critical review, Scand. [J]. Psychol. 1976,17:191-188.
[7] CZEISLER CA, WEITZMAN ED, MOORE-Ede MC, et al. Human sleep: its duration and organization depend on its circadian phase[J].Science,1980,210:1264.
[8] XIAO Y, ZHAO. ZX. Sleep deprivation effects on the immune system and the endocrine[J].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2006,11(49).
[9] ECKER J L, DUMITRESCU O N, WONG K Y, et al. Melanopsin-expressing retinal ganglion-cell photoreceptors: cellular diversity and role in pattern vision[J]. Neuron, 2010, 67(1):49-60.
[10] CRUZ C, BOQUET A, DETWILER C, et al. Clockwise and counter-clockwise rotating shifts: effects on vigilance and performance[J]. Aviation Space & Environmental Medicine, 2003, 74(6 Pt 1):606.
[11] KECKLUND G, ÅKERSTEDT T. Effects of timing of shifts on sleepiness and sleep duration [J].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1995, 4(Supplement s2):47-50.
[13] GAMBLE K, YOUNG M. Circadian Biology: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Morning Shift [J]. Current Biology Cb, 2015, 25(7):269.
[14] VETTER C, FISCHER D, MATERA J, et al. Aligning Work and Circadian Time in Shift Workers Improves Sleep and Reduces Circadian Disruption [J]. Current Biology Cb, 2015, 25(7):907-11.
[15] JUDA M, VETTER C, ROENNEBERG T. The Munich Chrono Type Questionnaire for Shift-Workers (MCTQShift). [J]. Journal of Biological Rhythms, 2013, 28(2):130-140.
[16] WU H C,WANG M J J. Determing the maximum acceptable work duration for high-intensity work[J].Europea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2001,85(3-4);339-344.
[17] ASTRAND P O,RODAHL H A, et al. Textbook of work physilogy: physiological bases of exercise[M]. Canada:Human Kinetics,2003:273-298.
[18] 徐凯宏,王述洋,宋春明. 合理构建视频显示终端(VDT)作业疲劳工间休息制度[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9(4):26-31.
[19] HSIE M,HSIAO W,CHENG T et al. A model used in creating a work-rest schedule for laborers [J].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2009,18(6):762-769.
[20] 赵小松,常陈英,张阳,等.考虑工人疲劳的工作排程研究.工业工程与管理[J]. 2012,7(1):112-116.
[21] BECHTOLD S E, SUMNERS D W L. Optimal work-rest scheduling with exponential work-rate decay [J]. Management Science, 1988, 34(4):547-552.
[22] KONZ S. Work/rest: Part II-The scientific basis (knowledge base) for the guide 1[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 1998, 22(s 1-2):73-99.
[24] LOMBARDI D A, JIN K, COURTNEY T K, et al. The effects of rest breaks, work shift start time, and sleep on the onset of severe injury among work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2014, 40(2):146-55.
[25] JUSLÉN H, TENNER A. Mechanisms involved in enhancing human performance by changing the lighting in the industrial workpla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 2005, 35(9):843-855.
[26] DAWSON D, ENCEL N, LUSHINGTON K. Improving adaptation to simulated night shift: timed exposure to bright light versus daytime melatonin administration. [J]. Sleep, 1995, 18(1):11-21.
[27] BRAINARD GC, HANIFIN JP, GREESON JM, et al. Action spectrum for melatonin regulation in humans: evidence for a novel circadian photoreceptor. [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2001, 21(16):6405-6412.
[28] DAUCHY R T, BLASK D E, BRAINARD G C, et al. Low-intensity light at night (LAN) exposure and alterations in hepatoma and human breast tumor lipid metabolism in rats: A dose-response study [J]. Cancer Research, 2005, 65.
[29] SASSEVILLE A, HÉBERT M. Using blue-green light at night and blue-blockers during the day to improves adaptation to night work: a pilot study. [J].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0, 34(7):1236.
[30] KRETSCHMER V, SCHMIDT K H, GRIEFAHN B. Bright light effects on working memory,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elderly night shift workers [J]. Light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2012, 44(3):316-333.
[31] NAJJAR R P, WOLF L, TAILLARD J, et al. Chronic artificial blue-enriched white light is an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 to delayed circadian phase and neurobehavioral decrements.[J]. Plos One, 2014, 9(7):e102827.
[32] 周太明.光的生物功能与动感照明 [J].中国照明电器,2005(10):7-8.
[33] 片山就司,野口公喜,伊藤武夫.生物钟照明的应用——关于应用人体生物钟的新型照明[C]//中国照明学会(2005)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照明学会,2005:445-447.
[34] PARSONS H M. What Happened at Hawthorne? [J]. Science, 1974, 183(4128):922-932.
[35] JUSLÉ H. Lighting, Productivity and Preferred Illuminances-Field Studies in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D]. Teknillinen Korkeakoulu Valaistuslaboratorio, 2007.
[36] FOTIOS S A, CHEAL C. Stimulus range bias explains the outcome of preferred-illuminance adjustments [J]. Light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2010, 42(1):433-447.
[37] WILHELM B, WECKERLE P, DURST W, et al. Increased illuminance at the workplace: Does it have advantages for daytime shifts? [J]. Lighting Research & Technology, 2011, 43(2):185-199.
[38] LIN C J, FENG W Y, CHAO C J, et al. Effects of VDT Workstation Lighting Conditions on Operator Visual Workload [J]. Industrial Health, 2008, 46(2):105.
[39] SHI L, KATSUURA T, SHIMOMURA Y, et al.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Source Color Temperatures during Physical Exercise on Human EEG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J]. Journal of the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2009, 12(1):27-34.
[40] 严永红, 关杨, 王宁,等.不同色温T5荧光灯光色配比识别率对比实验研究[J]. 照明工程学报, 2010, 21(5):59-62.
[41] 严永红, 晏宁, 关杨,等.光源色温对脑波节律及学习效率的影响[J]. 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 2012, 34(1):76-79.
[42] 蔡少波. 工业4.0来了,人去哪了[J]. 经济研究导刊, 2015(1):286-287.
Preliminary Study of Work-rest Schedule Optimization and Lighting Strategy in Industry
HE Siqi1,2
(1.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China;2.KeyLabofMinistryofEducationforNewTechnologyofMountainousTowns,Chongqing400030,China)
Workers’ health condition and industrial safe production have become issues of livelihood state of this social class. Based on a dynam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kers’ working time, fatigue period,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light, some aspects extending from group commonality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this way, dynamic lighting strategy that’s responding to workers’ time schedule is coming up. Combing field stud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possible issues and method in future study have been probed: work-rest schedule, lighting strategy in present and future should have appropriate adaption to workers’ circadian rhythm, preference, fatigue period; the whole system includes time placement, light irradiance dose setting, illuminance and CCT optimum match, and eventu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promoting alertness and fatigue recovery, working pace synchronizing with circadian rhythm. This can improve workers occupational health condition as well as promot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work-rest schedule; circadian rhythm; fatigue period; dynamic lighting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378518),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 (2009KB15),重庆高校创新团队建设计划资助项目(CXTDX201601005) 通讯作者:严永红,E-mail:65120701@126.com
TM923
A
10.3969/j.issn.1004-440X.2016.06.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