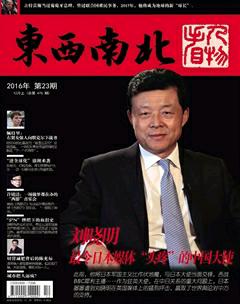红宝书的世界史
程映虹
当时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建筑物上悬挂着大幅标语,“一切教授都是纸老虎”,很明显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西方校园运动中的变体。
整整50年前,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内部发行并多次修订的《毛主席语录》(以下简称《语录》)在全国公开发行,被称为“红宝书”和“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短短几年中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印刷量最大的书籍,其语言风格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
就在同一年,《语录》也翻译成多语种向世界很多国家大量密集发行,几乎成了当时唯一对外发行的书籍。有关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两年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毛的小红书的世界史》(以下简称《小红书的世界史》),介绍《语录》在世界一些国家传播及其衰落的过程,对了解整个文革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小红书的世界史》收集了十三篇论文,除了介绍《语录》翻译出版的过程和在中国国内的作用,主要介绍了它在坦桑尼亚、印度、秘鲁、苏联、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西德国、法国和美国激进的非裔和亚裔社会运动中的影响。论文的作者们在梳理《语录》在这些国家的出版发行概况之外,都试图把它的影响和兴衰放在这些国家国内政治和对华关系的背景下,所以有一定的历史和思想深度。
几乎神化的《语录》
坦桑尼亚是中国上世纪60年代在非洲的重要盟友,其首任总统尼雷尔在独立后提出乌贾玛社会主义,把居住在传统村社中的农民集中搬迁到乌贾玛公社过集体生活。他数次访华,视中国为榜样。1967年,《语录》的英文和斯瓦希里文本进入坦桑尼亚,不但在主要城市的书店出售,而且在一些乡镇的书店也能见到。
受《语录》的影响,坦桑尼亚领导人也开始编辑出版自己的《语录》。1967年底,坦桑尼亚军队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总统卡鲁梅的《语录》(主要是他演讲的内容)。随着《语录》的传播,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公共场所也出现毛泽东的画像。
以《语录》为标志的文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和坦桑尼亚国内政治中某些激进的倾向很契合。1968年坦桑尼亚发动了“青年行动”和“服装行动”,扫除殖民时代留下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饰和发式,例如迷你裙,紧身裤,假发和化妆品等等,同时提倡坦桑尼亚民族服装,如尼雷尔本人喜爱的“毛制服”。
由于独立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偏差,城市青年就业成为问题,坦桑尼亚也发起了“回乡知识青年运动”,号召城市青年下乡落户或接受锻炼。
但是,以《语录》为象征的文革文化在坦桑尼亚也逐渐遭到了抵制。一些政府官员担心青年反西方和反传统运动中的暴力倾向失控。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一些独立思考的学生成立了批判文革影响的异议组织。但最重要的是尼雷尔的“乌贾玛社会主义”乌托邦试验本身的受挫,使得以《语录》为标志的文革文化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坦桑尼亚基本失去了影响。

阿尔巴尼亚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被称为是“天涯若比邻”的盟友。因为这种关系,《语录》在阿尔巴尼亚的传播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但得到政府许可而且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
1967年10月,首批5000册《语录》由专机送达阿尔巴尼亚,连同后来运去的,一共是10万册。后来运去的一些版本在装帧上考究了一些,有塑料封皮,内页有口袋,很多阿尔巴尼亚人把它当皮夹使用。
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语录》里的很多话和毛著中的论断开始广泛地在阿尔巴尼亚的学校、新闻和宣传材料上出现。当阿尔巴尼亚的运动队和文艺团体访华时,在北京机场上他们被要求朗读《语录》中的片断。阿政府有关部门特意为此发文,说虽然我们党没有这个习惯,但要这些访华人员尊重中方的要求予以配合。
阿尔巴尼亚在毛泽东去世后和中国公开闹翻了,起因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和解,后来是中国和阿的宿敌南斯拉夫和解。这两个和解使得中国的朋友大大增加,阿尔巴尼亚的盟友地位下降,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自然有妒意。
《语录》在坦桑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影响得益于国家政权和中国的关系,但在绝大多数国家,它的影响是通过激进的社会运动实现的。
在印度,《语录》一度成为革命的圣经。由于印度是多语种的国家,由中国运来的《语录》有英文、孟加拉文、泰米尔文、僧加罗文、马来文和乌尔都文的版本。印度共产党毛派领导人马祖达1967年正式和党主流派决裂,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西孟加拉的那夏巴里发起暴力斗争,他领导的印共因此被称作那夏里特运动。
那夏里特运动对《语录》的宣传和使用几乎和中国文革时一样。马祖达向每个新加入组织的成员赠送《语录》,数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交流心得体会,要求他们朗读、背诵和引述其内容,在此过程中融合来自知识分子、学生和农村平民之间的身份差距。
那夏里特宣传中把《语录》几乎神化,下农村发动群众时总是以朗诵它开始;战士们视《语录》为武器,一刻不离身。有一篇报道说一个少年战士回家对自己的母亲宣传《语录》,连吃饭时间也在引述和背诵毛的教导。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语录》的影响在那夏里特运动中突然衰落,原因除了马祖达对它的狂热信奉引起一些成员的反感,还和中国此时对个人崇拜的降温有关。
东西德国的毛圣经
在西方国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发行的《语录》最早1966年底就开始出现。在法国,到1967年1月,巴黎一地售出的法文版《语录》已有4000册。此后,以出版发行左翼和新左翼的政治和学术著作闻名的Editions Seuil出版社也出版了《语录》的法文版。
在西德,1967年时约有10万册《语录》在流传,共有三个版本。第一是中国官方北京外文出版社印刷的,外包红色塑料封皮,主要是由极少数前往东柏林的西德学生从中国驻东德使馆那里偷偷携带回来的。
1967年夏秋,大量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学生前往中国驻东德大使馆,有时一天可达六七十人,多半是要求得到《语录》和其他有关文革的宣传品。
1968年初,东德当局在中国大使馆周围设警,禁止进入使馆,此后北京版《语录》在西德外传的数量下降。
第二个版本是法兰克福一家名为Fischer的左翼出版社印刷的,由一个学习中文、喜欢毛泽东哲学思想和诗词的德国学生翻译。
第三个版本是由一个叫Marienburg的出版社印刷的,书名改成《毛泽东语录——七亿人的必读书》。但这个版本的《语录》是西德右翼用于反宣传的,在1967年,这本书出版了2万册。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语录》的推崇帮助了它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著名女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她的学生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阿玛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里兹。
罗宾逊是西方经济学家中著名的左翼人士,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数次访问过中国和朝鲜,赞扬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她关于中国的三本书中有一本题目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她也称赞金日成是救世主,他领导下的朝鲜创造了“经济奇迹”。罗宾逊关心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频繁访问印度,是印度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机构“发展研究中心”和德里大学的客座研究员。
《小红书的世界史》中关于印度的文章里介绍说,罗宾逊文革中访问了中国之后就去了印度,据说她手里挥舞着《语录》,用其中的字句回答批评性的问题。例如有人说:“难道你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很教条吗?”她回答说:“毛主席说教条主义比狗屎还糟糕。”
在实证方面相对做得比较详细的是有关《语录》在东西两个德国流传的文章,题目是“东西德国的毛圣经”。文章提到了西德大学生占领校园的过程中出现的《语录》,其中提到当时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建筑物上悬挂着大幅标语“一切教授都是纸老虎”,很明显是毛语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西方校园运动中的变体。为了限制左派宣传品的泛滥,西德警方宣布学生在公开场合出售书籍是违法经商。学生们想出了对抗的方法:因为学生出售西红柿不犯法,所以他们宣布每个西红柿卖两个马克(这显然是远高于西红柿的市场价),但奉送一本毛语录。这个行为不但合法化了《语录》的公开流通,也暗指着《语录》是可以投掷的“武器”,因为在和警方对峙中,学生经常投掷西红柿,后来确实也曾投掷过《语录》。
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言论和声明引起了一些美国黑人政治活动家的重视,黑人激进组织“黑豹党”的代表人物休伊·纽顿早在1966年前就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从1967年开始就向运动成员推荐《语录》,要他们认真阅读。在《语录》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地方,纽顿就说:“把它们换成黑豹党和美国黑人就行了。”黑豹党通过发放《语录》来招募成员,建立组织,通过阅读它理解斗争的概念。由于《语录》代表了非西方有色人种的革命理论,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来源于欧美的批判理论更受非裔美国人的信任。

如果要说《小红书的世界史》另外还有缺憾的话,那就是全书没有一篇论文介绍和分析《语录》在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世界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东南亚和这个地区的华人社会可以说是受以《语录》为代表的文革文化影响最大的地方。所以,东南亚地区研究的缺席,也是这本论文集的一个缺憾。
借助钟馗打鬼
就数量和规模来说,小红书在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越出国境的流行,可以算是世界文化传播史上罕有的现象。但它在绝大多数地方的流行大概最多只有4到5年,然后湮没无闻,今天除了在旧书市场偶尔可以见到,基本上没有读者。换了任何一本书,如果曾经达到如此规模的发行和流通量,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因此,可以说是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究其缘故,恐怕有内外两个重要原因。
内部原因是小红书当年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本来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中国特定国情下的文化输出战略,是国家斥巨资才得以实现的,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正常现象。当国家文化战略转型了,特定文化产品也就过时了。到1970年左右中国政府就不再支持《语录》的输出了。而外部原因,则像毛泽东1967年对阿尔巴尼亚专家说自己的书出了中国就没什么用了,这恐怕更多地不是自谦,而是自省。就在那之前,他还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说那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这个比喻用在《语录》的世界性影响上更符合实际:从《小红书的世界史》中以及笔者了解的其他案例来看,《语录》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流行,都和当地的实用主义政治有关。
这种实用主义政治或是像阿尔巴尼亚那样出于确保中国援助的需要,或是不顾《语录》的中国语境,生抄照搬,再不就是夸大它的象征性,把它当作政治波普和文化时髦。总之,都是把小红书当作钟馗甚至是道具来用。这就是《语录》的世界流行史留下的教训。
(周强荐自《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