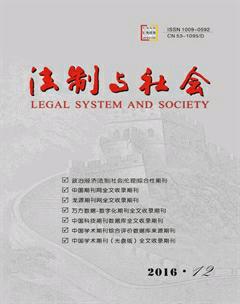入籍外国人民族成分法律确认问题研究
熊震+李昕阳
摘 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入籍外国人的民族成分确定问题进行研究,既是对少数民族成分和族别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特殊切入点,也是对我国移民日渐增多现实的回应。本文将就我国对籍外国人的民族成分管理规定进行梳理,分析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并在分析国际人权经验对入籍外国人民族或族群进行分类的优点和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现行管理办法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少数民族成分 入籍外国人 法律确认
作者简介:熊震,云南新秀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李昕阳,云南云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项目主管,执业律师。
中图分类号:D8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89
一、入籍外国人民族成分法律确认问题
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仅有3000余入籍外国人中国,对移民入籍管制相对于其他国家严格甚多,同时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民族成分确认需要本人自主申请和经过严格的程序批准,所以对于移民的民族成分进行确认多为个例,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
但是,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才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日益宽松和频繁,外国移民的增多在未来会成为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入籍外国人的民族成分确定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切入点,有利于对少数民族成分和族别问题进行思考。
笔者综合梳理了我国对于入籍外国人入籍后的民族成分的现行管理办法(详见本文下一章),是根据是否有相近民族成分来分别处理的:有相近的民族成分,则入籍外国人者可在入籍两年内申请该相近民族成分;无相近的民族成分,则可以采取在外国人原民族名称上加注和申请加入我国某一民族成分两个措施中的任一。
对于上述的现行管理办法提供入籍外国人获得民族成分的途径并参照少数民族待遇对待,笔者认为是不合适的,原因如下:
首先,对于有相近民族成分的外国入籍者可申请加入该民族成分的规定,笔者认为是不符合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的的。在我国的建国初期,中央所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结合实际国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择:“建立这一制度,目的是从制度上消除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真诚团结。”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促进中国本土民族的平等团结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入籍的外国人并非我国本土的少数民族,不属于我国民族政策所针对的适格主体,仅仅只是当时从权的特殊规定,对其按照少数民族对待并不符合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的。
其次,入籍的外国人在性质上并不能简单的归类为应受照顾的少数人群体。国际上对于少数人群体的概念是有严格的限制。笔者认为我国的入籍外国人既不符合国际上的少数人标准,也不符合我国对少数民族的相关标准。
二、入籍外国人民族成分法律确认规定
在我国建立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的少数民族法律保障体系中,少数民族是一个具有法定权利义务的法律概念。《中国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认为:一个权利主体在法律上所处的位置即是其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的含义主要指其在相关法律中的状态以及因之而产生的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所以,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即指少数民族在法律上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少数民族的法律确认,也就是指少数民族法律地位的取得。在法律和相关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法律确认,是少数民族公民取得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地位并且得以享有相应法定权利的前提。
我国少数民族的法律确认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对少数民族族称的法律确认,第二种类型是对公民个人民族成分的法律确认。根据2016年开始施行的《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对相关内容的规定,公民个人民族成分的登记确认必须填写“经国家正式确认的民族名称”。所以要确认少数民族公民个人的民族成分,必须是以对其所属少数民族群体的族称进行确认作为前提条件。
由于我国对少数民族族称的法律确认并无相关的法律或规范性规定,笔者将在本节中根据我国政府实践中确认少数民族族称的方式对其进行梳理总结。对于少数民族公民个人民族成分的法律确认,我国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并无与少数民族公民民族成分和入籍外国人的民族成分确定问题的确认主体、确认程序、确认效力等相关的内容。至今为止,与少数民族公民民族成分确认相关的规定共有六份份规范性文件(其中一份为规章)。规章即2015年6月16日由国家民委、公安部第2号令颁布的《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2015年规章),该规章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五份规范性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则依次是第一份1981年11月28日由国务院第三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共同公布的《新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以下简称为1981年通知);第二份1986年2月8日由国家民委单独公布的《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问题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为1986年补充通知);第三份1986年2月1日由公安部、国家民委共同公布的《关于居民身份证使用民族文字和民族成分填写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为1986年身份证通知);第四份1989年11月15日由国家民委、公安部共同公布的《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为1989年暂停通知);第五份1990年5月10日由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国家民委、公安部共同公布的《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以下简称为1990年规定)。
笔者将首先以上述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基础,从时间顺序梳理我国少数民族公民民族成分确认(以下简称少数民族成分)的管理主体、确认原则和确认程序,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入籍外国人民族成分法律确认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第一,从对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公布主体和其中关于少数民族成分确认的内容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成分确认的管理主体是国家民委和公安部门。理由如下:
其一,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和规章的公布主体主要是国家民委和公安部门。从1981年公布第一份规范民族成分问题的文件开始,到2015年共同公布迄今关于少数民族确认问题法律效力最高的《规章》为止,相关的所有规定都是由国家民委和公安部所公布。虽然1981年发布的《新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和1990年所发布的《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的这两份规范性文件是由国家民委、公安部和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共同署名公布的,但这是因为少数民族成分法律确认和这两次的人口普查工作相关,并不能仅仅据此将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也视为确认主体。所以,从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公布主体可以清晰反应我国少数民族法律确认事项的主管机关是民族部门和公安户籍部门。
其二,国家民委和公安部二者之间的分工配合自1986年补充通知明确后,直至今日始终是由各级民族部门负责审批民族成分恢复、变更,各级公安户籍部门负责相关的户口登记和身份证办理。在1981年通知中,由于时代背景的原因,对于民族成分工作的管理主体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只是在第七段中规定了需要到户籍部门办理手续。在1986年补充通知中,则规定了“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根据人数和范围由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审批,户籍管理部门凭县审批证明办理手续。在1990年规定中第七段对主管部门的叙述只是对1986年通知的确认,并无变动。2015年规章则规定的较为详尽明确。规章在第四条明确了有关公民的民族成分的登记工作和管理工作由国务院的民族事务部门和国务院的公安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管。在第11条规定了办理民族成分变更各个环节中,公安部门负责户口登记,民族事务部门负责审批。
第二,我国规范性文件对少数民族成分的确认始终奉行的是血统原则,即依据父或者母的民族成分确认子女的民族成分。在1981年通知中虽未直接规定子女的民族成分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确认,但在第三段中规定了隔代恢复或改变民族成分要求:如果是隔代要更改或者恢复自己的民族成分的,不能直接进行更改。在父母健在的情况下,需要先行对父或者母的相应民族成分进行恢复或更改,进而才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民族成分进行恢复或更改。如果父母已然去世的,则也需要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相关的民族成份进行恢复或更改,才能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民族成分进行恢复或更改。这一规定内容从侧面体现了我国公民的民族成分确认采取的是血统原则。在人类整体的历史进程中,血统一直是民族和族群认定其成员的主导标准。虽然有其他类型的民族和族群认定标准,但依据父系、母系的血脉延续对是否为共同体的成员进行认定一直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方法。我国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定也采取了这一原则,即依据父系、母系的血脉延续对公民是否属于少数民族群体成员进行确认(即公民的民族成分确认)。这一原则在具体的规定中是这样表述的:1986年补充通知中的第二段则直接提出了公民自己的民族成分,应该根据其父一方或母一方的民族成分进行相应的确定。1990年规定亦是在第二段中规定了公民自己的民族成分,应该从其父或母其中一方的民族成分里进行选择并予以确定。2015年规章则在第5条中再次明确了血统原则:“公民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据其父亲或者母亲的民族成分确认、登记。”并且在此条中将父母的定义明确化:即在2015年规章中,但凡其条文所涉及内容用到父、母一词的,其范围包括亲生的父母、法律上抚养的父母和合法过继的父母三种情形。如此便将依据养父母、继父母确认民族成分的情形涵盖至本原则的外延之中,由于此类情况较为特殊并涉及民族成分的更改,笔者将在下一节中详述。
第三,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公民确认的程序只在2015年规章的第6条中有所规定:负责办理户口登记的相应级别公安部门在进行该业务办理时,要依据新增人口的父亲或者母亲的民族成分进行确认和登记。如果其父亲或者母亲的民族成分并不相同,则应该让其父母先行共同签署新增人口的民族成分填报申请书,再根据申请书所确认的少数民族成分为新增人口进行户口办理。依据条文推理,则办理新增人口的户口登记时,只要符合办理户口登记的条件即可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确认其民族成分。
下文将根据上述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于入籍外国人者的民族成分管理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入籍外国人者的民族成分管理,最初是在1986年通知第三段中规定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当入籍外国人者原本的民族名称与中国的某个定称民族名称相同的,则可以填写为此民族。第二种是没有相同民族的情况,则处理如下:按照其本人所称的原本民族填写其民族成分,但是需要在填写的民族成分之后注明为是入籍的特殊情况处理,比如说“乌克兰(入籍)”。
1990年规定的第八段则不仅细化了1986年的规定,而且增加了对入籍外国人者子女和跨国婚姻子女的民族成分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规定当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经过符合规定的程序填报为属于我国的任一少数民族成分时,对该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参照其填报的少数民族所享受的待遇对待。
首先,入籍外国人者的民族成分可以申请为相近的我国现有民族,但是“须在入籍后的两年内申请办理”。这一年的规定并无入籍外国人之后在原民族名称上加注的规定,而是增加了入籍的外国人个人要求填报为中国国内任一民族成分的,应该先从其所属的部门内开具有关的证明,然后再向省一级别的民族事务管理部门提交申请。
其次,在1990年的规定之中,还增加了对于入籍外国人者后裔和中国人同外国人结婚所生的子女的民族成分的规定。即当父母中的任一一方属于中国人或者是加入中国籍者的情况下,并且申请填报为我国某一民族成分的。作为申请者(即具有中国国籍的子女)应该填报父母中属于中国一方的民族成分。
2015年的规章则在第二十条中完善了入籍者民族成分的规定。增加了当中国公民收养的子女取得中国籍时,其个人的民族成分应该根据收养其的中国公民的民族成分进行确定。至于其他的入籍外国人民族成分问题,则在该条中规定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综合上述内容,我国对入籍外国人者的民族成分现行管理办法为:
其一,对于入籍外国人者,有相近的民族成分,则入籍外国人者可在入籍两年内申请该相近民族成分;无相近的民族成分,则可以采取在外国人原民族名称上加注和申请加入我国某一民族成分两个措施中的任一。
其二,对于入籍外国人者的后裔、中国人同外国人结婚所生子女、中国公民收养子女,其在取得中国国籍后才可根据中国一方父(母)的民族成分确定其个人的民族成分。对于以上两种入籍外国人少数民族成分确认方式,可以明确地对比出是与本章上半部分我国少数民族公民民族成分确认原则和确认程序不一致,乃至相对突兀的。
三、入籍外国人确认问题的国际经验
过去的几十年中,人权已然成为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性话语、一个全球性的通用语、甚至是“世界性的世俗宗教”。 在国际人权领域当中,《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是对于少数人权利保护的主体和内容较为权威的法律文件。《公约》对于入籍外国人的分类和确认问题,笔者认为公约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其一,将入籍外国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分类入少数人之中,但并不归类为族群上的少数人。《公约》对少数人的概念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现在国际上对《公约》第27条中关于少数人这一概念的主流解释是卡波托第所做的:“它明确地只限于第27条的适用,并将下面这些群体成为少数人:第一,在所属的国家领域之内,在人口的总量上要比另外的群体少;第二,这个群体不能是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优势群体;第三,这个群体必须具有与所属的国家其他的群体在人种、信仰或者语言方面的特征,并且这个群体的成员至少在显示出了继续保持这种不同特征的希望或努力。” 以上的条件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不能被认定为少数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虽然只占十分之一的人口,但因为居于优势地位而非少数人。同时,少数人群体还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在这一问题上智利的修正案用词更为明确,指“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少数人。 所以,《公约》对少数人的认定是非常谨慎的。在此基础上,入籍的外国人只有在同时满足居住到一定期限、达到一定人数、处于非支配地位并且愿意保留其文化、传统、宗教、语言特征的前提下,才能在其所居住的国家之内享有国际人权中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规定。同时,由于入籍的外国人并非居住在本国内的世居族群,所以只被归类为语言或宗教上的少数人。
其二,《公约》将少数人群体的存在视作一个无需确认的客观问题,在具体个案的处理上留下了足够的弹性空间。但这也和《公约》将少数人的权利定位为消极权利有关,需要辩证的看待。《公约》关于第27条的讨论,达成了对于少数人是否存在是一个实际问题,而非取决于其他主体的承认。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是这样表述的:“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一国人口之中的某一群体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少数人是一个涉及实际经验的问题,而不是取决于有关的国家在法律上对相关群体的承认。 ”但是,对于实际操作中的如何凭实际经验认定,公约采取了模糊化的处理,为实践留下了足够的弹性空间。
其三,在《公约》之中,将少数人的权利定义为一种带有集体性质的个人权利。这种做法既保护了少数人的权利、避免了政治上的分裂可能性,又使上文中的对少数人群体确认的弹性处理具有了合理性。所以该条之中的少数人权利在性质分类上是消极权利和带有集体性质的个人权利。第27条是《公约》中唯一一个具有典型的消极表述的规定,即“不得否认个人享有”公约中的权利。 换言之,这一条款仅仅强调了国家不去侵犯少数人个体的文化、语言、宗教权利的消极义务,对于少数人而言这是一项明确的消极权利。同时,国际上公认这一条中的权利是带有集体性质的个人权利。虽然只有在集体有意识的情况下能够一起行使相应权利,但其本身的性质就是一种个人权利。这一条款只是用于“属于少数人群体的个人”。卡波托第在其编写的评注中详细列举为什么如此表述的具体考量:“首先,少数人保护这一权利最初便是以个人权利的形式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除了带有政治性的民族自决权之外,《公约》之中所规定的其他所有权利在性质上都属于个人的权利;第三,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让少数人的身份成为利益划分的一个标准会让少数人群体的政治性加强,甚至会增强其分裂的可能性。” 《公约》将少数人权利定义为带有集体性质的个人权利,从而在实践中将少数人群体视作一个实际问题来处理。所以《公约》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并不需要对少数人群体进行确认,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保护了少数人的权益,更避免了政治上的分离倾向。但是,这和公约将少数人的权利视为消极权利,仅仅限于国家有消极义务不得侵犯少数人权利亦有关系。
四、入籍外国人的民族确认问题思考
笔者认为入籍外国人的民族成分问题主要矛盾在于现行管理办法提供入籍外国人获得民族成分的途径并参照少数民族待遇对待,这一做法从我国制定少数民族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原则进行考量,并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并且简单的将入籍外国人的民族身份管理参照少数民族进行,是不符合入籍外国人所属群体性质归类的。即使在国际上也未把入籍外国人简单的归类入少数族群之中或是让其在个人身份上加入入籍国的少数民族群体之中。对于入籍外国人的民族成分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处理。
首先,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国的入籍外国人并不符合国际上少数人的标准和我国的少数民族标准,不应按照我国现有族称对其划定成分。笔者在上一章中已详细论述了入籍外国人在国际人权领域被列为少数人进行权利保护的条件和限制,在本节中就不再累述。
其次,当未来我国的入籍外国人达到国际上对少数人的标准时,则应参照少数人权利保护办法对其进行管理。但是,入籍外国人在性质上自始至终并不属于少数民族范畴,不能简单的套用我国的少数民族成分并参照少数民族待遇进行相应的对待。
综上所述,笔者的具体建议为:
首先,笔者认为要取消外国人加入我国民族成分(无论是相近民族成分还是入籍两年内自愿申请加入)并参照少数民族对待的规定,一方面,从少数民族成分管理的角度讲,对入籍外国人参照少数民族对待,并不符合我国的民族政策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国际上对待的入籍少数人的经验来看,如果直接对入籍的少数人进行认定并制定优惠政策,是不符合国际上的少数人标准和立法取向的。
其次,在当下我国入籍外国人较少的这一时期,可以继续执行入籍外国人在民族一栏统一加注的管理办法,但不能按照少数民族对待。即使在未来入籍外国人增多的情况下也不能提供其加入我国民族成分或按照少数民族待遇处理的法律途径。因为入籍外国人既不属于少数民族又非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照顾对象,对其的管理政策应参考国际上少数人的标准来对待。
最后,在有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我国应实事求是制定针对入籍外国人群体的管理办法。即使需要制定对入籍外国人群体的优惠政策,也不能简单的套用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并且,笔者认为,我国如果要制定对入籍外国人群体的优惠政策,必须是在其满足国际上对少数人定义的前提下才能制定。即对于以下标准全部能够满足:第一,在所属的国家领域之内,在人口的总量上要比另外的群体少;第二,这个群体不能是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优势群体;第三,这个群体必须具有与所属的国家其他的群体在人种、信仰或者语言方面的特征,并且这个群体的成员至少在显示出了继续保持这种不同特征的希望或努力。 只有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群体满足了上述的所有条件,才能对其参照少数人的国际经验进行照顾和优惠。否则只应制定针对外国人群体的管理办法,而不应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注释:
朱维群.关于当前民族工作几个问题的思考.中国统一战线.2011(1).15.
孙国华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246.
[英]马尔科姆·郎芳.人权与千年计划.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20.
[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上孙世彦、毕小青译.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三联书店.2005.670,672,685,665.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史密斯著. 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戴小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5]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 56 个民族的来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6]沈寿文.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7]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8]陈兴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识别.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3).
[9]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6).
[10]戴小明、盛义龙、刘木球.民族识别与法律认定——以(亻革)家人认定个案为研究样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11]戴小明、盛义龙.未识别民族法律地位探微——以民族平等为研究视角.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2(5).
[12]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l).
[13]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14]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 28(5).
[15]蒋立松.略论“族群”概念的西方文化背景.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2(1).
[16]金炳镐、毕跃光、韩艳伟.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2).
[17]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2).
[18]马戎.论民族意识的产生.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17(2).
[19]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20]马戎.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7(4).
[21]马俊毅、席隆乾.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民族概念及其英译的新思考(二)——National ethnic unit:我国亚国家层次民族英译的新探索.广西民族研究. 2013(2).
[22]聂文晶.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概述.民族学刊.2013(5).
[23]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5(5).
[24]沈寿文、董迎轩.对现行《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文本之解读——基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中央统一领导的取向.云南社会科学.2012(1).
[25]沈寿文.宪法文本中“民族”不同内涵的知识根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26]沈寿文.撤自治县(州)改设“市”异议之商榷——兼驳增设“自治市”主张.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4).
[27]唐建兵.也议“民族识别”与中国民族问题——与马戎教授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28]汪堂家.沿用“我国有56个民族”的提法有待商榷.社会观察.2004(10).
[29]王希恩.中国民族识别的依据.民族研究.2010(5).
[30]王文光、段红云、尤伟琼.当代云南民族识别的学术回顾.思想战线.2011, 37(1).
[31]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1).
[32]周刚志.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中国宪法权利性质之实证分析.法学评论.2015(3).
[33]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