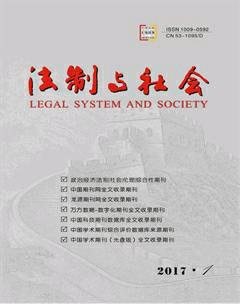探寻对声音利益的民法保护途径
摘 要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自然人的声音利益进行侵犯和利用的现象都越来越突出,而我国法律对于自然人“声音利益”的规定仍处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为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利用自然人的声音利益,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侵犯声音利益的问题,本着尽力维持法的稳定性和法律条文精简的原则,我国应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将声音利益有区别地纳入其它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范畴之内进行保护。
关键词 自然人 声音利益 声音权 声音肖像权
作者简介:梁震,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121
目前我国学界已经围绕如何保护声音利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比较法上不同国家对声音利益的保护途径也可以给我们相当的参考借鉴资料。本文拟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民法意义上声音利益中“声音”的范围
“声音”这一名词在物理学上的概念是指,是通过介质传播并能被人或动物听觉器官所感知的波动现象。而在民法意义上,声音利益当中的“声音”所涵盖的范围应当被缩小。
首先,并非所有的声音都在民法的规制范围之内,只有是自然人或拟制自然人所发出的声音才受民法的调整。其次,必须能为人所能感知。不同物种可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是不一致的,因此,作为具有人格利益的声音应当局限在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即必须能为人所感知。如果是其它物种如家畜听到了人类发出的次声波、超声波并因此产生不良后果(比如鸡受到次声波干扰后产蛋率明显下降),当事人可通过侵权等方式请求救济,而与此处的人格利益没有直接关系。
二、我国对声音利益进行民法保护的必要性
(一)保护的逻辑基础
1.“声音”具有可识别性,是重要的个人标识:
“声音”和“姓名”、“肖像”相类似,都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尤其是对某些公众人物而言,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声音已经成为的代言人,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比如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主持人赵忠祥的声音、著名相声演员赵本山的声音以及《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易中天的声音等,大家即便没有看见其本人面貌出现,但是只要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自然而然地把所听到的声音和本人一一对应起来,由此,“声音”便具有了相当的可识别性,成为重要的个人标识。
2.“声音利益”兼具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
自然人的声音关系到个人的尊严,即“声音利益”当中包含“人格尊严价值”。比如,在2006年世界杯时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解说员“黄健翔解说门”事件爆发后,网络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版本的黄健翔音频文件,当中有些并非黄健翔本人发出的声音,而只是通过电脑软件合成的,并且当中的内容甚至是恶意丑化本人形象的;这样一来,黄健翔本人的个人尊严受到了严重损害,公众形象也大打折扣,无论是对他的生活还是工作都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同时,自然人的声音也包含着财产利益,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自然人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财富资源,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法律应当鼓励和规范合理利用自然人声音创造经济价值的行为。比如,某歌手将自己所演唱的歌曲通过电子音频的形式刻录下来,然后向相关主体收取一定的版权费用来实现声音的财产价值;在淘宝上,还有部分商家提供代替买家进行电话道歉、表白甚至是哭丧等服务,这些都是声音的财产价值的体现。
3.“声音利益”具有较强的人身专属性:
“声音利益”具有其他一般人格权的共性即人身专属性,这也就是说“声音利益”的实现不能脱离个人的控制。“声音”和“肖像”、“姓名”不同,其之所以具有相当的可识别性,往往不是因为“声音”本身传达的内容,而往往因为声音的响度、音调、音色具有主体差异性;但“肖像”、“姓名”往往通过其表达的内容本身来与主体进行对应,比如通过肖像,那么一般就是根据肖像所展示的个人的五官、身材、身高等特征来进行识别。那么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声音”相较“肖像”、“姓名”而言,其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大、创造的空间也更大、传达的内容也更丰富,一旦脱离个人的控制,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自然人能够许可他人使用“声音的表现形式”,但是一定不能转让自己的声音。即便著作权法对声音版权进行保护,“声音利益”也没有脱离个人的控制,因为此类声音版权一经形成,就由“声音”转换为“声音的表现形式”,其内容固定下来,那么最初声音的所有者对自己声音的内容、用途都是有认知的、也是可控制的。
(二)保护的现实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声音”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更快,利用和侵犯声音利益的现象也日益突出,为进一步保障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规范合理使用“声音”财产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法律急需对声音利益的保护问题做出全面回应。
在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声音的传播范围和速度都十分的有限,除了日常对话能传播之外,只能通过电视、磁带、光盘等方式传播,声音利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并不明显,即使受到侵犯,其损害后果和影响范围也远远没有现在广。在当代,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传播的范围,以往只能通过磁带、光盘等传播的影音作品现在通过电子文件的形式轻易就可以被传播,不仅速度快而且成本低;另一方面,音频合成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成为合成音频的主体,而不再局限于那些具有专业性的组织或个人。
可以说,近年来我国相关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已经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化市场的产品种类,但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对个人的声音利益进行有利的保护,一方面是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鼓励更多原创文化作品的出现、活跃文化市场、增强本土文化作品的竞争力的应有之义。
但纵观我国整体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民法体系,对“声音利益”的保护其实并不完善。除了在《著作权》第三节“录音录像”中对声音的商品化有规定之外,其余民事法律鲜有提及。这种对声音利益的保护是不全面、不完善的,对于声音利益当中的精神利益无法进行保护,对当中的财产利益也只是进行了部分保护。
综上,声音利益关乎个人生存的尊严,同时也是重要的价值财产,面对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侵犯声音利益的案例,我国需要完善对声音利益的民法保护。
三、对声音利益进行民法保护的途径
(一) 比较法上
1.美国: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3344 条之规定, “……为广告、销售或招揽客户目的使用他人姓名、声音、签名、照片或画像”的行为属于公开权(又称形象权)的范围。“公开权是指个人对其姓名、肖像、声音等个人形象特征,得为控制,而作商业上使用的权利。”
在Midler v.Ford Motor Co.案 中,被告Ford Motor Co.雇用某演唱人员故意模仿原告Bette Midler的声音进行演唱,并以此推销自己的产品。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所取得的效果和播放原告录音磁带所取得的效果是相同的,系侵害了原告的公开权,并认为“当某一专业演唱家的声音广为人知的时候, 当他的独特声音被刻意模仿以销售某种产品时 ,销售者就盗取了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就在加州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实条件下,美国保护声音利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公开权(形象权),而这一权利又主要是用于保护人格权益中的财产价值,这有利于规范和保护市场经济中人格权的合理化商品利用,有利于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更可能多地创造社会价值财富。但同时这种保护方式也有缺陷:
首先,片面强调保护声音利益中的财产利益,而忽视了对声音利益中精神价值的保护。
其次,过分强调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会使得法律对人格权益的保护丢失最基础、最根本的价值,即实现个人的平等和尊严;并且,这会使得个人权利的泛商品化,会对全社会带来“金钱是衡量人格的唯一手段”的错误引导。
而在我国虽然某种程度上法律给予这种人格权商品化利用一定的保护,但是在我国法律中没有公开权的概念,我国对于人格权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并没有做明确的区分,因此,通过公开权的方式保护声音利益在我国缺乏立法基础。
2.法国:
《法国民法典》第 9 条规定:“一个人的声音是其人格特征之一,在某人因具有特色的声音而与鉴别其人身有关联时,这种声音可以受到本法典第 9 条所给予的保护。任何人都可以禁止他人模仿自己的声音,如果这种模仿会造成混淆与误会,或者会给被模仿人造成任何伤害。”
根据上述立法,可得知法国民法明确规定声音是个人的人格特征之一,声音权只能由自然人所想有,且该种声音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是具有相当的主体可识别性,即某种声音因具有相当的特色而得以与其他声音辨别开来,从而与每个不同的主体一一对应。也就是说,法国民法是通过单独的声音权来保护自然人的声音利益的,而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体系下,还没有单独规定声音权。至于在我国新设声音权的可行性分析将会在下节具体做分析。
3.加拿大:
《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第 36 条规定:“特别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为侵犯他人隐私:……将他人的私生活公开 (5)使用他人的姓名、肖像 、形象或者声音,但向大众合理公开信息的除外……”
由此可知,加拿大对于声音利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隐私权的方式,事实上其对于姓名、肖像等的保护均也是通过隐私权。因此,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地区,是没有姓名权、肖像权等概念的,这些权益都在隐私权的外延之内。
而反观我国隐私权的概念,我国隐私权的外延应当是小于加拿大隐私权的外延的。在我国,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都是并列的具体人格权。因此,只将声音利益的保护列入隐私权保护范围之内,会破坏我国法律条文之间的内在联系、破坏划分标准的科学性;如果将肖像权、姓名权等权利的权益保护都纳入我国法律规定的隐私权范围之内,那么就必须首先取消肖像权、姓名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地位,法律条文需要做大幅度修改,这会影响到法律的稳定性;如果有其它更好、对现行法律造成更小幅度影响的方法,则没有必要采取此种办法。
(二)我国学者的主要意见
1.通过单独创设“声音权”进行保护:
如杨立新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建议稿》第50条写道:“自然人的声音标识受法律保护。未经同意,不得私自录制他人的声音,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自然人可以同他人签订有偿的声音使用许可合同。两个以上自然人共同享有声音权,当事人具有共有支配权,使用人格利益的准共有规则。”
某种程度上,“声音”和“姓名”、“肖像”是并列的人格标志,因此单独创设“声音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考虑到我国现实情况,如果能够在既有体制内通过扩张解释的方法能够解决此问题,那么就毋须新设一具体人格权。
2.通过合并创设“肖像声音权”进行保护:
由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第377条写道:“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和声音享有支配权。”第380第1款规定:“除公众人物情形外,未经本人同意展览其肖像声音或将之出售的,自然人可要求停止展览或售卖其肖像声音。”
肖像和声音两者确实非常相似,但是也有不同。比如对肖像的侵犯往往表现为未经当事人许可以及故意丑化当事人肖像等方式,而对声音的侵犯除了未经当事人许可使用之外,更多地表现为利用当事人声音的特性去从事对其他法益的破坏,即将声音的利用作为对其他法益破坏的一种手段。因此,肖像和声音虽然相似,但也却又相当的不同,因此将两者合并成立一种新兴的权利类型或许不太合适,在我国立法过程中,也从未听说有此种立法方式。
3.类推适用“肖像权”的规则对声音加以保护:
“声音本身可以作为一种人格利益,但因为声音利益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侵权法等多个法律保护,所以没有必要将其类型化为具体人格权。” “考虑到声音与肖像具有共同的特点,即主体的可识别性,人们听到一种声音之后想到的就是特定的人,以你可以类推适用肖像权的规则对声音加以保护” 。
如前所述,肖像和声音一样,都是重要的人格标识,但是应当承认的是,一般情况下,声音所能够表达内容的范围比肖像要大得多。当行为人通过模仿“声音”的手段去侵害其他具体人格权如隐私权等权利时,是无法类推适用肖像权的规则的。
4.通过一般人格权进行保护:
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需特别指出的是……此种得将个人识别化的……尚有个人的声音等……个人的声音应认系一种‘其他个人法益” 。
将声音利益仅仅列入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会导致对于声音利益的保护力度不够,并不能与现实中声音利益受侵害的现实情况相适应。另外,而当侵权人通过模仿声音的手段去侵害其它具体人格权时,对“声音利益”的侵害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单单将这种“声音利益”规定为一种一般人格权根本达不到对受害人填补损害的功效。
四、本文对我国声音利益的民法保护与限制的看法
立足于我国现实,为了兼顾法的稳定性和法益保护的必要性,我们应当尽最大可能在现行立法体制内解决问题,即通过对现行法律的扩张解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随意立法,否则现行法律的权威性将受到严重挑战,人们对法律的信服度也将大大下降。
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护。
对于通过具体人格权保护部分,是指“声音利益”受到侵害不是通过“声音”本身,而是通过声音所传达的内容,这个时候“声音”不过是作为侵犯其它具体人格权的一种是手段、工具,侵犯者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听众对声音特质存在一种特殊的信赖。那么如果一个人通过电脑合成软件模仿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并且声音的内容涉及另外一个人的个人隐私或者名誉,那么可以通过“隐私权”和“名誉权”来保护,而非通过“声音”本身来进行保护。
对于通过一般人格权保护部分,是指“声音利益”受侵害时在具体人格权上找不到相对应的法益,则划入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以内。例如,对于如果声音所表达的内容并无不当,不涉及任何的个人隐私等,纯粹是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便公开传播其声音,则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的方式来予以保护。
所以,应结合侵权行为具体所侵害的法益来确定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法进行保护。虽然声音利益亟待保护,但这并不是说声音利益的行使就是随心所欲,完全不受限制的,在一些情况下,声音利益的保护和利用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一,出于科学研究、新闻报道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声音的利用不构成侵权。比如,某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新闻工作人员深入现场进行报道,在报道的时候录入了很多现场人员的声音,但是这并不构成侵权。
第二,国家机关出于依法行使职权的需要,对声音进行利用不构成侵权。比如,侦查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时需要录音作为最后的证据,即使犯罪嫌疑人没有同意,录音中对其声音的使用也不构成侵权。
第三,为声音所有人本人利益对声音所进行的利用不构成侵权。如当自然人下落不明时,其近亲属为尽早获得其下落信息,可以在网络上公布其日常生活视频,当中包含自然人的声音,但是这并不构成对当事人声音利益的侵害。
第四,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侵犯声音利益的时候应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只有当行为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所发出的声音有使听众产生混淆、误判的可能,仍不予以说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成侵权。这样既保护自然人的发声自由,又保护了声音人的声音利益。
注释:
王泽鉴.人格权——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64,249.
Midler v. Ford Motor Co.849 F.2d 460 (9th Cir. 1989).Wohl, The Right of Publicity and Vocal Larceny: Sounding Off on Sound-Alikes,57 Fordham L. Rev. 445(1988).
李明德.美国形象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03 年冬季号.
杨立新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379.
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2.
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90.
王利明.人格权法——王利明法学教科书系列(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