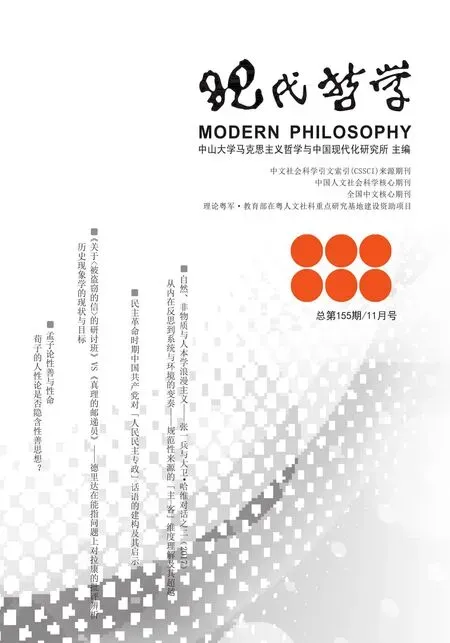货币的隐喻学: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之谜”
覃万历
货币的隐喻学: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之谜”
覃万历
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修辞性质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兴趣和注意,但这种理解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文本及其对现实的再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因此,本文的主旨是通过解答马克思解答货币之谜时所制造的文本的“货币之谜”,以说明马克思使用的隐喻及其所构建的货币理论之间的深层关系,这构成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货币的一种隐喻学。
货币;《资本论》;隐喻
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普遍关注不过是近些年来才发生的事情,而这种关注本身更多的带有现实的眼光,即一方面是马克思所指明的货币的拜物教性质在日常生活、文化、制度等方面全面展开的各种批判性分析,另一方面是在当代信用制度和金融制度高度发展的货币系统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何种程度上依然有效的争论。*可参见Anitra Nelson, Marx’s Concept of Money: The god of commod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edited by Fred Mosel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Nimi Wariboko, God and Money: A Theology of Mone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08; Georgios Papadopoulos, Notes Towards a Critique of Money, Waregem, Cassochrome, 2011; Fred Moseley, Money and Totality: A Macro-Monet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ogic in Capital and the 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Leiden, Brill, 2016. 此外,尽管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把西美尔(Georg Simmel)的《货币哲学》和韦伯(Max Weber)的货币理论看作是马克思所指明的货币的拜物教性质在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扩展性研究。([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然而,这些扩展性的批判和有效性的争论恰恰因为这种现实的眼光,使学者们往往过度专注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至少是忽略了对马克思文本的全面研究。当然,这种忽略主要不是指马克思的文本实际,而是指马克思的文本形式。不可否认《资本论》是关注并针对现实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这些研究者们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总是力图趋向现实;只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资本论》作为一种理论的文本,它是文本性的,是具有文本的形而上学意味。这不是要宣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也不是要把《资本论》当作文学来阅读,尽管我们可以这么做,*指出的这两点主要源自德里达。但用文学的方法来阅读《资本论》,在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看来从威尔逊(Edmund Wilson)就已经开始了。(Edmund Wils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40; Robert Paul Wolf, Moneybags Must Be So Lucky: On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Capital,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p. 7.)而是说《资本论》首先是一种写作,它与其它方式的文本写作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一种修辞的灵活运用,一种语言结构的叙事构型*这样一种理解实际上源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历史修撰的观点。因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或者说他对货币之谜的解答就是关于货币起源的历史,所以它也是一种关于货币的历史的修撰或写作。资本也一样。当然,与怀特只强调文本的形式相比,我更强调文本的形式及其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参见[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所以,《资本论》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再现,还是一种埋藏在马克思内心深处的想象性建构,而这种建构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某种修辞范式,相应地,这种修辞范式透过其所体现的叙事构型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再现。*马克思对《资本论》中的修辞是有所自觉的,比如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他没有自觉到的是,修辞的语言结构及其与内容之间的深层关系。([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换句话说,既要注意《资本论》的文本内容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也要注意《资本论》的文本形式及其对文本内容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本文就是在文本的这种意义上,从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的叙事构型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理论。
具体来说,其中的关切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货币理论的基本观念主要表现为对货币之谜的解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对货币的理解与第一卷中所建立起的基本观念相比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即是对货币起源的历史性叙述,而这种解答或叙述本身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物-有用物-劳动产品-商品-货币”这样一个可感到半可感的历史性的结构链条。对此,通常的做法是接受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的这一叙事构型所建构的相关内容,而没有注意到这一叙事构型本身,以及这种叙事构型与它所建构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围绕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结构链条,一方面从内容上来看,货币形式的历史起源就是简单明了的物逐渐转化为炫目复杂的谜之货币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形式上来看,货币形式的历史起源则是一种从炫目复杂的物逐渐转化为简单明了的货币形式的过程。所以,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如何通过这样一种在形式上不断简化而在内容不断谜化的方式揭示货币起源的历史事实?可以说,马克思在解答现实的货币之谜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文本的“货币之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答马克思解答货币之谜时所产生的这一“货币之谜”。当然,这种解答只是出于修辞的理论兴趣,而非要把《资本论》解释为某种修辞作品,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资本论》毫无修辞的性质,这种性质通过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的叙事构型所反映出的多重隐喻显示出来,这构成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货币的一种隐喻学。
一、物转化为商品
《资本论》的起点或许是商品,其逻辑结构的起点或许是劳动,但这些起点的起点必然是物。首先,商品得是一个物,马克思从没有否认这一点,“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还可以进一步说,劳动与物(劳动资料)的分离是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其次,劳动若没有物的前提就不能实现自身,马克思也深知这一点,“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208页。。所以,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把“物”当作《资本论》的起点,但仍然可以认为“太初有物”是《资本论》所隐藏的一个形而上学条件。*马天俊:《马克思物思想的形而上学探究——读〈资本论〉一得》,《学海》2011年第6期。当然,物是多样的、复杂的,在感觉经验上都无法否认这一点,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但他也不打算深究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根本上对于物的如何可能是不关心的。或者说,他首先关心的不是物及其条件而是物的并不神秘的有用性,即那些有用物,“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然而,把抛弃无用物的责任推给历史并没有解决问题本身。难道无用物不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其只是在不同方面没用,发现这些不同方面的没用同样是历史的事情。所以,根本上,对于物,不管是有用物还是无用物,其本身的存在显然是自然的事情,并不天生的就分为有用物和无用物。于是问题就转变为它对谁或什么有用或没用?显然,答案是对人。也就是说,从物到有用物的这一结构转化中,马克思用物之一种的有用物“替代”了物,因而无用物从马克思的物中被抛弃了,有用物则成了物的全部形式。这样,马克思就通过“撇开”无用物而将人从物中“排挤”了出来(ausgeschlossen),同时将物的使用价值“排挤”了出来,*“撇开”和“排挤”等这类隐喻性术语本身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常用术语,尤其是马克思经常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说“撇开”的事情。因为有用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了能够满足人的使用价值,自此,物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交汇了。可见,这种部分“替代”整体的转喻性隐喻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使物转化为有用物的同时,使人和使用价值凸显出来。随后我们还会看到不同隐喻的相同作用。
自然可以长出亚麻、青麻、黄麻、苎麻等有用物,却长不出麻布和上衣。这是说有用物也有其限度,因为只有凭借一定的手段,作为天然存在的有用物的麻类植物才能变成特定的有用物如麻布和上衣;与此同时,不管是麻类植物还是麻布和上衣,它们可以满足人的某方面的需要,却不能满足人的全部需要,如它们就不能满足人的胃的需要。所以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我们就必须不满足天然存在的有用物,或者它们本身就不能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这就迫使我们要去创造与我们的各种需要相对应的各种使用价值。因此,对于“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这种生产活动就是劳动,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出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即各种劳动产品,这样才能确保人类生活持续进行的可能性。但这种创造并非“无中生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劳动而使有用物“变形”(Metamorphose)为劳动产品。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Formen der Stoffe)”,同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马克思引用韦里( Pietro Verri)的话作为补充,“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自然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Umformung des Stoffes)”。*同上,第56页。比如,我们可以把麻布变成麻布上衣,甚至镶上金边,但决不能把麻布变成金缕玉衣。所以,种种劳动产品不过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实属无奈。*同上,第56页。总之,从有用物到劳动产品的结构转化要通过“变形”这一物理学隐喻来完成,或者说,只有经过劳动而变形的有用物才是劳动产品,没有经过劳动变形的则是非劳动产品,马克思所在意的只是作为劳动产品的有用物。于是,马克思通过撇开那些非劳动产品的有用物,将劳动及其对使用价值的创造从有用物中排挤了出来。
但劳动产品还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同上,第54页。。也就是说,织麻布者的麻布用在自己身上和用它去换圣经有质的分别。麻布作为劳动产品,它有使用价值,但如果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对织麻布者而言的,它就不能成为商品。它要成为商品,就要把自身的这种使用价值“让渡”出去,从而“转移”为卖圣经者或其他人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交换”(aus-tauschen)。问题在于交换的尺度是什么?不同质的使用价值的交换,即让渡和转移只是表面的现象或至少不是历史的常态,因为这种使用价值体现的只是劳动的质的方面,并不具有可通约性。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一种可通约的量的尺度,即在交换中它们必定能化为的“第三种东西”。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商品的价值,它“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比如,生产麻布和生产圣经明显是不同质的两种劳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不同形式”*同上,第57页。。这样,不同质的劳动作为同样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在量上就变得可计算、可通约了,具体表现为劳动时间的可计量性。因此,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的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同上,第60页。于是,问题就清楚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造成了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前者是后者的物质承担者,后者是前者的交换尺度。所以,从劳动产品到商品的结构转化要通过“交换”,即“到市场去”(zu Markte gehn)“让渡”和“转移”的空间隐喻来实现,这如同苏格拉底“下到佩莱坞港”般寓意深刻。劳动产品毕竟只是物,它不能反抗人,它要根据人的意志进行各种位移运动从而成为商品。这样,马克思将非商品的劳动产品撇开了,从而将抽象劳动和价值(在商品交换中表现为交换价值)从劳动产品中排挤了出来,而这种抽象劳动或价值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根源所在,这时历史在更高的形式上再次回到了最原始最野蛮的人与物对立的状态,但其背后所暗含的实则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对立。
总的来说,从物到商品的结构转化过程中,马克思通过有目的地撇开“无用物”、“非劳动产品的有用物”和“非商品的劳动产品”的同时,将“人”、“使用价值”、“劳动及其对使用价值的创造”、“抽象劳动及其对价值(交换价值)的创造”排挤了出来。其中,隐喻显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或正是这些隐喻使结构上的简化和内容上的谜化成为可能。
二、商品转化为货币
商品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过程一定是社会性的,它首先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经济关系上的反映。*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指出货币本身的社会性,“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62页。)因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具有法权关系的占有者来说是非使用价值,而对它们的不具有法权关系的非占有者来说才是使用价值,所以商品需要通过意志关系来让渡和转移,才能彼此作为使用价值而实现自身。也就是说,“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以前,必须作为价值来实现”*[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即需要通过价值的交换来完成商品使用价值的让渡和转移。比如,马克思的那位老朋友织麻布者,这次不是去换圣经,而是出于某种需要用20码麻布换了1件上衣,其中可以明显看到在交换过程中这两个商品之间的这样一种价值关系,即“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马克思认为,这个最简单的商品形式里就已经包含了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经济学家们一向都忽视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实: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码麻布=2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它自己的天然形式不同的东西——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1页。)简单来说,“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Keim)”。*[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页。现在,让我们跟着马克思的文本叙事,具体来看看马克思如何使第一种价值形式的“胚胎”逐渐发育成了货币形式,以致最终破解了货币之谜。
在马克思看来,“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价值形式中,20码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1件上衣则起等价物的作用,以作为表现麻布价值的材料,反之则相反。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不管20码麻布和1件上衣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等价形式,它们作为价值都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从而具有同一单位的量的可通约性,因此,麻布的价值存在可以通过它与上衣的直接相等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而其中量的比例取决于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间。但这个价值形式不仅是简单的,也是社会中个别的和偶然的现象,我们的织麻布者不可能每天都拿麻布去换上衣,尽管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而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他还要根据自己的其它需要去换圣经或烧酒等,其他人也一样。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即会“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如“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40磅咖啡,或=1夸特小麦,或=2盎司金,或=1/2吨铁,或=其他”。*同上,第77、78页。这样,作为人类劳动的凝结,现在每一个其它商品体都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充当等价物。但由于社会状况仍未完全发展,第二种形式即这种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不管它的表现系列如何无止境,它都不过是无数的第一种形式的并列。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的总和,或第一种形式的等式的总和构成”。所以,作为构成要素的简单的第一种形式和作为被构成的总和的第二种形式在基本意涵上没有实质差别,因为其中“20码麻布=1件上衣”与“20码麻布=10磅茶叶”等同样作为第一种形式,其基本意涵是一样的,第二种形式就是这些意涵相同而又相互排斥的等式构成的总和,虽然其在结构上扩大了,但“20麻布=1件上衣”依然是这个结构的意义核心。可以说,第二种形式不过是第一种形式的无限复制或分裂,即它的增殖,这确实符合“胚胎”发育的自然法则。
然而,当我们把第二种形式“倒转”过来(sich rückbezüglich)——这显然是一个空间隐喻——的时候,价值形式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因为这时“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么,其他许多商品占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它们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同上,第80—81页。。也就是说,当麻布与作为其等价物的其它商品在结构上“换了位置”时,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表现在麻布这一惟一且同一的商品上,这就使得第二种形式转化为一般价值形式或第三种形式。我们知道,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都只是使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不同的东西,而现在其中一个商品,如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所有的其它商品都可以用麻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即麻布可以和所有其它商品进行直接的交换。这时的人类劳动也就获得了一种统一的表现形式,即作为一般价值表现的麻布价值。但这种“倒转”或“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同上,第83页。,所以它不再是个别商品的私事,而是商品世界的公事,从而就产生一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形式及与之相应的一般的社会的等价形式。进而,当这种等价形式同某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时,这种独特的商品就“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同上,第86页。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个一般等价形式就是麻布,它在商品世界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然而,“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本身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6页。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商品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从而作为价值,它都可以充当任何其它商品的等价物,即可以充当货币。由此可见,货币本身只是一个代表商品价值(或交换价值)的“X”,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且不管这个X为了找到一个物质承担者,从而“化身”(inkarniert)为麻布或是化身为上衣或是牲畜等等,其在职能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却造成了货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这就是马克思认为的货币的秘密之所在。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并由于社会的习惯,作为特殊商品的金最终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于是金也就成了这种所谓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神秘之物。
总的来说,从商品到货币的结构转化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商品之间相互对立、不断排挤的过程,这通过“胚胎”的发育学隐喻和位置“倒转”的空间隐喻显示了出来,以致最终其它一切商品都与某种特殊的商品相对立。这种特殊的商品也就成了货币商品(最后固定为金),它既有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也有与之相应的表现商品价值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后一属性是其神秘性的根源。换句话说,马克思通过撇开其它商品而将某种特殊的商品如金从商品中排挤了出来,成了“货币结晶(kristallisieren)”,这也是商品内在矛盾外化的必然结果。
三、结语:关于货币的一种隐喻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文本的“货币之谜”就是:“物-有用物-劳动产品-商品-货币”这一历史性的链条,凭着多重隐喻(“替代”的转喻性隐喻、“变形”的物理学隐喻、“交换”的空间隐喻、“胚胎”的发育学隐喻和“倒转”的空间隐喻)在结构上有目的地撇开“无用物”、“非劳动产品的有用物”、“非商品的劳动产品”和“其它商品”而不断简化的同时,在内容上将“人”、“使用价值”、“劳动及其对使用价值的创造”、“抽象劳动及其对价值(交换价值)的创造”,以致最终将“货币”排挤了出来。当然,这种形式上不断简化而内容上不断谜化的过程,在马克思那里也是解答现实的货币之谜的过程。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货币之谜的解答,不只是对货币的历史的叙述,其中也包含着物的历史及人的历史,或者说,货币的历史、物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在这一叙事构型所建构的内容中相互关联地呈现了出来。而且,货币的这种历史奠定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本观念。因为基于这一叙事构型的结构关系,不管货币如何是神秘的、超感觉的,我们始终可以将它逐渐溯源到最初的物的前提,或者说,货币虽然有超感觉的一面,但它终究难以摆脱其是某种包含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从而具有作为某种特殊的物的“坚硬性”。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根本而言就是商品货币的理论,这也是他自己所强调的。正因如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不那么重视非商品形式的信用货币等相关问题,使得特别是那些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唯名主义的货币理论相融贯的研究必须得到重新考量。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一“货币之谜”的更深层次上,还可以看到从物到货币的转化实际上就是不同隐喻的转换,即从“替代”到“变形”到“交换”到“胚胎”到“倒转”的转换。这就是说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的叙事构型是靠着隐喻的修辞来运作的,所以正是这些隐喻在根本上建构着货币起源的历史叙事,以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货币起源的历史就是隐喻转换的过程和结果。而且,其中的意涵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简单来说。
第一,货币起源的历史是从物逐渐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过程,这明显反映在隐喻的不断转换中,关于这一点的分析上文已经给出。由此,可以看到隐喻对于文本或理论的建构有着非凡意义,很难把这些隐喻与货币起源的历史叙事或货币理论的基本观念决然分开,因为这些隐喻构成的是文本或理论的深层结构。不仅在马克思那,在其他思想家那也一样,比如柏拉图的“洞穴喻”等*参见田海平:《柏拉图的“洞穴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而且,即便是面对同样的货币问题,当我们换了套隐喻时产生的也是不同的理论结果。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算术隐喻”,其所产生的是一种可与政治、军事、伦理等社会问题相互计算、相互通约的货币理论,以致我们的生命、道德、婚姻等均可被标价;洛克(John Locke)的货币理论就是他的本身即包含隐喻的政治理论的隐喻化,是一种隐喻的隐喻,因而其货币理论实际上也是他的政治理论,当然,这不是因为它涉及了政治问题,而是因为它在深层结构的隐喻关系上植根于他的政治理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显然因使用了不同的隐喻而与二者有很大不同。*关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如何因使用了不同隐喻而不同的研究,笔者将以专题的形式在其它地方详细论述。另外,货币起源的历史,正如上文指出的,是与人的历史关联着的。因此,可以进一步说人类的历史同样是隐喻转换的过程和结果,比如当把先前为中心的货币的历史当成背景,而把先前为背景的人的历史当成中心时,这种隐喻的转换同样适用。这为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实际上维柯(Giovanni Vico)早就已经这么做了*参见维柯的《新科学》以及怀特的解读([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美]海登·怀特:《历史的转义学:〈新科学〉的深层结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相应地,也许可以从这种深层的隐喻结构来审视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发现通常被我们所忽略的东西,当然这有待进一步考察。
第二,从胚胎的发育学隐喻到倒转的空间隐喻的转换实际上是不协调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初衷,简单商品形式的胚胎应该要最终发育为货币形式,但这种发育却停滞在第二种形式上,第二种形式向第三种形式的转化被马克思换成了空间隐喻。通常认为混合的隐喻是坏的隐喻,因为这会造成理论的不融贯。*可参见Stephen C. Pepper, “Philosophy and Metaphor”,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28, pp.130-132; World Hypotheses: A Study in Evide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2; Edward W. Strong: “Metaphors and Metaphys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937, pp.461-471.进一步,从整个结构的转化来看,马克思明显使用了多重隐喻,所以就表面而言是非常杂乱的、显得随意的,根据上述看法,这必定会造成理论的不融贯。但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这种混合的隐喻相互补充地建构了他有关货币的历史叙事,也正是这种混合隐喻的不一致性成就了他的理论的更大合理性,使得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货币之谜的解答显示出极强的说服力。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混合隐喻对文本或理论的建构要优于单一的隐喻,马克思深谙这一点。*关于马克思在其它地方用混合的隐喻来建构他的理论的另一例证,参见马天俊:《马克思的修辞学实践》,《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第三,从整个隐喻的转换来看,这些隐喻都源自于不同的领域和方面,如变形的物理学、胚胎的发育学等,正是这种“借用”使这些被借用的概念发生了作用的改变,从而成了隐喻的。这就是马克思所使用的隐喻的实质。然而,同样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等*参见[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借用货币来隐喻地理解其它领域的问题,甚至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还直接借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谈哲学文本的隐喻问题*参见Jacques Derrida,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F. C. T. Moor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6, No. 1, 1974.。可见这种隐喻的实质不只是马克思所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留意这一点不仅对理解马克思,比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显然是建筑学隐喻,其包含了建筑结构的优点和缺点,而且对理解任何文本或思想至少是没有害处。
最后,这些隐喻的使用、隐喻的意义、混合的隐喻与隐喻的实质及其所造成的结果,构成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货币的一种隐喻学。
B27
A
1000-7660(2017)06-0018-07
覃万历,湖南张家界人,(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巳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