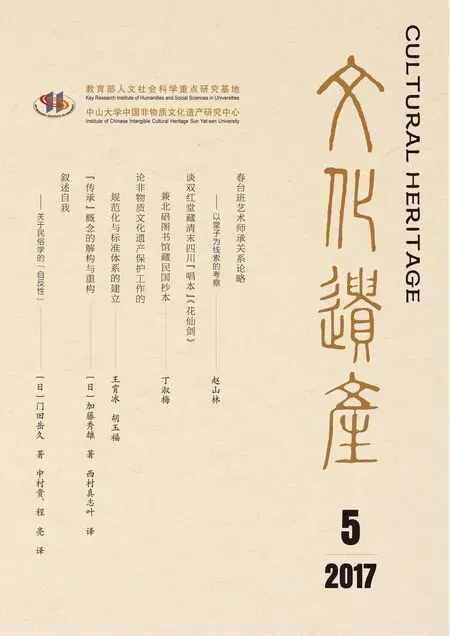明代南教坊制度考
刘 薇 李舜华
明代南教坊制度考
刘 薇 李舜华
早在朱元璋定天下时,便于南京设教坊司,并设乐院和官酒楼一统天下官妓;然而,“南教坊”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始于英宗正统初年,实为永乐迁都以来明代两京制度渐次确立的产物,北迁的教坊司从此成为天下教坊之首,而原在南京的教坊司最终退居次位。因为这一地位的变化,位处留都的“南教坊”,逐渐成为江南歌吹之地,也是南北士林、四方商旅往来风雅之地;更重要的是,在两京制度下,南教坊在明代乐制与演剧的变迁实际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简言之,正嘉以来,一方面是俗乐大兴,一方面是南教坊制度的日趋无序,其间种种曲事沉浮与文学往来,已直接折射出江南士林复古乐思潮的消长,而成为我们窥探晚明曲坛古(雅)乐与今(俗)乐、北音与南音之变的重心所在。
明代 南教坊 制度
明建以来,以南京为都,设教坊司一统天下演剧,即一统各地之教坊、乐院、勾栏等,后来永乐迁都北京,为遵祖制,以南京为留都,并继续保留了相关的建制,教坊遂有南北两教坊司。也就是说,所谓“南教坊”,实为明代两京制度的产物,因此,南教坊指的并非是字面意义的南京教坊。当明初之时,教坊原无南北之别,“南教坊”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始于英宗正统时期,也即北京教坊司明确确立为天下教坊之首时,原在南京的教坊司最终退居次位。这样,官方制度,以北京教坊司为重,以中央而统地方,因此“教坊”之称或为统称,或为指代北京的教坊司——而无需“北教坊”之称,原有南京教坊司,则别称作“南教坊”。也恰恰这一地位的变化,位处留都的“南教坊”,逐渐成为江南歌吹之地,也是南北士林、四方商旅往来风雅之地。再者,南京旧为六朝古都,其间曲事沉浮,与文学往来,更往往成为晚明,尤其是明亡之后,文人墨客的追忆所在,也是我们窥探晚明清初曲变的关键。
本文专考南教坊的演变,也即明英宗以来南京城教坊机构的演变。当然,这一“南教坊”与英宗之前南京城的教坊机构,其间沿革流变,也在考虑之中。
一、南教坊制度的演变
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纳陶安议,下集庆路,改名应天府。二十六年秋,改筑应天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括江淮之南北十有三府四州为畿内以统御万邦,有逾丰镐。次年即吴元年,始召天下贤士制礼作乐,于礼部下设立教坊参与其中。永乐十九年明成祖迁鼎于燕,迁都前一年诏天下曰:“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缵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国,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做古制,狥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明太宗实录》:卷23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微卷影印,1966年版,第2235页。但迁都后相当一段时间,朝廷仍举棋不定,并未明确都城即在北京,洪熙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仁宗欲还都南京,诏令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恢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都城之名又冠于南京。*《明仁宗实录》:卷8下,1966年版,第272页。直到正统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英宗才又定都北京,“改给两京文武衙门印,先是北京诸衙门皆冠以“行在”字,至是以宫殿成始去之,而于南京诸衙门增“南京”二字,遂悉改其印。”*《明英宗实录》:卷85,1966年版,第1696页。自此“南京”之名才正式确定,设立“南京”的原因正如闻人诠所言:“太宗迁鼎于燕,而宣皇犹以储君监国,迨至英圣始改顺天为京师,以应天为南都,台省并设,不改其旧,夫岂能忘惟艰之业哉。”*(明)闻人诠修,陈沂纂《南畿志序》,载于刘兆佑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三编第四辑,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7-8页。自明代设两京制度后,京师(即北京)、南京附近地区不设布政使司,各府、州直隶于朝廷,为畿辅,两京制度下的南京虽为陪都,仍然设有宗人府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故而礼部下的教坊司亦得以保留,正式改称为“南京教坊”,与京师教坊相对。
(一)南教坊之隶属
洪武建制,教坊与太常同属礼部,也即具体承应礼乐的教坊司在明代正式隶属礼部,如前所说,这实际是教坊司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教坊司隶属礼部,一应事务俱归礼部管理,相应的,后来的南教坊便隶属南京礼部,一应日常诸事都由南京礼部全权定夺。
首先,南教坊的官员由南京礼部任命。据《大明会典》记载:“凡南京教坊司官,及俳长、色长名缺,本部(南京礼部)查勘明白,咨礼部奏补。”*(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17,《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南京教坊官员有缺,即由南京礼部查勘,上奏以补充,可见南京礼部掌管南京教坊官员的任命权。
其次,南京礼部通过对乐籍管理,严格控制了南京教坊乐人。乐人入院造籍需南京礼部收查,而造籍的主要目的除了便利管理以外,便是收税。对造籍收税之事,《大明会典》有详细记载:
每至年终,南京教坊司须将六院乐户男妇户口,各造册送部,差人类送礼部收查。*(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17,《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1册,第179页。
凡南京教坊司,各该事因,随即具报本科(南京礼部),每月仍具甘结。*(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13,《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2册,第542页。
明代官方规定乐人需造籍入册,南京教坊司须将六院乐户户口编册,送与礼部查收。而造籍的作用,便是报丁口以纳赋税。明人谢肇淛曾言:“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明)谢肇淛:《五杂组》卷8,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5-226页。除此之外南教坊还应每月甘结。“甘结”即指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
而南教坊的乐人出籍亦由礼部管辖。明代乐人想要脱籍是十分困难的事,《广志绎》曾言:
旧院有礼部篆籍,国初传流至今,方、练诸属入者皆绝无存,独黄公子澄有二三人,李仪制三才核而放之。院内俗不肯诣官,亦不易脱籍。今日某妓以事诣官,明日门前车马无一至者,虽破家必凂人为之居间,裘马子弟娶一妓,各官司积蠹共窘吓之,非数百金亦不能脱。*(明)王士性著,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页。
该段记载首先说明脱籍之事不易,且裘马子弟也不能违籍娶妓,因为这样会招致官方处罚,非数百金不能脱。同时该段材料亦表明,旧院乐人的簿籍在礼部管辖,当乐籍中人落籍归良,则需要礼部官员核查。材料中办理黄子澄亲属脱籍事务的“李仪制”即是礼部官员,为礼部下设四部之一仪制司的主管,据《大明会典》卷二载:“国初设(礼部)子部四,曰仪部、祠部、主客部、膳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洪武二十九年,改四部为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改首领官主事为司官司各一员。”*(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89册,第62页。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年间,在张公亮为董小宛、冒辟疆所作传中,记录了冒辟疆为身在乐籍之中的董小宛赎身,是“移书与门生张祠部为之落籍”*(明)张明弼:《冒姬董小婉传》,张潮辑《虞初新志》卷3,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第39-47页。,乃由礼部祠祭司之主管管理,这一制度的变化虽原因不明,但南教坊的乐人出籍管理权始终未离礼部。
再者,国家对乐籍中人的婚姻、服制、日常行为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南京教坊的日常,例如乐人生活、播调承应、乐器修造之事皆由南京礼部管辖:
凡供应乐器,遇有毁坏,本司申礼部题请,咨工部造办其弦线等料。南京教坊司三年一解,南京礼部咨礼部验给。*(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04,《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1册,第73页。
相应的,南教坊乐人若不服拘唤,或违反法令,礼部有权发落,对于违规僭越的行为惩治亦由南京礼部裁定。明代法律就曾明确规定:
教坊司官俳精选乐工演习听用,若乐工投托势要,挟制官俳,及抗拒不服拘唤者,听申礼部送问,就于本司门首,枷号一个月发落。若官俳狥私听嘱,放富差贫,纵容四外逃躲者,参究治罪,革去职役。*(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61,《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1册,第699页。
这些规定应该同时也适用于京师、南京及各王府之教坊司系统。而且据《闻雁斋笔谈》记载,南京礼部确实要处理教坊乐工的讼事:
马湘兰名噪一时,有举人请见,湘兰拒之,后授留都礼部主事。适有讼湘兰者,湘兰来见,主事怒曰:“人言马湘兰,徒虚名耳。”湘兰曰:“惟其有昔日之虚名,所以有今日之实祸。”主事笑而释之。*(明)王初:《奁史》,《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52册,第492页。
材料显示,当时名噪一时的南教坊女妓马湘兰遭讼,正是经由当时钦慕她的南京礼部尚书维护,才得以释放。
但到万历时期,由于南都官员严重缺乏,礼部之事竟由他部尚书兼管,甚至一部尚书兼管数部事务。据孙居相于万历三十年十月上《请补南都大臣疏》所载:
迩年以来,嗜好少偏,登用弗广,以猜疑成壅滞,以壅滞成废格。在皇上方谓慎于用人,在诸臣亦且澹于用世。或缺而不补,或补而不来,或来而辄去。有一署缺至数官者,有一官缺至数年者。凡官皆然,大臣尤甚,两京皆然,南京尤甚。以南京大臣之缺,而历数之:如吏部缺矣,总督仓场缺矣,礼部缺矣,兵部缺矣,工部缺矣,都察院掌院缺矣,通政使缺矣,大理寺正卿缺矣。即其间有一、二已点已任者,又屡辞未至,久归未旋矣。……优游家园者,尚抵任之无期,迁延不补者又悬缺而废事,徒使一户部尚书张孟男也,既管本部矣,又管仓场矣,又管吏部、礼部矣。一刑部侍郎王基也,既官本部矣,又管兵部、工部矣。一操江佥都御史耿定力也,既管操江矣,又管都察院矣、大理寺矣。夫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圣明之朝原不乏士。今乃使一官而兼数官,一人而摄数篆。纵使诸臣之才力固足以胜之,然事非专制,官属代庖能保人心之不玩,政事之不弛乎?*(明)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67册,第516-517页。
由此可知,由于万历皇帝长期废政,在上者不肯用人,在下者也便淡于用世,以至于两京官署往往缺员,又以南京最为严重。当时南京礼部之事一直都由户部尚书张孟男兼管,这个户部尚书兼管礼部之外,又管吏部、仓场,所谓“一官而兼数官,一人而摄数篆”;如此,礼部暨整个南京官署实际已经不能保障政事的有效处理。也就是说,官方对南教坊乐工的管理基本已处于半瘫痪状态,南教坊之事,不过向礼部报备而已,这方有了晚明教坊乐工的种种脱籍、僭越、不法行为,也方有了四方音声在南京的大兴。前章所说,在任官员优游园林,终日啸歌,也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南教坊也因此成为文人与乐工往来考音,从复古到新变,南北雅俗交融最为剧烈的场域。
(二)南教坊之乐官
《明史·乐志》载:“吴元年……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明史》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00页。可知明太祖初定南京,草创教坊司时,教坊司的官制为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组成。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职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勋阶之升转、俸禄之损益,历年兹久,屡有不同,无以示成宪于后世,乃命儒臣复位其品阶、勋禄之制,以示天下。”*《明太祖实录》卷22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微卷影印1966年版,第3256页。其公布的百司官职中,教坊司由奉銮、左右韶舞、左右司乐组成。另据《明史·职官三》云:“教坊司奉銮一人正九品,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并从九品,掌乐舞承应。”*《明史》卷74,第1818页。可见自洪武二十五年后,明代教坊司乐官系统大致确定,奉銮、左右韶舞、左右司乐组成了北京教坊司的乐官体系。改和声郎为奉銮的原因不可考,但奉銮在古代是侍奉銮舆的意思,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都有奉銮肃卫这一机构,属于皇帝护卫,唐代有拱宸奉銮军,亦属于皇帝内侍护卫军,至明代时奉銮才开始用于乐官系统中。
而南京教坊司所设官员只有“右韶舞一员,左右司乐各一员”*(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78页。,可见南教坊并未设奉銮,最高官员只是韶舞、司乐。虽然明代之奉銮相较元代之和声郎,其品秩有所降低,但在具体的宴乐仪式中,奉銮承担的职责为举麾、唱盏等,实际引导了整个仪式的乐舞流程,责任重大。南教坊不设奉銮,即有意区别于京师教坊司。
南京教坊设有右韶舞一员,左右司乐各一员,是最高官员。与京师教坊司相比,南京教坊少左韶舞一名。韶舞与司乐都是明代新设立之乐官,韶舞原本即是舜时乐舞名,从其命名来看当是负责舞事之职,但据文献所载其职司似乎并不仅及舞事*在具体的乐舞承应中,其职名亦各有不同,且人数似不止二人,确知的韶舞职名有“侍班韶舞”与“领乐韶舞”,详见《大明会典》卷104。;司乐一官疑衍自周朝的音乐机构——大司乐,韶舞与司乐的职责大约皆作为教坊司之副官分管具体事务。
南京教坊还设有俳长、色长数名,与京师教坊同。《大明会典》载“凡南京教坊司官及俳长色长名缺,本部查勘明白,咨礼部奏补”*(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17,《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179页。,又邓之诚在南京古物保存所曾看见万历辛亥教坊司题名碑记,上有俳长、色长、衣巾教师、乐工等称谓*邓之诚:《骨董琐记》卷5,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这些都是为南京教坊司的下层管理者。
二、教坊六院的衰落与旧院的兴变
南教坊(司)以来,与之相辅的,又有乐院与酒楼——前者为六院,主要为供教坊乐户居住与接客的场所,又以旧院最著;后者为官酒楼,为教坊乐户往来承应的场所,当时主要是南市楼。乐院与酒楼早在洪武时期便已设立,数百来兴衰异变,却也一直延续到明末,成为我们透视明代乐事沧桑变化的重要风景。
(一)“六院”
“六院”本为居住乐户而设,这一词最早出现于弘治十年所修《大明会典》中:“(南京)教坊司将六院乐户男妇户口,各造册送部,差人送礼部收查”*(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17,《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179页。,修于天启元年的《南京都察院志》又有更明确的解释,“六院:旧院、和宁院、陡门院,会同院,南城之南院,西城之西院,以上六院太祖高皇帝设立,贬罚为乐户娼贱,设教坊司奉銮等官统辖”*(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1,明天启刻本。。但令人疑惑的是,查阅明初文献,只见太祖设立富乐院,而未见六院之痕迹,《南京督察院志》所言“太祖高皇帝设立”便值得思考,在此不妨暂存这一疑问,首先详细考辨六院下设各院的情况。
六院地址具体设于何处并未见明确记载,惟正德间陈沂所撰《金陵古今图考》中略及一二。陈沂述及陡门院在斗门桥(又称陡门桥)附近,和宁院在升平桥以北*(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另据陈沂所作《金陵古今图考》之《国朝都城图考》所示,西院在西城外石城门与三山门间,而其他三院并未提及。
陡门院之所以在陡门桥附件,可能因为斗门桥的特殊地理位置:
《南京都察院志》:“陡门桥、体字东桥,马头渡船系民间私渡,南通常平仓,北接陡门桥,往来稠密。”*(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1,明天启刻本。
《客座赘语》:“南都大市为人货所集者,亦不过数处。而最伙为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而已,其名曰‘菓子行’。它若大中桥、北门桥、三牌楼等处,亦称大市集,然不过鱼肉、蔬菜之类。”*(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版,第21页。
可见于水路而言,陡门桥南通常平仓,这一段水道乃民间私渡的稠密地段;于陆上而言,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的“菓子行”则是人货集中的“大市”。明政府在此地设置乐院,招待四方来客,不难理解。
会同院,考其命名,当与会同馆有关。洪武时,于应天府设立会同馆,以供四方夷使接引送别,都有宴饮。据《明会典》载:
旧设南北两会同馆,接待番夷使客。遇有各处贡夷到京,主客司员外郎主事轮赴会同馆,点视方物,讥防出入,贡夷去复,回部视事。……凡贡使至馆,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四夷归化人员,及朝贡使客,初至会同馆,主客部官随即到,彼点视正,从定其髙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仍加抚绥,使知朝廷恩泽。……一管待量其来人重轻,合与茶饭者,定拟食品卓数,札付膳部,造办主客部官一员,或主席,或分左右,随其髙下序坐,以礼管待,仍令教坊司供应。*(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90,《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2册,第112页。
于会同馆外,又别设会同院,大约是专门为便利承应会同馆宴事而设的。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陡门院与会同院似乎在英宗以后的南教坊系统中影响并不大。
而和宁院因何而立,不可稽考,但至万历十三年以后和宁院仍然存在,潘之恒《亘史外纪》卷六曾提及:
余友张季黄每为余言:“和宁院之康生也,是虽最少,而姿首耀目,精彩摄人,曲中之艳,无出其右者。”……(郝公琰)问年何字,曰:“蘂生”,何行,曰“四而班小”,见几岁,曰“癸卯初见,年十二,能擅新声,登场令坐客尽废。丙午再见,为破瓜时,艳发长干,倾六院。”*(明)潘之恒:《亘史外纪》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9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71页。
后来郑明选《为循例举刺存恤官员以肃军政事疏》在谈及讼事时,又同时提到“和宁院”与“旧院”同存:
南京武德卫右佥书指挥使徐应文,贪淫无似,刁恶有声,管屯而私验户田,每户索银一钱。当被刘荫爵之讦告,旧案可查。收租而多求,常例每甲科银五钱,时被辛坚等挟制,人言足据。与同寅吕文兆、吴日强互骂于公堂,体面安在?招识字周询妻王氏,共饮于私家,廉耻奚存?运江西则嫖李三,屯六合则宿金九,在在滛风;入旧院则结张六,在和宁则交马五,处处狂荡。*(明)郑明选:《郑侯升集》卷26,《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464页。
据清陈田《明诗纪事》所记:“明选,字侯升,归安人。万历己丑进士,除安仁知县,擢南刑科给事中”*(清)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可知郑明选为万历十七年进士,而《郑侯升集》现存最早为明万历三十一年郑文震刻本,虽不能确定此版是否为首刻(可能性极大),但至少可以将这封政事疏确定在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三十一年间,而此时和宁院尚存。
另外,南院与西院沿革时间也比较长。永乐年间,建文帝时黄子澄的四个女儿没籍后,即在南京西院,事载《建文朝野获编》:
黄子澄,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少年有文采,伴读东宫。建文时为太常寺卿,建议削诸王之权。大见信用,已而坐赤族,妻入浣衣局,生子名舜,家儿郑氏养为子,冒姓郑,今尚在。生女四,见在南京西院。*(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11,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另正德时有名妓赵丽华,“字如燕,小字宝英,南院妓,自称昭华殿中人,如燕父锐以善歌乐府奉康陵。如燕年十五籍隶教坊,能缀小词,被入弦索。”*(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3页。另据沈德符记载,隆庆中云间何元朗还曾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0页。,到万历年间十年左右,顾起元又称:
余犹及闻教坊司中在万历十年前,房屋盛丽,连街接弄,几无虩地。长桥烟水,清泚湾环,碧杨红药,参差映带,最为歌舞胜处。时南院尚有十余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门待客。其后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为茂草,旧院房屋半行拆毁,近闻自葛祠部将回光寺改置后益非其故矣。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俯仰不过二十余年间耳,淫房衰止,此是维风者所深幸,然亦可为民间财力虚羸之一验也。*(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7,第201页。
可见西院、南院在南教坊的历史上沿革较久,与城中旧院一起促进了为明代南都伎乐的发达。
(二)旧院
城中四院中最复杂、最重要的要数旧院。洪武建制,明确提及教坊司外,别设富乐院以处乐工,而后来记载,说及南教坊只说六院,那么,其间沿革已难以考清。值得留意的是,旧院与富乐院之间似乎尚有些踪迹可寻。据刘辰《国初事迹》载:
朱元璋初立富乐院于乾道桥,专令礼房典吏王廸管领,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后来因失火,复移武定桥等处。同时,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云云”。*(明)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存目丛书》第4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2页。
富乐院初设时间已不可考,失火后重建当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前。因为这一年,朱元璋敕修成书的《洪武京城图志》上,便标有两处富乐院:一在武定桥东南旧鹿苑寺基,一在聚宝门外东街,都已不是乾道桥处。可见,《图志》上的富乐院已经是重建以后的富乐院了。旧院与富乐院,皆在武定桥附近,然而,前者是否即是富乐院演变过来,并因此而规模最盛呢?其实,两家地址细看来令人有些疑惑。陈沂《金陵古今图考》说旧院在武定桥东北*(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而《洪武京城图志》标富乐院却在武定桥东南,后来《板桥杂记》也道:“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清)余怀:《板桥杂记》,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据今天南京遗存的钞库街与武定桥可知,《板桥杂记》所言旧院亦在武定桥东南。
旧院是否是富乐院后来向北扩张的结果,已不可考,但旧院在武定桥畔应无疑问。关于旧院地理,潘之恒《亘史》记录更详:“旧院有后门街、纱帽街、鸡鸢巷、长板桥、道堂街、旧院后门、旧院大街、厂儿街、旧院红庙,石桥街”*(明)潘之恒:《亘史外纪》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93册,第523页。,“旧院有琵琶巷”*(明)潘之恒:《亘史外纪》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93册,第565页。,可见旧院包含多条街巷,恐怕其规模远在其他五院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以后的文献中,“旧院”往往便是南京教坊代称:
《金陵梵刹志》:“小刹回光寺古刹在都城南隅,中城地。东北去所领鹫峰寺一里。梁天监间创,萧子云飞白大书寺额,名萧帝寺。唐保大中,改法光寺。宋太和中,改鹿苑寺。一云鹫峰是其址,今互存之。国朝永乐间,有回光大士自西域至,重建,改今额。寺在教坊内,道所必由,今为另辟他途。复有孔雀、道堂、宝塔诸庵,悉移徙之,而净秽于此始别云。”*(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2,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页。
《肇域志》卷四:“回光寺在旧院内,旧院国设朝教坊于此。”*(清)顾炎武:《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尺木楼诗集》卷三:“东花园在金陵闸东,明旧院,地有桥曰月明,相传为名妓马湘兰望月处,自明末乱后教坊无存,今比屋多禅院。”*(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2,第419页。
首先需要交代的是,洪武初设立教坊司于宫城外西南方向,但据陈乃勋、杜福堃编著的《新京备乘》考辨:“据考教坊司,初在西华门外,明都北迁,至嘉靖间,始移于东花园旧演乐厅,旧院在东花园之右。”*陈乃勋辑述,杜福堃编纂,顾金亮、陈西民校注:《新京备乘》,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165页。且不说此材料本身的孤证性质,明后期教坊司的移动还需考察外,就算教坊司移到东花园,但旧院与东花院也并非一地,而上引《金陵梵刹志》所言“寺在教坊内”,而《肇域志》又言“回光寺在旧院内”,都表达了旧院与南京教坊的是一地,但其实只是旧院成为南京教坊的统称而已。这可能是明中后期以来,旧院因其繁盛景况,故而成为南京教坊的代称。《板桥杂记》曾记载“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所谓上厅行首,原指官妓承应官府,参拜或歌舞,以姿艺最出色的排在行列最前面,后为名妓的通称,可知旧院以名妓著称。其时,金陵名妓,如马湘兰、傅灵修等,许多都是旧院中人。至此我们可以知道“旧院”可能有两层意义:一是具体的院名,在武定桥;一是南京教坊的统称。
但旧院的颓败晚明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时间当在万历二十年以后:
余犹及闻教坊司中在万历十年前,房屋盛丽,连街接弄,几无虩地。……其后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为茂草,旧院房屋半行拆毁,近闻自葛祠部将回光寺改置后益非其故矣。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俯仰不过二十余年间耳,淫房衰止,此是维风者所深幸,然亦可为民间财力虚羸之一验也。*(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7,第201页。
而此次改造回光寺是旧院愈发荒废的契机之一,明人南京本地人易震吉《秋佳轩诗余》之《旧院长桥》亦记载:
教坊司中大街回光寺之东,陂水沦涟,垂杨掩映,桥联亘百余步,红板绿波,光影荡漾,为勾阑游赏佳境,近年祠部将回光寺以东分置院外,此桥遂断歌舞之迹矣。*(明)易震吉:《秋佳轩诗余》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723册,第514页。
而据《金陵梵刹志》载:
国朝永乐间有回光大士自西域至,重建改今额,寺在教坊内,道所必由,今为另辟他涂,复有孔雀道堂,宝塔诸庵,悉移徙之,而净秽于此始别云。*(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2,第420页。
该书刊刻时间在万历三十五年前,至此我们可初步断定旧院的荒废时间当在万历二十年至三十五年间。可知旧院在万历中后期已经被拆改,被回光寺占用。到清代时“旧院则废圃数十亩而已。中山东花园仅存其名故址不可复睹,回光、鹫峰两寺亦金碧剥落香火阙如。至长板桥,尤冺没无迹询之。”*(清)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版,第63页。
(三)南市楼
洪武时,官方于南京建酒楼十六,以蓄往来官妓,宴饮四方宾客,朱元璋并数次设宴与臣同乐。据《洪武京城图志》载,计南市、北市、叫佛*《洪武京城图志》之《楼馆图》未标明叫佛楼,但图下文字中有所记载(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52页)。、来宾、重译、鼓腹、讴歌、鹤鸣、醉仙、集贤、乐民、梅妍、翠柳、轻烟、淡粉、江东。十六楼之设与明初官妓制度直接挂钩,官妓制度的衰落,十六楼也逐渐失去原有的繁盛而日益凋敝。
明后期,十六楼仅存南市楼。周晖的《二续金陵琐事》(初刻于万历三十八年后不久)中详细记载十六楼基地,于“南市楼”后注云:“在城内斗门桥东北,此楼独存。”*(明)周晖:《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同时期的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卷六:
今独南市楼存,而北市在乾道桥东北,似今之猪市。疑刘辰《国初事迹》所记富乐院即此地也。*(明)顾起元:《客座赘语》,第175页。
周晖又于《续金陵琐事》(初刻于万历三十八年)“宴南市楼诗”条下注:“今此楼(南市楼)虽存,不过屠沽市儿之游乐而已。”*(明)周晖:《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第196页可见至迟到万历晚期,十六楼皆废,仅存南市楼一座,且已不复初建时景象,成为“屠沽市儿”游乐地,据《板桥杂记》序言载:
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清)余怀:《板桥杂记序》,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可知南市楼所居住的都是轻贱的妓女,故而还出现了此地妓女搬到名声好的旧院的情况,“马如玉,字楚屿,本张姓,家金陵南市楼,徙居旧院。”*(清)厉鹗:《玉台书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值得一提的是,万历三十四到三十五年间成书的《万历野获编》亦记载“今南市楼虽在六院之一,而价在下中”*(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建酒楼”条,第900页。,指出南市楼乃六院之一,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晚明六院系统与十六楼系统混淆的情况。
南市楼至清代康熙年间为陈鹏年改建讲堂,《养默山房诗稿》记载:
十六楼明初建以处官妓,为游人蕙息之所。曰南市、北市、来宾、重译、集贤、乐民、鹤鸣、醉仙、轻烟、淡粉、柳翠、梅妍、石城、讴歌、清江、鼓腹,后皆废,惟南市楼在陡门桥东北。康熙中太守陈鹏年改建讲堂。*(清)谢元淮:《养默山房诗稿》卷2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45页。
因为南市楼的“狭邪”性质,陈鹏年还因为在此被治罪,《明史》记载:
陈鹏年,字沧洲,湖广湘潭人。康熙三十年进士。……寻擢江宁知府。四十四年,……鹏年尝就南市楼故址建乡约讲堂,月朔宣讲圣谕,并为之榜曰“天语丁宁”。南市楼者故狭邪地也,因坐以大不敬,论大辟。”*(清)赵尔巽:《清史稿》卷277,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094页。
可知入清以后,南市楼别作他用,大概康熙后,南市楼便弃而不用了。清人郑澍若《虞初续志》卷十一记载:“明初于聚宝、石城、西关诸处,建轻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楼,……今诸楼皆废,遗址无存。”或可作为证明。
(四)珠市
明代材料虽记载“六院”,可后来与旧院并称的,只是“珠(猪)市”、“南市”,《板桥杂记》序曰: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清)余怀:《板桥杂记序》,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南市楼作为十六楼之唯一遗存,已于上文详细考辨,现著重考辨与旧院并称的珠市。
关于珠市,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记载:
十四楼则知相沿已久,今独南市楼存,而北市在乾道桥东北,似今之猪市,疑刘辰《国初事迹》所记富乐院即此地也。”
顾起元认为珠(猪)市楼可能是之前的北市楼,而北市楼所处地点是富乐院的遗址。但值得推敲的是珠市在内桥,非乾道桥,两桥距离并不近(参考前图),所以顾起元的说法并不准确。
珠市地处内桥周围当是无误,据余怀《板桥杂记》中卷丽品载:
珠市在内桥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以余所见王月诸姬,幷着迷香神鶏之胜,又何羡红红举举之名乎,恐遂湮没无闻,使媚骨芳魂与草木同腐,故附出于卷尾以备金陵轶史云。*(清)余怀:《板桥杂记》,第21页。清人胡承珙《求是堂诗集》卷十五赏春集,亦记载:“白门与王微波姊妹皆居珠市,近内桥。”*(清)胡承珙:《求是堂诗集》,转自龚斌,范少琳编《秦淮文学志》下册,黄山:黄山书社2013版,第1235页。清人余宾硕撰《金陵览古》给出更详细的地址:“明朝中、后期,金陵曲中以旧院为最,余则珠市(即猪市,一名石城坊,清时称珠宝廊,地在今内桥西至建邺路口)。”*(清)余宾硕:《金陵览古》,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版,第223页。可知珠市在内桥周围当无误。
三、南教坊制度的衰落
教坊司因承应国家朝会、大小宴享等乐舞,得隶礼部祠司,南教坊作为官方乐署的一种,本为礼乐所设,承担朝会宴享乐舞,所谓“祭祀用雅乐,太常领之;宴享朝会兼用俗乐,领于伶人。奉銮、韶舞、俳长、色长、歌工、乐工、舞人,各专其业而籍用之。”*(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88,《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正如前文所述,明政府曾对金陵教坊有严格的管理,南京礼部通过对乐籍的管理,严格控制南京教坊司乐人的入籍、出籍、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自但英宗正统六年立南京以来,南教坊制度本身则愈发松动,至明末呈崩溃之势。
(一)正德朝之前南教坊制度的松动
自明中期始,南教坊乐籍制度渐趋松弛,买良家入籍愈发普遍,《大明会典》记载:
(弘治九年)又令私买私卖良家子女及媒合人等,俱于三院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照依律例发落,该管色长并邻佑人等不首告者,与同罪。官俳查提从重问拟。南京及各王府同。*(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04,《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1册,第73页。
弘治九年不仅加重了对参与买卖良人入乐户人惩戒,且特标注南京及各王府同,这说明了弘治年间买良人乐籍之事已渐趋严重,且此时南京教坊与王府乐籍的松动已为政府关注。
明初政府对乐户的妻妾等也有规定,《板桥杂记》曾言“乐户有妻有妾,防闲最严,谨守贞洁,不与人客交言。人客欲强见之,一揖之外,翻身入帘也。”*(清)余怀:《板桥杂记》下,第27页。弘治朝南京户部尚书郑纪便上疏请朝廷:
着令礼部查其名籍,开豁从良,男子仍充乐工,妻女不许接客,则民俗以正,风俗以敦,而礼乐之道实不外是也。*(明)郑纪:《东园别集》卷3,《四库全书丛书》集部1249册,台北:台湾印书馆1985年版,第751-752页。
从郑纪的疏请,我们可以看出弘治朝乐工妻女已经出现了接客的情况,早已不是“防闲最严”的状况。
而且在正德朝之前,南教坊乐人已经受到外来乐人的影响。据陈铎散曲【北吕朝天子】“川戏”、套数【北般涉调耍孩儿】“嘲川戏”、“嘲南戏”记载,明中叶外来路岐人在南京市井、富士豪民中都颇受欢迎,以致教坊乐人也争不过他们。*谢伯阳:《全明散曲》一,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42、617、619页。据李舜华《陈铎生平与家世发微》考辨,陈铎约生于正统七年至十三年间,卒于正德二年,其描述的路歧乐人的情况,乃正德以前之事,可以说正德以前,冲州撞府的路歧乐人渐盛,并影响到南教坊。
(二)正德至万历初年间南教坊制度渐趋无序
南教坊在武宗朝大盛,明人汪漠阳曾言“金陵教坊司当肃宗皇帝末年为全盛,一时名姝才技绝伦者不下十余”*(明)潘之恒:《亘史》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33页。,李舜华亦提出“武宗南巡直接促进了南教坊伎乐的发展”*李舜华:《南教坊、武宗南巡与金陵士风的渐变》,《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但与南教坊伎乐发达相佐的是,正德至万历年间南教坊便处于无序状态。首先,买良人入籍之事愈发严重,至嘉靖十五年以后,身为南京礼部尚书的霍韬在南都严惩败坏风化之事,其中便有罪乐户之买良人,可见此时南教坊以良人充乐籍之事已十分严重。*(明)焦竑:《玉堂丛语》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页。
而此时政府对乐人日常生活的管理也已不再严格。嘉靖三年,因言事贬官南部的何孟春曾记载此时对南都乐人服饰上不和规矩的情况: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员巾服之制。……教坊司伶人,制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女妓冠褙,不许与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诸浅淡颜色,其大红、青、黄色悉禁勿用,带以蓝绢布为之。女妓无带,所以别良贱也。伶人妇不许戴冠、着褙子;乐工非承应日,出外不许穿靴。所以贱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明)何孟春:《馀冬序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3页。
从中可见教坊司管理十分松弛,不别良贱。《板桥杂记》更记载旧院李大娘,“所居台榭庭室,极其华丽,侍儿曳罗縠者十余人,置酒高会。”*(清)余怀:《板桥杂记》,第14-15页。,以伶人的身份享受如此富贵华丽,毋庸置疑是有所僭越的。
此时南教坊更多的是服务留在南都的大臣贵戚,至迟到嘉靖年间,南教坊国家乐署身份已被破坏,何良俊撰《弟南京礼部祠祭郎中大壑何君行状》对此曾有过记载:
教坊乐工虽至贱隶,然朝廷所设本以供祭祀朝会,其他大臣燕非赐教坊乐,不得擅此役,此祖宗旧制也。南京则旧制凡大臣燕会以手本至,祠祭司拨送,今则诸司擅自差役,而勾摄乐工之使旁午于道。君曰:“凡是,是无祠祭司也。夫天下至大,朝廷所以能连属而纲维之者,徒以法制在耳。余蹇劣无状,于政事无所裨益,但欲坚守祖宗之法,持此以报朝庭。苟必圜转俯仰曲法以保名位,余不能复为祠祭郎中矣。”*(明)何良俊:《何翰林集》卷25,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201页。
此为何良俊为其弟——南京礼部祠祭郎中何良傅所作行状,嘉靖时祠祭郎中所面对的情况是:诸功臣之家朵颐于此,素以燕乐馈赠,能役使部寺诸大臣,祠祭官不与主张,即公肆陵侮,加以骂詈,官府的管理虚废至此,南教坊此时俨然已变成了南京王公大臣的私乐,余怀《板桥杂记》曾评价: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清)余怀:《板桥杂记》,第9页。
无论宗室王孙、乌衣子弟,还是湖海宾游,每开筵宴,就一定要命南教坊乐籍中人行酒纠觞。
此段时间内南教坊甚至成为了盗贼的藏身之处,而官方则对此毫无有效措施。万历六年张友舜上《严禁令弭盗贼疏》言:
再照南京地方广阔,居民麟列,啇贾蝐集,寇贼奸宄,本难悉办。故四方劫掠者亦潜入京,假装贵游豪杰宿妇饮酒,一入乐院重门委巷,穹室高楼任其自乐。本房乐工只图厚利,兵番缉捕,动辄拒阻,即便拏获,一时证不明,事过之后,又告称吓诈财物,以致不敢轻动。*(明)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六,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乐工只图厚礼,完全不配合官兵的缉捕工作,甚至拒阻,事后还告称“吓诈财物”,南教坊乐人不仅不服从官方之制度,甚至成为盗贼犯人的帮凶。
(三)明末南教坊制度崩溃
正因为正德至万历初年间,南教坊制度渐趋无序,故而南教坊在晚明(万历朝后期始)呈现出不可阻挡的颓势。
万历后期南教坊逃籍之事变得十分频繁,万历中旧院姜实竹便从里士方林宗“举空棺而逃籍,居荆州数年,乃归里中*(明)潘之恒:《亘史》,《四库存目丛书》第19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26页。。据钱士升《赐余堂集》记载万历后期的状况:“独教坊司四院萧条已甚,逃移未复,而岁办乐器,各衙门差役繁苦如故,夫此独非皇上赤子,而忍其流亡失所也”*(明)钱士升:《赐余堂集》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至明末,脱籍之事亦大幅增多。如琵琶顿老孙女顿文“生于乱世,顿老赖以存活,不能早脱乐籍”*(清)余怀:《板桥杂记》,第19页。,言语之间有不得已才不脱籍之意,反过来看,脱除乐籍亦非难事。崇祯年间,在张公亮为董小宛、冒辟疆所作传中,记录了冒辟疆为身在乐籍之中的董小宛赎身,虽言“未易落籍”,后也仅仅是“移书与门生张祠部为之落籍”*(明)张明弼:《冒姬董小婉传》,张潮辑《虞初新志》卷三,第39-47页。,而晚明名妓嫁士人之事不胜枚举,许多发生在南都,才子佳人,成为美谈,而脱籍已不算难事很可能是这一风气隐含的条件。《板桥杂记》所言:
曲中女郎,多亲生之母,故怜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连,不计钱钞;其伧父大贾,拒绝弗与通,亦不怒也。从良落籍,属于祠部,亲母则所费不多,假母则勒索高价。谚所谓“娘儿爱俏,鸨儿爱钞”者,盖为假母言之也。*(清)余怀:《板桥杂记》,第11页
从良落籍,虽然属于祠部,但“亲母所费不多,假母勒索高价”,可见就官方制度而言,对于乐籍中人落籍并不十分限制。
旧院乐人四处流动也渐次普遍。明初乐籍私自流动,属于违律,而明后期则十分普遍:
马四娘以生平不识金阊为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来吴中,唱北西厢全本,其中有巧孙者,故马氏粗婢,貌奇丑而声遏云,于北词关捩窍妙处,备得眞传,为一时独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还曲中即病亡,诸妓星散,巧孙亦去为市妪,不理歌谱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第646-647页。
王桂容由旧院徙居淮扬,岁余矣。辛亥七月,既望程定于觞旅髯,于云中君仙丹载王姬为侑请髯字字曰月修见其婉弱甚易之,勿强以酒座上酒人,陈山甫与之角,不能胜,颓然矣。姬惺惺自若,未沾醉者。虽马鼌采以豪夸,乃不动声色,而能制人,则月修为酒圣矣。征其歌工不欲奏吴音,以金陵艳声度小调曲,其溜亮如飘云,漠上听飞仙,缥缈歌也,人之静好无闻,抑至此哉。*(明)潘之恒:《亘史》,《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9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68页
上述诸材料中,马湘兰由旧院去吴中为王穉登过七十大寿在万历三十三年,王桂由旧院迁居淮扬在万历三十九年左右,可见到万历后期,乐人的私自流动已经是十分频繁之事,而此时未见官方对此进行过特殊管理。
从晚明旧院诸姬的自由程度,亦可看出南教坊对于自身基本义务已不复履行。正德朝,选教坊司乐妓十人备供奉,宝奴为首,姿容瑰丽出众,数侍巾栉。武宗回銮,宝奴还旧籍,咸以贵人呼之。宝奴自供奉归后,即闭阁不出,尝叹曰:“婢子获执巾天子前,安得复为人役!”遂长斋诵佛,为道人装以老*(明)潘之恒:《亘史》,《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93册,第519页。。王宝奴因侍奉御前,才得以不为人役,而万历时旧院诸姬,自隐不待客的情况屡有发生,如苗姬“益自匿不求侵暴,移栖旧院,门常闲,未尝以艳招人”*(明)潘之恒:《亘史》,《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93册,第562页。。可见南京教坊乐伎,可自定服务与否,其官署的性质几近全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甚至记载万历末年,南教坊中存在满足男同性恋而存在的男妓:
至于习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竞以此道博游壻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尚有不深嗜者。*(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第622页。
据此可知,在万历时“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而南教坊中的名妓,为了博得游婿宠爱,豢养男妓,而女伴甚至还戏谑为佳事。
另据《南京督察院志》记载,此一时期南京城外来私营娼妇颇多:
内桥、淮清桥路连三山街之鹰贼抢,砂朱巷之客寓多奸,……三山门里之茶府湾及水关地方多外来娼妇,饭店窝歇流来,强盗诸如此类之奸宄出没,真莫可方物者,惟有编葺保甲,严督稽核庶奸宄潜踪。*(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1,明天启刻本。
《南京督察院志》记载的乃为万历末年至崇祯初年的情况,此时外来乐人、娼妇,即为私娼十分猖獗,“所谓私字,只在于不设门户上,所谓不设门户,即不注册在官,其意义便是不受官府的管理,最重要的恐怕是不纳脂粉税”*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198页。。
余 论
因为明代的两京制度,作为留都的南京在有明一代政治格局的地位素来微妙,有着相对自由的空间,亦往往为士大夫舆论的中心。同样,位居留都的南教坊,自正统以来,亦在明代乐制与演剧中扮演着颇为微妙的关系;成弘以来,南教坊伎乐渐趋繁盛,在新声迭起的同时,复古乐之声也渐次兴起,当时南京陈铎、徐霖辈,吴中祝枝山、唐伯虎等人,往来南都,纷纷以考音定律相鼓吹。正德时期,一方面因了武宗的好乐与荒嬉,官方乐制渐趋崩塌;另一方面,武宗南巡却又成为一个新的契机,进一步促使了南教坊伎乐的繁盛。或许,也正是对南教坊伎乐大兴的一种反动,复古乐思潮也以南都为核心,而广为流播,一时士大夫礼乐自为,汲汲于复古复雅,只是这一议复古乐最终成了一种实验,一时风会,也一时云散。万历后期以来,南教坊制度日趋无序,而当时曲坛,古乐与今乐、北音与南音的复杂交会,更成为明末最特殊的一道风景。
[责任编辑]黎国韬
刘薇(1988-),女,江苏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李舜华(1971-),女,江西广昌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200241)
I207.3
A
1674-0890(2017)05-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