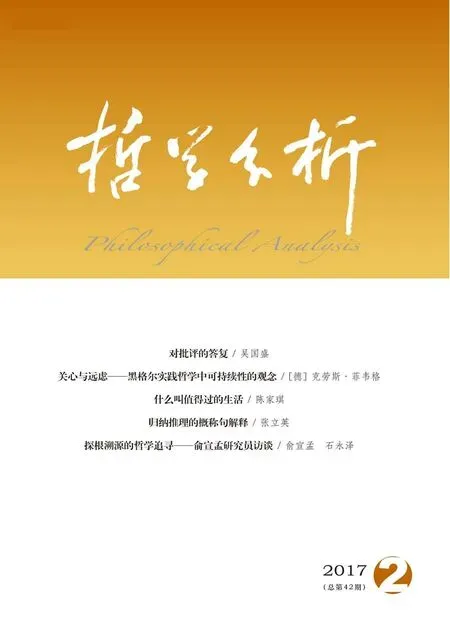汤一介与“中国诠释学”
——关于建构“中国诠释学”之我见
潘德荣

汤一介与“中国诠释学”
——关于建构“中国诠释学”之我见
潘德荣
一
汤一介先生为人儒雅敦厚,为学博大精深,有一代大儒之风范。我与汤一介先生接触虽不多,但在收到“汤一介研究会”约稿函后,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函表示愿意撰写一篇纪念性的文字。能以这种方式缅怀我所敬仰的学界前辈,是我的荣幸。
与汤先生的几次比较深入的交谈,主题都是“诠释学”(汤一介称之为“解释学”)。汤一介关注的重点是西方诠释学,他的话常常带有咨询的性质,希望对西方诠释学基本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而我的兴趣中心却转移到了中国的诠释传统。1987年,成中英先生应冯契先生之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开设系列讲座,我是学员之一。成先生的讲座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诠释学,我被这种新颖的诠释观念所吸引,此后的数十年,这一领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心。从上个世纪末起,学界开始反思如何借鉴西方诠释学的思想资源来完成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我自己也撰写了《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一文,从诠释方法论的角度梳理朱熹诠释思想的特征。尽管我尽量从“纯粹的”中国诠释传统出发来写这篇文章,文中没有一个外文词单词,也未出现一个西方诠释学家的名字,但是明眼的读者还是看出了该文的立论框架全然是西方诠释学,并将其戏称为“洋格义”之说。
在这种情况下,在与汤一介的谈话中我尤为关切中国诠释学的构建的问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后来我细细拜读了汤一介几篇关于建构中国诠释学的文章,感触颇深。他所做的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是一项从自我设问到自己探索答案的工作。汤一介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我注意到,出现在该文标题上的“中国的解释学”字样,在正文中未曾提及。在文章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今天,我们不必费心争论,应有的态度是传承前辈的成果,主动借鉴西方诠释学,以便我们对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某些可以利用的资源。最后,我必须再说一下,我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可以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不必再花时间在这个方面费力气了。”*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载《学人》1998年3月号。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汤一介先生在倡言创立新说时的谨慎与严谨,也可以看出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犹疑与彷徨。
在《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一文中,汤一介对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的看法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对于前引的那段文字,他写道:“现在我想,我的这个说法也许太消极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即使我们不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解释学来,至少经过我们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也是很有意义的,更何况这样做了之后总可以丰富西方解释学的内容吧!”*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两文都未就能否建立中国解释学做出肯定的判断,差异仅在于:倘若不能建立“中国解释学”,退而求其次的话,根据前文的说法,这便于我们今后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可以利用的资源;根据后文,我们对中国解经历史的梳理可以“丰富西方解释学”。正因为如此,我们进行中国解释学的研究是有其理论意义的。
汤一介之所以反复地极力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做出辩解,原因就在于他的提法受到了众多的质疑。我自己曾听到一些学界前辈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提法颇有微词,汤一介在《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汤一介:《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以下简称《三论》)一文中也做出了类似的说明。在香港召开的“经典与解释——中国解释学传统国际研讨会”上,好几位中外学者不同意汤先生的意见,赞同者只有一两个年轻学者。概括一下反对意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认为中国诠释学古已有之,何劳我们再“创建”?若有必要,也只是“重建”中国诠释学;另一类意见,认为诠释学是具有普遍性的,就像没有中国物理学、中国数学一样,也没有中国诠释学。
尽管汤一介在《三论》中对“解释”、“解释问题”与“解释学”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了作为“学”(理论体系)的“解释学”与“解释”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具有“理论与方法上的自觉”,他的辩解似乎并未被广泛接受,比如余敦康先生在几年后仍旧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汤一介说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还要你来建立?早就有了。中国的经典诠释学,从先秦就有了。这还要你建立吗?”*余敦康:《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进路》,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6月。
我们知道,汤一介倡言建构中国诠释学,意在呼吁更多的学者投入这一项研究,他这样写道:“……并无意由我来创建‘中国解释学’。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来考虑。”*汤一介:《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对汤先生说,学界对能否创建中国诠释学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既然您对建构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思考了这么久,这么深入,何不直接创建出来?或者至少提出一个纲要性的理论框架,以为入门之径。先生答道,以我的年纪来做这件事,已是力不从心了,我指望着你们来完成这一任务。其时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他说这番话时虽很淡然,但听者闻此言,心中不免有些酸楚。如今哲人已经驾鹤西去,吾后辈学人,唯将他的话当作嘱托与鞭策,勉力而为,方不负先生之期望。
二
我自己的理论思考,主要的用心、用力之处当然是西方诠释学。不过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诠释问题,撰有《诠释学的中国化研究述评》*潘德荣:《诠释学的中国化研究述评》,载《哲学动态》1993年第10期。和《文字与解释——训诂学与诠释学比较》*潘德荣:《文字与解释——训诂学与诠释学比较》,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2期。。但是必须承认,那时写这类文章我是没有底气的。原因很简单,我对中国的诠释传统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对于能否建立“中国诠释学”还心存疑虑。事实上,直到2014年,我的论著中基本上没有使用“中国诠释学”这一概念,而以“中国诠释传统”或“中国诠释思想”代之。在几处提到“中国诠释学”的地方,也只是采用了“如果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中国诠释学”等诸如此类的表达。
例(4)中,当A说由于海外需求强劲,我方决定扩大生产,B就立马夸赞太棒了,对方目光远大,这遵守了礼貌原则中的“赞誉准则”。对对方的赞美,也是给对方面子的表现,有利于维持双方良好的交际关系。
汤一介具有一种理论勇气,这是我很钦佩的。尽管在他的文章中,对于能否建构中国诠释学问题未给出正面的、确定的回答,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本文拟在汤一介所开启的诠释学方向上“接着说”。
在我看来,首要的问题是界定“中国诠释学”。质疑者认为中国诠释学古已有之。果真如此?这里涉及对“诠释学”一词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学”,是Hermeneutics或Hermeneutik的汉译。就其词源而言,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古代希腊就已经有了“诠释学”。现存的亚里士多德的《诠释篇》(PeriHermeneias,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本将其译为《解释篇》),其所述、所论者其实是语法学。因而,西方学者也从不将亚里士多德的《诠释篇》视为诠释学的著作。在西方的中世纪以及近代论著中,诠释《圣经》的著作被称为“解经学”(exegesis, Exegese),学者们有时也将其称为hermeneutic(hermeneutics的单数形式),但是直到18世纪末,它也只是作为神学的辅助性学科。据美国著名诠释学家帕尔默(R. Palmer)的观点,摆脱了教义学束缚的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学(hermeneutics),是由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所奠定的。*参见Palmer: Hermeneu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xi—xii。解经学与诠释学的区别在于:解经学的对象就是《圣经》,而诠释学指向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性文本;解经学预设了《圣经》的真理性,《圣经》乃上帝的话语,所谓经文原义与真理是等值的,而在诠释学中,对文本却根本没有做出这样的预设。
比较研究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方法,可通过对比较对象之异同的分析,找出问题之所在。在此,我们亦可以将西方诠释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为分析中国诠释传统的参照系。从词源上说,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根本没有“诠释学”一词,汤先生曾指出了一例类似的说法:“清初学者杭世骏说:‘诠释之学……语必溯原,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转引自《汤一介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页。这里“诠释之学”的“学”,乃是指学问、治学,而非“学科”,与作为学科的诠释学之“学”相去甚远。显然,在杭世骏的思考中,已有论及诠释的一般方法,诸如“语必溯原”、“事必数典”便是。这既是杭世骏自己的解经经验之心得,也是对千百年来解经实践的总结。毋庸置疑,中国有着悠久的解经传统和丰富的解经经验,其历史甚至可以从孔子编订六经算起,解经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这并不是诠释学,而是解经活动,是经学。据我所知,诠释学根本不诠释文本,而是探究我们的理解与解释依据,它关注的是下列问题:我们为何需要“诠释”?如何构建诠释的方法论及其本体论根据?进而言之,诠释学家不会论断某种解释是正确或错误的,而是旨在厘清为何会形成这种解释?几年前,我曾受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之邀,在该系做了一个诠释学讲座。当时我援引了一个解经实例,用以说明诠释学的某个原则。《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有“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语。按照旧有的理解,将“女子”解释为“女人”。但这种解释鄙视妇女,孔子作为“圣人”不当如此。所以将“女”释为“汝”(你),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只有你这样的人与小人难以相处”。或将“女子”解为“妾侍”,因其恃宠而矫而难养。另有人重新将这句话句读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通过这种句读之法,并将“惟”和“与”解释为语气词,终将一般意义上的“女子”排除在“难养”者之外。当场就有学者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列举这些解释毫无意义,此语的含义学界早有定论,何须枉费口舌。其实,我列举这些不同解释,并非想进一步判断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是符合孔子原意的。我的真正用意,是想说明何以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旧有的解释为何在现代被质疑,使得学者们劳神费心地去寻找新的解释?现代学者们试图获得新解的努力,其实是被我们的时代观念所推动的。质言之,我们的理解与解释始终被我们的时代观念所引导,我们的诠释活动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化解或缓和我们的时代观念与经文意义之间的冲突。孔子被视为圣人,若他的观念根本不见容于我们的伦理观念(比如在上述引文中所透露出来的鄙视妇女之意),我们就得放弃孔子;若我们根本不能放弃孔子之说,就必须对他的话予以新的解释。所以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尤其是在我们的观念剧烈变革的时代重解经典,乃是解经史上的必然现象。“五四”运动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与在当代中国学术语境中重现“尊孔”思潮,各自所面对的经典一般无异,所不同者,是时代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观念引导着我们对经典的理解。
对于将诠释学视同经学的学者而言,我列举数种解释而不提供明确的判断以断定孰是孰非的做法,等于在做无用功。当余敦康先生说“诠释学得诠释出内容来才行”时,他的批判锋芒实际上指向了整个诠释学研究领域。这一点,从他的一连串发问和质疑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伽达默尔诠释了什么?看看《真理与方法》,什么也没有诠释。”“本体诠释学诠释出了什么?”“傅伟勋讲‘创造的诠释’……也没有诠释任何东西。”“台湾的黄俊杰也有同样的问题。”*参见余敦康:《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进路》,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6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再重申一遍,诠释学并不诠释具体的文本,它的价值不在于诠释出文本的内容,或者为某种诠释提供新的证据。现代诠释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哲学,确切地说,是实践哲学。它并不能取代解经学,诠释学与解经学分属于关系密切但又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解经学为诠释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也包括我们鲜活的解经经验;诠释学孕育于解经学,是在解经学基础上展开的哲学反思,从反思中获得的成果亦将反哺于解经学,使之日臻完善。如果要求诠释学必须诠释出什么内容,无疑是以诠释学取代了解经学。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中国诠释学”中的“中国”一词。在学界,有不少学者否定“中国诠释学”存在的合法性。其论据是,诠释学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解理论,无古今中外之别。所谓的“中国诠释学”无非是诠释学在汉语语境下的应用。一如没有“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也不可能有“中国诠释学”。在我看来,这种类比性的推理方式是有瑕疵的。我们承认没有见到“西方数学”的说法,但是“西方哲学”的存在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西方的大学学科分类中,也一直有“印度哲学”。至于“中国哲学”,虽说黑格尔很早就否认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有“哲学”,这种观点也影响了西方学界很长时间,但是近年来“中国哲学”也逐渐为西方学界所接受。概而言之,所有的人文学科均应作如是观,诠释学自然也不例外。以此观之,“中国诠释学”有其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前提是我们真正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诠释学”理论体系。
我们并不否认诠释学有着普遍的适用性,不过这种“普遍”与自然科学相比,有着程度上的差异。自然科学所说的“普遍”是没有“例外”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universell);而在诠释学中追求的所谓“普遍”实质上是“一般”(allgemein)。施莱尔马赫和贝蒂的诠释学体系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前者将自己的学说称为“一般诠释学”(allgemeine Hermeneutik),而后者则以“一般方法论”(allgemeine Methodik)和“一般解释理论”(allgemeine Auslegungslehre)来标明自己的诠释学。
中国与西方因文化传承传统与语言文字之不同,其阅读与理解的经验也各自相异。这种差异性,在最明显的区别之一——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表现为两者不同的诠释观念:西方诠释学持“语音中心论”的(Phonozentristisch),亦即逻各斯中心论的立场;中国诠释传统代表着立足于形意文字的“文字中心论”(Schriftzentristisch)的立场。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做过比较详细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拙文《语音中心论与文字中心论》*潘德荣:《语音中心论与文字中心论》,载《学术界》2002年第2期。。在漫长的解经实践中,中国诠释传统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风貌,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诠释学的理解理念与方法论。从西方学者的角度看,它属于“特殊”的诠释理论形态。然而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日益深入,我们必将意识到并承认这一点,即中国的诠释传统正是汉语语境中的“一般”的诠释理论。我相信,在整体意义上的诠释学研究的大框架内,中国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具有一种互补性。
三
对于“能否创建中国诠释学”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甚至认为,对诠释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而言,创建“中国诠释学”是必要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创建?
在当今学界,海外华裔学者率先注意到了中国诠释学的研究问题。我这里指的是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本体诠释学”一语,首见于成中英的《方法概念与本体诠释学》(载《中国论坛》(台北)1984年第19期)一文。和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creative-hermeneutics)*傅伟勋在《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年后记》(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提出了“创造的解释学”。此后又阐发了创造性解释的五个步骤。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52页。。成中英侧重于从哲学的角度对诠释学的形上学依据进行探索,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Ontological Hermeneutics)进路异曲同工。傅伟勋的重心是借鉴西方的诠释方法论,提炼出中国的诠释方法与步骤,沿袭的是方法论传统。在国内学者中,最有力的推动显然来自汤一介,他曾撰有“五论”来讨论“中国解释学”之构建。郭齐勇对汤一介的中国诠释学之探索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汤一介“创造性地提出‘建构中国解释学’问题,成一家之言。他梳理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指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他还以僧肇注《道德经》为例,讲解中国经典注释的知识系统。”*郭齐勇:《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载《光明日报》2014年11月05日。以此观之,汤一介是在借用西方诠释学的诠释理念与方法,对中国的解经传统——尤其是解经的方法论——进行系统研究,希望能找到实现中国解经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道,创立有别于西方的、现代的中国诠释学。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从多重视角探索建构中国诠释学之路,且已获得值得称道的成果。这些成果,就其内容而言,颇具“中国”诠释学的特色,对中国诠释传统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与思考。但是,它们的底色却是西方诠释学,从思维方式到诠释理念,基本上来自西方诠释学的范式,是西方的范式在汉语语境中的运用。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并不是“借鉴”,而是在落实与完善西方诠释学,使中国传统的那种“特殊”的诠释思想融入具有“普遍性”的(西方)诠释学,成为西方诠释学理论的又一个新例证。如果我们的研究仅限于此,还能算是“中国诠释学”吗?这一疑问把我引向了更为基础的诠释问题之思考;中国诠释学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它区别于西方诠释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就西方诠释学而论,我们可以画出一条清晰的线路,各种诠释学都有其自身的诠释取向与核心概念。如施莱尔马赫方法论取向的一般诠释学,其诠释理念是揭示文本或作者的原意,属于此脉络的有狄尔泰、贝蒂、赫施等;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本于语言与(人的)存在的关联阐明了诠释的生存论性质,人们的诠释活动构造着“此在”(亦即人的存在)。能标识“中国诠释学”的究竟是什么?这尚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确立过程对我们厘清中国诠释学具有启发性意义。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哲学是认识论的,他是通过理性自身发展逻辑来构建关于“绝对理念”的知识体系。黑格尔据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黑格尔的看法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见解。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中国哲学从总体上说乃是基于人的内在体验,要义在于把握生命,阐发为人处世之道,以人道证成天道,以伦理学为进路抵达形上学。如今西方的哲学界,已频繁地使用“中国哲学”这一概念,说明中国的哲学思维方式已水到渠成地被世人接受了。
中国独特的理论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自身的诠释传统。且看《易纬·乾凿度》对《易经》的解释:“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所谓“八卦”,本是对自然现象的抽象。然在《乾凿度》中,直接将之与“五气”(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各自所禀之气)联结起来,并进而推及人之“五常”(五伦),此所谓“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直接赋予空间的五个方位概念以“仁义礼智信”的寓意,以阐发儒家的伦常理念,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表现。它不是纯粹的知识论进路,而是对宇宙论、形上学与价值论进行整体观照,最后落实于“五常”。而“五常”作为人伦之要旨,本立于“五气”,且“应八卦之体”,表明了“五常”乃应于天意。圣人能知天意而定人伦,进而“明至道”。是故“五常”所表达出的不只是人伦规范,而且是天道,确切地说,其所指向的领域是“道德之分,天人之际”。唯其如此,方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
中国诠释传统之大旨是孔子确立的。孔子解《易》时尝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为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为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长沙:湖南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页。此寥寥数语,奠定了儒家诠释经典的根本宗旨。孔子解《易》之前,史巫的卜筮之法大行其道。“巫”家解《易》,着眼于卜筮,旨在通过与神明沟通而知神意(“幽赞”),依据神的旨意而行;“史”家解《易》则能进而明其“数”。“数”与数字以及演算有关,每一卦象符号都能借助于数字表达出来(如六、八为阴,七、九为阳)。所谓神意便寓于数字运算的结果之中(达数),精于历算的史巫能通过历算推知神意之所示的时间节点(明数)。史巫二者解《易》的目标均在揭示卦象符号之原义(它被视为神意)。因人之吉凶全然取决于神意,所以不免看重卜筮(与神沟通,了解神意)与祭祀(取悦于神),以求得平安与福祉。与之不同,孔子虽不排斥卜筮,但是他之解《易》“后其祝卜”,而重在“观亓德义”、“求亓德”。他将“达德”视为解《易》的最终目标,“幽赞”与“明数”只是“达德”的辅助性方法。在孔子看来,与人的祸福凶吉密切相关的是其是否有德行,能否行仁义,而非卜筮祭祀,若已“达德”,便无需卜筮。是以孔子这样教导世人:君子寡祭祀而以德行求福;希卜筮而以仁义求吉。
孔子解《易》观其德义、求其德的解经宗旨,对后世儒家一脉的诠释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渐而成为中国诠释传统之主流。史巫卜筮之法被束之高阁,乃至被遗忘,今日的学者连卦爻辞的文义和原文读法也都模糊莫辨了。*详见付惠生:《〈周易〉爻辞原文读法与意义复原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虽是如此,史巫解经之精神(追求文本原义)却并未烟消云散。这种精神在儒家内部催生了各种解经方法,如文字训诂、离章辨句、文献考据等。这些方法,在形式上有别于史巫的“达数”、“明数”之法,然其旨趣是一致的。准此,在解经史中的古文学与今文学、章句训诂与微言大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争,有如孔子的“求其德”与史巫的“达数”、“明数”之辩,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孔子与史巫之争的延伸。
因孔子主张解经“立其德”,开启了以“立德”为旨的诠释路向,儒家解经的重心也从揭示经文之原义(神意)转向了以“德行”为核心的人文教化——“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1页。不过孔子自己并未因此完全放弃史巫之法,他只是寡祭祀、希卜筮而已。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说,也只是荀况比较极端化的说法。按照孔子的看法,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占”与“不占”,而是在透过“占”而“达数”、“明数”之后能否“达德”、“弘道”。
现代学者当然不再会纠结于“占”与“不占”了,它在一种更为深入的意义上转化为对诠释方法论的取舍问题。在我看来,孔子诠释经典重在“立德”的观念是可取的,但是基于方法解读经文原义的认识论之向度亦是不可偏废的。“立德”之旨引导着我们的诠释活动向着伦理、道德的目标而展开,并将其化为人自身的德行;方法论为这种诠释提供了合理性的保障,换言之,为此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能被我们的理性所接受的论证。
通过对中国与西方诠释思想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西方的现代诠释学并没有“立德”之诉求。在方法论诠释学集大成者贝蒂那里,所追求的是文本原义,至于所揭示的原义是否合乎道德,不在考虑之内。而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诠释学,其重心是对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论证,阐明理解是人的存在之规定性。至于通过什么样的理解来引导、规定人的存在,换言之,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在其理论思考中似有还无。*关于这一点,即在现代西方诠释学中未能给予诠释活动的伦理导向问题以应有的关注,参见潘德荣:《文本理解、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我认为,孔子以“立德”为宗旨诠释理念弥补了现代西方诠释学的伦理导向之缺位。以孔子的诠释理念建构的诠释学,我名之为“德行诠释学”(Die Tugend-Hermeneutik)。因它的诠释理念取自孔子,我们可以称其为“中国诠释学”。但它并非中国诠释学的全部,如果考虑到我们的解经学传统本身就有别于西方解经学,建立中国的诠释学方法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于现代诠释学研究本身而言,德行诠释学是一种方法论和本体论诠释学之后的新型诠释学形态。就此而言,它就不仅弥补了西方诠释学的缺憾,而且还是拉动西方诠释学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贝蒂方法论诠释学的经典之作发表于1955年,原文为意大利文。对学界真正产生影响的是经作者亲自校订的德译本Allgemeine Auslegungslehreals Method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一般解释理论》,出版于1967年)。本体论诠释学的经典之作为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于1960年。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诠释学研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有不少诠释学家投入诠释学研究中,但他们都只是在完善和补充贝蒂和伽达默尔所开启的诠释学方向,而未形成新的诠释学形态。所以,我认为西方诠释学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使诠释学在整体上发展为一种更符合时代所需的新形态。
如果我们将“立德”确定为诠释的宗旨,那么依此而建立的理想形态的诠释学无疑是“德行诠释学”。若我们要建立“德行诠释学”,诠释经典就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若就诠释的对象而言,德行诠释学便是一种经典诠释学(The Classic-Hermeneutics)。众所周知,在每一种文化传统中,我们所看到的书籍、文献都浩如烟海,但能够被列为经典的却屈指可数。经典与普通的文本不同,它们在形成文明与文化的精神传统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本身就具有一种典范功能,被视为载道之体。我们对“德行”的认知与体验,乃依据人们持续地对经典的理解及其与生活实践的相互印证,由此而形成了属于某种文明的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经典所蕴含的智慧,既属于经典所赖以形成的时代,同样也属于从中发展而来的现今社会。毫无疑问,经典不仅塑造了我们深厚的精神传统,也开启了我们的未来发展方向。
简要地勾勒一下我对“中国诠释学”的构想,这也是我就汤一介先生倡言“创建中国诠释学”“接着说”的一点心得:就诠释的宗旨而言,它应当是以“立德”为旨趣的“德行诠释学”。它既标志着“中国诠释学”之形成,也为世界范围内的诠释学之整体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中国诠释学”的主要诠释对象是“经典”,而非一般意义上“文本”,因此是一种经典诠释学。现代诠释学的起点是从“经典”转向“文本”(施莱尔马赫创立“一般诠释学”,其中“一般”一词的主要含义就是区别于经典的“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力图使诠释学研究摆脱神学的束缚。我主张当代的诠释学思考之重心应当从“文本”返回“经典”*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拙文:《经典诠释与“立德”》,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而成为解除了神学桎梏的“经典”诠释学。
(责任编辑:韦海波)
潘德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