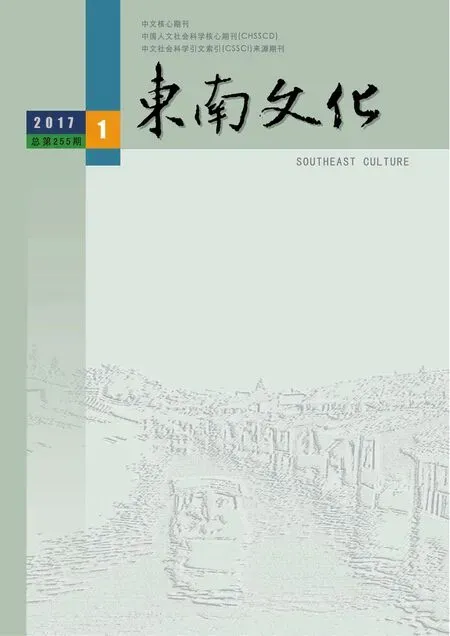探源文明 追迹历史
——李伯谦先生专访
李伯谦林留根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2.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探源文明 追迹历史
——李伯谦先生专访
李伯谦1林留根2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2.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中国考古学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考古学要与文献史学、社会学组成三个认知系统,考古学文化研究要将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要重视考古遗存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全面地研究、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要掌握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其中地层学在使用中应该与埋藏学相结合,而文化因素分析则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江苏的商周考古研究应该把握江北徐淮夷文化和江南吴文化两条主线;要正确处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使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考古学 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 精神领域考古 文化因素分析 夏商周断代工程 文明探源工程 徐淮夷文化 吴文化 地层学 埋藏学 文化遗产保护 李伯谦
李伯谦(1937—),男,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等。20世纪60年代初即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夏商周时期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1995年出任“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工程考古领域的总负责人;2000年出任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所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和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等学术观点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代表性著作有《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感悟考古》等。2017年是李先生八十华诞,本刊特委托本刊编委林留根研究员就考古人生、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以及江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等专题对李先生作了采访。
林留根(以下简称林):李先生,您好!2017年是您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又适逢您八十华诞,我受《东南文化》杂志委托向您表示祝贺!自从您惠赠我《感悟考古》这本书后,我就一直带在身边,随时翻阅。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深刻,既有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总结、回顾与展望,又有对当今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最前沿问题的探究和阐释,是一个考古学家的思想结晶。特别是书的《导言》,是您多年来对考古学深刻的感悟,所提出的诸多考古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正是考古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所以,我首先想请教您的是,您作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主持过这么多重要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如此多的科研成果,您是如何从一位考古工作者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又如何从一名考古学家成为考古学理论殿堂中的思想家的?
李伯谦(以下简称李):后面这个是溢美之词了(笑)。如果说我在考古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它们首先是和我走入考古行业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的。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在历史系,第一年是不分专业的。第二学期期末,各个专业老师开始动员大家报名选专业,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考古教研室来的是吕遵谔先生,他当时是教研室的学术秘书,现在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他当时说得特别好:“学考古可以游山玩水,到一些名山大川去,还可以学习照相,我们有这个课。”我当时对考古还没太多认识,一激动就报了考古专业。1958年上了一学期课,学习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等,到暑假时,学校动员我们过共产主义暑假,不放假,吕先生就带着我们去周口店发掘。当时我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发掘出不少东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认识了很多动物化石,有鬣狗、肿骨鹿等。发掘过程中,郭沫若、贾兰坡、裴文中、杨钟健等专家都去参观过。当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去访问老技工、查资料,编写《中国旧石器考古小史》。实习后我就算正式进入了考古圈,但那段时期对考古还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对考古的真正认识还不是很清楚。
1959年我们迎来了正规的田野考古实习,地点在陕西华县的元君庙和南台地遗址。当时是李仰松老师带队,辅导老师还有白溶基先生。实习从3月开始到8月结束,整整一个学期,包括调查、发掘、参观。当时我被分在了元君庙遗址,这是一处仰韶文化早期的墓地,有很多合葬墓。后来为了锻炼发掘地层,我又去了泉护南台地遗址,这个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通过发掘,我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实习结束后有半个月的参观,我们去西安参观了很多博物馆,还参观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等。这次实习后,我开始了解了考古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已经学过了林耀华先生的《原始社会史》、李仰松先生的《民族志》等课程,这些对我们探讨合葬墓的性质很有帮助,大家争论很激烈。联系到夏鼐先生给我们讲的《考古学通论》,我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先生讲到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历史学是靠文献记载来研究历史,考古学是靠调查发掘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所以他说,“考古和文献史学是车之两轮”。意思是历史学像车子,一个轮子是考古学,一个轮子是狭义的史学,只有两个轮子都跑起来,历史才能研究得好。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考古是研究历史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1961年毕业的时候,我们接受科研训练,当时是严文明先生负责,要求撰写《北京市文物志》,每人负责一个题目,我负责的题目是《明清北京城》,算是经过了科研训练。我们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困难时期,工作分配不容易,学校的政策是只要能找到接收单位就派学生去,暂时派不了的,就留在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正在昌平县建分校,修铁路时发现了雪山遗址,我一毕业就被安排去了这个工地。这个遗址很复杂,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汉代一直到辽金。工地结束后,我也正式留校。1962年我又带队去安阳小屯实习,当时教育部发布《高等教育六十条》,规定了一年要读的书,我由于一直在野外带队实习,规定的必读书目看不完。所以1963年教研室又派我去偃师二里头带实习时,我不太想去,当时的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知道了,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苏先生说:“李伯谦,听说你不想下去啦!是不是觉得田野这一套已经过关了?书本是学问,当然要读,但田野也是学问,对考古专业的老师来说是更重要的学问,不要以为参加过几次实习就算可以了,其实还差得远呢。考古教研室青年教师里头,除了邹衡,谁的摸陶片功夫过关了?当考古专业的老师,就要立足田野,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不会有大的出息……”苏先生的批评使我端正了方向,以后几十年我再没有为下田野有过怨气,而且每次下去都会得到新的信息,获得新的收获。
我毕业后基本是年年带学生实习,主要的发掘经历是:1961年毕业的当年在昌平雪山,1962年在安阳小屯,1963年在偃师二里头,1964年又去了安阳,1966年以后工地就停了;1972年又带学生实习,在河北承德整理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资料,同年还去了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发掘;1974年发掘江西清江吴城遗址;1975年发掘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和甘肃永登连城遗址;1976年发掘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因为毕业后一直在工地,看到了很多从事考古的人特别是很多知名考古学家是怎么度过一生、又是怎样成为考古学家的,所以我也想自己将来是否要像地方上那些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那样,一生中发掘很多遗址,编写很多报告。但是这条路在大学行不通,因为大学的主要工作是给学生讲课。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考古学家不能只是挖遗址、挖墓葬而不做别的研究,考古学家不仅要清楚自己挖的、整理的材料,也要会利用他人挖的、整理的材料,要学会利用他人的材料写文章。这点我深有体会。我从1961年毕业后一直到1972年都没有讲过课,都是在外带学生实习。1972年我第一次登讲台是在山东大学讲授商周考古,1979年又在南京大学授课,20世纪80年代初才在北京大学讲课。这期间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研究考古材料,特别是如何把它与历史联系起来。就像夏先生讲的,这是车之两轮,目的还是研究历史。我要把考古发掘的材料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历史挂上钩,解决历史上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我后来就朝这个方向写文章。我第一篇比较正式的论文是《试论吴城文化》,1974年发表。我首先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等器物的形制花纹变化,将吴城文化分了三期,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去还没有对江南这类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遗存分期。分期研究比较顺利,但是这类遗存的定性问题我一直把握不准。现在看来这个遗址是比较重要的,它是江南地区第一次发现的青铜文化,但是它的性质一直确定不下来。我个人觉得应该将它单独命名,原因是我根据资料整理,把它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数量最多,含有较多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与当地及周邻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存在的几何印纹陶遗存关系密切;乙组数量次之,与安阳出土的商时期陶鬲、豆、罐、盆等相似,显然是受到商文化影响才出现的;丙组数量最少,似与湖熟文化有某些相似。1977年文章写成后,我征求邹衡先生意见。邹先生说,湖熟文化缺乏典型单位,内涵不清楚,不如删掉。我认为邹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为稳妥起见,我在1978年将文章正式提交给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时,便将丙组因素重新做了分期,一部分归甲组,一部分归乙组,只保留了甲、乙两组。根据哲学领域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原理,甲组因素数量最多,决定吴城遗址一类遗存的性质,于是我便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会上讨论时,安志敏先生认为还应该是商文化。当时主办方为配合会议办了一个标本展览,吴城遗址的标本也在其中,我就陪安先生去看展览并向他解释,安先生参观后也同意了我的观点。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利用了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触是,研究考古学文化不仅是研究分期、性质,还要探讨它的历史,以及如何将考古发现的各种现象与历史相联系。后来我知道,夏鼐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还表扬了这篇文章。
从吴城遗址的实习到《试论吴城文化》的发表,我感觉到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发掘一个遗址、写出简报、作出分期,还需要把文化性质研究清楚,此外,还应该研究清楚这些遗存所反映的历史。我认为必须从方法论上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方法就是“文化因素分析”。回顾中国考古学史,很多先生的研究中早就运用到了这个方法,比如梁思永先生1939年发表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苏秉琦先生1964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邹衡先生1980年发表的《论先周文化》等,只是没有正式提出“文化因素分析”这个名称。若干年后,我才在1988年11月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正式发表了《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不过,1985年我在给商周考古研究生上课时,就将其作为考古方法论提出,并组织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所以,从1974年开始带学生发掘实习到1988年发表文章,期间酝酿了十几年。我认为,考古学研究,第一个就是地层学,如果搞不清地层学,基础就做不了;第二个是类型学,只有通过型、式划分,才能弄清楚器物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就是文化因素分析,只有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才能联系到历史学问题。所以当时我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回顾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我最初的研究也是不自觉的,从写出《试论吴城文化》到后来上课与学生们讨论再到写出《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我才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到考古学应该怎样走上研究历史问题这条道路。
林:您刚才提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问题。我觉得与其他考古学家相比,您特别注重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您一直都是带着历史学的问题来研究考古学材料。实际上,考古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而诞生的。刚才您也讲到夏鼐先生曾提到考古和文献史学是“车之两轮”,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方法。俞伟超先生在《考古学是什么》一书中也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掉自己是搞历史研究的,是历史学家,考古的最终目的是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研究今天。他也提出了“古今一体”的理念,和夏先生的观点实际是相同的。真正的考古学家一直把研究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当,所以,我想请您再概括一下考古学与历史学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我也是经过了比较长的过程后才真正有所认识。尽管夏先生在《考古学通论》中讲到,历史学一边是考古学,一边是狭义的史学、文献史学,但怎样具体体现,特别是对考古学研究者来说,怎样将两者结合起来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考古学界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考古就是考古,考古就是靠挖出来的遗迹、遗物说话,不要与文献相比附、相结合,因为容易出错,另外,也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对历史文献有质疑,认为不要越线,这个观点影响很深;另一种意见是,一些研究历史学的人也看不上考古学,他们觉得,考古只是挖出来瓶瓶罐罐,并没有文字,是研究不了历史的。我认为这是两种极端的看法,我们不能走这两个极端,而应该把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结合起来。那么应该怎样结合起来呢?这就是我们作为考古学者对文献怎样认识的问题。我认为,文献、包括传说时代的传说所记录下来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意义,这就是尹达先生所说的“史实的素地”。考古材料没有文字,但是它包含着历史的素地。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看法。我在《感悟考古》中曾提到,回顾我们的史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有三个不同的认知系统:第一个是从口耳相传的传说史学到用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学的史学系统;第二个是考古学兴起以后,通过考古学的遗迹、遗物研究历史的考古学系统;第三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即摩尔根讲的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学系统。我觉得,这三者既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不足,它们应该互相补充,才能取长补短。我认为要把考古学放在整个史学的发展中看它的地位和它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原史时代,所谓“原史时代”是指有了一定的文献记载,它或者是后人追记的,但是很少。那么我们中国的原史时代是什么时候?我认为至少是司马迁所记的三皇五帝阶段,《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等也是从传说记载逐步变成文献记载的过程。研究原史时代更应该把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研究解决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动摇过。
林:我注意到您提到的“考古学的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现阶段在考古学界,考古资料的积累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大家还没有从这个角度研究和展开问题的自觉性,这个可能是中国考古学今后工作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从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到现在的诸如“以良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明化模式”、“以陕西神木石峁片区为代表的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以湖北石家河为代表的长江中游的文明进程研究”等,都是从考古学区域研究的角度去展开的,但实际上一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历史发展、社会走向,是可以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研究的。所以,我想请您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展开论述一下。
李:“考古学的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从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发展而来的。因为我们考古学研究的是人文,是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人类的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下进行的,而自然条件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北方、南方的自然环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区域研究必须要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分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展开区域文化研究;第二,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内不会只有一种文化,可能有两种甚至三种文化;第三,厘清了一个区域内有几种文化、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之后,还要在这个前提之下理清相邻区域是什么文化。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区域文化的研究,从自然的分区到人文、社会的分区,要把两者统一起来考虑。而长时段研究一定要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因为一个文化的发展演变,虽然也与环境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社会密切相关。即便它是从一个系统的文化发展起来,也可能在某一个时段、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跨出了原来的分区,而存在一定的变化。所以,我们不能固守它的分区,要灵活看待,要把一个文化的来龙去脉理清楚。我在《感悟考古》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滕铭予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一个是宋玲平的《晋系墓葬制度研究》,两者都是对特定考古学遗存作长时段研究的著作。我认为对某一文化作长时段研究后才能看出它的规律性,如果不把它放在一个长时段背景下,就可能误读了它的发展和变化,也不容易看到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区域文化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相结合,那么对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就会比较全面、比较圆满。关于区域研究,我在同书中提到的是段宏振的《邢台商周遗址》一书。邢台是一个行政区划,在这个地区存在很多考古学文化,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我们不能只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我们不仅要看到早段的文化,还要看到晚段的文化,应该研究整个发展趋势。这可能是以后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常态。我们以后研究考古学文化,不能孤立地进行,一定要全面把握,要把它放在大的区系概念下来讨论、把握。
林:是的,比如龙山文化晚期阶段,中原地区与外围地区的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组合分化、激荡整合,这就需要我们使用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的方法。您特别关注考古学各个层面上的问题,比如您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变迁中的渐变与突变、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聚落考古与社会结构研究等问题;您还特别关注精神领域考古,这个问题一直是考古学领域的一个难题,因为考古本身面对的是物质材料,直接可见的精神材料很少,很难研究。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比如何驽先生的很多著作。我觉得您强调的精神领域考古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考古工作往往会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困境,但考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社会、复原社会,而一个社会的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往往更重要。所以,我还想请您再重点谈一下精神领域考古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工作者应该怎样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李:谈到精神领域考古,我是受到何驽的启发。当时我给研究生上“考古学理论方法”课,在讨论考古学文化时,他提出,“考古学文化是指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的表述不全面,应该在“遗迹、遗物”的后面加上“及其蕴含和反映的精神文化”的内容。当时,课堂讨论很激烈,但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让我想到1958年教育革命“大跃进”时,学生们向苏秉琦先生提了很多意见,说考古学是见物不见人,说考古学只是研究盆盆罐罐,等等。苏先生后来思考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认为学生们说的有一定道理,他也指出,我们做考古是干什么呢?我们就是从早到晚研究盆盆罐罐吗?他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是在回答盆盆罐罐里面有没有思想、有什么样的思想、反映了什么问题。俞伟超先生也特别注意精神领域的研究,早在1989年他就在《文物研究》上发表过《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应该重视精神领域考古。后来我也联想到考古学研究中,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都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之下形成的。这些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所以何驽提出这些观点以后,我是鼓励他的。实际上,我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何驽的启发,比如在后来的文明探源研究中我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转变问题。我认为如果单纯从遗迹、遗物来看,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绝对是发展、继承的关系: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前身,良渚文化是崧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后来,特别是在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发现了九座崧泽文化时期的大型墓葬,它们随葬很多玉器,比如玉钺等,但却没有随葬带有宗教色彩的玉器。而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大量带有宗教色彩的玉器。随后我就开始思考良渚文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崧泽文化在转变为良渚文化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凌家滩文化的影响,而凌家滩文化又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这种影响到底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但是影响确实是存在的。良渚文化阶段,特别是社会上层对带有宗教色彩的玉器非常痴迷,随葬大量的玉琮、玉璧、而且它们都刻有神徽图案。如果崧泽文化继续沿着君权、王权的道路发展,可能不会走向衰亡;而良渚文化的社会上层把神权发展到了极致,将大量的社会财富用于祭祀等活动,最后走向了衰亡。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觉得应该从精神领域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考古学限制在就物论物,而是要看到材料背后所反映的精神领域的内涵。
1.3 标本采集与处理 充分暴露宫颈阴道部,用棉球轻轻蘸去过多的黏液;用HPV取样器尖端置入子宫颈口,顺时针方向旋转至少6-8周,以保证收集足够量的宫颈管内脱落细胞;取样后将取样器立即放入HPV保存瓶中,室温保存待检。
林:就像良渚文化的神徽——而且是统一的神徽,它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它反映的是良渚文化共同的信仰层面。您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三大研究工程主导了国内考古学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以,我想问的是,您本身是从事夏商周阶段考古学研究的,但实际上您在文明探源研究的领域中也成果丰硕,比如《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从崧泽到良渚——关于古代文明演进模式发生重大转折的再分析》等多篇文章,我觉得这些都是文明探源理论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您是如何将夏商周研究与之前的文明探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与我自身的经历有关。尽管我毕业后确定的发展方向是东周研究,但是每年安排的实习遗址中,东周的很少,要么是商周、要么是新石器时代的,特别是接触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较多,比如雪山、小河沿、二里头、南岗、柳湾、连城、马厂、元君庙遗址,等等,所以我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比较感兴趣,也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另一个方面是我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作。比如参加后我才知道,1975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先生的初衷并不是夏商周断代研究,而是黄帝研究,只是后来与部分考古学家探讨时,大家觉得条件还不成熟,于是就先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以我们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后一年又酝酿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和朱凤瀚先生一起写了一个意见,建议怎么开展这项研究。当时的领导小组认为这项工程比较大,于是我们就先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要是我和李学勤先生主持工作,从2000年到2003年。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开始,这次由于我们几位年纪大了,就由年轻人主持工作。参加这两项工程的过程中,我一直也在思考您问的这个问题。我最早发表的相关文章是《考古学视野下的三皇五帝时代》,是将文献传说记载的历史与考古学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做大体对应。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刚开始那么发达,最后却走向衰落?为什么仰韶文化最初被看作是比较落后的文化?苏秉琦先生所划分的文明原生形态里面没有仰韶文化,他认为红山文化是原生型,仰韶文化是次生型,还有一些文化是续生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发展模式不一样,仰韶文化并不是落后的表现。比如,以西山大墓为例,它的墓葬规模很大,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墓葬规模相似,但是随葬的东西却特别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吗?我觉得并不是,主要还是它的理念不同,精神领域不同。红山和良渚的社会上层一心一意把他们所有的财富都贡献给神灵了,而仰韶文化不是这样。我想这正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个问题可能继续会有争论,不过我是这个观点。再之后我在苏秉琦先生“古国—方国—帝国”理论的启发之下,提出了“酋邦—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是在河南新密市的聚落考古研讨会上的发言。我觉得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从没有国家进入到有国家,是需要一个判断标准的。不管是过去说的城址、青铜器、文字、礼仪建筑等四个标准,还是后来讲的聚落形态分为几个层级的标准,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所以我提出了十个方面,当然具备其中五六个或七八个方面也就可以算是进入文明阶段了,这十个方面是我根据陶寺、良渚等遗址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我认为不能单纯只开展夏商周研究或者文明起源研究,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考古学研究不能单纯只研究一个时期的,更不能只局限于一个时期的一个小问题。特别是我作为大学老师,更应该涉猎广泛。再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先生是组长,我负责其中的考古部分,虽然结论得出后大家有争论,但我觉得考古部分还是取得了很多成果的。特别是其中的夏商分期问题研究得很细,比如将夏代分为三个阶段:登封王城岗大城的发现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做的工作,测年发现它比小城要晚,距今四千多年,这是夏代最早阶段,是传说中的大禹时期;然后是新寨遗址,这个问题就发现得比较早了,我在1986年就写过文章讨论“后羿代夏”,这也涉及到文献与考古资料关联的问题;到了二里头阶段就是“商汤中兴”以后。夏代基本就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这个结论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框架做基础,测年工作就没有依托,也就无法展开。
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长时段研究。所以,从商周到史前特别是史前的良渚、石峁以及顺山集的发掘、研究,考古界都要请您到现场指导,感觉这样就有了主心骨。特别是在良渚文化研究取得如此多的重要成果的今天,我尤其敬佩您那么早就看到了良渚文明的演进问题。而且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推动了二里头等遗址研究的新成果,没有断代工程,这些遗址就不会按照都城的思路开展工作。我们《东南文化》一直立足于东南地区,所以我想再具体谈一下南方考古的问题。南方考古近些年也取得了很多成果,长江下游地区吴越文化的研究也一直得到了您的指导。我记得第一次在镇江举办吴文化讨论会时,您就带着几十份油印论文来参加会议。之后我们每每在有重大发现的关键时刻也都邀请您来指导。我觉得南方吴、越、徐文化研究虽然有一些成果,但仍然缺乏一些大的突破,虽然最近我们在江阴佘城遗址、沭阳、万北遗址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主持江苏省考古所工作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在商周考古上有所突破,但总觉得有一定的难度,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第一个是吴越文化的问题,经常遇到一些瓶颈。比如镇江的葛城遗址,是西周早中期的一个城址,我们发现了一些城墙、壕沟,具备一些继续研究的条件,但是城内的工作却没有展开。我觉得在一些小城的平面布局方面应该开展一些工作,这样对于了解木渎古城这类大城会有更多的启发,比如南方城址的路、门、水系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否有水路就没有陆路?目前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在考古上还没有得到解决,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突破。第二个是徐的问题。我们想在“十三五”规划中开展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也一直觉得无从着手。所以我想请教李先生,江苏在商周这一时段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吴越文化和徐文化的发掘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可以有所突破?
李:这个就是江南地区青铜时代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以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指导思想,基本上江北地区就是以徐为中心,是徐夷、淮夷或者就是徐淮夷。徐与中原王朝有关系,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是很容易获得成果的。另外一个就是吴国的问题。吴国的起源在哪里?这是一个老问题,我还是觉得宁镇地区为最早。不过,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扩大一些,把周围一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这个问题自然就清楚了。我觉得应该抓住两点:江南就是吴文化,江北就是徐淮夷文化。
林:宁镇地区近年来又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像丹阳埤城附近的孙家村遗址,可能是一处与青铜铸造作坊有关联的遗址,整体可能是一个城址;丹阳延陵地区还有一些线索,可能能解决诸如季札的研究问题;高淳夏家塘发现的土墩墓,一座土墩内有五个大型石床,其中一个墓里还出土了青铜鼎等礼器,等级相当高,土著特色浓郁。
李:江南地区吴文化的研究要选择主要遗址、城址为重点,做长期的工作,要开展调查,注重点面结合。应该进一步把周边区域的情况理清楚,制订长期的工作计划,发掘几批墓葬,就可以解决诸多吴文化的学术问题。徐国的历史很长,徐族属于夷族系,嬴(或奄)姓,夏商时期即有其活动记载。但徐国作为一个迁徙复杂的国家,它的历史应当从西周初年开始算起。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在周初伯禽完成对徐国的进攻以后,徐国迁徙到鲁南、苏西北和皖东北一带;穆王征徐以后,徐族又继续南迁。今苏北的邳州以及洪泽湖周边的泗洪、盱眙都是徐人的活动范围。汉代的徐县就建在徐国的旧都之上。前些年你们做了大量调查发掘工作的邳州梁王城遗址是与徐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大遗址,应该进一步开展工作,从梁王城城址的建造年代、使用年代、废弃年代以及城内的布局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寻找证据。应该加大考古调查的力度,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抓住一些线索,再继续展开研究。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徐文化的研究一定能取得重大突破。
林:我们在2005年发掘句容金坛土墩墓的时候召开过一次研讨会,当时您对我们的发掘评价很高,在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上您还提出,土墩墓发掘应该把地层学与埋藏学结合起来。这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将地层学与埋藏学结合的理论。您后来也多次提及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具体的考古学研究中,我们也越来越多地需要这个理论来指导实践。比如我们在发掘泗州城汴河的时候,河内有很深的堆积,其中有一些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堆积,可能是自然的淤积或者冲刷,是人文与自然原因交织造成的。我觉得埋藏学对于我们的考古实践还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相关的研究似乎还很少,所以,想请您就这个问题再给我们展开一下。
李:埋藏学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应用很多。我是从地层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来思考的,我感觉我们对地层学理解得过于死板。过去我们划分地层,都是按照土质、土色,再加上里面的包含物来划分的。但是如果拘泥于地层学,研究就不全面,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不确定一个地层划多厚,既可以在这里分,也可以在那里分,缺乏一个掌握的度。我觉得划分地层时应该把地层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我在1986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发掘中受到的启发。当时我们发掘一个取土坑,一个泥炭层一层大概厚四五十厘米,从土质、土色看不出多大区别,但测年的结果显示,靠上层和靠下层的不同标本的年代跨度相当大,有1000~2000年的差距,可见,单纯按照土质、土色划分层位存在很多局限性。经过这样的反思后,我觉得应该尽可能多地划地层,十层、八层都可以划,划好后总结一下,再归入大的层位。以前考古界在发掘中还提倡统一地层,我觉得这样并不太合适,因为每个探方的情况是有变化的,应该动态理解地层的形成,在这个基础之上,尽可能多地划分地层。过去考古界还提到要参考“里面的包含物”,我觉得“包含物”更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包含物”受个人主观知识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不能用“包含物”做判断标准,“土质、土色”相对客观一些。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意见,具体应该怎样把埋藏学的理论运用到地层学的实践中,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解决的课题。
林:是的,我很同意您的观点,我们现在就要在考古发掘中带着这种想法和思路来指导实践,要考虑地层是如何形成的,地层中的遗迹单位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实际上是与人的行为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来,您不仅一直从事考古研究,还一直为文化遗产保护而奔走呼吁。特别是现今博物馆建设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文化遗产保护也深受公众的关注。实际上,我们的考古工作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密切相关,考古就是把古代文明中的精髓提取出来,传承下去。从这个角度看,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想请您从这个角度谈一下考古对当今的社会发展,对构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是怎么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就是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没有中国几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提炼不出这么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而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蕴含在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当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文化遗产就是提供、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源泉、载体和基础。当今社会,基础建设与遗产保护的矛盾日益激化,保护文化遗产是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其实,考古也是一种保护,考古学不是坐而论道,而是通过研究历史,揭示、保护、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总结经验教训,为社会发展服务。我在河南博物院演讲中总结过的“八项启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1)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2)文明演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一帆风顺的,中间是可能发生改变的;(3)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吸收异民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壮大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4)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从氏族部落社会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祖先崇拜,是自身保持绵延不绝、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5)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文字体系的使用与推广,是维护自身统一的重要纽带;(6)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存”等理念,及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自身比较顺利发展的保证;(7)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的兴建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过度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8)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也是阶段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断斗争—妥协—斗争的过程,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即使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不可超过他所能够忍受的限度。具体来说,如果理清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稳定、统一的作用,就能尊重不同民族的融合和发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就能避免汉字的拼音化等错误。
林:确实,考古学在今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现在考古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它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我想请您谈一谈。
李:中国考古学是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当时一些外国探险家、冒险家进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掠夺和破坏,激发了一批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下定决心学习考古。比如梁启超先生就给他的小儿子梁思永写信,劝他学习考古。当然我们现在不能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看待这段历史。审视考古学从产生到今天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要正确认识它的定位,它存在的重要意义,它对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有什么作用。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牢记田野工作是考古学安身立命的根本。虽然我们通过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研究,已经理出了中国历史的基本发展线索,但是距离恢复历史原貌、理清发展规律、指导今后社会发展的使命还差很远。第二,大力促进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的运用,提高野外的调查发掘、室内的解析研究以及遗迹遗物的保护等考古工作的质量。第三,加强国际交流,大兴理论探讨之风,不断引进、借鉴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在我们自身考古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高,提出符合中国考古学发展需要的理论方法,并指导实践。第四,正确处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文化遗产的存在是考古学兴起与发展的前提,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要求。面对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严峻形势,考古工作者应该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去。第五,打破自我封闭的藩篱,揭开神秘的面纱,积极开展公众考古,让考古成果服务社会,使考古学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林:您作为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一直非常平易近人,对年轻的考古学人也很关心,所以想请您指导一下,年轻人应该如何加强自身的学术修养,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作为?
李:怎样学好考古,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在大学阶段还是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熟练掌握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要老老实实做田野工作,浅尝辄止、蜻蜓点水都是不行的。第二,要注意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结合,在熟练掌握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以之为武器来指导实践,在具体研究调查与发掘遗迹和遗物时,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总结和分析,来解决历史上的问题。第三,随时看到学科在发展,要很好地利用自然科学科技的手段来为考古学服务。第四,考古是人民的事业,老百姓对挖出来的东西很好奇,我们一定要通过研究,通过浅显、生动的语言把它介绍出来,使之发挥作用,激发公众的爱国热情。真正的考古学家应该做到这些。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关起门来埋头研究;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还没有研究出成果,就大张旗鼓地到处宣传。
林:我的体会是年轻学者尤其应该认真读一读《感悟考古》这本书。这本书是您考古人生的写照,既是严肃的学术论著,也是开启心智的读物,而且它就像我读过的贾兰坡、竺可桢等先生的科普读物一样,将高深的理论通俗化,深入浅出、浅显易懂。
(本次采访由黄苑录音、记录并执笔整理;采访稿经采访者林留根研究员审订。)
(责任编辑:毛颖;校对:黄苑)
Exploring the Civilization O rigins,Tracing the H istory: An Interview w ith M r.LiBoqian
LIBo-qian1LIN Liu-gen2
(1.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2.NanjingMuseum,Nanjing,Jiangsu,210016)
A fter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of development,Chinese archaeology has gained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According to M r.Li Boqian,a renowned archaeologist in Chi⁃na,it is essential to form three cognitive systems by linking archaeology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studies and sociology in doi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to combine area studies and long-term analyses in study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focusing on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so as to achieve a more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societies.Regarding research methodology,M r.Li suggests to emp loy analytic methods from stratigraphy,typology,and cultural elements studies.Li further contends that the emp loyment of stratigraphy shall be combined with taphonomy and that cultural elements analyses are bridges linking archaeology to history studies.W ith regard to the Shang-Zhou archaeology in Ji⁃angsu province,Li points out 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the Xuhuaiyi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Jiangsu and the W u Culture of the southern Jiangsu.Li also signalizes the importance to balance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ignificant role thatarchaeology is supposed to p lay as a peop le’s cause.
archaeology;area study and long-term analysis;spiritual archaeology;cultural elements analysis;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ject;Xuhuaiyi Cul⁃ture;Wu Culture;stratigraphy;taphonomy;heritage preservation;Li Boqian
K 851
:A
2017-01-11
李伯谦(1937—),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与青铜时代考古、中国文明起源。林留根(1963—),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与青铜时代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