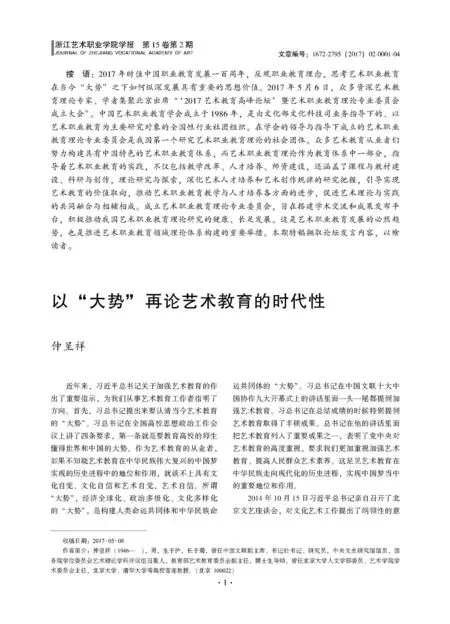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意识
——从唐宋婚恋传奇的戏曲改编中探寻
杨 玉
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意识
——从唐宋婚恋传奇的戏曲改编中探寻
杨 玉
男权社会的规则按照男性利益最大化制定,女性意识的表现是指女性对于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以及利用性别优势去选择合理的生存方式。对于意识觉醒女性的描绘始于唐传奇,并在后世的戏曲改编中得以发展。无论是关系萌动阶段的引诱暗示,还是促成婚恋的切实行动,以及对婚姻关系的维护,我们都可以从唐宋婚恋传奇的戏曲改编中找到典型案例。
女性意识;唐宋婚恋传奇;戏曲改编
在唐宋婚恋传奇及其后世的戏曲改编作品中,有一个基本情节框架是 “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中遭波折,最终或因男子境况的改变而团圆,或因男子忘恩负义而抛弃旧情”。[1]无论是始困终亨,还是始乱终弃,表面上来看,男性在婚恋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然而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在婚恋事件中,女性才是一段关系的真正主导,毕竟 “世间男子喜怒哀乐之事,其极点恒在女子之身”[2]。
在人类历史上,父系社会或者说男权社会的存在,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世界性现象。男权社会的规则按照男性利益最大化制定,女性意识的表现是指女性在社会规范的枷锁中找到了一种平衡和坚持,其表现形式未必是反抗,更多的是在枷锁中游刃有余的角色扮演。她们不盲目地接受,也不绝望地放弃。她们有好与坏的判断标准,在仔细衡量各个选择的利弊后,哪怕是选择权宜,亦是 “有意识”的,正如西方学者马杰里·沃尔芙 (Margery Wolf)的观察:成功的中国妇女 “学会了主要依靠自己,但同时表现得依靠父亲、丈夫和儿子”[3]。尽管男性在男权社会的绝大多数方面都占据着强势地位,但是任何时代的女性在婚恋关系中都没有丧失其主导地位,“哪怕这个世界似乎构筑了她们的弱势,她们还是其中非凡的即兴表演者。”①语出博妮·史密斯 (Bonnie Smith)在伊沛霞 《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序言。
纵观中国历代的文艺作品,对于这种意识觉醒女性的描绘始于唐传奇。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宋传奇所描绘的女性形象一脉而下,相关戏曲改编中的女性坚持着自己对于爱情、婚姻的追求,她们对于自身处境有着清醒认识,懂得审时度势地去选择合理的生存方式。她们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性别优势和性别劣势,然后善于利用,扬长避短,这种女性意识体现在婚恋事件的各个阶段。虽然古代的绝大多数小说、戏曲作品由男性写成,也并不妨碍我们从中窥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决定作用。这是由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占据的天然密码所决定的。不仅如此,从小说到戏曲,女性的话语表达更是得到了充分发挥。
简而言之,本文所谓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意识,是指在婚恋关系中女性有明确的目标——通常是明确的婚恋对象,并且清醒地认识到男权社会中自己的处境,巧妙地利用女性的优势将婚恋目标达成。在婚恋关系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可以从唐宋婚恋传奇的戏曲改编中找到典型案例。
一、关系萌动阶段的引诱暗示
婚恋事件中,爱情是最美好迷人的一部分,两性吸引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原始动力。“如果不是为了性,大自然中绝大多数艳丽、漂亮的东西将不复存在:植物不会绽放花朵,鸟儿不再啾唧歌唱,鹿儿不再萌发鹿角,心儿也不会怦怦乱跳。”[4]同时,爱情对于女性的意义又显得格外重大,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第一阵狂风吹熄掉。”[5]
然而,在进化心理学看来,爱情不是凭空产生的,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婚姻的本质是一个两性共同协作繁育后代的契约,其所追求的是理性的现实的繁殖利益。因而所谓爱情,不过是婚姻关系的前奏。设想一下我们会被什么对象所吸引?总是那些符合理论上的繁殖利益的对象,可以说繁衍操控着我们的爱情,“即使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所表现出的一切言行和好感源自何处,但它依然让我们产生冲动”[6]。爱情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感性的情感本能,但这在很多时候是不现实的、超出自身匹配价值的。
在婚恋关系中,“最稳定的浪漫关系和婚姻关系是从一开始支配结构就很明确的那种”[7]。男权社会中最稳定的支配结构是男性以社会资源支配女性所掌握的生育资源①尽管时至今日,男权社会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但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这种支配结构不是永久的。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力需求让位于机器,男性在争夺资源上的生理优势逐渐消失。有专家预言,婚姻制度在未来有消亡的趋势,至少不会成为主流选择。,以期女性 “生育确凿无疑的属于一定父亲的子女”[8]。女性主导模式是戏曲的主要模式之一,在明晰了男权社会的稳定支配结构后,我们可以得知,在爱情这一婚恋关系萌动阶段,女性意识的表现在于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进行引诱暗示,并在表面上将主动权放在男性手中。
许自昌 《橘浦记》[9]叙柳毅与龙女事,可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当柳毅传书使龙女脱离苦海后,龙女看上了柳毅,但是 “恐他形迹嫌疑,不肯应允这个亲事”(第二十二出 《遗佩》),龙女与洞庭君便趁着柳毅上京应试泊船之时,扮成了船客与柳毅“巧遇”。且看龙女如何行事。首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你看柳郎的船恰好泊在一处,待奴家只做无心在船头上玩月,看他怎么样再作区处。”确定柳毅看到她后,龙女先是 “回顾低介”,随即是若无其事地 “吃茶介”,待柳毅 “走出船去看他怎么样儿”,她又 “作惊介”、“作背生介”。至此龙女未发一言,已达到了第一层目的——引起柳毅注意。她通过 “回顾”表示有意,“吃茶”展示无情,“惊”、“背生”凸显娇羞,娇羞却又不回避,使柳毅认为她 “是个大雅的女子”,对她产生了兴趣,并想以 “借茶吃试他的心是如何”。面对柳毅借茶的试探,龙女的反应是 “低头不语介”却又“作偷觑生介”,前者是故作羞怯,后者是顾盼含情,欲拒还迎的态度引逗得柳毅进一步试探:“今夜得傍仙舟,这是有缘千里能相会了。难道茶也借不得一杯儿与小生吃不成?”龙女这才递茶给柳毅。柳毅 “喜琼浆饮”,说出了 “借蓝桥恨玉杵盟虚仙窟”的欢好试探。接下来就更精彩了:
龙女:奴家好意借你一杯茶吃,怎么说这许多话?那些都是姻缘上的故事,奴家今夜与相公邂逅邻舟,并无一些往来。正无缘对面不相逢哩!
柳毅:小娘子休说那些话来,可惜同对此明月相逢巧,难说道无缘情恝?
龙女:我不与你闲说,我自进船去罢!
(生作过船拽小旦)(小旦洒脱介)
柳毅:小娘子你看这等好月,忍得就去睡了?
龙女:相公,奴家是良家闺女,不是墙花路柳,你休得要如此造次。
柳毅:是小生得罪了。(揖介)
当柳毅一本正经地作揖行礼时,龙女反倒抛出 “惺惺忍把惺惺撇”的暗示、“你既有意奴岂无情”的明言,又后撤称自己乃是 “文君之新寡”,要柳毅遣媒妁方可成就姻缘,惹得柳毅若陷 “枯鱼之肆”。至此,柳毅完全陷入了龙女的 “圈套”。整个过程看似是柳毅处处主动,实则是龙女步步为营。这便是女性运用性别优势进行引诱和暗示的成功案例。设想,若是男子 “只做无心在船头上玩月”,会引得女子 “凰求凤”吗?
女性的性别优势还在于在男性的追求阶段,可以 “稳坐钓鱼台”,以不变应万变。清代张坚 《玉狮坠》传奇本事于宋传奇所述 “黄损”事,该剧中裴玉娥收到了黄损的情词,被其文采真情所打动,但她并未立即附和,而是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此生如果钟情,必然访问我们行踪,焉肯当面错过。倘竟不偢不倸而去,则直一轻薄之儿,亦可置之度外矣,不免熄灯而寝,且由他罢了。”[10]此处裴玉娥是极其明白的,她 “按兵不动”可以甄别出黄损到底是钟情还是轻薄,如果此时过于主动,则势必无法看清黄损的真意。总之,追求阶段的努力需要男性来完成,这便是女性的性别优势。
二、促成婚恋的切实行动
在一部分情况下,暗示和引诱是发挥作用的,这通常发生在女性对关系掌握主动权的时候,尤其是一段关系刚开始的萌动阶段。随着关系的进展,有时女性会由于种种原因,成为婚恋关系中的被动一方。此时,女性意识的体现便在于:首先认识到自己的被动局面,然后通过切实的行动促成婚恋。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认为郑光祖 《倩女离魂》中张倩女的离魂行为,是男权社会下女性意识的体现,同时也是男权社会下维护婚姻的无奈之举。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从唐代陈玄佑 《离魂记》到郑光祖 《倩女离魂》,王、张二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1]270《离魂记》中,王宙和张倩娘本为从小相爱的姑表兄妹,他们 “后各长成”,“常私感想于寤寐”,故而当倩娘被另许婚姻时,“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他们的感情是一致相通的。倩娘离魂乃是 “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故而王宙 “非意所望,欣悦特甚”。倩娘在这段关系中是掌握了主动权,并且王宙对此是深为感激的。但是,到了郑光祖 《倩娘离魂》中,王文举与张倩女的关系 “由相爱的青年男女的关系变成了士人心目中理想的男女关系:士人既是随时可另接丝鞭的婚姻优越者,也是给女性的一方带来 ‘驷马高车’、‘夫人县君’之荣耀的高高在上的荣誉施与者”。从剧作的诸多细节都可以看出张倩女在这段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张母一出场便交代张倩女与王文举乃是同僚间的指腹为婚,而两位做官者都已下世,官上加亲已无从谈起。对此,张母的态度是 “也曾数次寄书去”,希望王文举前来 “就成此亲事”,而王文举的态度则是往长安应举途中,顺便探望岳母。从双方态度的差别已经可以看出,是张母而不是王文举更盼望成就这门亲事。但是,张母却没有充分认清形势,反而是让张倩女出来 “拜为哥哥”,要他 “但得一官半职,回来成此亲事”。张母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女孩儿需 “婚嫁及时”;二是王文举高中后 “另婚高门”的可能。这些张倩女都意识到了。
作者在 “楔子”中已经点明,张倩女已经一十七岁了。所谓 “青春易老,佳配难逢”、“万种娉婷,二八青春富盛”(无名氏 《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第三出 《计议招婿》),据考证,“18岁是元文人心目中女性适嫁的最高婚龄”[11]44⁃45, 张倩女已经很接近了。此时王文举和张倩女,一个是 “矫帽轻衫小小郎”,一个是 “绣帔香车楚楚娘”,如倩女所言是 “恰才貌正相当”(《楔子》)的。而如果要王文举得中回来再成就婚姻,势必会增加张倩女 “婚嫁失时”的风险,以至于 “虚过了月夕花朝”(《第一折》)。相应的,王文举一心只在功名,“只为禹门浪暖催人去,因此匆匆未敢问桃夭”(《楔子》),并未将张倩女真正悬望心上。这从同样是 “拜哥哥”,他与 《西厢记》中张君瑞的反应截然不同便可以看出。况且,张倩女见了王文举是 “神魂驰荡”,王文举对张倩女的反应却只字无有,想来张倩女是没有像崔莺莺那般令人惊艳的。因而,如果王文举 “一举把龙门跳”后,“别接了丝鞭”(《第一折》)是完全有可能的。
张倩女在这段婚恋关系中落入被动,她的 “离魂”正是基于这个前提所采取的促成婚恋的切实行动,这是男权社会下维护婚姻的无奈之举。王文举“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私自赶来,有玷风化”的 “振色怒增加”反应,也正说明了他在婚恋关系中的主动地位。倩女离魂的行为,为的是变相地“行监坐守”,防止王文举 “新婚燕尔在他门下”。将这一层说破了,张倩女又表示倘若不中,“荆钗裙布,愿同甘苦”(《第二折》),于是王文举也便无法拒绝了。如果张倩女没有离魂相随,王文举会不会得官别娶真是说不准的事情,而到了那时,已经“婚嫁失时”的张倩女怕是连不得中的王文举也再觅不着了。正是因为张倩女洞悉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处境,才确保她与王文举顺利 “成其亲事”(《第四折》)。但是,这种女性在婚前就丧失主动权的婚恋模式,从理性角度是不被看好的。由于 《倩女离魂》的故事到 “成其亲事”戛然而止,婚后王文举和张倩女的生活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婚前便处于被动地位的张倩女,在婚姻生活中是更没有主动权的,这是由于伴侣价值失衡所造成的。
三、对婚姻关系的维护
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大概可以概括为 “为女而能贤,为妇而能孝,为母而能慈”①(元)马祖常 《石田集》卷12《安定郡夫人王氏墓志铭》。,夫妻的相处好坏在大多数时候是排除在典论之外的。但夫妻关系作为家庭的基石,和谐与否对家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自古便有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对于婚姻关系的维护主要是在于女性。对此,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是,繁育后代的压力使得女性在绝大多数时候需要借助男性的资源投资。而跨文化的数据表明,女性对于后代的投入是远远高过男性的。根据亲职投资理论,在养育后代上投入更多的一方会更谨慎、更在意关系的维护,而对后代投资较少的一方,则倾向于广撒网。②这一理论由罗伯特·特里弗斯 (Robert Trivers)1972年提出,并由威尔逊 (Wilson)1975年确立。这也就决定了女性会是婚姻关系中起主要维护作用的一方,现实确实也是如此。男性善于进攻,女性善于守成,原始社会的分工便是这般。一段婚恋关系的走向中,男性往往更容易受到社会、家庭乃至其他女性的影响,其选择是多方力量角逐后的自然结果。对于在婚恋中遭遇的困难,男性也很少有主观的反抗意识。这是因为广撒网的本性使男性将婚恋视为人生中的一部分,远不如女性看得重要。
在戏曲舞台上,展现曲折恋爱过程、以成婚团圆的作品要大大多于展现婚后生活的作品。“霍小玉”的故事在婚后的生活上着墨较多,加之后世的改编本众多,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版本中感受到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维护婚姻关系的不同方式。由黄文锡创作的赣剧 《紫钗记》[12]是以汤显祖本为蓝本,结合了蒋防 《霍小玉传》的相关内容改编而成的。剧中霍小玉看似懦弱的隐忍,实则是为她打赢一场婚姻保卫战的关键。李益被卢太尉遣往玉门关任参军,霍小玉表示不想让仓促而就的婚姻耽误李益的鹏程之路,“愿遗忘箫鼓画堂燕子妻夫,从此相疏”。这在进化心理学的择偶策略中被称为 “后撤”。正处于情浓似火、两心欢洽之时,女性的后撤会换来男性的承诺。果然,李益随即表示情坚如石、不需多虑。霍小玉又趁机道出了身世之谜,适时地将可能存在的问题抛给了李益,可谓是时机成熟的破釜沉舟。如果李益不能接受,那么趁早分手,也免得自己再存念想、千里悬望。不过,既然李益已经承诺在前,此时霍小玉提出的任何难处,李益都是要进一步表忠心、做出长期承诺的!即便退一万步讲,就算日后李益因为种种原因真的会负心霍小玉,也会因他曾经做出的承诺而背上沉重的良心枷锁。因而表面上看,这段婚恋关系的决定权在李益手上,并且也确实由他做着选择,但实际上处于地位劣势的霍小玉才是关系的操控者。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 “成功的中国妇女学会了主要依靠自己,但同时表现得依靠丈夫”。老子所谓 “柔胜刚,弱胜强”(《老子》第三十六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正是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之道!
如果说赣剧 《紫钗记》中我们主要关注了女性对于婚姻关系内部的维护。从唐涤生粤剧 《紫钗记》[13]中的 “争夫”到吴兆芬越剧《紫玉钗》[14]中的 “索夫”,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面对外部势力破坏婚姻时所做的坚决维护。粤剧版 《紫钗记》中,霍小玉不同于汤本中的 “落拓贵族”,在历经荣辱贵贱的变迁后,粤剧版霍小玉在性格上少了几许天真、任性,而多了一丝成熟、世故。她希望通过李益这样一个有为的夫婿来为自己争回一口气,也能让母亲 “归霍家耀晚景”。虽然在误以为李益负心的日子里,霍小玉感受不到自身的价值,但一旦明了 “薄命非关郎薄幸”后,痴情与刚烈促使她定要找机会争取回本属于自己的夫君。“论理争夫”是粤剧 《紫钗记》的高潮,霍小玉 “既有高傲复自卑的性格,使她有一份刚烈和果敢,所以才会拼死在华堂争婚”[15]。
相较于粤剧版中霍小玉心思的幽微深曲,越剧《紫玉钗》中的霍小玉则要纯粹得多,却在女性意识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洞悉了男权社会后的淡然、理性、机敏。贵贱荣枯的相易,使得霍小玉参透人情,淡看宠辱。她敬慕李益的才华,引为神交知己,见面后又看中他 “书卷气中含风骨”的品格,故而霍小玉故意遗落紫玉钗,以鲜明的自主意识和完美的策略引诱李益。二人相恋后,小玉也曾有过一丝色衰情移的担忧,但担忧的根源并不是对自己的日后生活产生远虑,而是出于彻悟世情的通透。她以 “生死情守俱从容”的气魄和胆识,敏锐地看出了卢府威逼招亲的阴谋。于是她戴凤冠、披霞帔,理直气壮地前往卢府 “索夫”。越剧版的 “索夫”与粤剧版的 “争夫”虽一字之差,却向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更进了一步。
上文通过对唐宋婚恋传奇的戏曲改编进行个案分析,简要地叙述了在男权社会婚恋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这里还有几句题外话:男权社会延续了上千年直至今日,女性在其中的生存法则已经根植在了基因里。虽然本文将关注点放在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与男性的博弈,但同时需要意识到的是,无论是在历史还在当下,男权社会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和桎梏,来自女性群体的并不比来自男性群体的少。因为,“男人间的自然情感顶多表现为相互冷漠,而女人间则就充满了敌意,原因在于同类间的嫉妒心”[16]。只是,女性的话语消失在史册之外,我们对女性的了解来自男性的揣度和转述,可是男性对于女性到底又能了解多少呢?这无疑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徐大军.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268⁃269.
[2]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 [M].上海:上海书店,1997:48.
[3]马杰里·沃尔芙.台湾乡村的妇女和家庭(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M]//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胡志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51.
[4]奥利维娅·贾德森.性别战争[M].杜然.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前言.
[5]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27.
[6]杨冰阳.完美关系的秘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2.
[7]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猿猴的把戏——动物学家眼中的人类关系[M].吴宝沛.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36.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3.
[9]许自昌.橘浦记 (北京图书馆藏日本景印明刊本)[M]//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
[10]张坚.玉狮坠 [M]//张坚.玉燕堂四种曲 (清乾隆间刻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1]张维娟.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黄文锡.黄文锡剧作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
[13]叶绍德.唐涤生戏曲欣赏[M].香港:香港周刊出版社,1987.
[14]吴兆芬.毋忘曲——吴兆芬剧作选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15]刘靖之,冼玉仪.粤剧研讨会论文集 [C].香港:三联书店 (香港)公司,1995:448.
[16]叔本华.叔本华文集:悲观论集卷 [M].王成.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35.
(责任编辑:周立波)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Study of Drama Adaption from the Love and Marriage Stories of Chuanqi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YANG Yu
The rules of male dominated society are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maximization of male interests.The expression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refers to the women’s awareness of their own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use of gen⁃der advantages to choose a reasonable way of life.The description of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bega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 the later drama adaptation.Either the lure of germinating stage, the effective action contributed to the marriage, or the maintenance of marriage, we can find typical cases from the drama adaption from the love and marriage stories of chuanqi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emale consciousness; love and marriage stories of chuanqi in the Tang and Song; drama adaptation
J809
A
1672⁃2795 (2017) 02⁃0070⁃05
2017-03-15
杨玉 (1988— ),女,江苏泰州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主要从事戏曲文学史、电视戏曲栏目研究。(北京 100024)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