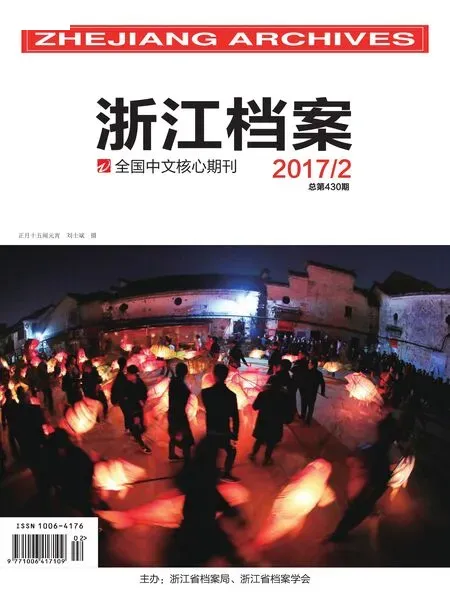身份认同对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及其趋势
朱 莉/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仅涉及政府的职责、能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还能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1]。随着档案观念开放程度的加深,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积极寻找各种能让档案回归大众、服务社会的契机;档案与知识、记忆、族群历史的相关研究深入开展,使档案价值得以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之中,身份认同这一关乎公众身份感、归属感的深层认知问题,促使档案与更多学科、更广泛人群发生新的联系。文件和档案在构建历史、集体记忆和国家或民族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涉及到看待个体身份、集体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方式[2]。将档案、社会或集体记忆、身份认同三者联系起来,能够实现档案记忆属性在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延伸[3]。
1 身份认同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转变
集体记忆常常是联结档案和身份认同的纽带,它使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得以确立,为公众获得身份认同提供了一条实现路径[4]。日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播出的《致我们正在消失的文化印记》节目,从徽州乡音的重拾之中,找到现代人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丢失的归属感与幸福感;通过数字化摄录手段采集的徽州方言样本,成为不被时间磨灭的徽州韵味。档案部门在历史文化记忆工程的语言建档工作中,汇集地区特质和风貌,达到地区思想文化与观念集体认同的目的。
1.1 开发理念的转变
正确的开发理念有助于更好地将档案工作者与民众结合在一起,共同参与身份认同式的档案资源开发,以民众建构属于自己的家庭记忆为导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协同开发、多元化开发,开辟档案惠民利民的实现途径。档案资源收集的主题随着社会网络世界的丰富与脆弱、真实与虚幻、个体角色的多重性与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档案新的人文价值,人们对精神归属的追求与迷茫,需要档案价值中的身份认同来实现和消除。法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经历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是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5]。自2008年国家档案局提出“建立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以来,档案部门尝试构建共享集体记忆库,把档案收集与保存的范围向公众扩展,使不同群体(特别是曾经被遗忘的边缘群体)实现身份认同的诉求能够从档案中获得帮助。加拿大图书和档案馆国家档案发展计划(NADP 2006—2011)的目标之一是“增加代表性不足的种族文化团体在加拿大档案遗产中的代表性”,为此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原住民、少数族裔档案保存和利用工作的开展[6]。20世纪以来,档案工作者以理性的职业自觉走出封闭状态,形成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寻找各种可能让档案回归大众、服务社会,促使档案与更多学科、更广泛人群发生新联系。
1.2 开发方式的转变
身份认同有纵横两个不同维度,即在历史的追溯中找到相同的社会基因,在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文化比较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这种追溯和判断需要以真实连续的信息为基础。档案部门在档案信息资源联结身份认同中,通过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整合,能够认识到身份认同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呈现出档案对公民身份认同的独特影响,并且积极通过构建集体记忆来建立身份认同的桥梁。目前档案部门主要以网站作为平台,对资源进行整合与分享,并实现与民众的对接与互动,即档案部门提供身份认证与认同的平台,汇集多种多样的资源;民众则根据自己的意愿与兴趣,进行身份认同式的找寻与利用,寻根问祖与构建记忆并用,实现新观念下档案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广泛传播。
沈阳市家庭档案研究会建立了家庭档案网,公众以家庭为单位,放置家庭照片、记录家庭琐事、构建家庭记忆,通过上传分享的方式参与到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探索中,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找寻到家庭的认可与包容。档案一方面为身份认同提供追踪性、连续性素材,另一方面为身份认同的结构分析提供多视角、多层次的素材。在国外,登录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网站中的“Genealogists”进行专题检索,不仅能看到1940年的人口普查档案,还能参与利用家族档案寻找祖先的活动,并且在论坛中关注话题,促使在构建家族记忆中关注新群体,在家族记忆之外构筑新的集体记忆;档案部门提出需要民众参与档案整理,并呼吁更多关注家族档案的社会公众参与档案部门的工作。个人自助的档案资源开发与共享将政府与公众成功地联结在一起,加快档案资源挖掘的收集与利用,这项工作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鼓动与“拉拢”,它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支持,民众愿意主动参与进来。
1.3 开发效果的转变
档案作为以国家、地区、族群为单元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能够支撑人们确认“我们”和区分“他者”。档案网站利用构建家族记忆对家庭成员进行身份认同的契机,对档案资源进行一门一户的对应与追寻,用一份份家庭档案诉说一个个家庭的故事。从沈阳家庭档案网数据来看,沈阳家庭建档的创新实践在业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国内各地区共3000多位档案工作者以及来自美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的外国政府代表团和档案工作人员前来参观考察家庭建档工作[7]。家庭档案网站已经成为沈阳市的一张城市名片,在外乡的沈阳人同样可以在网站中建设与找寻自己的家族记忆,在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个集体”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所属群体的熟悉感,获得归属感的满足。从文化角度讲,在个体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能够促使个体积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家庭档案网站开办8年多,已有15万多户家庭建立家庭档案,网站以家庭档案为素材,组织出版了家庭档案管理专著,此举大幅提升了公民的档案意识,推动公众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并使大量的家庭建档成果成为民众身份认同的记忆堡垒。此外,网站还组织开展志愿活动、举办家庭档案展览等,吸引更多民众利用档案进行身份认同。
2 身份认同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评价
2.1 载体单一,影响力不足
以家庭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为例,沈阳市家庭档案网站建设较为完善,能够不断地扩展影响力,并进行新闻、活动等信息的实时更新,目前包括论坛会员在内,网站会员已达12万人之多。但我国家庭档案开发多局限于建档、查档的层面,对于开展身份认同的贡献并不突出,在覆盖率并不是很广的前提下,难以高效捕捉相关的信息。在新媒体应用中,对于微博与微信两大平台的应用明显不足,特别是微博影响力较低,没有进行“加V”认证,内容多为转发,原创性不足,特别是缺少对家庭档案建设等问题的探讨,为数不多的245条微博(数据截至2016年10月31日下午15∶00),没有体现家庭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的号召力与吸引力,也没有推行身份认同观念。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非睡眠时间内,人均每四分钟就要查看一次手机;每天花在社交软件(如推特,脸书)上的时间,占花在手机上总时间的24%[8]。因此,我国可积极利用手机APP开展家庭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为公众利用碎片时间找寻自己记忆、构建家族记忆提供方便快捷的平台,并采取措施提升公众对于家庭档案“口袋服务”的满意度。
2.2 覆盖面较窄,针对性不强
囿于传统的档案工作思维,以及档案工作机制体制的局限,身份认同在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中显出“被选择性遗忘”的特点,档案馆主要收集并保存反映主流思想、主流文化的材料,对于反映边缘文化的材料没有予以足够重视,没有及时收集并妥善保管,带来的后果是,档案构建社会记忆的功能难以发挥。比如,针对农民工这一群体,一方面,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农民工普遍缺乏档案意识,且不具备留存档案材料的条件,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价值的材料或遗失或损毁;另一方面,档案机构对农民工形成的档案材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加之农民工档案不属于人事档案的收集范围,现实中,除少数用工单位保留有少量的农民工出勤务工记录外,其他更有价值的材料没有留存下来,农民工难以利用档案进行身份认同。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对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发现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观念开放,更向往和习惯城市生活,因农民工档案缺失,他们的心理冲突更为激烈,身份认同危机更为凸显[9]。所以,档案资源建设覆盖面还有待拓展,其针对性有待加强。
3 身份认同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方向
3.1 制定相关政策,推动身份认同策略
身份认同的过程主要基于信息分享的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分享,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则难以维系。因此,笔者建议应予公民获取自我认知信息的权利,从而推动相关政策的施行,尽可能地扩大档案的开放与共享,把更多档案信息归还给广大公众。此举符合社会公平、公正、公开的要求,也满足公民参与档案资源利用、改善身份认同的诉求。目前,我国档案开放程度有待提高,笔者建议我国实行如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样有利于信息公开透明的举措。其中,针对民众身份认同的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还需要新的策略,以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覆盖率与针对性,更多地关注边缘群体、关注公民本身,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长期开发,促进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3.2 扩大档案馆藏,关注边缘群体
对于档案馆而言,广泛的馆藏档案来源至关重要,这也是确保档案证据价值和知识价值的基础,以及公众身份认同的基础。当今一个重要趋势是档案资源收藏范围向公众扩展,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能够从档案中获得帮助。为各类群体特别是曾经被遗忘的边缘群体建立档案,是本世纪国际档案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内容,如上所述的加拿大图书和档案馆国家档案发展计划(NADP 2006—2011),其目标之一是“增加代表性不足的种族文化团体在加拿大档案遗产中的代表性”,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原住民、少数族裔档案的保存和利用[10]。我国也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档案资源再收集与再利用工作,扩宽档案事业的发展渠道,使档案工作切实贴近民生。
3.3 加大技术投入,拓展档案业务
借助档案资源帮助公众形成多元认同是档案工作参与社会建构、扮演“要素角色”的重要举措,档案触发公众心理感受和增进自我认同的过程可以给档案事业带来增益。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转向为“新媒介—用户”关系,信息、知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主要资源。由于媒介的融合,信息的传播方与接受方的身份不再具有明显的区别,每个人既可能是信息的制造方又可能是信息的传播方,同时又扮演着信息接受方的角色。档案资源的身份认同工作需要借助新媒体的蓬勃之势开展,形成新技术引领的局面,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保障,并效仿先进案例,如著名数据库开发商Pro Quest公司开发的美国档案(Archives USA)在线遗产探寻(Heritage Quest Online)(图书、档案及其他信息综合数据库)等,融入大量先进技术,为工作开展提供助力,推动工作快速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特里·库克.1989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2]Schwartz JM, Cook T.Archives, records,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 [J].Archival Science,2002 (2): 1-19.
[3]冯惠玲.张斌,徐拥军,等.多学科视角下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进展[A].创新:档案与文化强国建设——2014年档案事业发展研究报告集[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4]Ketelear,E.Archives.“Memories and Identities”[M].//Caroline Brown.Archives and Recordkeeping:Theory into Practice.London:Facet,2014:784.
[5]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
[6]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97-103.
[7]邹大挺.在沈阳市家庭建档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3-01-29)[2016-09-07]http://www.jtdaw.com/jdsj/ldjh/content/bd2109df 3c386d9a013c83e05daa0294.html.
[8]每日邮报:研究发现人均每四分钟看一次手机[EB/OL].(2016-02-26)[2016-09-07]http://www.199it.com/archives/441784.html.
[9]中国新闻网.全总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EB/OL](2010-06-21)[2016-09-07].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6-21/2353233.shtml.
[10]Summative Evaluation of National Archive Development program.Approved by LAC Evaluation Committee [EB/OL].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obj/012014f2/012014-297-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