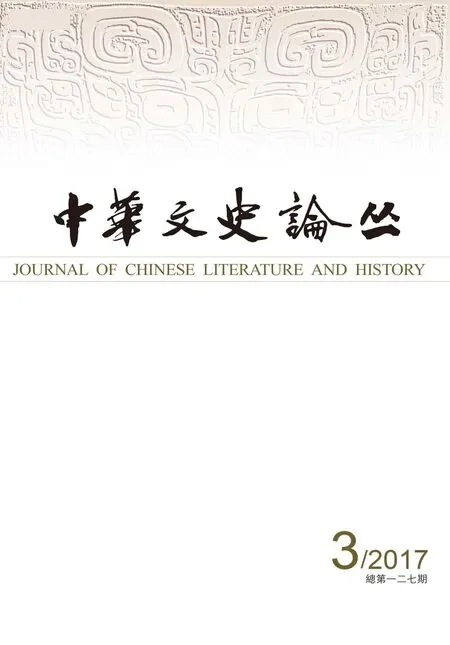論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
——兼論“牛李黨爭”的起因
周 浩
提要: 元和三年制舉,牛僧孺因反對削藩被選爲對策第一,是“放棄河北”的集體意識與反對削藩勢力對主戰派的抗爭;因此引起主戰的憲宗以及李吉甫、吐突承璀等人不滿。《舊唐書》此案相關記載中,憲宗態度比較曖昧;《通鑑》則對憲宗形象進行維護,將一切都轉嫁到李吉甫身上;《舊唐書》、《通鑑》遺漏、改寫了一些重要細節;《新唐書》則明確書寫了憲宗的不滿,代表了修史者的看法,是較爲合理的。《唐會要》、《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的記載,較爲真實地還原了事件的經過。
關鍵詞:元和三年制舉案 憲宗 反對削藩 事件過程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舉行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制科考試,應試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人對策,指摘時政,言辭激烈,被考策官擢爲上第,引起在上當權者的不滿,致使考策官、覆視官均被貶黜,牛僧孺等三人也受到排斥,久不升遷。這次制舉案,與後來的“牛李黨爭”形成有極大關係。
這次制舉案中牛僧孺等攻擊的對象,由於史料的闕失,歷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有認爲是針對宦官的,近人岑仲勉、唐長孺、傅璇琮、何燦浩、王炎平、金瀅坤等均持此論,他們的基本依據爲皇甫湜策文、李翱所作楊於陵墓誌以及史籍中“貴倖”、“權倖”的説法;*參見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429—430;唐長孺《唐修憲穆敬文四朝實録與牛李黨爭》,載《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16—223;傅璇琮《李德裕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0—59;何燦浩《元和對策案試探》,《南開學報》1984年第3期;王炎平《牛李黨爭始因辨析》,《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金瀅坤《論元和三年制舉科場案——兼論牛李黨爭之發端與影響》,《人文雜誌》2015年第8期。有認爲是因反對削藩而針對李吉甫與吐突承璀等主戰派的,陳寅恪、胡如雷、丁鼎、李潤强等持此論,他們的主要依據有杜牧所撰牛僧孺墓誌銘、白居易《論制科人狀》,*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98;胡如雷《唐代牛李黨爭研究》,《歷史研究》1979年第6期;丁鼎《牛僧孺年譜》,瀋陽,遼海出版社,1997年,頁66—76;李潤强《牛僧孺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05—108。認爲反對削藩的,推測較簡單,並無具體論述。另外,馮承基《牛李黨爭始因質疑》一文認爲,譏刺李吉甫者爲皇甫湜,而非牛僧孺。*馮承基《牛李黨爭始因質疑》,《臺大文史哲學報》1958年第8期。
筆者在《新輯牛僧孺賢良策文考釋》中,重新輯出完整的牛僧孺策文,並與皇甫湜策文作對比,認爲牛文對宦官與宰相均有指責,但以影射爲主,較委婉;皇甫湜文激烈而直接,直指宦官、宰相、百官之過,更易引起宦官與宰相的不滿。*參見周浩《新輯牛僧孺賢良策文考釋》,《唐史論叢》第20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頁199—217。
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礎之上,對元和三年制策案中牛僧孺策文的作用、憲宗的態度以及事件的過程進行探討。
一 該次制策牛僧孺爲第一
前引筆者《新輯牛僧孺賢良策文考釋》指出,皇甫湜文章比牛僧孺激烈,更易引起宦官及宰相的不滿。金瀅坤認爲此次制舉案,並非牛僧孺引起,而是朝中抵制削藩勢力和倒宰相李吉甫勢力借題發揮,導致李吉甫罷相,貶謫考官、覆試官。*金滢坤《論元和三年制舉科場案——兼論牛李黨爭之發端與影響》,頁89。但是,現存許多記載,與金氏論述是相牴牾的。
如果説皇甫湜的對策更爲直言極諫、更爲激烈,那麽在這次對策案中,皇甫湜的策文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應該以皇甫湜爲第一,諸處記載也應以皇甫湜爲首纔對。但是,現存的資料顯示,關於元和三年對策案的相關記載,除《舊唐書·憲宗紀》與《裴垍傳》之外,均以牛僧孺爲首,可見牛僧孺策文在這次對策案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現存六條唐代的材料,均以牛僧孺爲當年制舉人之首。一是制舉案發生後不久,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爲被貶諸人鳴寃。其中提到被録取的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三人時,均以“牛僧孺等”代替,“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奬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關外官”,“若以爲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3326,3327。這表明,當時即公認此次制舉案中,僧孺爲最關鍵之人物,其策文爲引起此次事件的焦點。
二是杜牧《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明言:“應賢良直諫制,數强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吴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01。
三是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明言:“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全唐文》卷七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7406上。“冠甲科”,點明牛僧孺爲第一名。
杜牧曾爲牛僧孺淮南節度掌書記,李珏曾爲牛僧孺武昌節度掌書記,均與牛僧孺有親身接觸,所知當爲可靠。後人多有指責杜牧、李珏在墓誌銘中爲僧孺避諱,但是,此處不可能虚美而謊稱第一名。因獲得頭名,必然衆所周知,不容僞托;且杜牧、李珏與僧孺同時代,了解當時情況之人尚多在世,怎容僞造?制科登第,已爲榮耀之事,若果真不是第一名,大可不必僞造。
四爲《太平廣記》卷四九七引《乾?槗7子》記載云: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敕頭。”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太平廣記》卷四九七,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4080。
這條記載明言牛僧孺“制科連捷,忝爲敕頭”,即是第一名。無論這是牛僧孺的原話,還是他人所言,都表明在唐代人的認知中,牛僧孺爲此次制科登第者之首。
關於“敕頭”,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六章《制舉》中指出:“按照唐代慣例,制舉登第大致分五等,但第一、第二等是向來没有的,第三等就稱甲科,或稱敕頭。”*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42。該書第七章《進士考試與及第》又説:“制科分五等,第一、第二等向來不授人,以第三等爲敕頭。”*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180。按照傅氏所論,則第三等即甲科,而凡屬第三等者均可稱敕頭。王勛成《唐代舉子及第登科等第考》一文提出不同看法,認爲傅氏此説有誤。他在文中指出:“制科雖分五等,但第一等從不授人,第二等自開元以後也不再授人,於是唐人便將第三、第四、第五等就又分爲五個等次;第三等和第三次等,俗稱甲科;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統稱乙科。只有甲科第一名,同時又是此年制舉諸科之首者,纔可稱作敕頭。”*王勛成《唐代舉子及第登科等第考》,《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頁112—113。他所舉“敕頭”的例子有天寶十三載(754)楊綰、元和元年(806)元稹、長慶元年(821)龐嚴、寶曆元年(825)唐伸、大和二年(828)裴休,論證頗爲有力。其實,牛僧孺的例子,可爲王氏之説作一補證。杜牧所撰墓誌銘説牛僧孺應制科“詔下第一”,李珏所撰神道碑説牛僧孺“冠甲科”,所謂甲科,即第三等,而第三等尚有皇甫湜、李宗閔等人,故言“冠”,以明確其第一名的身份。這與《乾?槗7子》“敕頭”的記載相吻合,而與王氏所論相符,可證制科第三等甲科所取之人,只有第一名方稱敕頭。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壬午歲與董琴南書》言:“陸贄、裴度諸公,高擢賢良,亦僅簿尉。惟元微之以第一授拾遺,而元和三年敕頭牛僧孺與李宗閔、皇甫湜並注關外畿尉。高才大科,所得如是,他可知矣。”*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清代詩文集彙編》(5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395上。將牛僧孺稱爲“敕頭”,與皇甫湜、李宗閔區分。唐代制舉關於“敕頭”,尚有以下幾則材料,可資參證。唐趙璘《因話録》卷三載:
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敕頭孫河南穀,先於雁門公爲丞。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贈封雁門公。*趙璘《因話録》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84。
按《登科記考》卷二一開成三年(838)載趙璘當年中博學宏詞科,*《登科記考》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778。八人之中,孫穀爲“敕頭”。《唐摭言》卷二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王定保《唐摭言》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8。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五載: 崔元翰“晚年方取應,咸爲首捷: 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敕頭、制科三等敕頭”。*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三五,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185。結合與解頭、狀頭並列而言,此處的“敕頭”即指制科三等中的“第一名”。宋錢易《南部新書》甲載:“韓昆,大曆中爲制科第三等敕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翠籠,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錫繒帛,以示殊澤。”*錢易《南部新書》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丙卷載:“裴次元,制策、宏詞同日敕下,並爲敕頭。時人榮之。”*錢易《南部新書》丙,頁35。這兩條均與《唐詩紀事》用法相同。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閨秀集》下指出:“案: 唐時舉宏詞第一謂之敕頭,原本‘敕’訛作‘初’,又脱去‘頭’字,今據《文獻通考》改正。”*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54。以上論述表明,牛僧孺確爲當年制科第一名。
五爲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在所作《和答詩十首并序》中言:“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惟與杓直拒非及樊宗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白居易集箋校》卷二,頁105。
六爲元和十年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云:“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白居易集箋校》卷四五,頁2792—2793。
這兩條材料,都是白居易在寫了有所興寄、諷刺時事的詩歌之後,或被人勸,或自己忖度,以牛僧孺元和三年對策事爲鑑戒,以免開罪權貴與在上位者,身受其禍。白居易爲元和三年制舉案覆視官之一。在《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詩中自注:“元和初牛相公應制策登第三等,予爲翰林考覈官。”*《白居易集箋校》卷三一,頁2104。兩次言“牛僧孺戒”,這裏又提及,表明牛僧孺在元和三年對策案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是唐代的材料,表明牛僧孺在元和三年制舉登第人中是第一名,在此次制舉案中發揮的作用最大。
唐以後的材料,如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基本史書,以及其他記載,除《舊唐書·憲宗紀》、《裴垍傳》,《新唐書·裴垍傳》、《李吉甫傳》以皇甫湜居首,《新唐書·牛僧孺傳》言“俱第一”外,其餘所有記載,均以牛僧孺居首。《唐會要》卷七六有此次制舉登第人員名録:“二年(按: 當爲三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宏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袞、庾威及第。”*王溥《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645。《册府元龜》卷六四五所記與此全同,《太平御覽》卷六三所記人名與順序全同,並改二年爲三年。清岑建功《舊唐書佚文》卷八指此條記載爲《舊唐書》佚文。清徐松《登科記考》卷一七即依此順序著録當科登第之人。
《舊唐書·憲宗紀》、《裴垍傳》和因循《舊唐書·裴垍傳》的《新唐書·裴垍傳》以及《新唐書·李吉甫傳》爲何將皇甫湜記載在前?《舊唐書·憲宗紀上》載此事曰: 元和三年夏四月“乙丑,貶翰林學士王涯虢州司馬,時涯甥皇甫湜與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語太切,權倖惡之,故涯坐親累貶之”。*《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頁425。這裏,因爲提到王涯,所以將王涯之甥皇甫湜提到牛僧孺的前面。而《舊唐書·裴垍傳》之所以將皇甫湜提前,應該是代表了一種少數的意見,也反映了一部分的事實,即如上引李潤强在《牛僧孺研究》中所作的推測,皇甫湜的策文因指斥激烈在此次對策案中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他正是因此而受打擊。而《舊唐書》這兩處雖先敍皇甫湜,後敍牛僧孺、李宗閔,但對於三人登第名次,並未特别説明。《憲宗紀上》言“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裴垍傳》言“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舊唐書》卷一四八《裴垍傳》,頁3990。都只强調三人在同一等級。而《新唐書·李吉甫傳》將皇甫湜提前,則因對結黨的牛僧孺、李宗閔有偏見(下文將詳述)。另外,在以上記載中,雖因一些原因將皇甫湜排在前面,但未明言其爲第一,除此之外的材料,也没有明確記載皇甫湜爲第一。而在當時人的認識與記載中,起主要作用的,應該是牛僧孺。
《新唐書》卷一七四《牛僧孺傳》云:“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新唐書》卷一七四《牛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229。此一記載殊不合理,因諸處或言牛僧孺第一(如杜牧、李珏、《乾?槗7子》),或言牛僧孺等升上第(如《舊唐書·韋貫之傳》),或言登第三等(如《舊唐書·憲宗紀上》),“俱第一”的説法,既無來源,與他處相悖,又不合情理。所謂上第,即第三等,即甲科。如果理解爲俱上第或俱第三等,則可通,但依然是牛僧孺居首。
二 牛僧孺與皇甫湜策文的根本差異
現在來看牛僧孺策文爲何會起到關鍵作用。上節引最新研究已指明,皇甫湜策文言辭激烈,直言宦官之禍與朝政之失;牛僧孺策文則言辭委婉,雖有譏刺,但並不顯言。而這樣一份策文,卻被選爲登第頭名,説明當時人認爲在此次制舉案中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細按策文,惟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此文反對削藩戰爭。
將皇甫湜與牛僧孺策文比較,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即對於戰爭與軍隊的態度。皇甫湜注意到軍隊的腐敗無能,認爲當時國家並未安定,内憂外患,不可罷兵,故需要整頓軍隊,揀擇精銳,淘汰冗員,加强訓練,以實現强兵的目的。皇甫湜在策文中説:
且天下所以葸葸然者,豈非以兵乎?使税之厚、人之屈而不可蠲復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賄以結恩澤,因循鹵莾,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事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敎閲,簡奮勇秀出之才,去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事,可省其五矣。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府虚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没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分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虚,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强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清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徭、蕩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不四三年,而家給人和,則横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皇甫湜《皇甫持正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78册,頁81上—下。
他並没有反對削藩的意見,相反,强調要加强軍隊組織的合理化,提升戰鬥力。
牛僧孺則明言反對削藩戰爭,並且所言的對象,不是某一宰相或某一將領,而直接是天子:
臣以帝王之難不在此。夫難者,一則持盈,二則定傾。所以九廟有不遷之宗,表定傾之難也;賓陛有二王之後,表持盈之難也。今陛下定傾之功,揭日月矣;持盈之道,頗有誠難。夫富於春秋,誡在黷武;果於英斷,誡在尚刑;深居無事,誡在好逸遊;宇内清平,誡在侵邊鄙。戒之不倦,政之不違,乃至於陰陽交和,父不哭子,帝王之功,臻是而至矣。*《牛僧孺賢良策》,《增注唐策》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61册,頁793下。
相比策文其他地方的隱諱而言,牛僧孺在表達自己反對用兵的意見時,直言不諱、毫無保留,態度明確。
在對待戰爭的態度、是否應該積極用兵削藩這一點上,牛僧孺與皇甫湜截然不同。而這惟一的鮮明不同,使牛僧孺策文成爲此次對策案的關鍵所在。
三 憲宗的削藩意圖與用人原則
孟彦弘《“姑息”與“用兵”——朝廷藩鎮政策的確立及其實施》一文,對安史亂後,朝廷與藩鎮之間的對抗以及策略的變化過程,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該文指出,德宗建中用兵失敗之後,朝廷逐漸形成了以“河朔故事”爲基本原則的藩鎮處置策略;這一策略的核心内容,即“放棄河北,控制其餘”;這一理性務實的策略在憲宗用兵之後,成爲明確的國策被堅決執行。這種意識,憲宗朝的大臣比憲宗本人提前具備。憲宗在位期間,不僅是想平定一般藩鎮,而且始終想收復河北三鎮,但收復河北三鎮的想法,從一開始就一再受到朝臣的反對。元和四年末討王承宗,李絳、白居易等多次上疏,堅決反對,憲宗一意孤行,討伐失敗;元和十年,因武元衡被殺,憲宗再次討伐王承宗,張弘靖、韋貫之、李逢吉等均表示反對,最終因戰事不利而罷。憲宗在位期間,都在與朝廷中放棄河北三鎮、區分河北三鎮與其他藩鎮的意識作鬥爭,而具有這種意識的人,是絶大多數,除上舉數人之外,尚有韓愈、李德裕等人。*詳參孟彦弘《“姑息”與“用兵”——朝廷藩鎮政策的確立及其實施》,《唐史論叢》第十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頁115—145。在這個大背景下,牛僧孺反對削藩,引發了制舉案。
憲宗是中唐時期較有作爲的一位君主,元和三年之前,就先後平定夏綏楊慧琳、西川劉闢、浙西李錡,與德宗貞元時期對於藩鎮的姑息政策,大爲不同。這對他平定藩鎮起到了巨大的激勵作用,促使他意圖統一全國,恢復唐王朝之前的盛況。終憲宗一朝,所任用的宰相,如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裴垍、裴度等人,均力主削藩,並爲之建言獻策,努力踐行。關於李吉甫在元和年間,爲憲宗所信任,幫助削平藩鎮,出謀畫策的過程,傅璇琮先生在《李德裕年譜》元和元年至九年的譜文内,有詳細介紹。憲宗所親信並甚爲倚重的宦官吐突承璀,也是削藩大計的積極支持者與執行者,此一點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已有論述。
憲宗對於因循保守、反對或破壞削藩行動的大臣,堅決罷免,以利其削藩政策實施。元和四年二月,憲宗削藩大業尚未完全展開時,就罷免了因循而無所作爲的鄭絪。在處理李錡事件時,鄭絪是主張姑息的。《舊唐書》卷一五八《武元衡傳》載:
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姦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兹去矣。”上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舊唐書》卷一五八《武元衡傳》,頁4160。
《舊唐書》卷一五九《鄭絪傳》載:“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黄裳同當國柄。黄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舊唐書》卷一五九《鄭絪傳》,頁4181。《唐大詔令集》卷五五存有貶鄭絪太子賓客的詔書:
鄭絪,早以令聞,入參禁署。永推勤績,出授台司。期爾有終,匡予不逮。歲月滋久,謀猷寖微。罔清淨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旣乖素履,且鬱皇猷。宜副羣情,罷兹樞務。朕以其久居内職,累事先朝。恩厚君臣,貴令終始。俾就優閑之秩,用申寬大之恩。可太子賓客,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鄭絪太子賓客制》,《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92。
詔書明確指出,罷免鄭絪,是因爲他無所作爲,辜負了憲宗的期待,阻礙了憲宗的遠大抱負。由此可見憲宗的志向所在。此後,元和六年,宰相李藩因授淮西吴少陽節度,經李吉甫提醒憲宗,也被罷相。《唐大詔令集》所載詔書言:
爰立輔臣,以熙庶績。聿膺其任,亦曰難能。至於明用捨之宜,全始終之道,兹惟大體,寧忘予懷。中散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藩,早以學行,聞於紳。洎升朝端,克慎素履。頃者拔於非次,列在鈞衡,是宜直己以佐時,匪躬而納誨,用副明奬,越於常倫。而授任以來,再逾年序,夙夜之勤雖著,弼諧之效未孚。將何以允至公之求,成天下之務。宜輟黄樞之重,尚居端尹之崇,爾其勉之。式謂優禮,可守太子詹事,散官勳賜如故。*《李藩太子詹事制》,《唐大詔令集》卷五五,頁292。
明確指出,李藩在相位,雖然勤勞其事,但功效不明,長此下去,難以“成天下之務”。所謂功效,所謂“天下之務”,就是憲宗的削藩志業。李藩因爲難以輔助憲宗完成這一事業,故而被罷免。元和十年,憲宗正式開始平淮西之役,戰事艱難,從元和九年開始準備,到元和十二年最終平定,持續四年之久。其間,朝廷久戰不下,停戰之聲不絶於耳。因反對削藩被貶斥者,有多位宰相和大臣。據《資治通鑑》卷二三九載: 元和十一年,春,正月“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7721。“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别流品,又數請罷用兵;左補闕張宿毁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爲吏部侍郎。……(九月)丙子,以韋貫之爲湖南觀察使,猶坐前事也”。*《資治通鑑》卷二三九,頁7724。《通鑑》卷二四又載: 元和十二年八月“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九月)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四,頁7738—7739。李吉甫元和九年十月卒,十二年,太常定謚爲“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議,以爲不可。《唐會要》卷八載其議論云:
夫人臣之翊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内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蠆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紡婦不得在桑,耗賦斂之常資,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流血,胔骼成岳,酷毒之痛,號呼無辜,剿絶羣生,逮今四載,禍亂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得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著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吴,則記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取其所輕,而捨其所重;録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輔。斥諫之士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於内,豈不近之匿愛乎?烏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唐會要》卷八,頁1760—1761。
張仲方實際是借駁謚之機,痛斥李吉甫而全面否定淮西用兵。這是憲宗所不能容忍的,故《唐會要》載:“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唐會要》卷八,頁1761。關於此事,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譜》“元和十二年”條譜文有詳盡分析。*傅璇琮《李德裕年譜》,頁91—94。由以上論述可知,終憲宗一朝,是否支持削藩,是一條具有決定意義的標準,凡反對或破壞憲宗削藩大計者,上至宰相,下至朝臣,均遭到排斥與打擊。
另有一點須指出,憲宗雖然依靠宦官的力量獲登皇位,並且其在位期間,也寵信吐突承璀,但從當時一些事件來看,憲宗對於宦官的態度還是比較清醒的。首先是對宦官劉光琦。《資治通鑑》卷二三七載: 元和三年“知樞密劉光琦奏分遣諸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資治通鑑》卷二三七,頁7648。其次是對宦官吐突承璀。李絳曾多次向憲宗諫言承璀之專横,《李相國論事集》卷五《上言承璀事》記載:
户部侍郎李絳於延英對。上曰:“朕發遣承璀爲淮南監軍,宰相總不知,外人以爲如何?”絳對曰:“外人不准擬陛下出得承璀。”上曰:“此朕家臣,何故不能出也?”對曰:“承璀受殊常恩私,當非次委任,威振内外,權傾朝廷,無有賢愚,望風畏伏。外間私語,亦不敢斥言其名。中外人云,寧可止忤陛下,不敢斥言承璀。忤陛下,或有恩貸;忤承璀,必有禍害摧破。黨類相托,無復振起。威福既盛,恩寵又深,所以衆人不准擬陛下動得。今聞新有處分,皆荷英明。謂聖斷必行,撓惑不得,不勝欣賀。且知守道之人,必不盡爲中人所害也。”上曰:“此輩是朕家臣,智識凡近,比緣經任使,所以假貸恩私。若事迹無良,違犯有驗,朕處置之若一毛爾。若有大事,朕亦能斷之。”*《李相國論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46册,頁238上—下。
此條亦爲《通鑑》所取,因不如原文詳盡,故引原文。元和四年,憲宗令吐突承璀領軍討王承宗,不克,以李絳諫,貶爲軍器使。三是對宦官許遂振。據《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載:“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旣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頁4744。楊歸厚既論宦官許遂振之姦,又力詆卿相,又上表借朝廷官府爲私用,憲宗因其輕薄,欲遠貶,爲李吉甫所救。據《舊唐書》卷一六四《楊於陵傳》載:“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己,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賴宰相裴垍爲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爲吏部待郎。遂振終自得罪。”*《舊唐書》,卷一六四《楊於陵傳》,頁4293。對於許遂振的誣蔑,憲宗起初是相信的,但在裴垍的申辯之下,改變了態度。通過以上述論,可以看出,憲宗對於宦官,是依賴甚至親近的,對於他們的行爲,也多有放縱。但是並不是無限制的放縱,只要有大臣以合理充分的理由對宦官進行抑制,憲宗均會采納。
由以上述論可知,削平藩鎮,統一宇内,是憲宗最高的理想志業,爲此他與大臣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元和中興,成爲有唐三百年間難得的有爲之世。而這一理想追求,也成爲憲宗朝的一條基本國策與根本標準。凡是與這一標準相違礙的,都要剔除。
四 因反對削藩而選牛僧孺策文爲第一
牛僧孺策文正因爲直言反對削藩與用兵,而被選爲制科登第之頭名。這一點,新舊《唐書·韋貫之傳》均有明確記載。《舊唐書》卷一五八載:“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户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舊唐書》,頁4173—4174。《新唐書》卷一六九言:“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新唐書》,頁5153。《資治通鑑》卷二三七載:“貫之署爲上第。”*《資治通鑑》,頁7649。可見,牛僧孺等三人爲上第,牛僧孺爲第一名,韋貫之起了關鍵作用。而將言辭温和隱諱的僧孺策文放在言辭激烈直接的皇甫湜策文之前,又可見其中有韋貫之的主張。前已論述,韋貫之對於削藩用兵,是持保守意見的,且在元和十一年因此被貶。據《舊唐書》本傳:
淮西之役,鎭州盜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鎭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於是朱泚乘之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鎭邪?”上深然之。*《舊唐書》卷一五八《韋貫之傳》,頁4174。
對於這段記載,孟彦弘分析指出,韋貫之因爲具有“放棄河北、控制其餘”的意識,因此極力建議憲宗不要討伐王承宗,雖然口頭上是説先討淮西再討成德,但淮西平定之後,成德王承宗並未被提起,則韋貫之實際上是表明,不要碰河北。*孟彦弘《“姑息”與“用兵”——朝廷藩鎮政策的確立及其實施》,頁131。這種保守的意識,與憲宗的意圖相違背,但與牛僧孺的主張相合。《新唐書》本傳在此事之後載:“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新唐書》卷一六九《韋貫之傳》,頁5154。而《資治通鑑》直言韋貫之“數請罷用兵”,則其反對用兵的成分,相比於支持用兵,明顯更多。正是因爲這一保守主張,使韋貫之將僧孺策文升爲第一。另一位受到打擊的考策官楊於陵,其對於削藩的態度,其實也較曖昧。他在憲宗平淮西期間,任兵部侍郎判度支,任用親信,供給軍餉不利,對平淮西戰役起到了破壞作用。《舊唐書》本傳載:“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爲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爲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爲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傅。”*《舊唐書》卷一六四《楊於陵傳》,頁4294。很明顯,楊於陵對於平淮西的戰役,不僅没有積極支持,反而阻撓破壞,導致局部失敗。其對於削藩與用兵的態度,從這一事件可以想見。而元和三年制科,升牛僧孺策文爲第一,主要是保守派韋貫之、楊於陵兩人。韋、楊二人,應該是藉此表達自己對於削藩與用兵的看法。另外,覆視官裴垍,雖然積極有爲,輔助憲宗振興,但其對待藩鎮的態度,也是根據具體情況而有所區别的。據《舊唐書》卷一四八《裴垍傳》載:
王士真死,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請代父爲帥。憲宗意速於太平,且頻蕩寇孽,謂其地可取。吐突承璀恃恩,謀撓垍權,遂伺君意,請自征討。盧從史陰苞逆節,内與承宗相結約,而外請興師,以圖厚利。垍一一陳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於朝,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宗,是賞罰不一,無以沮勸天下。”逗留半歲,憲宗不決,承璀之策竟行。……垍以“承璀首唱用兵,今還無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罷承璀兵柄。*《舊唐書》卷一四八《裴垍傳》,頁3991。
與韋貫之、李絳、白居易、韓愈等相同,裴垍也是主張放棄河北的,這是當時的主流意識。可見,此次制舉案確實具有明顯的反對削藩背景。不僅是朝廷放棄河北的集體意識對憲宗的壓力,而且還有全面反對削藩與用兵主張的表達。
僧孺因策文反對削藩用兵被選爲制科第一名,也因策文反對削藩用兵,引起憲宗不滿,導致了制舉案的發生。牛僧孺在策文中直接向憲宗進言,希望不要窮兵黷武,認爲當年平定夏綏楊慧琳、西川劉闢、浙西李錡,已經是“定傾之功,揭日月矣”,屬難得之功,希望從此收斂,以“持盈”爲戒,這肯定引起憲宗的不滿。鄭絪、李藩、韋貫之、李逢吉等以宰相之重,尚且因反對用兵而相繼罷免,何況當時地位低微的牛僧孺?
五 憲宗態度索隱與事件的過程
杜牧《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中言:“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强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毁,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杜牧集繫年校注》卷七,頁701。並没有説被誰所毁。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載:“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羔雁繼至,封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全唐文》卷七二,頁7406上。説打擊僧孺等人的是持權者、中執事。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司空楊公墓誌銘》載:“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全唐文》卷六三九,頁6450下。打擊考策官的,爲中貴人與宰相。其實,按照前面的分析,皇甫湜的策文引起宦官與宰相的不滿,是很自然的。
《舊唐書》記載此次對策案共有八處,除《李吉甫傳》外,其餘七處均涉及貶黜諸人的記載,分别是《憲宗紀上》、《楊於陵傳》、《李德裕傳》、《韋貫之傳》、《王涯傳》、《李宗閔傳》、《裴垍傳》。其中,《李宗閔傳》、《裴垍傳》記載了憲宗對於此事的意見,而其餘五處並未出現憲宗。在《舊唐書·李宗閔傳》、《裴垍傳》中,對於打擊制舉人與考策官、覆試官,憲宗是持被動態度的。《李宗閔傳》載:
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爲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爲中等,又爲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爲唱誹。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裴垍時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垍學士,垍守户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出爲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馬,貫之再貶巴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舊唐書》卷一七六《李宗閔傳》,頁4551—4552。
但是,《舊唐書》其餘五處的記載,憲宗並未出現。這是值得懷疑與推敲的,應該隱含了某種信息。《舊唐書·憲宗紀上》載: 元和三年夏四月“乙丑,貶翰林學士王涯虢州司馬,時涯甥皇甫湜與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語太切,權倖惡之,故涯坐親累貶之”。*《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頁425。《楊於陵傳》載:“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舊唐書》卷一六四,頁4293。《李德裕傳》載:“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舊唐書》卷一七四,頁4510。《韋貫之傳》載:“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户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舊唐書》卷一五八,頁4173—4174。《王涯傳》載:“元和三年,爲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舊唐書》卷一六九,頁4401。這五處記載,均未出現憲宗,導致貶黜發生的最高權力來源,分别記爲權倖、執政、吉甫,而《韋貫之傳》只言被貶,根本不言何人所貶。在這幾處記載中,憲宗未出場,表現出一種默認的態度。尤其是上引《李德裕傳》所載: 吉甫泣訴與考策官皆貶之間,本應該有憲宗的態度,憲宗肯定是同意的,但被隱去了。
《新唐書》將憲宗默認的態度改爲憲宗也不高興,使憲宗成爲此次事件中貶黜諸人的最高權力來源。這代表了《新唐書》修撰者對此次事件的認識。
《新唐書》關於此次事件的記載共有八處,分别是《李吉甫傳》、《楊於陵傳》、《裴垍傳》、《韋貫之傳》、《牛僧孺傳》、《李宗閔傳》、《王涯傳》、《李德裕傳》。其中,並無憲宗不得已的記載。《楊於陵傳》載:“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出爲嶺南節度使。”*《新唐書》卷一六三,頁5032。《裴垍傳》載:“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户部侍郎。”*《新唐書》卷一六九,頁5148。《韋貫之傳》載:“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新唐書》卷一六九,頁5153。《牛僧孺傳》載:“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骾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謫去。”*《新唐書》卷一七四,頁5229。《李宗閔傳》載:“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新唐書》卷一七四,頁5235。《王涯傳》載:“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新唐書》卷一七九,頁5317。《李德裕傳》載:“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新唐書》卷一八,頁5327—5328。其中,貶黜的最高權力來源分别爲宰相、李吉甫,其實是李吉甫一人。《裴垍傳》、《韋貫之傳》並未出現貶黜的權力來源。但是,《新唐書·李吉甫傳》中記載:“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悦。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新唐書》卷一四六,頁4740。明言皇甫湜等對策引起用事者的憤怒,憲宗亦不悦。這裏説憲宗不悦,並没説是因誰泣訴或進言之後方不悦,表明憲宗不悦,即因策文本身而引起。在《新唐書》敍述這件事情的所有相關記載中,憲宗只出現兩次(另一次爲《李德裕傳》“吉甫泣訴於帝”),只有一次被明確描述態度。這種敍述方式,能夠代表《新唐書》修撰者的看法,修撰者應該認爲牛僧孺等的策文是引起了包括憲宗在内的諸多用事者的不滿,而憲宗的不滿,又是決定性的。所謂用事者皆怒,在《新唐書》的記載中,主要指宰相李吉甫,也包括宦官。至於此處以皇甫湜居首,可能是修撰者以牛李結黨爲小人,對二人有敵意,故將皇甫湜居首。《新唐書》其餘諸處,《楊於陵傳》、《韋貫之傳》、《李德裕傳》以僧孺居首,《裴垍傳》、《王涯傳》以皇甫湜居首,係沿襲《舊唐書》對應部分,《王涯傳》乃因皇甫湜係王涯之甥。而《舊唐書·李吉甫傳》並在論述此事時言:“三年秋,裴均爲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摇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舊唐書》卷一四八《李吉甫傳》,頁3993。這裏並没有出現牛僧孺等三人名字,當修撰者撰寫《新唐書·李吉甫傳》時,便以己意,用“皇甫湜等”代替,以表明他對牛李二人的態度。
到了《資治通鑑》,司馬光在《舊唐書·李宗閔傳》、《裴垍傳》記載憲宗不得已的基礎上,又對憲宗的態度進行了不同的描述。憲宗先是大悦,且下詔對登第人“優與處分”,因李吉甫泣訴,不得已貶斥諸人。實際上是對憲宗形象的一種正面强化,徹底洗脱了憲宗打擊登第舉人與考策官、覆視官的責任。《通鑑》卷二三七載:
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户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考策官,貫之署爲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垍、涯學士,垍爲户部侍郎,涯爲都官員外郎,貫之爲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乙亥,以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資治通鑑》卷二三七,頁7649—7650。“户部侍郎楊於陵”,原作“吏部侍郎楊於陵”,據四部叢刊景宋本改。
實際上,《舊唐書·李宗閔傳》、《裴垍傳》與《資治通鑑》爲了維護憲宗的正面形象,記載憲宗“不得已”的態度,反使憲宗成爲毫無主見、受人擺佈的庸常君主,這與真實的精明强幹、富於主見的憲宗形象是不相符的。
這個“上不得已”的記載,是有來源的,《舊唐書》應該是在這一來源的基礎上進行了改寫。
《唐會要》對此事的記載與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均不相同。其卷七六載:
释智林,高昌人。初出家为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学,负笈长安,振锡江豫,博采群典,特善杂心。及亮公被摈(453-459),弟子十二人皆随之岭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465),勅在所资给,发遣下京,止灵基寺……林形长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谈吐若流。后辞还高昌。齐永明五年(487年)卒。春秋七十有九①〔梁〕释慧皎:《高僧传》卷8《智林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09-311页。。
其年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官員外,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爲考官。是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考三策,皆在第,權倖或惡其詆己。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爲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虢州司馬,楊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使。裴垍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乃爲貴倖泣訴情罪於上。上不得已,罷垍翰林學士,除户部侍郎。*《唐會要》,頁1649—1650。
《太平御覽》卷六二九所載文字基本相同,文繁不録。清岑建功《舊唐書逸文》卷六載此條,與《太平御覽》文字全同,*《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2818上—下;《舊唐書逸文》,《續修四庫全書》,2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8下。則當是從《御覽》所出,且將其定爲《舊唐書》逸文。
《會要》、《御覽》的相關記載對於是誰貶黜了諸人,頗爲曖昧不明。先言王涯、韋貫之貶官,續言考策官升牛僧孺等三人登第,再言權倖惡其抵己,再言落第者唱誹並舉報王涯隱瞞與皇甫湜的親屬關係,王涯因此同坐。這一段即完結,並没有明言是權倖貶黜諸人。這種敍述的空白與模糊,明顯表明了敍述者某種隱含而不便明言的態度,即貶黜楊於陵、韋貫之等人,是“權倖”等人在憲宗默許下進行的。而憲宗不得已的,只有貶黜裴垍一人。爲何不得已?已然貶黜了那麽多人,而裴垍又身陷其中,無法開脱,必須貶黜。但憲宗是欣賞看重裴垍的,所以纔不得已。《舊唐書·裴垍傳》記載:“垍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除户部侍郎。然憲宗知垍好直,信任彌厚。其年秋,李吉甫出鎭淮南,遂以垍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舊唐書》卷一四八,頁3990。在這次貶黜不久之後,裴垍馬上升任宰相,可見憲宗對其的信任。因而,憲宗“不得已”的態度只是針對裴垍,並非對其餘人。只對裴垍不得已,恰恰説明憲宗對於貶黜其他人是許可的。而《舊唐書·裴垍傳》與《李宗閔傳》卻將憲宗不得已的態度,擴大到針對當時被貶黜的所有人,是對憲宗形象的維護。又,此處記載表明,貴倖泣訴於上,也僅針對裴垍一人,並非針對所有當事者,而後來記載均籠統而言,造成了這樣的邏輯鏈: 泣訴於上然後貶斥諸人。使事實有所混淆。
這段記載中出現了“權倖”與“貴倖”兩個名詞,並且有所區别。權倖偏指宰相,貴倖則偏指宦官。《資治通鑑》與《舊唐書·裴垍傳》,有多次打壓宦官的記載。《通鑑》卷二三七載: 元和三年,春,正月“知樞密劉光琦奏分遣諸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資治通鑑》卷二三七,頁7648。《舊唐書·裴垍傳》載:
及作相之後,懇請旌别淑慝,杜絶蹊徑,齊整法度,考課吏理,皆蒙垂意聽納。吐突承璀自春宫侍憲宗,恩顧莫二。承璀承間欲有所關説,憲宗憚垍,誡勿復言,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吐突承璀恃恩,謀撓垍權,遂伺君意,請自征討。……逗留半歲,憲宗不決,承璀之策竟行。……垍以“承璀首唱用兵,今還無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罷承璀兵柄。*《舊唐書》卷一四八《裴垍傳》,頁3990—3991。
裴垍一向以來反對並曾多次打擊宦官,與吐突承璀之間多次交鋒。在元和三年正月,制舉案發生之前不久,即壓制了宦官劉光琦。制舉案發生,正好被宦官抓到把柄,受到貶斥。而李吉甫與裴垍的關係,傅璇琮《李德裕年譜》曾有辨析,指出二人政見多相同,從未交惡,*參見《李德裕年譜》,頁70—72。這又可以反證,裴垍所受的打擊,不可能來自李吉甫,而是來自宦官。貴倖泣訴於上,當指宦官。這樣,所謂權倖,則偏指宰相了。李翱所作《楊於陵墓誌銘》載:“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全唐文》卷六三九,頁6450下。也是將中貴人與宰相分開表述的,與《唐會要》等所載相同。
前引《資治通鑑》記載此事時,有“上亦嘉之,乙丑,詔中書優與處分”等語。“詔中書優與處分”,《册府元龜》卷四八一載:
王涯,爲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元和三年四月詔,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人第三等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權倖惡其抵己。有不中第者,注解其策,同爲班誹,言王涯與外甥皇甫湜登科,不先上言,遂左授涯爲都官員外郎,考官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果州剌史。數月,再黜爲巴州剌史,涯爲虢州刺史。*《册府元龜》卷四八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5743上。又見南京,鳳凰出版社點校本,2006年,頁5443—5444。
“上亦嘉之”,諸處皆無,應該是司馬光在“詔中書優與處分”的基礎上的加寫,以表明憲宗的態度,維護其形象。今本《唐大詔令集》並無“詔中書優與處分”的詔書,相反,卷一六政事卷存德宗貞元元年(785)《放制科舉人詔》、憲宗元和元年(806)《放制舉人敕》、穆宗長慶二年(822)《放制舉人詔》、敬宗寶曆元年(825)《放制舉人詔》、文宗大和二年(828)《放制舉人敕》,均明確指出,對於制舉登第第三等、第三次等,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可見,這是一個成例。對於《通鑑》所載憲宗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之事,極有可能是在事情尚未爆發時,依照過往成例由中書門下下的詔書,並不能代表憲宗真實的態度。此一詔書現不存,可能是後來被删去。另,《册府元龜》此處記載,王涯再貶,當爲虢州司馬。
《唐會要》等三處的記載,比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對此次事件具體發生過程的記載更爲合理。雖然《册府元龜》與《唐會要》、《太平御覽》記載有細微出入,但大體還是相同的。有個關鍵的地方,這個記載中出現了落第者這股勢力,對於這次事件的發生起到了重要作用。除《舊唐書·李宗閔傳》外,其餘諸處均未提到。但是,作爲覆視官的白居易,在《論制科人狀》中指出:“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奬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關外官。”*《白居易集箋校》卷五八,頁3326。明確指出落第者這股勢力的確存在,並且散佈謡言。另外,白居易《論制科人狀》只爲諸人訴説寃情,希望憲宗諒解,也並未直言是誰打擊了諸人;而白居易上言之後,憲宗没有任何反應,尤其可説明問題。
由此可見,《唐會要》等三處記載,應該更符合事實。根據《唐會要》、《太平御覽》所載,過程是這樣的: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參加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策語甚直,無所避忌,考官升三人皆上第,引起權倖不滿與厭惡;同時,落第者注解三人策語,散佈謡言,進行誹謗,施加輿論壓力,皇甫湜因是王涯外甥,被落第者指責未行避嫌;憲宗在知曉了策文内容的真實情況之後,應該是很不高興的,這裏並没有直言其態度,而是説在這兩種壓力之下,考策官、覆視官以及王涯均被貶黜,顯然是默許;裴垍覆視,無所異同,爲貴倖(宦官)泣訴,憲宗不得已,同時貶斥之。
在新舊《唐書》的相關記載中,除《舊唐書·李宗閔傳》外,均未出現落第者這股勢力,而是將所有人被貶,籠統歸結爲宰相或權倖;有幾處記載憲宗不得已態度的(《舊唐書·李宗閔傳》、《裴垍傳》、《通鑑》),也是將這種態度從僅針對裴垍一人擴大到針對當時所有貶黜者;還有幾處記載吉甫泣訴於上(《舊唐書·李宗閔傳》、《李德裕傳》、《新唐書·李德裕傳》、《通鑑》),也是將宦官針對裴垍的單獨行爲轉換爲吉甫針對所有人的行爲。按照上面的分析,憲宗亦怒,故吉甫不須泣訴,諸人也當被貶。《通鑑》更是將皇甫湜爲王涯外甥而没有避諱這一事件的告發者由落第者轉爲李吉甫,泣訴於上而貶黜裴垍的也由宦官變爲李吉甫,使李吉甫獨承全部惡行,而增寫“上亦嘉之”,爲憲宗洗脱責任。《通鑑》對李吉甫有所偏見,多采納誣蔑吉甫之《李相國論事集》中的相關記載,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譜》於相關條目辨之甚詳。*參見《李德裕年譜》,頁44—48、56—59、74—75。此處將他人之惡,全部歸罪於李吉甫,也是這一態度的表現。對於憲宗的態度,整個《新唐書》以交互相見的手法,表達了修史者的看法,認爲憲宗也不高興。這個看法,是合理的。
結 語
由以上論述可知: 元和三年對策案,牛僧孺因直言反對削藩與用兵,遭到積極削藩的憲宗與李吉甫乃至支持用兵的吐突承璀等人的不滿;引起憲宗不滿,是此次事件中的關鍵因素;皇甫湜贊成强兵削藩,但其策文則因强烈的譏刺,引起宦官、李吉甫等人不滿。韋貫之、楊於陵等人將僧孺策文升爲第一,實際是藉機反對憲宗的削藩政策。此次事件,憲宗、李吉甫、宦官等人均不滿,因而遭到貶黜之人如此之多。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指出:
牛李黨派之爭起於憲宗之世,憲宗爲唐室中興英主,其爲政宗旨,在矯正大曆、貞元姑息苟安之積習,即用武力削平藩鎮,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當時主張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屬於後來所謂李黨,反對用兵之士大夫則多爲李吉甫之政敵,即後來所謂牛黨。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閹寺一派又與外朝之李黨互相呼應,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閹寺始終柄權,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維持不改。及内廷閹寺黨派競爭既烈,憲宗爲别一反對派之閹寺所弒,穆宗因此輩弒逆徒黨之擁立而即帝位,於是“銷兵”之議行而朝局大變矣。*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97—98。
對於理解此次對策案,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説,元和三年對策案因反對削藩而爆發,是“牛李黨爭”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