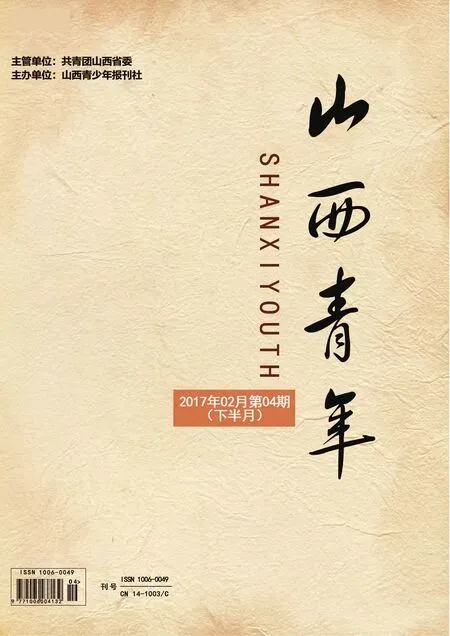个性迷失的世界
——读《美丽新世界》有感
王佳欢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个性迷失的世界
——读《美丽新世界》有感
王佳欢*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刻画了一个500多年后的未来世界,人们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大满足、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的世界上,看似幸福的社会却无所谓个人的喜怒哀乐和精神自由,道德的面孔下潜藏的是一个毫无人性的虚假世界。
《美丽新世界》;“幸福”;“个性”;迷失
小说中,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推出福特T型汽车,并将第一次在汽车工业中引入流水线作业的1908年作为“新世界”的开元之年。故此,福特纪元632年就相当于公元纪年的2540年。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存在着三个并行的空间:一是“野人”约翰出生成长的印第安村落;二是约翰游历的“文明社会”万邦国;三是赫姆霍兹及其他思想犯们被流放的荒凉岛屿。这三个空间分别象征了野蛮荒诞、过度文明和思想新生。小说中的“文明社会”以福特作为信仰对象,建立的是一个讲求绝对权威,要求民众保持原始思维的愚民社会。
一、万邦国的“幸福”
在万邦国里,机制的核心就是“幸福”,穆斯塔法·蒙德自言:“我们信仰的是幸福与稳定。”为了达至所谓的“幸福”,万邦国以技术为基础,对国民进行严密的思想、行为监控。
小说中,通过“最先进的洗脑术”对婴儿进行驯化——采用电击方式,以及比电击更普遍的睡眠教育方式。睡眠教育号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道德,社交力量”,通过睡眠时向婴儿、少年灌输固化的思想而戕害其独立的思维能力。“六万四千两百多次的重复就能制造一个真理。”[1]通过不断暗示宣传,使社会所要求的律令成为人们终生而唯一的心灵内容。化学药品“索玛”制造出了一个躲避现实的幻觉的天堂,“索玛”是“完美的药物,他令人精神愉悦,令人镇静,还能让人进入美妙的幻觉世界。这药物综合了基督教和烈酒的长处,却没有遗留二者任何一个缺陷。他可以让人随时远离现实生活,仿佛遁入休闲假期,醒过神来不仅一点都不头疼,而且还不会胡言乱语。从技术上来说,社会和谐终于得到确保。”[1]这种药物可以使臣民按照统治者所期望的模式去思考、感受、行动。
二、消失的“个性”
小说中提到的技术手段看似达到了社会的全体幸福,可是在这套完美的社会体系的表层之下,又何尝不是千疮百孔。所有与这个“幸福”社会格格不入的因素都是因为产生了“个人的思想”,追求自由。睡眠教材中有一句名言:“当个体自作主张,社群将蹒跚混乱。”
在未来世界中,还未出世的小生命即被划分成五个不同的等级,出生后,不同等级的儿童开始接受不同等级的潜意识教育,这些教育使儿童意识到自己应处的阶级地位,因此他们从小就安于现状,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命运抗争,没有抗战的臣民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大的安慰。而这些丝毫没有反抗心理的人们,他们缺失的不仅仅是抗争的力量,更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个性”,他们没有了自己的个性需求,没有兴趣爱好,甚至没有自己的思想。[2]
个体的消失除了导致个性的消失以外,也表现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传统区分被打破以后,前者对后者的侵犯与渗透,也即个性与私人性的一并消失。从教导婴儿们弃绝美丽花草的育婴房到提供大量麻醉人药品的弥留医院,一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构成对个人进行体制规训与曝光的领地。[3]人们满怀着“创伤性的空虚”,纵情享乐,分享共同的趣味,没有任何私密性和个性可言。
穆斯塔法·蒙德放弃了“个性”,成为了元首,而赫姆霍兹因为发展了“个性”被流放到荒凉岛屿。伯纳德·马克思虽然最终因恐惧放弃了抵抗,但他也曾经拥有过“个人性”,他开着飞机带着列宁娜悬停于大海之上,在列宁娜的恐惧中,他喊出了独立的声音:“似乎我原本可以是一个更像我的人,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更纯粹的自己,而不是彻底成为别的事物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肌体内一个小小的细胞。”[1]这段话深深体现出这个看似“幸福”的社会体制下隐藏的恐怖与黑暗,而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人民是多么可悲。
三、结语:迷失
作为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媒介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尼尔·波斯曼深切地感受到赫胥黎的预言相比奥威尔的预言来说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赫胥黎的寓言击中了人性的软肋。他告诉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4]我们会对一个长相凶神恶煞的人充满警惕,而对一个“笑面虎”却无法相信他有伤害人的意图。一看就鬼鬼祟祟的人不一定能给社会带来多大危害,但是笑里藏刀的人说不定转身就给社会的心脏上插上致命的一刀。在生活中,电视媒介、网络游戏和手机娱乐等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当我们沉溺于感官的享乐和娱乐的堕落中不能自拔时,我们的个性就已经被它们杀死。面对“老大哥”,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它狰狞的面目,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起来奋力反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4]
止庵先生曾经将《1984》和《美丽新世界》放到一起做了个对比,他对于两者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要在《1984》和《美丽新世界》之间加以比较,我会说《美丽新世界》更深刻。我不认为‘一九八四’有可能百分之百实现,因为毕竟过分违背人类本性;但是裹挟其中,还是感到孤独无助。然而‘美丽新世界’完全让人无可奈何。对‘美丽新世界’我们似乎只能接受,因为一个人能够抵御痛苦,但却不能抵御幸福。”[1]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我,迷失了个性,幸福从何而来。
[1][法]阿道斯·赫胥黎.重返美丽新世界[M].庄蝶庵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258,288,106,9.
[2]张秋子.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给人们的启示[J].时代文学,2010(6).
[3]张秋子.审判与救赎——反启蒙及其论域中的《美丽新世界》[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2(2).
[4]尼尔·波斯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2,203.
王佳欢(1991-),女,汉族,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
A
——记舟山万邦永跃船舶修造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