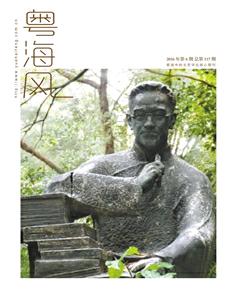“比利,不要发呆!”
李伯文
美国作家本·方登的《漫长的中场休息》(张晓意译,南海出版社2016年11月版)是李安最新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底本。李安此前对王度庐、扬·马特尔等人作品的甄选,证明他的人文情怀和艺术眼光绝对一流,因而本·方登的《漫长的中场休息》也值得我们认真细读。
《漫长的中场休息》是一部反战小说。反战小说当然不能用标语口号来煽动人们上街游行,而是需要用文学手法启人深思,以剥下意识形态的虚伪面具,消解其发动战争的合理合法性。B连二排一班B分队十名战士因为在伊拉克运河战役中作战勇敢,受到特别礼遇,除牺牲的施鲁姆和受伤截肢的莱克以外,其余八人获准在“感恩节”前回国享受为期两周的“凯旋之旅”;此前的新闻宣传已将他们炒作成当代英雄,因而资深电影制片人艾伯特一路随行,想挖掘B班故事以拍摄一部《野战排》那样的战争电影。在这八位战士中,二等兵比利虽然只有19岁,但在爱读书的施鲁姆影响下,已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因此他常常陷于“发呆”状态,渐渐发现了他们被安排的行程背后有着种种内幕:他们行经的州城大都是“选举摇摆州”,因而B班就成了政府发动战争的合法性证明,成为唤起美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工具,甚至成了政党角力、总统竞选的一枚精致棋子;他们被赋予的“光荣与梦想”是为国而战,但别人想的却是趁机发一笔战争财,甚至随军大厨都从伊拉克带回了大把的金子;B班回国后的所有活动都是被操纵的政治表演和商业行为,使“B班早已全部沦为畅销产品”(第36页)……所有这一切都使比利在狂欢之后陷入迷惘:他们战斗是为“九一一”死难者报仇吗?是为了瓦解萨达姆政权和消灭恐怖主义分子吗?可是“九一一”之前的仇恨因何而起呢?他不得其解。比利还发现:达拉斯大财阀诺姆款待战士们并非出于尊敬,而是为了借机给自己涂脂抹粉以进军政界,还为了取得故事“版权”以拍电影渔利——当戴姆和比利拒绝合作时,诺姆便撕下假面、派出打手公然挑衅并群殴八位战士。小说结尾,B班战士带着肉体和精神创伤重返伊拉克战场,从而为B班的“凯旋之旅”留下了一个烂尾。可以说,《漫长的中场休息》继承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揭示了美国政治“如此完美的悖论,如此缜密的现代循环逻辑”(第34页):今天发动战争的政客如布什,和支持战争的大财阀如诺姆等人,当年都是坚定的反战者或逃避兵役者;B班被赋予了“爱国者”、“你们就是美国”的符号性身份,因而所有的奉献牺牲就成为他们理所当然的义务;他们被赞为“二十一世纪的平权英雄”(第57页),也就被公共舆论和群体道德绑架,因而即使明知受骗上当、被利用,也无法通过民间组织寻求法律保护,而只能别无选择地遵守纪律再返伊拉克战场。——如果扩而大之,那么何止是B班战士,所有当代人都已被纳入庞大的政治游戏圈套之中而无法脱身。就此而言,本·方登与约瑟夫·海勒都是典型的黑色幽默作家,他们同样反战,同样揭出了现代政治已经异化了的、体制化的疯狂病态和荒诞悖论。
本·方登在《漫长的中场休息》中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中士戴姆、施鲁姆,电影制片人艾伯特,大财阀诺姆,二等兵比利等。当然,叙述人、思考者兼重大事件参与者比利无疑是小说真正的Hero。真实的比利一点都不高尚:姐姐凯瑟琳车祸毁容被甩,他就砸了“准姐夫”的豪车;他为了免于不良纪录,也为了六千元征兵奖金而入伍;他目睹了好友施鲁姆的牺牲和莱克的截肢过程,心理受到巨大创伤,精神近乎崩溃,故而回国后酗酒饕餮、麻痹自己;他不时“发呆”并在反思中回归了常识,就像他的好友施鲁姆一样开始总结出一些箴言,比如他对文明本质的概括:“这就是文明的全部意义,吃美味的食物和得体地拉屎”(第60页);他还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像橄榄球运动一样“占领守不住的地盘纯属徒劳”(第212页);他在经历了两周的凯旋之旅后明确意识到:“B班不过是又一个笑料。……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当然,受人摆布是他们最基本的要素。”(第29页)他知道“战争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孽”(第46页),但在媒体面前仍要保持“数代影视剧的男演员塑造出来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美国男人形象”(第38页)。然而,B班一方面受到隆重欢迎,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反战人士打出的“上帝痛恨你们”、“美国大兵下地狱”、“停止在伊拉克的强奸”等诅咒式的标语,这使比利更加感到困惑,因为对他来说,可怕的不是受伤或死亡,而是不知为了何种正义目标而牺牲,更可怕的是他发现战士们一直生活和战斗在荒诞逻辑和政治圈套之中。小说最后有一段比利的感慨:“过去是一片迷雾,吐出一个接一个的幽灵,现在是以时速九十英里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将来是深不见底的黑洞,任何猜测都是徒劳的。”(第314页)此时他说服自己“试着什么都不再去想”。——在整部小说中,“发呆”是比利的重要特征;而班长戴姆时常唤醒走神的比利:“比利,不要发呆!”这位咋咋呼呼、扮帅装酷的中士班长戴姆,早年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对主流的正统观点嗤之以鼻”,他之所以唤醒比利也许因为他当年曾有过类似经历,也许是因为他更加清楚:清醒的思考者最为痛苦!因此可以说,比利是戴姆的“前传”,戴姆是比利的后来者,而他们共同延续了前辈“垮掉一代”的反思精神;而作家本·方登则通过比利这个核心人物及其意识流动,将现实主义题材、现代主义技法与后现代主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架构起了这样一部既通俗又严肃、既好看又发人深思的小说。
一部优秀的小说不仅要有一个精彩故事,还应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漫长的中场休息》叙事时间高度浓缩:B班的凯旋之旅为期两周,但作者只取此行最后两天发生的人事纠葛,主要写B班观看达拉斯牛仔队橄榄球赛、在球员俱乐部用餐、与碧昂斯一起参加“中场秀”狂欢活动,中间插叙比利返家团聚那一天的经历和感受。但小说的内容却绝非如此简单,作者极为娴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从容地穿越时空,将伊拉克与美国、现在与过去联结在一起:两天经历的场景和事件常让比利触景生情,回忆起上学、入伍、训练、战斗和战友,叙述了姐姐凯瑟琳的车祸、父亲的中疯等家族背景,还包括电影行业的内幕以及大财阀的敛财手法等等,从而串联、容纳了颇为广大的社会内容。而凯旋之旅中的美酒与欢筵、柔情与蜜意、劲歌与狂舞、烟花与赞誉,最后都被那场拳脚相加的群殴消解了,于是小说以一种反高潮、反好莱坞电影“皆大欢喜结局”的方式,留下了一声巨大的叹息:“现实如此寒碜,令人大失所望”(第11页)。就此而言,《漫长的中场休息》中的意识流手法以及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让读者很容易联想起《尤里西斯》《一日长于百年》那样的经典小说。
《漫长的中场休息》是一部典型的电影小说。这首先是因为小说本身就像电影剧本,内容浓缩,戏剧性和画面感强烈,人物语言具有动作性,因此几乎不需要编剧即可投入拍摄;二是小说通过电影制片人艾伯特列举了当代美国最重要的战争电影,可谓当代战争类型电影简史和资料库;三是小说批判了好莱坞战争电影模式。“认同、救赎、死里逃生,都是让人振奋的东西”,当然还要有“皆大欢喜的结局”(第6、7页),这就揭出了美国战争电影的恶俗套路和虚伪做作;而那位三获奥斯卡奖的电影制片人艾伯特进一步指出:“好莱坞是一个恶心变态的地方,这点我可以保证。腐败、堕落、充斥着整天惹是生非的怪胎,就好像,嗯,十七世纪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宫廷。”(第63-64页)——对好莱坞电影模式的解构,似乎是本·方登“解构美国梦”这一创作题旨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方登是一位语言魔术师,从深邃哲思到世俗俚语,从江湖黑话到政治辞令,从经典广告到政治、军事、财经、医学和电影等行业术语,他都表达得极为自然恰切;这不仅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美国小说的经典标签符号,也使他笔下的每个人物的语言都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透露出了各自的职业身份和道德本性。而本·方登语言的更大魅力在于,他营造了极为真实生动的现场感,引领读者与B班战士一起进入了橄榄球场的狂欢,但他没有让人们“娱乐至死”,相反,他让读者与B班一起领受了诺姆打手的群殴,然后从狂欢天堂堕入忧伤黑夜,让人由此想到了鲁迅的《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看来,中外伟大作家的心灵是相通的,他们揭出病苦,他们歌以当哭,他们让我们更加接近世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