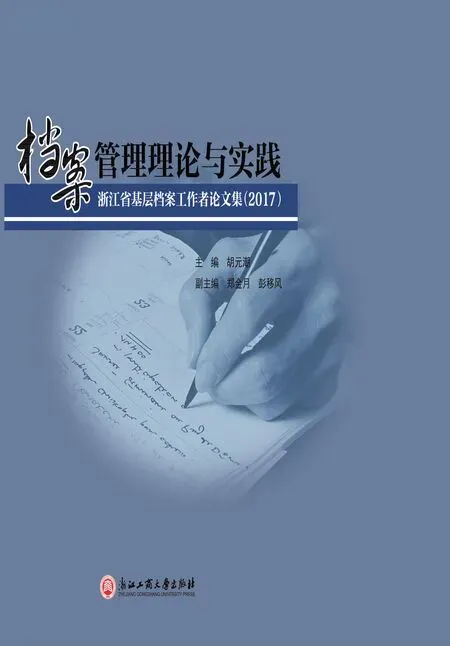在编史修志过程中对档案工作的思考
楼雪丹
(遂昌县人民武装部)
“还原历史的真实”是编史修志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参与史志编修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档案对于历史真相的考证与还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档案是编史修志的最佳起点。但是,档案真迹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在使用过程中应将档案、文献、口述历史“三结合”进行甄别,确保史志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一、利用档案是编史修志的最佳起点
档案是特定的形成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整理的原始文件。其在历史真相考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少历史学家给予了“不可替代”的评价。德国兰克史学学派甚至认为历史没必要研究,只要将那个时期的档案摆放在桌子上就是历史。这一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档案的确是编史修志的最佳起点。在编史修志之前认真查阅档案,可以有效避免或纠正已有史志书籍中的错误。
以2016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遂昌英烈》所涉烈士巫云的考证情况为例。烈士巫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遂昌县大队副大队长,其牺牲时间,《遂昌县民政志》(1993年10月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遂昌县志》(1996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遂昌县军事志》(2008年5月内部出版)、《碧血丹心——浙江烈士英名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均记载为“1950年”。在编写《遂昌英烈》时,我们没有轻信这一论断,而是从档案入手,查阅了中共遂昌县委、遂昌县人民政府、遂昌县史志办公室、遂昌县民政局、遂昌县人民武装部5个单位形成的相关档案。在遂昌县档案馆14-2-4案卷中,我们发现了1950年1月5日龙泉县人民政府致遂昌县人民政府的公函,公函的附件为1949年12月29日陈才刚、季余华上报的关于巫云烈士牺牲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中写道:“巫同志于阳历十一月廿四日在四五保(上锦村)发出通知,想要在本月廿七日召开本保斗争会议。因第九保农会长练孝明赶到四保(即上锦村)要求他到第九保召开斗争会,因此巫同志于廿五日早上就去。先到第八保召开会议,当日就在第八保(岭根)住宿。廿六日才到第九保开会。会议完竣后天色已晚,他就带同通讯员返回第四保。于途中林承洪在后面追来,他们三人就一同走。走到牛扼岭头下十几步的光景,就被土匪打了一枪。第一枪就打到他的右心膛上面一点。据说巫同志还想拿枪抵抗,不及土匪又复打来一枪正打在他的左眼角上,头颅已经分裂。巫同志的通讯员就马上逃躲,在七八分钟的时候已经逃到上锦村范延年家里,告诉他有土匪,现在大队长已经被土匪打死了。”依据这份档案,我们轻松地还原了巫云烈士牺牲的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形。试想,如果《遂昌县民政志》《遂昌县志》《遂昌县军事志》《碧血丹心——浙江烈士英名录》的撰稿者或者编辑看见过上述档案,是否能够避免错误?答案是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档案实在是编史修志的最佳起点。
二、编史修志中使用的档案需要仔细甄别
档案是编史修志的最佳起点,那么,是不是只要将那个时期的档案转载到书中就是真实的历史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某些档案,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会出现“是历史真迹但不是历史真实”的现象。
以《遂昌英烈》所涉烈士华沛堂的相关档案为例。华沛堂,1935年8月参加革命,任遂昌县王村口商会主席。同年10月被遂昌县政府判处“扰乱社会罪”,送九江监狱监禁1年。1937年,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当兵,不到半年逃回家。1941年1月再次被捕,7月被押送到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次年2月在狱中去世。“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叛徒”批判。华沛堂为什么会被当作叛徒批判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民国政府留下的一份档案——1941年5月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印发给《浙西日报》的《遂昌华沛堂等578人脱离共党宣言》。这份档案是不是1941年5月由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形成的呢?是,也就是说它是历史真迹。但是,它的内容不真实。华沛堂受审后,《浙江省遂昌县获案匪党名册略情表》中记载:“讯问结果,在区属里供认于(民国)二十四年参加共产党,到县府否认前供,仅认系逃兵。”华沛堂在狱中死亡后,省保安司令部准予备核的命令中写的是“逃亡犯”。原国民党遂昌县党部书记长俞乃普在1957年3月23日供认:“规定宣言具名的是共产党有声望、职位比较高的(人),完全以欺骗方式,诱惑共产党内部分离。”由此可以断定,《遂昌华沛堂等578人脱离共党宣言》是特殊时期国民党妄图瓦解共产党的一种政治欺骗,华沛堂并不是叛徒。
对于“敌方”留下的档案我们要甄别,那对于“己方”留下的档案要不要甄别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以《遂昌英烈》所涉烈士毛文均的相关档案为例。遂昌县档案馆135Y-148案卷中有一份遂昌县人民政府致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关于追认毛文均同志为革命烈士的请示》,成文时间为1986年4月24日,上载“毛文均,一九三五年农历四月参加革命,任挺进师领导的黄塔村游击队副队长”“一九三五年公历五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驻王村口”。红军挺进师在浙江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党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浙江各地的党史部门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调查研究,已经形成统一看法:1935年4月28日,通过“庆元斋郎大捷”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5月9日,进抵松阳县;5月12日,首次进入遂昌县境;6月3日,首次进抵王村口;6月24日,再次进抵王村口地区;7月初,在王村口组建以当地农民积极分子为主的第五纵队;7月中旬,建立中共王村口区委;7月下旬,师部进驻王村口镇,在王村口设立了建设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中心。根据这一定论,我们可以发现:遂昌县人民政府1986年4月24日形成的这份档案中有关毛文均参加革命的时间、挺进师进驻王村口的时间均有误。
不能正确反映史实的档案会造成史志书籍的硬伤,所以编纂史志书籍时对档案一定要进行认真仔细的甄别。
三、档案、文献、调访“三结合”,是甄别档案的有效手段
甄别档案是一项并不简单的工作。除了要有“甄别档案”的意识外,还需要一定的方法。实践证明:档案、文献、调访“三结合”,可以有效甄别档案。
以《山东南下干部入浙》(2012年12月内部出版)所涉干部李春田的考证情况为例。在搜集资料时,我们发现档案和文献有矛盾之处——遂昌县档案馆4-1-3案卷《1949年8月预算花名册》和《1949年8月份津贴费报销花名册》中,李春田的职务都是遂昌县委组织部部长,任遂昌县湖山区区委书记的是黄盛。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遂昌县组织史》(1992年10月内部出版)记载“湖山区委书记李春田(1949.6—1950.11)”“组织部部长崔玫光(兼,1949.8—1951.11)”。我们借助调访手段解开了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以及历史真相。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50年5月任蕉川区副区长的离休干部邱锡龄告诉我们,解放初期,湖山匪患严重,因为工作脱不开身,李春田未能到组织部上任,在1950年七八月间曾以湖山区委书记的身份和邱锡龄一起到衢州参加衢州专署组织的区委书记、区长培训班。除了此例,前文所讲的华沛堂、毛文均情况的考证,也有赖于文献、档案、调访“三结合”。
细究档案出现“是历史真迹但不是历史真实”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多方面的。譬如1941年5月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印发给《浙西日报》的《遂昌华沛堂等578人脱离共党宣言》这份档案的虚假,是因为记录者有意欺骗,而《关于追认毛文均同志为革命烈士的请示》这份档案的失实是因为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档案形成时间滞后。毛文均参加革命、牺牲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35年,可是这份档案是在1986年形成的,滞后51年。二是知情人人数有限且年事已高。对红军挺进师进驻王村口的时间和毛文均参加革命的时间,依据的是当地老党员、游击队员的口述,在口述时,这些知情人大多已经年逾七十,容易发生记忆错误。三是调查不够全面深入。认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工作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刚刚恢复,地方党史的编写工作尚未提上议事日程,许多党史基本问题都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所以档案、文献、调访“三结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编史修志者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其意义是重大的。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活动都有档案文献留存,并且档案史料常为孤本,在保管、流传过程中容易出现散失情况,如果能将档案、文献、调访“三结合”,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甄别档案,还在于可以弥补档案史料的缺失,使略显呆板的档案史料鲜活起来,最终还原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