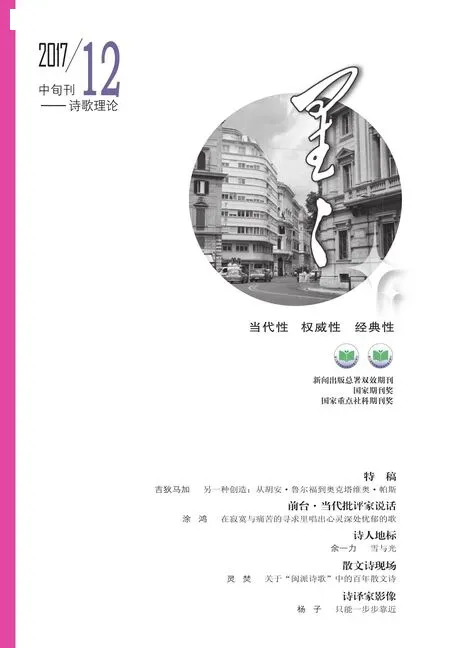生命之累与敬畏之心
李 洁
一直以来,信仰都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话题。它往往代表了种种不便描述、不可言说的内涵,这倒并不是说信仰本身有多么神秘,相反,也许正是因为被谈论得太多,牵涉其中的因素过于驳杂,使其反倒愈加说不清楚。与西方深厚的宗教背景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除了对于权力和神灵的崇拜之外,由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自然界中一些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会带给人类恐慌与畏惧,早期对于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便成为人类信仰的一部分。这种情绪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表现在对自然的爱护与对生命的尊重。衍生到文学作品当中,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探索,对生命的关注与颂扬就成为不断阐述的主题。本期“每月诗歌推荐”中的诗作可以说是对于这一话题的最好诠释。
面对浩瀚无边、深不可测的大千世界,个体生命的渺小不言而喻。在面对无法改变的际遇安排,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也会暴露无遗,在诗作《小黄马》里,命运的轮回带给人的无助之感便渗透其中,“小黄马在草原上悲伤地慢慢跑”这一句在短短的诗行当中重复出现,一方面强化了诗歌的韵律感,另一方面却也在无形中使得诗中命运的轮回之累更加重了一层。从“妈妈累死在草原”的一刻起,“小黄马”“承袭”的命运便已注定,诗人除了对这种无奈的安排表示深深的“悲伤”之外,结尾一句“蒙古包里马头琴声多么悠扬”,更是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显示出了强烈的悲悯情怀。如果说臧克家的《老马》写出了对苦难的忍耐,那么,这里的《小黄马》无形中将生命的脆弱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之间玄妙的关系揭示了出来,“蒙古包里马头琴”悠扬的乐声背后隐含着人类对动物界的残忍掠夺,从“小黄马”的视角去揭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自然呈现出不一样的心理感受。
如果说对动物界的悲悯在某种意义上出自于一种生物的本能,那么,自然界在人类的情感世界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会较为复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造就的一切杰作均是那样难以捉摸,此时可能是会带给人类灾难与痛苦的“魔鬼”,彼时可能会成为人类的知音,这也是历代文人笔下经常表现的主题,纵情山水,徜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歌咏唱和,书写千古风流文章。这一主题延伸到当代新诗,面对现代文明的浸染,能够寻得一方未经雕饰的天地实属难得,出现在诗人笔下的种种自然界的美好往往带有人工斧凿的缺憾,但是对于自然界的期许与寄托的情感却也从未改变过。在《小谣曲》中,无论是“流水”“乱石”中时空之永恒,还是在盛春时节“峡谷”之幽美,终究都是“我”记忆中关于“你”的印记。“手指纤长,爱笑//衣服上的碎花孤独于世。”昔日的场景在自然界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每一处自然风物都带上了人类情感的羁绊,那么这里的情与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完美的交融契合。而《小风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更深了一层。诗歌采用了倒叙的形式将一个归乡的游子内心的波澜层层掀开,“风”见证了“多年前我顺风漂移的轻/行囊的重”,“风”也懂得在衣锦还乡的荣耀之下所经历的辛劳。当此时的“我”已归于尘土,成为“一捧泥土的组成部分”,并且“愿意就此身陷故土心如止水”,但是“风”——这个自然界的精灵仍然会找到这个曾经不甘寂寞的灵魂,纵使时间已经模糊,岁月早已变迁,“我们”已经回归到了生命最初的形态,人类经历过的所有荣辱苦难在这里已然化为乌有,但是自然界作为最终的见证者,它的记忆永远不会抹去。
无论是动物界无奈的命运轮回,还是自然界留给人类飘渺、神秘的印记,都源于对生命存在形态的深切追问。如何活着,如何面对不可掌控的未知,在尘埃落定之后的灵魂如何安置,面对种种困惑,“信仰”的意义似乎也愈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