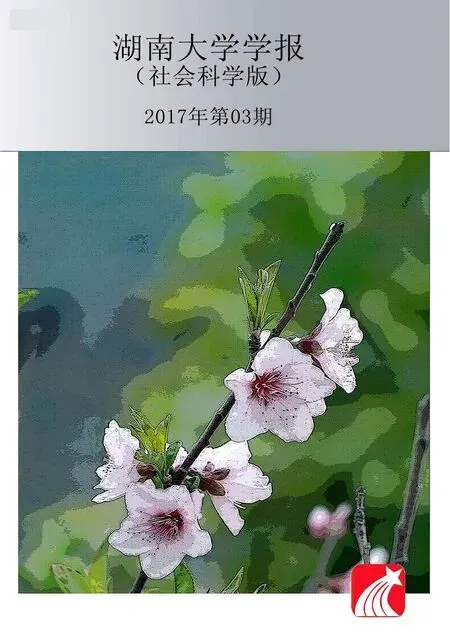传统军礼的萌芽、演进与初步成型
陈 雄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传统军礼的萌芽、演进与初步成型
陈 雄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中国古代军礼的渊源可追溯至远古洪荒时期,至少在黄帝时已有“命将”“振旅”等仪,后历经尧舜直到夏末,此为传统军礼漫长的萌芽时期。殷商时,军礼的五个项目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大师之礼”的“告庙”“谋伐”“册命”“迁木主”“逆旅”“献俘”等均见于甲骨。周承殷制,“大师礼”的部分项目(“谋伐”“册命”等)及“大蒐礼”与殷代类似,它如“告庙”有“类祭”、“振旅”有“丧迎”皆其所异。要之,周代军礼的各种仪式渐趋成熟,每个项目基本都配有一套完整的仪注,传统军礼至此已大体成型。
军礼;萌芽;成型;殷商;周代
关于军礼,《周礼》将其分为“大师”“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五个项目。*见《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沈凤笙(文倬)先生释曰:“五个项目中,大师之礼是天子或诸侯的征伐行动,究竟要举行多少典礼,经传亡佚,已无法稽考。但宗庙谋议,命将出师,载(木)主远征,凯旋献俘,凡《诗》《书》《国语》《左传》等书所涉及的,处处都有典礼的痕迹,可见军礼的内容是繁复的。大田之礼是定期狩猎,而军事演习往往寄托于狩猎活动。还有三个项目俱凭借军事力量来进行的国家事务:大均之礼是王在畿内、诸侯在各自的封国内校比户口、厘定各项赋税,依仗威力推行,自能减少阻力;大役之礼是国家兴办的筑城邑、建宫殿,以及开河、造堤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无偿征发的民工,如不用军法部勒,自难迅速完成;大封之礼是勘定国与国、私家封地与封地间的疆界,需要依靠军事力量的支持和保障。这三项重要事务至少在开始和结尾时需要有礼仪性活动。”[1](P904)后三个项目如沈师所说,属“国家事务”,其军礼的纯粹性不如前二者,再加上史料的阙如,我们只好是兼而顾之。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大师之礼与大田之礼这两项,对此,我们从追溯军礼在远古时期的萌芽开始,经过唐虞夏商这段漫长的演变过程,直至周代军礼的初成。
一 先殷及商代军礼的萌芽与发展
在远古洪荒时期,各个部落之间不免会出现一些争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提到的黄帝部落与炎帝、蚩尤部落的战争: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这里的“修德振兵”“帝命”“征师”等与后来的诸如“命将”“振旅”“征伐”等军礼军仪无疑有着渊源关系。也就是说,战争就离不开军队,军队必定有首领负责集结、指挥、行军等,军队出发之前可能还会有占卜祭祀祈祷之类的活动,*原始先民关于自然界知之甚少,他们对天地人鬼甚至包括一些动物(它们往往被视为本部落的图腾)在内充满了敬畏与崇拜之情,所以他们的祭祀活动几乎无处不在,像军队的出动此等大事怎会不祭祀。打了胜仗会有一定的仪式庆祝一番,这些都可以视为军礼的萌芽。
尧舜时,除军礼继续向前推进外,宗法制度开始萌芽,孟子说尧舜禅让之后舜曾到“河之南”以避开丹朱(尧子),舜禹禅让之后禹也曾到阳城以避开商均(舜子)。*见《孟子·万章》:“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舜、禹为什么要避先君之子呢?他们好似将普通家庭的父母去世将财产分拨给子女的观念潜移默化的映射到了国家层面,这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奇怪,因为换个角度思维,国家就是放大了的“家”,这其实就是宗法的萌芽。禹后,情况不同了,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的:宗法从“萌芽”到“成熟”的生长速度显然比“礼制”要快得多,总之,宗法与吉凶宾军嘉五礼的缘起相比起来最起码在时间上并不是先后者而生的。然,诚如陈师所说:“礼与礼制的产生在宗族宗法之前。但是自从有了宗法,礼与礼制就离不开他了。宗法一旦产生,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礼制(当然包括军礼)的重要部分。”[2](P727)
到夏朝,由始及终,其间所发生的战争不可胜数。启即位之初,即有伐有扈之战,《史记·夏本纪》载: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战争即将打响之前有《甘誓》之作,这有点类似于誓师大典,“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周礼·春官·小宗伯》),听从军事命令的于“祖”前有赏,不听命令就会遭到在“社”前被杀的命运,后世所谓“告庙礼”“立军社礼”与此的渊源关系不言而喻。《尚书·五子之歌》还提到启子太康的畋猎:“(太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此为类似于违反军礼大田之礼在史册中较早的记载。其后各帝均有征伐行动,至夏桀征有施、伐岷山最甚,不断的征伐加上大兴土木(此间或多或少有一点“大役之礼”的痕迹),《史记》谓:“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最后“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夏朝灭亡。
殷代军礼有关的史料非常丰富,加上甲骨文旁证,我们尝试还原一下殷代军礼的大致结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大师之礼”,殷商所涉及此礼的内容包括“告庙”“谋伐”“册命”“迁木主”(载主远征)“逆旅”“献俘”“振旅”等。
前面说过,有虞、夏后之前的原始先民对神灵的崇拜贯穿于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殷人亦不例外,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都要预先卜问吉凶:
乙卯卜,贞:王比望乘伐下危,受有佑?贞:王勿比沚戛伐巴? 丁巳卜,贞:王教众伐于方,受有佑?王惟出循?庚申卜,贞:作宾?(《甲骨文合集》32)[3]
甲午卜,宾贞:沚戛启……王比伐巴,受有佑?(《合集》6471)
王勿惟沚戛比伐巴方,帝不我其授佑?二告。(《合集》6473)
贞:王比戛伐巴,帝授佑? 翌乙巳侑祖乙?王勿比鬼?(《合集》6474)
这里的“帝”属殷人天神崇拜的范畴,“祖”即祖先,从这些丰富的卜辞看出,殷人不厌其烦的对战事进行预先的卜问,祈求得到天地和祖先的护佑。除此之外,甲骨文中还频频出现“告”“祖”“宗”“征”“伐”等字眼。“告”的对象往往是“祖”,即诸如“大甲”“示壬”“祖乙”等殷商历代先祖;“宗”即宗庙,是殷商先祖的庙堂,也即祖庙;由此看来,“大师之礼”中的“告庙之礼”在殷商已有施行是确定无疑的了。而“征”“伐”就是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了,我们从甲骨文中看出,商代的征伐分商王亲自带兵与否两种情况,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要精细的“谋划”一番,甚至要进行一些仪式,当然,“谋划”的目的当是为了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从甲骨文中时常看到“比…伐…”的句型结构,这是殷人与其他部落、方国等结成的军事同盟的关系,这无疑是“谋划”的结果。准备工作完成了,接下来就要出征,如果不是天子亲自出征,还要行“命将”与“册命”之礼:
辛丑卜,宾贞:令多比望乘伐下危,受有祐?二月。(《合集》6525)
乙卯卜,殼贞:王勿比望乘伐下危,弗其受祐?(《合集》32)
贞:惟子画呼伐?(《合集》6209)
贞:惟师般呼伐?(《合集》6209)
己巳卜,争贞:侯告爯册,王勿卒……(《合集》7410)
□卯卜,宾贞:舟爯册,商若? 十一月(《合集》7415)
从前四条看,商代对将领的选择极为重视,认为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吉凶,所以他们不断的占卜。即使商王亲征,将领对王的辅佐作用亦不可忽视,上引前两条就是在占卜武丁时期的“望乘”随王征伐的吉凶。关于“爯册”,于省吾先生说:“称,谓述说也;册,谓册命也……振旅出师必有册命。”[4](P166-169)于先生对于“爯”的解释可备一说,对于“册”的解释当是合理的,选择好了将领要进行一些仪式,此即“册命之礼”。此礼既罢,即将远征,甲骨文常见之“示”字,据唐兰先生考证,当为“主”[5],亦即“神主”“木主”之意。所以,“载(木)主远征”之仪殷商即有,目的是为了在战争中及时向木主祈求、占卜以获得护佑。如果战争胜利,会俘获一些战俘,将在祖庙行献捷与献俘之礼,如同出师“告庙礼”一般,向先祖报告战争成果,然后商王会对得胜的将士进行嘉奖,可能还要大肆庆祝一番,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商代军礼军仪的组成部分。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振旅”,这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刻,如:
丁丑王卜,贞:其振旅,延过[于]盂,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在九[月]。(《合集》36426)
丙子卜,贞:翌日丁丑王其振旅,[延]过不遘大雨?兹御。(《合集》38177)
如前所说,“振旅”的目的是向列祖列宗的神灵“献功”,一则感谢祖先的护佑,一则以示自己不敢居功,其仪式是对战俘特别是战俘首领的处决,所以,“振旅”或多或少有一些“献俘礼”的成分在里面。另外,如果不是商王亲征,当有一个对得胜将士的迎接或接风仪式,这对后代的军礼亦有影响,我们称其为“逆旅”,与此礼相关文字亦多见于甲骨。
大田之礼主要指商王的田狩(田猎):
丙寅卜,子效臣田,不其[获]羌?(《合集》195)
……伐下危?……归田?九月。(《合集》6521)
贞:卯?贞:勿卯?王勿归,惟呼?贞:王归?呼酒登?贞:示?贞:勿示?勿呼田?令戊田……(《合集》7772)
乙未卜,今日王狩,田率,擒?允获虎二、兕一、鹿十二、豕二、彘百廿七、□二、兔廿三、[雉]七。□月(《合集》10197)
……王获鹿?不其获?允获四。贞:弗其擒麋?王获兕?王弗其获兕?获不?允乙未卜,翌丙申王田,获?允获鹿九。(《合集》10309)
……获麋四百五十一。(《合集》10344)
庚戌卜,今日狩,不其擒印?(《合集》20757)
戊子卜,王往田于东,擒?辛卯卜,王往田于东,擒?(《合集》33422)
戊戌,王蒿[田]……王来征……(《合集》36534)
……于倞麓,获白兕……王来征盂方伯……(《合集》37398)
大田之礼在其性质和目的上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军事演习。田猎之前要卜问吉凶,这是他们的传统,卜问内容是询问能否得到猎物。依后世所谓大田礼定制,田狩大部分情况是有定日的,但我们从卜辞看到,商人对田猎之日无所谓确定性*本文所说商王田猎无定日是相对于整个殷商王朝始终来说的,而关于具体各时期商王田猎的日期,李学勤、陈戍国二位先生均做过研究,参见《殷代地理简论》之第一章、《先秦礼制研究》之第三章。,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吉凶与否。不管哪一日田猎,只要有收获,就要把猎物带到宗庙如同战争后的“献俘礼”一样有一个贡献猎物的仪式,用自己亲自打来的猎物来祭祀先祖,是他们表达虔诚的一种方式。关于商代大均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的文字在甲骨文中极少出现,但商王对自己疆域内百姓进行管理之时要对人口进行登记、管理,也要收取一些税赋,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太平的,但总是有些特殊情况要靠武力的保障,这便有大均之礼的成分在里面了。殷商的都城出现过若干次的大迁徙,贵族不会自食其力去大兴土木,还有战争要筑城、治水要造堤、农业要兴修水利,这些大规模的工程要征发苦力,甚至是无偿的征用,这其间武力的支持必不可少,这就是“大役”,若其中多少有一些礼仪性的活动,即是“大役之礼”。商王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他所能行使完全意义上的主权的仅仅是“邦畿之内”,邦畿之外有大小千余诸侯国,这些国与国之间,特别是诸侯国与中央之间的疆界划分离不开“大封之礼”,起码在确定了疆界之后应该会有一个仪式,由于材料的匮乏,我们无法详究。
二 周代军礼的建构与初步成型
周代基本继承了夏商以来的鬼神崇拜,但有鉴于商代灭亡的教训,周人更为重视“德”。比如对天帝的崇拜,他们依然认为天神是王权的授予者和监督者,但他们要为自己所承系天命的合法性做辩护,还要回答为什么殷商如此敬重并崇祀天神却仍然绝灭的原因,周人给出解释是:天神是无私的,他以“道德”作为标准赏善罚恶,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君王必须“敬德”方能“保民”从而得到上天的保佑,这种“以德配天”的思想,给周人的天命神学注入了理性主义的因素,使得周人的思想向人文主义发展。因此,我们在周代礼制(尤其是在军礼)中发现周人在进行某件或大或小的事情之前不再像殷人那样不断的占卜、反复的贞问吉凶,尽管周人也经常进行一些卜筮活动(这种传统是不可能绝迹的,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之时),但远没有殷商那样繁复。此外,还有一个时代划定的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和西周相接的周代后一时期——东周,周礼逐渐走向了衰变和崩溃,这的确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也不当是毫无周礼之留存,通过广阅先秦各方面相关的典籍我们认为,最起码就军礼而言,春秋与战国时期对周代军礼大体上是继承的,只是在一些具体的仪节上(如战前战后的祭礼)有若干改革罢了,这些不同于西周军礼的方面在我们接下来的论述中也会加以关注,然不论怎样,其礼意大致相通,所以本文所探讨的周代军礼包括春秋战国时期。
关于“大师之礼”,首先是“告庙”:
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周礼·春官·大祝》)
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尔雅·释天》)
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庙,择吉日斋戒……(《孔丛子·问军礼》)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礼也。(《左传·桓公二年》)
梁馀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左传·闵公二年》)
这里谈到了“设军社”、“有事乎社”、“脤于社”,“社”即“社神”,以上所引皆是战前祭祀社神之事,祭祀之物一般为肉,称为“脤肉”,祭祀结束之后还要把“脤肉”分发给参与者,战前祭社在周代之前是没有的,可能为周代军礼之新内容。与祭社相对应,战前还有祭祖的仪式,也即“告庙之礼”,依周代军礼,告庙之礼虽曰“告”亦应“受”,即“受命”。周代吉礼天子七庙,故而告庙需有一定的次序,又因为受命必须是受“庙主”也即“始祖”之命,所以要最后“受命”。换言之,战前的祭祖与告庙之礼当是先从近祖庙开始,最后到始祖庙祭祀并“受命”。当然,不论祭社还是祭祖,“择吉”“斋戒”之事以及卜祝之辞是免不了的,这些都是在表明自己的虔诚之心、体现整个仪式的庄严与肃穆。与“告庙”相关的是“谋伐之礼”,合称“宗庙谋议”,这是在谋划战争的策略,比如建立军事同盟、制定战争路线等等,此礼与殷商基本相似,不再累述。再者,关于战事的祭礼除了“祭社”“祭祖”之外还有“类祭”(可能是祭祀“上帝”也可能就是上面的“祭社”或“祭祖”)、“祃祭”(类似于祭祀战神,但在后世慢慢演化为“祭旗”“祭牙”等),如《诗经·大雅·皇矣》曰:“是类是祃,是致是附”,但详细的仪式已很难考证了。
其次是“迁庙主礼”(载〈木〉主远征):
九年……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遂兴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史记·周本纪》)
社稷不动,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左传·定公四年》)
臣战,载主契国以与王约,必无患矣。若有败之者,臣请挈领。然而臣有患也……(《战国策·秦三·魏谓魏冉》)
我们看到,武王曾两次兴兵伐纣,第一次由于各种原因(如武王自己说是“未知天命”)中途而返,第二次不仅得以顺利进行,还进行了誓师大典*牧野之战打响前,似还有一次誓师大典,如《尚书·牧誓》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我们发现这两次的誓词内容大致相近,所以两次誓师大典也可能就是同一次,附之。,誓词的内容是历数纣王的种种罪行,也即之所以“伐纣”的原因,其目的是为自己的征伐行动提供理由,以彰显自己所带军队的正义性,并起到振奋军心、鼓舞士气、严明军纪的作用,总之,他要表明自己是“代天行伐”,是仁义之师。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中国古代的任何战争至少在字面上都强调“正义”,但凡能与“正义”挂上钩,就能获得各个方面的支持,所以,总是要有足够的“理由”来装饰其所发动的战争,“誓师大典”的“誓词”即此作用。而关于“迁庙主礼”,此四则材料皆提到了“载木主”之事,前两条是武王载文王木主而伐纣,第三条引的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子鱼的话,最后一条可能是张仪或者毋泽说的*魏谓魏冉曰:“公闻东方之语乎?”曰:“弗闻也。”曰:“辛、张阳、毋泽说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战,载主契国以与王约,必无患矣。若有败之者,臣请挈领……’今公东而因言于楚,是令张仪之言为禹,而务败公之事也……”(《战国策·秦三·魏谓魏冉》),但肯定是出自战国无疑,也就是说,“载木主礼”在经历了春秋战国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之后仍然是有留存的。
再次是“命将”与“册命”之礼: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诗·大雅·江汉》)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诗·大雅·常武》)
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虢季子白盘》铭文)
其后襄之二路,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此四则说的都是命将之事,命将与册命是出征前最为庄严肃穆的典礼,前两条是周宣王命令召穆公平淮夷、程伯任大司马*是周代辅佐王室的军事长官,《周礼·夏官》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均未涉及具体的仪节。第三条虢季子白盘的铭文中,“乘”即战车,“马”即战马,“弓”即弓箭,“戉”即大钺;第四条中,“二路”即大辂、戎辂之车,“鏚钺”为斧钺、“秬鬯”是黑黍酿造的香酒,“彤弓”是红色的弓、“虎贲”即勇士甲兵。所以,册命将领之时当有所颁赐,比如上面提到的“鏚钺”就代表王权,如《尚书·牧誓》说:“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赐给将领斧钺就是要代行王权讨四方。而前面我们说过,商代对将领的选择极为重视,因为将领的当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周代亦如此,册命将领决不是随心所欲的,要与宗室、大臣们反复商量、讨论之后才能定夺。一旦定下了将领人选,就要进行卜筮、择吉,要到宗庙当面授命,以上所列赐斧钺、弓箭、车、马之类皆在此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命将册命之礼”。
复次是“献捷”之礼:
夏六月,齐候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左传·庄公三十一年》)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左传·成公二年》)
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按,周代军礼之“献捷”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奉周王之命所行的讨伐之事在获胜归来后方能行“献捷之礼”,正如定王所说:“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而且,如果奉王命讨伐的是诸侯国,那么,即使凯旋归来也不行献捷礼,换言之,献捷礼只针对奉王命征伐“夷狄”而言。然而我们从以上三条材料来看,春秋时期所行的献捷之礼已经不合理(礼)了,第一条说的是齐侯向鲁庄公献捷,一则没有奉王命,一则所献对象为诸侯,非周王,实为非礼之举;第二条是晋侯派巩朔向周定王献捷,不当之处亦有二,一是没有奉王命,二是所献战俘为诸侯国战俘,此举非礼已甚;第三条说的是晋楚城濮之战,晋人曾两次向周襄王献楚俘,此次战役晋人当亦未奉王命,但却两次都受到了襄王的礼待,这里面一则因为周王室自来有视楚国为“南蛮”的传统(实际上楚国最初也确实只是“子”爵),另一方面可能跟长期以来受冷落的政治地位有关,现在有人想向自己行礼——而且是诸侯当向天子所行之礼,虽然有违礼的成分(未奉王命),或可欣然接受了吧?但不论怎样,前面我们说献捷礼只针对奉王命征伐“夷狄”而言的,那么诸侯之间就更加不存在什么“献捷”了,然而春秋、战国时的礼崩乐坏大环境亦触及到此,诸侯之间相互“献捷”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周代献捷的军礼到东周已经发生了质变。
最后是“振旅”之礼:
伐鼓渊渊,振旅阗阗。(《诗·小雅·采芑》)
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振旅阗阗,出为治兵,尚威武也,入为振旅,反尊卑也。(《尔雅·释天》)
隹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王令毛白(伯)更虢城公服……公告氒(厥)事于上,唯民亡茁(拙)才(在)彝,昧天令,故亡……(《班簋》铭文)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南宫贶。王赐……(《中觯》铭文)
明,王格周庙,□□□□宾延邦宾尊其旅服,东向……王令盂以□□伐鬼方……王命赏盂……(《小盂鼎》铭文)
在战争获得胜利之后即行“振旅”之礼,对“振旅阗阗”,毛氏传曰:“入曰振旅,复长幼也”,这个解释与我们所引第二则材料是一致的,那么由此看来,“振旅”与“治兵”一“出”一“入”,一“尚威武”一“反尊卑”,有来有往,军权的使用亦是有“授”有“归”,这就是“振旅之礼”的意义所在,即完成同属一种礼仪的往复与循环,这也是军礼与其他诸礼的相通之处,即“尚往来”。军队凯旋归来,除了前文所讲要向周王“献捷”之外,将领还要到宗庙报告战事成果,如《班簋》铭文谓:“公告厥事于上”当是此仪。天子例行慰问、检阅,对于有功的将士进行嘉奖,如《中觯》与《小盂鼎》铭文所讲“省公族于庚”“王赐”“王命赏盂”之类为此意。其他比如对阵亡将士的哀悼,以及对其家属的抚恤亦是“礼”所当然,而对于那些不从王命之人也要进行处罚,如“师旅鼎”的铭文便有类似的记载。此外,有战争就有胜负,有战胜之礼亦有战败之礼,战败者简而言之就是要以“丧礼”处之,要“丧迎”,甚至还有可能“哭师”“哭庙”等。
接下来我们讨论周代军礼的另一个项目:大田之礼。周代大田之礼的材料颇为丰富,我们从中摘录有代表性的如次:
四时之田(畋),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谷梁传·桓公四年》)
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尔雅·释天》)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礼记·王制》)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诗经·大雅·灵台》)
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史戒泉庶,修战法,虞人菜所田之野,为表;百步则一,为三表,又五十步为一表,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乃陈车徒,如战之陈,皆坐,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车徒皆噪,徒乃弊,致禽饁兽于郊。入,献禽以享烝。(《周礼·夏官·大司马》)
按,大田、田狩之礼又被称为“大蒐”之礼,《谷梁传》谓“秋曰蒐”,《左传》也有此说*《左传·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红。”,盖“秋主肃杀”,故以秋蒐代四时田猎之名。然《尔雅》又有“春蒐”“秋狝”之说,“狝”亦有肃杀之意,《左传》同样也有“秋狝”之说*《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我们不拟对两说的取舍详细论述,依陈师见解,当以《尔雅》较为合“礼”[6](P298-299)。但是,从第三则材料我们看到,《礼记》谓“岁三田”,虽未将“三田”对应于季节,却将“三田”所获分用于“乾豆”“宾客”“君庖”。我们认为,《礼记》系晚出,其所谓“三田”之说存疑,而将田猎所获分用于祭祀、宾客之类当可信,而且,它所提出来的“不合围”“不掩群”以及“田”要以“礼”颇有自觉维护生态的意味,甚合礼意!第三则材料“灵台”“灵囿”是文王时田猎的场所,“灵沼”即池沼,或为文王渔猎之所,而照字面意思,“灵台”当是靠庶民之力“攻之”,这里面是否涉及到大役之礼已不可得闻。最后一则材料是关于大田之礼的具体仪节,略述如次:首先是田猎之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除去一些杂草之类的障碍,这个工作由虞人来做;除去了杂草就要“为表”,即设置“标志”,一百步设一表,先设三表,再间隔五十步设一表。然后是田猎当天早晨,司马要提前在后两表之间设立旗帜,各个乡吏率所辖民众扛着旗、敲打着钟鼓、木铎、金镯、金铙等乐器来到司马所立旗帜之处。然后在天亮之前隐蔽旗帜,对于迟到的人要进行处罚。接下来就如同军事化一般布阵,一应徒众、车马按照将领的要求陈设,如同战争即将打响一般严阵以待。接下来,各军吏在阵前恭听誓言(类似于誓师大典),然后斩杀牲畜殉左右军阵,说:“有不服从命令的,斩(就如同这牲畜一般)”。再往下是中军大将击小鼓命击鼓三通、司马振木铎、军帅举旗、众徒起立,还有前进、停止、再击鼓、放旗、徒坐、又击鼓等等如此进坐反复直至击鼓进攻、再次退回,到此,田猎开始,还要布阵、划分地段、设置栏阻野兽的车,举行祭祀,大兽留给贵族,小兽自取,割兽左耳以计功。田猎停止之后要集中起来进行祭祀,进入都城更要以所猎禽兽祭祀宗庙。以上便是周代大田之礼的大致轮廓。再有关于周代“大均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一则史料涉及太少,一则如沈先生所说属“国家事务”,虽“至少在开始和结尾时需要有礼仪性活动”,但毕竟不如“大师”“大田”之礼那样贯穿于事物始终,况且,这些仪节大多已不可考,再加上我们前面大致介绍了商代此三种礼仪的大致情况而周代的相关内容并无太大差异,所以关于军礼的这三个项目便付诸阙如了。
通过以上对周代军礼的粗略的描绘,我们认为,军礼的五个项目在周代应该都具备了一套完整的仪注,可惜的是这些仪注大多都已不见于史料,尤其是“大均”“大役”“大封”这三个军礼项目无法考证,但我们从所见的包括出土文献、青铜器铭文等在内的相关材料仍然更够看出周代军礼的大致面貌,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军礼在周代已基本成型。周代军礼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有些仪节如誓师大典、命将礼、振旅、阅兵仪等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直到清末,我们仍能看到周代军礼的遗存,就是当代社会,我们设定的“烈士纪念日”,在抗战纪念日举行的“阅兵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周代军礼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1] 沈文倬.菿闇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3]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2.
[4] 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唐兰.怀铅随录(续)[J].考古社刊,1937(6):328-332.
[6]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Germination,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Salute
CHEN Xiong
(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The origi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ilitary salutes should trace back to the immemorial times.In the time of Yellow Emperor to Yao and Shun, the etiquettes like “Mingjiang” and “Zhenlv” already existed, which was the sprout period of the long-term traditional military salute.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 five projects of military salutes got a certain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Dashi Ceremony”, in which “Gaomiao”“Moufa”“Ceming”“Qianmuzhu”“Nilv”“Xianfu” and other contents were recorded on turtle shell.Then in the Zhou Dynasty, parts of “Dashi Ceremony” were similar with those in Shang Dynasty, while the difference showed in the addition of “Gaomiao” to “Leiji” and “Sangying” to”Zhenlv”.To sum up, the ceremony of military salutes of Zhou dynasty was gradually mature, and each project was equipped with a complete set of notes, which means a general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salutes had been taken shape.
military salute;germination;maturation;Shang dynasty;Zhou dynasty
2016-10-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3&ZD05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12AZD077)
陈雄(1988—),男,河南新乡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礼学。
K892.98
A
1008—1763(2017)03—00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