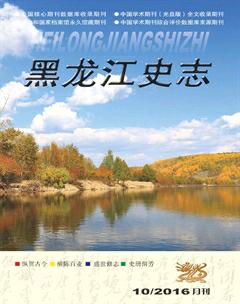郑玄注《三礼》方法略探
[摘 要]自郑玄注解《三礼》之后,始有《三礼》之名。郑玄注经,先是总体上纲举目张,兼采今、古,既注重名物训诂,又注重章句之释,然后再具体而微,深入到经文的具体字词,兼用直训和义界的方法注解之。
[关键词]郑玄;三礼;今文经;古文经;注经方法
所谓《三礼》,是指《周礼》《仪礼》和《礼记》。这三部传世文献,奠定了中国传统礼制的基础,研究者代不乏人,注疏者亦难以计数。但影响最大者,非东汉学者郑玄莫属。
虽然《后汉书·马融传》言马融所注之书中有《三礼》,(1)同书《卢植传》亦言卢植作有《三礼解诂》,(2)但此《三礼》,有学者认为是《后汉书》作者范晔自起之名,“盖范蔚宗自后记而名之欤?”(3)因为同书《儒林列传下·董钧传》有言“(郑)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4)近人黄侃《礼学略说》亦云:“……郑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礼》者(以《周礼》、《仪礼》、小戴《礼记》为《三礼》,亦自郑始。《隋书·经籍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5)可见,《三礼》之名,始自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东汉经学世家子弟,顺帝永建二年(127)生,献帝建安五年(200)卒。据《汉书·郑玄传》,其先从京兆第五元习今文经,又从东郡张恭祖通古文经,后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灵帝末,黨禁解”,虽被征辟,但仍隐居不仕,专心经业。“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万余言。”(6)其著述宏富,除本传所载之外,另有《周礼注》、《丧服经传注》、《丧服变除注》等。(7)
笔者在读郑注《三礼》之时,结合时彦前贤的研究成果,细致思考,发现郑玄注经是先总体再具体,采用层层深入的方式,既高屋建瓴,又具体而微,总体感觉是循序渐行,逐层深入,有章可循。现试探之。
一、纲举目张,兼采今古
《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章帝下诏白虎观:“(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欲议减省。”(8)《后汉书·桓郁传》:“初,(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9)《后汉书·张霸传》:“初,霸以樊■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词,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10)《后汉书·张奂传》:“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11)在《后汉书》中,多可见关于汉代经注“浮辞繁多”之弊,为此,统治者多次下令删减,但结果却不理想。至郑玄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12)在这种情况下,郑玄提出了“纲举目张”的注经方法。在《诗谱序》里,他对自己的注经方法作的概括:“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纲举目张”之法,可谓有的放矢。
在“纲举目张”之法的指导下,郑玄注经往往简明扼要。据统计,其经注之文字,往往少于经。如《仪礼》之《有司》篇经4790字,注3356字。《礼记》之《学记》、《乐记》两篇,经6459字,注5533字;《祭法》、《祭义》、《祭统》三篇,经7182字,注5409字。凡此种种,皆注少于经。另据郑氏门徒仿照《论语》所整理关于其言论的著作——《郑志》,郑玄答张逸语,“……文义自解,故不言之。”(13)为了简洁明了,对于“文义自解”之处,常常“不言之”。比如《周礼·地官·司稽》有“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郑注:“不物,衣服视占不与众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14)对于此句经文的注解,确实唯“不物”一词令人犯难,余者皆可“文义自解”,郑注抓此关键,全句之意即明。
如前所述,郑玄所生活的时代,不惟立于官学的今文经“异端纷纭”,家法林立,浮辞繁多,学者之间“互相诡激”,彼此诘难,令“后生疑而莫正”,尚有今、古文经学之对垒。那么,郑玄作为贯通今古文的大家,注经时就能够高瞻远瞩,冲破家法之藩篱,打破今、古之壁垒,网罗众家,兼采众长。对此,皮锡瑞有一段议论可明:
案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丘《易》又亡,无以考其异同。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多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15)
同时,也正是因为郑玄注经,兼采今、古两家的特点,既看重“训诂名物”,又重视章句之义,“……有时不得不繁。岂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二字,至十余万言之比哉?”(16)故而遭到诸如黄侃这样的古文经学家的“讥其繁”。
二、名物训诂与章句释义兼重
一般而言,今文经学注重章句释义,擅于汪洋恣肆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但其弊端也如前所述,常常“浮辞繁长,多过其实”,(17)故为杨终指责:“……章句之徒,破坏大体”。(18)而古文经学家,重在训诂,举其大义,不为章句。《后汉书·桓谭传》谓其“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19)《后汉书·班固传》谓班固“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20)《后汉书·王充传》也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21)《卢植传》同样也说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22)等等,皆谓古文经学家好训诂,不守章句之实。但郑玄注《三礼》,兼采今、古,前已述及,正是由于兼顾名物训诂和章句之释,“有时不得不繁”。
郑注《三礼》中,关于名物训诂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周礼·天官·笾人》:“掌四笾之实”,郑注:“笾,竹器如豆者,其容实皆四升”;(23)《礼记·玉藻》:“王后■衣,夫人揄狄”,郑注:“■读如■,揄读如摇。■、摇皆翟雉名也。刻缯而画之,著于衣以为饰,因以为名也。后世作字异耳”;(24)《仪礼·士昏礼》:“设洗于阼阶东南”,郑注:“洗,所以承盥洗之器弃水者”。(25)
当然,既然兼采今、古,兼重训诂与章句,郑玄并非毫无目的的“繁”,而是为更全面明晰地解释经文服务的。比如《周礼·地官·媒氏》:“禁迁葬者与嫁殇者。”郑注:“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乱人伦者也。”(26)此句经文,若无对“殇”字的训诂,就难以理解经文的全意,章句之释亦不会如此易懂。
三、长于直训和义界
传统训诂学中训释的方式有多种,章太炎先生曾经进行了归纳,他认为:“训诂之术,略有三涂,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27)章学后人黄侃亦云:“训诂之方式,以语言解释语言,其方式有三: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三者为构成训诂学之原因,常人日用而不知者也。”(28)尽管学者们的分法有异,但总体而言,在郑注《三礼》的训诂方式中,据笔者所见,至少有直训和义界两种。
在名物訓诂和章句之释兼用的情况下,为了便于注经的简洁扼要和利于阅读,郑玄在注释词义时,常常采用直训的方式。所谓直训,即“直接用单词训释单词的一种释义方式”,(29)就是在注释时选用常人容易理解的字词,以解释经文中较难理解的部分,从而扫除阅读经文的障碍。而常人容易理解的字词,一般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意义相同的词,即同义词,具体操作就是选用与经文中意义相同的字词来解经。此例不胜枚举。如《周礼·天官·大宰》篇:“以八柄诏王驭群臣。”郑注:“诏,告也,助也。”(30)即此句经文中“诏”的意思与“告”相同,将“诏”理解成“告”,有助于理解经文。《仪礼·觐礼》:“坛十有二寻,深四尺。”郑注:“深谓高也。”(31)就是“深”、“高”同义。《礼记·曲礼》:“疑事毋质,直而勿有。”郑注:“直,正也。”(32)同样是用同义词注经。此外,在找不到合适的同义词的情况下,郑玄就退而求其次,选用意义相近的词加以解释。如《礼记·哀公问》:“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算,备其鼎俎。”郑注:“言,语也。”(33)《说文·言部》:“直言曰言,论难曰语。”(34)“言”和“语”本来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在此处,都可指“表达”或“说”之意,算是运用二者词义相近的现象来解经。另如《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郑注:“典,常也,经也,法也。”(35)此句中的“典”本意是指“五帝之书”,但结合上下文,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则可理解为一般原则和规律,所以在解释的时候,郑玄选用了几个意义相近的词对其进行注解和补充,以期更加充分地表达“典”字所传达的内容。
在同义词或近义词无法注经,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同义词或近义词的时候,郑玄就采用义界,即下定义的方法,使经文的注解更易于人们理解。如《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以旌为左右和之门。”郑注:“军门曰和,今谓之垒门,立两旌以为之。”(36)就是归纳出相关字词的外延和内涵,以下定义的方式,将其说明之。但此种注经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其弊端。那就是词义的改变,致使人们不仅对经文原字的理解不知所以,且对其所下的定义亦不知如何解读。所以,在郑注中,这种下定义的方式,相对于直训的方式,不甚普遍。当然,郑玄对经文中具体字词的注解,所采用的方法,肯定也不止直训和义界这两种,而笔者只是就自己所熟悉、所察觉的这两种方法分析之罢了。
四、余论
经书难读,更难懂。不仅唐代大文豪韩愈为之苦恼不堪,(37)清代硕儒阮元亦深有同感。但郑玄却能贯通今古文,遍注经文,而《三礼》经文,也因此举,嘉惠后学。但由于郑玄所生活的时代,不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研究与注解都硕果累累。这就决定了郑氏在注经时不得不独具慧眼,在兼采今、古的同时,采用纲举目张、简明扼要的方法。并打破今、古经学家法的藩篱,兼重名物训诂和章句之释,在具体的字词解释方面,采用直训和义界的方式,做到注经的简明易懂。
统而观之,郑玄所采用的注经方式,可谓层层深入,循序渐进。先是高屋建瓴,从总体上统观全局,提纲挈领,“举一纲而万目张”,做到以点带面,从而“解一卷而众篇明”。然后,再根据今、古文已有的研究成果,为了兼采并蓄,取长补短,而兼用名物训诂和章句释义这两种在此之前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互不兼容的注经方式。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到具体经文字词的解读,采用直训和义界的方式训释经文。如此,从面到点,从全局到具体,郑玄注经犹如层层剥笋,既兼顾得当,有条不紊,又透彻深入,巨细无遗。
注释:
(1)[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72页。
(2)[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16页。
(3)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4)[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下·董钧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77页。
(5)黄侃:《礼学略说》,见氏著《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48页。
(6)[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7-1213页。
(7)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8)[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下《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页。
(9)[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七《桓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56页。
(10)[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张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42页。
(11)[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38页。
(12)[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2-1213页。
(13)《郑志》答张逸云,见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卷第一《国风·周南·螽斯·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14)李学勤:《周礼注疏》卷第十五《地官·司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9页。
(15)[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页。
(16)黄侃:《礼学略说》,见氏著《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49页。
(17)[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七《桓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56页。
(18)[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99页。
(19)[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55页。
(20)[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0页。
(21)[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9页。
(22)[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13页。
(23)李学勤:《周礼注疏》卷第五《天官·笾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24)李学勤:《礼记正义》卷第三十《玉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09页。
(25)李学勤:《仪礼注疏》卷第四《士昏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26)李学勤:《周礼注疏》卷第十四《地官·媒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
(27)章太炎:《与章士钊》,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7页。
(28)黄季刚著,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6页。
(29)徐启庭:《训诂学概要》,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30)李学勤:《周礼注疏》卷第二《天官·大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31)李学勤:《仪礼注疏》卷第二十七《觐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5页。
(32)李学勤:《礼记正义》卷第一《曲礼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
(33)李学勤:《礼记正义》卷第五十《哀公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4页。
(3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35)李学勤:《周礼注疏》卷第二《天官·大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36)李学勤:《周礼注疏》卷第二十九《夏官·大司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79页。
(37)见韩愈《进学解》:“《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及《读<仪礼>》:“余嘗苦《仪礼》难读……”参见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39页。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2016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仪礼·士昏礼》相关文献与注疏研究”(项目编号:2016QN29)
作者简介:雷铭(1982-),男,汉族,河南信阳人,安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