踯躅于历史骸山的新天使
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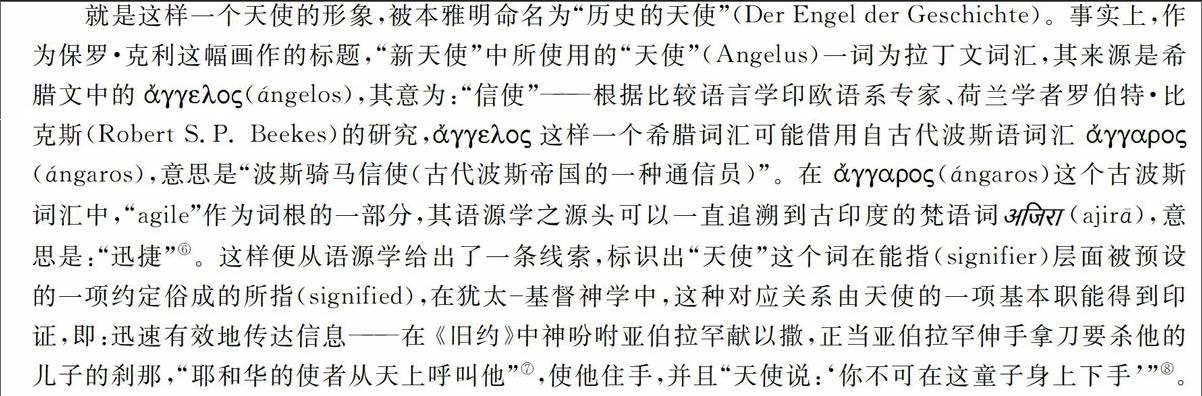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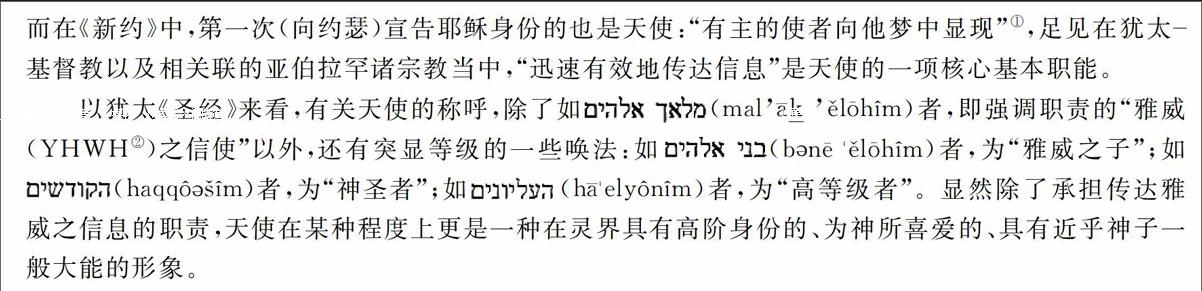
摘要:藉由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瓦尔特·本雅明后期思想的重要文献《历史的概念/历史哲学论纲》围绕着“经验之碎片”、“历史之主体”这两个核心观念,提出了一种以“弥赛亚”作为主体的历史哲学。本雅明的“历史”观既呈现出鲜明的犹太-基督神学的色彩,又显露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轮廓——本雅明始终将历史视作一个并非“照本还原”的“过去”,而是某种经验“碎片”的堆积物,而主体,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却并不总是“在场”。本雅明认为,正是这样一种“主体缺失”的历史现状给了政治野心家以僭越的机会。作为面对历史现状的研究者,他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然而这并非仅是一种知识论上的危机,当历史的危机向当下在场的政治哲学过渡,便会迅速转化为实存的灾难——处于“例外状态/紧急状态”之中,唯有重新确立历史的真正主体,才有可能实现对历史本身乃至人类全体的救赎。
关键词:历史哲学;时间;救赎;弥赛亚;天使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6)05-0015-06
瑞士艺术家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于1920年5月至6月在艺术经纪人汉斯·格尔茨(Hans Goltz)的画廊展出。1921年6月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花1000马克在慕尼黑替本雅明购得了这幅画作。当年11月肖勒姆将作品寄到了本雅明位于柏林的寓所——根据以色列学者科比·本梅尔(Kobi Ben-Meir)的记载,“无论是身在柏林还是此后为了躲避纳粹而客居巴黎,本雅明都始终将这幅作品挂在自己的书房”。他对克利的这幅《新天使》可谓情有独钟,甚至试图以它命名自己筹办的第一本杂志。二战爆发后不久,法国战败,为躲避纳粹迫害,本雅明于1940年再度出逃。这一次,他在位于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布港(Portbou)停下了脚步,给他漫长的流亡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留下一堆遗稿,彻底告别了这个世界。至于《新天使》这幅画作的下落,则“交由法国学者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藏在一个手提箱中存放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战后,它曾先后辗转于北美和法兰克福,并由本雅明曾经的同事、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保管。根据本雅明的遗愿,《新天使》应该留给他的挚友卡巴拉神学家肖勒姆——于是肖勒姆战后在法兰克福继承了这幅画作,于是《新天使》便一直悬挂于他在耶路撒冷里哈维亚区(Rehavia)艾巴巴尼街(Abarbanel Street)住所的起居室,直到他1989年去世。根据肖勒姆的遗愿,画作被转交给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Israel Museum),珍藏至今”。
1921年在为本雅明购得了《新天使》之后,受到克利的艺术感染,肖勒姆写下了一首题为《来自天使的问候》(GruB vim Angelus)的诗,附在7月5日的通信中寄给了本雅明。在《历史的概念》第九章,本雅明引用了其中四句:“我的羽翼已振作待飞/我的心意却迟滞倒退/若我浪掷鲜活的时光/好运便不再与我相随。”这首诗与克利的画作可谓交相辉映:诗句既可以当作是对《新天使》的短评,而画作也同样能看作是对诗情的演绎——本雅明深谙这一点,因此花了一整段篇幅来谈论克利的这幅画作以及由画面本身所激发出的针对人类历史而展开的一系列哲学思考:
有一幅克利的画作,叫作《新天使》。画面中的天使看起来仿佛正要从他所凝视的对象那里抽身离开。他双目圆睁,嘴巴张开,翅膀伸展。历史的天使一定就是这副模样。他把脸别过去,面对着往昔。从那里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只是一连串事件,从那里他所看见的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无休无止的残片层叠在残片之上越堆越高,骸山向他立足之处滑涌而来。他大概想要停留一下,把死者唤醒,并将那些打碎了的残片拼接复原起来。然而从天堂刮来一阵暴风,击中了天使的翅膀,风力如此猛烈以致他根本无法收拢两翼。暴风势不可挡地将天使吹往他所背向的未来,与此同时,在他面前的那片废墟则堆砌得直通天际。在这里,被我们称为“进步”的,便是这场暴风。
正如肖勒姆的诗句中所呈现的那样,在保罗·克利构思的画面中,那被命名为“天使”的形象,其双翼左右张开呈飞翔状,然而飞行的方向却摇摆不定,一双圆睁的双眼,视线正从凝视的对象那里缓缓移开——无奈而决绝的姿态。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在空中格斗中不幸受伤的战斗机:摇摇欲坠、濒临失控,飞行员却依然努力地平衡双翼保持飞行的姿态——铺天盖地的炮火笼罩着机身,冥冥之中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与受损的机翼做着最后一搏,飞行员的心中被沮丧和恐惧所充斥,却仍又抱着一丝对幸运的期待。这是一种无比复杂的紧张情绪:必须把握这滞空的每一秒钟时间——正如本雅明所言,那是在来日“能够被援引为据的鲜活的瞬间与片段”,任何一次错误的判断都有可能将一切都葬送,唯有正确的选择才能够实现一次全盘的拯救,从这疾风骤雨一般险恶的境地当中抽身而出,重新占据一个让自己相对更有利的位置——正是这么一丁点黑夜当中如同螢火一般、跟“运气”纠缠在一起的希望,透过“弥赛亚侧身而入的窄门”,照亮了飞行员的视线,给予他信心,从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紧急状态/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当中逃离地心引力的。 而在《新约》中,第一次(向约瑟)宣告耶稣身份的也是天使:“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足见在犹太基督教以及相关联的亚伯拉罕诸宗教当中,“迅速有效地传达信息”是天使的一项核心基本职能。
有关天使的等级分配以及他们在天国的组织形式,古罗马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认为:“我们无从确知”——“至于那天上的极为快乐的群体,其组织形式又如何?他们有无等级区分?如何解释所有成员都统称为‘天使,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中读到的那样,‘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右边(如此表达方式显然意在说明所有天使,并无例外);然而我们又发现有些天使被称作‘天使长,这些天使长是否等同于所谓的‘诸军呢?若然,那么诗篇中‘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的意思或许就是,‘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天使长都要赞美他。使徒保罗在统称天使群体时使用了四个名词——‘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名词所指又分别如何?若是有谁能回答这些问题,且能证明其答案属实,就由他们来回答吧。至于我,我承认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关于这个问题,当代学术界亦有探讨。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天使》(Angels)一文,通过系统梳理天主教神学传统当中自教父时代起历代经院学者所归纳的天使等级及其相应职能,指出:在一个神治世界的范畴当中,“天使”的真正身份乃是作为一种“执行者”(minister)。阿甘本通过词源学的一系列考察指出:类属于不同阶层,属灵的天使职务名称和等级分别为在地的世俗政权以及教会所借用,用以指称类属于不同阶层的政府官员以及神职人员——天主教在规划圣职圣事的时候,正是以这样一个体系为蓝图,依据经文中所提及的“祝圣司祭仪式”和“司祭受职礼”,分别定义了如教宗、主教、神父、修士等不同等级的圣职;世俗的政治机构以及企业集团亦有样学样。这种具有类型化特征的结构规划都无一不是仿效了雅威划分天使职责、界定天使阶层的方式——其管理模式也都不免受到这种行之有效的权力贯彻体系的影响。阿甘本通过这样一番阐释回应了圣奥古斯丁这位古罗马神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更点出了权力通过信息来传达——“天使”同时作为雅威的信息载体与神权执行者的双重身份属性。
作为本雅明从克利的画作当中解读出的“历史的天使”,有别于上文所述的各种身份,正如克利的标题,是一种全新的天使(Angelus Novus)——他并非面对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对象世界,而是“历史”这样一个抽象的、时间性的受造物:作为“过去”,历史无法被“照本还原”地呈现于当下;位于“现在”,历史被形形色色的逻各斯话语所包裹,每一套都在自圆其说,每一套又都自相矛盾。面对时间本身,天使张开嘴巴像是要传达神的信息,然而却又空无一物——显然“时间”并非恰当的传达对象。
“一连串事件”(eine Kette von Begebenheiten)在历史的新天使面前无休无止地铺陈展开——正如被本雅明批判的历史主义及兰克之流的编年史家所倡导的那种“事无巨细一把抓”——在新天使眼中,它们呈现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Katastrophe):一座由无休无止的残片层叠堆砌而成的骸山。而这些残片是“被打碎了的”(das Zerschlagene),意味着它原本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形状,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破碎的样子,这就是肆意将历史主体抽离所导致的后果。恰恰由于这样一座骸山是没有主体、失去灵魂的——因此无论它能够堆砌得多么高,看起来是多么的宏伟而无懈可击,危机从第二块残片堆叠在第一块之上的时刻便已经在酝酿。当新天使目击这一切的时候,这座高高的历史骸山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分崩离析的紧急状态——并非以一种向四面八方炸裂的方式,而是缓缓地、却又难以遏制地朝天使脚下如同泥石流一般滑涌而来——正是这样一种难以阻挡的、地壳运动式的推擠压迫,产生出令人窒息的恐怖。
天使想要“停留一下”(verweilen)——在这里,“停留”典出歌德的剧本《浮士德》:由于与魔鬼靡菲斯托(Mephisto)作了交易,浮士德博士愿意以自己的灵魂献给魔鬼换取片刻满足。当这一刻到来时,靡菲斯托正要取走他的灵魂,沉浸在“美”当中的浮士德感叹道:“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Verweile doch!du bist so sch6n!)浮士德发出的这声感叹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绝望与沉醉的交织,上帝将他从魔鬼手中拯救了出来。不过,新天使在这里进入的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景——新天使的悲剧性体现在:当他试图以天使的身份来规整错乱而崩溃的历史对象的时候,这种行动已经超越了“天使”本身所能承担的大限,他在试图扮演拯救者的弥赛亚之角色。诚然,这种僭越的用意本身是无可指摘的——当骸山向他的脚下滑涌而来的时候,新天使仍然想要去唤醒死者,因为假如骸山将一切埋没的话,“死者也将不复存在”。天使意识到历史的危机正在发生,然而对历史实施救赎却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任务。
“从天堂刮来一阵暴风”,把天使从困境当中拯救了出来,正如那架伤痕累累、摇摇欲坠的失控战机,被一阵强劲有力的气流托起了双翼,因而避免了被击落坠地的灾难。任何一个对《圣经》有着最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创世记》第一章开篇这样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这里,“神的灵”(spiritus Dei)一般被认同为圣灵(the Holy Spirit),也就是基督教中“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的组成部分。不过,在犹太圣经《托拉》(Torah)当中,“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却被表述为“一阵神的风从水面上刮过”,在这段文字的旁边标有注释:“亦可作‘神的灵(Others‘the spirit of)”。这也便意味着依照犹太教的传统,“神的灵”是可以“风”的形式予以表现甚至代指的,那么在这里,“从天堂刮来一阵暴风”同样也可以理解成:从上帝那里传来了圣灵将天使拯救了出来。尽管依据前文,历史的新天使宁愿冒着僭越弥赛亚的风险,也要重整历史残片并“将死者唤醒”,不过显然这个历史危机已经超越了天使力所能及的范围,因为天使与拥有救赎大能的弥赛亚则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雅威的意志化作天堂的暴风,将他从这种僭越企图的进退两难之中解救。
关于天使、耶稣基督(弥赛亚)与上帝(神、创世者)这三者的关系,阿甘本在《天使》一文中亦作了详尽的梳理:“在基督教中,一个外异于世界的上帝,和一个统治世界的造物主之间的二元,是通过神性中的转换来协调的。三位一体就是这样的装置,借助它,上帝不仅承担了创造,而且,通过基督和他的道成肉身,也承担了对造物的救赎和治理。这意味着,基督教把天使的权能投到了上帝自身之上,并把对这个世界的治理,变成神的一个形象。……在马勒布朗士的天命神学(providential theology)中,基督,作为教会之首,依然以世界机器(machine mundi)——这架机器的最高立法者是上帝——执行首脑的身份出现;就此职能而言,他被比做天使并被毫不迟疑地定义为‘新律法的天使,即便至今这也只是一个隐喻。……如果说基督是天使而不是上帝的话,那么,基于天使向神的生命投射的三位一体装置,就不仅不能运作,还会威胁到神的独一性。尽管最终的解决方案借助同质(homousia)说消除了圣子的天使性质,但基督学的天使学起源却依然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作为一种倾向于把永恒存在的首要性替换为拯救的历史经济,并把被实体的独一性所界定的内在的三位一体,替换为本质上是实践和治理的经济的三位一体的非神学偏移,而起作用。”
根据阿甘本的见解,显然,作为弥赛亚的耶稣基督可以作为天使呈现,然而天使却不能像耶稣一样实施救赎。耶稣基督与雅威既是父子又是同一,因此耶稣实施救赎的大能,实际上等同于雅威所实施的救赎本身。那么,能够将新天使从僭越企图的进退两难之中解救出来的唯有这“来自天堂的暴风”,它是圣灵,作为三位一体,它也是雅威,同时又是耶稣基督,即弥赛亚。
这阵神秘的暴风将历史的新天使刮向了他所背向的“未来”(die Zukunft)。从力学与空间的关系来看,由于新天使所面向的是经验残片堆砌的历史骸山,也就是“过去”,那么他所背向的必然是“过去”的反面,即未来。既然将新天使吹向未来的圣灵是来自天堂,这也就意味着“天堂”的实际方位恰是新天使所面朝的方向,越过那堆碎片骸山的更远处——真正的、原初的“过去”。
关于“过去”这个概念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中的重要性,倘若回到犹太基督神学的话语范畴里来理解它,本雅明在这里所要传达的信息便清晰得近乎直白——因为“过去”的源头便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历史便是从雅威创世的那一刻起发生的,因此力量来自“过去”。正如《历史的概念》第三章中所言:“像祖祖辈辈的先民一样,我们也被赋予了些许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这股力量的权利属于‘过去”,弥赛亚的力量便是从历史的原点爆发的。那唯一能够将历史的残片重新规整恢复如初的力量,恰恰就是来自“历史的主体”本身。在这里,本雅明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弥赛亚”在历史中的地位。在这里,被他唤作“进步”的,正是来自天堂的暴风、历史的主体、拯救的实施者——弥赛亚。关于这一点,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这样表述道:“对基本的历史概念的定义:灾难——失去了机会。危机时刻——现状恐怕要被保存下来。进步——所采取的第一个革命步骤。”在《历史的概念》第十四章,本雅明引用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指出:“起源即目的。”
在本雅明笔下“历史的新天使”所面对的那座由经验残片堆积而成的歷史骸山,在精神世界的对应物便是“历史的废墟”——主体被抽离的破碎历史观——历史主义(Historicism)作祟所造成的恶劣现状。在《拱廊计划》中本雅明评论道:“一个最终无法回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历史就必然要求以牺牲历史的直观性为代价吗?或者怎样才能将一种高度的形象化(Anschau-lichkeit)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施相结合?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就是把蒙太奇的原则搬进历史,即用小的、精确的结构因素来构造出大的结构。也即是,在分析小的、个别的因素时,发现总体事件的结晶。因此,与庸俗唯物主义决裂。如此这般地来理解历史。在评论的框架内。”根据本雅明的观点,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样隐含着由逻各斯话语带来的对历史主体僭越的危机:这种观念仍然在试图构建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宏大体系,从而将历史纳入其中。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实事求是,却以牺牲“直观性”与“形象化”为代价,并不能萃取出某种真实的实存性,而是无可救药地在话语的结构性迷宫中不可自拔,陷入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座由一堆杂乱的经验残片堆积起来的骸山,恰恰是切中本雅明写作生命的一个关键词。正如历史的新天使那样,本雅明花了一生的时间,拣选着他在柏林度过的童年、德意志的悲苦剧、达盖尔发明的散发着灵韵的银版摄影作品、巴黎拱廊街上一盏一盏亮起来的煤气灯以及波德莱尔笔下擦肩而过的女子……他小心翼翼地给他们编号作注,从青年时代的“未来哲学论纲”到宏伟的“拱廊街计划”以及这部未完成的《历史的概念》——然而这些宏伟计划没有一个能够实现,甚至放眼全世界也未必有谁能够真正完成这些如同圣经一般无所不包的整理编纂计划。英国左翼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的序言中曾经记述了这样一则轶事:“一天下午,沃尔特·本雅明闲坐在圣日耳曼德普雷(Saint-Germain-des-Pres)的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其时他灵感激荡,想为自己勾勒一幅人生图表。此时此刻,他清楚地知道该从何下笔。他画出了这个图表,可是约一两年后,却由于典型的运气不佳将它遗失。于是这一图表成了一个谜,这毫不令人意外。”恰如本雅明在巴黎绘制的这样一幅自己的人生图表,关于“历史哲学”的人类思想总图表也随着1940年他生命的逝去戛然而止,呈现为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只言片语。恰是基于这一点,在本雅明人生图表的下落与他对历史哲学的断章式论述之间,在面对历史的新天使与踯躅于历史哲学骸山前的本雅明之间,冥冥中倒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互文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这毫不令人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