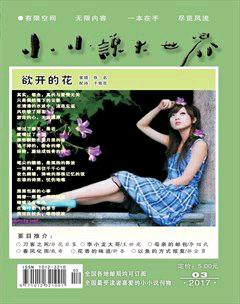刀客之死
南衙的东邻是一座铁匠铺,明代建南衙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人民政府搬到人民路,南衙变成“南衙街小学”,铁匠铺还在那里。
白发苍苍的铁匠躺在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叫道:“兰,拿来。”
兰顺着他的眼神望向墙上挂着的那把裹着皮革的刀。皮革上落着厚厚一层灰,沉沉地、幽暗地静默在泥土壁上。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它没有变换过一下姿势。
年近六十的兰腰身依然灵巧,大概是没有生育过的缘故吧。
她取下刀,抹去尘灰,打开皮革,里面是红木刀鞘,金丝缠绕的刀柄。由于年代久远,一股陈腐的怪味弥漫在屋里。铁匠颤抖着双手,接过刀,两手一用力,听到的不是那种熟悉的、令人快意的“铮”的一声,而是朽木断折的“噗”,像空气中有人望着他讥讽地一笑。他只拔出一只刀柄,那曾伴他传奇人生的神刀,被岁月蚀成一块废铁。
铁匠也随着这讥讽一笑咽下最后一口气。
下葬时,兰将那把刀放在他的手边。
兰知道,铁匠是一名刀客,他必须带着他的刀一起面见祖先——兰是铁匠之外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豫西地区从清末到建国初,匪患猖獗,打家劫舍,为害一方,统称刀客。
他们有结伙聚众占山为王的,也有隐身单行,什么人也不知其刀客身份的。当年在豫西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刀客,叫“玉面独行”。但他长什么样子,隐身何处无人知道。他从不随意打劫,只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有一个固定的线人,为他承揽生意,他们有独特的联系方式,线人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还有一种“双面人”,他们在国民党内部做官,明官暗匪;有的本来就是“土匪”,抗战胜利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剿匪英雄”。当时,南衙的文化股主任王成桢,出身书香门第,写得一手好公文,老百姓称他是师爷。一有机会,他便抢劫作案。
师爷的双面人身份,路人皆知,但是,没人敢说一个字。
民国35年腊月三十的夜晚,他身披大衣,头戴礼帽,一手打着电筒,一手提着盒子枪,在紫逻口遇着一个过路人,不问青红皂白猛打一顿耳光,把过路人身上仅有的盘缠10块银元搜去。然后他抢先一步回到南衙,把衣帽一换,坐在办公室里。当这位被抢者到南衙报案时,王师爷一拍桌案:“哼哼,你是共党派来的奸细,故意惑乱民心。来人,押进牢里,审出同伙。”
兰只身到南衙为父亲收尸,她才十八岁。师爷强留她,她便住进南衙后院。
兰常闲闲地在一方阁楼上走来走去,从东窗,正好眺望见东邻的铁匠院落,三十来岁的李铁匠的身影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师爷在床第之间也存着防范之心,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哪一句话会使兰捕捉到父亲死亡真相的蛛丝马迹。
但兰却知道了所有真相。
兰用全部财产,向“玉面独行”买下王师爷的人头。
那是春风轻拂的夜晚,兰朦胧睡去,一激凌惊醒,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床前,正对着一帐春光。
兰快意地看着身首异处的师爷,再看看蒙面大侠。她说:“谢谢你。”
望着“玉面独行”的身影融于夜色中,良久良久,兰才大声呼叫起来。
师爷一死,兰和师爷那些值钱不值钱的物品一起在南衙门口拍卖。
兰看向铁匠铺,用一双眼睛乞求着他。铁匠用三十块大洋买下了她。
新婚之夜,兰轻抚着床侧那把刀,一使劲,要把刀从鞘中拔出。李铁匠敏捷地制止她。
刀客的刀是不能随便拔出的!这是他十二岁时,从父亲手中接过这把自他一出生就在锻打锤炼的刀,跪在祖宗牌位前接受的规矩。刀客的刀,一但出鞘,便要饮血而还。如果没有杀到人,则必须杀狗杀鸡替代,一时找不到狗、鸡,便要拿自己的血祭刀。刀客生的第一个儿子必须继续做铁匠,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然后继续做刀客。
兰伏在铁匠的怀里,哭了。一直哭了一夜,她说,要用眼泪祭奠那些不明不白无辜丧命的亡魂。
铁匠在地上站了一夜,當第一缕晨光照进木格窗,兰止了哭声。
铁匠把刀挂在墙上,发誓再也不让刀见光。
铁匠打铁器维持着二人的生活,直到老死。他们一直没有要孩子。
最后一名刀客终于消失了,他杀了无辜的人,杀了杀人的人,时间杀了他!
他没有后人,刀客时代结束了。
他们在农大的操场相识,那是课外活动时间,夕阳正红。
瑞像一阵轻风拂过跑道,她修长清瘦,水洗过的绿竹一般。
培智静静地站在跑道边,像老僧入定。
经过培智面前的时候,瑞很诧异: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昂首看着路边杨树上的一只毛毛虫。
两个人都记不清是如何搭讪起来的,她知道了他在学习农林病虫害防治,而她学习的是食品营养学。
瑞爱动,所有热闹的活动都少不了她。但她却喜欢陪着培智看树上、草间的小虫子。他会告诉她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告诉她蝴蝶的肢体语言,他说:蝴蝶是有感情的……她便把他说的话带回宿舍,对一群见了毛毛虫就变色大叫的女孩子们复述。日子就在卵、虫子、蛹、蝴蝶的循环往复中过去了,回想起来,两个人的话题竟从来没有离开过蝴蝶。
毕业的时候,培智到了西南。
瑞只身到了深圳。她有了一个香港恋人。他们在一个公司,她在内地部,他在香港部。一点都不浪漫的相识,但是有一种渗透人心的感动。每到周末,一水相隔的小伙子,便越过罗浮桥,到深圳与她相会,他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那年“十一”培智发给瑞短信的时候,瑞告诉培智自己恋爱的消息,她说:男孩是个很宽厚的人,博学且上进,给她稳定与温暖的感觉,她爱他。她灵巧的手指点击按鍵,发出短信时,心里暖暖的,有了一种依归感。她随男友去了香港,拜见他的父母。
培智好久没有回音。
几个月后,培智说,他在云南大理,他看到蝴蝶哭了。
——香港有蝴蝶吗?他问。
瑞走在这个高度发达的金融社会,在这个高楼大厦丛林般耸立的国际大都会里,她看到苍郁的亚热带植物在楼间空地,在河畔,在公园,随处瀑布般倾泻下來,从高楼顶端俯视,香港整个是一个绿城了。他们居住的小区花草丛生,蝴蝶翩翩起舞。
男友的妈妈是一个极传统温和的家庭主妇,吃饭的时候,用生涩的广东普通话告诉瑞,这里的蔬菜和肉食都是本地自产的,各项指标都合格。大陆上用了化肥和添加剂的蔬菜和肉制品根本过不了海关检测。
瑞当时有些吃惊。她以前认为农村种菜用上了农药和化肥是一种现代化的标志,没想到现代化有那样大的负作用。她爱自己内地的家,但她极力用一种豁达的接受表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热爱。她喜欢这个优美的环境,喜欢这个家庭,也爱这个香港男孩。
瑞把这些用短信发给培智。
培智只回了一句话:我正在保护蝴蝶。
瑞返回家乡办理出境签证和结婚证明时,听说培智死了。在蝴蝶生长的崖边,掉落下去。
瑞赶到了云南,到了培智工作的地方,那里曾有非常奇妙的自然景观,有些地区,高寒地带的雪山冰峰和河谷地带的热带雨林共存于同一时空,它曾经有过外边罕见的“立体气候”。
“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歌一直在唱,
但是那里却找不到蝴蝶了。
因为农药的大量施放,以及空气的污染和森林的砍伐,蝴蝶泉几近断流,一年一度的大理蝴蝶会也被永远取消了。
人们说,培智来了不久,就坚决不让人们用农药,他不断地对见到的人说:蝴蝶哭了。
他走进森林,不停地制止人们伐木、捕蝶,他追寻着蝴蝶的足迹,他要把蝴蝶找回来。有一次,他走进藤盘枝绕的密林,一直没有回来。
人们最后发现他静静地躺在蝴蝶谷底,身下是一株蝴蝶兰,身边环绕着一种蓝色的大蝴蝶。
为了纪念培智,当地的蝴蝶馆用培智来命名。
瑞进了蝴蝶馆。一个个精致的玻璃盒子里,蝴蝶静静地展开翅膀匍匐着,这是一个悄无声息的蝴蝶世界,美妙无比,却又死气沉沉。
瑞感受到美,也感受到沉痛。
二楼,一方大大的玻璃橱中,有一只耀眼的蓝色大蝴蝶。标本旁有一张图片说明,简单地记叙培智殉职的经过——他为保护这只稀世大蝴蝶不被捕蝶人捉去制成标本卖给顾客,不慎坠崖,还附了一张照片。
培智微笑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瞳仁里有一种狂热的东西。
那大蝴蝶足有一人来高,蓝色的翅翼上有着彩虹般的细密鳞片,随着光线的变化而闪动着不同的色泽。它的两只触须像两只柔美的长瓴。这哪里是一只蝴蝶,宛然飘飘欲飞的美人!她那一对稀有的蜜蜂一样的复眼,在大厅明亮的顶灯下,闪烁无数个光点,像人眼中盈盈的一汪眼泪。
瑞记得,培智说过,蝴蝶是有感情的。
犬祭
十三岁的甲洛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自治县中学上学,他是乡长的儿子,但他在地图上找不到家乡的位置。它实在太小了,只是藏北的一片草坝子,四周是连绵的雪山,不走近,很难发现这里还有人家。
甲洛很想家,总盼着两周一次的休假,坐着大客车到山口,阿爸扎西会骑着乡里唯一的摩托车把他载回家。
拉巴相距一、二十米就颠颠地来迎接他,围着摩托车摇头摆尾,一改平日凶残的面相,变得温顺可爱。
甲洛从摩托上跳下来,便和拉巴滚到一处。五月的阳光很暖和,照着绿毯似的草地,羊群在草丛间懒洋洋地吃草。
拉巴是藏北草原上特有的牧羊犬,学名藏獒,足有小牛犊那么大,通身油亮的黑毛在阳光下闪出一圈幽蓝的光晕。它两耳耷拉着,大得能盖住半边脸。生人与它对视,会被它眼中的寒气吓得打哆嗦。
但它是乡长扎西的好帮手,放牧时,每次与狼遭遇,它都毫不畏惧,英勇异常。与狼厮咬时又凶又狠,四周几十里内的狼都不是对手,几次与狼群交手,咬得狼群落荒而逃。白天拉巴随着主人外出护牧,晚上它睡在主人帐篷外放哨,因为有它,附近牧民的羊都没损失过一只。
这晚甲洛在帐篷里,拉巴在帐篷外,静静地过了一夜。天亮时,拉巴突然拉长声音嘶叫起来,像狼的悲鸣。扎西说:“拉巴这几天很怪,一直悲鸣。牧民们接二连三死了十几只羔羊,大伙没有见到狼,都怀疑是拉巴野性发作时咬死的。”
甲洛跑出帐外,看到拉巴正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引颈长鸣,四周一片野性的、神秘的恐怖。
“拉巴,”甲洛叫,“是你干的吗?”
拉巴回头望了甲洛一眼,向远处跑开。
甲洛赶着羊群去放牧。晚归的时候,看到门前牧民围了一圈。
甲洛挤进去。拉巴蜷成一团,双爪朝前,脸趴在双腿间,身子一动也不动,两只眼睛却四处张望,眼里仿佛挂着泪珠。它那光滑明亮的黑毛被风吹得竖起来,在风中抖动着。一见到甲洛,它猛地跳起来,扑向他,但它的身子趔趄着,倒在地上,它的脖子和后腿被包扎得严严实实,血微微渗透纱布。
甲洛颤抖着用手轻抚拉巴的脊背。他转过头来,生气地大吼:“拉巴怎么了?”
乡长扎西推开围观的牧民,手里抱着一只死去的小羊羔,走到甲洛面前,用藏语数落着:“该挨枪子的狼群,大白天竟敢闯到牧区防护栏里,咬死羊羔。拉巴……”
看到血淋淋的羊羔,拉巴愧疚地垂下头,像一个自责失职的卫士。
一个牧民不满地说:“这么多年狼群都不敢白天进牧区的防护网,这些天就是怪,拉巴总是狼哭,说不定是它把狼给招来的。”
甲洛愤怒地说:“你胡说,拉巴决不会犯野性的。”
甲洛慢慢走过去,抱紧拉巴的身体,想让它进帐篷。但拉巴挣脱了,依然伏在门口。它低低地咆哮着,从胸腔发出的重低音,震得地面共鸣着。
这时,人们突然发现,将近五六十条大大小小,花色不同的狗不知何时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半圆。这些狗或站立,或半卧,都竖着耳朵,目光炯炯,复仇的火焰从眼睛里喷射出来,每条狗的喉咙都发出低沉的咆哮,仿佛天边滚滚惊雷,令人毛骨悚然。
狗群的愤怒比狼群的威胁更惊心动魄,牧民们被这种原本忠厚驯顺的生灵震慑了,眼望着它们向牧场外的山口飞奔而去。
乡长扎西招呼猎手们骑上马,拿起猎枪追了出去。当他们半夜回来时,拉巴软沓沓地趴在扎西的马上,紧紧闭着双眼——它拼尽最后一口气,死死咬住了头狼的咽喉。
群狗呜咽着,眼里都淌出了泪水。牧民们按着藏族人对朋友的礼仪,为拉巴诵起佛经。狗群在梵唱里慢慢散去。
甲洛病了,发着高烧,不停地叫着拉巴。
第二天一早,散开的狗群又聚拢来,一起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长鸣,情景怪异。
午后,阳光明媚的天空突然黑暗下来,狂风滚过草原,一大团乌云从东南方涌上来,迅速铺满天宇,像巨大的拉巴的身躯笼罩了上空。
人们分明感到大地在震动。
当强烈的震动过去后,下起了大雨。雨过天晴,草原又一片明朗。
电视里说,东方的四川发生了大地震。乡长扎西忙着招集牧民把帐篷、酥油、糍粑装上马车,运出山口,从县里送往灾区。
甲洛一直病着,他总梦见一个穿黑袍的黑黑壮壮的少年,与他一起在草原奔跑、欢笑。
扎西又抓回一条小狗,和拉巴小时候一模一样。一来,便围着甲洛打转。甲洛挥手赶它:滚!但小狗不走,用一双小眼可怜巴巴望着他。
甲洛叫了一声“拉巴”,小狗便钻进他怀里,甲洛抱起小狗,终于哭出声来。
【作者简介】
非花非雾,本名丁丽,河南省作协理事,洛阳市作协小小说学会副会长,洛阳文学院特约创作员。现已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400余篇,有百余篇小小说、散文被转载并入选各种年选本和精选本,小小说集《梅花玉》获洛阳市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类优秀作品奖,并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出版小说集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