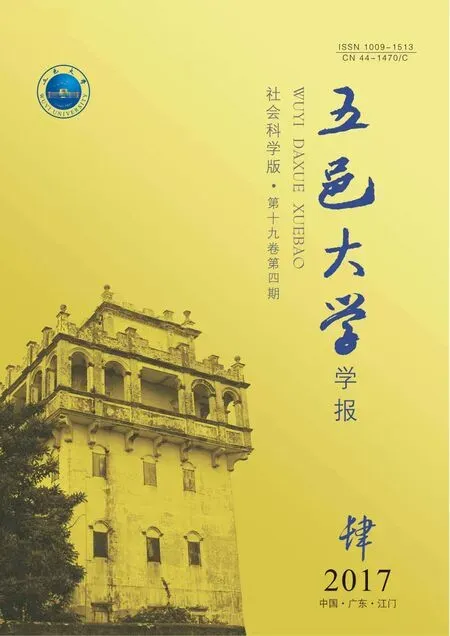明清时期广州商业文化特征研究
潘 彤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1450)
明清时期广州商业文化特征研究
潘 彤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1450)
明清时期,广州商贸繁盛,其商业文化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独特的内涵:商业物质文化层面形成“品质精良、新颖多样”的商品文化、“讲粤语敬神灵,好风水重意头”的商俗文化、“以商筑城,以墟聚镇”的商业城建文化;商业精神文化上以追求商人社会地位、促进商尊社会氛围等构成其时代特征。
明清时期;广州;商业文化;特征
一、商业文化研究综述
我国对商业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亚文化,学界对如何准确界定其研究范畴尚有不同的认识。林文益认为商业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而庞毅则认为商业文化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长期的商业活动中与商业活动直接关联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多种形态;[2]单红波把商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归纳为商品文化、商品营销文化、商务环境文化、商业道德文化、新商人文化、商业精神;[3]刘建生、张宇丰则把传统商业文化的内涵界定为以中国传统商业活动为载体,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现象,并且能够借助商业活动开展交流、包容、继承、异化等一系列传播过程。认为传统商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以商业贸易为基础,以官商关系为纽带、以制度伦理为核心、以民俗文化为外在表现形式等方面;[4]薛光明将商业文化从客体上分为商品文化、商业设施与设备文化、商业制度文化、商业管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等;[5]王兴元、李斐斐认为商业文化与普遍意义的文化一样,是从事商业行为的经营者拥有的价值观,以及受这种价值观影响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6]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商业文化是商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共同体。本文认为:商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与商业实践相伴始终。商业文化涵盖了经济行为和文化行为两方面的多种关系。商业文化产生于商业经济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表现出来,离开了现实的商业经济活动,商业文化便无从谈起。但商业文化并非商业经济活动的本体,而是商业经济活动中蕴含的各种文化现象以及商业运行的文化环境。因此,商业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期商业活动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遗产,它既包括精神层面的商业信念、价值观念、商业精神等,也包括物质层面的商品、商俗、商业场所和商业器具等。本文以史载及现有成果文献为依据,从商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研究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府)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
二、明清广州商业物质文化特征
(一)“品质精良、新颖多样”的商品文化
明清时期的广州受中西文化和岭南文化影响,以及随着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广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永乐年间,广州丝织棉织业迅速发展并开始商品化,嘉靖年的一口通商和澳门开埠,使得广州丝绸外销的量越来越大。由于采用手拉足踏的木织机丝绸质量大幅提高,“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7]376,“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8]。其时广州造船业也很发达。广船是我国明代著名的船型,船头尖体长,上宽下窄,线型瘦尖底,远洋船长30多米,宽近10米,船上有夹舱,船帆面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更适合于远航。佛山的铁器也以优质出名,畅销国内外,《广东新语》中道“铁莫良于广铁”,指的就是佛山铁产品。石湾陶瓷是广货中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的产物。石湾所在地佛山是中原移民的聚居地,他们把北方的陶瓷技艺带到石湾,与石湾原有的制陶技艺相融合,大大提高了石湾陶器制造水平与艺术水准,成为南国“善仿”为特色的名窑。蔗糖以南方甘蔗为原料制作,明代用黄泥水淋脱色法熬制白糖,“双清者曰白砂糖,次清而近黑者曰瀵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7]605。葵扇是新会最著名的传统手工艺品,《新会县志》载“始于魏晋,盛兴明代”。新会盛产蒲葵,新会葵扇在扇面绘图描画,工艺精湛,高雅实用,远销英、美、法等国。明清时期,流传着“苏州样、广州匠”[7]405之谚,可见广货工艺之精良。英国人斯当东所著《英使觐见乾隆纪实》中记述,广州工匠加工的铜片“质地精细,颜色光亮,远远超过欧洲方法所制造的”,铁匠在加工薄铁片方面“本领超过欧洲工匠”。[9]
广货善于吸纳世界其他地区商品的优点,结合市场消费喜好,生产出各种新颖的商品。清康熙年间,广州已有钟表制造业,《广州通史(古代卷)》载“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按: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10]。乾隆中期后,广钟的制作工艺有了长足进步,浓缩了中西方文化和工艺精华的广钟成为“贡品”,故宫博物院现存几百座乾、嘉时的广钟。[11]广州工匠善于模仿国外商品,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各式各款新颖商品,“螺钿器,本出倭国,物象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泊宅编按:今粤人亦善制之)”[12]。“广彩”是选用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器贩到广州,在广州请善于绘画的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在白瓷器上绘西洋人喜欢的图画,再开炉烘制成彩瓷,然后售给西方商人。
(二)“讲粤语敬神灵,好风水重意头”的商俗文化
广州商人是以广州话(Cantonese)为主要交流语言的商人群体。广州话源于古代中原地区的雅言,初始时期跟中原汉语差异并不明显。晋朝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对中原文化和语言带来巨大的冲击,作为当时各民族共同语的雅言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胡化成现代的普通话。同时期由于岭南地区保持较为稳定的局面,由雅言演变而成的广州话却没有发生中原汉语那样的变化。尤其在元朝,中原汉语与中古汉语和广州语的差别越来越大。明中叶后,随着广州商贸经济的大幅发展,在国内外逐渐形成以广州话为聚集基础的“广州商帮”,将广州话推向了世界,被联合国定义为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的语言之一(Leading Languages in daily use)。
广州商人受岭南民俗的影响,特别重视祖灵崇拜和鬼神信仰。广州人在面对浩淼大海时会感到恐惧无助,因此对海神的信奉祭祀形成了习俗,无论是南海神、真武北帝还是天妃、天后、妈祖,只要与海上行船有关的神都是信奉祭祀的对象,“然今粤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7]182商人们通过捐建捐修南海神庙、妈祖庙、天妃阁,举行庄重而讲究的祭拜仪式来祈求海神的保佑。广州商人不仅崇敬海神,也崇拜财神,除了供奉财神赵公明外,更将关公视为财神,借关公表明正气正义、童叟无欺,盼望关公能带给商家足够的财运。广州商人对各神都是尊崇非常,多神崇拜,不拘方式。如造祃,又称做祃,是商家极为重视的一种祭祀活动。每逢初二、十六为“祃期”,正月初二开年称“头祃”,腊月十六为“神祃”,雇主解雇伙计多在“头祃”进行,称“吃无情鸡”。店家祭过关财神或者土地神之后,要加些酒水肉菜与员工同餐共饮。年初一的迎财神、年初开业拜财神都表现了对神的敬重,敬神成为广州商业的一大习俗。
广州商人特别讲究风水。明清时期由于皇室对风水的崇信,助长了民间风水活动的兴盛。当年永嘉侯朱亮祖因梦见青龙出海与越秀山上的喷火赤龙恶斗,奉诏在越秀山上“建望楼,高二十余丈,以压其气,历二百余年,清平无事”[7]440。风水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竞争的激烈化而扩张,因为争夺风水而发生械斗纠纷成为普遍的现象。宗族尤其重视庐墓的风水。明代南海石头霍氏,看重了南海西樵山的风水,就在山上营造了霍氏祖先的墓地。自嘉靖年间霍韬成为朝廷重臣之后,霍氏家族对风水更加笃信不疑,并利用霍氏声望维护西樵山的风水。[13]十三行巨商潘振承“清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在广州府城外对海地名河南乌龙岗下运粮河之西,置余地一段,四围界至海边,背山面水,建祠开基,坐卯向酉,兼辛巳线,书扁额曰‘能敬堂’”①。此地紧临珠江,退潮时原先满注的潮水,从涌内和窄长水道同时急速冲出,宛如涌往北岸之海珠石,有堪舆家认为,此乃“卧龙漱珠”之象。[14]潘家选此地,可见其对风水的迷信和重视程度。
广州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还特别讲究意头和禁忌。广州的商家为了争取好意头,过年时会在店铺里摆放大柑桔和鲜花,寓意为大吉大利等。广州每年正月二十四有办“生菜节”的习俗,借“生菜”谐“生财”之意。新春期间有醒狮采青风俗,各家在正门上方垂一颗生菜,也是寓意生财。广州商人也有不少浓厚地方特色的禁忌。首先体现在言语上,多是因为发音或者字义不吉利而被改称。如海商忌讳说“住”、“翻”。商行里为了账目上多进少支,忌讳“支”字。数字偏好三、六、八、九,寓意生、禄、发,久,忌讳“四”。广州方言“舌”与“蚀”同音,于是“舌”改称“脷”,寓意大吉大利。除了言语上的禁忌,经商过程的行为也有禁忌。如出海经商的人吃鱼不能翻转;商铺平日扫地,忌向外扫,定要从店铺门口往里扫,称之为“招财进屋”等等。
(三)“以商筑城,以墟聚镇”的商业城建文化
广州商品丰富,店铺林立,商品贸易繁荣。“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径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7]420反映了当时广州城南的繁荣景象。嘉靖四十四年广州“新城”的筑建,阻断了贸易的便利,商业中心也由南逐渐转移至西关一带。明朝时市舶亭和怀远驿设于西关的蚬子步,初期只是接待外国人的场所。嘉靖年间西关开凿了大观河,河道基本与珠江平行。很快沿河兴建一批商业店肆,逐渐成为广州商业繁华之地。广州所有经济因素都集中在西关,有贸易码头、货栈和仓库,更有各国商业机构和洋行,十三行也在这里。清朝中后期起,西关先后兴建了宝华街、逢源街、多宝街等居民住宅区。中国最早的海关也设置其中,更有西关南端外国人的租界“沙面”,因商而形成岭南特色的城区。
广州西关的骑楼建筑连绵千米,始建于清代,是吸取南欧建筑特色和北方满洲式装饰,又适应南方炎热多雨气候,可供商户、顾客在任何天气下环境下进行商业活动的实用又美观的建筑长廊,成为岭南建筑的典型代表。
广州乡村的商贸也在不断发展,并促成了珠三角乡镇城建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明永乐年间广州地区约有墟市30多个,至嘉靖年间发展到90个,万历年间达170多个,清代墟市数量更是急剧增加。[15]早期墟、市是有别的,“粤俗以旬日为期,谓之墟,以早晚为期,谓之市。墟有廓,廓有区,货以区聚,概犹有城遗制。市则随地可设,随便买卖而已。故墟重于市,其利亦教市为大……”[16]。后发展到墟内设市,可以互称。墟市的分布,是以广州城为中心,由密而疏分布散在佛山、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县。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围绕着墟市慢慢出现了墟肆、商店、酒铺、客栈等商贸服务设施,逐渐发展成以商品交易为主的小镇。整个广州地区这种小镇众多,嘉靖年间在广州的克鲁士说:广州“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17]。
但大小墟市的布局,却并不与政治中心完全重叠。不同于中原,小镇不因权利而生成,主要是因商业而聚。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中描述:明初佛山从“孤村冶铁”起步,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至明中叶已经发展成为“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18]的工商业重镇。
三、明清广州商业文化的精神内涵
(一)追求商人的社会地位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中,商人为四民之末。“为富不仁”的思想观念使得商人在心理上和社会地位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唐《均田令》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因此商人们最大的愿望还是后代考取功名,走仕途之路。岭南地区虽然重商的地域特征显著,但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底下。宋苏缄任南海主簿时,因樊姓商人失仪,“缄诘而杖之。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19]可见既使是在对商人相对包容的宋代广州,商人地位依然不及吏官。
明中后广州商人群体逐渐壮大,他们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试图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商人地位有所提升,出现了“弃儒就贾”现象,如南海县冼文清,因童子试不第,“乃弃儒而商,于道、咸年间航海天津贸易。”[20]也有弃吏而贾,如佛山的冼树藩,虽然弱冠考吏中选,但因“生计艰难,非经商不能昌业,弃吏而贾”[21]。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
1.思想上对正统观念的挑战
明代思想家灿若星河,思想激辩前所未有。王阳明为弃儒经商的方麟所写“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22]。李贽是极具个性的思想家,他不同于正统思想,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23],认为商业交易合乎天理。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24]李贽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因此他的思想对商人价值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思想界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引导市井百姓认同商人的身份价值。
2.物质上商人的财富积累暴增
明清时期,中国经历了数百年闭关锁国的时代,仅仅留有广州作为唯一的政府特许对外贸易基地。“一口通商”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让广州商人的财富急剧增加。这些商人通过商业贩运活动,集中了社会较多财富。顺德人邓仲豪、邓仲钊两兄弟:“弱冠经商,以贩丝为业,仲豪居省(广州)发售,仲钊在乡购买,一外一内,各展所长。初在泮塘开张义和纺织生理。在第七甫营创淬和祥洋庄丝店,积富数十万。”[25]新会潮连乡商人卢继俗“操商业,有远志,设商船转运几十数艘,于高州典肆数处,因成巨富”[26]。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十三行行商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道光十四年,伍秉鉴的私人资产已超过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半。财富的增长推动商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追求。
3.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思想熏染
广州地处中国对外交易的前沿,最早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思想。1553年葡萄牙人占住澳门后,作为中转港,澳门的进出口货物主要通过广州向各地集散,所以澳门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广州贸易。另一方面,澳门对内地联系需要通过广州进行,于是产生了买办商人。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商业思想,推动中国的洋务运动,改善和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如香山人郑观应提出了“商战”理论。他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和“商战”,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从而更加强化商人的地位。
(二)促成尊商的社会氛围
1.从商昌业的商业思想
明清时期广州人经商,更多是出于从商的自觉性,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非经商不能昌业”传达了广州人对于商业的普遍认同感,使得广州人无视“舍本逐末”的批判,经商求利似乎成为了广州商人的天性。嘉靖徽州人叶权《游岭南记》记述:“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27]道光年间商人梁玉成贾一年,“获资累距万”。咸丰时顺德商人梁炜也是经商后“遂致巨富”[28]。“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以时逐(利),以香、糖、果、箱、铁器……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7]332反映了当时广州人从商昌业的社会观念。
2.义利兼顾的商业理念
儒家思想一向倡导“重利轻义”,但是对受中原正统思想束缚较少、较早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广州商人来说,他们既坚守儒家的仁义,却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正当利益的追求。商人经商投入巨大,他们东奔西走,受劳苦、挨孤独、担风险,更有甚者丢了性命,《聊斋志异》中述,“粤东往来商旅,多告无头冤状。千里行人,死不见尸,数客同游,全无音信,积案累累,莫可究话”[29]。如此以生命为代价的投入,获取高额利益也是必然的。因此在广州商人群体中逐渐产生了一个利义兼顾的商业理念,其基本内涵是商人在逐利的过程中要讲仁义道德,要有道德底线。其次商人在经营获利后,要将一部分盈利反哺社会,为家乡办学、办医、建庙,“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嘉庆年间,广利行商卢茂官之子卢文举,在家乡新会兴建紫水义学,据记:“在邑城内花巷,嘉庆十九年,候选道卢观恒之子文举等承交遗嘱,买地、创建,后捐田二顷二十亩,交邑中绅士公举首事管理,收租以为掌教修脯生童膏火各项之需,三年一代其田。”[30]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商人的经商理念就是力求在“义”和“利”之间寻找一个商人群体以及整个社会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从而为商人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
3.创新、开放、诚信、灵活的商业精神
天然地理条件赋予广州人天生的商业意识, 长期频繁的海内外贸易,形成了广州人勇敢开拓、开放变通的性格。
自永乐三年南海商人梁道明出海爪哇贸易而移民定居始,至正统年间到爪哇定居的广州商人已有约千余家,清光绪二年移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粤籍华人4万人[31]。不同于其他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观念,广州商人积累的资本部分流向生产领域, 推动了广东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如南海商人陈启沅、陈启枢兄弟在南海西樵乡创办继昌隆,成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万历年明政府在广州设立三十六行,将官治商贸改为由民间组织三十六行管理招商等事宜。到清朝演变成有名的十三行,他们每年冬夏两季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也就是今天广交会的前身。清代岭南商品经济极其繁荣,甚至出现中外各种货币通用的局面:“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曰北流锭,曰镪,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墨西哥。又有鬼头之名,盖外人往往以其国王之像印于钱面也,今民间呼为番面钱,以画像如佛,故又号佛番。”[32]这种使用多种外国货币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州商贸的开放性和国际性。道光十年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33]。
广州商贸所以得以快速发展,是与广州商人诚实守信、灵活变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合约精神:“作为一个商业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34]。广州商人所遵守的合约很多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和签字,却能很忠实认真地履行。
灵活变通是广州商人的又一特点。广东人信奉“精崽哲学”,精崽者,多赞其顺应环境做事融通,人际关系方面具有圆润通达之本领,即变通所包含的内涵。梁启超认为陆上一条路走到黑没什么,航海则发觉不对便须即刻变通。可见变通是岭南先民实践的成果。康有为有名言道,“盖变者,天道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晚清时广东南海人谭宗浚在北京所创著名的谭家菜,也是结合北京四季环境及饮食习惯变通,将广东经典菜肴与宫廷菜风格谐调统一,成为北京最富有特色的粤菜代表。
结语
商业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期商业活动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遗产,它既包括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形态也包括商品、商场等物质财富。明清的广州,形成了物质文化层面“品质精良、新颖多样”的商品文化、“讲粤语敬神灵,好风水重意头”的商俗文化、“以商筑城,以墟聚镇”的商业城建文化,以及精神文化上追求商人社会地位、促成尊商社会氛围的商业文化特征。
注释:
① 参见《番禺龙溪潘氏族谱》第30-31页,潘福燊编撰,1920年(民国九年)刊刻。
[1] 林益权.商业与商业文化[J].经济经纬,1990(4):8-12.
[2] 庞毅.商业文化的概念及研究范围浅议[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0(1):74-77.
[3] 单红波,张耀宇.关于商业文化对消费文化渗透与引导的思考[J].商业经济研究,2016(2):210-212.
[4] 刘建生,张宇丰.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论纲[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39(6):134-144.
[5] 薛光明.浅谈当前商业文化在企业中的主要表现[J].上海商业,2001(9):33-34.
[6] 王兴元,李斐斐.基于儒家价值观的鲁浙商业文化比较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1):42-49.
[7] 屈大均.广东新语注[M].李育中,等,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A11].
[8] 张嗣衍,沈廷芳.(乾隆)广州府志:卷48 [M]//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影印版.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22.
[9] 斯当东.英使渴见乾隆纪实[M].叶笃文,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503.
[10] 杨万秀.广州通史(古代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0:962.
[11] 黄庆昌.清代广州制造的西式钟表及其历史背景探析[J].南方文物,2011(3):196-201+208.
[12] 方勺. 泊宅编: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
[13] 吴建新,衷海燕.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J].学术研究, 2007(2):98-104.
[14] 唐嘉鹭.十三行行商的民间信仰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2013.
[15]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2):10-12.
[16] 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乡域·墟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11.
[17] 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M].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63.
[18] 霍与瑕.上吴自湖翁大司马书[M]//霍与瑕.霍勉斋集.霍与瑺校刻本.1588(明万历十六年):162.
[19] 脱脱.宋史:卷446[M].北京:中华书局,2000:10235.
[20] 冼宝干.鹤园冼氏家谱:卷6[M].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
[21]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M].合肥:黄山书社,1993:226.
[22] 王守仁.节庵方公墓表[M]//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821.
[23] 李贽. 藏书:德业儒臣后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26.
[24] 李贽.焚书;续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329.
[25] 叶显恩.明清珠三角商人与商业活动[G]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308.
[26] 卢子骏,潮连乡志[M].香港:林瑞英印务局,1946:129-130.
[27] 叶权.贤博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44-45.
[28] 顺德县志(清咸丰、民国合订本):卷27[M].顺德市地方志办公室,点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824.
[29] 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沙:岳麓书社,2001:490.
[30] 黄培芳,曾钊.新会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73.
[31] 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39.
[32] 胡朴安.中国风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83.
[33]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康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55.
[34] 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M].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49.
[责任编辑李夕菲]
2017-09-04
潘 彤(1963—),男,江苏南京人,教授,主要从事商业经济与文化研究。
F299.29
A
1009-1513(2017)04-004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