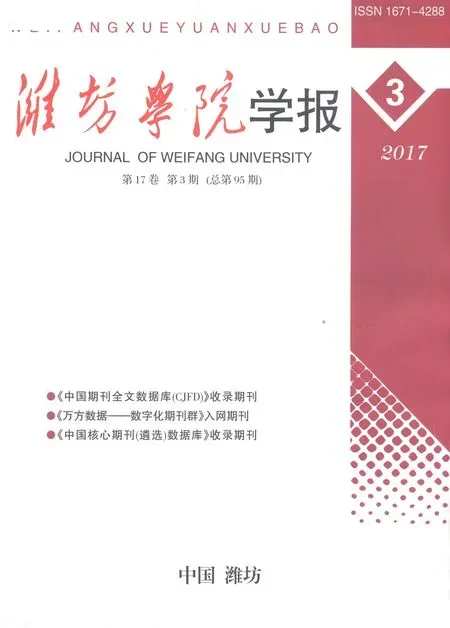创作上的“出轨”
赵德发
(日照作家协会,山东 日照 276826)
编者按::2017年4月14日,潍坊学院承办的山东社科论坛“全国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学术研讨会在潍坊举办,学院邀请了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开办学术讲座,本刊选取其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日照市作家协会主席赵德发的报告刊发,以飨读者。
创作上的“出轨”
赵德发
(日照作家协会,山东 日照 276826)
伟大的作家往往在写作题材上不断“出轨”,国外的如马尔克斯,国内的如贾平凹。赵德发最初从事乡土小说写作;然后因为一次机缘,选择以宗教作为传统文化介入途径,写出了《双手合十》《乾道坤道》等小说;最近则通过批判性关注社会现实,对人类的生存境遇表达自己深深的忧虑,写出了长篇小说《人类世》。作家具有“出轨”心理,首先是出于普遍性的喜新厌旧心理,其次是对新的表现题材敏感好奇,再次是为了寻求突破。
小说创作;出轨;传统文化;《人类世》
在2016年9月份山东大学文学院和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人类世》研讨会上,一位朋友调侃说:赵德发在创作上不断出轨。我明白她的意思,是指我的小说题材不断变换,就立即点头:对,我是出轨成性!
“出轨”本来不是一个好词。交通上的出轨,可能造成伤亡事故;婚姻上的出轨,可能带来家庭解体。创作上的出轨,也会带来一些风险。
风险之一,可能会有读者流失。因为有的读者偏爱某种题材,你如果转向别的领域,他们可能离你而去。
风险之二,形不成所谓的风格。有人告诫:没有风格的作家,可以变换题材源源不断写出新作;有风格的作家,大多会坚守一个阵地。
风险之三,评论界对你不好定位。有些评论家习惯于给作家分门别类,诸如“乡土作家”、“都市写手”、“军旅作家”、“情感作家”等等,一顶顶大帽子分送出去,成为他们眼中的作家标识。你如果写得过杂,题材多变,就难入他们的法眼。
其实,题材的变与不变,与作家的经历有关,与作家的追求有关,与机缘有关,与灵感有关,甚至与宿命有关。有的时候,忽然碰到了一个题材,你一下子激情迸发;忽然来了灵感,你欣喜若狂;忽然觉得自己必须写什么,让你有了必须投入身家性命去完成的神圣感。
凡此种种,让作家的创作面貌有了不同。有人汲汲于某一种题材,自己给自己筑就了轨道,方向既定,高歌猛进。有人则在原先的轨道上行进一程,又另觅新路,给人以“出轨”的印象。
两种做法,皆能成就作家。
有些作家的题材领域基本不变,如福克纳、莫言、张炜等等。福克纳一直把自己生活的小镇描绘成“邮票那样大小”,说他一生都在写一个邮票大的地方。他的小说,故事发生地多在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种文学模式的建立,引起世界文坛的“喧哗与骚动”,许多作家竞相仿效。莫言就是仿效者之一,他在高密东北乡上,建起了霸气十足的文学帝国。张炜则从芦清河出发,在胶东半岛盘桓行走,将这里变成了气象万千的文学高原。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是一个经常变换题材的作家。众所周知,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他40岁时出版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部伟大作品中的马孔多小镇,成为全世界读者眼里的一块圣地。但是马尔克斯并没有在此停留,又写了《族长的秋天》,讲述一个独裁者无所不能却孤独落寞的一生。继而写《霍乱时期的爱情》,几乎将人世间的种种爱情一网打尽。写《迷宫中的将军》,将笔触投向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在他76岁身患癌症时,又写了《苦妓回忆录》,讲一个老记者为了庆祝自己的九十大寿,特地到妓院找了个14岁的处女睡觉,以纪念这个难得的生日。这个题材,简直是匪夷所思。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马尔克斯就这么不断变换题材,攻城掠地,成为一个誉满全球的文学大师。贾平凹也变换过题材。他一直写商州系列,写农村题材。他在《极花》出版后接受记者访谈时,谈到他专注于农村题材的深耕,说:“我习惯了写它,我只能写它,写它成了我一种宿命的呼唤。”但我们也都记得,他在1993年却有《废都》问世。这是一部标准的城市小说,表现时代生活真切到位,刻画文人心灵入木三分。我认为,这是贾平凹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不朽之作。可以这样说,他如果没有这一次“出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矮了三分。
下面,我要讲讲我的“出轨”经历了。前面之所以要讲到这些大作家,是想让大家了解,像我这样一个在文学道路上碌碌爬行的一个小作家,如何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斗胆做出的一些尝试。
一、乡土小说:我的发轫之轨
我1955年出生于莒南农村,那片水土决定了我的血质,血质又决定了我的创作取向。所以,我刚走上文学道路时,写农村是必须的,也是宿命的。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能够引起我持久而深沉的创作冲动的,是土地与农村。我最早的一批中短篇小说多是乡土题材,其中《通腿儿》《选个姓金的进村委》分获《小说月报》第四、第八届百花奖。但我不满足于中短篇小说的零打碎敲,从1993年开始,准备创作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
这部作品,我想表现百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关系,以及给农民带来的命运之变。我在写作中定下了三点追求:首先,理念要新,能够反映历史真相,贴近历史本质。其次,要有鲜活生动的情节和人物,把小说写得好看;第三,要有密集的审美信息,适应快节奏社会的读者口味。总之,我要求自己把大半生的积累和全部的功力统统用上,争取把书写好。
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部40万字的长篇杀青。出版,我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我给了《大家》杂志。1996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李巍主编的电话,说他决定在《大家》第三、四期发表《缱绻与决绝》。我觉得分作两期不好,问他能否压缩一些篇幅,一期发出来,他说删掉5万字就可以。我立即坐飞机去昆明,用两天一夜时间删定书稿,杂志社将稿子发排。我看着他们设计的版式与题图,有了痴心妄想:莫言先生凭《丰乳肥臀》荣获第一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得奖金10万,第二届大奖说不定就是我的啦。然而,我受莫言株连,未能遂愿。怎么回事呢?我改定稿子之后去西双版纳玩了三天,回到昆明,李巍主编说:出大事了。有人写文章批《丰乳肥臀》,我们的压力很大。你的稿子有土改方面的内容,现在不敢发,只能缓一缓。我得知这个消息,垂头丧气回来。等了三个月,我打电话对他说,你光发第一卷吧,这样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于是,《缱绻与决绝》的第一卷就在第5期发了,大约是10万字。1997年初,人文社的单行本上市发行。当年秋天,《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创刊,选载了《缱绻与决绝》。此书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并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缱绻与决绝》表现的是农民与土地,之后我又写了一部《君子梦》,表现农民与道德;一部《青烟或白雾》,表现农民与政治。这个系列总共120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觉得,不如此大规模地写乡土,对不起那片土地,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我对文学的一片痴情,甚至对不起我卑微而有限的生命。
《当代》1998年第6期发表《君子梦》第一卷时,配有“编者的话”,第一句是“作者赵德发是个写农村的高手”。我的写作到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认定我是个乡土作家,我也给自己筑起了写作轨道,认为自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了。然而,我却“出轨”了。
二、佛道小说:我的文化之旅
完成“农民三部曲”,我忽然不想再写乡土,想换换题材。就在此时,机缘来了:五莲山光明寺的住持觉照法师捎口信让我上山,研讨如何发掘五莲山佛教文化,我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写一部关于当代汉传佛教的小说。念头一出,心驰神往,我立即开始读书、采访。我的写作,也从经验之内转向了经验之外。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写出了长篇小说《双手合十》。
这部作品问世后,被我的一个道士朋友看到,他十分赞赏,建议我再写写道教,于是,我又用三、四年时间,写出了反映当代道教文化的《乾道坤道》。
人类的各个民族,各有一套文化基因。它体现民族的文化积淀,彰显民族的文明印记,影响着民族的信念、习惯与价值观。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绵长而复杂。如果说,生物的DNA是双螺旋结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则是由多条文化线索拧成的长绳。两千年来,儒、释、道这三条线索紧绞密缠,甚是粗壮。儒释道三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也可以称作中国人三个精神支柱。我在《君子梦》中,表现了百年来儒家文化在农村的存在与流逝,在《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中,我要全面反映这两种宗教文化在中国当下的存在形态。
宗教文化的载体,是经书、庙宇、仪规、信徒。我就从这几个方面着手了解。
一是读书,与佛教有关的书,我读了上百本,包括佛教经典、高僧著作、禅宗公案、佛家仪规、佛教历史等等,作了几十万字的笔记。道教方面的书,我也读了不少。我在网上发现一个道长的博客,他的文章嬉笑怒骂,深入浅出,十分喜欢,就从网上一篇篇下载,打印出来研讨,还做了索引。后来,我专程拜访了这位道长,将他当作《乾道坤道》主人公原型。
二是去寺院、道观参访。在那七八年的时间里,我走了几十家寺院,几十家道观,在多家住过。我与出家人一起吃斋、打坐、出坡(劳动),打成一片,深入体验他们的宗教生活。
三是参加宗教仪式。在寺院、道观居住时,我随信众一起参加早晚课及各种活动。有一次,我想到扬州一座著名禅寺体验,可是该寺知客僧不让我进禅堂。我一再央求,他就让我背诵经书,考我,幸亏我还能背诵几段,这样才得以进去,见识了中国最正统的坐禅仪规。
四是结交朋友。在采访中,我以我的真诚以及对他们的尊重,结交了一大批僧人、道士朋友,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乃至内心世界,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总之,这两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就是我的两次文化之旅。我学习传统文化,思考其前世今生,表现宗教人物,讲述中国故事,让我的创作轨迹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三、人类世:我的写忧之行
写忧是抒发排除忧闷的意思。《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陈子昂在《春台引》中写道:“怀宇宙以汤汤,登高台而写忧。”
2011年春天,我从媒体上了解了“人类世”这个新概念,世界观从此改变。我在地球46亿年的背景下看人类,看世界,在俯仰之间、呼吸之间感受人类世。2013年10月26日,我准备给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开宗教文化讲座,早晨起来重读《圣经》,脑际突现一个念头:写一部关于“人类世”的长篇小说。这时我激动不已,立即发了一条微博:“一个念头,一部作品。记住今天早晨,这将成为我创作生涯的重要时刻。”从那以后,我日思夜想,神魂颠倒,“头脑风暴”经常发生。尽管这个题材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但浓厚的兴趣、强烈的冲动让我不得不去付诸实施。
写这本书涉及许多学术领域,我读了地质学、地史学、人类学、基督教神学等方面的书,还参观了好几家地质博物馆;同时,我四处考察,大量采访,走了许多地方,接触了各方人士。这些准备,有效地帮助了我的创作。
该作品以一座大型海滨城市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同时写到美国、非洲及太平洋岛国。作品展现人类生活的宏阔图景,描述人们在“人类世”的种种造作,揭示地球形态与生态之剧烈变化,表达对人类未来和地球前景的忧思。全书完成后,在《中国作家》2016年第1期发表,《长篇小说选刊》第3期头题转载。《长篇小说选刊》转载这部小说时的推荐语这样写:“《人类世》从大处着眼,关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同时又在宗教和哲学的引导下,探究人性的幽微之处以及人类获得救赎的可能。”《人类世》单行本2016年7月份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策划人、著名出版家安波舜先生在封面上写道:“《人类世》的故事注定要镌刻在民族崛起的路标上:我们拥有汽车和豪宅,却失去赖以生存的空气、食物和水!我们的性爱拥有更多的选择,却失去健康、一往无前的精子!我们拥有飞船和核武,却向上帝和诸神祈求怜悯、同情和爱……”
除了以上两次题材转换,我还有另外几次“出轨”经历。如2005年写了一部小长篇《魔戒之旅》,内容是在电影《魔戒》拍摄地新西兰旅游的经历;2012年写了纪实文学《白老虎》,揭秘中国大蒜行业内幕。还有中短篇小说《下一波潮水》《针刺麻醉》《摇滚七夕》等等。
分析我的“出轨心理”,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喜新厌旧
就像恋人常常发誓要“白头到老”,若干年后却分道扬镳一样,我当年也说过,农村题材“会引起我持久而深沉的创作冲动”,但我在新世纪之初,完成“农民三部曲”之后,却对农村题材减弱了冲动。不是耗光了相关库存,我积累的农村生活素材还有不少,但就是找不回前些年心心念念想着乡土、处心积虑要写乡土的感觉。长篇小说构思有好几个,我掂量掂量这个,又放下了;琢磨琢磨那个,又否定了。我觉得,再写农村题材,很难超过“农民三部曲”,至多是在一个平面上滑行。这是我不愿看到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不愿把“乡土作家”的帽子戴一辈子。我上学很少,小学没毕业,后来又上过四个月的初中,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三十岁之前没有任何文凭。这样的学历,让我前些年很自卑,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想写出有文化含量的作品来证明我不只是一个乡巴佬。虽然《君子梦》是写儒家文化在农村的传承流变,算是一部文化小说,但我觉得还不够,因为这部小说依旧是乡土题材。
就在这时,机缘来了,我决定写一部小说,反映当代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有好多流派,禅宗最为深奥,我偏偏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青年禅僧。这给我带来了严重挑战,也让我十分兴奋。我重新找回了感觉,痴迷地读书,广泛地采访,投入地写作,终于完成了《双手合十》。此后,道教题材同样给我一种探险的感觉,让我以饱满的热情完成了《乾道坤道》一书的创作。
写完佛道姊妹篇,我还有一些材料没有用上,有一些思考没有表达。本来要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以佛教居士为主要表现对象;还想写两部纪实文学,全面反映当代佛教与道教状况,但这些计划最后都是付之东流。主要原因,是我遇到了另一个题材。
这个题材是“人类世”。它给我带来的创作冲动不可遏止,于是,我又用三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一部全新题材的长篇小说。
写《人类世》期间,我因为经常回老家伺候父母,农村见闻积累了不少,准备写一部纪实文学。全书构思基本成熟,已经向出版社报了选题计划,马上可以动笔。但我没觉出新鲜,产生不了那种强烈冲动,只好又放弃了。
我向朋友自嘲:我现在找写作选题是“重口味”了,如果不是陌生而新鲜的题材,很难把我激发起来。与长期从事专一题材创作的作家相比,是我定力不够吧?
二、敏感好奇
我这人木讷呆板,但内心敏感,尤其是对一些新鲜事物,能及时给予关注,做出思考。
譬如说,我对一些词语比较敏感。第一次从媒体上看到“人类世”这个词,就像过电一样,身心战栗。这个词太有分量了,太有内涵了,其能指与所指都给我的心灵带来严重冲击。它一下子开启了我的视野,我看待人类,再也不是“上下五千年”,而是从地球四十六亿年的历史背景下去审视他们。
本人虽然一天天变老,但好奇心不退,对许多未知领域都想搞懂。我去寺院、道观参访,就是想搞清楚,佛教、道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僧人、道士,为何要脱离惯常的生命轨道出家修行?佛教中的禅宗,道教中的内丹术,这些传统文化中最幽深的领域到底是什么样子?诸多问题,都想一探究竟。我现在想,撇开写佛道姊妹篇这个目的,我平生有了这么大规模、这样独特的探访,是平生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是源于我的好奇心。譬如说,“文革”期间,我就听说了“针刺麻醉”这个所谓的“新生事物”,前几年又想起来,一心想弄清楚当时的真实情况和实际效果,于是就翻阅资料,采访麻醉医生,写出了《针刺麻醉》这个短篇,发在《人民文学》杂志。我坐轮船去韩国,在船上发现了“带工”这个群体,就通过采访,写出了《下一波潮水》,发在《十月》杂志。
有人说,好奇心是不成熟的表现。但我希望,我宁可不“成熟”,也要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三、寻求突破
我从事创作近四十年,有七百万字作品问世,但一直对自己不满意,与那些大作家相比,更是汗颜。人家是才高八斗,我恐怕连一升也没有。有句老话讲:“天生只有八合命(合读gě,量词,十合为一升),走遍天下不满升。”但我不甘心,还是想不断进步,寻求突破。
那么,突破口在哪里?我这人很笨,形式上玩不出花样,就想在题材上求新,思想上求深。思想上求深,也不是那么容易,很可能你一思考,读者就发笑。再说,一味表达思想,那也不是小说的功能。所以,我就把突破口选在了题材上。通过一次次“出轨”,展现我的努力。我的老师、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曾说:“德发打一枪换个地方,枪枪都是十环九环。”这是过奖了。我至多打个七环八环,没有脱靶就不错了。
今后,我还能否出轨?看老天给多大恩典,看本人有多大造化。
谢谢大家!
I206.7
A
1671-4288(2017)03-0065-04
2017-05-02
赵德发(1955—),男,山东莒南县人,日照市作家协会主席。
(此文根据赵德发2017年4月14日在潍坊学院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