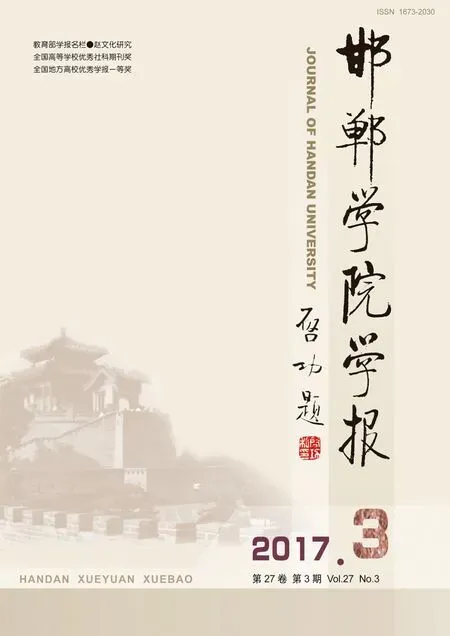《史通》研究现状述略
吕海龙
《史通》研究现状述略
吕海龙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国内《史通》研究按其研究角度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从经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二,从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三,从文献角度进行的研究。第四,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这四类研究,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关系,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浑融状态。
《史通》;研究现状;述略
国内《史通》研究按其研究角度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从经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二,从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三,从文献角度进行的研究。第四,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这四类研究,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关系,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浑融状态。海外研究工作多是对《史通》个别篇目内容进行修补或者进行文本译介等,相较而言,国内多针对《史通》的学术价值进行研究,成果甚多,且更为深入。故而本文所述主要立足国内研究,同时借鉴海外研究成果。详论如下。
一、从经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史通》撰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该书已经开始流传,但是,赞赏者不多,质疑者不少,刘知几还专门写了一篇《释蒙》来为自己进行辩解。《释蒙》其文已佚,所以不知道当时人为何对《史通》作何批评,亦不知刘知几如何应对的。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刘知几去世后,唐明皇令人抄写其《史通》进呈,读后大为赞赏;“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1]3171然该书问世伊始虽已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和同时代史家徐坚的认可及褒扬,但在复古崇经之风盛行的中晚唐很少有人提及其书,好像并未大行于世、广泛流传,至少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说明其大受欢迎。其主要原因概为《史通》的《疑古》与《惑经》两篇对儒家经典和圣贤人物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史通·疑古》篇质疑《尚书》所载不实,尧、舜、禹、汤、周文王、周太伯事迹不尽为实录,刘知几认为尧治理天下时善恶不分、贤愚混杂;舜遭放逐而死;“汤之饰让,伪迹甚多”[2]387;文王为西伯时心怀不臣之心欺凌天子;太伯让天下是为了避免招来杀身之祸的无奈之举。刘知几怀疑周公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2]392,同时认为“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乎?”[2]388为桀、纣辩护,认为远古之书如《尚书》“其妄甚矣”[2]394。
《史通·惑经》篇批评《春秋》有“十二未谕”,即有12点不合情理让人不明白的地方。后世对孔子有“五虚美”,即后世对孔子的赞美有五个方面言过其实。人们对《春秋》的褒扬可能只是人云亦云的随声附和。而对孔子,也不过是“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2]414。
《史通》一书对《尚书》《春秋》所载圣君贤臣的事迹大胆质疑,对孔子修史的某些做法也大加批判。这让后世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一些文史学者极为不满。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学者柳璨撰《史通析微》(又名《柳氏释史》)一书,该书是最早专门评论《史通》的著作,今已不存。但据两唐书《柳璨传》可知柳璨在书中批评《史通》对先贤经史多有指摘,评价失当。北宋孙何著有《驳史通》“若干篇”,今已经不存。其《驳史通序》尚在,批评曰:“恃其诡辩,任其偏见,往往凌侮六经,诟病前圣”,“逆经悖道,拔本塞源,取诸子一时之言,破百代不刊之典,多见其不知量也”[3]178。其后,张唐英《刘知几论》其一批评刘知几“徒好辩而不知《春秋》之旨。其他事以类推之,圣人之志皆显然明白,故不复辩,学者当自求之,无惑刘子之异说可也”[3]606。张唐英一方面说“不复辩”,但还是忍不住,又于《刘知几论》其二云:“刘子(按:指刘知几)之罪,过于杨、墨远矣。苟不辟而归坦途,愚恐学者径驰于淫说矣!”[3]608这些指责,虽然只是针对《史通》的部分篇章的某些问题,但措辞严厉,对《史通》的整体评价,对唐宋时人对《史通》的接受或与一定影响。
总的看来,唐宋时期的学者多从经学的角度对《史通》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指摘。《史通》一书从宋至明,少人问津,论者不多。正如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序》所言:“昔人以其诋诃前贤,语伤刻核,而《疑古》《惑经》诸篇,尤为世所诟病,故其书始成,传习者少,而讹脱者亦甚。”[4]1
二、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
较之前代,明清时期是《史通》整理、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明代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陆深《史通会要》3卷,李维祯、郭延年《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20卷。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20卷,浦起龙《史通通释》20卷、纪昀《史通削繁》4卷。
陆深《史通会要》分上中下三卷。既有《史通》书中精粹,又有后人论史,同时间有自己的观点,既作选编又有评论。内容逻辑性、系统性不是很强,其大致顺序为先举《史通》中的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两篇,次举内篇部分的诸篇目,最后集中笔墨进行评论。李维祯、郭延年最早对《史通》进行训释。王惟俭对郭的训释和所用刻本都不甚满意,又重新进行校释梳理。黄叔琳又对王惟俭的训释有所补充。
浦起龙是封建时代对《史通》研究最深、成就最高的一个学者。其《史通通释》较为晚出,且吸取了先前的校释成果,浦起龙在《史通通释》序文中以与蔡敦复问答的形式,对郭延年、王惟俭、黄叔琳对《史通》所做的工作都作了一番评价。对郭本批评《史通》的相关评论部分表示了认可。同时,对蔡敦复认为王损仲本“粪除诸评,世称佳本”的看法,做了进一步说明,指出其本不足之处在于“蔽善匿”“未见其能别彻也。”再有,浦起龙谈到了其书与黄本进行了互正,“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干条。”[2]3浦起龙对《史通》字间作释,疏通句子,同时划分章节,逐节做按,串讲大义。对《史通》注解非常详细,为后世读者解读文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史通》“其书自浦二田通释出乃大体可读。”[5]2
《四库全书总目》对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最为重视,把其书置录于《史通》之后,而郭、王、黄三家皆仅存其名,归于存目书之中。《史通通释》目前之通行本是据求放心斋初刊本的三个印本中的最后一个印本刊印,由王煦华校点。该本王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如《杂述》篇,浦起龙注干宝《搜神记》为十卷,王则据《隋书·经籍志》改为“三十卷”。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分为上下两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8年排印。王煦华此校点本又于200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为一册重刊,重刊本附录部分增彭仲铎《史通增释》、王煦华《浦起龙生平及其著述》等内容。
明清时期的学者主要进行的是对《史通》的校勘、注释、评论、撮要或删削等工作。在对《史通》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学者逐渐认识到《史通》的史学价值。这一时期对《史通》之史学价值给予很高评价者不乏其人。如明代张之象《史通序》云:“剖击惬当,证据详博。获麟以后,罕见其书。”[6]清代纪昀《史通削繁自序》曰:“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7]1《四库全书总目》云:“亦可云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矣。”[8]751《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赞《史通》曰:“故自唐宋以来,史家奉若龟鉴焉。”[9]332
民国以后至当代,从史学的角度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继续深入进行。这些研究成果或以传统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现,或以生动活泼的人物传记形式呈之,持论公允、认识深刻。大致如下:
对《史通》进行校注或笺证的相关成果颇多。1990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其书正文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的《史通通释》为底本,体例大致为先对正文作注释,然后辅以作者说明,同时个别章节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前人研究成果。共作注解6300余条,校勘记约有2200余事,100余万字,是当代《史通》文献校注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赵吕甫之前,另有数家。陈汉章为浦起龙《史通通释》作《史通补释》,其书被柳诒征赞曰:“钩稽事实,疏通证明”,“以唐事证《疑古》篇之说,使子玄文外微旨昭然若揭。”[2]611杨明照于陈汉章后又作《史通通释补》。程千帆在陈、杨等人的基础之上又兼采诸家之说将卢召弓、孙星如等所为校勘记汇为一编,作《史通笺记》。程千帆以后有张振佩作《史通笺注》。
对《史通》进行译注的则不得不提到程千帆作序,姚松、朱恒夫先生译注的《史通全译》一书。该书以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为底本,同时吸收了前人的校注成果。每一篇目先有“题解”,再录《史通》原文,然后加以注释,最后对原文进行翻译。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专门研究者来说都非常方便且实用。然美玉有瑕,个别地方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为沿袭前人注释之误。如《史通·采撰》“禹生启石”四字,该书注曰:“《淮南子·修务训》:‘启,夏后子,其母涂山氏女……石破北方而启生’”。这段话本出自颜师古为《汉书·武帝纪》“见夏后启母石”句所作之注。师古其注又云“事见《淮南子》”。[10]190此说又为《佩文韵府》所承袭。浦起龙《史通通释》在“禹生启石”四字所作按语时即指出:“(《韵府》)谓是《淮南》之文,《淮南》实无其文,亦编书家不根之一征也”[2]118。笔者细考《淮南子·修务训》篇,看到其只有“禹生于石”[11]2四字,浦起龙所言为是。《〈史通〉全译》没有说明这一点,而是直接承袭了颜师古的说法。再为产生了新的注释问题。概因对《史通》引书之具体内容不可能一一翻阅,所以个别地方对《史通》的原意理解不够彻底,如对《史通·二体》篇说的“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一句中提到的“《项传》”,注释为“《项羽本纪》”。将《史记》和《汉书》详细对照发现,刘知几提到的“语在某某”,《汉书·项籍传》有,而《史记·项羽本纪》无,故而可知此处注释稍有不妥,实际上应注为《项籍传》。三为有些翻译还不够通达。如《史通·叙事》篇刘知几引《礼记》云:“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作为自注。《史通全译》把这段引文翻译为:“阳门的介夫死了,子罕哭得非常悲痛。老百姓心情舒畅,恐怕不能攻打”[12]331。把“说”直译为“心情舒畅”,本无不妥。但这里容易产生歧义:让人误以为老百姓对介夫之死感到心情舒畅。愚以为可加上“对子罕的做法非常满意故而”数字。当然,凡事皆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总体来说,笔者认为《史通全译》一书对普通爱好者及一般研究者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对《史通》的“评”与“平议”之作。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吕思勉《史通评》以浦起龙《史通通释》及四部丛刊本相较而定为一本,用现代史学观点对《史通》评议,于《史通》正文后并附有考据和辨证,以“抉刘氏思想之所由来,扬榷其得失,并著其与今日之异同。”[13]452此类作品另有张舜徽《史通平议》等。
对刘知几行年进行研究的著作也很多。傅振伦《刘知几年谱》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该书分别从“刘知几的史学地位”、“刘氏世系”、“刘知几之家世”、“刘知几学行述略”、“年谱”、“史通要论”等方面对刘知几兼及《史通》进行系统研究。问世最早,最有代表性。其他有周品英的《刘知几年谱》和刘汉之的《刘子玄年谱》等。
对刘知几进行评传的著作也不少。此类著作有许凌云《刘知几评传》,许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述“刘知几的生平”,下篇论“刘知几的思想”,既对刘知几生活时代、家世、生平活动等一一叙述,又对《史通》之构思、史料论、史笔论、史家修养论等方面加以评论。全书较为系统全面。另外,赵俊与任宝菊《刘知几评传——史学批评第一人》在刘知几评传类作品中颇有新意。该书前三章由赵俊所写,从“青少年”、“中年”、“老年”谈刘知几生平及著作等,文笔活泼生动,不同于传统的学术著作的写作方法。后两章由任宝菊所撰,阐述《史通》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意味较为浓厚些。
将刘知几及其《史通》结合起来从史学批评角度进行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其中张三夕《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1992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该书从史学批评角度出发,上篇对刘知几进行述评,下篇对《史通》引书中先秦部分的文献进行了考证。尤其是下篇在文献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值得重视的。其他还有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等。
纵观各家所作,基本上都是从史学的视角对《史通》进行研究。这些著作,或对《史通》进行校注或译注;或对《史通》的史学思想逐篇进行评议梳理;或从刘知几的行年述略进行考察;或以非严格学术论著的人物传记形式对刘知几及其作品进行论述;或将作者和作品结合起来对刘知几及其《史通》进行研究。它们都从《史通》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出发,给予刘知几和《史通》以较高的评价,从史学的角度将《史通》研究向前推进。
针对学术界对《史通》的研究现状,董乃斌先生《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一块里程碑——论刘知几《史通》的叙事观》一文曾指出:“唐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著名的发愤而作的史论,对从上古至唐代的诸多历史著述作了种种批评,并由此概括和阐述了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前人先贤对《史通》文本的考订、注释和解读,对刘知几的历史观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贡献,均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中,《史通》也已被当作一种古代文论而加以关注。”[14]157
三、从文献角度进行的研究
这里所谓从文献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指的是对《史通》征引书目进行的相关研究。刘知几本人在《史通·自叙》篇中就提到了自己博观群书而有所心得:
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2]289
刘知几旅居长安、洛阳,累计数年,其间,将“公私借书,恣情批阅”。彼时一代之史,有多种著述;杂记小书,说法不一。刘知几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钻研穿凿,尽其利害”。他从小读书就喜欢谈论分析其中的道理是非。“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其中“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只因不肯盲从前人定说,故被别人斥之为“轻议前哲”。知几深感“流俗之士,难与之言”,所以只能“蓄诸方寸”。然而,刘知几对自己迥异乎世俗的精见卓识充满自信,充沛于胸的新颖观点一旦酝酿成熟,就不能不诉诸于言论,笔之于文章;从而创作出了《史通》一书。
刘知几自言其《史通》“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含千有”[2]292。据浦起龙所见《史通》旧注所言:“除所阙篇,凡八万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2]1。《史通》见在篇目共八万余字,论及三百余部书。①刘知几在其著作中所征引的书目,是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引书研究是《史通》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方面。
《史通》引书涉及经史子集,无所不备。然而遗憾的是,刘知几毕竟不可能有现代人的学术意识,也没有给后世列出一个详细的参考书目。刘知几所看过的书到底是什么、具体有多少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史通》所征引的书目所涉为何,还是大致有迹可循且必须弄清楚的。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我们就无从揭晓刘知几的学术源流,那么对刘知几及其《史通》文学观的研究恐怕也要流于表面,仅仅看到刘知几些许浅层次的观点,甚至会对其观点作出断章取义的结论。这样的话,则恐怕很难真正地理解刘知几及其《史通》所论为何,最终亦成为与刘知几无法沟通的“流俗之士”了。
关于《史通》的引书问题,早在明代后期已经有文学家、思想家、文献考据学家焦竑等着手开始研究。明代嘉靖年间,思想界涌起一股反对程朱理学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尊重个性张扬的思潮,潮流翻腾,影响甚大,余波所及,在文学艺术领域,文献考据与训诂之风随之大起,焦竑(1540—1620)是这股风潮的领军人物之一(另有一位是杨慎)。大概出于同刘知几有着思想堪称超前、官场可谓失意、参与过国史修撰等等诸多共同点的原因,焦竑对刘知几大为赞赏,他说“余观知几指谪前人,极为精核,可谓史家申、韩矣”[15]124。焦竑自幼好读书,兴趣广泛,所阅杂博,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而且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焦竑有这个意愿同时也有这个能力成为对《史通》引书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第一人。焦竑在其《焦氏笔乘》卷三《〈史通〉所载书目》篇罗列《史通》所载“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记”共148种。[48]
不过,令人可惜的是,焦竑是自唐迄清,对《史通》引书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人;所撰《〈史通〉所载书目》一文,是清前开列《史通》引书单的唯一的一篇文字。也有人怀疑此篇非焦竑所作,如王春南《〈史通〉征引古籍及其存佚》就质疑说:“焦竑作为颇有名气的学者,按理不应疏阔一至于此,竟弄不清‘颜师古《隋书》’跟‘孔颖达《隋书》’本是一书。或序焦氏写作《〈史通〉所载史目》,曾借手他人。”[16]
其余学者要么对《史通》引书避而不谈,要么对这个问题简而化之。或言“数万卷”,或言“何止千百卷”等等,如清代的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即云:“然其荟萃搜择,钩抓拍击,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2]3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则曰:“观其《史通》之所援引,自六家、二体以及偏记、小说,何止数千百卷?”[17]177
民国至今,对《史通》学术价值的研究虽然进入了高潮阶段,但引书问题的研究,仍然很少有学者涉足。有学者着意为之,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卒章。如王绍曾先生发表于《无锡图书馆协会会报》1935年第4期的《〈史通〉引书考初稿(部分书录)》。
较为完整的研究成果有论文两篇、论著三部。论文分别为王春南的《〈史通〉征引古籍及其存佚》及吴荣政《刘知几〈史通〉评述书目考》。三部专著则是张三夕的《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及马铁浩的《史通与先唐典籍》《〈史通〉引书考》。就当下而言,最为晚出,且参考价值较大的应属2011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马铁浩《〈史通〉引书考》一书②。简述如下。
王春南《〈史通〉征引古籍及其存佚》一文认为《史通》引书共376种,王春南撰文所用的似乎是较少有人提到的卢文弨《史通》精校本③。王春南指出焦竑《〈史通〉所载书目》一文,“列出《史通》引书一百四十八种,出去复重、衍文,尚有一百四十三种(王的原注:此据南京图书馆抄本。粤雅堂丛书本仅有一百四十二种),此数不到《史通》实际引书数的一半,缺漏过多。对焦竑《〈史通〉所载史目》,应加以纠缪”[16](王的批评是以自己的实际研究结论依据的,很有说服力,不过王却忽视了一点,即焦竑之文标榜“史目”,其文确实也没有载入“经”、“子”、“集”类引书,这可能是焦竑所列引书数量过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王文认为焦竑之文“缺漏”而进行“纠缪”,恐言之过重)。王文仅仅只是列出了一个数字,所征引的书目具体为何,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
吴荣政《刘知几〈史通〉评述书目考》一文没有说明所依据之版本,据他“考证,《史通》的《原序》、内篇36篇和外篇13篇的正文、原注评述书目共340种”[18]。吴文一一列出了所征引书目的具体名目,却没有列出具体的出句。吴文列出的书目在《史通》中有无征引;是在正文中还是在注文中征引;具体以何种形式征引的,所引书目只是提及作者,还是出现了具体的篇目,亦或是出现了具体的内容,还是上述三种情况有其二或全部都有等等诸种问题,我们很难从文章中得到满意的答案。
焦竑的书目仅列书目未作分类。王春南的文章没有一一指出《史通》所征引的书目具体为何。吴文对所列书目一一归类,并在注释三中指出该文“以隋志为准,部居《史通》评述书目,并参考汉志、两唐志和宋志。有少数为上述史志未录者,则窃据己意,安排在有关部分。但某些篇名,如《史通·序例》提及《七章》,无考,不录”[18]。吴文对《史通》引书做出归类,将《史通》引书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点。不过对于吴文的这个分类标准,笔者认为尚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首先,吴文的分类,是按《隋书·经籍志》来分类的,而刘知几本人却是反对《隋书·经籍志》个别分类方法的。如刘知几在《史通》中评及隋志唯一的一处中指出:[49][50]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2]138
可见,刘知几本人对隋志“流别群书,还依阮《录》”之做法的态度是有所不满的。
接下来,再以《国语》、《史通》这两个在归类上历代分歧较大的引书条目为个案,看一下吴文参考两唐志和宋志(吴文还参考了汉志,但由于《史通》引书涉及汉志中的书目不多,所以不再将汉志归类作为研究对象)所做出的的归类是否科学。
先看《国语》这一条目,《旧唐书·经籍志》把《国语》(《旧唐书·经籍志》以“《春秋外传国语》”条目收录)归入“甲部经录”“春秋”类[1]1979。《新唐书·艺文志》更是把《国语》(《新唐书·经籍志》亦以“《春秋外传国语》”条目收录)列为“甲部经录”“春秋类”之首[19]1437。《宋史》把《国语》列入“经类”的“春秋类”。而吴文承上所分类,把《国语》归属于“经部”,排在“春秋类”与“孝经”类之间。
再有《史通》这一条目。刘昫的《旧唐书·经籍志》根本没有收录《史通》。《新唐书·艺文志》把《史通》归入了“丁部集录”其三“总集类”[19]1625。《宋书·艺文志》把《史通》和《文心雕龙》、王昌龄《诗格》等一起收入了“集类”其四“文史类”[20]5408。吴文的分类中,也把《史通》归入了“集部”类存本之末。
由上刘知几本人的意思和实际的分类效果两方面来看,吴文分类依据《隋志》,参考两《唐志》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妥当。
张三夕以1978年版浦起龙《史通通释》为底本,统计出“《史通》全书引用文献共三百余种”[21]128,并将先秦部分的54种书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类书目皆先列书名,次记条数,同时附有引文出句,凡出句皆于其前标明卷数页数及篇名,检核查证颇为方便。只是正如作者“附记”所言:“《史通》全书引用文献三百余种,因时间、篇幅等因素的限制,现先印出先秦部分,征求意见,至于其他部分,姑俟异日。”[21]128《史通》所涉秦汉以后的书目还有待进一步整理。
马铁浩的《史通与先唐典籍》,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12月出版,为新出之作。其书未说明所用底本,他统计得出“《史通》引书凡340种。另有单篇文章50种。”[22]343所列书目先注书名、次记条数,然后附上出句,出句较多的列其中数条。该书对所列书目考证缜密,列书目的同时附上在《史通》中的出句,做到了征而有信。只是没有明示其所依据之版本。不同的版本在具体的遣词用字、标点断句、文本理解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根据不同版本进行征引书目相关研究时,这些不同可能会使相关研究得出差距过大,甚至迥然不同的结论。
马铁浩《〈史通〉引书考》一书,对《史通》引书,搜罗最为全面。其于该书“自序”中云:“不敢作子玄功臣,唯望不作其罪人而已”。是自信,也是自谦之词。其书,以浦起龙《史通通释》为底本,考《史通》所引典籍345种,以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排列之。每一条目下,先是书名,然后是出句,最后辅以考辨。非常方面后来学者使用,不过亦有美中不足:出句不全,不利于全面完整地把握刘知几对所引书目的认识、评判与利用情况。
上述《史通》引书研究成果的共有问题是对《史通》征引书目的出句没有全部列出,征引书目的分类还有进一步合理化的空间等等。这些工作,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大多数研究者对其的研究价值不够重视,前人可供借鉴的成果又相对很少,问题的解决需要花费的时日很多,对研究者学力和精力的要求也教高。因这些原因,目前《史通》研究者中尚未有人将这项圆满完成。本人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史通〉与刘知几文史观研究》之“附录”部分,以“《史通》引书索引”的形式,以征引书目通用名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为序排列,同时将《史通》引书所涉之篇目及其出句尽数列出,可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些方便。
四、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刘知几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早在宋代已经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如北宋黄庭坚《与王立之四帖•其二》即云:“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23]597黄庭坚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刘子玄的《通史》这两部书的观点虽不高深,但是要评论古人文章的缺点就不能不读这两部书。宋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刘知几在文论方面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到了明代,情况变化更大,一些学者篡改黄庭坚的原话,为了推崇刘知几《史通》在史学方面的价值,竟然把文学价值完全掩盖了。这里杨慎可谓始作俑者,而后推波助澜者不乏其人。
明杨慎《丹铅余录》卷十三或《丹铅总录》卷二六《琐语类》《升庵集》卷四七《老泉评史通》都收录了黄庭坚的话,但作了很大的改动。其云:“黄山谷尝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其将《史通》局限于评史范畴之中,此语一出,影响甚大。此后直至清末,数百年的《史通》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将《史通》单纯视为史论的路子。人们对刘知几《史通》的价值的关注焦点仅仅局限于史学方面。
明王惟俭在自序《史通训故序》中说明其书写作缘起及相关情况时,其文亦云:“余既注《文心雕龙》毕,因念黄太史(黄庭坚)有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复欲取《史通》注之。”[2]2照录杨慎改造后的所谓黄庭坚之语。清代学者黄叔琳在《史通训诂补·序》中说:“(《史通》)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2]3偶有如毛先舒《诗辨坻》一书,注意到刘知几为“善论文章者”[24]71,也曲高和寡,少有人回应。
五四以来,现代学术体系建立后,《史通》的文学价值,才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刘知几《史通》文学观的相关研究几与所谓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开启同步。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单篇论文如王家吉《刘知几文学的我见》(《晨光》,1924第2卷)、李振东《刘知几的文论》(《燕大月刊》,1928第2卷)、宫廷璋《刘知几〈史通〉之文学概论》(《师大月刊》,1933第2期)等。同时期对刘知几《史通》文学观予以介绍的专著,主要是文学批评史著作。如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盛唐文评”其三“刘知几史评”重点介绍了其文学观。其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第五篇“隋唐五代——文学观念复古期”的“刘知几之《史通》”、罗根泽《隋唐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3)第五章“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之“刘知几的意见”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第十八“刘知几”等都专节介绍了刘知几《史通》的文学观。前辈学者有意识地考究《史通》文论篇章,难能可贵,然多着眼于其“崇真”、“尚简”、反对藻饰与泥古的散文观,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渊源影响较少发明。
建国后,《史通》文学观研究经历了一段较为漫长的沉寂阶段。其中可以一提的有白寿彝《刘知几论文风》(《文汇报》,1961年4月18日)一文与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隋和唐代前期的文学批评”之“刘知几”一节。二者持论较为公允,关注到了刘知几文学观对古文家的影响。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著作从儒法斗争角度分析《史通》对文学作品的论断。如《刘知几著作选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75)、《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刘知几传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等。其所持观点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重提《史通》文学观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史通》论及散文、小说及诗歌等文学体裁的观点。散文观方面的研究,如吴文治《刘知几〈史通〉的史传文学理论》(《江汉论坛》,1982第2期)、李少雍《刘知几与古文运动》(《文学评论》,1990第1期)等文,皆论及《史通》对韩愈等古文家的影响,然研究时限囿于唐代,未能充分展开。小说观方面的研究,有王齐洲《刘知几与胡应麟小说分类思想之比较》(《江汉论坛》,2007第3期)、肖芃《〈史通〉的散文观与小说观述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第4期)、韩云波《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第2期)等论文。王齐洲等人的论文既关注到《史通》中小说观念、小说功能、小说价值方面的相关理论阐述,又对《史通》的散文观有所涉及;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林时民的硕士毕业论文《刘知几及其〈史通〉》第四章“刘知几之文学观”,从“时代之风气”与“史文之形式与目的”两个方面探讨了刘知几的文学见解,但内容不多,资料有限,所论不深。这里存目而不详述。二是观照《史通》文学观在整个文学史上的意义。从叙事学、文体学角度对《史通》文学观展开更为宏观的研究,如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2)、谭帆《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等对《史通》小说叙事观进行专章论述,多有新见,惜篇幅所限,未暇展开。
现有研究成果除关注《史通》自身外,还将《史通》与他书进行比较以探讨其文学观。如汪杰《论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第1期)及香港陈耀南《〈史通〉与〈文心〉之文论比较》(《唐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7)、台湾林淑慧《〈史通〉与〈文史通义〉史传文学批评观探析》(《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第六届研究生学术论文研讨会论文集》,1999)等单篇论文;对《史通》文学思想与文艺理论均有论述,然皆较零散。
此外,《史通》文学观研究还应当关注不同文化区域尤其是西方学界已取得的“跨文化”研究成果。如美国《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收录的Prof. David McMullen的“Liu Chih-Chi”等文及日本西胁常记《唐代の思想と文化》的“刘知几と《史通》”等章节。这些异域资源虽未直接论及《史通》的文学观,然对之进行必要的借鉴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具体的对话,由此则可以探讨、生成新的《史通》文学观研究范式。
四、结语
总的看来,由于论述重点的不同等多种原因,上述研究亦有待开掘之处。现有成果对《史通》文论的研究多是孤立进行的,缺乏一个纵向的关照,没有对《史通》在中国文学史发展链条上的价值及意义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位。又没有作横向的拓展,不能联系到刘知几的其他文学作品对《史通》文学观作全面深入地研究。同时缺少一条内在的贯穿线,将刘知几及其《史通》所论及的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之文学观点、观念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刘知几是一位史家,或者说他的本职工作是撰史,所以他的文学观在其史学观的影响、制约下,较之文学家论文,也许反而更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效果。仔细研读刘氏现存著作后,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知几及其《史通》除了对史学颇多真知灼见外,对文学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文学观的相关研究工作,尚有必要向纵深方向进一步推进。
[1]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浦起龙. 史通通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曾枣庄. 全宋文[M]. 成都:巴蜀书社,1993.
[4]张舜徽. 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序[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程千帆. 史通笺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刘知几. 史通[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7]纪昀. 史通削繁[M]. 扫叶山房刊行,1926.
[8]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9]永瑢.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姚松,朱恒夫. 《史通》全译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3]吕思勉. 史通评[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14]张寅彭. 文衡[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15]焦竑. 焦氏笔乘[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王春南. 《史通》征引古籍及其存佚 [J]. 南京大学学报,1986(增刊社会科学文集).
[17]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吴荣政. 刘知几《史通》评述书目考[J]. 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19]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21]张三夕. 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2]马铁浩. 史通与先唐典籍[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3]郑永晓. 黄庭坚全集编年辑校[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4]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朱艳红)
①具体数字各家统计不仅相同,但基本上都在300部到400部之间。
②该书如作者《自序》所言“考中寓论、论中兼考”。其书个别条目所论尚有待斟酌。如“集部”“楚辞类”“《楚辞》”条,先引王逸《离骚经章句后叙》内容,后引《文心雕龙•辨骚》。误把《文心雕龙•辨骚》复述《离骚经章句后叙》的内容当成了刘勰本人的观点。《〈史通〉引书考》言“《文心雕龙•辨骚》亦曰”。实际上刘勰对王逸的观点是有很大保留的,而非简单的“亦曰”。
③王春南文章中提到“查阅了一百五十余种古今图书”“有卢文弨《史通》精校本”。
K207
A
1673-2030(2017)03-0079-08
2017-07-2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史通》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WC011)
吕海龙(1978—),男,山东鱼台人,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