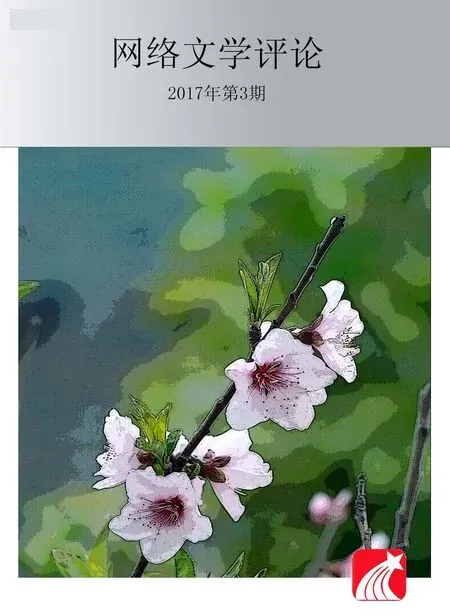新媒体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文/黄鸣奋
通常所说的“媒体”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包括声音、气味、图像、文字等在内的交往手段,它们对应于人类不同的感觉通道,在艺术领域中转化成为不同的表现手段、不同的样态划分;二是指人类通过信息革命所创造的各种传播平台,它们对应于人类不同的信息网络,在艺术领域中转化成为不同的衍生产品、不同的运营空间;三是以加工和传播信息为已任的社会角色,他们对应于人类不同的岗位划分,在艺术领域中转化成为不同的思维定势、不同的创意取向。“新媒体”之“新”既可能体现为从无到有的发明,也可能体现为反常合道的应用,还可能体现为革故鼎新的努力。科幻电影为我们把握新媒体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向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因为它既是一种已经获得公认的艺术样态,又是一种富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同时还代表了一种激浊扬清的创新精神,值得深入研究。
一、科幻电影与作为表现手段的新媒体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人在社会交往中首先将自己的身体及其衍生物(如发音)作为表现手段,然后将应用工具所制造的产品(如饰物、图符等)作为表现手段。与上述过程的演进相适应的新媒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具备不同的含义。就与科幻电影的关系而言,活动影像、多媒体影像和数码影像是我们认识新媒体特征的三个切入点。波兰罗兹大学克吕辛斯基(Ryszard W.Kluszczynski)就此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电影是唯一赋予活动图像性的艺术,如今却必须在非同寻常的条件下寻求其身份。它已经变成只是众多活动影像艺术中的一种,因此必须做出有关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多媒体音像艺术中定位自身的抉择:或者仍然培育传统的原则和形式,仅仅将数码技术当成工具;或者朝交互性电影转变,抛弃当前的惯例,为观众提供迥然有别的体验,即重视数码媒体。①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幻电影的发展和作为表现手段的新媒体的关系。
(一)活动影像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活动影像是诉诸人类视觉器官的有效信号。它是从活动图像中分化出来的,以投映于屏幕之影区别于西洋镜之类器具所直接呈现的画面。对于19世纪末的观众来说,它是货真价实的新媒体。由于活动视镜(1877)、电影摄影机兼放映机(1886)等发明的问世,活动影像逐渐具备了流行的条件。美国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所发明的电影视镜(1893)将活动影像展现于一个小匣子,让人窥视。法国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 Brothers)制成的电影机采用直接放映方式,面向公众,这标志着电影的诞生(1895)。通常将法国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拍摄的短片《月球旅行记》(Le voyage dans la lune,1902)当成科幻电影史的起点。实际上,梅里爱在此之前还拍摄了科幻题材的《小丑与自动化》(Gugusse et l'automaton,1897)、《 伦 琴 射线》(Les rayons Röntgen,1898)等。卢米埃尔兄弟拍过科幻题材的《熟食机械公司》(La Charcuterie mécanique,1895),英国的史密斯(George Albert Smith)也制作了《X射线》(The X-Rays,1897)。也许是由于它们的情节相对简单,因此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科幻电影史上溯到19世纪末。
活动影像不仅是我们认识科幻电影诞生契机的切入点,而且是我们认识科幻电影演变的重要参照系。早期的影片几乎都是二维的。至迟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了美国《宇宙访客》(It Came from Outer Space,1953)那样的黑白三维片。这类电影以高度逼真的画面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在当时显示了高技术的震撼力。后来的各种彩色3D大片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二)多媒体影像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多媒体影像是同时诉诸人类多种感觉通道的活动影像。它诞生的标志之一是1900年在巴黎进行的配音电影公开演示。从1910年开始,电影进入了从无声片向有声片过渡的历史时期。作为新媒体的有声片以多媒体影像(而非单纯视觉性活动影像)作为表现手段。它得益于爱迪生所发明的可以同时摄影、留声的机器(1910),艺术化于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1927)、《纽约之光》(Lights of New York,1928),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逐渐普及,并导致作为旧媒体的无声片寿终正寝(1936)。就科幻电影而言,美国电影《化身博士》(Dr. Jekyll& Mr.Hyde,1931)是早期有声片之一。它由马莫利安(Rouben Mamoulian)执导,派拉蒙电影公司制片并发行,负责音乐的是汉德(Herman Hand)。到1936年之后,有声片已经是科幻电影的基本形态。
为了增强多媒体影像所产生的心理效果,电影工作者进行了不少尝试。例如,骑乘电影让观众坐在液压控制的可移动平台或座位上,体验与巨大的活动影像及环境音响同步的倾斜、旋转、摇晃。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推出的《大地震》(Earthquake,1974)启发了主题公园的相应景点设计,环球影城和好莱坞都有这类诉诸多种感觉通道(除听觉和视觉之外还诉诸触觉、动觉等)的景点。
(三)数码影像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数码影像依托算法在计算机上生成,区别于先前的各种影像。20世纪中叶,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爆发。受其影响,电影(包括科幻电影)逐渐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数码电影术(digital cinematography)开始作为新媒体的独立范畴起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是电影从模拟技术向数码技术转型的历史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几乎都和科幻电影相关:美国《西部世界》(Westworld,1973)率先运用了数码图像处理技术,标志着电影从特技入手推进数字化。1979年,英、美合拍片《异形》(Alien)率先利用电脑技术描绘了外星怪物对人类的袭击。这是第一部采用三维计算机图像的长片。《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1982)率先描绘赛伯空间的奇景;《星球迷航》第二集《可汗之怒》(Star Trek II: The Wrath of Khan,1982)率先用颗粒着色算法描绘生命在一个星球上的诞生……科幻电影编导敞开胸怀欢迎数码影像,因为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它的卓越表现力。1999年6月18日,美国《星球大战I:幽灵的威胁》(Star Wars,Episode I:The Phantom Menace)开始进行全球数字电影的首次商业放映(为期一个月),这标志着世界数字电影发展史元年的到来。如今,数字电影主要不是指仅仅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制作特效的电影,而是指全面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拍摄、后期加工和发行放映等环节的电影。
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不但促进了电影的数字化转型,而且更新了人们对于先前就已经存在的活动影像、多媒体影像的认识。如今我们所理解的活动影像不仅来源于用照相器材所进行的拍摄,而且来源于计算机通过各种算法所进行的生成,所谓“引擎电影”(Machinima)就是这样诞生的。如今我们所理解的多媒体影像也不仅是指既有图像、又有声音,而且是指可以在不同平台上自由流动、诉诸用户不同感觉通道(不限于视觉)、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人机交互、充分满足人类驰骋想象之需要的媒体,所谓“虚拟现实电影”(VR Movie)就是这样构想的。因此,从表现手段对科幻电影所进行的考察既必须关注各种科幻游戏所包含的过场动画(属于引擎电影),又必须关注各种数码娱乐所呈现的动态奇观(涉及虚拟现实电影)。这些科幻游戏或数码娱乐有些和科幻电影本来就出自一源(如大名鼎鼎的《星球大战》系列、《蜘蛛侠》系列等),有些已经实现了向科幻电影的转化(如《星际争霸》等)。
二、科幻电影与作为传播平台的新媒体
人类历史上先后爆发了以口语、文字、印刷术、电磁波和计算机为标志的五次信息革命。每次信息革命的成果都通过打造新的传播平台等形态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有相辅相成的“口碑”、“文苑”、书刊报纸发行网、广播电视网和移动互联网络。从历史上看,科幻电影作为信息固然可以通过所有这五种平台获得传播,作为本体(即活动影像)却只有依托后两种平台才能充分展示其风采,至少在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交互式印刷流行开来之前是如此。不过,由于上述五种平台如今都在数字化大潮中朝新媒体转变,因此,科幻电影与它们的联系正多侧面、多方位地显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肯考迪娅大学沃森(Haidee Wasson)指出:电影不论作为活动影像或者作为物品,早就是时空专门化的物质网络的一部分。这种网络包括诸如胶卷罐、邮件之类运送方法,也包括轮船、火车、飞机以至于电视频道等传送节点。这些方法和节点都是电影史的一部分。如今网络化电影发展出两种迥然有别的形式:一种是小巧的“迅时”,另一种是巨大的IMAX系统。不过,它们都宜于好莱坞电影,都有其对应网络的标志。②
(一)电力网络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早期电影以影院为主要传播平台。原先的剧院只要能放电影,就成为影院(Movie Theatre)。专门为放映电影而建造的场所(Cinema)固然有之,但非专门性的场所也不是不能放电影。唯一的必要条件是那儿得有电力供应。没有电力,就没有电光源,也就没有电影。这是不言而喻的。电力网络铺设到哪里,那儿的演艺场所就可能告别烛光照明或油灯照明,就可能使用电影放映机,原先的剧院就可能朝影院转化。输电线路将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街道、不同场所的影院联接在一起,使之成为电影的传播平台。当然,在电影实现数字化之前,影院之间的跑片还需要电力网络之外的交通设施的支持。但是,任何电影拷贝都只有在电光源的照耀之下才能显示出活动影像。就此而言,电力网络的决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虽然电力网络至今为止仍然主要是能源网络、让它同时兼有信息网络功能的努力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它对于科幻电影和新媒体联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中介,电力网络促使科幻作品将传播平台由书刊报纸发行网转移到广播电视网,有力地促进了观众由读书向“读屏”的转变。早先主要通过印刷品传播的科幻小说因此得以大量朝科幻电影转化。这种现象早在1898年就已露端倪。当时法国出品的《太空人的梦》(La lune à un mètre)就基于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1865)与《环绕月球》(Autour de la Lune,1870)。20世纪以来,这类改编在科幻电影领域比比皆是。例如,英国作家雪莱夫人(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受到科幻电影编导的钟爱,先后十余次被搬上银幕。值得重视的另一个历史现象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起,一些带有科幻色彩的连环漫画被改编成系列电影。美国13集系列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1936)就是一部标志性的作品。图画和影像之间的相互转换,至今仍通过美国漫威漫画公司(Marvel Comics)所塑造的超级英雄等产品显示出巨大魅力。
(二)电视网络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广播电视网络是第四次信息革命所打造的传播平台。电影就其本性而言是活动影像,因此和电视网络的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也有某些影片取材于广播剧,如英国科幻片《航天之路》(Spaceways,1953)等。
电视网络是以电信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和以电光源技术为基础的电影本来运行于不同轨道,但它们也存在交会之处,所谓“电视电影”(TV movie)可以为例。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雷电华影业公司(RKO Pictures Inc.)就制作了这类专供电视放映的影片,在纽约市电视台WABD播出。科幻电影将电视网络当成新的传播平台的现象,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导演亚历克斯(Alex Segal)推出了《谋杀与机器人》(Murder and the Android,1959)。此后,科幻电视片的数量日益增多,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日本石井辉男(Teruo Ishii)执导的《空间入侵者》(Invaders from Space,1964)、美国布坎南(Larry Buchanan)执导的《金星怪人》(Zontar,the Thing from Venus,1966)、美国萨拉菲安(Richard C. Sarafian)执导的《地上之影》(Shadow on the Land,1968)等。
电视电影在视听效果方面比不上剧场版,但在传播上却具有便于融入家庭生活等优势,和电视电影具有亲缘关系的科幻电视剧在容量上更是无与伦比。例如,英国BBC出品的科幻电视剧《神秘博士》(Doctor Who)1963年11月23日首播,至今已经播出800多集。就供给端而言,某些科幻作品在影视界发展成为阵容强大的系列,如美国《星际迷航》(Star Trek,1966-)目前已有6部电视剧、1部动画片、13部电影,堪称“人丁兴旺”。它不仅在社会上催生了诸多科幻迷,而且引发了学术界的重视。以之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已有多种,如杰洛德(David Gerrold)与萨耶斯(Robert J. Sawyer)合著的《登上企业号:吉恩·罗登贝瑞〈星际迷航〉中的传输、毛球族与瓦肯人的死亡支配》(2016)③等。
(三)移动互联网络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基于数字技术的移动互联网络是第五次信息革命所打造的传播平台,也是网络电影生长的温床。1993年,美国导演布莱尔(David Blair)推出当时最大的超媒体叙事数据库——《蜡网》(Wax)。它基于布莱尔本人1991年拍的长度为85分钟的科幻片《蜡:蜂群中电视的发现》(Wax or the Discovery of Television Among the Bees),被认为是第一部在线长片。换言之,网络电影是以科幻片为先锋而载入史册的。
若将网络电影理解为在互联网上首发而专门拍摄的电影的话,那么,Sightsound.com公司所策划的短片《量子计划》(The Quantum Project,2000)可以为例。它由阿根廷的扎尼提(Eugenio Zanetti)执导,讲述物理学家、奇才保罗对量子宇宙的探索与其生活、尊严与爱情冲突的故事。近年来,网络大电影在我国风头正健。由于科幻片通常包含大量特效、制作成本较高,因此在以低预算为特点的网络大电影中并非主流,不过,也出现了《墓志铭》(EPI,2016)、《妙龄爷爷》(2016)这样的作品。前者讲述某手术系统形成自我意识篡改重生者大脑、屠杀人类的故事;后者则描述被外星人抓走的爷爷托体妙龄女椰椰向孙子示警,两青年在抵抗外星人入侵过程中渐生情愫。与之相关的新品种是网络剧。在我国,2016年被业界称为“中国科幻网络剧元年”。此前,土豆网《乌托邦办公室》(2011)、北京幻思《金刚葫芦侠》(2014)、上海聚力等《执念师》(2015)、杭州新媒世传《大面曹天》(2015)等作品络绎问世,而且反响都不小,已经为我国科幻网络剧的兴盛做了铺垫。PPTV聚力等《执念师2》、银润传媒《迷航昆仑墟》、合心天誉(东阳)等《天才联盟》、杭州已立《命运规则》、腾讯视频《微能力者》与《守护者》等科幻网络剧同在2016年播出,彼此响应,使这一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是“元年”之说的根据。不仅如此,我国科幻网络剧还显示出强大的后劲。因此,在产业的意义上,“元年”并非止步之年,而是振兴之年。
尽管移动通信网络早已深入千家万户、移动视频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但是,手机电影的定义、起源及其和科幻的关系仍是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英国“未来一切”(FutureEverything,1995-)艺术节将“移动与位置媒体”(Mobile & Locative Media)当成议题(2003-2006),美国“洛杉矶自由波”(The LA Freewaves,1989-)、“新媒 体电影节”(New Media Film Festival,2010-)等节展都对移动媒体予以关注。2004年12月1日,美国Zoie电影公司举办首届全球性手机电影节(Zoie Cellular Cinema Festival)。2006年10月15日,我国西安举行了首届手机电影大赛,由崔雪峰导演的科幻片《第三界》获得创意大奖。本片所表达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必须和谐相处的理念。虽然手机电影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了,若将它理解为完全以手机为工具进行拍摄、加工、传播与欣赏的电影,那么,它在科幻领域迄今为止仍然乏善可陈(像《第三界》那样的作品相当罕见);若将它理解为由专业工作者对电影进行适应移动通信特性的再制作,或者是由手机用户通过网络付费方式进行观赏,那么,它对科幻电影的流通倒是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不少手机电影网站都设有科幻频道,像国内的80s电影网、在线6手机电影、8亿手机电影、A6780手机电影等都是如此。吉布森(Ross Gibson)认为电影是使时间碎片化、细薄化的艺术形式之一,未来电影将朝这方面继续发展(2003)。④
手机电影看来是顺应了这一潮流。
从总体上说,电影在上述电力网络、电视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络支持下的发展呈现出去地域化趋势,所追求的是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中的自由流动。不过,由于增强现实、卫星定位等技术的渗透,加上逆全球化潮流的激荡,电影发展又呈现出再地域化趋势,表现为对城市空间的深入融合。例如,法国艺术家拉米斯(Catherine Ramus)与德利特雷兹(Caroline Delieutraz)《M 理论》(Théorie M,2006)借鉴了当前仍在发展的以承认物理世界之多维、探索宇宙之多重为特色的M理论,将互联网、移动电话、电影、绘图法和城市空间结合起来。它给巴黎城贴上了二维代码(一种由黑白方块组成的矩阵条形码),每个代码都与一段可在手机上观看的电影相联系。在相应的网站(www.theoriem.net)上,个性化的Google地图为上述标签做了定位。这一作品因此将现实宇宙和虚拟空间重叠起来。像这样的作品亦真亦幻,表现了地域化与去地域化、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
三、科幻电影与作为构思内容的新媒体
科幻电影不仅将新媒体当成表现手段和传播平台,而且将新媒体当成构思对象,对它的历史、现状及其与人的关系予以审视,对它的前景加以展望。在这一意义上,新媒体是科幻电影的内容,来自科幻电影编导的想象。尽管具体的科幻影片在内容上都有所侧重,但是,由两千多部(这是笔者所统计的数字)科幻电影所组成的艺术长廊却作为集合体为观众展示了迥异于现实环境的大千世界。在科幻世界中,就物的意义而言,新媒体可能是多样化智能生物用以交往的手段,由新颖科技所支持的信息工具和产品,或者多重宇宙之间彼此往来的途径;就人的意义而言,新媒体是具有新定位、新能力和新使命的社会角色,或者说是活跃于跨物种交往、跨物态交往和跨时域交往领域的新人物。下文所关注的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新媒体。
(一)跨物种交往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科幻世界以多种智能生物并存为特征。媒体必须不断推陈出新,才能适应原版人与克隆人、纯种人与变种人、电子人与机器人、实体人与虚拟人、地球人与外星人等彼此沟通的需要。很难预测这些智能生物之间的交互需要多少种类型的媒体来支持,也很难预测这些媒体将通过什么样的通道发挥作用,因为不同种类的智能生物完全可能拥有不同的感受器、处理器与效应器,殊别迥异的生存环境完全可能有大相径庭的要求。这既是未来实践的难题,也是现在构思的机遇。就此而言,科幻电影大有可为。
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媒体”是媒人之体,是作为中介的人的身体。当人们将弘扬主体性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时,媒体似乎成为工具性、手段性、附属性的东西,新媒体似乎只是人类的新工具、新手段、新附属。然而,在跨物种交往的视野中,人本身(首先是人的身体)是具有本体性、目的性、主导性的媒体,因为是人引领同时并存的多种智能生物的发展,主动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担负着不同生物之间相互沟通的使命。就此而言,美国动画片《最终幻想:灵魂深处》(Final Fantasy:The Spirits Within,2001)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万物皆有灵魂,星球也不例外。支配各自星球的灵魂的地球盖亚(原始神或星球灵魂)和外星盖亚必须和平相处,宇宙才能安宁。为了实现不同盖亚之间的沟通,格雷上尉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充当传导灵魂波的媒体。他虽然因此而死亡,但也因此魂归盖亚而永生。能够沟通不同星球灵魂的媒体是现阶段任何媒体都无法比肩的,在发挥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功能方面无疑是新媒体。充任这种新媒体的是人,当然不是凡夫俗子,而是具有高度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的人。
(二)跨物态交往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现阶段人们对于新媒体的认识主要是依托电子计算机这一参考系建立的。这体现了20世纪中叶爆发的第五次信息革命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新的信息革命正在酝酿之中,量子计算机可能就是它的旗帜。我们无从知道未来量子计算机的细节,但尽可以依托量子计算机的原理展开想象。如果量子比特序列不但可以处于各种正交态的叠加态上,而且还可以处于纠缠态上,那么,以之为依托的量子通信、量子媒体势必具备有别于当下电子媒体的特征。早在1987年,一群旨在追求跨学科的西方艺术家就在《多变媒体宣言》(1987)中宣告:“量子机制已经证明最小的基本粒子(如电子)存在于不断变化的形式中。它们没有稳定的形式,却以动态可变性为特征。电子的这种不稳定的、灵活的形式是多变媒体的基础。”⑤
就科幻电影有关新媒体的创意而言,量子学说所给予的启示之一是多样化物态及其相关性。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因为处身不同维度的空间而具备不同的存在状态,那么,如何进行自我交流,又如何与人交流?这是英美合拍片《星际穿越》(Interstellar,2014)所触及的问题之一。在影片中,想用重力波向书房中的父女传递编码信息的未知智能生物居然是穿越虫洞到了五维空间的父亲,他想帮助女儿破解人类撤离地球的关键问题,与之交流量子数据。不同维度空间的交流无疑是难题,本片只想到应用莫尔斯电码,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其实,这无疑蕴含着媒体创新的契机。同年出品的美国影片《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想到利用量子计算机实现幽明世界之间的通信,让生者与死者(其意识上载于虚拟空间)对话。这种新型计算机是否有助于实现不同维度空间的交流呢?或者说,如果有了量子计算机,人们是否可能发现自己果真(同时)存在于不同维度空间?生生死死也许不过是不同维度空间的来来去去。特定维度空间的我们也许只是生命在众多平行宇宙之间一种存在形态。多重自我为什么非得像美国动作惊悚片《宇宙追缉令》(The One,2001)那样拼得你死我活呢?也许,乐于充当媒体、善于沟通,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如果我们发现他人除通常身体状态之外还有其他存在状态,那么,如何恰当地与之互动?这是美国《幽灵》(Spectral,2016)触及的问题。它讲述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一位科学家接受一项致命任务,带领一群精挑细选出来的的三角洲部队士兵进驻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城市。这里游荡着被称为“幽冥”的神秘生物,它们由亦生亦死的人转变而来,无形无色,出没不定,能在不经意间造成大规模的伤亡,其特点是几乎全部原子都聚集到能量最低的量子态,形成宏观的量子状态。这就是物质第五态——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生产、组织和控制这类幽灵的方法是东南欧小国家摩尔多瓦的官方科学家发现的。他们曾经可以给它们下达命令,指挥它们远程行动,可惜最后失控了。尽管在本片中这些人是没有多少戏分的否定性角色,但他们的科研成果已经通过四处出没的幽灵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幽灵连同其基地最终都被美国特种部队所消灭,但有关物态的想象无疑仍将通过类似影片的构思和欣赏得以延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状态之外,生命的存在状态究竟还有哪些?与我们交往的其他人究竟是其生命或自我的唯一本体,或者只是引导我们去认识其本体的某种多变媒体?多变而无常,是否必定代表宇宙中的恶?我们能够欣赏其他人在多种存在状态中所呈现的美吗?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乌托邦电影和恶托邦电影可能给出不同创意。
对习惯于单一状态生存的人来说,同时性多态存在无疑很怪异,不论亦生亦死、亦此亦彼,还是亦人亦己、亦趋亦返,都是如此。在加拿大《异次元杀阵2:超级立方体》(Cube 2:Hypercube,2002)、美国《创世纪》(Terminator Genisys,2015)等影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类创意的痕迹。神奇的量子设备被用于直接从佩戴者的大脑皮质中记录事件,如美国《末世纪暴潮》(Strange Days,1995)中的超导量子干涉仪;又被当成非人类的自我意识的物质承担者,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拍的《绝密飞行》(Stealth,2005)中加载有人工智能“艾迪”的球形量子计算机;也被用为前往未知奇异世界的端口,如美国《神奇四侠》(Fantastic Four,2015)所描绘的量子门。澳大利亚《无极》(Infini,2015)则告诉观众:人可以量子化传送到别的地方再还原,由他们脖子上的装置完成。也许,量子通信技术所取得的突破真的能够掀起新一波信息革命,造就不同于当今数码媒体的量子媒体。这场新的信息革命的弄潮儿,将是标领风骚的新媒体(人)。
(三)跨物域交往与科幻电影的发展
我们所说的“跨物域交往”特指源于古代灵媒某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活动。这些灵媒据说能够和鬼神交流,沟通阴阳两界。不论在古代传说或当代奇幻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类人也出现在科幻电影中,但往往经过科技之光的折射。例如,美国《魔域煞星》(Dreamscape,1984)描写政府机构招募灵媒,利用共享梦境技术将观念植入美国总统心灵。本片中,灵媒行事的奥秘变成了科研课题。又如,美国《超能敢死队》(Ghostbuster,1984)设想纽约三个前超心理学教授开商店提供驱鬼服务,将科学家变成了灵媒。
灵媒既能回到过去,与先人对话;又能前往未来,与后人对话;还能周行异域,与鬼神对话。尽管如此,装神弄鬼毕竟不符合科幻的本性。因此,源于古代灵媒的跨物域交往在科幻电影中接受了相对彻底的改造,以时间旅行的形态表现出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习惯的是以时间不可逆为前提创立的各种模式。在空间维度上,它们可以允许信息多向扩散;在时间维度上,它们却只允许信息单向传播,亦即由过去流向现在,由现在流向未来。在科幻世界中,信息在媒体中流动的向度要复杂得多。如果信息由未来流向现在,这就成了前景预测;如果信息由现在流向过去,那就成了后顾启示;如果信息在不同时间线之间流动,那就成了横向交错。如果进行复杂方向流动的不仅是信息,而且是携带上述信息的人,那么,这就构成了时间旅行(常言之“穿越”);如果实现上述流动的是某种专门化的工具,那就构成了时间机器。在某种意义上,时间旅行者就是科幻电影所特有的媒体(人)。他们像传统灵媒那样可以穿越于不同时空之中,发挥沟通不同时间段、时间线(因而也可能沟通不同空间域)的作用,又没有传统灵媒那种神秘气息。
与魔幻、玄幻相比,科幻的特点是试图根据科学原理来解释科技起作用的机制,或者根据人伦规范来反思科技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在所有的媒体科技中,难度最大的恐怕要数试图让时间定位可以任意变化的媒体工程。这当然不是说拨弄一下钟表指针或重设电子定时器读数那样在名义上改变时间定位,而是指实际改变当事人所处的时间坐标,甚至改变整个周边环境的时间参数。正因为如此,相关想象获得了科幻电影编导的格外喜爱。例如,有关时间机器的描写至迟在20世纪40年代的科幻电影中就已经出现,美国系列片《布里克·布拉德福德》(Brick Bradford,1947)可以为证。迄今为止,多少和时间机器相关的科幻电影估计多达数百部,直接以之为名的至少就有匈裔美籍波尔(George Pal)执导的美国长片(1960)、英国威尔斯(Simon Wells)执导的美国长片(2002),还有美国(Alexander Singer)执导的电视片(1978)、印度阿莱提(Arati Kadav)执导的短片(2016)等。
跨物种交往、跨物态交往和跨物域交往构成了科幻世界多种智能生物互动的基本场景,也构成了新媒体发展的科幻背景。在这一背景中,新媒体固然可能是某种表现手段或传播平台,但最主要的还是人,或者说是致力于沟通不同物种、不同物态、不同物域的社会角色。他们之所以成其为“新媒体”,既是因为所具备的新能力,也是因为所承担的新使命。
上文分别从表现手段、传播平台和创意内容三个层面考察了新媒体与科幻电影发展的关系。大致而言,作为表现手段的新媒体丰富了科幻电影的形式,作为传播平台的新媒体开拓了科幻电影的渠道,作为创意内容的新媒体激发了科幻电影的想象。反过来,科幻电影也以自己层出不穷的作品推动表现手段、传播平台和创意内容的推陈出新。人机互动的梦幻界面、作为虚拟世界的赛伯空间、多元宇宙中的时间旅行等议题之所以脍炙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科幻电影的推波助澜。不仅如此,科幻电影对新媒体应用所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颇为警觉,从不同角度加以批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著《科幻影视对新媒体的展望与批判》(《福建论坛》2017年第4期)。
注释:
①Kluszczynski,Ryszard W. From Film to Interactive Art: Transformations in Media Arts.In MediaArtHistories.Edited by Grau,Oliver.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2007,pp.207-214.
②Wasson,Haidee.The Networked Screen:Moving Images, Materiality, and the Aesthetics of Size.In Fluid Screens, Expanded Cinema.Edited by Janine Marchessault and Susan Lord. Toronto;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pp.74-95.
③Gerrold, David, Robert J. Sawyer.Boarding the Enterprise: Transporters, Tribbles, And the Vulcan Death Grip in Gene Roddenberry's Star Trek.New York, NY, US: BenBella Books, Inc.,2016,
④Gibson,Ross.The Time Will Come When....In Future Cinema: The Cinematic Imaginary after Film.Edited by Jeffrey Shaw and Peter Weibel.Cambridge, MA: London: MIT, 2003,pp.570-571.
⑤V2_Organisation.Manifesto for the Unstable Media. 1987. http://framework.v2.nl/archive/archive/node/text/.xslt/nodenr-124560.[200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