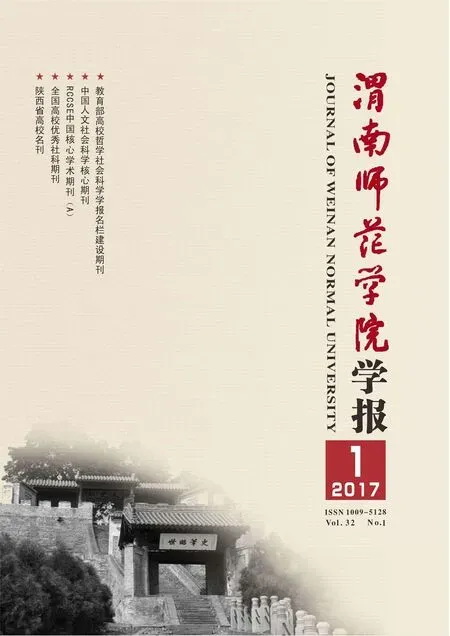《史记》评点与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
党 艺 峰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史记》文献与传播研究】
《史记》评点与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
党 艺 峰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史记》评点全面介入到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并对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明清时代的《史记》评点确立了《史记》的文章原典地位,使《史记》不仅成为古今文章渊薮,而且成为文章法度的准绳和标尺。方苞等人对《史记》义例的阐释使之转换为文章通则,但也隐含着文章世俗化的可能。章学诚以六经皆史的命题抵抗文章天下的观念,抵抗与之相伴随的越来越沉溺于文牍主义陷阱的政治实践,对文道关系这一明清文章学观念作出全新的阐释。
《史记》评点;文章学;方苞;章学诚
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文章学最为发达的时期,其标志之一就是自觉的文章学观念建构。迄今为止,对明清文章学观念的理解还局限在文学批评史的范围之中,尤其集中在对古文创作理论的技术主义阐释。如果在更宏阔的文化视域中观察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说它具有超出文学批评史的意义。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的历史过程与科举制度转型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规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叙事在重建生活世界的合理边界时拥有特殊的奠基性意义,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正如顾炎武所说:“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1]1106即使顾炎武对此种现象并不满意,但我们必须承认文章的叙事功能在一个较大的时段持续得到强化,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文化潜流。这种历史文化潜流体现于文章学观念,则是从古文义例的具体探寻开始,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体系化理论建构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评点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蔚为大观的《史记》评点确立了《史记》作为文章原典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把《史记》义例逐步转化为文章通则。因此,以《史记》评点为核心,我们可以有效把握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的历史轨迹,可以更有深度地把握明清文章学观念的丰富内涵,反过来说,也有利于我们更确切地认识《史记》的崇高历史地位及其巨大文化影响的根源。
一、明清《史记》评点及其作为 文章原典地位的确立
北宋时期,作为文章领袖的欧阳修、苏轼显示出贬抑《史记》的倾向,但是,随着科场程文样式越来越成熟,举子应试往往需要借助某些考试用书,他们“备考时依据考试范围,对相关内容加以整理,以便应试时直接套用,这些论学套类虽属取巧性质的终南捷径,却也反映了当时举子的基本素养。论体选本的大量出现则为举子们提供了研阅效法的样本。古今奥论取材宽泛,时贤典范中论体格式基本成型,而举场程文则是论体的成熟样态”[2]21。在这种背景下,洪迈的《史记法语》和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应运而生,《史记》的文章学地位也得到空前提升,正如唐庚所说:“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3]443不过,唐庚于文章而专美《史记》给后人提出了一系列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唐庚那里,六经以后文章只有《史记》和杜诗。这种并置与宋人的“诗史”概念有关。南宋以后,许多人注意到《史记》与杜诗在写法上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同时也强调它们在阅读美感上的一致性。[4]62-66然而,元明之际,越来越明确的文章辨体意识使得并置《史记》与杜诗背后隐含的问题开始浮出。明初,以唐庚之论为前提,宋濂指出:“世之论文者有二: 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 虽然,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论,而予之所见,则有异于是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榛荆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去此则曲狭僻径耳,荦埆邪蹊耳,胡可行哉?”[5]2004宋濂分文章为“载道”和“纪事”二体,并因之直接勾勒“载道”之文的谱系,由六经而孟子、韩欧。这来自于他的自我认知,宋濂从不以文人自居,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道学家身份。作为道学家的宋濂,徘徊于朱陆之间,试图逃离烦琐的穷理格物,转向内在的本心冥悟,但又不能彻底离经叛道,或者说六经始终横亘在物理与本心之间。因此,他虽然极力张扬文道一体的理念,并以此为前提,一再强调六经皆心学,皆源于个体之本心,只要能够养气守心,则所言即经,在这个过程中,言文就成为一种媒介,成为个体觉悟本心的介质,但是,在可操作的层面上,文道一体面临着许多问题,其核心是如何理解六经的文章学意义。也许宋濂期望自己的双重身份能够合一,他在阐释文道一体的理念之外花费更大的精力探寻所谓文法,如其所说:“濓尝受学于立夫,问其作文之法,则谓:‘有篇联,欲其脉络贯通;有段联,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联,欲其长短合节;有字联,欲其宾主对待。’又问其作赋之法,则谓:‘有音法,欲其倡和阖辟; 有韵法,欲其清浊谐协; 有辞法,欲其呼吸相应; 有章法,欲其布置谨严。总而言之,皆不越生、承、还三者而已。然而字有不齐,体亦不一,须必随其类而附之,不使玉瓒与瓦缶并陈,斯为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择不能到也。’顾言犹在耳,而恨学之未能。”[5]1946不过,宋濂并没有最终达成自己的期望,他对文法的探寻始终局限在六经的文章学意义这个问题之外,因而也就不能圆满阐释文道一体的理念。
宋濂之后,杨慎转换了提问的方向,他引述元儒张行言:“史之为体,不有以本乎经,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为体,不有以本乎经,不足以为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书,其体本乎《尚书》;司马公之《通鉴》,其体本乎《左氏》;朱子之《纲目》,其体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体本乎《周礼》;惟《易》《诗》之体,未有得之者;而韩婴之《韩诗外传》、邵雍之《皇极演易》可谓杰出矣。此论甚新,余尝欲以汉唐以下事之奇奥罕传者汇之,而以苏、李、曹、刘、李、杜、韩、孟诗证之,名曰‘诗史演说’。衰老无暇,当有同吾志者。”[6]368杨慎在经史之间提出两个判断,一是史之为体本乎经,二是以诗证史,其中隐含的正是从史之为体的角度理解经的文章学意义。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杨慎以《史记题评》发端,开拓出明清《史记》评点的新局面。
根据杨昊鸥的统计,明代《史记》评点的各种单行本有29种,即“1.杨慎、李元阳《史记题评》;2.沈科编选、黄养吾校《史记抄》;3.唐顺之《史记选要》;4.王鏊《王守溪史记评抄》;5.何孟春《何燕泉史记评抄》;6.茅瓉《茅见沧史记评抄》;7.凌约言《凌藻泉史记评抄》;8.王慎中《王遵岩史记评抄》;9.王维桢《王槐野史记评抄》;10.陈沂《陈石亭史记评抄》;11.王韦《王钦佩史记评抄》;12.董份《董浔阳史记评抄》;13.张之象《太史史例》;14.柯维骐《史记考要》;15.茅坤《茅鹿门史记评抄》;16.凌稚隆《史记评林》;17.凌稚隆《史记纂》;18.钟惺《史记辑评》;19.陈仁锡《史记评林》;20.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议》;21.葛鼎、金蟠《史记汇评》; 22.朱东观《史记集评》;23.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24.孙鑛《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 25.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 26.邓以讃《史记辑评》; 27.陈继儒评、黄嘉惠辑《陈太史评阅史记》;28.焦竑、李廷机注释、李光缙汇评《史记综芬评林》;29.郑维岳《新锲郑孩如先生精选史记旁训句解》”[7]155。留存于今的有20种。其实,这个统计并不完整,其他还有于慎行《读史漫录》、汤宾尹《史记狐白》、梅之焕《史记神驹》、黄淳耀《史记评论》、张溥《史记珍抄》、刘宗周《史汉合钞》、戴羲《史记文抄》、史大纲《史记纲鉴评注》、朱东观《史记集评善本》等。从整体上看,明代《史记》评点也有如柯维骐《史记考要》那样侧重于考据的作品,但尤其重视的是文章学意义的挖掘。
明人对《史记》文章学意义的挖掘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从归纳整理《史记》义例着手,这种整理表面上看是琐碎的,非系统化的,但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达成“古典文学精神客观化”,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古典作品的审美意蕴和艺术魅力的可阐释和可理解化。历代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都试图对经典作品的艺术内蕴作出阐释。明代的古典主义者们试图越过前代的阐释模式,重新寻找理解和阐释经典作品的方法”[8]156。它影响于清代,这种努力就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概念系统来表述。与明人的《史记》评点相比,清人如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汤谐的《史记半解》、方苞的《史记评语》《读史记》,孙琮的《山晓阁史记选》,张履祥的《读史记》、储欣的《史记选》、李晚芳的《读史管见》、牛运震的《史记评注》、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邵晋涵的《史记辑评》、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和王拯《归方评点史记合笔》等都体现出这种特点。另一方面,对《史记》义例的领悟必然落实在作文上,则是“因事立言”,最终以“尊史体”终结,如归有光说:“余少好观古事,尝有意于考论其世,而废置草野,无史官之任。然时有慕于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着其是是非非之迹,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几他日有裨于史官。”[9]357在“因事立言”的背后,则隐含着另一种变化。以归有光、茅坤和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古文论述是明代文学观念转变的关键,他们在观念上都游移于理学和心学之间,只有唐顺之最终完成从文人到心学家的角色转换,以心学为中介,把宋濂的文道一体转换为经史一体。其后,方苞虽然回归到朱子理学立场,但从孜孜不倦于古文义法的阐释而最终以发扬儒家礼学遗绪自命,坚持把对礼学遗绪的阐发与日常生活的践履结合在一起,体现出还原儒家礼学发生现场的意欲,这依旧是经史一体。而经史一体则是“尊史体”最典型的表现,它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代的《史记》评点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力确立了《史记》的文章原典地位,因此,《史记》不仅是古今文章渊薮,如梁章钜所说,《史记》为“文章不祧之祖”[10]5156,而且成为文章法度的准绳和标尺。
二、《史记》义例与文章通则
在明清时代所形成的《史记》评点文本群中,其核心是对《史记》义例的挖掘。明清《史记》评点无疑受到时文取士的影响,往往以时文手眼提醒《史记》的字法、句法、章法和文法。张亚玲在研究牛运震《史记评注》时指出:“牛氏于《史记》文法笔力的探讨用力最勤,对精彩字法、句法的分析,对呼应、收截、提掇、隐括、点染、附带、叠复之法的揭示,对篇章艺术特色的把握,依由小到大、由点及面的顺序,构成牛氏文学批评的表层。”[11]98这种状况不仅是牛运镇《史记评注》的特点,明清《史记》评点大体上都以近似的面目表现,但是,无论是否介入到《史记》评点之中,明清学人对于这种浅层的技术主义批评始终抱有警惕,如杨慎谈及自己时代举子陋习时就指出:“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6]447-448章学诚也对归有光的《史记》评点有严厉的批评,他说,归氏《史记》录本“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12]342-344。因此,明清《史记》评点对其义例的挖掘并不止于浅层的技术主义批评,它还有另外一面。要理解明清《史记》评点的另外一面,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在于到底什么是《史记》义例。作为历史叙述的《史记》,其义例归根到底是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叙事对象,也就是在缤纷的历史事实中,司马迁为什么选择某些事实叙述,同时又把另外一些事实排斥在叙述之外?二是叙事方式,也就是在众多可能的叙事形态中,司马迁为什么用这种形态完成叙述,同时又拒绝其他那些叙事形态?这两个问题都是历史哲学层面的,如果问题本身的确属于明清《史记》评点并被其回答,我们就必须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从总体上把握明清《史记》评点。
钱钟书曾经发现明前期在文化上呈现出某种分裂,他说:“有明弘、正之世,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理学则有阳明之师心直觉。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倍。”[13]303在这种分裂中隐含着某种历史趋势,王阳明曾经与李、何为首的前七子相与唱和,但最终从中出离。与此相类似,前七子同时代的杨慎也坚定地站在复古的诗学立场上,但无论在师古的方向还是在作文为人又都仿佛与阳明之师心直觉遥相呼应。这种分裂依旧是在文道关系的逻辑框架中产生的,文道的分裂或者文不足以载道决定了明代持有复古立场的文人的选择。王阳明在谈到自己出离于前七子的原因时说:“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就论立言,亦须一一从圆明窍中流出,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傍人门户,比量揣似,皆小技也。”[14]268不仅王阳明如此,前后七子也有类似的取向。前后七子不满于台阁文人而张扬复古,其旨趣在于用古文以救时文之弊,但从前后七子的接续及其内部诸人的观念反复来看,这种努力并不成功。正是因此,前后七子以文人的身份转而回归理学。前后七子的回归理学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他们都出身于科场,长期为郎吏,有强烈的用世事功愿望,但更重要的则是内在的思想原因。他们的回归理学并不是就皈依于程朱,而是隐含着对道的本源追寻。在前后七子中,王世贞独自主盟明中叶文坛20年,他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有所反省和批判,试图回归原始儒学,最终“提出了理、事、辞三位一体的新道论”,并“建立一套以理、事、辞为核心的文学思想体系”[15]64。在现实的功利驱动之外,明清《史记》评点始终是复古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物,而理、事、辞三位一体的新道论应该正是其赖以展开的基础理念。
明清《史记》评点在提醒《史记》的字法、句法、章法和文法之外,尤其注意到《史记》的叙事。凌稚隆的《史记评林》选录的评点家多达150人,周建渝通过对《史记评林》的观察发现,明人的《史记》评点呈现出从“文章之学”到“叙事之学”的过渡形态,同时也注意到《史记》叙事的“正体”和“变体”之别,其“变体”就是“以议论叙事”[16]。如果不囿于现代结构主义崛起后形成形式主义叙事学视角,明清《史记》评点建立的“叙事之学”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茅坤在《史记抄》中提炼出的“神”论。它是对叙事本身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阐释,如邓国光所说:“古文讲‘神’,集中于‘叙事’的层面,表明‘事相’或‘材料’一任作者的个人意志力所驱使。如果这个‘事相’和‘材料’比喻为‘世界’,则是‘界’为我所役动,我是‘世界’的真宰。于是,成功的‘叙事’,表现的是作者的‘神’,一种最精彩的个体生命特征,《史记》是成功的典范。”[17]49这样的叙事世界是生成性的,虽然它根源于叙事者个人意志,但更突出的则是对世界的同情性理解。其次是牛运震《史记评注》中提炼出的“繁复”,他说:“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盖他史只是书事,而《史记》兼能写情。情与事并,故极往复缠绵,长言不厌之致。不知者以为冗繁,则非也。一部《史记》,佳处正在此,故特于舜纪指其端。”[18]7牛运震的“繁复”不是叙事细节繁简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强调写情,强调需要一种往复缠绵的形式写情,因此,它显示出的正是经由对世界的同情性理解而回归主体心性的可能性。第三是所谓“以议论叙事”。这是许多《史记》评点者对《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共同的看法。“以议论叙事”,就是以辞为介质,建立“理”和“事”之间的有效联系。这三者正是明清《史记》评点家对《史记》义例的整体性把握。
明清之际,因为从理学到实学的文化思潮的转换,与考据学相比,《史记》评点的学术价值受到怀疑,在这种背景之下,方苞以自己的《史记》评点为基础,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学术转换,把《史记》义例转换为文章通则。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方苞辞京回乡,其好友万斯同正任职于明史馆,即以明史列传写作寄望于方苞。其后,方苞开始用力于《左传》和《史记》,而且持续20年时间,如刘咸炘所说:“《太史公书》人所共读,而前人用功最深者莫如方苞、梁玉绳,方则藉以明其所谓古文义法,梁则借以考秦、汉前事迹,二人之说义例较多于他人,然梁氏止知整齐,方则每失凿幻,盖考据家本不明史体,而古文家又多求之过深。”[19]3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方苞形成了他的“义法”概念。
在《史记评语》中,方苞指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20]851方苞的“义法”概念就来源于《史记》,他以“言有物”和“言有序”赋予这一概念以自己的内涵。在方苞那里,文虽然有纪事之文、道古之文和论事之文的区别,但其根蒂是古圣贤德修于身而功被于万物,于是有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后世奉以为经,此即所谓“言有物”。而“言有序”,“顾名思义,应该包括详略虚实等和篇章结构有关的一切技巧,然而方苞给我们展示的是他对古文对称格局的由衷偏爱,方苞用‘对称’对付散漫无检局的史料,显现出八股‘对偶’思维的深刻影响”[21]131。虽然方苞的“义法”说明显受到清初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以自己的巨大影响开拓出桐城古文传统,使“义法”成为文章通则。
三、文章天下与六经皆史
方苞对“义法”概念的阐释的确有融通经史文道的意愿,但如果从其思想演进的轨迹看,这种意愿甚至“义法”概念本身就包含某种悖论。石雷指出,方苞曾批评清初以遗民群体为代表的流行文风,称“吴越间遗老犹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而原因在于“方苞是新朝子民,出生时已是康熙七年(1668),祖籍桐城,也不在吴越之地的范围之内。所以方苞超越了‘遗老’的时代和地域,批评起来也就更能客观冷静和不留情面”[22]76-77。这种批评应该是在更复杂的文化脉络中形成的。方苞早年多与遗民结交,好事功,鄙弃宋儒宋学。24岁入国子监,其时,因为康熙的倡导,理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朝廷也多用所谓理学名臣,这种风气无疑会影响到方苞。43岁遭遇南山集案,系狱两年,而后皈依理学,则俨然一代文宗。方苞对理学的态度自然会影响到他对清初遗民的评价,这是时代风气和个人遭遇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方苞借助“义法”概念融通经史文道的意愿就难免受到理学观念的干扰,因为理学在形而上与形而下分裂的道器论中始终坚持经本史末的原则,同时方苞在阐释“义法”概念时虽然强调宗经,但根底却是宋儒的经义之说。因此,方苞的“义法”概念虽然成为文章通则,但其内涵的悖论并没有解决。
如果超出方苞个体观念的局限性视域,我们说“义法”概念及其背后的文道一体论本身就隐含着更根本性的悖论——如阿甘本所说:“能指与所指之间在根本上的不充分对应关系,构成了‘所有有限的思想的残缺性’,因而誓言也表达了这样的要求(对于所有言说的动物来说这一点至为重要),即将他的自然本性置于语言之中,并在伦理和政治的关联中将词、物和行为绑在一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某种像历史之类的东西,才有可能与自然区分。然而,历史与自然是不可分的,这种区分是被生产出来的。”[23]153阿甘本的“誓言”不是一种语言类型,而是词与物的关系的两可性:即“誓言”或者“伪誓”,对应或者不对应。在词与物的关系的两可性背后,它所关涉的问题是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从这一更根本性的悖论出发,明清《史记》评点能够折射出文章学之外的内容。
贺次君对钟惺的《史记》评本有极为严厉的批评,他说,钟惺“乃拾杨慎、李元阳、茅坤、凌稚隆所为论说,稍加编裁,或间出己意,亦不过如评诗文,争论文句之长短,堆陈浮辞而已。……明自杨慎、凌稚隆而后,评论之风日烈,钟敬伯辈其实无学,但好高论,所以不惜重资以刻《史记》者,乃投合时尚,愿求名之一闻耳”[24]179。钟惺的《史记》评本不仅在字法、句法和章法的评点中有这样的缺陷,而且在理解历史现象时也渗透有同样的倾向。如他在《大宛列传》的总评中写道:“‘大宛之迹,见自张骞’二语,本末要领既明,下笔自不犯手。然张骞本以应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为其所留,亡如大宛,道之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领,乃归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过为骞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题。而骞竟以此作应募结局,将错就错,免罪之路,久之,用以邀功。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此自愚,几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在有意无意之间,功罪得失,见于言外。事变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笔。叙诸国情形变化,首尾腰腹,曲折无端,而脉络井然,如目见口陈,只是胸中极透。张骞瞻智,为千古远使第一人,驱之战,枉其才矣。然因战失侯,乃有通乌孙一段枝节,绝处逢生。此辈功名之路,岂可以一端尽哉!”*清代蒋善的《史记会纂》第八集第44页。在这里,历史被文本化了。自然,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文本化的,但在钟惺的理解中,往往是因为叙事者的“心眼之透”或者“胸中极透”,所以能够以文情驱动事变,甚至是为文情而驱动事变。这种状况到了方苞那里,就呈现为一种创作模式。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受命主持清《一统志》的纂修,由他草创修志凡例,有同僚议论应该增加某些材料入志,但不为所许,而他给出的理由是这种做法“未达于文之义法”[20]137。文之义法在历史书写之中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性的规范,制约历史图像的呈现,因此有了文章天下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能指与所指间的不对应最终体现为能指对所指的吞噬,词对物的吞噬,而古文辞章之学则使之转化为一种修辞格式。与这种观念相适应,世界也随之发生变化,明清政治就有一特殊的倾向,“那就是文书胥吏横行官场,把文字的流转程序统统给档案化了,变成一种套路和技术”,而“胥吏政治一旦转化为文书政治,对文字的刻意琢磨就会达到变态的程度,严重时可以让官场丧失效率,变成一种极为低劣的冗政”[25]20。因此,文章天下自然不仅是明清文人的夸张想象,而且也是政治实践越来越沉溺于文牍主义陷阱的表征。
抵抗文章天下的观念,正是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起点。在章学诚的理解中,自战国以下,就有了官守学业的分离,也因此有了知识的分化和文体之辨,如所谓,“自古先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12]86-87。文章起源于官礼声诗之变,而变的核心就是专门治术与达其情志的分裂。这种情况从战国到章学诚当世是愈演愈烈,而要克服此一状况只能借助对六经的重新理解,“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2]1。在章学诚的论述框架中,所谓“六经皆史”具有多方面的内涵,第一,“史”是一种话语规范,而不单纯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形态或者学科分野,其核心是“未尝离事而言理”;第二,“史”作为话语规范,其具有原典意味的文本是《春秋》,“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也”[12]127;第三,《春秋》同时开拓了专门史学的传统,即《春秋》家学,其标志是司马迁及其《史记》,如所谓“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似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12]628;第四,《春秋》家学也就是要成一家之言,“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乎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12]635-636;第五,六经皆史,而其根底在于载道,“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言夫道矣”[12]150。第六,载道之形式是即事明道,而即事明道期望的是知识和语言的行动力,但其可能的途径是守护书写和阅读的伦理质地,在深情投入和批判性反思之间形成某种导向和共识,即所谓“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12]158-159。否则,“即一切科第之文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12]628。
在章学诚之后,明清《史记》评点实践依然在持续,但在理论层面上,六经皆史论无疑是《史记》评点的终结,如章学诚所谓“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12]708。
[1]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慈波.套类、选本与论诀: 南宋举场论学的三个维度[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21.
[3] [宋]强幼安.唐子西文录[M]//[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 [明]宋濂.宋濂全集[M].黄灵庚,编校.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6] [明]杨慎.升庵集[M] //四库全书:12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杨昊鸥.论《史记》文章学经典地位在明代的形成[J].学术研究,2015,(8):152-158.
[8] 高小康.文学观念:时代特征与文体分野 近古文学观念中的古典主义精神[J].江海学刊,2001,(1):151-156.
[9]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 [清]梁章钜.退庵论文[M]//王水照.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1] 张亚玲.《史记评注》批评体系探微[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7-100.
[12]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全译[M]. 严杰,武秀成,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3]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上)[M] //吴广.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5] 张德建.学术分裂与明代复古文学的“道”论[M] //陈文新,余来明.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6] 周建渝.从《史记评林》看明代文人的叙事观[J].复旦学报,2010,(3):87-97.
[17] 邓国光.古文批评的“神”论——茅坤《史记钞》初探[J].文学评论,2006,(4):43-49.
[18] [清]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附史记纠谬[M].崔凡芝,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19] 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0] [清]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1] 罗军凤.方苞的古文“义法”与科举世风[J].文学遗产,2008,(2):124-136.
[22] 石雷.方苞古文理论的破与立——桐城“义法说”形成的文学史背景分析[J].文学评论,2013,(5):76-81.
[23] [意]吉奥乔·阿甘本.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M].蓝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24] 贺次君.史记书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5] 杨念群.皇帝的影子有多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朱正平】
Comments o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Articl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ANG Yi-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The Comments on Historical Records were fully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article scienc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had a decisive imp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mments established the classical status of Historical Records, made it not only become the birthplace of all articles, but also become the principle and scale of the article. Fang Bao explained narrative rul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make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article, but also make the article become secular. Zhang Xue-cheng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six classics are all history”, and resisted the notion that the world was equivalent to narration against the political practice to red-tapism trap, and ma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orality.
comments on Historical Records; article science; Fang Bao; Zhang Xuecheng
K207
A
1009-5128(2017)01-0059-07
2016-10-15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项目:科举视野下的明清《史记》评点研究(15SKYM02)
党艺峰(1966—),男,陕西合阳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魏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