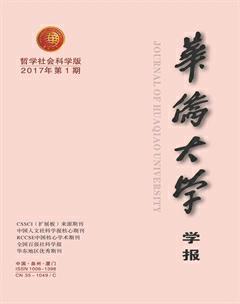民间信仰中的大众心理与官民博弈
王辉+李书源
摘 要:民间信仰虽然缺乏系统的宗教理论和戒律,却能吸引民众自发地组织相关的活动。由民众自发形成求仙讨药活动在民国时有发生,在活动中,大众的整体心理意识超越了个体的自觉意识,影响着求仙讨药者的行为,也影响着政府管控的结果。以民国时期的求仙讨药活动为例来探讨东北民间信仰活动中的大众心理因素与官民之间的博弈。
关键词:东北民间信仰;大众心理;政府管控
作者简介:王辉,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李书源,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吉林 长春 130012)。
中图分类号:B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1-0130-13
民间信仰源自民间的万物有灵崇拜和多神崇拜,以崇拜某种超自然力量為基础,以祈福禳灾等现实利益为目的。表现为神鬼的信仰、家庭及社会祭典、巫觋跳神、卜筮堪舆、岁时节庆、生活中的祈福禳灾等仪式。关于民间信仰的概念中外已经有多种解释,堀一郎1951年出版的《民间信仰》论述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乌丙安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把民间信仰界定为“多民族的万灵崇拜与多神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页)。林国平教授将其定义为“信仰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万物有灵为基础,以鬼神信仰为主体),以祈福禳灾等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自发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准宗教”,参见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第7页。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行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求仙讨药活动即为其中一例。进入民国以来,东北地区的求仙讨药活动,因其动辄人数众多,屡见于文献记载。由于在民间信仰活动中大众的感情和思想全部转移到了同一个方向,个体的自觉性消失,因而有一种明显的集体心理和从众倾向。与勒庞关于大众心理的相关理论暗合。在民国时期的东北,当政府针对有一定规模的民间信仰活动予以整顿时,这种集体心理与大众倾向,又无时不在影响民间信仰行为的走向,并进一步影响着政府相关整顿行为的结果。其中自1929年8月起,发生在沈阳大西关附近的一次小庙求仙讨药活动,表现尤为明显。虽经政府多次整顿,直至1931年7月底,在同一地点仍有求仙讨药活动发生。因此本文试以此次求仙讨药活动为主,结合此前发生的东北民间求仙讨药活动,来探讨东北民间信仰活动中的大众心理因素与政府的管控。
一 民国东北地区的求仙讨药活动
求仙讨药是东北地区常见的民间信仰活动,其过程可以看成是民间与神明间一种契约关系的建立和履行过程。
(一)求仙讨药的地点
求仙讨药的地点是民众观念中神明出没的场所。祠庙是求仙讨药活动的首选地点。例如城西北有新修的一座大仙堂,供奉胡黄多年,显然托兆舍药医人。“近屯患病男女祷药者以碗盛水用红布盖上,置诸神前祝明病状,焚香待立,启视药在其中”《大仙舍药》,《盛京时报》,1928年8月30日第五版。;由于东北地区特殊的“胡黄常柳灰”(即狐狸、黄鼠狼、蛇、蟒、灰鼠)五大仙信仰,五大仙出没之处也常被视为大仙舍药之所。1931年7月沈阳小南边门外,清福尔善将军墓有古树一株相传为百年前之产物。附近人称该树有蛇神降临,专为世人除灾免祸,求之无不灵验。于是一般男女,纷来讨药或祈福,久年荒僻之地,竟一变而为繁华之场《(沈阳)定将军坟间,蛇神舍药惑众》,《吉长日报》,1931年7月22日第四版。;野狐出没山洞也会传有狐仙舍药。1929年五常堡土山洞中因曾有狐出没,某男在洞口焚香长跪以碗求药,“炊顷视之内均有土黄面,药味扑鼻”。后人听闻后前去求药,“所得为丸为散或黑或黄均不一致,因病施药”。《(五常堡)胡仙施药》,《盛京时报》,1926年6月29日第五版。
(二)舍药的神明
舍药的神秘力量有胡仙、黄仙、蛇仙、龙母、神树等动植物化身的神仙,也有济公、九圣等民间俗神,甚至也包括巫觋、萨满等民间信仰从业者。五大仙是东北民间最普遍的动物仙信仰,其形象在人间常化身为老媪、老翁或者俊男美女的形象。民众认为动物仙重视民间疾苦,因此民国年间五大仙尤其胡仙、黄仙和蛇仙舍药的活动最为频繁。1929年8月本邑西门外路北住户姓院内之西墙角向有小庙一座,多年失修,破坏不堪,8月上旬该庙胡仙将陆姓家属迷住令其将庙修饰一新,预备施药。“熟料此言传出至庙社祷者日多一日,当被陆家阻止,老幼妇女持瓷碗至该庙烧香,求药者络绎不绝。当被公安局西分所韩巡官迭次禁止迷信家不但不听,按日增加每日求药者有数百人之多”《胡仙显灵》,《盛京时报》,1929年8月31日。巫觋、萨满多是在请神上身后假借胡仙和黄仙之口,施舍仙药。这些人往往不明医理,“以香灰为药饵,藉以欺骗钱财。因之误人,冲突之事时有所闻”《(奉天)巫医误人》,《盛京时报》,1920年6月13日第五版。此外,原始崇拜中的动植物或器物也可以舍药。1928年1月营城子会双台沟村北有大酸查(楂)树两枝大可三四人围抱,“因村中妇女患病夜间至树根前烧香求药治病,吃药后,有将病愈者,亦有无效者。”村人还是将大树挂满了红布条子。《(营城子)神树出现》,《盛京时报》,1928年1月29日第四版。因器物崇拜而发生的讨药活动也屡见不鲜。1920年10月舒兰县属大白旗屯神塔显灵治病,附近居民男妇老幼焚香讨药,挂匾悬彩。《禁止迷信神塔》,《吉长日报》,1920年10月6日第五版 。
可见,在大众看来可以施舍仙药的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神明,一切具备超能力的神、人甚至事物皆有舍药的可能,人们关注的并不是该神明是否具有舍药的功能,而是大众的祈祷是否能有象征物作为回应。
(三)求仙讨药的仪式
求仙讨药的仪式可以看做世俗世界与神明世界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的建立与执行过程。首先是民众对神明做出承诺许下愿望。讨药者均携香烛纸钱,齐集斯地,焚楮拜祷乞方讨药,以此与神明建立一种基于功利关系的契约。然后以空碗盛水覆以红布置于神前,或树上满插各色之纸兜,或大小异样之玻瓶瓷罐。焚香罗拜,喃喃有声,即使在炎天暴日之下,挥汗如雨,跪地下不敢稍动《(沈阳)定将军坟间,蛇神舍药惑众》,《吉长日报》,1931年7月22日第四版。
第二步是检验神明对讨药者的回应,即神明所施舍的药物。求仙舍药活动所求得的“药”究竟为何物?1931年海城山城子村西有一古树,传闻内有蟒仙舍药,适有一少女患眼疾,至古树下讨药,不一时果在碗内,现有黑豆大小药丸数粒《(海城)古树施舍药》,《吉长日报》,1931年5月4日第二版。1928年松树邑郭某家人至村边庙前祷药,“于所摆酒杯现有金色药丸,气味冲鼻”《(松树驿)仙方活命》,《盛京时报》,1928年12月16日第四版。1928年团山子山洞狐仙舍药则是“药丸散汤剂不一而足”《狐仙舍药》,《盛京时报》,1928年8月2日第五版。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求仙者得到的“药”形式多样,经验后不过是“由庙内因风吹出香灰几许”《小庙内发现小蛇,迷信男女跪香求药》,《盛京时报》,1929年8月6日第四版。或者为“风吹入之尘土而已”《火化神树,蛇灵安在》,《盛京时报》,1931年7月23日第四版。有的庙中放有带药房的神签,讨药者也會在许愿后抽取神签按方服药。华佗药签、医圣大帝药签词中便有治病的药方。大连天后宫的“灵应药王仙方”第五十一签便有专门治疗妇科的药方。签文为“双展飞龙养性天,半丸痴枣却烦难。身虽有恙终无患,须防心地恐为牵。茯苓、泽兰各二钱;大枣三钱;益母草、赤芍、甘草各一钱;竹叶十五片,灯心一子,两剂见功”[日]泷泽俊亮:《满洲の街村信仰》,出版地:第一书房,1982年,第88页。可见,药无定式,野地风狂,将污土秽物,吹落纸兜瓶罐中可以为药;树上流下的汁液可以为药;神前吹落的香灰可以为药;甚至坑中积水也可以为药。作为神明超自然力的象征,药物本身的形式并不重要,甚至药物是否真的能够治愈疾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众对神明超自然能力的的深信不疑。
仪式的过程并未因求药得药而结束。一旦服用药物自觉治愈后,酬神便是兑现承诺的时候。酬神以广为宣传的形式报答神恩为主。讨药者传播怪诞的传闻突出仙药的神奇。如1928年4月,“县东高家屯东有大树一棵(颗),枝干早枯,树旁有一池面积有五六丈,深约尺余,虽久旱不涸,去岁冬月因商贩行走路程甚远,两脚气泡难行,在树前休息,朦胧间由树间出一长虫,初数丈粗如巨,吐人言,此树有仙,可以求药,用池中水饮之当愈时,莫忘明年三月三日更求口传四方,凡有难医之病务来求药”,能使大病离身,商人如命转身取水,回顾长虫不见,饮药毕当脚愈。该商人返家后转扬此事。满邑致病者前往挑水取药络绎于途《迷信神权》,《盛京时报》,1928年4月20日 ,第四版。在这个传闻中,能吐人言的长虫(即蛇)和服后即可治愈疾病的水增加了事件的神秘性,而应神明的要求“口传四方”又使神话的传播具备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性质。 1918年6月伊通城西北尖山子地方民人李某,“近患目疾医药罔效,忽于夜晚梦人告知山有灵药,服之即愈,李未敢遽信,次夜梦如前并示以取药之方,遂信尔不疑,黎明备办瓷(磁)碗一个,覆以红布携带香烛至山前焚香跪拜,越一小时许启视果有药丸在内,服之疾若失。未及旬日,旧病复发,至夜梦有人责其忘恩不为传名,翌日,一面为之挂红一面遍传邻里,从此由近及远,凡病者群往拜求赐药,举国若狂”《(伊通)妖由人兴》,《吉长日报》,1918年6月16日 二版。可见,为神明传名是在得药后必须履行的酬神方式,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为了表示衷心的谢意,讨药者插旗送匾额,大书“心诚则灵”“保佑一方”“仙之不灵只恐人心不诚”《(通化)心诚则灵》,《盛京时报》,1929年10月30日第五版。以此作为舍药神明的广告牌,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往此处讨药。也有地区以更为隆重演戏形式酬神。如1931年11月貉子窝狐仙洞,“近数年来,此洞多有祷药者,一般红男绿女,每日有往来不绝之态。现有一般好事者化缘凑资,以假该洞前高搭席棚演戏五日,以为酬神”。《(貉子窝)狐仙洞演戏》,《盛京时报》,1931年11月23日 。
总之,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求仙讨药活动仪式以大众向神明陈述心愿为起点,以大众许下承诺视为契约达成,若得偿所愿便要酬神以履行契约,但是即便没有达成心愿,大众也只是认为心不诚而非神不灵。讨药大众并不拘泥于神明的类型、讨药的地点和仙药的形式,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是吸引大众前往讨药的重要原因。
二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求仙讨药盛行的原因分析
求仙讨药盛行反映了群众内心需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匮乏而落后的医疗资源与民众重疾沉疴亟待医治的现实之间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如“桦川县原无西医,诊病皆为中医,直到民国10年(1921年)西医才逐渐传入,均系个体小型诊所或医院设备简陋。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才逐渐增多”王志声:《民国时期卫生综述(1909-1932)》 ,《桦川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桦川县文员会编,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8年,第32页。农村医疗条件落后,许多村医“医理不明,医术根本不懂”,夏美驯:《农民对于巫医迷信之思想应如何铲除》,出自《医论公事》,南京:中国医事改进社出版,1935第二卷,第三期,第22页。“庸医杀人”事件时有发生。人们在治愈疾病的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将希望寄托于神秘力量。多数的讨药者都是由于旧疾缠身,“百般调治尚无成效,”于是在神前求仙讨药《(安图)大仙舍药》,《盛京时报》,1921年7月31日第五版。如1926年本溪东太子河沿药王庙右铁道东处有一多年柳树。该村张某之子患吐血病,服药无效。后经某甲告知该处至大树内有二大蟒神,足有二百余年,“汝即去求解药必可痊愈”,张某当赴该树前设桌案,焚香求药,携回服之,顿觉痊愈。《(本溪)迷信神道》,《盛京时报》,1926年7月18日第五版。因此,每年春季为疾病多发季节,也是讨药活动较为频繁的季节。
民众对自我的心理暗示,推动了求仙舍药活动的发展。心理暗示是人们自我保护潜意识的一种体现,在焚香讨药时,因对治愈疾病心存渴望会不自觉的对服药后的效果形成美好的心理体验。1929年8月6日《盛京时报》报道了沈阳大西关南兴化街李姓住宅的南墙外有一小庙,由于有小蛇出入,“于是一般迷信之愚夫愚妇以为神灵,遂纷纷前往焚香,长跪祈祷,请予施药”,某甲患病服其香灰后觉得痊愈,于是赠该小庙红绸匾额一方丈曰“灵仙堂”,此事一传,迷信者因之大起竟人山人海,焚香祈祷昼夜不绝《小庙内发现小蛇,迷信男女跪香求药》,《盛京时报》1929年8月6日第四版。这种对神力的期待和信任使得某甲患病服其香灰后觉得痊愈。这种病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服用香灰与病愈之间虽无必然的联系但是会有偶然的巧合,而另一种是某甲因信仰而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因此我们在诸多资料中看到民众服药后的结果多为“屡有奇验”“其病立愈”等。这种心理暗示无疑为其他人的效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人故意散播谣言,存心蛊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有些造谣者为了借机敛财,散布有仙舍药,1924年4月黑龙江某大仙堂,不知姓名之人口操京音侍香于案,称大仙显灵,能疗人疾,以致一般民众接踵于门,络绎于途,其疗病之法“则茶一盂,灰一包,符(一)道,谓之符水”,而“每日能得,药资数百吊”《迷信难除》,《盛京时报》,1924年4月17日第五版。
民国期间的消息传播多以民间的人际传播为主,口口相传,以讹传讹更加增添了该事件的神秘色彩。《泰东日报》的一则新闻可以说明传言对求仙讨药活动的推动作用。1930年郭家店北山花园后与附属地连之土坡有一豆鼠小洞,“因今夏一向蒙雨,将鼠洞冲豁,大如碗口,市民传言是为仙人之洞。记者亦同人往观,时有人用水灌洞,忽向洞内冲出一五六寸之小豆鼠,当经人捉住,顽弄而死。后不知何人藉端,竟说仙人洞府,向有仙人,舍药济人等事,而今一传十,十人百,讨药之人,频来如蚁。今又有某青年好趣者,将洞挖下二三尺,又用磚头砌做洞门,以戏愚人,至于远处闻说,亦竞前来,顶礼焚香,祈福讨药,而拜鼠其愚甚矣”。《(郭家店)人而拜鼠,愚莫大焉》,《泰东日报》,1930年8月23日第五版。文中三次关于该洞有仙的传言将讨药活动从个人行为推动至小规模的群体行为进而成为跨越社区间的大众行为。
总之,民国时期求仙讨药活动盛行东北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时的东北地区医患供需矛盾严重,大众往往在身染沉疴后因求医罔效转而求仙医治,因此满足治愈疾病的需求是大众讨药的心理出发点。二是基于大众对神秘力量的共同信仰,这使得讨药者有治愈的自我感应并且能够达到“喧传邻近患病者亦前往讨药”《(安图)大仙施药》,《盛京时报》,1920年7月31日第五版。效果。
三 民间信仰中的大众心理特征
求仙讨药者无论其职业、生活的阶层、性格和智力如何,“他们变成了一个大众这一事实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8页。大众的求仙讨药活动是“不理智的”“盲从的”,但是这恰恰是民众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从众心理的一种表现。
(一)求仙讨药者丰富的想象力
由于大众对超自然能力始终处于一种普遍期待的状态,因此,他们对与神秘力量有关的事件极为关注,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能够暗示大众有仙舍药的情况很多。在求仙讨药的事件中最初的导火索往往只是具有民间信仰象征性的几组符号偶然联系在一起。例如有的山洞中因有狐狸出现,便有人认为胡仙显灵,前往讨药;古台因年代久远,被传闻有蟒仙灵验。《(牛庄)迷信难除》,《盛京时报》,1925年5月23日第五版。有时因看到有蛇或狐狸出入而聚集讨药。1928年拉林团子山的古洞穴中因有“老狐隐居其中”并不惧人,有好事者“奉香跪洞求愿”,自认为皆应所愿。于是邻居凑资“筑庙于山下,以供俸之,病者求药有求必应”,很快朝拜聚集如蚁;有因天有异象,民众认为神力所为而求神赐药。如同年双城因夜间狂风大作,翌日出现山洞数个,“于是大众疑云有神仙下降,一般愚人咸赴山洞求药问病”,“由此传遍各村区,每日前往求药者途为之塞”。《(双城)狐仙舍药》,《盛京时报》,1928年8月24日第五版。更有奇者,有因庙宇附近出现水坑而祈祷求药的。1924年双城西南关帝小庙“该处重建新庙挖坑淋灰,挖有四尺多深清水,以讹传讹,指水疗病百症余”。老妇少女手执香纸水壶,虔心祷告许愿,如能治好病情愿送匾立碑《(双城)迷信难除》,《盛京时报》,1924年8月8日第五版。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能够引发求仙讨药活动的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该对象承载着某种民间信仰的象征性符号,如庙宇、狐狸、神仙等,而大众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将其与神灵给予的预兆联系在一起,引发了求仙讨药活动。而一旦讨药活动演变为大众的行为后,个体的想象力便在群体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如1930年沈阳五斗居胡同南小庙的蛇神自舍药后,又有李姓叟“向一般人传言此蛇有百余岁”《可谓至愚,迷信蛇神威灵,有人再倡修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3日。正是大众的想象使超自然能力的形象不断的被具体化和形象化,促成了民间信仰中神明体系的形成和分工。
(二)讨药者的互相传染性
最初的想象经过相互暗示和传染后进入大众所有成员的大脑,大众内部个人第一次的曲解的情绪和行为会被其他成员相互模仿,这就造成了民间信仰大众心理上的相互传染特性。大众通过情感和观念的相互传染,促使个体的意识逐渐朝同一个方向转化并且导致群众的求仙讨药行为呈现不断扩散的态势。以1929年8月——1931年7月的求仙讨药活动为例。
扩散传播首先反映在地域上的拓展。由1929年8月沈阳大西关南兴化街小庙蛇仙舍药为起点,逐渐发展到沈阳大西关五斗居胡同,由于五斗居小庙蛇神舍药使得“蛇之一物大走运气”,蛇神舍药止不(不止)白塔堡一处,西塔、黄旗坎亦均同日舍药。1931年7月9日,沈阳小南边门外丁家坟南门柳树亦忽然舍药,“据传者云,蛇神支派甚多,日内尚有多处舍药发现云”《迷信,蛇神太多,在南郊由四处舍药》,《盛京时报》,1931年7月11日第四版。而后“大南边门外定秃子坟地方又哄动有蛇神舍药之事”。《蛇神越闹越多,定秀子坟树上又舍药》,《盛京时报》,1931年7月22日第四版。随后讨药活动又波及至营口和安东等周围城市。1930年至1931年春,安东元宝山后坡土洞发现取药。1931年7月西四道沟龙母庙,又发现一帮迷信男女,手执茶碗,覆以红布顶礼焚香虔诚求药《(安东)龙母庙舍药》,《吉长日报》,1931年7月23日第四版。总之一旦某地传闻有仙舍药,先是男女老幼不远数十里前去焚香求药,随之讨药的行为会被其他社区的成员模仿,而民国时遍布乡村的寺庙和仙洞为讨药活动实现地域上的拓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次,民间信仰大众间的相互传染也表现在信仰对象范围的扩展。“在大众中能够轻易传播神话的原因,不仅仅源于他们极端轻信的禀性,还是大众奇思妙想,过度歪曲的结果。受大众关注的最简单的事很快会变得面目全非。”[法]古斯塔夫·勒庞:《心理操控术》,周婷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16页。最初是沈阳五斗居胡同传闻蛇仙舍药,1931年7月营口新甸村传该村小庙有胡仙舍药医病《(营口)胡仙迁乔,原因是怕胡匪》,《吉长日报》,1931年7月16日四版。后阮家胡同小庙又有黄仙显灵,“于月之19日下午二时许,突有数十人烧香,庙前焚香拜祷,求赐灵药”。《(营口)警察捣毁黄仙巢》,《吉长日报》,1931年7月22日四版。随后安东又传龙母舍药。大众心理的相互传染加之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使得舍药之神仙范围由蛇神扩大到胡仙、黄仙、龙母。
再次是舍药的场所变化。1929年8月沈阳大西关南兴化街小庙的舍药活动被取缔后,1929年9月其舍药的空间也由大西关南兴化街小庙转移沈阳大西关五斗居南胡同小庙。1931年7月舍药空间不再拘泥于祠庙而是拓展到沈阳小南边门丁家坟南端的大树,同年安东元宝山后坡土洞又发现类似讨药活动。
讨药者的互相传染性首先是基于讨药者有共同的民间信仰基础,因而彼此之间更加容易接受关于群体神秘力量的想象和暗示,并且这种想象和暗示又在大众之间被不断的发酵膨胀和蔓延。
(三)求仙讨药者的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特性
这类特性表现在民间信仰大众容易对刺激有所反应,并且这种反应会不停的发生变化。相对于个体,大众的冲动和急躁使得他们难以控制。
大众心理的冲动性使讨药活动总是处于一种预备的状态,一旦听闻何处有仙舍药,便会闻风而动,讨药大众会立即携带器皿前往讨药,人数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个体的理性思考被淹没在讨药大军虔诚的祈祷当中,并呈现出一种亢奋的状态,这种亢奋使得讨药大众难以平静而稳定,他们常常因为其他传闻的干扰而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
大众心理易变特性在1931年7月营口新甸村的讨药事件中体现尤为明显。1931年7月埠东川新甸村“旧有小庙一座,自前月不悉何人作蜚言,谓该庙有胡仙舍药医病,一般善男信女,均携香烛纸钱,齐集斯地,焚楮拜祷乞方讨药,以医灾疾 。每日之手擎磁(瓷)盆,上覆红布者臂擦踵接络绎载途,近日市上又盛传胡仙以转瞬青纱障起,诚恐胡匪危及香客,及发生意外枝节,顷胡仙为谋信士弟子安全计,特迁至牛家屯小寺油房东,以避匪氛,一般信士弟子,闻命之下皆舍此就彼,而用心甸村南一带骤成荒凉景象云”《(营口)胡仙迁乔,原因是怕胡匪》,《吉长日报》,1931年7月16日第四版。可见由于在求仙讨药者的冲动和易变性,传言便成为一种影响大众行为的危险信号,大众往往成为受传言摆布的木偶。
冲动和易变性使求仙讨药大众在行动时缺乏理智的思考,往往采取急躁的行动,但又缺乏持久性,这种非理智的冲动变化使政府感受到危险,也是导致政府对其管控的重要原因。如沈阳大西关五斗居南胡同小庙原本因蛇神舍药的传闻而香火隆盛,但在1930年7月间因“据附近者言,该庙蛇神已迁居无良堡,迷信之人都下乡进香而忽然冷落,朝拜无人”。《仙人洞发现巨蟒,五斗小庙蛇神迁居》,《盛京时报》1930年8月24日第四版。但是时隔不久至8月间“香火又渐隆盛、自晨至晚不绝云”《五斗居小庙,蛇神又显灵》,《盛京时报》1930年8月24日第四版。
(四)求仙讨药者的固执和保守的特性
民间信仰中,民众表现出来的感情,其突出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其结果就是全然不知不确定和怀疑为何物。[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96页。并且当他们在面对反对和质疑时表现得极为固执和保守。一旦人们期待神仙能够舍药,不论碗或袋中为何物,他们都会毫不迟疑地吃下去。讨药大众在传蜚言者的引诱和暗示下,固执地认为所得的灰尘或香灰正是神明赏赐的丸散丹膏。求仙讨药者的固执和保守性源于他们对民间信仰所持的观念。观念分为因短时期的影响而形成的短暂观念和因传统、环境、遗传等因素形成的基本观念。民间信仰属于后者,观念被大众全盘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让大众改变固有的观念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
如1931年7月7日一时许,沈阳公安局忽派警士及清洁夫多名,将该五斗居小庙用镐锹刨毁,复将木缎等匾砸折并捆之送局《五斗小庙寿命终矣,蛇神其安在乎?公局拆毁后仍有人望空叩拜》,《盛京时报》1931年7月8日。“一般迷信者,笃信之诚,庙虽毁而仍多往,至则大向空处焚香,望空叩拜”。《五斗小庙寿命终矣,蛇神其安在乎?公局拆毁后仍有人望空叩拜》,《盛京时报》1931年7月8日。随后的日子里“迷信之男女仍三五成群前往该庙遗址地方叩拜。一面焚香,一面持纸袋讨药,昼夜不绝,一若此地真有回生之术者”《小庙虽毁,余威犹在,焚香祈药,继续不绝》,《盛京时报》1931年7月9日第四版。并且有人甘愿“拟施本人座落边门外香火地一块,募修小庙,使蛇神恢复栖身之所”《可谓至愚,迷信蛇神威灵,有人再倡修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3日第二版。因为在信仰者心中神灵仍在,并没有因小庙的销毁而消失。同样的,1931年7月21日警察将沈阳小南边门丁家坟南端蛇神舍药之大树穴内填柴,用火燃烧,表示神已无灵。《火化神树,蛇灵安在》,《盛京时报》,1931年7月23日第四版。“群众仍旧迷信讨药,九分局长饬该管分所长于廿二日返回该处守候,随时驱逐群众,但一般迷信者均不忍离去”《大树被焚后》,《盛京时报》,1931年7月24日第四版。
虽然有时强制性的反对会使民众的讨药行为暂时有所收敛,但是心理上他们总是不愿轻易抛弃固有的信仰习俗。1912年开原县署对面的大仙堂,“自日俄战后,該庙异常兴旺,不论昼夜一般善男信女焚香祷福求药祝寿等人,所挂匾额一千余块。去岁经王大令因迷信异端男女混迹实与风化有碍,立谕巡警将所挂匾额,统行搬归县署贮藏,并将该庙之牌位移出,将庙门封闭,一面出示不得再有焚香等事,违者罚款等,因自严禁后无一违反。不料近来仍有送牌位敬匾额,焚香求药执迷不悟者”《(开原)迷信难除之》,《泰东日报》,1912年12月27日第四版。由此可见,胡仙堂乞药是民众传统信仰观念的表现,很难在朝夕之间就被摒弃的。
这种大众心理上的固执和保守正是导致民国年间东北地区求仙讨药活动屡禁不止的原因。文献资料显示尽管官方对历次求仙讨药均持反对态度,甚至出动大规模的警力予以取缔,但是东北地区的求仙讨药活动并未因此销声匿迹。
四 东北地方政府与求仙讨药者的官民博弈
民众简单冲动的信仰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大众的冲动和易变使该大众的行为变得急躁而不稳定,大规模的大众活动成为了社会治安稳定的隐患,因而引起政府的关注和治理。面对政府的管控“大众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大众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他便表现的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100页。因此,官民间的博弈在所难免。
(一)官方警告与民众无视
当求仙讨药活动在政府看来并未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时,官方的管控力度松懈,流于表面,而这样的管控并不能够引起民众的重视。1913年,吉林县公署向警察事务所转发内政部训令,“内务部令开查吾国祠庙林立,附会者凑合药品拉杂成方,付之剂汤,编列甲乙,名为神方。一经祈祷,即砒霜,亦不必配服,此等陋习相沿,一般无知愚民因迷信而转致夭扎,可悯是甚,本部负有保护民命之责,合亟令仰饬属协同各处自治机关一体严禁,将所有各庙刊列方单,暨排印各板立即销毁,以绝根株而重生命,至女巫左道惑众以术为市,尤为民病之害,应一并查禁,勿稍瞻徇”。档案资料显示,仅1917年4月之6月间,吉林县地区便有四处讨药活动发生。1929年,吉林省公安管理处向吉林县转发了卫生部禁止仙丹神方的训令称“查各地庙宇常有施给仙丹药签神方以及乩方治病等事,在者民智未启,迷信神权以为此种丹方系由仙佛所赐,视为一种治病良剂,以致每年枉死者不可以数计,现值科学昌明,文化日进,自不容再有此种迷信情事,亟应严行禁绝,以杜害源而重民命”,并令各地政府所属将各地神宇中施给仙丹药签神方扶乩开放等事情一律禁止,切实查禁并布告人民周知,以杜危害。吉林市档案馆:全宗号:28 目录号:3 案卷号368。接到训令后,吉林县派遣各甲牌长、干警四处调查传禁辖境各庙宇一律免施药方房,仙丹暨杜绝扶乩治病。但从吉林县各地区的回呈来看,全部回覆都是区境庙宇并无私给仙丹药签神方以及扶乩治病等事。
事实上1929年8月15日当沈阳大西关街南兴化街传闻有蛇仙舍药之初,白铭镇厅长便以青天白日下竟有如此怪现象殊属非是,“遂于十二日下令第四区公安分局加派警士在小庙之前日夜看守,严重取缔,凡往焚香礼拜祈求讨药者,无论张王李赵具何阶级即于驱逐以维风化而重治安”。《小庙捣鬼,实行取缔》,《盛京时报》1929年8月15日第五版。而此时,虽有官方警告,民众仍趋之若鹜。“传闻小庙蛇神显灵舍药,引致一般善男信女前往膜拜”《小庙捣鬼,实行取缔》,《盛京时报》1929年8月15日第四版。而官方管制稍一松懈,相应求仙讨药活动则能持续蔓延。至1930年初,“除旗竿、香炉、布匾等项日形增多外,四乡各村镇及外县远道闻名而来者亦日益增多,一般迷信之红男绿女老老少少在香炉缭绕中拥拥挤挤,经过其地者,见其繁盛景况不亚于三月间之天齐庙会”《五斗小庙威灵及于四方》,《盛京时报》,1930年1月14日第七版。至1931年“三年以来自晨自晚香火不绝,各方赠送之匾额层层悬挂,竟达至四五百付之多,另外尚有香烛蜡台旗竿等事,因其如此热闹,附近小商贩亦增涨不少,有维持风化责者从未出予取缔”。《五斗小庙寿命终矣,蛇神其安在乎?公局拆毁后仍有人望空叩拜》,《盛京时报》1931年7月8日第四版。
从1929年到1931年,沈阳五斗居小庙求仙讨药活动能够持续近三年来看,当官方的管控在警告层面时,很难使求仙讨药大众屈服于其管控之下。
(二)官方强制与民众反抗
当求仙讨药活动中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后,官方通常采取强制措施制止该活动进一步的发展。如沈阳五斗居小庙除了因人群聚集而产生了周边的商业活动外,还发生“索要钱财”事件。1930年2月20日该小庙“又添一香火侍者,专负焚香,乞药伺候责任。有举香者,彼为焚之;有扣礼者,彼为扶之;并照顾老爷太太上车下车,有携带小孩者彼亦为之保护”《小庙越闹越阔,又添一香火侍者》,《盛京时报》1930年2月20日第四版。1931年4月间春寒咋暖,杂疫盛行,讨药者日见增多,“而看守小庙之朱某,日间忙于系磬,晚间满载香资供果而归”。《小庙威灵还在,焚香膜拜者络绎于途》,《盛京时报》1931年4月4日第四版。至1931年6月间进香求药者每日“均达二百余名之上”,“每届阴历初一十五,人数加倍”,同时庙中有僧人照料香货,每逢有人上香叩首钟磬齐鸣,“每日所索之香资亦有现洋两三元之巨,系由僧人与一朱某分劈云”《小庙香火不减往昔》,《盛京时报》1931年6月18日第四版。可见,引起官方重视的原因是小庙中有人借香索财,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于是,官方首先驱逐了借香索财的僧人。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官方进一步采取了强制措施,于1931年7月8日拆毁小庙,砸折匾牌,驱逐讨药者,与此同时又将沈阳小南边门丁家坟南端蛇神舍药的大树焚烧,并驱散民众。
在处理手段上,通常官方的做法是力求毁坏求仙讨药的象征性符号,以及神秘力量的承载体。“致用蛮横手段即将讨药之妇女进行逐散,并将讨药之碗器摔坏多件”,《(新民)迷信难除》,《盛京时报》,1916年5月21日第五版。或是强制损毁求仙讨药的场所。针对官方的强制管理,有些民众采取的是非暴力的抵抗態度,包括面朝小庙遗址或被焚大树方向,望空叩拜或者企图另择他处为蛇神募修祠庙等等。
但有些求仙讨药者面对基层官方的制止时,行为则更极端化,甚至出现民众暴力反抗政府管控的情况,因为对群集的讨药群众而言,“数量上的增加使它感到势不可挡”[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87页。1917年4月16日吉林县地方保卫第八团团总杨常禄呈称吉林属届太平沟南山骤于本月之初旬“该处乡人声扬有胡仙太太显灵施药,红男绿女络绎不绝,日在百人。目今以来,风声更甚,而城乡车马连毂不断”,“诚恐嗣候滋生事端”于是呈报。 对此上层批覆为“将该胡仙堂即行拆毁,勿任无知编氓,聚众祷祀,以维风俗而保治安”。在收到批覆后杨常禄于4月22日“当即带同团丁五名,携同铁镐斧锯,前往该处,指挥拆毁。无奈人民信仰甚重,迷信已深。未待举斧,则人民环围罗守,不听拆毁。若遽强力执行,势必反抗。团总百般劝解,而该乡愚执迷不悟,形势胸胸,团总深恐攘出事非,未敢擅变” 吉林市档案馆:全宗号:29目录号1案卷号42。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团总采取暂缓拆庙,即时上报的策略。可见,人数众多使讨药者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力量,因愿望受阻而形成了群起激愤的状态。
(三)官方加强管制与民众屈服
讨药大众聚集扰乱了社会秩序,又不同程度地对抗官方的管控,在此情形下,官方不断加强了管控力度,于是畏惧强权的情绪在大众中迅速传染蔓延,面对强权大众往往比个体更容易屈服。
针对民众的暴力抗法,官方则是由更高权威代表亲临现场,率众检视,以辨真伪从而使讨药群众信服。在上述1917年吉林太平沟胡仙庙讨药事件的处理上,面对群众的武力抵抗,警察所长于4月23日,偕带警团亲临前往解散。
为了消除群众的疑虑对其进行实地解惑,警察所长首先亲自“检视所持水碗,不过地面沙尘,随风扬入,沉落碗底确无真实药饵,则该庙神之不灵尤为显著”。继而指挥警团当众拆毁,继而验证并无祸患产生,以此祛除迷信。随后出示布告告知民众“(讵)查,第八区太平沟地方近日忽有狐仙堂施药情事。一般无知愚民不察真伪,竟相率前往祈祷,祈获仙丹,奔走道途络绎不绝,男女混杂,难免不滋生事端,亟应严加取缔,以维风化而保治安。□□该处灵仙堂现经本警所长偕同警团亲往拆毁,并无祸祟,且亲验各碗中,实无药饵,该庙之不灵抑又可知,为此布告仰尔商民人等务须破除迷信,勿再轻信浮言,拜祷顽石,致被人讪笑,倘仍执迷不悟,阳奉阴违,定即派警驱逐,决不姑息,勿诏言之不预也”。同时仍责成该管警团随时严行禁止,以保公安而维风化,“复若奉行不力,特派警佐付铭暨马步各队之官逐日(前)往监视,俾免阳奉阴违,近据报告”吉林市档案馆:全宗号:29目录号1案卷号42。
由此可见当面对更高的权力打压时,大众便放弃了反抗,继而散去。后续档案显示,在官方的强硬态度下“经竭力劝阻趋赴求药者现已不过数人,日内可望绝迹等情”吉林市档案馆:全宗号:29目录号1案卷号42。为了彻底取缔求仙讨药活动,官方采取的是蹲守驱逐的方法,强行驱散后续讨药大众。官方之所以这样做为了防止求仙讨药者因其固执和保守性不会马上终止其行为以致望空跪拜或久久徘徊。
从吉林县政府对此次事件的处理上看,官方采取了警告、拆除、布告及后期蹲守等一系列的措施,可谓有序完整。面对官方的强力措施,大众心理易变化的特质显现出来,“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受群体意识的影响,讨药大众仍是容易屈服于政治强权。
(四)官方松懈与民众伺机再起
从历次东北地方政府对求仙讨药活动的管控来看,政府取得的胜利并不彻底。求仙讨药活动在东北的民国期间并没有因为国民政府的历次整治而销声匿迹。官方在管控方式上往往前松后紧,缺乏长远的可持续性。这使得民众总是会在官方管控松懈时伺机而动。如1931年7月沈阳小南边门丁家坟南端在大树被焚后,讨药群众经警察驱逐禁止后仅两日无人讨药,廿五日又有人前往焚香膜拜求药《蛇果灵欤?迷信大有人在》,《盛京时报》,1931年7月27日第二版。
以下面四则摘自吉林市档案馆的资料来看1917年4月吉林县太平沟求仙讨药在活动经过短暂的平息后吉林县的讨药活动仍有复燃之势。1917年4月30日吉林省省长郭宗熙训令吉林县称“该县太平沟地方近有莠民假托神道,谣言惑众。……前经面令该知事督警前往解散,闻近日男妇趋赴者尚不乏人,应即严行禁止,以祛迷信而安地方”。 从这份训令中可以看出,太平沟胡仙讨药活动并未彻底根除。
1917年5月9日王麻子沟榆树屯又发生求仙讨药活动,据第四团团总赵双魁呈报“兹查本团属界王麻子沟地方有榆树屯居民,徐润田之祖坟存在,只因年久塌成一洞,为野狐所居,该坟主徐润田意存煽惑,挂匾一块,上书灵仙洞字样。近有些迷信甚深之男女前往讨药疗病,传闻之下殊深诧异,当红区官会同,第四团团总前往考查,详经征求毫无应验,足见魔由心起虚伪无疑,除随时填平洞口,摘除匾额,并布告宣禁外,合即具文报情。”
1917年5月17日巡长于泮文呈吉林县警察所“宪所传近闻大绥河地方又有灵仙施药情事,引诱一般愚民,前往讨药者日益众多,诚恐匪徒煽惑,从中扰害,应由该巡长严加取缔,以保治安。合仰该巡长即便遵照及时解散,勿任滋生事端,仍将办理情形逐行具报来所”“因奉此查,分所已于此事发生之初,随即函请本区指示,嗣奉区示,着巡长相机解散,当已遵示实行,已见势微,兹奉前因,巡长复带警前往至该处,止见妇女四五人,当又婉言相告,勿被迷惑等语,该讨药等亦因屡析无效,均置不信,度不日即将自为消灭”。
1917年5月19日吉林省省长郭宗熙令吉林县文:“吉林县呈覆奉令查禁太平沟地方莠民,假托神道,谣言惑众情形由,据呈已悉近闻城东龙潭山地方又有无知莠民聚众讨药情,仍责成该知事切实查禁具报”。吉林市档案馆:全宗号:29目录号1案卷号42。可见,在经历了太平沟胡仙舍药事件后,尽管政府通过发布布告和实际的取締行动早已将官方的反对态度公布于众,但是讨药活动却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大众心理顽固保守的特性使之然,另一方面与官方处理此类问题的方式也有一定关系。虽然官方会以强制手段取缔讨药活动,但其管控缺乏有效后续措施,只是令地方官员“特别注意,倘再有讨药情事,务须随时勒令散去,以祛迷信而保公安”吉林市档案馆:全宗号:29目录号1案卷号42。后续并没有行之有效的科学宣传和引导行动,而社会医疗设施的完善才是最终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
总之,讨药者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聚众焚香讨药,因人群聚集而导致交通阻断、商贩林立甚至有人借机诈索钱财,东北地方政府取缔求仙舍药活动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固政府的控制力。但因地方基层管理者对大众的求仙讨药活动缺乏应有的预警措施,在人群聚集后管理者又碍于舆情民愿,或者为避免造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出现不可控的局面,只能以“未敢擅变”为理由将问题上交主管部门。鉴于官方基层管理者的消极态度,讨药者往往无视官方的管控甚至公然反抗。讨药民众对政府权力的忽视促使官方最终以强制措施暂时平息了求仙讨药活动,但由于缺乏后续的管控措施,往往难以取得持久的效果,讨药者总是伺机而动。
五 对求仙讨药活动的评价
求仙讨药活动作为一种自发的民间信仰活动在民国东北地区时有发生,此类民间信仰活动在稳定社会情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社会和民众也有一定的负作用。
(一)求仙讨药活动与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在一定的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弥漫在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体现了这段时期内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取向。民国时期的东北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东北民众而言,共和初建、国体变更带来的种种变化还未完全适应,民众又被卷进了军阀混战和奉系内战之中,农业经济下的天灾人祸使恐慌情绪在社会上蔓延。如1918年官屯和五硼峪两村疫症流行,“已亡之家,病得连坐,陆续不决(绝)”,“两村居民不下四百户之多,患病之家十之八九,延医服药越加沉重”辽宁省档案馆编:《海城县官屯石硼峪公诚会因疫症流行祈祷酬神演戏》,出自《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东北卷)5》,第404页。在这种绝望情况下民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为社会治安埋下隐患,祈求神明的庇佑成为民众求得生存的心理寄托。大规模的求仙讨药活动带动社区成员参加,从而成功的将民众恐慌情绪转移到积极的求仙讨药活动中。民众在神前祷祝求得的“神药”无疑对患者的恐慌情绪是一种心理安慰的良药。
(二)求仙讨药活动与社区互动
纵观民国期间东北地区的求仙讨药活动有如下特点:第一跨阶层。求仙讨药活动既有底层民众,又有“老爷太太”《小庙越闹越阔,又添一香火侍者》,《盛京时报》,1930年2月20日第四版。等社会社会上层参与,还有僧道等神职人员参与其中,因此该活动促进了社区成员间的交流。第二跨社区。由于大众心理的互相传染性,求仙讨药活动往往由社区内的活动演变为四乡各村镇及外县远道闻名而来社区间的交流。讨药者受传闻影响奔走于不同的社区之间也扩大了此类活动的影响。第三经济性。求仙讨药活动因人群聚集而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连锁反映。如会有“许多小贩在附近摆设摊床,呼喊叫卖”《小庙内发现小蛇,迷信男女跪香求药》,《盛京时报》,1929年8月6日第四版。;为了给讨药者提供所需清水,附近守候担水之人日收取香资。总之,求仙讨药活动带动了社区间人员、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与互动。
(三)求仙讨药活动中的多元化角色
底层民众始终是求仙讨药的主体,对超自然力有着虔诚的敬畏和崇拜。由于处于社会底层,底层民众承受着来自社会和自然界的双重压力,面对自身力量的渺小,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神明。因此在历次求仙讨药活动中,底层民众显得尤为虔诚和积极。
乡绅是民国时期的东北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政府与民间沟通的中介,乡绅也是民间信仰活动倡导者和资金的支持者。在求仙讨药活动中,为了感谢神恩,乡绅往往会出资修庙。如1920年8月营口西街灵神庙“灵应异常,凡有灾难及患疾病前往该庙求治者莫不立获痊愈。去岁某营长及埠,由绅士捐洋甚钜,将庙从前建筑,因之前往求药者不绝于门” 《(营口)灵神有灵》,《盛京时报》,1920年8月30日。
新文化精英对对民间信仰持批判态度。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在东北的传播,新文化精英极力宣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将求仙讨药视为“迷信”,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反驳。他们高呼“破除迷信”“迷信误人”等口号,一面疾呼“望地方官者即取缔焉”《巫医被惩》,《盛京时报》,1919年7月15日。一面对讨药活动屡禁不止又感慨积习难除殊可叹。与此同时新文化精英深入民间用通俗的讲演向民众宣传卫生健康知识。如1918年8月省立通俗教育演讲所长与全体职员议定拟开防疫讲演大会,决定“自本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九时起开始讲演,至讲演人员除由该所各讲演员轮流切实讲演外并邀请各界名人讲演一切”,内容包括“防疫应破除迷信”等《防疫演讲会之筹备》,《泰东日报》,1918年8月。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为求仙讨药者提供了更多维护健康的科学方式。
政府官员是国民政府对东北地区政治管控的主要力量,对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实施了一系列的管控措施。主观上讲,政府官员并不支持求仙讨药活动,而是采取多种管控措施。但是有时政府官员对舍药祠庙的维修和保护往往客观上给民众造成政府支持讨药动的错觉。例如1922年8月样子哨河沿旧有胡仙祠一所相传最灵。“前任宋知事佐治镇时曾重修祠宇,孙少臣团长亦送有匾额,近又舍药,而求药之善男信女连络不绝”。《(样子哨)果有仙耶》,《盛京时报》,1922年8月18日。
(四)求仙讨药活动的负面影响
讨药者动辄聚集数百人,车马塞途,阻碍交通。民国年间,东北匪患成灾,聚众讨药容易招致胡匪杂沓其中,对社会治安造成压力。而且民众盲目依赖仙药不但浪费钱财,贻误治疗,也会影响患者康复甚至威胁生命。1928年3月九连城住户于某有幼子年六岁患咳喘病甚重,“医治未愈,近闻埠内圣宗阁内吕祖降乩赐方服药后,功效甚著,于某信以为实,遂于日前亲至吕祖像前请求乩赐一药方,计麻黄三钱服后发汗,于某如法治之,其子于出汗后气息奄奄,命在旦夕”。《 信乩误人》,《盛京时报》,1928年3月16日第四版。可见,聚众求仙讨药无论是对民众的个人生命财产还是对社区的交通治安来说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导致官方取缔该活动的重要原因。
另外,民众迷信仙方神药容易被异端邪说利用,成为其骗取钱财,招募教徒的手段。由于民国时期放松了对宗教的管控,一些民间宗教势力纷纷抬头。民间宗教往往以天灾人祸恐吓民众,同时兜售仙方神药愚骗民众。1919年8月吉林省因天旱导致霍乱,吉长各埠有人发送传单,讬言张天师并附有治疫药方,“盖其方所用半夏,麻黄、陈皮等药纯系辛温之品,若以之治热病,不啻火上加油,恐其不死而速之死也”《时评》,《吉长日报》,1919年8月20日。 。受巫医舍药的影响,民国时期东北地方的一些会道门也往往打着舍药治病的幌子勒索钱财。1920年营口郜家屯曹某组织邪教名为天地门“搜罗教徒数十人,分布各处,劝诱人民入教。一般乡愚被其煽惑者颇不乏人,凡入教者须纳资若干,以为会费。如有疾病请求调治者,曹某又先索香资若干,病不愈谓病者无诚意,病即愈即勒索资财”《(营口)左道惑人》,《盛京时报》,1920年9月2日。
总之,求仙讨药活动作为民间信仰的一种形式在稳定社会心理,增强民众治愈疾病信心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大规模的讨药活动也增强了社区内外的互动。虽然社会上的不同阶层对求仙讨药活动持有的观点不同,但社会上的反对声音推动了民众对求仙讨药活动本质的认识。
六 结语
民间信仰大众因心理上对神明和超自然力量存在着宗教般的狂热和偏执,而对民间信仰有关的象征性符号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和想象力。求仙讨得之药其实是一味心理上的安慰剂。是因为在落后的医疗环境下,药石无效后的另一种需求或一种希望。但是讨者不仅只是与神明直接进行利益上交换。作为求助者一方,付出了香楮、冥镪、牌匾的花费,希望得到的报酬无疑是神灵所施舍的仙药。
大众中的个体通过暗示自己相信神明赐药,并将其想法迅速传播于民间信仰大众中的其他成员。由于讨药大众对超自然力量有共同的信仰基础,个体的暗示在他们之间迅速互相传染,因此在短时间内求仙讨药者逐日聚集多人。
“东北地区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相对自由,但一直未曾脱离过中原政府的管理,与中原文化保持着长期而稳定的联系”。徐栋梁、王国平:《闯关东文化与美国西部开发文化差异性研究——以<闯关东>与<与狼共舞>为例》,《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34页。盡管国民政府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对类似求仙舍药活动严加取缔,冀图达到祛迷信而安地方的双重目的。但是由于大众心理的顽固性致使其不会轻易的放弃对神明的信仰,因此官方和民间围绕“讨药还是散去”展开博弈。鉴于当时东北地区落后的医疗设施建设发展缓慢和官方的管控缺乏行之有效的可持续性,因此求仙舍药活动出现屡禁不止,此起彼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