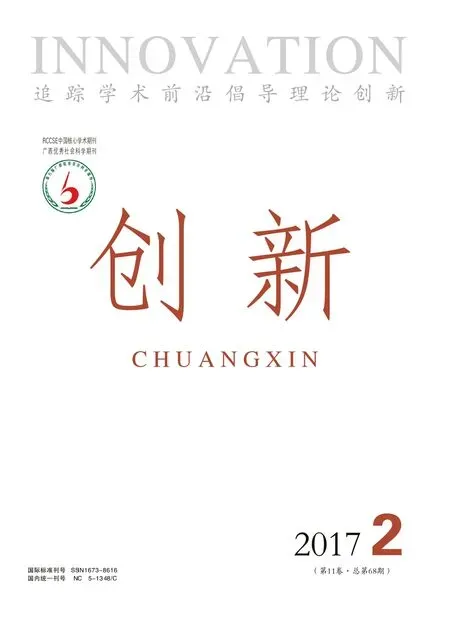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阶段性历史考察
■ 易显飞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阶段性历史考察
■ 易显飞
西方科学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传播,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期间,“自然辩证法”进路下的译介与研究对于我国科学哲学的传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1956—1966时间段将其视为“自然科学哲学”来研究,以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我国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文革”期间是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一个缓慢与停滞阶段,相关研究依旧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号下进行,其研究价值取向也主要是对西方科学哲学进行“批判”,表现出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研究的学术独立性较弱。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科学哲学家及其相关著作被译介,几乎涵盖到西方绝大部分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流派。这些翻译和介绍浓缩了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精华,为较长时间封闭的国内科学哲学界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西方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西学东渐
自19世纪下半叶,西方科学哲学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在中国传播。在新中国成立前,这既包括诸如进化主义思想在内的“广义的科学哲学”,也包括诸如实验主义哲学以及维也纳学派等在内的“狭义的科学哲学”。这些传播,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传播相比,更多的是局限于比较狭小的学术圈子,但依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继续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国内进行传播。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播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对不同阶段的传播过程进行历史描述,并试图对传播历史进行一定的理论阐释。
一、第一阶段(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是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进路展开的。若从1956年我国制定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长远规划来看,可将这一阶段划分为前后两期,即1949—1956年和1956—1966年两段。1949—1956时段主要是广泛学习阶段,1956—1966时段则是研究工作逐步深入的阶段。新中国的成立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的,这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部分的自然辩证法在全国范围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在1949—1956年时间段,全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热潮。由于在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必然要联系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而,自然辩证法的传播、学习与研究成为当时的潮流。主要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是“自然发展史”部分的最后一章和“社会发展史”部分的第一章,成为了《自然辩证法》中熟知程度最高的一篇;《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开始连载《自然辩证法》中的部分章节(由于光远、曹葆华等新译);1950年《自然辩证法》新译本(郑易里译)的由三联书店出版;地质学家李四光(1950)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举办的刊物《自然科学》上发表了文章《科学的中心思想在怎样转变》;于光远(1955)主持的《自然辩证法》的新译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且艾思奇的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于同年8月发表在《人民日报》,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加上这个新译本比较完善,发行量很大,“在自然辩证法学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2]19。
在1949—1956年时间段,尽管当时苏联错误地“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许多活动对我国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与研究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苏联纠正过去错误批判的一些主要文章也都译介过来了,如《反对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无知的批判》《科学中的学派》《论科学中的批评、革新精神和教条主义》《什么是控制论?》《控制论的若干基本特征》《苏联科学院工作的主要方向》《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文章经翻译刊登在国内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对于当时国内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了积极影响[2]19。由于受苏联错误评判“资产阶级科学”的影响,我国当时自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纠正错误观念的一些文章便逐渐产生了积极影响。如1955年龚育之、李佩珊先后发表理论文章,论证了自然科学不具有阶级性特征;1956年5月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批判了给自然科学“贴标签”的错误做法,指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与阶级性无关。随后发表在6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明确指出,对于之前受苏联影响形成的“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资本主义的”之类的提法是极其错误的[4]24。1956年12月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一文指出:“正如好的哲学会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一样,不尊重事实和科学的、僵化而专断的坏的哲学,当然会要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5]25他并于1957年在第1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中强调,“哲学的任务,主要不是去堵塞和限制自然科学的这条或那条道路,而是为许多自然科学问题的解决从思想上去开辟更多更宽广的道路”[6]25,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对以往错误批判科学做法的一种清算,这种清算对于后来我国自然辩证法的继续学习与研究工作都是具有积极影响的。
在1956—1966年时间段,当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时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召集了一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对哲学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讨论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1956—1967)。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独立的学科被规划出来了,数学以及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受到重视,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杰出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自然辩证法”紧密联系起来,“自然辩证法”俨然成为当时国内科学技术界精英的方法论[3]。这实质上为我国科学哲学的发展定下了基调或基本框架。
尽管这个规划没有具体目标,主要是意向性的和指导性的,且后来由于“左”倾错误等原因并没有尽如人意地实施,但在组织措施方面有两个重要成果,这对后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是1956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下面正式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于光远亲自兼任组长。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机构,该研究机构不仅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骨干力量,而且推动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队伍;二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成立不久后就于同年10月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该杂志是新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学术刊物,到“文化大革命”停刊时,共出版了27期,为集中和交流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信息与成果提供了重要园地。并且,科学出版社还陆续将各期编订成册加以出版,如1960年2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选辑(第一辑)》就收录了34篇文章,几乎包括195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上的大部分文章[4]。这进一步扩大了自然辩证法的影响与研究范围。
当时关于科学技术论、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关于科学技术论的研究方面,如1961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收集了龚育之关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哲学思考方面的10多篇论文,是我国自然辩证法领域第一本个人的研究论文集;李宝恒在1962年第2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胡文耕在1963年第3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及不少有名望的科学家如钱学森等探讨自然科学与哲学方面的文章,也往往会给很多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关于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方面,如195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开设了“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笔谈”栏目,发表了许多自然科学家谈论科学技术的方法论问题。何祚庥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11期与1962年第2期分别发表了《实验、抽象和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和《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随后,他又于1962年第10期上发表了《数学方法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1963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与周光召合作的《物理学研究中的理论和实验》以及在《新建设》1962年第9期上发表了《谈谈科学方法论问题》;张巨青在1961年10月和1962年8月的《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了《论假说》和《再论假说》;陈昌曙在1963年2月的《新建设》上发表了《关于类比法的几个问题》、在1963年第4期和1964年第3期的《哲学研究》上分别发表了《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哲学意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吴忠伟在1962年4月和6月的《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了《自觉地运用实验、抽象、假说》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程序问题》;陈国达在1963年11月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怎样严密组织科学研究过程》;李宝恒在1964年2月的《文汇报》上发表了《科学实验的特点和作用》以及齐振海在1963年第6期《新建设》上发表了《自然科学中真理和错误的相互关系》等,都是些涉及自然科学方法论或认识论的研究。
概括地讲,从规划的制定到“文革”开始这十年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各方面逐步向深入发展,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都是有收获的。”[2]28再与规划制定之前一阶段合起来看,不难发现当时的政治因素实际上反而推动了自然辩证法传播与研究快速发展。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这种研究进路的积极影响往往被科学哲学界所忽视,这从学者们通常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划成一个传播阶段就可见一斑。如有学者在总结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时指出,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新中国成立前,笔者注)为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一时间段,属于自然辩证法传统下的发展。这种传统将相关研究限定意识形态内,主要是对《自然辩证法》原著的阐发,着重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和遗传学等科学理论及相关科学家也连带当作了批判目标[5]。另有研究者也指出,“五四”前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哲学对当时的启蒙运动扮演了积极角色。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哲学开始在中国大陆地区失去影响,直至1978年,科学哲学才得以重新传播并迅速发展壮大[6]。本文主张,这“第二个阶段”所跨越的时间段不仅应该进一步大致分为“文革”前与“文革”时期两段来看,而且如前所述,将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像龚育之先生一样分为两个小阶段来看会更接近史实。
二、第二阶段(1966—1977年)
“文革”期间,由于较特殊的政治环境,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基本处于相对封闭和停滞的阶段。如《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停刊,许多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家、哲学家一样,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分子”来批斗,原来确立的关于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和学术应该“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也被指责为给“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修正主义观点”。就连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都被当成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著名的科学理论“相对论”也被当成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是“引导(自然科学)危机不断加深的一面黑旗”[2]42。在此种语境下,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正常传播,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幸运的是,“文革”期间,在几乎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都遭受较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自然辩证法”相对而言受到的影响反而是较轻的。由于《自然辩证法》为恩格斯遗著,人们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批斗”更多的是针对科学哲学的西方渊源与具体的研究西方学问者,而往往不是针对自然辩证法研究本身。正因如此,上海才可能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停刊的时候还创办了《自然辩证法杂志》[2]42,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科学哲学相关研究才可能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号下进行。尽管当时“对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过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使得科学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并没有真正成为现实,甚至根本得不到提倡”,但还是“在提供批判资料的名义下,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名著,为科学哲学的传播和研究,做了一些资料上的准备”[7]。如在此期间,《外国自然科学哲学摘译》《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思想体系的对话》《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生命是什么?》《偶然性和必然性》《宇宙发展史概论》《物理学与哲学》,等等。即使1977—1979年才陆续出版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也是在“文革”期间成稿付印的[7]。
这说明在“文革”期间,相较于其他西方分支哲学,科学哲学受到的阻碍相对是较小的,这无疑得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进路。在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的有效传播只能在简单、粗放的批判狭缝中艰难进行,倒是涉及科学方面的哲学研究还能有点生存空间。正如黄见德所说:“翻译和出版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尚且如此艰难,想要摆脱‘学点哲学史’的政治框架,把西方哲学作为科学对象进行研究,不单单是个困难的工作,而且常有几分风险,搞得不好便会大祸临头。然而,中国学者并不放弃这样的追求和努力。在公开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选择那些与政治关系较为间接的西方自然哲学论题,如宇宙天体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正是过去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的薄弱环节。”[8]如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了李迪著的《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斗争》和郑文光著的《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1975年出版了申先甲著的《牛顿的力学及其哲学思想》,虽然这些作品篇幅不大,所述内容也多为科学常识,但作者在介绍和概况自然科学原理的基础上,都着力于揭示这些原理的哲学意义,都可算作是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进路下进行的科学哲学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都为科学哲学的传播起到了薪火相传的作用。
“自然辩证法”具有其特殊地位,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与当代科技革命及引发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因而作为科学哲学的中国样式在整个国内科学哲学变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像是一个“孵化器”,研究主体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但研究对象均稳定地限定在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断地孕育出诸多子学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9]由此可见,“文革”期间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仍然是我国科学哲学界不应忽视或回避的一个时段。
三、第三阶段(1977—至今)
“文革”过后,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一开始仍然主要是围绕自然辩证法研究进路来展开的。在这方面,于光远做了不少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为推动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文革”一结束,1977年就开始考虑恢复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1977年3月,在于光远的倡议下,在北京召开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主要工作是探讨如何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如何恢复和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随后,于光远倡导并组织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信》小报,以便于推动研究和加强学术交流。会议之后,于光远在中国科学院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并担任主编。1978年夏季,在于光远的倡议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主办了自然辩证法讲习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人参加了该会。1981年10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光远亲自担任了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若说以上还只是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组织建设上的贡献的话,那么他在具体学术建设上也是贡献不小的。如1983—1993年,于光远倡议并主编了《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并亲自撰写了部分条目,该书1994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96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长达48万字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其所论及的正在我国兴起的哲学学派指的就是“自然辩证法学派”。于光远在60年代和“文革”后共培养的27名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先后成为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骨干力量[10]。于光远所倡导组织制订的《1978—1985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拟定了要加强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并明确将“国外自然科学哲学研究资料的翻译”作为主要项目之一[2]45。这在当时对于人们在自然辩证法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无疑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后,大量的西方科学哲学相关著作才被引入;教育部和国家教委指定将《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科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和本科生的选修课;以及陆陆续续有高校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传播与研究开创了崭新的局面[11]。至此西方科学哲学的传播也终于进入了在我国生根、发芽和成长的春天。
由于科学哲学渊源于西方,加上较长时间对西方学术的拒斥,改革开放后,“学习模仿”就成为当务之急了,所以“文革”后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主要是以译介西方相关著作开始的。这在“文革”之后至2000年之前表现尤为明显。如1978年《世界科学》(1978年3月试刊时名为《世界科学译丛》,1979年1月该刊名为《世界科学译刊》,之后才改名为《世界科学》)创刊,就是以译介为办刊宗旨的。当时最为重要的两个平台是1979年先后创刊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科学和哲学》杂志,至1989年期间,分别出刊43集和48集,主要翻译介绍了西方科学哲学名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述文献。基本上同一时期,国内还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哲学著作,概要地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中,一些名家的科学哲学著作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1]。在丛书之外还有不少,如: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文集》1~3卷(1977—1979),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80)、《必要的张力》(1981),劳丹的《科学与价值》(1989)和《进步及其问题》(1990),等等[12]。总的来说,所翻译过来的科学哲学著作都是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性作品。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的“20年来,对原苏东和西方的研究成果全方位开放,译介的著述之多是空前的”[9]。这些经典作品对于窒息了很久的国内科学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来说,“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13]事实上,2000年之后时至今日,不断涌现的科学哲学家的代表性作品仍在不断译介过来,也仍将继续。如盛晓明等翻译的约瑟夫·劳斯的《知识与权力》、韩连庆翻译的唐·伊德的《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戴建平翻译的约瑟夫·劳斯的《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王巍等翻译的伊恩·哈金的《表征与干预》,等等。西方科学哲学重要作品不断翻译过来,这是说明其在不断传播的重要标志。尽管我们在剪裁西方学术思想的时候“的确有食洋不化、浅尝辄止的毛病”[9],但这是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准备和积累阶段所难以避免的。
与此同时,我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数量与硕博士招生数量呈直线增长,这也是考察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至2008年为止,我国共有108个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和26个博士学位授予点[14],近几年又稍有增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2012年中国哲学年鉴》记载,2011年统计上报的27个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点的毕业生数为156人,考虑到少量的直博生不在毕业生之列,且按照上报硕士点数量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计算,可以推知每年招收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大概在700~800人之间;2011年统计上报的16个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点的毕业生数为75人,上报博士点数量占总量的约一半,可以推知每年招收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数量大概在100~200人之间。[15]
四、结 论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作为连接科学与哲学的“科学哲学”,基本上是与“科学”同时传入我国的,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交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它的传播主要是以“自然辩证法”为基本研究进路的。1949—1956年的传播主要是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来学习的,为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跃迁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提供思想基础。1956—1966年的传播主要是将其视为“自然科学哲学”来研究的,以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我国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1966—1977年的传播主要是将其视为“辩证法”来推广的,旨在为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提供“批斗”的思想武器。总体上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里,西方科学哲学基本以“自然辩证法”为进路,且呈现出受政治因素干扰的演变轨迹。
改革开放后,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呈现出“井喷”之势,译介西方相关著作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而陈述、梳理西方科学哲学相关文献也是这段时期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2000年之后,虽才短短10多年,但学术界已经开始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到我们过去“陈述”太多、“创新”太少。总体上,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表现出了从译介到创造这样一种基本的演变轨迹。
[1]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40-341.
[2]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尹继佐,高瑞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75.
[4]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选辑(第一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i-iv.
[5]胡新和.科学哲学在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5):1-8.
[6]李彤宇,王利.论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演进取向及其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9):29-35.
[7]胡新和.科学哲学三十年——从历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看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10):76-80.
[8]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44.
[9]刘大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J].哲学动态,1999(6):2-5.
[10]于光远.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xi.
[11]李彤宇.论八十年代中国的西方科学哲学翻译运动[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5):61-70.
[12]尹继佐,高瑞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77.
[13]何锡蓉.新中国哲学的历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182.
[14]乔宏刚.1987年—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概述[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9:9.
[15]肖显静.国内卡尔纳普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概况[J].创新,2016(6):43-51.
[责任编辑:杨 彧]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our Nation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Yi Xianfei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new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I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orientaliz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e foundation of PRC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of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ve produce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our n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Especially in the year between 1956 and 1966,it was deemed as natural scientific philosophy,so as to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march toward science,and then provide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on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n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diffusion proces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our nation is relatively slow and even has been curbed. However,research related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s was continuing under the flag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Such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critiqu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which has displayed a strong ideological color with little academic independenc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are many scientific philosophers' works which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to our nation. These works nearly covered all influential scientific philosophers and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se translation works have introduced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and it has provided domestic philosophy of science circle a brand new chance of development.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Dialectics of Nature,Orientaliz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N02
A
1673-8616(2017)02-0038-09
2017-01-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问题及其影响”(12&ZD121)、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技术的社会性别视角诠释”(XSP17YBZC180)、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学习共同体’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及实证研究”(17B26)(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资助)、研究生教研教改课题“基于质量文化的校院两级研究生质量监控体系研究”(JG2017ZD03)
易显飞,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后(湖南长沙,4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