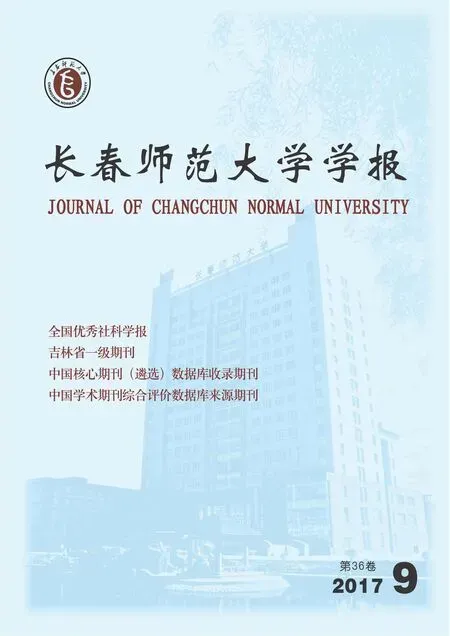莫里森与铁凝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对比探析
朱 林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74)
莫里森与铁凝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对比探析
朱 林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74)
本文以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两部小说以及中国当代女作家铁凝的小说《玫瑰门》为研究文本,利用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方法,在女性主义理论关照下,对比研究了佩科拉和姑爸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及秀拉和司琦纹女性意识的恶性爆发,阐明了极端女性意识对女性意识健康觉醒的危害。
托尼·莫里森;铁凝;女性主义;女性意识
自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国内学者运用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对其作品进行研究,女性主义解读、文化批评、叙事方式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层出不穷。国内外近年来基于比较文学理论发表的莫里森小说研究论文呈现出以下几个现象:西方学界在2000—2010年间多关注莫里森小说系列之间的整体比较;近五年来西方学界的研究视角转移到莫里森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乔伊斯等西方作家的比较;一些国际学者尝试进行莫里森与本国作家作品的比较;我国国内对莫里森的比较研究较多地关注其作品的叙事技巧与其他西方作家的异同。[1]虽然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莫里森与中国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但较多地停留在与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之间的对比,如汤婷婷,而与我国本土作家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几乎为空白。本文尝试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利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方法,选取托尼·莫里森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中的两位主人公,与铁凝小说《玫瑰门》中的两位人物分别进行比较,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制度下的女性在男性话语权控制下两种极端的女性意识状态——女性意识的完全丧失与女性意识的恶意爆发,阐明只有理性的、正确的女性意识才能真正帮助女性获得救赎。
一、作家及作品背景介绍
1.作家及作品简介
托尼·莫里森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到目前为止共发表11部小说。她的小说多以黑人女性的视角叙事,探究她们的心理活动以及黑人女性在种族与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所表现出的不同应对行为,“以现代艺术和人性的光芒实现对诸如黑人妇女这样的双重(多重)弱势群体的观照和关怀,为他(她)们和他(她)们的心灵修史。”[2]《最蓝的眼睛》(1970)和《秀拉》(1973)中的两位主人公代表了黑人女性的两种极端女性意识:《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试图通过祈祷拥有蓝色的眼睛来改变自己的黑人身份,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但最终幻想破灭,造成精神崩溃发疯的悲剧;《秀拉》中的秀拉通过挑战传统道德的方式,把男人当玩物,只谈性不谈情,以此报复不公平的社会,这种偏激的女性意识觉醒使得秀拉最终被黑人社区抛弃,孤独地死去。
铁凝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家级文学大奖。她的小说弱化政治背景,强调平凡人的生活;擅长刻画不同的女性形象,细腻描写女性心理,探索女性命运的主题。铁凝因而被称为女性主义作家,被赞誉为“目前中国最具有女性意识的小说家之一”。小说《玫瑰门》一改之前中国女作家“唯美、动人、纯真”的爱情叙事,以犀利、冷静、残酷的笔锋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揭露女性生存状态的现实大门,是新中国第一部描写女性意识觉醒的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3]。
2.小说创作背景简介
莫里森的小说均以美国黑人的生活为叙述对象,源于从他们的父辈以货物的身份被送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刻起,在美国的黑人就失去了自由、人权与话语权。他们被当作牲畜被奴隶主任意买卖和杀戮,他们没有自由选择生活与命运的权利,甚至被剥夺自己的语言,在白人统治的文化中只有沉默顺从。《最蓝的眼睛》和《秀拉》的故事背景都发生在废除奴隶制度后的美国,但奴隶制度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白人霸权文化依然统治美国,黑人仍处在社会的边缘,处处承受不公平的待遇。而黑人女性挣扎于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夹缝中,处在社会的底层。作为社会人,她们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作为家庭成员,她们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依照家中男人的意志生活。《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亲在女儿遭受亲生父亲强奸后竟然无动于衷,直接导致女儿的精神崩溃。秀拉的祖母把男人奉为上帝,讨好男人,并教导社区的女性要尽心伺候自己的丈夫。黑人女性对自己的身体、生活甚至孩子都处在“无权”的状态下,备受压迫。
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前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教化,女性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女子以裹小脚为美的扭曲审美观把女性囚禁在闺阁之中。封建礼教下的女性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社会要求,终身生活在男性的权力之下。在婚姻中女性没有任何自主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女性盲目地踏进未知的婚姻生活,从此承担起起照顾丈夫、伺候公婆、生儿育女的责任。男性被允许三妻四妾,女性则被“守贞”束缚。可见,无论是在奴隶制度已废的美国还是封建制度已被推翻的中国,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依然处在从属地位,她们对周围环境所产生的极端心理变化值得探究。
二、女性意识完全缺失——佩科拉与姑爸
佩科拉是《最蓝的眼睛》中的主人公,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黑人家庭。由于比其他黑人肤色更黑,佩科拉在学校里备受同学和老师的歧视与欺凌。在家中,母亲一心向往白人的世界,行为举止都以白人为榜样,与丈夫水火不容,对孩子漠不关心,甚至在女儿佩科拉打破白人雇主家的盘子时,她第一时间安慰白人的小女孩,却狠狠给了自己女儿一耳光。在她所生活的黑人社区中,白皮肤蓝眼睛才被认为是美丽。深感自己不被他人接受与不被爱的佩科拉认为,如果自己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那么大家就会像喜欢秀兰·邓波儿一样喜欢自己。父母就不会再打架,因为他们“mustn’t do bad things in front of those pretty eyes.”[4](不能在这样一双漂亮的眼睛前作坏事)于是,在父母打斗的时候,她向上帝祈祷一双蓝色的眼睛;在被亲生父亲强奸怀孕后,她来到Soaphead教堂向牧师祈祷一双蓝色的眼睛;在孩子早产夭折后的精神崩溃中,她陷入了自己拥有一双蓝色眼睛的病态臆想中。11岁的佩科拉只是一个孩子,在成人社会的审美观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白为美”的主流文化否定了黑人的自我价值,使得佩科拉在被排挤的社会中最终迷失自我,妄图通过改变身份赢得接纳。莫里森曾在谈到《最蓝的眼睛》的写作动机时说:“I try to show a little girl as a total and complete victim of whatever was around her.”(我想要描写一个女孩,把她作为周围环境的祭品)确实,佩科拉代表了白人主流文化与男权思想统治下被牺牲的黑人女性。
在《玫瑰门》中,姑爸其实是司琦纹的小姑子,她在作品中完全是一个男性形象。不仅如此,她和几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却最终被封建礼教吞噬。究其原因,姑爸把自己不幸的婚姻生活归咎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想摆脱这样的低贱身份而成为一个男人。
佩科拉和姑爸都是社会主流文化下的牺牲品,她们想要通过改变自己的特质来迎合主流文化,“这是一种没有真正自我的意识,而仅仅是通过另一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这是双重意识,一种总是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用另一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女性意识的丧失带来的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缺失是造成她们悲剧的主要原因。
三、女性意识恶意爆发——秀拉与司琦纹
莫里森的小说《秀拉》是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秀拉生活在一个没有男性的家庭中,祖母夏娃在生活中处处偏袒男性,敦促社区里的女人要好好伺候自己的男人。母亲汉娜要求与男人平等的性爱关系。受够了祖母对男人的谄媚,同时受母亲对性爱态度的影响,秀拉成长为黑人社区中离经叛道的异类。“她尽量多地和男人睡觉”[5],甚至勾引好朋友的丈夫。但是一旦把男人弄到手,只一次便把他们丢弃。秀拉用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对待身边的男人,把男女关系看作一种简单的性关系,无关情爱。因为“她发现,[男人只是]一个情人并不是一个同志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她以反传统、反道德的勇气,冲破社会对女性的枷锁,无所顾忌地挑战男权中心,即使受到社区黑人的指指点点,也不曾改变自己的行为。她对祖母说:“我不想造就什么人。我只想造就我自己。”[6]然而秀拉忽视了一点:她不仅是女人,同样是社会人。她反抗白人主流文化和传统家庭观念,却拒绝与社区同胞交流,把自己隔绝在集体之外。这种极端的女性意识造成了秀拉的悲剧,她一方面认为“我确实在这世界上生活过……我有自己的头脑,也有自己该想的事,也就是说,我有我自己”;一方面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儿时伙伴,希望得到她的原谅,却最终孤单地死去。正如黑人领袖杜波依斯所言,“把自己的双重自我融入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自我。”这个双重自我在秀拉的身上就体现为作为女人和作为美国人的双重身份。
《玫瑰门》中的司琦纹是怀着对美好婚姻的憧憬嫁入庄家的,婚后她恪守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克尽为人媳、为人妻的职责,在家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在外面处理庄家大大小小的事物,多次挽救庄家于危难之中。但她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夫家的认可,公婆认为庄家的灾难是她的不祥造成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对她百般羞辱,把自己不能得到心上人的怨恨发泄在她的身上,婚后不仅常年漠视、嘲讽她,更甚至到处寻花问柳,对她不闻不问。女权主义代表人物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她[女性]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男性]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7]为了获得“贤妻良母”的身份认同,她带着一双儿女到扬州寻夫,幻想丈夫看在孩子的份上回心转意。但是丈夫却在妓院与她亲热,令她染上梅毒,儿子也在回家途中生病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早夭。这一次“扬州寻夫”彻底摧毁了司琦纹的生活,使她的女性意识渐渐觉醒。回到庄家后,“在毒水里浸泡过的司绮纹如同浸润着毒汁的粟栗花在庄家盛开着”[8]。她用自己的身体征服道貌岸然的公公,从“变性”的小姑姑爸那里获得性欲宣泄。她用乱伦与强奸冲破封建男权统治,用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把家庭中的男性变为自己的性欲奴隶,成为庄家真正的一家之主,颠覆了男性的主体地位。但是扭曲、异常的心理使得她的女性意识恶意爆发,突破了人类的基本伦理道德底线,最终堕入悲剧的深渊。秀拉和司琦纹都是挑战男性话语权的反叛者,她们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冲破道德对女性的枷锁,挑战男性的权威。她们身上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极端的反叛缺乏真正彻底的自我认知,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斗争。
四、结语
托尼·莫里森和铁凝作为中美文学领域中为女性呐喊的代表人物,处在不同的文化与制度下,但同样用女性的视角观察女性、书写女性、思考女性的命运。作为社会存在,处在“他者”地位的女性急需独立的女性意识维护自己的人权,但是必须区别避免罔顾作为社会人的基本伦理道德的极端女性意识爆发。彻底地丧失自我与恶意地释放自我都是健康女性意识的障碍,也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她们用冷静克制的态度,反思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中所面临的自身问题,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法,反映女性在寻求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的自我障碍,对女性自身问题的内省和女性意识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杨金才.托尼·莫里森在中国的批评与接受[J].外国文学研究,2011(4):55-56.
[2]托妮·莫里森.宠儿·前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罗婷.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嬗变——从《方舟》、《玫瑰门》到《紫藤花》[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1998(2):86-90.
[4]Morrison,Toni.TheBluestEye[M].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2007.
[5]蒋欣欣.认同反抗超越[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3):126.
[6]托妮·莫瑞森.秀拉[M].胡允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8]铁凝.玫瑰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AComparativeAnalysisofFeministConsciousnessinNovelsofToniMorrisonandTieNing
ZHU 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The thesis employing parallel method i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and an approach of feminism, conducts a comparison in the light of a lack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a hostile outlet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TheBluestEyeandSulaby Toni Morrison, an African American author, andGateofRosesby Tie Ning, a Chinese contemporary author, which illustrates that an extrem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does damage to a healthy feminist consciousness.
Toni Morrison; Tie Ning; feminism;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106.4
A
2095-7602(2017)09-0100-03
2017-06-08
朱林(1983- ),女,讲师,硕士,从事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