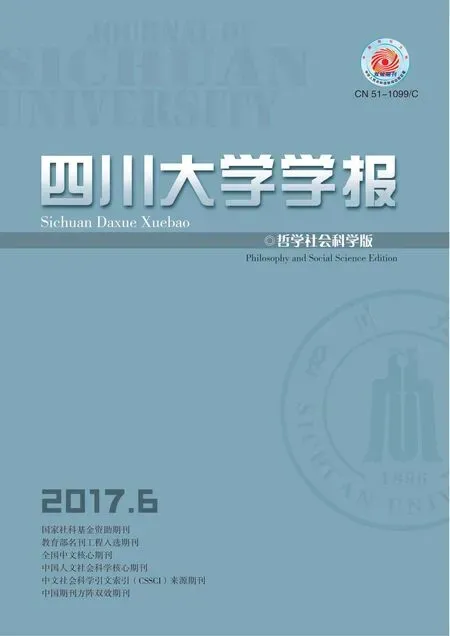多元社会的政治对话与权力合法性
顾 肃
§政治哲学研究§本栏目特约主持人:顾肃
专栏导语:政治哲学是哲学研究中一个相当热门的学科。它研究公共生活的政治领域规范性的哲学问题,探讨权力、国家、正义、平等、自由、权利等核心概念,并对其进行哲学的分析、论证和概括。它也讨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探究政权合法性的道义基础。因此,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的,即探讨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由此而进行的论证,特别是以伦理理论为基本出发点的证成便显得十分重要。政治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促进良好政治体制的构建,推动社会的进步。
本专栏本期共发表三篇研究当代政治哲学的论文,分别讨论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阿克曼和霍耐特等人的重要理论。《多元社会的政治对话与权力合法性》一文探讨了多元社会的共识基础、稳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的问题。文章总结了阿克曼的相关论述,人们通过政治对话求同存异,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以证成权力的合法性;论述了对话的一些根本要求和需要避免的策略,突出了约束对话的合理性、一致性和中立性的原则,通过以理服人和逻辑自洽来论证资源分配的正当性。这些中立的政治对话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和社群内部,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建筑术》一文讨论了罗尔斯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它所使用的方法试图解决早期所不能解决的公共证成的难题,以及实现学说的自主并获得客观性。罗尔斯的建构目标是一个自由站立的、扮演公共角色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过程的完成标准是获得反思平衡,这也为多元社会中学说的自主提供了范例。《作为正义的肯认与自我的分隔》一文探讨关于正义目的的思考之两种进路,即二元论式与一元论式的进路。它所重点讨论的一元论的进路将人的伦理生活看作整体,从而将肯认视作正义的唯一目的,把经济领域的公平与否视为肯认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文章强调霍耐特的一元进路中存在着某种二元倾向,即人们在道德和伦理两个领域分别获得认同。这些前沿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政治哲学核心观念和方法论的认知,强化其规范性的道义证成。
多元社会的政治对话与权力合法性
顾 肃
在现代多元社会,不同政治派别、群体持有不同的广包学说,共存于一个社会,其稳定性的基础是建立在公共理性上的超越具体善观念的重叠共识。阿克曼认为,达成共识的必要方式是政治对话,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以证成权力的合法性,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对话的根本要求是超越各方所信奉的道德真理和价值的中立性,因而需要避免直觉主义和内心独白式的思维方式,还要防止预设一种所有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来压倒对手的“优胜策略”,和要求把不同观点转换成一个经过特别处理的评估框架的“转换策略”。约束对话的原则是合理性、一致性和中立性,通过以理服人和逻辑自洽来说明自己在分配资源上的正当性。对话的中立性并不意味着无是非观的道德相对主义,而是体现了正当对善的优先性,而各方共同持有的正当性观念才是对话得以开展的根本保障。中立的政治对话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和社群内部,也适用于国际社会。
政治对话;合理性;中立性;权力合法性;阿克曼
在现代的多元社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各个群体,不同的政治派别、社会集团持有不同的广包学说、价值观和信仰,却又共处于一个社会当中。这些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权力合法性,才能巩固其权力的道义基础,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实现合法的统治。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相关论述,其中重要的是强调坚持中立的立场,通过政治对话达成重叠共识,并提出了约束对话的基本原则。这些论述对于当今多元社会如何处理价值观的分歧,实现权力合法性,促进社会稳定,具有借鉴意义。
价值冲突中如何达成重叠共识
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表现为不同群体和个人间价值的不一致性,有时候甚至存在严重的冲突。比如,政治思想上的左与右,在涉及社会政治体制安排的许多问题上存在价值的冲突,弱势群体争取自身权利和得到同等对待的呐喊和抗争需要主流社会的积极回应。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各种文化自身的特点和差异,要求不同的族群和文化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和承认,这涉及种族、性别、阶级、语言、教育、宗教、性倾向和残疾人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对于那些传统上的弱势文化和族群来说,由于他们缺少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更需要得到承认和平等对待,甚至需要通过积极行动计划给予必要的照顾,以扩大和完善社会福利。然而,由于社会强势群体或主流族群的存在和持久的影响力,对弱势文化和族群的承认和平等对待一直是一个事关社会正义的问题。今天,难民和移民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美国的总统大选和欧洲的议会选举,经常因为这一议题而造成族群对立,挑起冲突。
由此来看国际关系,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价值冲突同样难以避免,甚至比一国内的不同族群间的冲突更加严重。东方与西方,弱国与强国、穷国与富国,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经常是各说各话,互不理解,甚至相互指责埋怨。比如,穷国说富国掠夺自己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这种剥削是不正义的,富国则说穷国自己的社会体制存在问题,尤其是不民主的体制所带来的政府腐败,加上一些人的懒惰,才是其致穷的根源。东方社会的一些人批评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不关注人伦亲情和集体价值,导致了其唯利是图的道德沦丧;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则批评东方集体主义导向和宗法等级体制,是东方专制主义长期存在、民主制度难以立足的根源。于是,双方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和攻讦也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在许多问题上,这种观念上的冲突长期存在,如此莫衷一是,难以沟通。
面对这样的多元价值冲突,人们之间是否存在达成一致、实现社会稳定的途径?政治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论述,以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多元文化主义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是:在承认多种文化和族群生活方式的时候,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性?是否存在合理的方式来化解这些冲突?在多元民主社会,不仅存在宗教、哲学和道德等广包学说的多元化,而且还存在那些不相容却合乎情理的广包学说的多元化现象。这些学说没有一个是公民普遍认可的,谁也不能预期在近期的将来,其中的一个学说能够得到全体或接近全体公民的认可。正如罗尔斯所明确指出的,“政治自由主义断言,出于政治目的,合理但不相容的广包学说的多元化是在宪政民主体制下自由制度的构架内行使人类理性的正常结果。政治自由主义还断言,合乎理性的广包学说并不排斥民主体制的实质。当然,一个社会也可能包含不合理、非理性甚至疯狂的广包学说。”*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pp.xvi-xvii.
罗尔斯认为,只有在政治的领域内,一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对合乎情理的所有其他人才是可辩护的。因此,文化、道德和传统的问题都包含在对正义的合理说明之中;自由的政治思想只需要接受现代世界特别是其自由政体的不可消除的多元性。鉴于民主文化合乎理性的多元化的事实,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揭示公众为基本政治问题作辩护的合理基础之可能性条件。如果可能,它应当规定这一基础的内容,并说明它为什么是可接受的。为此,就必须把公共观点与许多非公共的观点区别开来,并解释公共理性何以采取目前的形式。而且,它必须在合乎情理的广包学说之间保持不偏不倚。这里就提出了所谓政治中立性的核心论题。这种中立性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示。比如,政治自由主义不抨击或批判任何合乎情理的观点。这包括它不批判、更不排斥有关道德判断真理性的任何特定的理论。它只是断言这种真理性的判断是从某个广包的道德学说的观点得出的。在考虑了所有事情之后,决定哪些道德判断是真理,这并不是政治自由主义所承担的任务。政治自由主义与真理观念不相干,因为真理观念无论如何都要定出一种学说的是与非,即便是相对意义上的是与非,而政治自由主义考虑的是各种对立的、不相容的广包学说何以共存于一个民主社会的现实政治问题,因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定出谁是谁非。
各种广包学说由其各自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构成,对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观念,包括所认肯的生活方式,持有各自的标准和信念,难以强求统一的尺度。但是,文化多元主义的要求并不必然意味着道德相对主义,即不同的文化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基础。比如,东方的儒家伦理与西方的基督教的道德,是否完全不存在共同的因素。道德相对主义主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认为不存在共同的道德价值。但这里存在重要的误区,即不可否认少数普遍的价值观,共同的道德律,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普遍道德,几乎在世界主要的道德论述中都有类似的表述。道德黄金律的普遍性,即足以挑战道德相对主义。社会稳定性的基础即在于人们的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
那么,基于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重叠共识可以是少数普遍的共同价值观,通常这是由直觉来把握的。重叠共识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正义的观念,但是,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正义的观念和公正的制度安排。按照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正义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其产生的机制应是一种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初状态。自主的个人在不知道各自背景的原初状态下通过社会契约选择了正义的原则。也就是从康德以自主人格的价值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和程序性的道德哲学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这些正义原则是可以通过受到某些程序规则约束的集体选择模式确定下来的。也就是说,正义原则的选择并不是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之间对话的结果。这是正当性的第一条路径,即道德建构主义的路径。
达成重叠共识实现正义观念的第二条路径,即诉诸经验的对话的路径。人们通过公开的对话、批判的交流达成共识。这是行动的哲学达成共识的路径。著名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和卡尔· 奥托·阿佩尔提出了程序性的对话模式,把规范的辩护理解为一种公共的对话。阿佩尔把在这种对话情境中受到尊重的程序约束称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哈贝马斯则称之为“理想的对话情境”模式,认为理想的对话情形是合理的正义产生的分析机制。*参见Jurgen Harbamas, “Wahrheistheorien”, in Wirklichkeit und Reflexion, edited by H. Fabrenbach, Pfllingen: Neske, 1973; Karl-Otto Apel, 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and Paul, 1980, pp.225-301.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布鲁斯·阿克曼则从权宜之计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论述了对话机制。他把自由主义理解成一种谈论权力的方式,理解为一种以某些对话约束为基础的公共对话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通过理性的对话来寻求共同点,达成共识。在阿克曼看来,为权力而斗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只要人还活着,就无法避免。当实际权力增加时,一个充满诱惑的前景就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权力会腐蚀人,增加权力自然会受到质疑。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如此普遍,以致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以回应质疑。“当一个人行使的任何权力给任何人带来不利而遭受质疑时,他都应当准备回答合法性的问题。”*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董玉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5页。因而必须通过广泛的政治对话来为权力的合法性作辩护。这种对话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和约束。其中最重要的对话约束是中立性原则。阿克曼的自由主义对话的理想详尽阐述了正当性的一种程序性的公共商谈。
通向中立性的错误方式
政治对话对于权力合法性是重要的,但实际的政治生活并不可能是以对话寻求道德真理的论坛,那为什么坚持认为政治对话对于政治是尤为重要的呢?阿克曼对此的回答是:“因为还有比道德真理更重要的其他事情需要讨论:特别是,那些在道德真理上意见不同的人如何合理地解决他们当前的共同生存的问题。而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者典型地就是以这种方式表述政治秩序问题的……换句话说,我并不想把我支持公共对话的理由建立在道德生活的一些据说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之上,而是要建立在自由主义者看待公共秩序方式之上。”*阿克曼:《为何要对话?》,载应奇等编:《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也就是说,公共政治对话的基础不是寻求道德生活的普遍性特点,而是解决公共秩序的问题,也就是共同生存的问题,同时又与权力合法性问题相关。
阿克曼以自由政体的简单模型来说明政治对话的重要性。假设该模型由N个初级团体组成,每个团体由一名或多名成员组成,他们在寻求道德真理时把信仰与理性相结合。同一个团体的成员对道德问题提出了相同的答案,不同团体的成员则有着不同的答案。虽然如此,他们发觉自己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由于资源稀缺而始终面临着潜在的冲突。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不同的团体如何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来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多元社会的重叠共识何以实现,以完成共同生存这个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此而突显对话对于成功解决这个问题之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团体都可以单方面宣布自己的道德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并且授权政府官员通过参考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来解决所有的冲突。假如所有团体持有的道德真理是一致的,那就没有必要为了就合法政府的目标达成妥协而相互对话。但问题恰恰在于,正是因为某个团体的道德反思者P有理由知道他团体之外的人即非P并没有得出与他相同的道德结论,对话才迫在眉睫。尽管道德真理只有一个,但通向道德谬误的道路却有无数条。“正是由于P相信自己最接近真理,他对于非P所知道的就是,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他们每个人都采取了无数条错误的道路之一。”*阿克曼:《为何要对话?》,第56页。究竟是哪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解决自由主义者关于共同生存的问题至关重要。这完全取决于非P犯下的特定道德错误,取决于这些“谬误”与P和非P共同生存于一个星球上就必须解决的争议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此,P只有一种方法发现情况究竟如何,这就是与非P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
作为自由国家的一名参与者,自由的公民有义务进行这样的对话。在这种对话实践的过程中,P并不是试图说服非P改变他们的想法,并最终看到P所持的才是令人信服的真理。相反,这种对话的一个更实际的意图,就是承认至少在目前阶段,P或者非P都没有打算赢得道德争论以便让他人满意,而且,尽管存在这种分歧,他们都没有思考以何种方式共同生存的问题。恰恰是因为自由的国家不以道德真理为目标,其公民才必须认识到自己有这种绝对的对话义务。阿克曼将此称为最高的实用命令:如果我和你关于道德真理的意见不一致,那么,唯一能使我们有机会以双方都认为合理的方式解决共同生存问题的方法就是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阿克曼:《为何要对话?》,第57页。
那么,如何与那些在道德真理上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交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自由国家的公民必须学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他人交谈,“这种交谈的方式应该能够使他们每个人都决不把他人的个人道德谴责为邪恶的或错误的。否则,对话的实用意义就丧失了。”*阿克曼:《为何要对话?》,第59页。阿克曼坚持认为,政治对话需要坚持中立性的原则,即不纠缠于论证或让人接受具体的道德真理,而是坚守中立的态度,这样对话才能富有成效。为此,他指出需要超越妨碍对话的两种思维方式,一是直觉主义,二是内心独白。
直觉主义思维有其原初的吸引力和独特的尝试,但仍然是存在缺陷的思维方式。直觉是一个重要的向导,但政治判断如果依靠直觉,也会出错。每个人的政治观点或偏见,都源自出生以后的前人所述,而每次改变都是因为某些特殊的人生经验。由于自由国家的人们成见多种多样,“伟大的直觉主义作家会将各种直觉观点摆在我们面前。毫不奇怪,英国人善于将存在的各种自由主义成见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面对直觉的偏颇,“只有通过对话过程掌控我们的直觉,我们才能确保我们最强烈的情绪不只是社会教化的阴暗情绪形式。”“只有理性对话,而不是我直觉的深刻性,才能证明我自己享受的权力主张是合法的。”*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第362、353、367页。
内心独白式的思维也是需要避免的。内心独白,也就是自说自话,即只讲自己的价值观和理由,而不顾他人的价值观和理由。一个人只从各自认同的领域出发,提出经过自己理性抽象形成的看法,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和所持的理据,就会形成自说自话的思维习惯。阿克曼指出,这是通向合法性问题的演绎主义的策略,即认为政治哲学的第一原则是真正次要的原则,它是从哲学话语的某些“更高级”的领域得出的结论演绎出来的。也就是主张政治哲学的原则是由哲学的更高级的结论推导出来的。比如像柏拉图那样,一旦回答了有关真、美、善等问题的本质,就可以很容易地回答对合法性的质疑。*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第368页。这种演绎主义的思维同样不利于有关合法性的政治对话。
阿克曼还指出了需要避免的通向中立性道路上经常出现的错误做法。
一、优胜策略。这种通向中立性的错误做法是说,尽管所有人在许多价值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需要力图离析出一种所有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通过集中关注这种最高价值的政治效应,也许所有人都能以大家认为合理的方式谈论我们是如何解决共同生存问题的。阿克曼之所以将此称为“优胜策略”,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设定一个大家都承认作为中立政治对话基础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来克服基本的道德分歧。但在实际上,这样所有人都接受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并不容易找到。比如霍布斯式的自我保存原则,看起来也很难让所有人都接受为惟一的至上原则。*阿克曼:《为何要对话?》,第59-60页。
二、转换策略。这种错误做法不是试图要求认可一个凌驾于所有次要道德分歧之上的最高价值,而是要求把不同观点转换成一个经过特别处理的评估框架,以此来消除这些不同观点中不中立的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功利主义者边沁关于幸福的计算方法,它建立在一个“针戏和诗歌一样好”的看似中立的原则之上,即把各种给人带来快乐的元素转化成一种幸福的指标,可以进行总量的计算。一旦公民们学会把他们的分歧转换成效用的公分母,就可以进行对话,以一种专家政治的方式讨论他们之间的冲突,它不要求任何人说出与自己的基本道德信念相悖的话。*阿克曼:《为何要对话?》,第60页。功利的计算看起来具有中立性,但计算功利份额的标准并未在不同的群体间形成共识,因而排除了多元化计算标准的可能性。在实际上,这种转换策略并不成功。
总结这些通向中立性道路的错误方式,主要表现在仍然预设了自己所接受的道德真理或看似中立的计算方式,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中立性。或者以至善论确定了自己认可的最高价值,并且以此来强加于人,认为这是共同接受的最高价值。或者以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立场作为大前提演绎出政治哲学的原则,要求政治哲学服从于抽象的哲学大前提。或者以所谓转换策略自认为可以把人们的偏好都转换成中性的功利计算,通过确定幸福总量的比较来决定伦理原则。这些看似中立的做法之所以不成功,主要问题是预设了自己所接受的价值观或转换方法,没有真正站在中立的理性的立场参与公共的政治对话。
约束对话的中立性原则
在批评了通向中立性对话的一些错误的思维方式和策略之后,阿克曼提出了以中立价值作为克服这些错误思维方式的对策,要求对话的参与者以中立作为约束的准则,阐述了对话的约束条件和需要遵循的原则。
在阿克曼看来,这样中立性的对话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其政治建构的过程是这样进行的。“在对话中,当他人挑战我们的基本权利地位的合法性时,我们每个人必须在原则上做好准备去向他人证明它的正当性。这里的基本理念是:如果我不能向他人解释为何我拥有我所拥有的权力是正当的,那么,我就不应该拥有它。我们对话的界限应该界定我的权力范围。”*阿克曼:《中立性种种》,载应奇等编:《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6页。对于对话的辩护因其世俗的目标和承诺,并不依赖某些神秘的本体自我的无负担的优先性。我们因为与他人争夺权力而负有重担。对这种重担作出反应的问题在于,是准备与同类就规范权力斗争的最好方法进行讨论,还是力图用压倒性的力量让他们闭嘴?
显然,不应该用压服的方法,而是展开公开的政治对话,这就需要把中立性引入对话。为了证明每个人获得的有关规范的特定主张的正当性,任何公民都不应该声称:(1)自己对良善生活的理想值得政治共同体的特别认可,因为他的理想优越于其他人的理想,或者(2)依照独立于他所肯定的特殊理想的根据,他值得特定的群体肯认他在本质上优越于其他公民。“在这两方面受到限制的一种政治谈话在以下两个意义上是中立的——它拒绝表达公民之间或他们的善理想之间的一种原则性的公共偏好。”*阿克曼:《中立性种种》,第77页。中立的对话需要寻求的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元素,而不是将自己所坚信的道德真理和信念强加于人。
阿克曼阐述了以中立价值为准则的约束性对话的合法性模式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合理性、一致性和中立性原则。通过这三项原则的约束,公民们将在政治对话过程中达到更大的社群。“中立性让像城邦一样的社群在与群体外的局外人相处时听到一个声音,这些局外人将不可避免地挑战其被遗弃者的地位。通过重视对话优先性的自由原则,社群边界两边的人们能够以自尊的基调继续相互商谈。他们暂且把其根本的分歧搁置一边,可以通过受约束的对话来构建更大的政治社群。”*Bruce Ackerman, “What is Neutral about Neutrality?” Ethics, Vol.93, No.2, Jan. 1983, p.375.
第一个原则是合理性。它要求“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质疑其他人的权力合法性时,权力持有者都不应通过压制质疑者来回答,而应给出一个解释为什么他比质疑者更有权利获得该资源的理由。”这就是要言之有理,不是压制质疑者,而是耐心解释自己更有权利获得资源的理由。一些人获得其他人想要的东西,并非仅仅凭借所有权制度和政府机构这些手段,也不只是凭借所谓话语的权力,而是解释和说服,随时准备回答合法性的问题。合理性原则假定权利只有在人们面对稀缺的基本事实,并开始讨论它的规范性含义之后才具有一种现实性。权利对话的前提是,规制权力之争是通过一种既定文化行为模式来确定的,对合法性质疑的回应是通过竭力证明其正当性来进行的。*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第4、5-6页。这就是说,合理性原则对话诉诸理性的解释和说服。
合法性模式的第二个原则是一致性,也就是“同等情况应该得到同等对待”。权力持有者在某个时刻提出的理由,未必与他提出的证明其他权力诉求合法性的理由相一致,因而需要坚持一致性原则,以便能够说服人,也就是所坚持的权力合法性的理据必须普遍一致,而不是因人因时而异。比如,权力持有者不能一边以“因为雅利安人优于犹太人”来证明他对X主张的合法性,然后又用“所有人都生而平等”的宣言去证明他对Y主张的合法性。这就是用以证明的理据的不一致,缺少自洽的说服力。*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第7页。
合法性模式的第三个原则是中立性。受约束的对话需要坚持中立原则,即不偏向某些道德真理或理论。自由主义反对家长式的统治,无人有权维持这样的政治权威,即主张具有洞察他人所否定的道德领域的特权。“如果一种权力结构只能通过某些人(或群体)断言他(或他们)具有特权式道德权威的对话来证明它的正当性,那么这种权力结构就是不合法的。”阿克曼指出,如果权力持有人基于某个理由而宣称以下两点,那这个理由就不是正当的理由:(a)他的正当性概念比其他任何同胞的都要好;(b)不管他的正当性概念如何,他天生就优于其他一个或多个同胞。这样的预设前提就违反了中立性原则,即以他自己的正当性概念比他人的优越或者他自己优于他人自居,居高临下地参与对话,就无法保证人们之间平等的尊重这个基本的前提。这种中立性原则的理据在于,从认知上说,每个人对美好生活都有自己的观点,无人能知道优于其他任何善的概念的看法。其结果,任何断言他或他的目标具有内在优越性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第11页。
关于对话约束的这些原则特别是中立性原则,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论证。正如阿克曼所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原则为自由国家提供了合理性的首要原则,这就是坚持当每位公民被任何由于其统治权而处于劣势的人质疑的时候,都要准备好给出自己所处权力地位各个方面的理由。对那些处于弱势的群体,尤其需要权力持有人讲出自己所处地位的合理的理由。“事实上,这正是中立性对话的重点:允许每位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且无需要求他让同伴相信自己个人的善是符合共同利益的。”因此,他可以对一些或所有同伴彻底隐瞒自己对善的定义。“只要他回答说‘我应该得到X,因为我至少和你们一样好’,其他人就无权刺探他的思想或精神的隐秘体验。这并不是说,一旦摆脱法律强制的约束,公民们就没法相互讨论生命的终极意义。相反,一旦公民们再也无需向真、善、美的官僚主义守卫者证明自己每种表达形式的合法性,多元化的当代文化形式促发了集体谈话的广泛性和生命力。”*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第384页。
阿克曼还论述了对话得以进行的其他条件,如参与者具有公民资格,以及拥有共同的语言,这样才能够相互理解,而不是各说各话。参与对话的人们首先需要相互平等的尊重,而不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以势压人。这种自由的对话的核心是为实现一个世界定下基调: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使用自己合法的初始禀赋。“只要初始禀赋的分配是建立在中立性对话的基础之上,那么每位公民要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合法的,就只需要告诉每个人:‘虽然你认为我应该以追求其他一些好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一生,我还是不能同意。而且,我拒绝承认你有权说我是错的。因为我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和你的一样好。’”*阿克曼:《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第188页。
总的来看,阿克曼关于政治对话的论述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所表达的多元文化当中坚持中立性,保障广包学说和善观念的多样性,通过肯定重叠共识来实现社会稳定性的观点,是一致的,体现了自康德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正当优先于善”的基本精神。其立足点是公共理性,相信公民们通过诉诸理性达成相互理解,实现政治共识。只是阿克曼侧重于探求可行的实现途径,即通过坚持中立的政治对话来应对多元社会的观点分歧。
以上的分析给我们处理当代多元社会的意见分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些论述基本上是针对自由国家内部的政治对话,但这些中立对话的原则并不只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也可以推广到国际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间,尽管存在大的差异,包括文化上的差别,道德真理的分歧,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还有政治体制和司法习惯上的不同,但为了和平共处于一个世界,仍然需要进行平等的政治对话。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是惟一正确的优越的价值和道德真理,以优胜策略压制对手,强加于人。也不应该以自身的身份地位的优越性作为前提,在对话中预设居高临下的立足点,以最终让对方接受自己的道德真理为目标。尤其是面对道德真理的分歧,只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无论哪一方,为了证明自己在资源利用上的权力合法性,就需要通过对话合理地解释和说服他方,摆明理据,讲清道理。这在对待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上的分歧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当今世界,因为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冲突,相当严重和广泛,如今相当普遍的难民和移民与本国现有居民间的冲突,成了影响各国政治和族群矛盾的重要议题。各方均预设了自己的道德真理和生活方式是最优越的神圣的,从本质上要求他人服从自己的真理,因而出现没完没了的摩擦和纷争。重要的是坚持中立性价值,以平等的政治对话、同情的理解、合理的说服来解决纠纷。在说理时必须坚持自洽一致,所依据的原理应当普遍一致,对己对人使用同样的准则,而不可以采取多重标准,因时因地而异。
与此相关的是话语权的问题。批判理论中经常使用“话语霸权”这个概念,说的是权力持有者习惯使用一种主导的话语,以致在讨论问题和对话时明里暗里预设此话语为主导和标准,加诸各方,忽视非主流话语的价值。于是,批判话语霸权就成了一些人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头禅。他们以一贯的弱者、被压迫者、被忽视者的面目出现,要求为自己被欺负的历史伸张正义。但是,他们用以对抗话语霸权的方式经常是为反对而反对,自己建构起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与原来的话语霸权针锋相对,凡是对方反对的,我就拥护,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如此对抗的方式不是对话,而只是内心独白,自说自话。这里并不存在理性的政治对话,而是完全另起炉灶,本质上是要建立自己新的话语霸权,以此来代替旧的霸权。由于不承认共同点,尤其是一些基本的普遍的原则,因而言谈就缺少合理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同样无法说服人。完全没有共同点的交谈不是对话,而是简单的排斥。因此,对话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坚持合理性、一致性和中立性。需要建立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原则和共同逻辑上,承认各方共同接受的最普遍的游戏规则和正当性,由此展开对话,互通信息,设身处地地思考,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解,以理服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立性的对话要求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道德真理强加于人,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共同的普遍的原则。避免道德相对主义的前提是承认正当优先于善这一最高原则,即普遍的正当性要求是统摄对话的基础。这里的正当性就是那些像公理一样处理人际关系最普遍的原则,比如平等的尊重,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平等对待和相互尊重,对公民权利的普遍认可,尊重公民基本的自由权利,推己及人的道德原则。可以就各方在尊重人权、平等、自由等基本正当性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展开批评对话,但不能完全不承认人权、平等、自由权利这些基本观念,或者用一些限定语将这些变成了实际上只有个性而无共性的观念。权力的合法性也应建立在围绕这些普遍观念的对话的基础上。中立性要求超越具体的道德真理或广包学说的信念,但不可放弃像公理一样的普遍正当性原则。面对具体道德信念的分歧,全民的和解和融合也需要以中立的对话为基础,为了共同的正当性原则通过对话来巩固权力的合法性。
(责任编辑:曹玉华)
PoliticalDialogueandLegitimacyofPowerinaPluralSociety
Gu Su
In a modern plural society, with various political factions and groups co-existing in a community, its basis of stability is overlapping consensus that transcends concrete conceptions of the good. Bruce Ackerman holds that a necessary way of reaching consensus is political dialogue through which we seek common grounds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justify legitimacy of power and facilitate co-existenc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dialogue include going beyond moral truths held by different parties and insisting in neutrality of values; therefore, we need to avoid thinking in an intuitionist and monologue way, presupposing any “superior strategy” to overwhelm opponents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s held by all, and using “conversion strategy” to convert different viewpoints into a specifically dealt framework of valuation. The principles to govern dialogue are rationality, consistency and neutrality, accounting for justice in distributing resources by convincing people with reasoning and logical consistency. Neutrality of dialogue does not mean moral relativism without a view on right or wrong; it embodies the priority of right over good, and the justice conception held by all parties is a guarantee for a dialogue to carry on. The principle of neutral political dialogue applies not only to a national society but also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olitical dialogue, rationality, neutrality, legitimacy of power, Bruce Ackerman
顾肃,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南京 2100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政治哲学平等正义理论研究”(17BZX082)
D0-02,B561.5
A
1006-0766(2017)06-008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