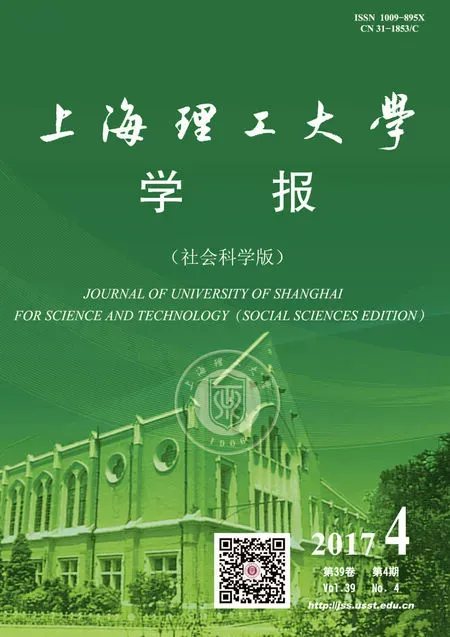语言、爱欲与诗
——但丁语言诗学管窥
王彦华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语言、爱欲与诗
——但丁语言诗学管窥
王彦华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语言与诗的内在关系是但丁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关系奠基于哲学-神学爱欲观。按照这种爱欲观,诗歌的源泉和本质是爱的启悟与运动;作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语言本身和诗歌一样,有着属于它自己的爱欲和爱欲运动。语言和诗的爱欲运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由上而下的爱欲运动和由下而上的爱欲运动。正是在爱欲和爱欲运动的基础上,语言和诗在《神曲》中被内在地关联起来了。《神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诗与语言的爱欲运动;但丁诗学是一种“爱欲诗学”。
语言;爱欲;诗;爱欲运动;《神曲》
众所周知,中世纪最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是用意大利俗语,而不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学语言——拉丁语写成的。但丁的这一选择当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事实上他明确地主张:“那些最伟大的主题似乎应该用最好的方式,因此也就是说,应该用最伟大的俗语加以处理。”[1]而但丁的《论俗语》既是一部语言学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诗学论著。正因为如此,诗与语言的关系向来就是但丁诗学研究史上一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课题。我国学者缪朗山认为,但丁选用俗语来创作《神曲》旨在开创意大利民族语言文学[2]。德国当代文学史专家埃克里·奥尔巴赫则认为,但丁此举意在创造一个读者群[3]。这两种解释均未触及语言与诗歌在但丁诗学中的内在关联。本文试图探讨但丁诗学中诗与语言的内在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所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
一、诗与爱欲
“爱欲”(Love / Eros)原本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植根于人的灵魂的对于真、善、美的不断渴望,是一种具有超越指向的欲望和能力。后来,这个主要用于描述人的灵魂和自我的概念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提升到宇宙观的层面,并且在中世纪进一步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但丁深受这种富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神学爱欲观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爱欲观。而正是这种爱欲观,为但丁的诗学思想和语言观提供了哲学基础。
在但丁看来,上帝不仅是万有之源、万动之源,而且本身就是“爱”。“太初的大能非言语可以说明。/他和圣子恒在散发着大爱。/他怀着大爱,于凝望圣子的俄顷/井然创造了万物,使它们存在/运行于心间或空间。”[4]129上帝的创世活动,本质上是大爱的流溢。在爱的流溢中,上帝不仅创造了无限的精神存在物,而且将爱扩展到不死的和有死的事物上,将存在的现实性从它的根基处依据等级向下传递到所有具有潜能的各层次。因此,“无论朽或不朽,宇宙万物/都只是一个理念所放的光彩。/该理念,是充满大爱的天父所出。”[4]175反过来说,宇宙万物无不来自神性,无不根据它与上帝的距离,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神的本质。上帝之爱不单是宇宙万物存在和持存的终极根据,也是贯穿整个宇宙的组织原则,正是由于渗透于宇宙各个部分之中的爱,整个宇宙才被聚合在一起并形成为一种秩序。
作为上帝之爱的有限流溢物,宇宙万物全都禀有一种由上帝赋予的爱,即先天之爱。“先天的爱心绝对不会有乖偏”[5]238,也就是说,万物皆有回归本源、趋赴至善的倾向,或者说,都有爱上帝的能力和倾向。人和其他受造物一样禀有先天之爱,但不同于其他受造物的是,人还具有后天之爱。因为在万物之中,除了天使,唯独人被上帝赋予了自由意志。人从其自由意志生发出来的爱欲,就是后天之爱。后天之爱意味着,爱欲的对象和爱的程度,都是由人自身自由地选择的。因此,“后天的爱心却会有舛讹;因目标/错误,因爱得太深或太浅”[5]238。当人选择至善即上帝为爱的对象,或者在亲近上帝之外的次善时适可而止,后天之爱与先天之爱合而为一,人就不会沉湎于邪乐甚至犯下罪愆。在选取次善为爱的对象时,如果人选错了对象,或者爱的程度有失分寸,过犹不及,那么后天之爱就会乖离先天之爱,违反造物主的意旨。因此,“众善及其反面,/全部从爱中衍生”[5]247,而“一切该受/惩罚的行为和一切美德,都必然/在你本身的爱心中找到根由”[5]239。
基于上述爱欲观,但丁在《炼狱篇》第24章阐述了其诗学思想的核心主张。在炼狱山的第六环,亡魂博纳谆塔认出了朝圣者,问道:“不过,告诉我,我跟前的人是否/新体诗歌的作者,第一首诗/以‘心灵受爱所感悟的女士’开头。”但丁以谦卑的口吻回答:“我这个人,心智/受爱的启悟而留神,再追摹/内心的感应而记下它的训敕。”[5]342显而易见,但丁在这里把诗歌从本质上看作是对“爱的启悟”的忠实记录。但丁对于诗之本质的这种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认为诗是一种“记录”。这种观念与通常的看法大相径庭,以至于许多批评家认为这不过是但丁的自谦之辞。其实不然,它应该被视为但丁的真实主张。事实上,但丁后来再一次重复了这一主张。在《炼狱篇》第32章,贝缇丽彩训谕正在观瞻凯旋车的但丁记录所见,以教导凡间的人:“当你/返回了人间,请把所见写真。”[5]471而在《地狱篇》第32章,但丁在形容宇宙最底层的状态时倍感人类语言难以胜任,因而渴望有神袛相助以“使我的话不致与事实乖离”[6]471,也间接地强调了诗歌的记录性质。
更为重要的是,但丁强调了诗歌的源泉和本质是“爱的启悟”。那么,这里的“爱”(Amor)究竟是指什么呢?首先,“爱”是指但丁在《新生》中理想化了的那种高雅的、世俗的爱。在但丁看来,爱情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相反,它可以成为一种能够拯救人类的宗教力量。因为灵魂经过净化、脱离了感官之欲后,是一股神圣的力量,与崇高的灵魂浑然难分,能够使人升华。事实上,在《新生》中,但丁的贝雅特丽齐就是作为一个具有至高无上的美貌、美德和力量的女性形象而出现的。其次,“爱”是指“对智慧之爱”,这种“爱”可适用于所罗门的智慧,也可适用于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在《新生》之后,对于哲学的兴趣占据了但丁的全部思想。经过哲学探索,但丁决定抛弃原来的温柔的爱情诗,创作了一组力图表达其哲学观念的新诗,要去描绘那些使人真正得以高贵的品质。高贵是人天生的美德,从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中生发出来,这种天性由上帝注入。最后,“爱”是指上帝或者说“大爱”。这一点可以从但丁的用词得到证明。这里的“启悟”,和《炼狱篇》第25章中用以表达人类灵魂之创造的“呼入”,以及前文所引述的《天堂篇》第10章第2诗行中的“散发”,但丁使用的都是同一个词语,即“spira”。而在《天国篇》最后一章,但丁更是直接用“Amor”来指代上帝。这就说明,在但丁看来,就其终极源泉而言,或者说,在最高的意义上,真正的诗歌来自于大爱亦即上帝,是大爱的具身化。大致说来,但丁对于“爱”的领悟经历了一个从世俗之爱到智慧之爱、最后到上帝之爱的过程,这同时意味着,但丁对于诗歌的本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深化、提升过程。
二、语言与爱欲
众所周知,在一个以拉丁语为正统诗歌语言、俗语被视为低级语言的时代,但丁却选择了用意大利俗语来写作《神曲》。但丁的这一选择不仅在当时就遭到了许多同时代人的质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神曲》在近两百年时间里几乎无人问津。但实际上,但丁的选择是有其理论根据的,这一根据就是在但丁看来,语言和爱欲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按照但丁的语言观,语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用以满足人际交流需要的工具,它连同理智和自由意志一起,共同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体论规定。早在《论俗语》中,但丁已经将有无语言能力和有无语言需要看作是人区别于下等动物和天使的根本不同之处。在《神曲》中,但丁通过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之口,不仅解释了人类语言的起源,而且明确地提出了人是语言的存在物。按照斯塔提乌斯的解说,在人类灵魂形成之前,胚胎尚属于“可塑的物质”,还不是“一个人”;唯有经历了这样一个神圣时刻,胎儿才能够跃变为“人”,即:“万动之源就眷顾它,因自然的大能/造出这样的精品而欣悦,并呼入/力量充盈的新精神为它催生。/在脑里,新精神见到活跃的外物/就加以吸收而合为魂魄,靠自己/就可以生长观照,自给自足。”[5]357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这里“人”的意大利语用词是“fante”而不是“gente”,而前者在词源学意义上是指“说话的存在者”。这就意味着,成为语言存在物是成为人的一个本质规定。其次,语言源始于上帝,是上帝在“欣悦”中赐予人类的一种礼物。事实上,在《论俗语》中,但丁把人类语言直接称作“这么伟大而且是上帝所慷慨赐予的才能”[7]267。
以上述两点为基础,但丁进而提出,作为上帝对于人类的一种赐予,语言不仅源始地勾连着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变动也必然要投射于语言,由语言状况的变化而表现出来。正是根据这种对应性,但丁在《论俗语》中勾画了三种语言状况。第一种状况是,作为第一个说话者,亚当的“第一句话首先是说‘上帝’,而不是别的”,“人类的第一句话是在天堂里说的”,是“快乐的呼声”[7]267。第二种状况是,自从人类因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以来,“人们最先讲的第一声,是苦恼的号哭”[7]266。第三种状况是,语言的混乱直接作为一种惩罚。人类本来操持着同一种语言,即后来被称作希伯来语的“神圣语言”,因此彼此之间能够毫无阻碍地沟通。不料人类却藉此条件而联合起来兴建巴别塔以期直通天堂。上帝为了惩戒人类便淆乱了他们的语言。从此以后,人类无法沟通,只好散居各地,并逐渐形成各自的“俗语”。从“亚当的语言”到俗语这种语言变动,反映了人类与上帝的关系不断恶化、人类日趋疏远上帝的存在状况。
最后,由于俗语具有二重性,俗语的高贵性的证成需要从其罪性返回其神性。作为一种能力,俗语就其本源而言是“天赋的”“自然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神性。但是,另一方面,俗语是人类第三次犯罪的产物,它标示着人类“以自己的愚蠢放肆的傲慢激怒了上帝而受到鞭挞”所留下的“鞭痕”,所以又具有罪性。而从但丁在《论俗语》中为意大利俗语所作的辩护来看,俗语之所以比“文言”更为“高贵”恰恰是因为它在本源上赋有神性,而“文言”是“人为的”,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一种“技术”。但是,兼具神性和罪性的俗语当然并不现成地就是高贵的。根据但丁所作的界定,“高贵”是指“任何一种事物之天性的完善”。这就意味着,俗语要证成其高贵性,就必须经由净化其罪性而回返其神性,从而完满地实现其本性。
从上述分析来看,但丁在《论俗语》中制定标准,试图将意大利俗语提升为诗歌语言,实质上是从神学上对俗语所提出的要求。按照但丁的神学语言观,语言是上帝对于人类之爱的体现,是人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本规定;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决定着人类语言的状况。从实然角度来看,伴随着人类的堕落,人类语言也相应地从其高贵天性堕落了;从应然角度来看,倘若人类能够在神学向度上不断改善其灵魂状况,那么人类语言也将逐步恢复其神性,从上述第三种语言状况返回到第一种语言状况。而但丁的神学语言观对于意大利俗语所提出的要求就是,它应该、也能够产生一种指向更高境界的上升运动,朝着至善而不断地攀升,最终证成其高贵性。可以说,这正是但丁毅然决然地选择用意大利俗语来写作《神曲》的神学原由。
三、语言与诗的爱欲运动
至此,我们可以有理由提出,《神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诗与语言的爱欲运动。总的来说,《神曲》描写了三种爱和两种爱欲运动。前者是指上帝之爱、先天之爱和后天之爱,后者是指由上而下的爱欲运动和由下而上的爱欲运动。
在《神曲》中,诗作为“爱的启悟”,涉及到了三种爱,并且将它们动态化为两种爱欲运动。《地狱篇》的主题是不正当的后天之爱,给予朝圣者以启悟的爱也主要是这种爱。《炼狱篇》则以先天之爱为主题,朝圣者所获得的启悟也来自这种爱。《天堂篇》着重描写的则是上帝之爱以及它对朝圣者的启悟。将这三篇结合起来看,《神曲》表现的就是两种爱欲运动。一是由上而下的爱欲运动,主要包括朝圣者所获得的恩典、宇宙万物及其秩序对上帝之爱的领悟,以及朝圣者但丁从天堂返回人间后对《神曲》的书写。二是由下而上的爱欲运动,即从后天之爱逐步走向先天之爱并最终走向上帝之爱。
这里详细分析的是容易被忽视的语言的两种爱欲运动。《神曲》中还内含着另外一种语言的爱欲运动,即,但丁在《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堂篇》分别描写了三本书,它们构成了自下而上的语言爱欲运动。
在《地狱篇》第5章中,芙兰切丝卡和保罗,这一对永远被暴风雨席卷的恋人,因未能恰当地结合理智与欲望,丧失了理智之善,被罚为地狱情欲圈的永久居民。而误导他们将理智屈从于欲望的“根源”,乃是一本名为《湖上骑士兰斯洛特》的书。用芙兰切丝卡的话来说,“书和作者,该以葛尔奥为名”,意即这本书及其作者起到了大媒人的作用。该书描写了兰斯洛特和茛妮维尔之间逾越礼法的爱恋,试图将心灵、理智与逾矩之爱以文字的方式结合为一体。然而,芙兰切丝卡和保罗阅读这本书的结果却是理智与爱的乖离:他们停止了阅读,开始拥抱在一起。这本书自称要结合心灵与超逾礼法界限的爱,然而,它对芙兰切丝卡和保罗所产生的“爱的启悟”却是适得其反,爱背离了理智,并且直接走向了两性的肉体结合。
第二本书出现在《炼狱篇》。根据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的亲口讲述,是维吉尔的史诗《爱涅阿斯纪》激发了他的诗性潜能,使他成为了一位诗人。不仅如此,斯塔提乌斯还提到,维吉尔在其《牧歌集》中所写的诗句,即“时代在更生复苏;/公道和人类的太初年代正重来;/一代新人从天堂降落下土”[5]311,因为“话语和新教士的宗旨相承”,故而照亮了他走向基督的道路,引领他成为了一位基督教徒。
但丁所描写的第三本书出现在《天堂篇》终末一歌。“在光芒深处,只见宇宙中散往/四方上下而化为万物的书页,/合成了三一巨册,用爱来订装。”[4]472显然,这是一部宇宙的象征之书,其作者是上帝,它所使用的语言则是宇宙万物及其运动,它所遵循的语法则是“爱”。这部书在人间有其用人类语言书写而成的对应物,即《圣经》。
这三本书的依次出现,对应着从后天之爱升向先天之爱、最后通达上帝之爱的爱欲运动的三个阶段。《神曲》是对这一运动的诗歌叙事,首先是朝圣者但丁在“人生的中途”迷失正道,误入了幽暗的森林,然后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游历地狱,在往昔恋人贝缇丽彩的引导下攀登炼狱山,最后穿飞过整个有形宇宙,面见上帝。其次是朝圣者但丁从天堂返回人间,并以诗人和先知的双重身份动笔创作《神曲》,开启语言的由上而下的爱欲运动。《神曲》是一本完整地表现爱欲运动的书,也就是说,它是将前三本书囊括其中的第四本书。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但丁学家辛格尔顿说,但丁是在模仿上帝写作,他想要写出属于他自己的《圣经》。
四、结束语
但丁诗学可以归结为一种“爱欲诗学”。但丁的爱欲思想并非完全属于他的独创,事实上,它根植于中世纪成熟时期的爱欲文化,特别是圣伯纳德的爱欲神学。但丁爱欲诗学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没有简单地将语言看作是诗歌叙事的一种工具,而是认为语言,特别是俗语,也有其自身的爱欲和爱欲运动。为了突出这一点,可以将但丁的爱欲诗学称作“语言诗学”或“俗语诗学”。在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的诗学思想中,诗和语言被内在地关联起来了。如果把朝圣者但丁看作是诗歌的人格化,那么他的朝圣之旅表现的就是诗的爱欲和爱欲运动。如果把从天堂返回人间的诗人但丁看作是意大利俗语的人格化,那么他对于《神曲》这第四部书的写作,所展开的实际上是语言或者说意大利俗语的爱欲和爱欲运动。无论如何,在爱欲和爱欲运动这一基础之上,诗和语言被内在地关联起来并融为一体,其产物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神曲》。
[1]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70.
[2] 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272.
[3] Caesar M.Dante:The Critical Heritage[M].London:Routledge,1989:2.
[4] 但丁·阿利格耶里.神曲3·天堂篇[M].黄国彬,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 但丁·阿利格耶里.神曲2·炼狱篇[M].黄国彬,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6] 但丁·阿利格耶里.神曲1·地狱篇[M].黄国彬,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7] 章安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67.
Language,LoveandPoem—AnInsightintoDante’sPoeticsofLanguage
WangYanhua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UniversityofShanghaifor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200093,China)
An important topic for Dante’s poetics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poem,which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theological view of love.Such a view of love emphasizes the essence of poem is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vement of love.As a gift from God,language also has its own love and movement of love.The love movement of love and language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bottom-up movement and top-down movement,on the basis of which language and poem are innat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Commedia”.In this sense,“Commedia” is fundamentally the love movement of poem and language;Dante’s poetics is “love poetics.”
language;love;poem;lovemovement;“Commedia”
I 106.2
A
1009-895X(2017)04-0352-05
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4.010
2016-05-10
王彦华(1977-),女,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中西诗学比较。E-mail:1977wangyh@163.com
(编辑: 巩红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