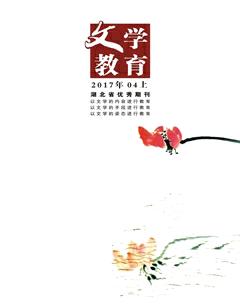挣脱历史的束缚:《反生活》中的伦理冲突解读
内容摘要:《反生活》是菲利普·罗斯“朱克曼”系列作品的第五部,它讲述朱克曼在参加弟弟亨利的葬礼后产生对自己犹太身份的反思。本文将从伦理环境和伦理冲突的角度对朱克曼进行解读,通过对朱克曼在巴以等犹太国家所遇到的伦理冲突和他在欧美国家遇到的伦理冲突,以及在家庭伦理环境中的伦理冲突分析,得出他追寻犹太伦理身份的根源:是什么驱使着他去追寻自己的犹太身份,他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犹太人。在伦理环境下的伦理冲突驱使着他对犹太身份的追寻:他在坚持犹太本性的同时走出传统的伦理环境的约束,走出历史的禁锢。
关键词:反生活 伦理冲突 伦理环境 犹太人身份
在1987年《反生活》出版后,美国作家威廉·加斯在同年的《纽约时报》上将它定义为“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新作同时也是小说主题的一次重要转变”,它用词精美却富有争议,它用词诙谐却又严谨。[1]凭《终结感》荣获2011年英国布克文学奖的朱利安·巴恩斯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这样评价:罗斯在《反生活》的创作中做出了大胆挑战。他将朱克曼不再设计为对新泽西州犹太人的反叛,而是对整个以色列犹太世界的反叛,朱克曼与以往的角色呈现相比,在罗斯的笔下更加激進了,巴恩斯将这部作品定义为罗斯的最精彩的作品。[2]菲利普·罗斯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德里克·帕克·罗亚尔认为《反生活》可以算作是罗斯的经典佳作,理由有三:第一,它是罗斯的作品中最复杂并且最能够体现出后现代特点的小说,尤其是在对自我的建构上;第二,在这部小说中,朱克曼的叙述声音开始作为主角出现,这为该系列后四部小说的创作铺平了道路;第三,也可以看作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这部小说中开始对犹太人的种族的自我身份的探讨,这个主题始终贯穿全文。[3]
对《反生活》的解读,有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将朱克曼的家族历史和宏观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分析,把《反生活》看作是朱克曼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将历史的虚构性和现实的真实性结合起来。[4]也有从跨学科的角度运用鲍恩的家庭系统理论进行解读,从而得到一个创新的结论:这不是作者对犹太人和女人的憎恶,也不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人格体现,关于它的创作意图也许目前暂时无法得出确切结论,但是通过心理学的解读丰富了对朱克曼的理解。[5]在前人研究中,朱克曼的历史伦理环境中的冲突和家庭伦理环境下的冲突是理解朱克曼追求犹太身份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将从伦理冲突的角度,对朱克曼的伦理环境下的冲突进行分析。在个人成长伦理环境下,朱克曼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他有着犹太人的血统,却在有着种族大熔炉之称的美国成长并接受教育,这与那些本土的犹太国家的犹太人是不一样的,使得朱克曼在多年后回到祖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伦理冲突,这不是对犹太人的厌恶抑或对朱克曼自我的厌恶,而是两种不同的伦理环境作用下伦理主体所面临的伦理冲突,这种伦理冲突体现为朱克曼对生活的反叛以及对自己伦理身份的定义和追寻。朱克曼的伦理身份是对他进行评价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于是导致伦理冲突。[6]在历史的伦理环境下,历史伦理冲突作用于不同的伦理主体,以至于当这些有着各自特点的伦理主体汇聚在一个家庭伦理环境时导致了家庭伦理冲突。家庭伦理环境中,朱克曼与英国籍妻子玛利亚的矛盾,以及她的家人与朱克曼自己的矛盾都将家庭伦理冲突的矛盾持续发酵。可见,《反生活》是一部将伦理冲突集合的作品,在主人公朱克曼世界里的多重伦理冲突使得他对伦理主体的定义更加困难,即对自己伦理身份认定的困难。朱克曼在深陷伦理冲突的同时,对自己伦理身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也使得《反生活》成了对朱克曼追寻自我的主题解读的重要作品之一。
一.个人成长伦理环境影响下的冲突
在朱克曼与艾尔恰南开始交谈时,他这样对朱克曼说“看见那棵树吗?那是一颗犹太树。看见那只鸟吗?那是一只犹太鸟。瞧,那边,一片犹太云彩。只有这儿才是犹太人的国家。”[7]艾尔恰南当时六十五岁左右,在海法当焊工,他用英语和朱克曼交流,英语是在当年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候学会的。在艾尔恰南的眼里,在犹太国度的事物才具有着犹太性,鸟儿、云朵和大树,这些本就是随处可见的事物只因在犹太人的国度也出现了,就被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既然在犹太国家飞翔的鸟儿、成长的小树和漂浮的云朵都是具有犹太性的,那么本来留着犹太人血液的朱克曼,更加被确定为是生来就具有犹太性的,朱克曼是犹太人,他应该留在属于犹太人的国度,这是艾尔恰南对朱克曼的看法。这种对犹太文化传统的保守与朱克曼在美国的伦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伦理价值的冲突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更加凸显。朱克曼告诉艾尔恰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一直觉得自己恰如其分。朱克曼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国家,因为美国并不是一个排外的国家。在朱克曼的伦理价值看来,他不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不是在犹太人国家,譬如以色列这样的国度成长,而是在美国那种文化包容的伦理环境里成长。这是他和艾尔恰南成长的个人伦理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不同的伦理环境作用下,同一种族的人产生了不同的伦理价值。
在同艾尔恰南的谈话中,朱克曼认为美国并不简单地归结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问题,反犹主义者也不是美国犹太人最大的问题。没有一个地方像美国那样,将自己公开宣称的梦想置于多元文化的中心。尽管他对美国存在点儿理想主义,就像艾尔恰南的儿子——舒基对以色列有点儿理想主义一样。[7]艾尔恰南和朱克曼的伦理冲突来源于他们不一样的成长环境,他和朱克曼成长于不同的伦理环境,艾尔恰南对犹太人传统文化的坚守,不愿踏出这个犹太国度,去接受一种资本主义的包容文化。在朱克曼看来,他的第一重犹太人的伦理身份应该拥有着艾尔恰南那样的坚持,但是,朱克曼的第二重伦理身份却是如何做一个美国人,这两重身份不仅意味着对犹太文化的坚守,而且意味着一种和谐,一种对美国文化的包容,一种对非犹太文化的吸收。
历史的伦理环境作用于不同的伦理主体后产生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舒基和艾尔恰南都是在犹太国家成长,受到传统的犹太主义洗礼的犹太人,朱克曼是生长在美国犹太家庭的犹太人,尽管都是犹太家庭环境,但是朱克曼是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大融合的伦理环境,人们更加包容的接纳其他事物,相比之下,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以色列国家则显得更加的保守。
二.家庭伦理环境中的冲突
在关于主人公朱克曼的解读中,由于伦理主体在多部小说中的行为都与性有关,有评论家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从女性角度来分析罗斯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认为作者罗斯是位厌恶女性的人。[8]朱克曼的妻子玛利亚是个英国人,在遇见他之前,她已经有过一段婚姻。在玛利亚对朱克曼的陈述中可知她的母亲是不介意朱克曼是个犹太人的。但在朱克曼看来其实玛利亚的家人对朱克曼的犹太人身份是心存芥蒂的。玛利亚的姐姐,甚至玛利亚的母亲显得像是代表某个纯种的社会组织,会经常宣告朱克曼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劝诫他最好不要加入这个组织。[7]在这里,“这个组织”是一个种族的代表,一个拥有共同伦理意识的伦理环境,它与朱克曼的犹太伦理环境不同,并且存在着一些敌对。这在朱克曼看来是极其受辱的。尽管从玛利亚的对话可以看出她对朱克曼犹太身份的认可,但是,直到她们一起在伦敦餐厅吃饭时,一位英国太太对餐厅侍者要求打开窗户,原因竟是因为朱克曼的犹太身份而引发的“这里有一种臭味”的无理言论。朱克曼认为玛利亚实则是背负着严重的精神包袱才选择跟他在一起的,并且玛利亚对他们的未来并没有严肃的考虑过来自她的家庭带来的压力,至少在美国他没有遇到在公众场合如此明目張胆的对其他的种族的排斥。而玛利亚认为“如果事实上你一点也不喜欢一个犹太人的话,那么一个犹太人的一举一动,你都会认为是犹太作风。那就是说,他们应该摒弃那种作风。”[7]夫妻两人的立场代表了两个不同伦理环境的冲突,玛利亚是英国人,她的母亲和姐妹都对犹太教有着很强烈的排斥。朱克曼是美国的犹太人,第一重犹太人的伦理身份是他无法改变的,是他的父母遗传给他的,美国的包容让他学会了接受过去,并且试图将过去和美国的伦理环境很好的进行融合,学着做一个美国的犹太人,可见,他对自己的犹太人伦理身份是不排斥的。然而,玛利亚的家庭以及伦敦的餐厅见闻让他明白了,即使玛利亚不会对他产生排斥感,他也无法自我欺骗,也无法去否定两个不同伦理环境间的冲突。
在玛利亚和朱克曼的吵架中,他们的争论焦点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的辩论。朱克曼第一重犹太人的伦理身份是不可厚非的,他从祖父母辈那里知晓犹太文化、犹太传统。玛利亚则是一个彻底的非犹太人,她的伦理身份和家庭的伦理环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文化传统和不一样的伦理环境里有着激烈的伦理冲突。在他们的家庭中,夫妻俩的争吵,归根结底是在于两个不同伦理环境影响的伦理主体间爆发的伦理冲突
三.个人信仰伦理环境下的冲突
在朱克曼对自我的认知中: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恰如其分。我的背景在工业化移民的美国,我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受教育,我的圣书不是《圣经》,我不是从纳粹死亡营中逃出来的辛存者。[7]在这段朱克曼和艾尔恰南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朱克曼对自己伦理环境的认知:我不是一个在犹太环境中成长的犹太人,我没有受到犹太人文化氛围的彻底熏陶,我也没有受到犹太教的洗礼进而成为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我不是一个非犹太教的异教徒,我也不是从纳粹集中营逃离出来并对社会主义有一种狂热追求的犹太人。在朱克曼的家庭里,她与玛利亚的一次最严重的分歧就在是否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进行割礼。在他写给玛利亚的信中,他给出了对割礼的看法:“要在一个崭新的男孩的生殖器官上施行那种精巧的手术,在他看来就是人类荒谬无理性的奠基石。”[7]这段话写于小说的结尾,朱克曼将割礼看作是犹太人心目中所推崇的一幕。关于割礼的问题,朱克曼将它提升到了犹太人身份认定的高度。在朱克曼看来,每个人生来是自由的,他不期望将每个人的自身与自己的犹太祖先甚至现代体制挂钩。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带任何宗教色彩,朱克曼是赞同割礼的。他不赞同的是将割礼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一种在一个新生生命身上落下烙印的仪式。所以,他在反对割礼之时,也承认了“而我也不愿意简化那种联系,任我们的孩子包皮耷拉着”。[7]割礼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盛行。在《圣经》里记载着上帝和先知亚伯拉罕的盟约,上帝告知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子孙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的盟约的标记,你的子孙后代中出生有八日的必须实行割礼。因此,割礼在犹太人家庭是如此重要,犹太人父母都会坚持给小孩实行割礼。按照犹太的传统,小孩会被割礼,反过来,进行了割礼的孩子就会被当做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9]因此站在父母的角度,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子女的将来考虑,希望以此有益于将来的发展,朱克曼赞成割礼。站在宗教的角度,它是犹太教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的进行意味着犹太身份的确立,他不赞成割礼是因为,他不希望一个崭新如白纸的新生命一出生就被各种传统以及宗教所压迫。这个伦理冲突的根源,在于朱克曼对自我伦理身份的定义。朱克曼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小孩也理所应当是犹太人的小孩,就如同他的本人的第一重伦理身份一样,他并不排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如果犹太人的身份的认定就是割礼,他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出生就背负着宗教的枷锁,他会更愿意给他的小孩讲述着属于犹太人的文化和历史,就像美国的包容的文化环境一样,而不是将自我完全献身于宗教的束缚中。
这本小说通过内森和亨利在美国的遭遇以及在以色列和英国的一系列行程中对于犹太身份认识的变化,探索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犹太身份的内涵。[10]美国著名的犹太学家沙亚·科亨教授在他的《为什么不给犹太妇女行割礼?犹太教性别和契约研究》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对犹太人割礼进行了研究,从女性未割礼的角度论证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因为没有进行割礼,所有犹太妇女不能算是真正的犹太人中的一部分。[11]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克曼处于伦理冲突的原因所在,对犹太人身份的认定一直就包含割礼,朱克曼在努力追寻着自己犹太伦理身份和美国人伦理身份的统一,作为一位父亲,他对孩子寄予了厚望,他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可是他又不愿意将一种枷锁,一种种族的枷锁带给下一代。犹太人身份的定义之一就是必须进行割礼,然而这种宗教性的强迫与他在美国成长时所接受的包容的伦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伦理冲突。伦纳德·格里克在他的《你身上的印记:从古犹太到现代美国的割礼研究》一书中探讨了为什么有些人不在传统和宗教的指引下给他们的儿子进行割礼。这本书从历时的角度解读了为什么大量的美国男性,在他们其中甚至很多不是犹太人,他们选择去进行割礼。在该书第五章中,他认为在关于割礼的问题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观点越来越接近,同时,在它的结尾处,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无论割礼对于美籍犹太人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但是在当今社会主题下,它对于犹太身份确立的意义以及和上帝契约的意义都不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了。[11]
《反生活》作为“朱克曼”系列的第五部,主人公朱克曼的成长日趋成熟。反抗生活,反叛独立,这些并不仅仅是他对自己犹太身份的追寻,而且也体现了他在不同伦理冲突下的伦理选择:在朱克曼与犹太人国度中的犹太人群体的伦理冲突,朱克曼就割礼这件事与以妻子玛利亚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伦理环境群体的冲突,这些冲突成为了朱克曼对伦理身份追求的诱因之一。在美国做一个犹太人,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美国人,还是做一个深刻具有民族使命感的犹太人?在朱克曼看来,当成为犹太人意味着时刻肩负历史使命,戴上宗教的枷锁,而成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对犹太文化的摒弃,他的决定是逃离犹太文化历史的束缚,寄希望于一种包容的伦理环境中实现他的双重伦理身份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William H.Gass.Deciding to do the Impossible, New York Times. 1987, January 4.
[2]Julian Barnes. Julian Barnes on Philip Roths“The Counterlife”, 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2007, September 25.
[3]Derek Parker Royal. Postmodern Jewish Identity in Philip Roths The Counterlife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2, Volume 48,number2, 422-443.
[4]Matthew Wilson. Fathers and Sons in History: Philip Roths The Counterlife [J]. Prooftexts, 1991, 41-56.
[5]Sarah Eden Schiff. Family Systems Theory as Literary Analysis: The Case of Philip Roth [J]. Philip Roth Studies, 2006,Volume 2,Number 1, 25-46.
[6]聶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7]Philip Roth. The Counterlife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Inc,1988.
[8]David Gooblar. Introduction: Roth and Women [J] Philip Roth Studies, 2012, Volume 8, Number 1, 7-15.
[9]J. M. Glass. Religious Circumcision: A Jewish View [J] British Journal of Urology International, 1999, 83, 17-21.
[10]管建明. 对立生活版本的并置与犹太文化身份的探寻———评菲利普·罗思的小说《反生活》[J].国外文学. 2009(04):69-78.
[11]Elisheva Baumrarten. Marked and Unmarked Flesh: Jewish Identity, Gender, and Circumcis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08, Volume. 26, No. 2, 143-148.
(作者介绍:乔姝,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