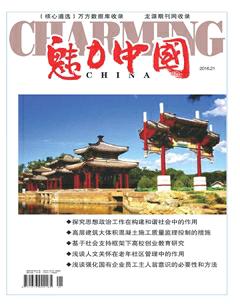反乌托邦视角下的《黑暗昭昭》
摘 要:《黑暗昭昭》是20世纪伟大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作品。这本在作者沉寂十年后发表的惊鸿之作,错综复杂地交织着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其中诸多方面皆折射出反乌托邦的哲学立场。本文试图借鉴以赛亚·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小说中反映出的反乌托邦哲学立场进行深刻剖析。
关键词:《黑暗昭昭》;威廉·戈尔丁;反乌托邦;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主义
威廉·戈尔丁是1983年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小说“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脉络,其虚构的故事对现世人类的生存状况做出了普遍性的阐释”[1](James 1982)。戈尔丁在其诸多作品中不断地探讨人类的生存现状,用黑暗、邪恶等元素的交织来诠释他对自由与枷锁的思考,无论是早期作品《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品彻·马丁》(Pincher Martin,1956),还是晚期的《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1979),皆折射出这一点。《黑暗昭昭》可谓是一本复杂的小说,不同于《蝇王》中描绘的荒岛上的自相残杀这一单线条主题,《黑暗昭昭》以多重视角,描述了两位主人公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们一位代表黑暗,一位代表被黑暗世界笼罩着的一束光明,以半神的形象出现,肩负着对整个混沌世界的救赎。在小说中,戈尔丁延续了其一贯的黑暗笔触,以罪恶与恐惧的交融阐释了其不断探索的主题,即:人类的生存状况、斗争与发展[3](Fiddes 1991)。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背景为战后英国。彼时,这个身心俱疲的国度还未完全从二战结束后的萧条中走出,又卷入了美苏冷战下的两极格局。战后的贫困、混乱使英国笼罩在愁云惨雾当中。小说带着后现代主义式的荒诞与晦暗的基调,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及国家秩序深深的幻灭与绝望。这一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模式、价值取向引发了人们的重重忧虑。无论是整个世界还是个人范畴,乌托邦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并没有被付诸现实。作者将整个社会环境放置于反乌托邦视角之下,对乌托邦不切实际的愚昧、虚幻的构想进行了间接的讽刺与反击。同一时代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其价值多元主义学说中的主张正与戈尔丁的小说存在着高度契合,引发了人们对乌托邦哲学深刻的反思。
乌托邦(Utopia)源于希腊语,意味着“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乌托邦思想源远流长,回望历史长河,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培根的《新大西岛》都描绘了理想社会的景象。中世纪提出的神学一元论以“天国”为完美世界的最终归宿。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的观念,同时点燃了乌托邦思想的活力。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导致了人们在经济、社会地位上越来越大的不公。彼时,空想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登上了历史舞台。圣西门、欧文、傅立叶都在其著作中对乌托邦进行了细致的构想,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宗教、教育。乌托邦哲学家的描述、规划,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渗透,逐渐形成了乌托邦式哲学思想与自由观。总体来讲,一元价值理论始终是乌托邦哲学家的导向,他们坚持以永恒的唯一真理作为现世事物的裁定者。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一元论就阐明:无论是理性还是共识,它们的存在都是“一”而不是“多”[4](Lassman 2000);同时,乌托邦主义者倡导解放自由与人权,却带着强制性。巴贝夫主义将乌托邦规划为绝对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人民走他们所设计好的、能完满实现人生目的和愿望的道路[7](谢江平 2007)。反乌托邦,正是揭露了乌托邦思想中的种种漏洞,在描述乌托邦所带来的恶果的同时,理性地表达理想与个人愿望。反观戈尔丁的《黑暗昭昭》,这部反乌托邦小说,在诸多方面都对乌托邦构想进行了抨击,无论是思想上的价值一元论,还是政治上的自由观,乌托邦思想都充满着矛盾与虚幻。
一、反乌托邦一元论
伯林认为,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一元论,若一元论中存在着不合理,那么乌托邦的大厦也将倒塌。一元论(Monism)是C.沃尔夫发明的术语,指任何主张实际只存在一类实体的形而上学理论[7](谢江平 2007)。一元论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流传千年,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洞穴理论,到近代基督教的神学一元论,乌托邦主义者继承了这种一元论的思想,他们相信,完美世界必然是由一个终极真理作为导向。而这一终极真理的道德与精神源泉正是来自上帝。他们笃信上帝是唯一的神,是无所不能、完美的神。然而这种神性一元论恰恰只能使乌托邦走向毁灭。就像无论其如何粉饰太平,也无法遮掩十字军东征与宗教法庭的血腥。
1.1多元宗教色彩
《黑暗昭昭》中的世界,是撒旦眼中的地狱,是黑暗昭然若揭的世界。男主角麦蒂,作为拯救这个堕落世界的救世主,被赋予了半神的形象,他代表的神蕴含着多元意义。
麦蒂具有复杂的神秘性,因为他身上兼具了基督教、摩尼教以及佛教中“神”的形象。麦蒂是个孤儿,他是闪电战的受害者。德国飞机的轰炸导致他的左半边身体被严重烧伤,进了医院。他的名字是医院的工作者为他取的,然而,他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姓。他的姓被人们任意称为“Windy, Windrap, Windwort, Windgrove, Windgraff, Windrave”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姓的前缀都带有“风”的意思,虽是人们对其的任意称呼,却都蕴含神学所指。从神学角度来说,基督教的神圣三位一体中的圣灵,正是用“风”这一意义来象征的,故而“灵风”[6](阮炜 1988)。同时,他笃信圣经。小说数次提到,他把《圣经》放在床头柜,每日阅读。当他无意中翻到一本圣经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找到熟悉的页数,反复阅读。并且前后翻阅,对他而言毫无困难。麦蒂读圣经是心无旁骛的。基督教中神的形象在麦蒂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黑暗昭昭》是一本充满对立面的小说,正如书名,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这种善恶的对立颇具摩尼教的宗教色彩。摩尼教又称明教,昭示着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其教义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苍生的夙愿。麦蒂,仿佛也是一名摩尼教的先驱者。在他的日记中,他提到两个幽灵经常来和他对话。在1966年7月11日的日记中,麦蒂记录道:“今晚我问他们,世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他们回答,你是最接近万物中心的人。”[5]在10月3日的日记中,幽灵对麦蒂说:“你有张可怕的脸,身处世间险恶,但你在精神世界里仍是我们的朋友……你可以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向死者布道。”[5]在麥蒂的日记里,幽灵多次暗示他的重要性以及其特殊的身份。在1978年6月17日,麦蒂人生的最后一篇日记中讲道,顶着太阳之光的白色幽灵问他愿不愿意拯救一个孩子,麦蒂表明他愿意做出牺牲。通过这种神秘的手法,作者仿佛深谙摩尼教之道,刻画了麦蒂这一形象:由神明指点,降临凡间。他修身养性,求索真理,拯救苍生,不辱使命。通过激烈的斗争,光明最终战胜黑暗。6月17日当晚,苏菲所在的犯罪团伙在贵族学校内引爆炸弹,企图在混乱中劫持孩子。当时在校内工作的麦蒂不幸受到牵连,引燃的炸弹令他浑身着火,但他仍义无反顾冲向挟持人质的歹徒,使对方丢下了孩子仓皇而逃。麦蒂最终以一名摩尼教殉道者的姿态,在光明中走向了永恒。
《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的书名取自弥尔顿的《失乐园》,意为“地狱之火”[3](Fiddes 1991)。然而,无论是对与苏菲还是麦蒂来说,这个寓意都颇为模糊。相反,火焰并不是来自地狱,这更像是神圣之火,是赫拉克利特眼中永恒的活火:世界的本原是火,万物皆动,按一定尺度燃烧,按一定尺度熄灭[3](Fiddes 1991)。麦蒂自烈火中诞生,又从烈火中离开。如同凤凰涅槃,承受着来自凡尘的阴谋、苦难,焚身以火,用个人的生命换取了世人的祥和、安宁。麦蒂死后的某一天,他的老师佩迪格里在公园亲眼目睹了他的“到来”。“麦蒂来了……金色的光芒在他周身闪耀……他仿佛融化在了那团如火的光芒中;面容也不再是两种颜色,而是融为一体。万丈光芒如同孔雀羽毛上的眼睛,他的嘴角洋溢着可爱的微笑”[5]。此刻,麦蒂的牺牲带着佛教中涅槃的色彩,与其说牺牲不如说是得到了永生。是圆寂,解脱,不老不死,不伤不灭。对于小说中的角色埃德温来说,麦蒂的形象也如出一辙。当他的老邻居问他,麦蒂到底是谁?是方济会修士(a Franciscan friar)、印度教圣哲(a Mahatma)、还是那个想在威尔士建造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转世?埃德温回答,他不是达赖,但他也是个喇嘛。埃德温把麦蒂喻为藏传佛教徒。虽然这段对话并未作出深入展开,但这一讳莫如深的叙述暗含着作者对麦蒂多元形象的塑造。
值得一提的是,麦蒂具有神性,同时也是一个不完美的“神”。从外表上,他的半边脸严重烧伤,肤色半明半暗,面目可怕,与传统的“神”的光辉形象大相径庭。从品行上,他努力修身养性,有时却拘泥迂腐。他勇于奉献,却也不免怀挟偏见。麦蒂崇拜他的老师佩蒂格里,但是当他得知佩蒂格里对美少年亨德森过分宠溺之后,心怀嫉妒的他向后者掷鞋以对其进行诅咒,此处戏仿《旧约圣经》中的故事:雅各向其兄以扫丢掷鞋子,通过这种原始诅咒觊觎以扫的长子之名。残缺即为真实的人性,却亦是一种美。弦月虽为残缺,不能与满月同辉,却也给世人照亮一条回家的道路。麦蒂则以一种残缺的形象成就了人与神的浑然一体。戈尔丁作品中价值的多重性就此展现。
戈尔丁小说中的救世主不是完全的基督教的神,而是包含了多重宗教主义的神性。他将个人的渴望寄托在这样一个多元主义的角色之上,无不体现其宗教立场。“我不属于任何一方教派。”戈尔丁把自己称之为“不虔诚的教徒”,他既不是一名合格的基督徒又不恪守宗教仪式、清规戒律[1](James 1982)。这一宗教立场在《教堂尖塔》(The Spire,1964)中可见一斑。戈尔丁在《教堂尖塔》中塑造的圣母马利亚大教堂的教长乔斯林,自诩为上帝的代言人,声称感受到神的召唤,欲建造一座教堂尖塔,却因操之过急,在地基不稳的情况下硬逼着工人施工,工程最终前功尽弃。坍塌的不止是塔,还是宗教狂热主义。作者的观念即与神性一元论背道而驰,其主张在《黑暗昭昭》中阐明:乌托邦思想只是空中楼阁,只有多元主义的价值观才能最终拯救人类。
1.2荒诞中的一元论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阐明其观点:“这个世界上没有普世的爱,更没有普世的价值”。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自古以来饱受争议,却也流露了价值选择之艰难与无奈。伯林认为,价值与价值、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冲突与不可调和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塑造一个完美社会的构想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唯理性论”、培根在《新大西岛》中表露出的“科学主宰一切”的思想都反映出人们对于建立完美社会的迫切愿望。并且完美社会的构想,往往是以一种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来左右的。乌托邦思想正是受这样的文化背景的熏陶而滋生。伯林对乌托邦思想中价值观的主张总结如下。一、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其他答案必定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二、真理与真理之间可以相互融合。这两个阐述归根结底都是以一元论为归宿。然而,这种唯一真理观却容易导致武断、以及更大的分歧。
戈尔丁在《黑暗昭昭》中就多次以诙谐的笔触,反讽了价值一元论的荒诞。麦蒂在昆士兰格拉德斯通市有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期间的一天,他的车在半路上没油,周围尽是荒野和沙漠。他从车里走出,试图找人寻求帮助。一个人不停地走着,炽热的阳光令他他又累又渴。终于,他遇见了一个土著。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向土著人挥舞圣经。而后又猛地倒下,双腿伸直,两臂伸开,形成十字架的形状。然而土著却大吼一声,将手中淬过火的长矛刺进麦蒂张开的手掌。这一幕荒诞的景象恰恰反映了文化的差异与冲突。麦蒂以为对方也是基督教徒,因而以种种方式向对方表明是自己人。而土著人却以为对方是在挑衅,于是无情地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戈尔丁认为,“他者”永远不能被同化,这符合价值多元主义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非可比性和非通约性(the incomparabi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4](Lassman 2000)。文化多样性折射出的价值的非通约性可以被人们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可以冲破任何文化间的障碍。
伯林认为,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不协调以及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建立一个彻底的乌托邦社会,便是将各类观点笼统地归为对或错,那么真理将沦为强权下的产物,而失去其意义。《黑暗昭昭》中就以两个人充满对立面的对话揭示这一问题。小说的第三部分叫做《一就是一》(One Is One),這一名字带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一元独断思想,颇具讽刺效应。在这一部分中,古德柴尔德书店老板西姆·古德柴尔德和老邻居埃德温·贝尔展开了无休止、无逻辑的关于真理之争,令人联想到《等待戈多》中两位老翁的荒诞对话。两人不断地争论,都试图以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他们在看小学生踢球的时候,甚至围绕“球到底是从双腿之间穿过还是从脚下穿过”展开激烈的争辩。然而,谁也说服不了谁,这象征着各种价值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乌托邦主义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企图把不可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注定是要失败。
二、乌托邦式自由之困
价值多元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自由观的探讨。林肯说:“尽管我们都宣传为自由而奋斗,但在使用同义词语时,我们却并不意指同一事物……当下有两种不仅不同而且相互不容的事物,都一名冠之,即自由”[2](Berlin 1969)。伯林的自由观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区分: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指的个人有行使自我意志的权力,并且作为主体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令事情的发展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消极自由指,个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其思想、其活动不受外在干涉,即:“不被奴役”。乌托邦主义者试图解放人民的积极自由权,然而这种借助“积极自由”之名的运动反而导致对人的压迫和奴役。因为积极自由的倡导往往是家长制式的解放运动。而家长制(paternalism)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2](Berlin 1969)。我喜欢宁静与独处,你却认为我认为我身陷孤独的囹圄要将我解放。你迫使我进入喧嚣的氛围,我的权力因此受到了侵犯,而你却认为我获得了自由。乌托邦式的解放是家长制的,这实则是更大的专制,不仅因为它比残暴、野蛮的暴政更具压迫性,还因为它忽略了人的超验理性,侮辱了人的独立思考与个体观念。
苏菲,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极端的恶的象征。苏菲在罪恶中一步步沉沦,她是黑暗的象征,同时也是乌托邦式自由观之下的牺牲品。苏菲的童年是与父亲和她的双胞胎妹妹托妮一起度过的。父亲认为她有些孤僻,于是让托妮和她形影不离。父亲认为她缺少母爱(她们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于是想和家里新来的保姆结婚。父亲总是把他认为的苏菲缺少的自由赋予给她,然而这些却滋生了苏菲的叛逆和逃离。她从来就不喜欢托妮,她甚至希望托妮有一天消失。“她还小,不会把类似于杀了托妮的内心想法说出来。可她真的不希望她回来!”[5]同时,她也不喜欢父亲跟保姆结婚。她无法忍受父亲的爱就这样迁移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她把鸭蛋捏碎塞进父亲床头柜的抽屉,那臭气熏天的秽物,正是她无声的抗议。尽管外人眼里,她是光鲜艳丽、美丽动人的淑女,可是父亲灌输的家长制式的自由给予模式实质是对人的压迫。这条从小产生的罅隙导致了日后苏菲与父亲的决裂,也为苏菲一步步的堕落滋生了温床。
乌托邦式的解放思想是一种自我导向、自我控制的解放思想,它把“自我”区分为“高级的自我”与“低级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这导致了“高级自我”对“低级自我”的专制和压迫[7]。这种人格划分使高级的以理性控制的“自我”凌驾于带着冲动、欲望的“低级自我”之上。长期的自我压制将导致两种人格的发展不断背道而驰,继而分裂成更大的沟壑。苏菲就是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个体。文中多次提到苏菲认为她后脑勺长着一双“眼睛”。“当她前方的眼睛闭上以后,她脑后的‘眼睛便会睁开,然后射出一道黑色光线,注视着广袤无垠的黑暗”[5]。可以说,苏菲最热切的渴望,便是怪诞、反叛,用黑暗将平淡无味的光明世界笼罩在它的怀抱。脑袋前面那双看到光明的眼睛可以说是苏菲的“高级自我”,脑袋后的“眼睛”则是她的“低级自我”,这种黑暗令她激动不已。两种自我的长期压制与斗争令她的人格陷入了分裂。当她的“低级自我”逐渐战胜“高级自我”时,苏菲也走向了极恶。她的性行为十分随意,且带着施虐的倾向,曾在与男友发生关系之时将刀扎入他的肩膀。她同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犯罪组织,企图绑架贵族学校中的孩子以索取高额赎金。她幻想一名男孩成功绑架得手,并对其施加疯狂的虐待,而后,在发现男孩只是她的幻觉后,歇斯底里、几近崩溃。
戈尔丁善于描写人性之恶。《蝇王》中孩子们在荒岛上分为两派,互相厮杀,堕落成为嗜血的野兽。《品彻·马丁》描绘了主人公马丁以堕落的人性与死亡相抗衡。而在《黑暗昭昭》中,戈尔丁更是将人性的黑暗面极致展现,从而支撑了其反乌托邦的价值立场。乌托邦往往始于“自由”而终于“专制”,人性的阴暗面讽刺的不是人性本身,而是造成其走向极端的周遭世界。《蝇王》中的荒岛是如此、《我们》(尤金·扎米亚金,1924)中绝对理性主义的国度亦是如此。
关于人生的思考,乌托邦学者认为,人生的终极指向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于是,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生活方式,皆朝着这一目标不断前行。戈尔丁以晦暗的笔触表达了悲伤的隐喻,这种对积极自由的解放反而成了桎梏与压迫,人性在长期的压抑中滋生了極恶。乌托邦式自由终将走向破产,如同玛丽·雪莱笔下的佛兰克斯坦,最终被其创造的怪物所毁灭。
三、结语
乌托邦是一篇辞藻华丽却经不起推敲的文章、一座壮丽恢弘却没有地基的楼阁。它是屏风隔断上孤傲的仙鹤,画师精湛的笔锋造就了它,却难助其脱离画卷,飞出青天。反乌托邦正是对乌托邦浮华、空洞的价值观、自由论的质疑,它揭露了其虚幻性与阴暗面。一如《堂吉诃德》终结了中世纪历时两百年的骑士文学,一部《反杜林论》让社会主义自此开始脱离空想,走向科学,同时也加快了反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反乌托邦文学家们独具慧眼、针砭时弊,对乌托邦梦想中深埋的残酷现实进行深刻地挖掘、无情地揭露。于是,俄国有了《我们》(尤金·扎米亚金,1924)、《切文古尔镇》(普拉东诺夫,1929),英国有了《美丽新世界》(赫胥黎,1932)、《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1949)、以及《蝇王》。一部《蝇王》更是将威廉·戈尔丁推向了世界文坛的巅峰。而《黑暗昭昭》,虽诞生于《蝇王》发表的十年之后,却毫无承前者之荫的迹象。即使同样带着反乌托邦元素,《黑暗昭昭》比《蝇王》更复杂、更神秘,也更具震撼。作者以富含寓意的描写、宗教文化、后现代主义色彩,以恢宏的想象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刻画到极致。当象征黑暗的恶魔在自由的桎梏中爆发,乌托邦的大厦终于土崩瓦解。在生死存亡之际,另一个多元主义的象征:半神的麦蒂,奋不顾身,力挽狂澜,挽救于万一。《黑暗昭昭》是英国战后文学作品中反乌托邦意识的里程碑。戈尔丁所展现出的人性关乎他对世界观的探索,关乎社会、国家发展的深邃思考,对现世社会建设、人类发展具有深远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Baker, Jame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Golding [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82(2):130-170.
[2] Berlin, Isaiah. Four Essays on Liber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3] Fiddes, P.S. Freedom and Limit: A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hristian Doctrine [M] Palgrave Macmillan, 1991:205-233.
[4] Golding, William. Darkness Visible [M]. London: Bantam Books, 1979.
[5] Lassman, Peter. Pluralism and Liberalis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Isaiah Berlin [J].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0:119-131.
[6] 阮炜. 茫茫黑夜中的一线希望之光——戈尔丁《黑暗昭昭》初探[J]. 外国文学评论, 1988(4): 60-65.
[7] 谢江平. 《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作者简介:
姓名:李慧杰,出生年月:1992.10,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江苏省镇江市,当前职务:硕士在读,学历:文学学士,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美文学方向,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单位所在地:上海,单位邮编: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