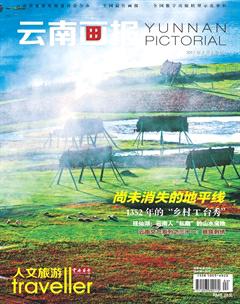尚未消失的地平线
李旭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所著一本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首版发表于1933年。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发表,在英语中多了一个新的词汇——“shangri-la”,香格里拉,这个词成了永恒宁静和平的象征。随着希尔顿的小说1937年后多次被拍成电影,那片神奇的土地和香格里拉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引得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探险家、旅游者、考古者,甚至淘金者纷纷寻找这个似乎是虚幻存在的地方,人们几乎忘了那只是一部虚构小说中的地名。新加坡华侨巨商郭鹤年将他遍及全球的酒店集团命名为“香格里拉”。位于滇藏川地区东南部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将自己的县名改为“香格里拉”。
对于“香格里拉”的确切意思有多种说法,如“心中的日月”“你好,朋友”“通往圣洁之地”等,而我们更愿意把它引申成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那个等同于“乌托邦”的词语——世外桃源!
据说,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就以滇藏川交界地带的神秘地区作为书中所描绘的“香格里拉”的自然地理和文化背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大气豪迈而确切地将滇藏川相交接的这一大片区域称为中国最美的地方。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人生历程上,我得说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对此我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一直与这片地区有缘,我在这一带流连了近二十年。自从1986年起,我就在滇藏川大三角區域不停地奔波行走,即便是我的家多,我也没有如此频繁而深入地走过。横贯这一区域的茶马古道就跑过十七趟,我甚至在香格里拉市(藏区习惯把它称为“建塘)生活过一年以上的时间。
如果可以站在地球以外观看,你会发现滇藏川大三角地区是地球上“眉头”皱得最紧蹙的地方。中国的众多山系为东西走向,而这里的却是南北纵贯,好几系列高山如同被神的巨手从北向南划拉过,并行耸立,并为深邃的峡谷切割,形成独具一格的地理单元。
这一大片被称为横断山脉的地域别具魅力,令人心醉。这是一片耸入云天的高原,无数雪岭冰峰,簇拥起我们这个星球上最神奇的地方。它不仅拥有一系列、一簇簇壮丽无比的雪峰,而且有亚热带的莽莽丛林和美如仙境的湖泊、变幻无穷的云海和超逸飘缈的山岚,更奔腾着汹涌咆哮、姿态万千的澜沧江、金沙江、怒江、岷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等世界著名的大江大川,它们千万年来刻划雕塑出了气势恢宏、惊心动魄的虎跳峡,神秘莫测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和怒江大峡谷等等,更孕育出种种与之相应的神奇文化。
那是一个令人顿生虔诚的宗教感情和泛起各种奇思妙想的地方。在那儿,轻易便可沉入一种超然的静寂,在那静寂中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呼吸和热呼呼的鲜血在体内奔涌的声音。循着山谷间和草甸上泥土的浓重碱味儿,就能碰撞到一串串古老而新奇的谜语,那里面有鹰,有雄健的牦牛,有高山牧场里哔啵作响的火苗,有山腰间翻卷迷漾的云雾,有满天云雀的啾啾鸣叫,还有陡峻的雪峰后闪闪烁烁的星星……
在喜马拉雅南北以及与之相连的横断山脉地区,高海拔的雪峰大多数时间高高地隐在云雾之中,雪山和雪山之间则是深深的大峡谷,雪峰和峡谷之间的绝对高差随便就是几千米,气候和植被都呈垂直分布。一年四季,这些山都有不同的颜色,我恐怕永远说不清这一带大山的颜色。石头间油黑松软的土地上长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其间更有数百种杜鹃花竞相斗妍。山里还有各种珍禽异兽,太阳鸟的鸣叫令人销魂。只要去过那里,就将永远深深沉浸在那扑朔迷离的造化之中。
在横断山脉的东西南北四方,排列着一组组、一簇簇海拔五六千米以上的雪峰,它们终年积雪、银光闪烁,其中的南迦巴瓦、贡嘎山和卡瓦格博海拔都在六七千米以上,接近它们,仰望它们,随时都能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苍茫和旷世的沉寂。世界静得出奇,周围的大山一下子全都沉默不语。它们以一毛不生而令人震惊。那种苍凉的美、严酷的美轻易就把人带入史前时代。难以想象它们亿万年前还是孕育了地球生命的大海海底。
太阳一隐在雪峰背后,寒冷马上窜了出来,把我赶到火塘旁边,松柴弥漫起的青烟,带着来自大森林的清香,将我的双眼熏得眯了起来,只能望见银光闪闪的雪峰。雪峰就像一块巨大而威力无比的磁铁,又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宇宙黑洞,曾有的欲望,曾有的躁动,曾有的迷茫等等,都被它们吸附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消失的地平线》里的主人公康韦在“香格里拉”的感觉,也是他在香格里拉第一眼看到的那种雪峰:它们像完美的冰雪砌筑的尖锥,造型简洁如同孩子们信手描画而出,人们的眼光不由得为它们那四溢的光芒所吸引,为它们那恬淡安详的姿态所吸引,简直不能相信它们就在眼前,就在世间。看着它们,能感觉到山谷中流溢出一种深藏不露的奇异力量,使人身不由己为之倾倒。希尔顿如此写道:“康韦凝视此山时,整个身心都被一种独特的宁静所灌满,他的整个心灵、眼睛里满是这奇异的景象。”
有的地方,雪山之间挟着的是一大片一大片茫茫无涯的原野,随着一片无垠的原野在眼前展开,地平线越来越远。视线的灭点处还是雪峰,雪峰之上是蓝天,蓝天的腰际是卷曲成团的白云。原野上常常有溪流像一条条被风扬起的飘带从它中间流过。盛夏时节,原野上开满了黄色的、紫色的、白色的,以及其它五颜六色的鲜花,大地仿佛铺上了花毯,镶上了全世界的宝石。鲜花的芳香使人心旷神怡。走过原野,就像走过童话里小女孩们的梦境。白云灿烂得晃眼。满天都是鹰在盘旋。天蓝得可以掬在手心里。高大挺拔的杨树如同挂满了闪烁的金片,每一片树叶上都跳动着一个太阳。脚下的草原金黄金黄,满鼻子都是草籽浓郁的熟香味儿。
有的地方,是深邃幽远的河谷将一系列雪山分隔开来。如果是干热河谷,两边都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水,没有人家,火焰山般的灼热,仿佛来到了赤道。即便是干暖河谷,有一些灌木丛生长,但峡谷两面仍是陡立的大山,看天看云准得掉帽子。仰首放眼,只见两山凌空对峙,巨壁直落江中,江水汹涌澎湃,江风呜呜作响,翻云疾走,石岩倒旋,令人头晕目眩。河谷里总是江水滔滔。耳朵里灌满了隆隆的轰鸣,随时感受到受阻的江水那雷霆万钧的冲击。河谷两岸的山脊重重叠叠,绝壁相连,无路可循,根本没有人烟。千万年来山水冲刷出的沟壑,日晒雨淋后斑斓的石壁,加上各色灌木点缀,远远看去,构成了一幅幅国画山水,很有些味儿。如果是月夜,月光如水一样注满整个河谷,漫步其中如同在水上漂浮:如果是星夜,满天星斗,星汉灿烂,人的视野刚好与山谷的空间重合,于是你得到的就是一个圆满的、值得你永远铭记的星空景象。
如果在晴天的晨曦中走过高原大地,就会为那种剔透明朗的光泽所震慑。那是真正的神光,暖暖的,红红的,像是将山水镀了一层,石头和土仿佛有了生命,殷红的血在它们的皮肤下流动……
有的地方则是与世隔绝的山谷,是一片片神奇的、给人予强烈归宿感的山谷,是一片片需要具备超凡想象力偶然才能抵达的山谷。
那也就是希尔顿笔下蓝月亮山谷那样的山谷。希尔顿写道:“漫步那里会有一种奇袭而来的舒适与安逸,总有一种闲适而欣慰的快感。”后来,仿佛交响乐里的主题乐章一样,希尔顿在书中反复地写道:“卡拉卡尔雪峰在无法接近的纯净中熠熠生辉。”“在香格里拉,整个格局都被奇异的平静所垄断,无月的夜空也是星光灿烂,卡拉卡尔山的雪顶永远弥漫着淡淡的蓝色气息……”
在那样的山谷里,清晨,只要一睁眼就看到金色的雪峰,跟梦境完全对接在一起。
白昼,蓝天灌满了狭窄的山谷,像海水充满大海:原始森林布满谷间,松萝飘垂,松香扑鼻。黄的桦树,红的枫树点缀其间,秋色醉人:永不消褪的层层绿色随着山脊线起起伏伏,忽明忽暗,一直流向远方的大江河谷。完好、丰富的森林是藏民们以佛心护持而未遭破坏的佛境。正如希尔顿笔下的康韦所感受到的:“整个山谷恰如一个被灯塔般的卡尔卡拉山俯瞰着的宜人港湾。”他想不出更好的词来赞美它,我也是。
夜晚,星星遍布静默的天空,像枫叶长满树枝:当月亮渐渐饱满,银光下的雪峰超然于尘世和寒冷之上,一切纯净无边……太阳一落山,黑暗立刻就围了上来,山野立刻变成另外的嘴脸。大概只有在高原的荒野里才能经历这么黑的黑暗。呆在那样的黑暗中,就仿佛存在于永恒之中。雪峰将寂静围拢起来,连藏獒都停止了吠叫,任由你把外面的厌倦和时间一起带来,在这寂静的山谷里任意挥霍。如果是在月夜,月亮冉冉升上雪峰,皎洁月光下的雪峰比亚当斯拍摄的美国约塞米蒂岩崖更超凡绝尘。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在这里,有着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壮丽最动人的水。夏季的雨水汪洋恣肆,冬季的雪水清碧如玉。不管是雨水还是雪水,它们从无数大山上奔泄而下,那水流漫漫涣涣,迅速汇聚成溪流,又很快流淌到无数的大江和河流中。当乌云散去,浩浩荡荡的江水就襄带着古老的历史和浓浓的思绪,流向远方的山峦。远山显露出它们强劲而优美的山脊,它们是那么峻秀,又充满了張力。蓝蓝的山岚,使它们显得英姿勃发,十分年轻。如果说山脉架起了高原的骨骼,那这些江河就是高原的血脉,它们奔涌流动,为高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为高原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这里的江河有着最为多样化的姿态。刚才它们还是一股涓涓滥觞,一忽儿就变成了磅礴跌宕的激流:它们一会儿像一个文静羞涩的少女,一会儿又成了暴烈狂乱的怒汉:在有的地段它们温柔平和,静得就像熟睡的婴儿,而到了另一些地段它们简直可以吞噬一切,宛若受伤的凶龙。
有的水汇注到一汪汪湖泊中,成了镶嵌在蓝天下的一片片明镜,水映着天,天连着水。再没有比高原的湖泊更宁静清洁的地方了。有的湖水深邃无比,湖周围完全为原生态的植被所覆盖,草木葱茏,鲜花怒放:有的湖水同蓝天一样清澈,但湖畔却是月球地表一样的荒寂。湖边有海鸥和一些罕见的水鸟划出优美的曲线,湖里有多得不得了的高原无鳞重唇鱼和高原鲵鱼。无鳞重唇鱼像湖水一样透明,鲵鱼则像鸟石一样油黑。湖上要么万里无云,水天一色,要么盖着一堵堵镶着黑边的云,有时会亮出光泽奇特的一片,并出现绚丽的彩虹。在这高海拔的湖边上,只要大声叫喊,云就会聚集起来,接着就是一场暴雨或冰雹。这些湖泊都有着不似人间的神圣美丽。当你突然来到它们面前,面对那仙境般的景象,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生怕踩脏了那份纯洁,生怕踏碎了那份宁静,只有双膝跪下,才能得到那大自然的至高无上的宽恕与恩赐。
高原的高山湖泊,大多是冰川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冰成湖,洁净、清澈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它们就像一颗颗明珠散落在高原上,无比圣洁。这些高山湖泊往往是众多江河的源头,而且哺育出一片片丰茂的高山草甸。它们常常与雪峰相依偎,一双双一对对永生于藏民的信仰和传说中。因而,美丽洁净的高山湖泊,也是藏族心目中的神圣之地。高山湖泊在他们看来是那么神秘莫测,不可侵犯。藏民们到了湖边,一般不愿大声呼喊和喧哗,否则,一场突降的大雨或雪会被认为是神灵发怒的征兆和降下的惩罚。有的神湖甚至被人们认为能从其中看出人的今生和来世。于是它们更成为藏族保护的对象,现在也成为理所当然的自然保护区,如西藏的然乌湖、三色湖、莽错湖,四川的新路海,云南的纳帕海、碧塔海等等。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高原上的湖泊就是神灵们永久的居所。在那里他们静思着最形而上的问题,他们直接触摸着世界的本源和生命的主旨。
有的湖水是淡水,有的湖则是微咸湖。不管它们的味道如何,那些湖泊总是牵系着人们的梦、人们的呼吸、人们的脉搏,牵系羞人们的魂灵。
除却大山大川和湖泊,雪域高原还有的是极富灵性的石头和无比奇妙的云,以及超凡脱俗、如梦如幻的天光。这些石头、天光和云似乎就是一种神示,告诉你已经到了人类世界的边缘,正处于神仙天国的门槛。那些历尽沧桑的石头,那些石头上历久弥新的摩崖石刻,那亿万年来不老的蓝天,那一逝不再、永不重复的云,那似乎来自极地或外太空的光芒,它们组合成的色彩令人激动不已。
这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一会儿又电闪雷鸣。当浓重而阴森的乌云紧贴着地平线压过来,世界立刻一片昏黑,十分壮观亮丽的风景一下失去了光和色彩,高原好像不再是高原。高原紧紧地把自己抱成了一团,让你无法看清它,得到的只是无边的敬畏和恐惧。
这一带有些地方的石头巨大而顽强,它们曾经在海底经历了数十亿年的磨砺,它们曾目击地球上最初诞生的生命。在它们身上,嵌有早已成为化石的海螺和贝壳——这些大海永久的记忆。如今它们矗立在地球之巅,没有一声叹息,默默地注视大地的沧桑变迁。
如果在晴天的晨曦中走过高原大地,就会为那种剔透明朗的光泽所震慑。那是真正的神光,暖暖的,红红的,像是将山水镀了一层,石头和土仿佛有了生命,殷红的血在它们的皮肤下流动。只要看到一眼,只要沐浴一次,人生便因之而生辉。
那是个由雪峰构成的世界,而雪峰又为各位神灵所拥有,因此那也是个神灵的世界。那是一片生长神灵的山水。這片高原养育出了善良、朴实、友好的藏民,这与佛教千百年来的滋润熏陶不无关系。
在这片区域,倍感藏民们宗教崇拜之浓烈。到处是寺庙、玛尼堆和经幡,人们深深沉浸在信仰世界里。各种神灵犹如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但宗教在这里仿佛失去了它固有的飘渺空幻而转化为种实在的虚空、宁静和宽和,就像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所描述的那样。
股潜在的、顽强的、不绝如缕的生命气息穿透那神的圣光而成为藏族文化中深厚无穷的内蕴。因为紧邻西藏,藏传佛教成为这一带普遍的宗教信仰,也正是由于藏民们对之近乎绝对虔诚的崇拜,佛教仪式、佛教精神无处不在,更使这里原本已很浓厚的神秘气氛平添几分博大与深沉。
唐调露年间(公元679年~680年),吐蕃即在迪庆境内金沙江上架起了著名的吐蕃铁桥,并设神川都督府,派驻“伦”一级官员,“收乌蛮于治下,白蛮贡赋。”于是白族、纳西族、彝族、傈傈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深受其影响。公元九世纪中期,赞普朗达玛兴苯灭佛。佛教徒有一批人携经典逃往东部的康区避难,对佛教在滇藏川地区的传播起到了桥梁作用。至公元十世纪,佛教在西藏再度兴起,滇藏川地区有僧侣争当前期高僧真传弟子,自称他们所念的是“伏藏”真经,得的是藏传佛教真传。到1950年代初,仅云南迪庆境内就有藏传佛教寺院二十四座,其中格鲁派十三座,噶举派七座,宁玛派四座。
翻看藏传佛教在滇藏川地区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它在当地人民观念中这么根深蒂固。尤其是在佛教兴盛时期,这带几乎每户都有一名僧人或尼姑。佛教教义在藏民中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无论是文字、绘画,还是建筑、戏剧,甚至包括民歌、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方方面面,几乎无一不与佛教有关。
所有的寺院和民居都绘有壁画,内容都与佛教有关,宗教色彩极为浓厚,所绘内容有佛像、菩萨、宗教人物、寺庙、佛经故事,以及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等。寺庙壁画有着严格的艺术规范和要求,其尺度、构图、色彩等必须与佛经的内容相吻合。这些壁画,画风简朴,色彩单纯厚重,线条简洁,风格浑厚,明显保留了藏传佛教画的传统技法。同时,因为受到内地画风的影响,画面纯净,线条挺秀,色彩和谐,造型准确。在藏族民居壁画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吉祥图案,如八瑞相(即宝瓶、宝伞、胜利幢、吉祥结、法轮、妙莲、金鱼、右旋海螺)、和气四瑞、六长寿等等。
雕塑当然是以藏传佛教的寺院里最为集中。在各地寺院里供奉着成百上千尊神态各异的佛像,着意刻画诸神的性格特征,赋予人物以个性,使之更加传神、生动,富有情趣。像昌都强巴林寺、迪庆松赞林寺、东竹林寺内的强巴佛,高达三丈以上,雕刻技艺精湛,造型逼真,上面镶嵌无数金银珠宝、琥珀、绿松石等装饰。各地寺院的门、梁、檐、柱之上均有大量的雕刻图案,或为浮雕,或为镂空精雕,刻有龙纹,云纹,八宝,花鸟等,用传统生漆漆饰,色彩绚丽。在藏族民居里也可看到这样的雕刻。
藏民们还将他们的宗教感、美感等以旷世罕见的大地艺术形式铺展在整个高原上。
据说,是米拉日巴上师发明了那弯弯曲曲,极具美感的藏文,那文字念起来带有连续不断的辅音和哑音。那文字天生就是用来赞美自然和歌唱生命的。它们能够在绵绵无尽的诵读中和不经意间直达上天,沟通此生和彼岸。
“喳嘛呢叭咪畔”,这是回荡在雪域大地上最频繁的声音。这声音不仅出自喇嘛的口,也出自老人和孩子的口。这声音还镌刻在无数的石头上,还铸造在永远从左向右顺时针旋转的转经简上,它还飘扬在无数风马旗上。据说它们能使人气息调和、血脉通畅、心安神定。它们能祛除人类和世间的各种恶业,能使心灵净化,能使精神升华。在危难的关键时刻,据说念诵它们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它甚至能使面对死亡的人坦然、超然。
如果你问一个旅行者:在滇藏川藏区见到最多的人文景观是什么?也许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玛尼堆和风马旗!
藏族为什么到处堆玛尼堆,我以为完全出自天启——在那离天最近的地方,在那最富有灵性的高原,何以表达对神奇大自然的尊崇和敬畏?唯有玛尼堆;何以将飞升的心灵精神与苍茫天地沟通?唯有玛尼堆;何以将在茫茫大地上的漫游转经朝圣的历程一一记录下来?唯有玛尼堆。那是藏民族精神累积起来的金字塔。
我最早见到这神圣的玛尼堆,是在云南迪庆的大宝寺,是在1986年。那是一座小小的宁玛派寺庙,建在一座原始古柏密布的小山上,小山周围,就是圈玛尼堆,以一块块圆形、椭圆形或各种不规则形状的石块垒成,石块上镌刻有各种各样的“喳嘛呢叭咪畔”六字真言,以及各种各样的佛像、神异动物形象和各种图案。它们像圈围墙样环绕着寺庙,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雪掩,一个个一块块显示出深刻的历史和无际的苍茫,默默无语地吐露着神秘和庄严。
后来在这一带走得多了,才发现,雪域高原上的每一座山口,每条路口,每一个村口,都矗立着座座石刻玛尼堆,飞扬着一面面、一串串五彩缤纷的风马旗,那是无数朝圣者和旅人的信念的堆叠,是人们向神们的致敬。人们相信,在积聚了自然之精华的石头上刻下经文,并供奉在天地之间,是让所有众生受用不尽的大功德,它们犹如一份盛大的礼物,来自自然又重新安放在自然之中。每一块镌刻上经文和佛像的玛尼石,都是一份虔诚而博大的心意;风马旗的每一次飘扬,都会向上界送去人们的祈愿。那吉祥的祝福布满雪域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在高原的每一片天空。藏民们虔诚地用石头石片,牛头羊头,用全部的心血和信念,堆起这醒目的神坛。他们相信这是神们聚集的地方,从这里,神们能听见人世间的祈祷,能领受人们的虔敬奉献。藏民们每经过一个玛尼堆,都要庄严地堆上几块石头,或是插上几根木棍,手扪左胸,高喊几声:“哦啦嗦!”那野性的呼喊震撼心灵、震撼山峦、震撼天宇。
组成玛尼堆的石块上有的刻满藏文经咒和多种图案造像,其文字内容多为“六字真言”(喳嘛呢叭咪畔:和各种佛教经典。而所刻造像更是丰富多彩,内容广泛。有反映苯教拜物意识的龙、鱼、日、月画像,各种鸟头、兽头人身像;有反映佛教意识的释迦,十一面千手观音、度母;各种护法神像、天王像、莲花生、文殊菩萨等佛像。云南藏区的玛尼堆上还要竖一根木柱,顶端刻出日、月、星的形状。玛尼堆石刻藏文和图案雕刻对研究藏地文化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藏族一样有如此强烈而浓厚的宗教感。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哪个民族像藏族一樣,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召唤下,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毫无反顾地在高原大地上走来走去,去朝拜他们心目中的圣城、朝拜神山圣湖、朝拜每一个神圣的地方。
我很佩服那些宗教圣徒,他们在那么遥远的年代,以最为原始的交通方式,也许仅仅凭着某种传说,总是能够寻找到超凡出世的绝美之地,赋予这些地方神圣的生命力,让后人前赴后继地景仰,而且绝不会失望。
神山圣地作为神灵居住的地方,又有众多佛教大师大德的圣迹,被公认为世界上的奇异之地,朝拜这样的地方自然就有各种功德,会增加福报。而众多百姓更普通的说法是,绕神山圣湖和圣地礼拜,可以洗尽人生的罪孽,多转的话,能够在无数的轮回中免受地狱之苦,并有好的转世,在来生享有更为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成了大多数转经朝圣者的信念。他们由此坚信,转经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修行,是种消罪积福的过程,这样做就能够止恶行善,趋吉避凶,就能够超越苦难、罪孽和死亡,达至和谐宁静善美的彼岸。
在滇藏川交界地带,在贯穿这一带的茶马古道沿途,经常会碰见成群结伙或只身一人的信徒,他们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有的甚至离乡背井达数年之久,有的甚至就在转经路上“仙逝”而去。这在藏民看来竟是最大的福份了。他们的脸上刻满了旅途的艰难,但却透露着一种宁静的满足。崎岖蜿蜒的山道上,善男信女们牵骡拄杖,络绎不绝。没有朝山转经的,被认为死后不能超度苦海,生前就要受人歧视。即使是在脖子上系根黄色或红色缨带跟随主人朝山转过经的羊只,也成了圣洁的生命,此生不许宰杀,任其自然死亡。
神山上,禁止砍伐林木、破坏水源和猎杀动物。在某种意义上,转山表达了人们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藏族不仅经常长途跋涉优游高原大地,他们也在当地打转,甚至让玛尼筒和念珠在自己手里转。在藏传佛教的寺院外围或佛殿、经堂的外侧,一般都建有经筒(也叫经轮),村子里也建有玛尼经筒房,藏传佛教信徒们,有事没事都要转上几圈。特别是那些老年人,几乎人手一个小的玛尼小经筒,不停的摇转,小玛尼筒转动几圈,就等同于诵经数遍。因为无论是大经筒还是小经筒,尽管形式,大小,质量,外观各有区别,但一律是外刻经文,内装经卷,且要顺时针转动(苯教徒除外)。许多老年信徒每日都要清晨起床前往寺院,用手依次转动经轮,绕转寺院,往往一转就是一天。如果将他们一生转动玛尼筒和转经的距离合计起来,恐怕足以绕地球几圈,甚至可以抵达月球或更远的星球。
在高原的每条路上,都有朝圣转经的藏人。他们坚定、执着,一丝不苟地行进在路上。他们在寻找理想中的香巴拉,他们在寻求解脱之道。世界上只有这个民族,一代又一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大地,用自己的五体投地来亲吻、接触生养自己的大地,用自己肉身的尺度,来缩短自己与神圣之间的距离。那是数以月计、数以年计的时间概念,那是数以千里和万里计的漫长旅途,那是数以十万计的匍匐。
他们没有显出疲劳,更没有半分抱怨。他们一个个神态平和、宁静安然,表情犹如睡足后又吮饱了乳汁的婴儿。爬山、行走仿佛就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而在这神圣的旅途中,他们人性中那些隐秘而恶劣的层面统统消失不见。
他们从来想都没想过要向雪山挑衅。他们从来承认自己在雪山面前的卑微和弱势。他们有的只是敬畏和崇信。以人的血肉之躯,没有谁会将那漫长的餐风宿露、沐雨浴雪的艰难路途当作轻松享受之旅,但他们以宗教的热忱,做到了以苦难置换幸福,以饥寒交迫寻求精神充实,以自己的脚步和身体,围绕着雪山湖泊表达他们的敬畏和崇信,从而实现了对生命和真挚感情的拥有,达到了灵魂的净化和人性美的一个超高度。
藏族是一个在路上的民族,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唤,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不可抗拒的召唤,引领着他们放下一切,走上遥远的朝圣之路。
他们主动为自己开辟出无穷尽的旅途。他们对旅途现实的苦难说“是”,对苦难的未来说“不”。他们为了希望,为了未来而忍受现实的苦难。他们就这样看着死亡行走,没有害怕,没有恐惧,任死亡在自己头顶飞翔,像他们崇敬的度母和空行母。他们就这样走啊走,一直走进了神话,一直走进了香格里拉。
因此,藏族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规范等等皆来自佛教。而一个民族如此深爱佛教,对之顶礼膜拜,将自身文化与之如此深刻融合,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在这里,当你亲眼看到那些信徒磕头、烧香、转经时,往往会被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虔诚所打动,从他们几乎毫无表情的面容上,终于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什么叫做“信仰”!
这是个时间停滞的地方,人们在停滞的时间中走过一个个山口,穿过一片片丛林,涉过一条条溪流。他们用虔诚的信仰使时钟停止了转动。
看着不停行走的转经者,我不由得想,也许世界上真有某一种力量,能够凝固住时间的流动,能够使生命长驻或轮回旋转?
人类拥有汽车、飞机之类,也不过百来年的时间,然而眼前这无垠的太空,这苍茫的大山,这喧腾不已的大江,这烙在藏族群体意识中的神圣精神,这从他们掌上升腾而起的威严畏惧和确凿信仰,这洋溢在他们面膛和眼睛的虹彩之中的宁和而厚重的理想主义光芒,使人犹遭雷击,仿佛一下子触及到了博大精深神秘无限的时空。
这也正是康韦在香格里拉深切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