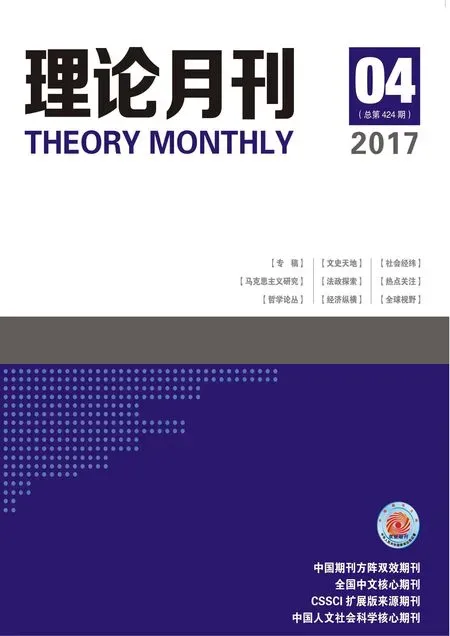晚清中国学校美术教育取向的历史考察
——以社会为中心兼以学科为中心
□ 万竹青,王昌景
(1.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上海 200241;2.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南京 210097)
晚清中国学校美术教育取向的历史考察
——以社会为中心兼以学科为中心
□ 万竹青1,王昌景2
(1.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上海 200241;2.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南京 210097)
晚清中国深刻的社会体制变革催化了学校美术教育的产生。在“西学西艺”理论影响下,晚清时期中国的教育思潮处于一种对西方的模仿期,美术教育领域同样也呈现了对西方乃至日本不同程度的效仿,它们分别体现在洋务学堂、中小学堂、师范院校等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上,反映在课程标准、课程设置、教科书上。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晚清学校美术教育形成了以两种方式为侧重点的教育取向——“政教合一”制度下的以社会为中心取向和“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以学科为中心取向。
晚清;学校;美术教育取向;以社会为中心;以学科为中心
1 晚清中国特殊的社会状况及教育背景
晚清,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体制变革。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条约》。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权,社会性质由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发生多次战争后,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成为晚清统治者应付外来侵略的唯一手段,也是其对于社会体制变革的力不从心的主要表现。这些条约的“签订”使得本来落后的晚清经济、文化体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华民族在国家主权、疆土、经济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重重“矛盾与危机”。
纵观晚清时期的文化教育,在“国家危亡”与“民族矛盾”双重“危机”激化下,学制改革响应了朝野一致的“呼声”。“光宣时代,当时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1]。无论是封建统治者还是革新的资产阶级都认同教育是改造国家的重要出路。维新派人士康有为①康有为(1858-1927)字广夏,又字长素,号更生,别署西樵山人。清光绪进士。爱国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官授工部总事,总理各国衙门章京。1898年领导“戊戍变法”。提出,中国之败,败在教育,输在人才,在《请开学校折》中他写道“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2]。内忧外患的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不得不寻求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对策,探求富国强兵的方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应运而生,它们既是政治运动,也是教育改革运动。这些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艰难尝试,虽没有从根本上对旧中国的制度进行改革,但它们带给人们的思想影响是远大的——要想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不仅仅要继承传统的“儒家”学说,更要学习满足工业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因此,晚清这一特殊阶段,中国清政府、资产阶级纷纷提倡学习西方,以西方的技术来抵御西方的侵略,“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正如近代教育史学者舒新城所言,清末时期中国的教育思潮处于一种对西方的模仿期,这些教育思想可归纳为:方言思想、军备思想、西学思想、西艺思想和西政思想。而这些思想中与美术教育相联系最为密切的即是“西学思想”和“西艺思想”。根据文献记载,当时西学所指的内容概要为:以经学、中国文学以外的各科统称为西学①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中,有一条题为《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意即如此。。其内容广泛,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此时相应的图画一科则在学堂里呈现两种学科取向:即以“制图技术”为主的应用科学取向和以“传统绘画”为主的社会科学取向。这两种学科“取向”都同时受到了西方思潮的猛烈冲击:一方面,外国的“坚船利炮”深深撞击了中国保守的儒家思想学说,在民族危机下清政府为自救不得不学习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将这种“理性的审视声音”与“现实生命价值”的回眸共同表现在图画教育方面:即严谨的制图技术;另一方面,西方带来应用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与中国传统绘画不同的社会科学,在图画上则表现为“西方绘画体系”,这两种叙事技法都是以西方世界视角、原生态地呈现给广大受众并被我们可以理性的追忆那种自身美术教育的思考和叩问。这一新兴的绘画系统与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在材质、技法、评价标准上都有所迥异,这些不同的特点亦给中国美术界以冲击,使中国学者在全盘西化、中西合璧、保守主义间争论与徘徊。
如果说西方教育理念通过塑造一系列的教育 “评判规则”并以晚清教育视角对当时社会弱势群体的集中体现的话,那么,西学的思想又进一步分化为“西政”和“西艺思想”。“西艺原为西学的一部分……学与艺并无区别……甲午过后,因日人之屡欺我而对于其变法自强的情形有较深的了解,西艺思想又进一步,乃以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为西艺”“西艺思想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二十九年(1903)之间即隐然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谓西艺均为中国古时所有,其内含有算学、天学、测量、化学、电学、光学、声学、矿学、农学、学堂、赛会、重学、汽学、力学、画图学、轮车、轮舟、火器、自鸣钟、仪器、机巧、铸象、照相、铸器等类。”[3]。从舒新城对西艺思想的诠释可以看出,当时的西艺包含画图学,也就是各种机械、轮船的制图学,其明显倾向与应用学科取向。不论西学思想还是进一步细化的西艺思想都包括图画,可见这一时期图画是学习西方教育思想的最为重要的部分。
2 洋务学堂:“图学”作为学习轮船机器等其他课程的“语言”
清政府向西方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标志,就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以改变中国的贫弱状态,振兴国力。他们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基本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省安庆建立军械所②安庆军械所是清朝1861年在安徽安庆建立的近代第一个以学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优秀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式军事工业企业,又称“安庆内军械所”,1864年迁至南京,后改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用西洋的科学技术生产武器。后又于1865年,与李鸿章一道,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
曾国藩在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新造轮船折中谈及建局意图:“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传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现已译成《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妥立课程,先从图说人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书。”[4]
曾国藩认为:当时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机器、轮船制造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究其缘由是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很好地揣度意思,因而不能够使西方技术在中国很快流通。因此在语言沟通有障碍的情况下,“图学”作为一种学习语言,更为可视化、直观化和普及化。清政府也更倾向于提倡用图说和图解的方式来介绍施工方案和工艺流程,以壮大本国军事力量、促进工商业的方法,这样也为当时的清政府提供了一个学习西方技术的良好“契机”。
这种良好的“机会”出现后,也在清政府的号召和感召下,清政府官员纷纷提出建议,例如增设实业学堂学习西方技术。“近年来风气大开,一切工艺均效法泰西,诚自强之荣也……设工艺学堂以振商务……”[5]“洋务之所当讲求焉,不同洋务则商务亦有所不明,何能与西商贸交往哉”[6]。这些学堂都重视西学对本国工商业的促进作用,并且将“图学”作为其他“泰西课程”的解读方式而视为重中之重。据文献记载,洋务派所开设的实业学堂几乎都开设图学课程,有的配有专门的画图房或绘事院。1866年福州船政局设立,其教学科目除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之外,还包括画法,主要学习绘制船图和机器图。“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7]。图画被提升到是否授予水师官职的评价标准。从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的课程中亦可以看出当时学校对图学课程的重视:第一学年,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做英文论、翻译英文。仅有7门功课里就包含一门“笔绘图”,这一课程被视为与翻译英文等课程同等重要。第二学年8门功课中包含一门“笔绘图”。第三学年6门功课中包含一门“笔绘图并机器绘图”[8]。在提倡学习西方轮船、机器的主张下,图学成为一种学习造船、机器等工艺流程的间接手段,其俨然成为实业学堂的必备课程和核心课程。

图一船中电机图:较电机器用银线制《知新报》1897年第21期

图二英机器报纺织机二十图《萃报》1897年第8期
康有为曾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疾呼:“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可见,这一时期,图学作为一门课程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力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偏向于“实用”,注重技能传授。洋务学堂提倡的图画教育更多倾向于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为主要目标,其目的是运用工艺、设计制图法来促进民族实业发展,提高器械、轮船绘图技术来制造抵抗列强、保家卫国的武器。
3 中小学堂:载以“自在画”和“用器画”为内容的图画课程以“备职业之需”
3.1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从制度上肯定了“图画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1902年,清政府派遣吴汝纶①吴汝纶(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1865年中进士。历任直录深州、翼州知州。1889年退出政界。在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并创办了几所外语学校,培养学生有1 200人之多。1902年应张百熙约聘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到日本进行考察,试图以日本学制为参照进行国内基础教育改革。管学大臣张百熙②张百熙(1874-1907),字野秋,湖南长沙人。早年担任过光绪帝的侍读。戊戌变法时,“滥举康有为”,受革职留任处分。《辛丑条约》后,“抗疏陈打计”,积极提倡变法自强,主持学务,颇得人心。以日本考察报告为基础草拟《学堂章程》,即所谓《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清政府在钦定学堂章程的基础之上作了稍许改动,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于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布,也称“癸卯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是近代第一个经法令颁布施行的学校教育章程。它从制度上规划了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对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方面进行了深化设计,对课程设置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奏定学堂章程》对中小学图画是这样规定的:初等小学图画要义在练习手眼,以养成见物留心,记其实像之性情,教学内容为简易之形体;高等小学图画要义在使知观察实物形体及临本,由教员指授画之,练成可实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习于精细,助其愉悦,教学内容为简易之形体、几何画;中学图画要义在于“习图画者,当就实物模型图谱,教自在画,俾得练习意匠,兼讲之大要,以备他日绘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教学内容第一学年到第四学年,皆为“自在画、用器画”[9]。观其教学内容,自在画与用器画为主要部分,李叔同曾对“自在画、用器画”两个画种进行了分类,自在画分为两种:西洋画和日本画;用器画分为几何画、投影画、阴影画和透视画[10]。这样的解释与西学西艺思想所谈论的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不谋而合,这也恰恰证实了中国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应用科学——即图(用器画),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西洋画和日本画。
近代早期的学堂章程虽然深受日本和西方的影响,但它的颁布却从制度上肯定了图画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图画课的对象不再局限于陶冶情操的官宦和士大夫子弟或者是作为“艺匠”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民子弟,而是从全体社会出发,对小学、中学、实业学校、高等院校都作了规定,使全体社会人员都接受图画教育,为日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基础;教学形式上从师徒传授制转型至班级授课制,教育形式的转型是图画教育不再是少数人专属的权利,而逐渐催生了教育全民化的萌芽,大大推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教学内容上突破了传统毛笔画,加入了一些现代科学技术成分如几何画、用器画等制图课程。总之,在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图画教育在国家制度保障下逐渐开展起来,在教学组织上实现了学校教育规模化,教学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3.2 教材集中于画贴、范本和几何画、用器画
清末时期中小学美术教材集中于毛笔画、铅笔画、水彩画、钢笔画和以备他日职业所用的几何画、用器画。这些教科书最早的有1902年俞梁编、文明书局出版的《笔习书帖》三本,《新习画帖》五本,《铅笔新习画帖》四本;张景良译《几何画》一本;丁宝书编《高小铅笔习画帖》以及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洪赉编 《投影画》一册、徐咏清编《铅笔习画帖》八册[11]。
据文献记载,1906年4月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中关于美术的有:文明局印刷和发行的生徒用《毛笔习画帖》三册、生徒用《毛笔新习画帖》四册、教员用《毛笔新习画帖》一册、生徒用《初等铅笔习画帖》四册、教员用《画法教法规则》一册、教员用《小学分类简单画》一册,商务馆出版、固化小学校发行的教员用《画学教科书》一册和同文印书社出版、武昌图书馆的《图画临本》一册。1906年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有:商务馆印刷和发行的学生用《高等小学毛笔习画帖》八册、《高等小学堂用铅笔习画帖》八册;湖北官书局发行的学生用《图画临本》八册、教员用《图画临本》一册;文明局印刷和发行的学生用《高等小学堂铅笔习画帖》三册、教员用《高等小学几何画教科书》一册[12]。除此之外,普遍流行于学校图画教育的还有: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高等铅笔画贴》;1907年商务出版社的《铅笔画范本》《水彩画范本》《钢笔画范本》等。
图画的实用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小学美术课堂。从当时的教科书可看出这种“以备他日绘地图、机器图”的技术倾向,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张景良编写的《小学几何画教科书》,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我国言富强垂四十年而贫弱卒如此者,何哉,夫东西国之所以日臻富强者不第政治修明而工业发达之故,其间正局多数焉,然不明算数不精图学,亦莫得而言工业……”。作者将东西国之所以富强归结于工业发达,而工业发达与精通图学紧密联系,换言之,我国应加强图学教育来发展工业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又如190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学教课书用器画》(孙钺编辑,杜亚泉校订)、1907年5月上海启智学社郭德裕编辑 《最新用器画教课书》、1908年2月北京旅京学堂出版的有日人白滨征编著的 《用器画教本》、1908年11月北京编者刊出版的(日)竹下富次郎著(阎永辉编译,阎永仁等校阅,阎清真总校)《新式中学用器画》等用器画教材中都对这种实用技术的目的有所说明。
以上教科书反映了清末阶段中小学美术教育的整体面貌和教育取向。根据汪亚尘的回忆,“各地任图画教员的人,他们所持的教授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国粹画,一种是西洋画”[13]。而从1906年4月学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也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图画的教育取向:初等小学的毛笔画帖教科书占的比重为38%,其余为西方画法和用器画;高等小学的毛笔画帖教科书比重17%,几何画的比例有所上升。总体看来,清末中国中小学美术教育在吸取西方技法的同时也注重传承本民族毛笔画的优秀传统文化;随着年级的递增,实用技能的倾向有所加重,正如李华兴在《民国教育史》中所述“普通教育中的课程设置,除初小学生年级尚幼…高小就须考虑学生皆有谋生之计虑”,“自小学校高年级起应渐渐注重用器画,使学生一方面可以得到精密,正确之思想及习惯;一方面能认识及制作简单之机械图及工程图,以助工业之发展也”[14]。
4 师范院校:“泊来”之日本课程及师资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兴学堂,一时患在无适当的各级师资,故首先注重办师范教育,这就需要造就大量师资以应急需”[15]。中小学堂图画课程的开设,图画教材的编纂、出版、发行,使得早期学校美术教育趋于正规化。而中小学美术师资的培养则更多有赖于师范学堂,因此,师范学堂美术教育的兴起成为必然。
20世纪初到民国前这一时期建立的师范学堂有两江师范学堂 (1902)、天津的北洋优级师范学堂(1902)、通州师范学校①1902年,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开中国私立师范学校之先河。该校设4年本科、2年简易科和1年讲习课,课程主要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算术、理化、史地、博物、图画、手工、体操等。(1902)、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7)、广东优级师范学堂(1906)和天津北洋女师学堂(1906)。这些学堂都相继开办图画手工专科,实行新式美术教育,以培养美术师资为目标。
4.1 师范学堂的模范:两江师范学堂及其图画课程
近代最早建立美术师范专科的师范学堂首推两江师范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两江师范学堂创立于南京北极阁下,校长李瑞清②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晚号清道人等。1893年(光绪十九年),中举人;1895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905年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教育家,曾受到日本和西方美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两江师范学堂创办了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美术师范专科,所建立的新艺术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艺术师资人才,对于开辟我国美术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拓荒作用。两江师范学堂共计办10年。此10年中,全办优级,初仅设史地、数理化、博物等科,后添办图画、手工为主科外,并以音乐为副主科,规定三年半毕业。共办过甲乙两个班,毕业生共有六七十人。教师除萧俊贤等外,还有好几个日本人。我国最早的一辈艺术教育师资,如吕凤子、姜丹书、沈溪桥、吴溉亭等都是该校出身[16]。
两江师范学堂美术师范专科以 “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其中的“图画课”为:素描(铅笔、木炭)、水彩画、油画、用器画(平面几何画、立体几何画……正投影画、均角投影画、倾斜投影画、透视画、图法几何等),图案画、中国画(山水、花卉)。西画教师:盐见竞(日人)。用器画教师:亘理宽之助(日人)、盐见竞。中国画教师:萧俊贤(字厔泉,湖南衡阳人)[17]。课程设置对应中小学图画课程,以自在画和用器画为主,而自在画以西画、中国画为载体,用器画以几何画、透视画、图案画为载体,体现了中小学与师范教育课程的连贯性。
当时的师范学堂美术教材,是与中学大部分相同的,即如前文所述的西画教育倾向的习画帖和实用美术倾向的用器画,以及日本人井村雄之助编的画贴《洋画讲义录》。这些书也是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最早的教科书[18]。另有不同于中学图画课程的、适合于当时情境且较便捷的图画教习方法即黑板范画。“清光绪末年各中小学校都设有图画、手工、唱歌课。记得我在高等小学里学的图画是临摹,教师在黑板上用粉笔绘范本……这就是当时的图画教学”[19]。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师范学堂用《黑板画教科书》即证实了当时的教学方法——黑板范画。

两江师范学堂作为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有利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师范学校的发展,而培养的优秀师资又惠及了各地中小学校。正如姜丹书所说:“此辈专门艺术师资造成后,再分头服务于各省,主教图画手工专科,如此辗转造就师资,艺术教育始得逐渐推广,而普及于一般中小学校。”
4.2 师范学堂多从日本引进师资
在师资方面,清政府更倾向于从日本引进师资以加强学校教育的力量。1902年,清政府派遣吴汝纶访问日本,向日方正式提出延请教师事宜,日本接到请求之后,开始在国内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师范教员中选拔,经过短期培训之后,派往中国[20]。汪向荣先生根据日本教习中岛半次郎在1909年11月间的调查基础上罗列了一份表格,其中摘录出来一些有关的美术教员的名单,从这些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清末时期日本学者散布于各个师范学堂中。
如两江师范学堂(南京)的图画教师:山田荣吉、伊藤村雄、亘理宽之助;山西优级师范学堂(山西太原)的图画教师: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丸野野;南京高等学堂的图画教师: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棍原熊雄;江苏两级师范学堂(苏州)的图画教师:村井里之辅;女子师范学堂(南通)的图画教师:森田政子;北洋师范学堂(北京)的图画教师: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安成一雄(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教员)等。
日本荫山雅博的 《清末教育近代化过程与日本人教习》一书亦记载了有关日本美术教习在中国师范学堂的情况。1909年在中国就有8名日本教师任教于图画科目,2人担任工艺科目的美术教学。之后的1907到1910年期间,先后有5名日本美术教师在两江师范学堂任教,在以日本美术教师为图画、手工教学力量的支持下,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开办不到5年时间就培养了两届共69名毕业生,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批美术教育师资队伍,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开拓创造了条件”[21]。
日本师资对中国近代早期的师范学堂贡献了应有的力量,他们所培养的中国近代最早一批美术师资促进了全国各地中小学堂的图画教育,使美术教育逐渐推广。师范学校的建立和扩展促进了教育、经济乃至社会的发展,正如贺拉斯·曼所说的那样:“师范学校之重要,宛如弹簧一样,在师范教育中聚缩着一股活力,它一旦舒张开来,就会推动各项事业。”
5 结论
20世纪美国美术教育家埃利奥特·W·艾斯纳(Eisner,E.W.)①埃利奥特·W·艾斯纳(E.W.Eisner)(1933-2014),斯坦福大学杰克·李教育学教授、艺术教授。曾在芝加哥大学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后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设计研究院学习设计及艺术教育。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艾斯纳的美术教育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本质论,又被称为“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Discipline-Based Education简称DBAE)。本质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主流。在他的研究中提到,历史中美术教育的各种侧重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其中一个顶点代表以社会为中心的观点,第二个代表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第三个代表以学科为中心的观点[22]。纵观中外美术教育历史,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美术教育取向,晚清美术教育形成了两种方式为侧重点的教育取向——“政教合一”制度下的以社会为中心取向和“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以学科为中心取向。
5.1 民族危机下,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取向
中国教育的特点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教育政治化。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为维护封建统治,倡导所有的学说都为“政治服务”,教育是科举的附庸,学校亦是官员培训所。中国士子所欲的思想、论述全是儒家经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教学内容仅以四书五经、八股词章为法定范围,教育目标以人伦道德和培养官吏为唯一宗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接受外国变相侵略。故步自封的中国在与外国政治周旋的过程中认识到外国科学技术的先进之处,终于从全盘排斥到慢慢接受,进而主动学习。民间呐喊,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最有影响;政府方面,则以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鼓吹“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劝学篇》举足轻重。全国各地洋务学堂的开设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表现在美术教育方面,图画则作为一种应用技术科学被提到国家教育制度层面。图画、制图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工业机械设计、轮船制造、民族实业等社会各层面,其作为美术学科的一个分支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社会为中心的观点将教育看成一种通过公立学校组织起来的社会机制,将文化传统传给年轻一代。这种观点将学校教育计划看成满足社会需要的载体,如果社会需要更多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教学计划就应该强调培养这些技能”[23]。从洋务学堂课程中可以看出,图画正是以机器制图、轮船画图学等课程呈现出来,以提高军事、工业技术为手段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中小学堂图画课程亦是在原有以陶冶情操为宗旨的基础上增设实用主义美术教育目的,大力倡导增加振兴国民经济的几何画、用器画课程,其课程开设的目的是以增强国力、繁荣民族实业为目的,因而可以看成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取向。图画的目标在于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机械工程师、民族实业家。
5.2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学科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取向
所谓西学东渐,泛指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自西徂东、敷布中土的过程[24]。美术作为一种人文学科,亦深受西方的“影响”。它一方面表现为西方绘画向中国的辐射与渗透;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吸纳和消化西方绘画,将西方绘画融入中国绘画,成为特定的中国本土绘画。中国美术学科从保守的毛笔国画技法逐渐接纳和吸收西方的绘画技法,使之更开放、更具有世界性。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逐渐形成了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取向。“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计划的目标、内容和教学方法重视学科的完整性,对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运用,及其内在价值。在这种美术教育目标的观点指导下,教师要重视美术本身的研究”[25]。晚清,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绘画体系迅速涌入中国,一些学者对西方画法进行了积极地探讨。如1905年发表在醒狮杂志的 《水彩画法》解释了西方水彩画——“西洋画凡十数种。唯与我国旧画法稍近者唯水彩画。”,而1907年商务出版社便出版了针对中学的《水彩画》范本;《图画修得法》[26]中对图画课程的内容作了总结:“图画之种类至繁綦赜。匪一言所可殚。然以性质上言之判。图与画为两种。若建筑图制作图装饰图模样等。又不关于美术工艺上者。有地图海图见取图测量图解剖图等皆为之图。多假器械而补助之成之。”又如1907年发表美术杂志上的 《西洋画科》、1906年环球中国学生报上的 《美术通诠》、1908年实业报上的《西方颜料制作法》等多篇文章对西方美术教育体系进行了详尽的诠释和说明。这些史料证明,在“西学东渐”的驱使下,晚清中国原有的以毛笔画为主美术教育体系不再孤立,而是兼容并蓄,打开怀抱积极地接纳西方美术教育体系。而中小学、师范院校西画课程的增加,使教师不得不对水彩画、钢笔画、铅笔画等来源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的加以审思和研究,无疑,这段时间的美术教育体系较之前更加完整,美术学科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以学科为中心的美术教育更注重延续和发展美术知识与技能,以满足人类社会物质、精神和文化的需求”。西方美术知识与技能,在中国晚清这一特殊时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和发展。
5.3 待发展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取向观
艾斯纳认为“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其目的、内容和方法的起点是:美术或者其它科目教育计划的内容必须首先用于解开儿童潜力之锁,教育内容是自我意识的工具,教师的首要职责是充分了解学生以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通过对奏定学堂章程和当时的教科书的解读可以看出,在清末这一阶段以儿童为中心的创造性美术教育取向在中小学阶段尚未提及,而是更倾向于如上文所述的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学科为中心的美术教育取向。我国美术教育家尹少淳认为,中小学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美术教育促进学生思想与道德的发展、情感与审美的发展、智力发展、人格与心理发展和个性与创造力的发展[27]。美国美术教育学家罗恩菲德(Viktor Lowenfeld)认为,中等学校和小学课程中的艺术教育在发展个人心灵、感情和关感的成长,注重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未来生活作好准备。在艺术教育里,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富创造力,而不管这种创造力施用于何处。假如孩子长大了,而由他的美感经验获得较高的创造力,并将之应用于生活和职业,那么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已达成[28]。显然,清末时期的中小学美术教育聚焦于实业美术技巧的培训,如《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几何画、用器画课程,其目标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而不是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目的过于急功近利和片面,只注重当前社会的需求,而没有从长远角度看人与社会的整体互动关系。台湾美术教育家黄冬富也认为“以今日观点视之,仍然未曾考量儿童造形心理发展能力之配合”[29]。这一局限,在民国建立以后蔡元培的领导下得到弥补,美术教育渐渐踏上了“以美育代宗教”的道路上,美术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完善个人全面发展,以达到改善整个社会的目的。但艾斯纳也认为,“美术教育对教育事业有独特的贡献,虽然在不同时间美术可能有需要被用来实现别的教育目的,这些其它目的应该被看作短期目标,这些短期目标对于实现只有美术可以达到的目的是有必要的。 ”[30]
[1]梁任公莅教育部演词[J].东方杂志,1917(14):3.
[2]陈学询.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10.
[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62.
[4]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李鸿章校刊.曾国藩奏折[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394.
[5]政事:湖北擬设工艺学堂[N].集成报,1898(26):19.
[6]论川东设立洋务学塾[N].万国公报,1892(10):47.
[7]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二十[M].上海:上海古香阁,1902:62-68.
[8]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M].上海:上海译书局,1898:18-25.
[9]章咸,张援.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54.
[10]弘一大师全集编委会.弘一大师全集:第7卷·图画修得法[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445.
[11][12]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170,40.
[13]庄俞,贺圣鼐.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M].商务印书馆,1931:234.
[14][26]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84,23.
[15]姜丹书.我国五十年来艺术教育史料之一页[J].美术研究,1959(1):55.
[16][19]吴梦非.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段[J].美术研究,1952(4):11,12.
[17]朱伯雄,陈瑞林.中国西画五十年[M].北京:人民美术出社,1989:80.
[18]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M].浙江: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20.
[20]张少君.中国近现代学校美术教育形成与发展时期师资状况分析[J].艺术百家,2007(4):172.
[21]胡光华.20世纪上半叶来华外籍美术教授(习)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J].中国美术教育,2003(3): 48.
[22][23][25][30]艾斯纳(Eisner,E.W.).儿童的知觉与视觉的发展[M].孙宏,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51,56,33,63.
[24]陈媛,周治军.论近代中国大学教授群体的演变动力[J].江苏高教,2008(4):34.
[26]息霜.图画修得法[J].醒狮,1905(3):87.
[27]尹少淳.美术教育学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69.
[28]罗恩菲德.创造与心智的成长[M].王德育,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35.
[29]黄冬富.中国美术教育史[M].台北:师大书苑发行,2003:252.
责任编辑 刘宏兰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4.008
G633.95=52
A
1004-0544(2017)04-0053-07
万竹青(1983-),女,江苏连云港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博士生;王昌景(1966-),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