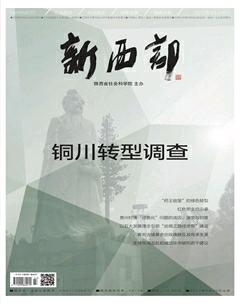贵州村落“过疏化”问题的成因、演变与对策
李航 袁婧
村落“过疏化”是任何一个进入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必然发生的社会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国家大力推动反贫工作的背景之下,贵州依然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范围最广和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其贫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那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位于高原山区的“过疏化”村落。精准扶贫是应对村落“过疏化”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除此以外,还应采取综合性措施以激活乡村社会,促进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实现了腾飞,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2016年3月9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介绍说,我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已经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1]这样一个反贫事业的成就如果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做支撑是不可能取得的,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则必然伴随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讲,两个进程也是经济现代化的显著标志,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引发了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变。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表现为农业经济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工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比重迅速上升,我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工业化国家。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则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和收入差距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的农业人口比重在迅速下降,城市化推动人口由乡村大量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呈现逐步拉大的态势,存在两极分化的风险。近年来逐渐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的村落“过疏化”问题,就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村落的“过疏化”及其在贵州的表现
“过疏化”的概念源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短期内实现了产业化与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出现了人口“由乡村后进地域向都市先进发达地域快速流动的趋向”,日本学者将之称为村落的“过疏化”。[2]而村落“过疏化”的现实表现就是村落人口的减少,留居乡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低下,生活信念也缺乏活力。
村落“过疏化”并不是日本的“专利”,它实际上是任何一个进入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必然发生的社会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与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束缚被逐渐打破,发达地区的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欠发达地区包括城市和乡村人口特别是后者向发达地区城市集中的趋势都十分明显。
贵州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相对落后。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的规模十分巨大,这些流出人口当中乡村人口又占据了绝大比例,加之贵州高原山地众多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贵州的村落“过疏化”问题尤为凸显,出现了人口数量稀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生活信念缺失的景象。在国家大力推动反贫工作的背景之下,贵州依然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范围最广和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其贫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那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位于高原山区的“过疏化”村落。《中国农村扶贫纲要(2011-2020)》中,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并将其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其中武陵山区包括贵州的15个县(市、区)、乌蒙山区包含贵州的10个县(市、区)、滇桂黔石漠化区包含贵州的40个县(市、区),贵州共有65县(市、区)进入新一轮的扶贫开发连片特困区。从《纲要》中可知,中央已从顶层设计上认识到了村落“过疏化”问题的解决对于扶贫、减贫工作的有效推动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纲要》,我们会发现村落的“过疏化”问题在贵州更为突出,解决的难度也更大。
村落“过疏化”问题的发展演变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从农村开启的。1978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推行,在农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和农民收入快速增加的同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大量产生。为了解决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逐渐地,数量众多的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国家也给予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农民在距离家乡不太远的乡镇打工就可解决自身的生计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村落走向“过疏化”的开始。贵州同样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全省主要地州市的乡镇都成为了各自下辖村寨人口的流向地,暂时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因城市具有人口集中、经济基础好、集约效益高等特点,自然成为各个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城市的繁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受到自然和技术发展条件的制约,无限地快速提高是不实际的,加之国家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转移,使得城市的发展快速提升,城市的物理边界越扩越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而城市的新增人口又多数来自乡村。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贵州就开始了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出,流出的人口部分集中在本省及周边省份的中心城市,更多地还是流向了东南沿海等发达省份和地区。在此阶段,贵州的村落“过疏化”问题开始加剧。
进入新世纪,国家出台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促使城乡经济社会要进一步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纪初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和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目的就是要促进城乡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尽管乡村的面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法否认的是乡村持续走向凋敝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长期困扰乡村社会的“三留守”问题即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问题十分突出,乡村在整体上看仍然没有焕发其本该具有的活力。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1月最早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它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可见这一概念最初就是针对乡村扶贫而提出来的,尽管精准扶贫概念的外延后来扩展到城乡的所有贫困对象,但其对象的主体仍然在乡村。因此,我们认为精准扶贫可以成为一种应对村落“过疏化”问题的重要和有效的手段。
“过疏化”村落的激活与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精准扶贫是应对村落“过疏化”问题的重要手段,那么就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即将有限的人力与资源真正投入到乡村的贫困对象身上,增强其自身抵御返贫的能力。与此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精准扶贫还不是激活“过疏化”村落的惟一手段,这是一个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性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的长期过程。
2013年,财政部将贵州列为全国七个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省份之一,投入了很大的支持力度,同时也要求试点省份出台配套措施、政策和资金支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继续抓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逐步实现道路硬化、卫生净化、村庄绿化、村庄亮化、环境美化等目标,改善村容村貌和农民人居环境,为乡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农家乐等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促进农村产业形态优化升级;加强中心村和农村新社区建设,推动有条件的行政村、自然村落归并整合,优化村庄布局,引导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居住,节约集约土地;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的长效管護机制。贵州为此制订了总投资1510.68亿元,包括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在内的六个美丽乡村行动计划。[3]很明显,从财政部到贵州省对于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出台的各项措施更加倾向于对贵州“过疏化”村落的物质“改造”,而对“过疏化”村落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关照却略显不足,这也恰是未来村落“过疏化”问题应对工作的重点努力方向,比如可以在组织制度的建设、民间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唤醒村民对自己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方面加大工作的力度。最终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真正激活“过疏化”村落的活力,真正达到乡村与城市的繁荣共处、美美与共。
有人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乡村走向消亡的过程。还有人说,乡村可以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继续保持繁荣,后一种观点近年来得到了更多的认同。作为人类史上最早的文明——乡村文明,完全可以与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逐渐崛起的文明——城市文明和谐共处,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将为人类提供更为多样和理想的选择,而不至于让乡村消亡或是仅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参考文献
[1]张烁.我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到2015年减少7.1亿[EB/OL].人民网-人民日报,2016-3-10.
[2][日]内藤正中.过疏和新产都[M].今井书店,1968:29.
[3]王军善.七省市重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N].中国改革报,2013-1-8(9).
作者简介
李 航 遵义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袁 婧 遵义师范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