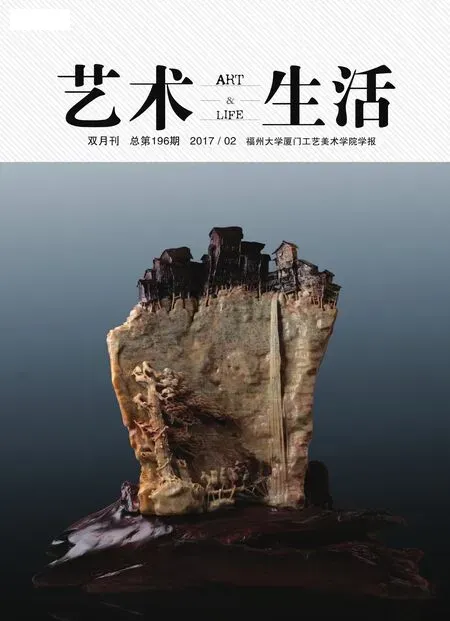四川省宣汉县清代曾氏墓葬建筑雕刻装饰艺术探究
涂天丽 罗楠
(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404100)
四川地区遗存有大量清代民间石质墓葬建筑,其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被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对象。宣汉县的曾氏墓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家族墓群,建筑外观模仿了中国高等级传统建筑。该墓建筑规模较大,装饰内容丰富,雕刻技法精湛纯熟,有着极强的装饰性。墓葬建筑在当地被称为“花碑”,可以想象墓葬建筑外观的华美盛况。而曾氏墓就如传闻所言,其墓葬建筑雕刻的丰富多样的装饰就如同一座“花碑”,这样的精致华丽的墓葬建筑,一方面是厚葬观念的折射,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清代民间匠人的高超艺术修养。文章通过对该墓葬雕刻装饰分析,探究该墓葬建筑雕刻装饰的艺术旨趣。
一、曾氏墓概述
曾氏墓位于四川省宣汉县,是一座家族墓群,由院落式组合形式的墓葬建筑构成,建筑外观模仿了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墓群分为三座碑楼,中间是主体墓碑,左右两侧各有一座陪碑,四周茔墙环绕,山门立有牌坊,该墓群占地面积宽阔、体量高大、雕刻精美,是该地区较为典型的墓葬建筑样。“中国建筑是装饰的建筑”[1],装饰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曾氏墓群也可以说是“装饰”的建筑,丰富的装饰是该墓最显著的特点。从建筑的山门到建筑的主体碑楼,甚至在陪碑这样的附属构件中,都布满了繁复多样的雕刻装饰,装饰内容多样、雕刻手法细腻、艺人技法高超,是清代民间雕刻装饰艺术的典范(图1)。
二、造型结构的对称性


图1 宣汉曾氏墓群 罗晓欢摄影

图2 亡堂左右次间 罗晓欢摄影

图3 左侧碑楼左右次间碑版 罗晓欢摄影
对称是形式美法则之一,人们把对称视为形式美法则,是因为在大自然中存在着许多对称的现象。对称首先来自于我们自身的人体,人们在对自然及审美对象的长期关照中,发现了对称中所具有的美。古希腊的美学家们早就指出:“人体美确实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不仅如此,对称性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也是常用的法则,对称的建筑宜于表现静态的稳重和沉静,对称使人感到整齐、庄重、安静,对称可以突出中心,这恰合了传统建筑中庄严的礼仪性成分。墓碑作为礼仪性建筑的仿制,对称性是其必然选择,墓碑建筑的雕刻装饰造型也大多以对称的方式展现。在传统的对称的图案中,有相对对称、均衡对称和相似对称这三种对称方式。曾氏墓的雕刻装饰中兼而有之,以相似对称和均衡对称的运用较为典型。
相似对称,即图案的纹样是并不是雷同的对称,而是在对称中富于变化,相似对称可以表现不同的内容,丰富墓碑装饰。在该墓葬建筑中间主体碑楼的亡堂左右两侧次间中,雕刻了两幅装饰植物装饰花卉,左右两侧次间的门框雕刻都是以植物为元素进行的装饰,两边的装饰看起来非常相像,但是在具体的造型设计中,花卉的穿插、走向、布局都有着明显区分,是两幅不同的装饰,看起来虽然相似,实则不同,这可称之为相似原则,是民间美术中常用的一种造型方式(图2)。相似的造型方式,在符合了庄严对称的丧葬礼仪情境的同时,又能从中变化而不至于呆板,遵循了传统图案中统一和变化、均衡与对称的审美法则。这种造型结构,彼此响应,左右相称,显得庄重严肃,也给人一种自然、稳重、平衡的感觉,产生和谐、统一的美学效果。
均衡对称是指在造型艺术作品的画面上,不同部分和造型因素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空间关系。也即是指在左右两边的造型不对称,但是视觉上却不会失去平衡的视觉效果。在传统造型艺术中,通常也会如此,为了丰富画面内容,在对称的两边设计不同的样式,既能满足对丰富画面的需要,也能使两边产生均衡的效果,这种即是均衡对称。
曾氏墓在某些雕刻造型的设计中,就采用了均衡对称方式造型。如曾氏墓左侧碑楼,碑楼左右次间的碑版两边各雕刻两幅场景人物,左边的碑版雕有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刻画三个人物,两个人物对其中一人作揖;下面部分刻画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场景,从其两幅的人物及环境表现,应该为世俗生活场景的再现。右侧亦刻画了数个人物,但环境的设置跟左边碑版雕刻明显不同,左上角雕有房舍,画面大面勾勒了云雾缭绕的仙人场景,人物姿态迥异,腾云驾雾,这应为神仙鬼怪的场景。两幅画面表达了不同的主题,人物的设置安排和环境的营造都有着严格区分,这种均衡的搭配方式,虽然画面不一样,但是也能起到两侧和谐平衡的视觉效果(图3)。
该碑楼二层额枋的雕刻也非常精彩,额枋一般是雕刻塑造的重点,这里通常会设计大量的戏剧人物雕刻,而该部位却并非如此,这里刻画的是两幅以动物和植物为主题表达的场景。额枋的左边雕刻植物花卉,中间雕刻一个硕大的牡丹,两侧陪衬叶脉,花朵雕刻较深,两侧较浅,主题突出;右侧雕刻的则更左边不同,右边的雕刻是动物和植物的组合样式,左右两侧刻画两幅相同的植物叶片,纹路和走向相向而行,中间则是两只相对的兔子,做低头样子,周围衬以树木,兔子的雕刻手法简洁,看把兔子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因此形象鲜明突出。额枋这两幅雕刻形象造型结构和表达的主题思想都各不同相同,是两幅不同的独立装饰内容,但这样的装饰表达并没有显得突兀,反而起到平衡碑楼两边的视觉作用,也丰富了墓葬建筑的装饰内容(图4)。
三、追求“满密”的空间布局
罗晓欢在《川东、北地区清代墓碑建筑装饰结构研究》说道:“民间艺术对热闹、丰富、满密、完整的崇尚,当然与后者奢靡的传统相关,但是这种对满密、对丰富的追求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特殊文化心理。通过对这种密集以占有更多的东西,以显示自己及其家族在财力、收入、人口等方面的发达,才是重要的动机。”[2]在墓葬建筑中,这句话可以得到印证。
如该墓的牌坊构件,牌坊在古代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修造的建筑,而曾氏墓的牌坊修建的异常高大,三重檐庑殿顶,看起来非常气派,可知墓主人在当时应该是有着较高的身份地位的的人。牌坊在墓葬建筑中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位置,由于位置的特殊性,就如同的人的脸,就像门面一样重要,因而牌坊的装饰性不言而喻。从画面可以直观看到,该墓在牌坊雕刻了大量精美的装饰,整个牌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布满了形形色色的雕刻,看起来纷繁多彩。无论是像牌坊的亡堂和额枋这样的重要构件,还是立柱的边角空间,画面在雕刻的设计上,几乎不留空白,各种人物、动物、植物、书法等的形象自由穿插其间。牌坊的装饰看起来非常密集,每个空白处的构件都填补了合理的雕刻装饰,画面看起来非常的丰富,这样的组合方式,正是民间艺人对于热闹、满密、繁复的喜好(图5)。
这样的“满”不仅是牌坊上有着众多雕刻内容的体现,在雕刻相对比较单一的对象上,也体现了这种所谓的“满”。
在曾氏墓群的中间碑楼的碑版上则是另一种“满”的体现。在画面的额枋部位,雕刻了数十个人物,以及映衬环境的房屋、船桨等,画面可分为几段不同的场景,人物形态各不相同,画面布局紧凑,在狭小的空间里雕刻了众多人物形象,布满画面。在额枋下面是两块碑版,两幅碑版造型相同,中间是牌位,牌位的四周以植物纹样作为装饰。碑版的左右两侧和上部是以博古纹为元素搭配花卉纹样进行的组合装饰,画面装饰内容较为单一,但是是画面的布局非常饱满,简单的植物纹样和博古纹将大面积的碑版装饰得非常充实。额枋和碑版这样的构图方式这正是基于“满”的造型理念。

图4 左侧碑楼额枋 罗晓欢摄影

图5 牌坊
前文所言,在碑楼的大空间中体现的是一种“满”的布局方式,那么在碑楼的局部小空间的具体雕刻上,则可以用“密”来形容。密,在这里的指的是密集,对象安排上的密集,也就是在一幅小的画面中,穿插了许多对象在内,使画面看起来丰富密集。在该墓葬建筑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密集雕刻。
在牌坊的右次间碑版雕刻着男子读书的画面,碑版宽高都不超过一米,单画面却穿插了众多形象。人物呈坐姿跷二郎腿坐于椅子之上,手拿书本,男子前面雕有桌子,桌子上有茶几等生活学习用品,人物的后面是环境的雕刻,深浮雕的手法刻画了房屋屋檐,内饰以那个年代的众多服饰等挂件,画面的四周边角也添加装饰。画面不留多余的空白,布局紧密,在这个非常有限的空间里,匠人却将世人生活学习的状态和场景都复述出来,画面的紧凑而又合理的布局,看起来密而不乱,将那个时代的书生读书的形象完整地展现出来。
在牌坊的的亡堂部位,也有着一幅密集场景的雕刻装饰场景。亡堂以字牌匾为主题,牌位中间镌刻文字,四周则是人物装饰。雕刻共有人物10人,左右对称2个,上部分6个,其中有7个老者,1个青年男子,1个女子女子怀抱婴儿,人物的大小略有区别,形态各异,人物衣着飘逸,如同飞升的神仙形象。这幅画面在这样的狭小的空间里安排如此众多人物,且错落有致。匠师在这样极小的空间将繁密的形象布置结合着自身高超的技艺表现,才能使墓葬艺术看起如此的精致美奂(图6)。
四、繁复新巧的雕刻层次表现

图6 牌位亡堂 罗晓欢摄影

图7 碑楼亡堂 罗晓欢摄影
在该墓群中间的碑楼亡堂部分,则是一副精彩的雕刻技法的展现。亡堂作为墓葬建筑的一个特殊空间,有着特定的礼制意义,尽管作为一个狭小的空间,但这里却有着重要地位,从而亡堂也成为了匠师打造的重点。该亡堂是中间是“亚”字型牌位,这是亡堂中常见的安排,亡堂的边柱两侧是两个胡须老者,头戴帽子,左右两边人物的稍有区别,左侧人物雕刻较浅,体型比较扁平,右侧人物雕刻较深,形象比较立体圆润,形象更为突出,这或许是一种等级的体现。
亡堂的上部横梁为花卉和禽鸟组合图案,花朵以深浮雕刻画,形象鲜明,植物纹脉自由舒展,少部分有镂空雕,禽鸟刻画细致,站立于枝条之上,画面和谐生动。亡堂的下部为两个相向的狮子,狮子刻画简洁明了。牌位四周则刻画了大小各异的11个人物,分布于前后、左右、上下。雕刻的层次多样,尤其是牌位上部分的老人形象刻画得尤其精彩,老人乘坐仙鹤,仙鹤的翅膀采用了深浮雕刻画了多个层次,形象灵气生动;老人的后面雕有两只手捧蟠桃的猴子,形象活泼;牌位的左右两周则雕刻了10个人物,安排有前后之分,前面6个人物较大,后面4个形象反之,这两组人物雕刻前后安排有序,人物刻画细腻逼真,多层次的布局安排使画面看起具有艺术的美感,更是该地区清代民间艺匠高超雕刻技艺的展现(图7)。
罗晓欢在《四川地区清代墓碑建筑稍间与尽间的雕刻图像研究》言道:“通过那些熟悉的人物、奇幻的传说、宏大的场面、复杂的构图、高超的工艺技巧所创造出来的观看的愉悦背后,既有造墓人的用心、匠师的炫技;也有对传统教化、审美、习俗的多重层次的指示性。”[3]其中谈到匠师的炫技,在曾氏墓的雕刻装饰中或许也可以这么理解,正如上述所言的精彩雕刻,是匠师施展才艺的一种体现。匠师借助墓葬建筑这一载体发挥自身高超的技艺,在获得了自己的成就的同时,使得四川地区的墓葬建筑雕刻装饰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结语
四川地区的墓葬建筑是在明清时期的厚葬文化观念下衍生的产物,在丧葬文化的影响下,对墓葬建筑形式的打造也就极为用心。曾氏墓从对墓葬建筑外观形式的打造、雕刻装饰的图案设计、装饰内容的布局形式、雕刻技法的精深实施,体现了该墓葬建筑的艺术审美特点。从其墓葬建筑体现的装饰内容和精湛的雕刻技艺可以推断当时的民间艺人有着较高的艺术审美和操作能力。这些民间匠师可以称之为民间的艺术家,代表了那个时代民间艺人的水平。墓葬建筑作为一种丧葬的礼仪性建筑,在表达象征性作用的同时,使其建筑的装饰艺术有了丧葬以外的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庄裕光,胡石.中国古代建筑装饰[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2]罗晓欢.川东、北地区清代墓碑建筑装饰结构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4(5).
[3]罗晓欢.四川地区清代墓碑建筑稍间与尽间的雕刻图像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