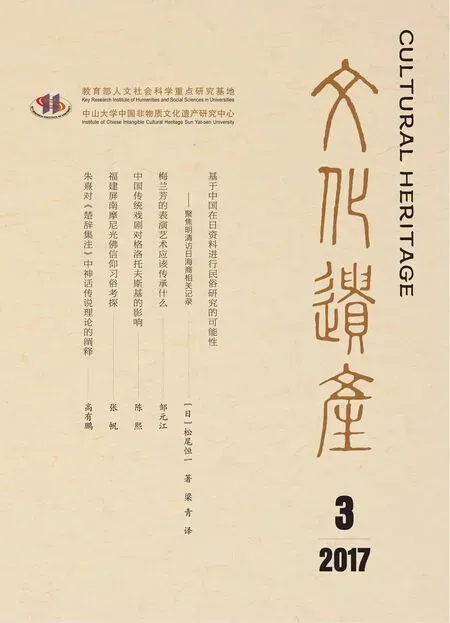西汉“九主”传说探论
孙燕红
西汉“九主”传说探论
孙燕红
《史记·殷本纪》有伊尹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未有详论,后世不得其意。马王堆汉墓帛书《九主》及《九主图》的出土,为追溯文本来源提供了史料。本文以帛书《九主》与《史记·殷本纪》《别录》等为文献参照,探讨“九主”的内容及其在文献记载上的变迁,分析帛书《九主》记载,对九主的含义和九主故事做一个统合的疏理和解读。
九主 八啇 史记 帛书
一、九主传说的由来
《史记·殷本纪》载:“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之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文中提到伊尹与汤之关系,以及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被司马迁采入《殷本纪》的史料。《殷本纪》并未详细记载“九主之事”是什么,即使“素王及九主之事”可以说是伊尹施政理念的总领。既然是政治纲领,必有其重要地位和详细内容,然而,无论是否史实,《殷本纪》并未言明,这给后人的造成认知难点。文献记载,最早与此有关的注解,出自汉成帝、元帝时期的刘向。据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録》云:“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①(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页。
《史记》成书于武帝时期,刘向《别录》编撰于成元之际,《汉书·艺文志》: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②(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司马氏父子在撰写《史记》时应见过与“九主”有关的资料,刘向校书必定是检校整理过与“九主”有关的书籍才能在校阅之后写成书录,九主之名得以保存。所以,至少在西汉之时,石渠阁保存有记载“九主之事”的文章。后来书籍散佚焚毁,也可能“九主之事”这样的文章不再受关注,在典籍的选择中被淘汰。那么,“九主”除了刘向记录下来的名称,各有什么含义,“九主之事”是怎样的故事,在未有新材料之前,注解者各有所说。
唐司马贞《史记索隠》曰:
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谓九皇也。然按注刘向所称九主,载之《七録》,名称甚奇,不知所凭据耳。法君,谓用法严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劳君,谓勤劳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谓定等威,均禄赏,若髙祖封功臣,侯雍齿也。授君,谓人君不能自理,而政归其臣,若燕王哙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专君,谓专已独断,不任贤臣,若汉宣之比也。破君,谓轻敌致冦,国灭君死,若楚戊、吴濞等是也。寄君,谓人困于下,主骄于上,离析可待,故孟轲谓之‘寄君’也。*按:今《孟子》中无“寄君”之说,(清)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卷九《孟子》二:“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刘向《七録》载九主之说,一曰寄君谓人困于下,主骄于上,离析可待,故孟轲谓之寄君也。按:今孟子书但言诸侯失国托于诸侯,似是寄君之谓,又非民困主骄,离析可待者也,恐七録所记有讹”(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国君,国当为‘固’,字之讹耳。固,谓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苗智伯之类也。三岁社君,谓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汉昭、平等是也。又注本九主,谓法君、劳君、等君、专君、授君、破君、国君,以三岁社君为二,恐非。”*(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94页。
据上可知,司马贞虽然认为九主指三皇五帝及夏禹,或九皇,但同时也依《别录》所记载九主之名,与上古至西汉诸君进行比附推论。另据《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亦有类似的循名而责实的描述。*按:此段,《考证》有脱文,今据《校补》。(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吏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页。又,关于《史记会注考证》所辑《史记正义》佚文,研究者多有辨其真伪者,本文对此不予讨论。而关于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此条,有研究者认为泷川资言所辑《正义》佚文当为真,《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二卷《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正义》佚文的真实性可以通过他证、旁证、本证等来加以确认。《正义》佚文之可自证于《史记》者,如《殷本纪》: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此条较之今本所存之《集解》及《索隐》,佚文之释文论事与《集解》、《索隐》极为关切、得当;其体例、语气亦与《正义》合。且其内容与《索隐》多近似,若为后人读书笔记,无需在《索隐》之上重录一过。”(张玉春、应三玉著,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536页)
不过,北宋董逌撰《广川画跋·书九主图后》对此类做法进行了批评:
九主图,本伊尹事,世失其传,或书以汉九君者,误也。夫以法君况髙祖,以专为孝文,以授为景,以劳为武,犹有类取也。谓昭为等,谓宣为寄,则名与实戾。元帝柔仁,基祸汉室,其谓破君,理有信者。及谓成为国,谓哀为三岁社君,则又不可也。昔伊尹干汤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说,是亦以人主九事要其君尔。后世托之画图,谓当时有此制也。此说或然,亦未可必其信,岂可谓汉世诸帝哉。九主非有名号,以治功效者,知所后先,人主于此可以取法矣,是亦不可废也。*(宋)董逌:《广川画跋》,《丛书集成初编》第163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页。
董逌认为将“九主”与汉代的九位皇帝相比附是错误的,他认为,伊尹所说的“九主之事”是指“人主九事”,“九主非有名号,以治功效者,知所后先,人主于此可以取法矣”。
从文献记载来看,对“九主”的说法,主要是从《史记集解》所引《别录》而来,但是,对《别录》的记载,诸说在理解和认识上有很多不同,如在“九主”的名称、数量、次序、解说上不一致。从汉至南朝宋至唐而宋,每隔两三百年便有学者做出解读。注解者没有见到九主文本,引用注本也不单一,因而出现猜测和分歧。
不难看出,仅仅一个历史名词,因文献缺失,后人便纷纭附说,莫衷一是。所谓“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而从《索隐》《正义》《广川画跋》所记载的对“九主”的注解来看,都有一个共同而明显的错误,假设《殷本纪》确以“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为伊尹与汤所言,则如何会出现秦孝公、始皇、髙祖、汉元、成、燕王哙、汉宣、楚戊、吴濞、春秋寄公、孟轲谓之寄君、智伯之类、周成王、汉昭、平等后于伊尹与汤之人?即使承认司马迁是以“战国人语”“采择不精”,也不会出现战国之后人。同时,司马迁与刘向所见应为同一文献,则“九主”中不应该有晚于司马迁之汉代君主;尤其《索隐》《正义》《广川画跋》注解“九主”中有汉宣、元、成、平帝,按:刘向历汉宣、元、成三朝,约卒于哀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且不论刘向所见“九主”之记载不当有宣、元、成、哀帝,更不可能出现刘向卒后的汉平帝,从《别录》的记录成书上来说,也不合史实。
出现此种状况,究其原因,皆因去古久远和史料缺失,“文献不足故也”,这给后人预留了解说空间,及注解者未加详审的发挥。那么,司马迁与刘向所见记载“九主”的文献及“九主之事”到底指什么?其中又涉及哪些相关问题?
从司马迁来看,《殷本纪》载言伊尹与商汤论说“素王及九主之事”,显然是将其作为历史传说来看待。不论是否史实或后来的注说者如何解读,从《史记》的时代来说,这一传说本身反映了在西汉初中期,“九主”是一件值得关注和讨论的事情。
二、马王堆帛书《九主》的内容
值得庆幸的是,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使九主传说的具体内涵得以明朗。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四种的第二篇,原无篇题,整理者据其内容,名之为《九主》。*关于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九主》的命名,先此在这里称为《九主》,关于其名称,还将涉及该篇帛书佚文与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所载之《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类所在之《伊尹说》二十七篇,及其与《殷本纪》《别录》的关系,本文放在后文进行论述。这是一篇佚文,其内容为伊尹向汤王论述九主之事。帛书《九主》的成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其抄写年代大约在秦末至汉高祖时期。*此篇文献的成书、传抄,与战国秦汉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发展相适应,与汉初统治者提倡和运用道家黄老思想有很大关系,其出土与楚地汉墓与汉代楚地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可参见李学勤:《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文物》1974年第2期;《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修改版),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魏启鹏:《前黄老形名之学的珍贵佚篇——读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余明光《帛书〈伊尹·九主〉与黄老之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帛书〈伊尹·九主〉与古代思想》,《文献》1993年第3期。孙燕红:《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九主〉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年代早于《史记》,应该是史料来源。帛书《九主》篇是一篇内容完整、思想表述集中的文献。开首即交待了叙述的缘起:
汤用伊尹,既放夏桀以君天,伊尹为三公,天下大(太)平。汤乃自吾(御),吾(五)至伊尹,乃是亓(其)能。(以上352行)吾(五)达伊伊尹,伊尹见之,□□于汤曰。
所以,通过对比帛书《九主》与《殷本纪》所载的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可知《殷本纪》此说当即来自帛书《九主》的内容,帛书对“九主”有较为明确的论述,可以补正历史记载的差误,《九主》云:
其中的“剸(专)授之君一,劳〔君一,半〕君一,寄〔主〕一,破邦之主二,烕(灭)社之主二,凡与法君为九主”,正是“九主”,此乃九主的名称。《殷本纪》及《别录》提到的九主,当来源于此,正如李学勤所云:“帛书所谓‘九主成图’,正与‘九主者,……图画其形’一致。这充分说明,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和成帝时的刘向,都是读过今天我们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的这篇文字的。”*李学勤:《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文物》1974年第2期。同文修改版见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这为我们了解《殷本纪》的“九主之事”提供了明确的资料。《九主》开篇即指出伊尹总结了八位不好的君主,即剸(专)授之君一,劳君一,半君一,寄主一,破邦之主二,烕(灭)社之主二,加上法君,就是九主,其重点却是在申明法君法臣这一对符合政治理想的君臣。《九主》一文逻辑清晰,叙述明确,有冠有靴,中间分别论述法君和八啇,用以阐述九主命名的原因和他们的具体特征,旨在抒发作者的思想理念。
现存“九主图”残存有两个“烕社之主”和两个“破国之主”的图像和文字题记,其中两幅“烕社之主”图像和题记比较清楚;两幅“破国之主”图像残缺比较严重,题记不够完整。而《九主》中的“剸授之君”、“劳君”、“半君”、“寄主”题记和图像均已残缺不见。*此据陈松长:《简帛研究文稿》,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彩页五。另外,“九主图”残片和《九主》篇存在某些不同之处,最明显的是两者的抄写字体不一致和帛图文字题记的避讳问题,反映出在抄写年代上,“九主图”残片略晚于《九主》篇。但是从内容来看,“九主图”无疑与《九主》篇有很大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值得探究的。不过,图文相证,以图佐文,也有其局限,如九主图的绘画年代晚于《九主》文,仅有简单的图绘,没有详细的解图说明,我们仅能看出九主的文章和图画有相应关联,却不知如何指点图画来解说九主。所以对“九主之事”的分析还是需要以文为主。
根据帛书《九主》,可知“九主”是由法君和“八啇”构成的,他们是一种理想君主(法君)、八类谪恶君主(八啇):
法君者,法天地(以上358行)之则者。
剸(专)授失道之君也,故得乎人,非得人者也;作人邦,非用者(以上第383行)也,用乎人者也。
劳君者(以上第385行)剸(专)授之能吾(悟)者〔也〕,□吾(悟)于剸(专)授主者也。能吾(悟)不能反道,自为亓(其)邦者,主劳臣(以上第386行)失(佚)。

半君者剸(专)授而〔不吾(悟)〕者也。……是故〔臣〕获邦之〔半〕,(以上第395行)主亦获亓(其)半。
寄主者半君之不吾(悟)者。……则主寄矣。

“九主”之名和九主之事,结合“九主图”上的残存文字可以更好地做出解释和探讨。下面笔者试为之解读。
《九主》篇以论述法君、法臣和八啇为主题,分别对“法君”、“法臣”、“八啇”作出专门论述。以天道为法则对君臣关系提出的理想准则,文中以“主法天,佐法地,辅臣法四时,民法万物”来对“法君”、“法臣”做出描述和赞扬。以“法君”之“法天”,法君、法臣之“法则明分”为准绳,指出“八啇变过之所道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主不法则”为臣下所“得(控制)”。在总括论述“八啇”产生的根本原因之后,再次以法君、法臣的君臣关系为准绳分论“八啇”产生之原因及其命名之由来,从主之过、臣之罪、臣主同罪三个方面阐释了“八啇”是属于不同原因导致的不同类型的君主,又将之分为对“剸授”之“能悟”和“不悟”两个不同的系统,“剸授不悟”与“剸授能悟”的程度不同,危害亦有所不同,但其最终极端都是“亡国”。但这样做的原因始终在于强调君主要法天则、明分职,做到君臣各守其职,君主既要集中权力控制臣下,又要任臣专事,实现君操其名,臣效其实的政治统治。
在重点论述九品君主之时,以法君和法臣为例强调了合理的君臣关系。一以法则为准,“主法天,佐法地,輔臣法四時,民法萬物,此胃法則”,君臣民各有分度,讲究的是平衡,君主不可过度苛责也不能无所事事一任于臣。法君要法天地之则,顺应天地四时,不随意指手画脚,执守法度;法臣辅佐君主,各当其职,佐主无声,不凌驾于君主之上。君臣各有分守,君主执符以听,按照法则分度来管理臣下,则君明臣贤。
要言之,九主就是法君和八啇:法君,即遵循天地之则的君主,乃黄老家理想中的明君,遵道守法顺应自然。与法君对应必须贬斥防戒的是八谪,君不明则臣不贤,国家最终破灭。“剸授之君”是由于君主对剸授任下不觉悟(“剸授之君”的“过”)以及“剸授之臣”乘君主的剸授不悟而擅主(“剸授之臣”的“罪”)导致产生的。也因为君主的专授不悟和臣的剸授擅主,所以称之为“剸授之君”。
“劳君”因为看到了“剸授之君”剸授不悟的危害而对剸授有所觉悟,但对剸授有所觉悟,却不能返归臣主“法则明分”的君主之道,事事亲劳,致使主劳臣佚,仍免不了国家的危亡,所以称之为“劳君”。
“半君”因为对剸授任下不觉悟,半君之臣就利用君主的不觉悟,对群臣严刑杀戮,群臣恐惧,归从于擅主之臣,擅主之臣比周成党,与君主分享国家权力,臣主各得国家权力的一半,导致臣专横而主危殆,国家危亡。主要是半君之臣的罪过导致了半君的产生。这种君主因为其臣与之半分邦国,所以被称为“半君”。
“寄主”对剸授的危害比半君还不觉悟,他的臣下利用君主的剸授不悟,国家治乱不遵循法度而被擅主之臣控制,重臣掌握生杀之柄,就会导致君主失去权势而依托于大臣,成为“寄主”(《九主》对“寄主”的论述,原文残缺比较严重,此据《管子·明法解》:“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作出补充解释)。
“烕社之主”能够认识到剸授的危害,于是严法威势控制臣下,群臣只能事事听从于君主,因为君主的专暴而恐惧不能尽职尽忠,君主暴虐无道视臣民如仇雠,臣民无处申诉,就会共谋一致对付君主,王君利用这一点,对其进行征伐,其邦国被攻破。这种君主被称为“烕社之主”,导致其产生的原因是君主的专暴。这样的君主有不同的两位。
“破邦之主”是由于这种君主对剸授不觉悟,君主与重臣共同掌控君主的权术,欺压下民,百姓对君主绝望,归依大臣,王君乘机攻破其国家,使之邦国破灭,这种君主被称为“破邦之主”。“破邦之主”也有不同的两位,导致其产生的原因是君主和臣下共同的罪过(即“臣主同术为一,以策于民”)。
总之,《九主》对法君和八啇(谪)的评判标准以道法为标准,法天地之则,以清要为正,直接表达了作者的作文意图。
三、九主传说中的黄老道家理想
因为帛书《九主》的内容是伊尹与汤论说“九主之事”,这关系到该篇文献的分类和思想归属。李学勤等人根据《九主》的思想为道家黄老刑名之学,依《汉志》对《伊尹》的分类,将之归于道家之言。陈奇猷在《吕氏春秋·先己》校释中也认为《伊尹·九主》应归之于道家伊尹学派。其后主张称该篇帛书为《伊尹·九主》的学者亦多从此说。*陈奇猷在《吕氏春秋·先己》校释中认为“《伊尹》书虽佚已久,得此篇存,亦可窥伊尹学派之梗概。《伊尹》书未必即为伊尹所作,但观上所论,先秦道家者流中确有伊尹学派甚明。然以其学不着,故先秦书中未有道及此一学派者。今《吕氏》此篇,对于研究先秦百家争鸣者提供极有价值之数据也。”(北京: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吕氏春秋·本味》校释:“《汉书·艺文志》道家着录《伊尹》五十一篇,而于小说家又着录《伊尹说》二十七篇,是先秦有两伊尹学派,一属道家,一属小说家。”(《吕氏春秋校释》,第742页)。李学勤等人认为《九主》是《汉志》所载《伊尹》五十一篇的佚篇,称之为《伊尹·九主》也是认为该篇与伊尹学术有关。此外,关于伊尹学术的研究,还可参见骆啸声《论伊尹》,《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日]三条彰久《〈吕氏春秋〉と伊尹说话》,《中国古代史研究》第六辑,研文出版社1989年版。夏毅榕《伊尹及其学术源流初探》,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
伊尹确有此人,现在已经被证明为史实,但伊尹是否有独特的学说思想主张,并使得战国诸子中有人可以围绕或依托他而形成伊尹学派或伊尹学术,却是有待辨别、值得商榷的问题,而本文认为,从帛书《九主》的内容为汤和伊尹问对君臣关系和诸侯的存亡得失,以及它所反映的思想来看,该篇文献确系依托伊尹为说,但是否可以称帛书《九主》为“伊尹学派”的作品,恐怕还有待商榷。《九主》与《五行》《明君》《德圣》抄写在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同处一卷,属于道家黄老类。所以,《九主》叙述的“九主之事”其实是以黄老思想为准则,论说明君与昏君的差异,传达作者崇尚道法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的情形相符合。
《九主》篇肯定法君法臣,否定其它八主,反映了重道法刑名的思想倾向。其思想是典型的道家黄老思想,它以天道和自然法则来论述君主的为君之道和君臣关系以及社会和政治秩序,其集中的要点是要求权力的集中,即国家权势集于君主一人。在此前提下,主张君主的“无为而治”,君主对臣下循名责实,控制臣下。主要表现在对分和名的重视上,通过对道法、刑名思想的阐述,来表达君主执一无为的政治思想主张。《九主》篇的思想与《管子》、帛书《黄帝四经》以及《韩非子》中的许多内容非常接近。在内容和结构上与《管子·七臣七主》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思想上与《明法》《明法解》颇多相合。*可参见李学勤:《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修改版),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日]浅野裕一:《古佚书〈伊尹九主〉の政治思想》,《岛大国文》第十二号,1983年。余明光:《帛书〈伊尹·九主〉与黄老之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日]浅野裕一:《〈伊尹九主〉の道法思想》,《黄老道の成立と展开》,创文社1992年版。连劭名:《帛书〈伊尹·九主〉与古代思想》,《文献》1993年第3期。[日]渡边贤:《〈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九主篇〉译注》,《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创刊号,1997年。魏启鹏:《〈伊尹·九主〉笺证》,《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九主》篇与“九主图”图论结合的论述方式,以及它所运用的用数字将政治归类,为现实政治提供直接指导的思维方式,这一表述方式和思想特点,在先秦思想中比较重要,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政治特征,而其本身就是汉初黄老思想的反映。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有《伊尹》五十一篇(班固自注云:汤相);小说家类有《伊尹说》二十七篇(班固自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自然,无论是《伊尹》(后代人又往往称之为《伊尹书》)还是《伊尹说》,都不可能是伊尹所作,而是托伊尹之名。帛书《九主》与《殷本纪》采用的“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同出一源。《九主》抄录在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并未单独一卷,一是因为篇幅较短,二则与《老子》同属道家文献,从内容上看,可能属于《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伊尹》五十一篇之一。或如李学勤所言:“值得注意的是,《殷本纪》所述有一些内容不见于帛书,又非来自其它文献,如伊尹为处士,汤聘迎伊尹,五返而后从汤,以及伊尹言素王之事。显然,现在我们在帛书中看到的,不过是本纪所依据的古籍中的一篇,同书还有其它篇章,有待于未来的发现。”*李学勤:《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
综上,因地下材料马王堆汉墓帛书《九主》的出土,使我们不必因文献缺失造成无知和推测附会,得以了解《史记·殷本纪》载录“九主之事”的详细内容,知晓汉初政治背景下,《九主》这样的反映黄老之言的文本颇受推崇,随着大势所趋之下的学术思想与统治意识的争论和选择,此类书文渐趋泯灭。值得庆幸的是地不藏宝,越来越多的地下文献和一手的考古资料重新面世,成为当今世人最为珍贵和难得的文化遗产,使今人能够有条件将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相佐证,凭此便利,今人反而可以超越诸多古人,比古人看得更清楚,从而可以校正传世文献记载之缺失衍误,或更加详尽的探论文本内容和意涵,或直接从一手资料本身着眼再现鲜活的历史情景。
[责任编辑]刘晓春
孙燕红(1980-),女,山东淄博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K890
A
1674-0890(2017)03-1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