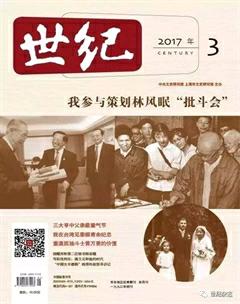我在台湾访辜振甫余纪忠
周瑞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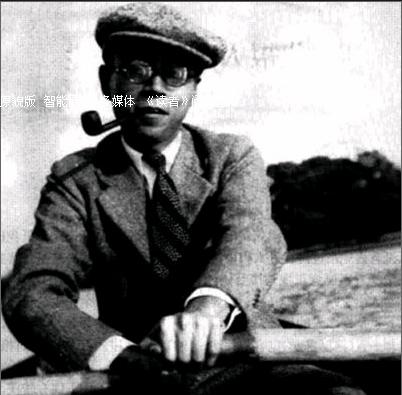

辜振甫:台湾儒雅精明实业家
两岸对话协商开启人
我与辜振甫先生素昧平生,我是在1993年到人民日报社履新后,从新加坡第一次“汪辜会谈”的新闻报道中认识了他。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以推动两岸关系走向和平统一,作为两岸协商对话的开启人,而青史留名。
新加坡“汪辜会谈”后,由于李登辉访美搅局和陈水扁当选“总统”鼓吹台独,两岸关系停滞了五年多。直到1998年初,汪道涵先生审时度势,主动出招,让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2月24日、3月11日、3月26日分别三度致函台湾海基会,热诚邀请辜振甫先生率团前来祖国大陆访问。经过两会副秘书长级、秘书长级负责人在北京、台北的多次磋商准备,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先生率领海基会参访团终于在海内外的关注之下抵达上海,开启了有历史意义的新一轮“汪辜会晤”。
辜振甫夫妇抵沪的第二天,汪道涵携夫人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茶憩”。当时,汪、辜两位老者神清气朗,一边品茗,一边交谈,相谈甚欢,不时地用手势加强语气。而两位夫人则轻依着茶几,悄声话着家常。 在汪辜两次会晤后,双方达成了两会要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对话,汪道涵会长在适当时候应邀赴台访问等四项共识。接着,辜振甫夫妇去北京,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記江泽民,江总书记对两会达成的四项共识表示赞赏,并就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发表了意见,也坦诚地听取了辜振甫先生的意见。
就在这样的两岸关系发展新背景下,我率领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一行五人,于1998年10月27日启程访台,适值辜振甫先生成功参访大陆返台一周之后。
这次邀请我们代表团访台的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汪万里社长按我们要求作了精心的安排。很有幸,我们到达台湾的翌日,即10月28日上午,辜振甫先生就在台北市锦州街口的造型秀丽的台泥大厦,在自己平时工作的宽敞办公室,亲切地会晤了我们代表团一行。
辜振甫先生的办公桌上有块铜牌,上面刻着美国总统里根的一句名言:“You can accomplish much if you don't care who gets the credit.Renoald Reagan 1972”。辜振甫先生把它翻译为:“不居功,成就会更大。”于是,“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就成了他人生的一条座右铭。辜先生一向主张“鸭子”哲学,认为一切有成就的大企业家、大商人,都应当像鸭子那样“脚在浮水,却不外露”,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做事,而不显山不露水。由是,辜振甫先生在台湾工商界赢得甚佳口碑,并缔造了一流的政商关系。无论在蒋介石时代还是蒋经国时代,抑或是李登辉时代,辜振甫家族都立于不败之地,在经济贸易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成为台湾一代既精明又儒雅的著名实业家。1998年他名列台湾百大富豪第11位,1981年出任国民党中常委,1991年被委任为“总统府资政”。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经常衔命为台湾周旋于国际谈判桌之间,因此获得“专业经贸大使”的美誉。1990年11月海基会成立,他成为董事长的不二人选。
那天我们就在奉行“鸭子哲学”的辜先生办公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无拘束的交谈。一开头他十分感慨地谈大陆之行与汪老会晤的感受。他说:“我有五十五年未到北京,五十三年未到上海,再到大陆我有惊世之感,和以前的情况不能比。大陆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成功的景象,令我印象深刻。这次与汪老会晤是在两岸关系的冰冻很久后举行的,显示了两岸以协商代替对立时代的来临。我看,两岸只要多接触,以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子来的。”辜先生说这次大陆行,与江泽民和汪道涵先生见面聊天情景,颇为感奋欢愉。他特别说到在台湾“立法院”报告大陆行时,有三位立法议员高兴得唱京戏,还有人给他献花,这在“立法院”是前所未有的。他还说“行政院长”萧万长急于了解大陆情况,在他返回台湾第二天,就特请辜先生共进晚餐,详尽听取大陆行的情况报告。台湾政界人士大都正面看待四点共识,各部门也都着手作出规划,推动两岸关系。
我在访谈一开始,就转达了汪道涵会长对他的诚挚问候!辜先生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这次我们会晤获致四点共识,江泽民先生完全赞同,也说了让双方受到鼓励的话。我很受鼓舞,这是很好的开始。照此方向走,彼此会拉得更近,大陆和台湾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我了解辜振甫先生祖籍在福建闽南,就说与他还有乡亲之谊。我的祖上也是福建惠安、同安那一带人,清初迁到浙南温州地区,至今我的一家都还讲闽南话。到台湾听到乡音有“回乡”之感。
听我谈起乡谊,辜先生说他与大陆的关系很复杂很深厚,盛宣怀的女婿是他的舅舅,沈葆桢的媳妇是他的姨妈,辜鸿铭是他的堂伯父。
在谈到辜老很喜欢京剧,与汪道涵先生有共同的爱好时,辜先生说自己的京戏老师是已故世的孟小冬,人称“京剧冬皇”。现在她的门生只剩下两人,另一位是九十多岁的老先生了。他说喜欢京戏是源自父亲是戏迷,父亲告诉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唱戏、看戏会了解中国人的历史和为人之道。正如汪道涵先生说,京剧是迷人的,一迷上就忘不了。
在谈及两岸协商中断了好几年,如何以这次“汪辜会晤”为新起点推进两岸关系时,辜振甫先生说,在进行政治谈判前的程序性协商时,要关注与人民权益有关的事务的处理。到目前为止,台湾已有1200万人次到大陆,台商有百亿元的投资在大陆,有30万台商在大陆做事,有8万至9万人结成夫妻。这当中当然有问题产生,但是不要因为个案的发生而伤了两岸的感情。双方在谈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政治性障碍问题,那就可以拿出政治性障碍来谈,不偏废。这样可以取信于民,老百姓觉得我们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此两岸民间关系会拉得近些,也可建立长远的关系。
他进一步说,两岸问题不是国际关系,不需要国际见证,关键是彼此要相信。他向来主张不要回避任何问题。大家多沟通,中国有句古话,“见面三分情”,多见见是有益的。没有什么话,就是“今天天气如何”也好。不见面就会有误会。隔海放话,有时越放越糟,误会加深,产生误判。
接过辜老话题,我问他对未来落实四点共识有何高见?他说台湾方面是希望走得快些。这个月26日全国青联邀请台湾一个青年访问团访问大陆,后面有台湾言论界、司法界人士组织的访问团到北京,研讨共同打击犯罪问题,还有渔业纠纷问题。两岸要加强各阶层的交流,不要为一些琐碎的事伤害大局。台湾现在已开始规划汪道涵先生来访事宜,在汪来以前,唐树备、张金成会先来,预先沟通辜汪再次会晤的议题。作为辜汪第二次会晤也可以,作为参访也可以,两岸之间的参访也是很有用的,两会董事长见面对两岸、两会关系发展有指标性意义。对汪先生到台湾访问,还有一点时间好好规划。两岸的事不能太着急,因为两岸隔绝多年,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政治、社会体制,今后交流多一些,彼此的了解会增加很快,在这一基础上发展,两岸一定会越走越近。
我接着向他请教这次会晤双方主要的分歧是什么?辜先生直言不讳地说,国际空间问题,这是台湾人最伤心的了。台湾人个个有独立奋斗的性格,现在可以当家作主了,都希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与大陆人民一起创造中华文明,这个心愿是存在的。二次大战后,一些殖民地纷纷独立,台湾没有独立。要承认这个分治状况,现在台湾与大陆没有统一是前提,要在没有统一的前提下谈统一。在国际外交上不要打压,台湾没有一定的国际空间,有些人是会豁出去的。两岸文化相同,很多事情一点就通。对发展国际空间的对峙状态,我认为这中间不要刻意去讲,要为台湾留一点空间,特别是政府发言人在发表谈话时要注意,犯不着刺激台湾。当然,你们不刻意去讲,这边也不要太过敏。这种事大家要相互体贴些比较好。我这次与江泽民先生、钱其琛先生聊得很好,很有帮助。
谈到这里,辜老先生感慨地说,我这一辈的人在有生之年也许看不到两岸统一了。今年我已83岁,所剩时间不多。我的经历很复杂,从日本占领到现在,我想为年轻人留下一些东西,趁糊涂之前写点书,有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多。我这个年龄已经无所求,只想为两岸统一贡献一点力量,希望两岸统一快一点。这是他真情的流露。
最后,辜老先生谈到,这次参访大陆的唯一遗憾,是没有与朱镕基先生见面聊天。亚洲金融风暴还没有停止,他很想跟朱总理谈谈金融问题,还有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希望下次去有机会与他见面谈话。
一个多小时的愉快交谈很快过去了。在即将告别时,辜振甫先生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热情握手,并在他办公室亲切合影留念。据后来“中央社”记者说,这是辜老先生晚年与大陆来访代表团,最轻松自如的一次畅谈,也是他生前少有的对两岸关系充满乐观期待的一次交谈。
遗憾的是,不久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使他在台湾与汪道涵先生再度会见的愿望破灭了。设身处地想想,辜老先生当时是什么心情,可想而知。辜先生一直认同“一个中国”,使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对话有了基础,并借此促成“九二共识”“汪辜会谈”和“汪辜会晤”。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可惜,他多年倾注的心血,却被两位同是祖籍福建的麻烦制造者李登辉、陈水扁,或明或暗地给“蒸发”了。因此,垂暮之年的辜振甫常怀遗恨,并积郁成疾,在2000年赴美做肾脏手术。在美国治病期间,他仍然放不下被陈水扁随意操弄越弄越僵的两岸关系,50年没再作诗的他感于时局,特地吟咏《落叶三题》诗以抒发心情,并赠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病中的辜振甫先生,每天早上一定要看台北传来的报纸,看台湾的电视新闻,了解台湾的局势。有次,他叫妻子搀扶,看看外面有没有喜鹊,有没有喜鹊带来的喜讯。这是辜老先生晚年,期待与失望相交织的何等复杂而悲怆的心情!
2005年1月3日,88岁的辜振甫先生与世长辞。当天,汪道涵先生给辜振甫先生的夫人辜严倬云女士发去唁电,对辜先生逝世深表哀悼:“ 惊悉振甫先生遽归道山,哲人其萎,增我悲思。 振甫先生致力于两岸关系凡一十四年,夙慕屈平词赋,常怀国家统一,私志公义,每与道涵相契。汪辜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而今风飒木萧,青史零落,沪上之晤,竟成永诀。天若有情,亦有憾焉。 两岸之道,唯和与合,势之所趋,事之必至。期我同胞,终能秉持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之谛,续写协商与对话新页。庶几可告慰先生也。”
接着,辜严倬云女士致信汪道涵先生,诚邀他赴台北参加辜振甫先生的追思会。2005年1月30日,90岁的汪道涵先生发表谈话,他将委托个人代表前往辜振甫先生的灵堂吊唁,并向辜严倬云女士转交亲笔信,称“唯道涵髦年,杖履不便,未克亲赴为憾。今特托亚夫、亚飞二君执礼代行,以申我悃。老友永逝,精神长存。云海遥念,思绪无限”。
2005年5月2日,汪道涵先生会见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祝愿连战主席“和平之旅”成功,连战主席當场将辜振甫先生生前来不及送给汪先生的自己画作《纱帽山俯瞰》,郑重地赠送给汪先生。
历史常给人以“万事天定,人生如寄”的感慨。两岸闻名遐迩的“汪辜会谈”,两位主角、好友、会谈伙伴,谁也料不到,一个在年头(2005年1月3日),一个在年尾(2005年12月24日),相继驾鹤西行。两位老先生一为儒宦,一为儒商,共同酷爱中华文化,同样学贯中西、儒雅倜傥,如此紧密相随,也许他们可以在天上相逢神聊,但在人间已成绝响!
余纪忠:台湾新闻报坛一巨擘
两岸统一模式倡言人
1998年10月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遍访了台北主要报社,10月30日下午来到中国时报社,与报社骨干编辑记者座谈,我单独拜会中国时报新闻集团余纪忠董事长,那一幕情景和感怀留给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与余先生是神交多年的新闻报界同行。上世纪80年代中期,解放日报社订有台港澳的主要报纸,我每天浏览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和香港的《信报》《明报》。我通过《中国时报》的社评对余纪忠先生爱国情怀早有所了解。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又有幸与余老先生有过一段相互切磋两报合作办杂志的难忘交往。
余老先生是台湾最大的民营报纸《中国时报》创办人。他一生充满瑰丽而传奇的色彩。1932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历史系毕业,193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余先生当即义无反顾中断学业,由英伦兼程返国投笔从戎,投入全面抗日战争。抗战胜利时,他担任青年军某师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等职务。1949年他举家迁居台湾,1950年在台北创办了《征信新闻》,1968年印刷出全亚洲第一份彩色报纸,为全球华文报纸开启了彩印报纸的时代。从此《征信新闻》改名为《中国时报》,余先生明确提出《中国时报》的办报理念是“政治民主、民族认同、稳定大局”,并以“开明、理性、求进步;自由、民主、爱国家”作为办报宗旨。《中国时报》对台湾和国际某些重要问题的评论、报道深受岛内朝野重视,发行量不断扩大,上世纪70年代末便突破日发行100万份。1975年又决定走出台湾到美国办报,9月《美洲中国时报》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地正式发行,深受北美的华侨华人欢迎。
余先生倾心新闻事业,大力发展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群,开创了中国时报新闻集团。旗下《时报周刊》《时报杂志》《工商时报》《中时晚报》等相继创办;又从报纸、杂志,发展到出版业、影视业、旅游业及文化产业等。尤其《中国时报》的言论风格从一开始就富有自由民主色彩。余先生有意识借助报纸影响力促进岛内政治革新,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上经常新意迭出。台湾很多学者、政坛人士及企业家都习惯把《中国时报》的社论作为岛内政治气候的风向标。1984年《美洲中国时报》在洛杉矶奥运会报道时,顶着“为匪作伥”的巨大压力,大幅报道大陆选手荣获十枚金牌的消息,引起岛内外舆论轰动,也遭到当局打压,曾一度被停刊。
我们到《中国时报》参访时,中时新闻集团已成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拥有报纸、杂志、出版社和互联网业务,旗下共有20多家公司,员工近万人。集团董事长余先生,成为台湾舆论界的巨擘,社会的风云人物,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
由于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新闻经验,余先生对政治、社会与文化动态十分敏锐。早在1992年秋,他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激起大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就敏锐判断推动两岸关系的有利时机到来。他主动派《中国时报》两位骨干编辑胡鸿仁和杜念中来上海,与我商谈合作办刊事宜。我先征求汪道涵先生的意见,得到他的首肯以后,又请示了市委主管的领导,然后派出解放日报社贾安坤、俞远明两位编委级的编辑,与之协商谈判,共同确定办刊宗旨为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社会的交流,每月一期,在两岸三地发行。《中国时报》与《解放日报》各自设立编辑部,由贾、俞、胡、杜四人小组决定每期刊登内容,分头组织稿件,最后由我和余纪忠先生共同审定,双方各具否决权,只有我们两人一致认同的稿件才能刊登。刊物在台北印刷,重点在大陆和台湾发行。出版、印刷、发行事务由四人小组负责裁定。贾安坤作为小组的牵头人,四人小组曾在解放日报社举行过四五次往复商谈。最后,我与余先生批准了四人小组提交的关于双方合作出版刊物的报告,确定了刊物名称为《太平洋经济评论》。四人小组很快就在1993年初合作出版了《太平洋经济评论》月刊的试刊号,印刷了几百本分别赠送台湾和大陆各界人士阅读,征求意见,获得各方好评。汪道涵先生也十分赞赏,两岸双方媒体都很高兴。遗憾的是,1993年4月中央發来调令,要我到人民日报社履任新职。我把此事移交给报社另一位负责人,虽然双方也进一步商谈了几次,终无进展,后胎死腹中。
因为有以上的交往背景,1998年10月30日当我率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到《中国时报》参观访问时,余先生与我相见,虽是第一次面晤,却神交已久,像老朋友一样握手拥抱,亲切热烈,坦诚交谈。余先生时年88岁,身体健硕,精神矍铄,谈吐儒雅,侃侃而谈。他在大陆生活40个寒暑,在台湾度过近50个春秋,对两岸一直存有深厚的感情。
在与他单独交谈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对两岸局势清晰的分析,坚定主张两岸统一的立场,令人叹服。但对如何实现两岸统一的路径,他并不赞成简单的“一国两制”说法。他开诚布公对我阐述了自己经过长期缜密思考提出的独立见解。他说,鉴于台湾与香港的政治地位不同,要承认中华民国客观存在这个现实,先走中华邦联的道路,然后与香港、澳门一起组成大中华联邦,实现真正的中华民族大统一。谈到兴起,他竟拉着我的手离开报社办公室,带我到他家的大书房,亲切而坦诚地向我出示了1995年台海两岸局势紧张时,他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互相交换信函、商议对策的亲笔函件,还向我讲述了国民党连战主席当时到他书房交换意见的经过。他说,他倡言的“中华邦联”的两岸统一模式,得到了连战先生的赞同,也得到李光耀总理的赏识。
在谈到运筹《中国时报》新闻集团的成功经验时,余先生说了一段老报人的话,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报纸一定要有自己观察新闻事件的视角,要有独立发声的勇气,关键时刻不能成为缄口金人。如果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是我们报人的失职,也就不得不为国事前途慨叹了!”当时,我一瞥余老先生的书房,墙上挂着名家书赠的一副对联:“高论明秋水,贞心比古松”,这确是他的人品、文品、报品的真实写照啊!
那天《中国时报》同仁们盛情炙人,晚宴上双方都开怀畅饮,喝掉好几瓶“金门特高”。晚宴后黄肇松社长陪同我们参观报社,我们在夜班编辑部的一张大办公桌前停了下来。黄社长介绍说,这是中国时报新闻集团董事长余纪忠老先生的办公桌。我当场惊讶地问,他老人家已88岁高龄,晚上还来值夜班吗?黄社长点头肯定说,他一般晚上9时半来这里看当天要闻和审改社论。他一直主持报社社论委员会,定期确定社论选题,并审定社论,有时还亲自执笔起草涉及两岸关系的重要社论。听了介绍,我伫立余老先生值夜班的办公桌前,沉思良久,心潮澎湃。
这种把生命与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老报人敬业精神,确实令人感动。我绝对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如此高龄还能坚持上夜班,主笔政。当时我脑海里很快闪现着:大陆有哪位报业集团的董事长还上夜班主笔政?大陆全国知名的报纸哪还有年过八十的老总仍在为国家与新闻传媒的大政操劳?由此我产生一个“余纪忠情结”:职务可以到龄,责任没有年龄限制;官可以不当,文章不可不写。即使退休了,也应当以余老先生为榜样,继续挥笔谠论国是。因此,2004年我退休以来,正是这个“余纪忠情结”,让我这10多年笔耕不缀,不断为改革开放呐喊和鼓呼。
我们新闻代表团返回北京后,曾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六篇访台新闻报道,并向中央有关领导送呈访台总结报告。我在报告中突出了余先生为化解台海两岸僵局,提出“中华邦联”架构的倡言。翌年5月,余先生重返大陆故乡途中,在上海受到汪道涵先生热情接待,并在汪先生邀请下到达北京,于5月1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江泽民主席亲切会见,两人畅谈了110分钟。余先生向江主席详细阐述了两岸统一的“中华邦联”模式,江泽民主席认真听取后,对余先生说:“今天碰面,我们难得有这一番畅谈!”
2000年9月,《中国时报》创办50周年前夕,余先生亲撰长文,呼吁台湾当局痛下决心,与主张“两国论”者划清界线,强调中华民族不能分离,矛头无畏直指李登辉。2001年10月,余先生和夫人捐资150万美元建造的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教学实验大楼“玉辉楼”落成启用。此前,余先生曾捐资743万美元设立“华英文教基金会”,专门资助母校南京大学提升学术水平。
2002年4月9日余纪忠老先生在台北逝世,享年93岁。《中国时报》在题为《一代报人的典型、一世理念的坚持》的社论中说,余先生由于他亲历战祸频仍、黎民生离死别的沧桑悲剧,“不愿再见到两岸同胞兵戎相见”,因而余先生晚年一直殚思竭虑,为两岸如何迈向和平的进程“寻找模式与出路”。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将学校一栋基础实验大楼命名为“纪忠楼”,2012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校史馆又为余纪忠先生设立永久陈列特展。
我于4月12日给余老先生长子余建新(2001年他从余老先生手中接过中时新闻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发去唁电表示深切哀悼:“余老先生青年时期爱国心炽,投笔从戎,返国抗日;中年时期呕心沥血,创办报业,中时业臻巅峰;晚年致力两岸和平统一,悉心斡旋,慷慨文章。其一生高论明秋水,贞心比古松,堪称报界巨擘、爱国耆宿。忆及九十年代初期余老先生勠力推动中国时报与解放日报合作,以及1998年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访台时余老先生同我促膝长谈,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无限感怀。先生虽逝,精神永在,事业永在,爱心永在。”
我的唁电被显著刊登在当时的《中国时报》上。
写于2017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