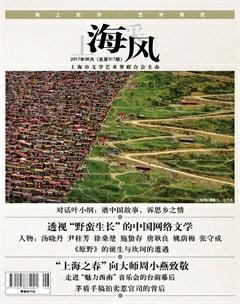向施蛰存约稿琐记
曹正文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入复刊的《新民晚报》,先当三年记者,后调入副刊执编“夜光杯”,1986年晚报扩版,我自告奋勇提出执编一个“读书乐”专刊,一编22年。由于独立执编,我有机会向不少活跃在民国文坛的学者作家约稿。现在这些民国文人已经仙逝,但至今回忆,那些访谈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奔涌,比如施蛰存先生。
壹
认识施蛰存先生,是在1985年参加上海出版社的一个会上,施老当时已80岁,四方脸,高鼻阔口,双目很有神采,只是耳有点背。后来,我执编“读书乐”,想约施老写一点自己读书的经验,便登门拜访。
施蛰存的寓所在愚园路上,他的书斋兼卧室沿窗靠马路,到处放着书,83岁的老人坐在一张大的写字台前。由于他听觉不太灵敏,施蛰存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我从他谈话中得知,他在前几年刚战胜了一次癌症,病愈后更加勤奋写作,除了研究碑帖,写《水经注碑录》,还写了一本《唐诗百话》。他说写《唐诗百话》只是他搞学术研究的一种消遣,他想到一个唐诗题目,便随手记下来,陆陆续续便积成了一本畅销书。施老说到这里,不由呵呵地笑了起来,八十开外的老人笑起来还宛如一个稚童。
我的访谈,先从施老年轻时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开始。施蛰存是民国文学中有影响的人物,他生于1905年12月3日,浙江杭州人。据他说,他在8岁时随家迁居松江,17岁考入杭州的之江大学,18岁到上海,转入上海大学,后来又在大同大学、震旦大学读书。施蛰存虽已年迈,但记忆力很强,他说起自己21岁读书时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创办了《璎珞》旬刊,三个月出一期,我便向施老询问:“璎珞是什么含义?”施蛰存淡淡一笑说:“我当时对印度佛教很感兴趣,璎珞是印度佛像脖子上的一种美丽装饰,璎珞的寓意是:无量光明,我们当时年轻人都向往光明,故以此作刊名。”
据施蛰存回忆,他大学毕业后,先在松江一所中学当教员,后来便去书店当编辑,并参加了《无轨列车》《新文艺》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任现代书局的两位老板洪雪帆与张静庐考虑出版一份不冒政治风险的纯文学杂志,经过多方寻觅,便选择了施蛰存,因施蛰存有过两年编杂志的经验,而且敢作敢为。
25岁的施蛰存开始独立主编《现代》,他说:“我编《现代》杂志,并不是编一本狭义的同人刊物,我的选稿标准不以个人好恶来评判稿件,只要有文学价值与独立见解的文章都可以刊登。当时批评过我的楼适夷先生,他的文章照样刊登在《现代》杂志上。”
据施蛰存先生回忆,《现代》杂志的作者队伍相当精锐,鲁迅、茅盾、巴金、周作人、老舍、戴望舒、郁达夫、郭沫若、周扬、沈从文、苏雪林……易嘉在1932年还发表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对胡秋原与苏汶等人的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施蛰存说:“当时争议与批评很热闹,我认为只要是一家之言,都可以杂志上发表,各种争鸣的声音都有。”
施蛰存希望《现代》的内容与题材杂一些,除了中国文学,他还刊登欧美与日本文学的译作,并设了一个“外国文学通信”的栏目,邀请在国外的留学生以写信形式刊登来稿。在上世纪30年代的杂志上,《现代》是最早刊登西方现代重要作家的刊物,施老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还有在世界文坛刚冒尖的海明威、福克纳也有作品在《现代》上刊登。
1935年施蛰存离开现代书局,与阿英合编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他从1937年起开始在多所大学任教,并于1952年调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教授。
贰
与施老的访谈,以后又进行过多次,一是他的寓所离我报社不远,一部20路电车可直达,二是施蛰存先生的经历很丰富,他在民国文坛影响很大,被当时文学界誉为“中国现代派文学鼻祖”“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但媒体对他的报道并不多,因此我对他的访谈,主要是请他谈自己的创作。
我记得,几次访谈都是在雨天的下午進行,笔者请施老谈谈怎么会从事文学创作。施蛰存喝了一口茶,回忆道:“我从事文学活动,主要受陈望道的影响,写小说则受西方文学流派的影响,我曾翻译过一些俄罗斯作家的文学作品与东欧文学作品,如《渔人》《波兰短篇小说集》《捷克短篇小说集》《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施蛰存说到这里,把手一摊笑道:“有人以为我的俄语很不错,其实我对俄语只略知一二,主要是借助于这些东欧小说的英译本与法泽本,我的英语与法语还不错。”
由于施蛰存在主编《现代》杂志时,要处理许多外国文学来稿,他也趁机读了不少西方文学丛书,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施蛰存影响很大。他开始试写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分析小说,小说中借鉴了意识流手法,塑造了二重乃至多重人格的人物,并有内心独白,这样施蛰存就被文坛冠上了“心理小说家”“新感觉派作家”与“文体作家”三个称号,他的代表作为《鸠摩罗什》《将军的头》《梅雨之夕》《石秀》《周夫人》。施蛰存往往用细腻婉约、温柔伤感的底色,并运用内心独白的形式,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内心的潜意识。
施老谈起他当时的创作,不胜感慨,他说他创作的心理小说,希望今后结集出版。后来,即1992年,他给我寄来一本《施蛰存心理小说》的签名本。
叁
施蛰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由于他学贯中西,外文与古文的底子都相当厚实,很受学生们尊敬。
据施蛰存回忆,他与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曾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友,姚文元在新中国成立后见到他时也恭恭敬敬叫一声“施伯伯”。
但1957年反右开始,姚文元突然对过去尊敬的施伯伯进行口诛笔伐,他在《文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驳施蛰存的谬论》,文中说“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射来的一支毒箭。”张春桥也在《解放日报》上刊发了《施蛰存的丑恶面目》。施蛰存谈起这些往事时,不屑一顾,他说:“张春桥当年曾投到我工作的上海杂志公司求职,我让他编辑一套古代珍本丛书,对《柳亭诗话》与《金瓶梅》作断句标点,由于张春桥的古文底子差,标点断句差错很多,我便将他除名了。也许他记着这点旧恨,对我乱加批判。不过,由于张春桥因这段事心虚,他批判我的文章,用的是笔名。”批判施蛰存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徐景贤也是一员猛将。
施蛰存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在“文革”中再次遭受冲击,据他的学生回忆,已逢花甲之年的施蛰存弯腰曲背站到批斗台上,他头上的帽子被打飞掉了,他捡起来,拍去灰尘,重新戴上,继续从容站在那里挨批斗。在没有批斗的日子里,有定力的施蛰存先生仍旧在资料室中做卡片,他在苦难的行列中终于熬到了“四人帮”下台,一些平反的右派摇身一变成了新贵,而施蛰存依然故我,住在愚园路那幢房子里,他与邻居家合用一个卫生间与厨房。他依旧很低调的生活,唯一快乐的是可以写文章发表了。
肆
与施蛰存成了忘年交,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他寓所拜访,一方面听他谈三四十年代的民国往事,另一方面学习他编辑的经验。施老对我的支持,是他在忙完大部头稿子之外,写些小文章支持我的“读书乐”,如《谈读书》《关于独幕剧》《我看心理小说》《海外学者怎样研究词》《什么是“汇校本”》《“自传体小说”及其灾难》《我说漫画》《钱钟书打官司》《一本出版的图书》,等等。由于他写的文章观点鲜明,思想解放,好几篇文章都要经过我几次与领导力争,才能刊出。由于被删去了一些段落,我上门很惭愧地向施老表示抱歉,他总是一笑了事说:“这很正常的,领导与你考虑的角度不一样。”
每年春节,我会向施蛰存等一些老人寄贺卡,祝这些民国文坛老人健康快乐,有意思的是,施老也向我这个晚辈寄贺卡,几乎每年春节我都能收到。我在1993年获上海市首届新闻韬奋奖,也收到了施老寄来的贺卡,这是我个人获奖后收到的唯一一张贺卡。
施蛰存先生晚年写作相当勤奋,他1987年出版了《唐诗百话》《词学论稿》,1989年出版了《金石丛话》,1992年出版了《枕戈录》,1997年出版了《卖糖书话》,1998年出版了《散文丙选》,1999年出版了《北山说艺录》,2000年出版了《云间语小录》,2001年了《北山散文集》《唐碑百选》,最后一部书稿出版时间是施蛰存先生过了90歲生日,这大概是民国文人最年长的出书者之一吧!施蛰存与同辈的文人相比,大他1岁的巴金,与他同岁的楼适夷,小他5岁的曹禺,他们在80岁后就没有新作了,只有施蛰存先生活到老,写到老。
施蛰存在生前,就被文化界喻有“北钱(钱钟书)南施(施蛰存)”之称,又有学者把他与陈寅恪相提并论,这位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与外国文学翻译上均有很高造诣、学贯中西的文学家,终于在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柯灵与王辛笛。这也是历经坎坷的施蛰存老人在新中国荣获的最高荣誉。翌日,我去拜访老人,他只是淡然一笑,对我说:“棉花还有弹性呢!”
原来,施蛰存曾请评委把这荣誉给予年轻的学者,他说他本人对生死已看得很淡,名利对他毫无用处,他说的“棉花”哲学,他曾这样解释:“棉花看来很柔软,但受到外部挤压,看来渺小无力,但一旦外部力量消除,棉花松弛,又恢复原貌,妙在弹性十足。”这段话,也许反映了施蛰存一生的际遇。
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这位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